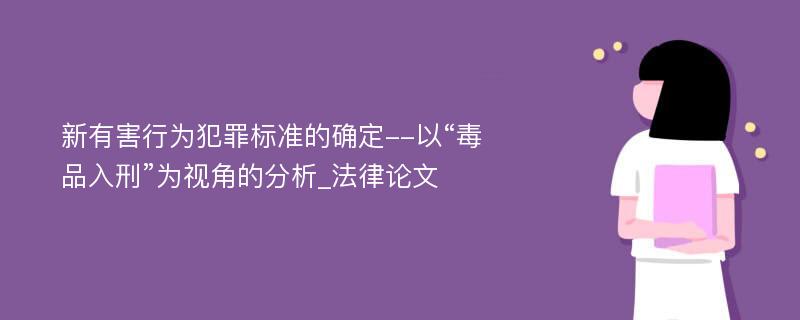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定——以质疑“毒驾入刑”为视角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标准论文,毒驾入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15/j.cnki.fxpl.2014.02.01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犯罪化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主流,不少新型危害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如恶意欠薪行为、醉酒驾驶行为等。谓之“新型危害行为”,是因其伴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而产生,它们不是立法的漏洞,而是历史变迁的产物。新型危害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是复合且多元的。就客观角度来看,一方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且快步渗入人们的生活,为众多采用新型技术手段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社会变迁使得一些过去不曾被关注到的轻微不良行为在质和量上出现恶化,从而上升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国民的主观意识来看,随着人们文化素质与法律观念的增强,其依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逐渐觉醒,创造出各种“新权利”来寻求法律的确认,这也促使了更多的新型危害行为被“挖掘”出来。
新型危害行为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正如人类的生命过程中难免遭遇病痛,对症下药即可,但目前我国对待新型危害行为的态度却呈现出一味依赖“刑事立法”这剂猛药的情形。一旦某种新型危害行为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谴责,群情激愤之下社会管理者就迅速以“入罪”的方式来安抚民心,屡试不爽的“推动立法”经验也使得媒体与网民习惯了“愤怒发声,呼吁入刑”。刑事立法呈现出这种民粹主义的趋势固然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丛生引发了民众的犯罪恐惧感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民众法治理念的缺失。在美国,大部分民众认为宁可放纵危害行为,也要谨慎行事以免无辜者受到处罚,使个人免遭被压抑的自由比减少犯罪更加重要。①而我国民众基于朴素的同情被害人心理和锄强扶弱的浪漫主义情怀,总是坚定地站在支持新型危害行为入罪的立场上,却极少考虑犯罪化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问题。民众对犯罪化的狂热需要长期的法治理念教育来引导,但立法者不能对法治失去耐心,“刑事法治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给予国家刑罚权,但又限制国家刑罚权的随意发动”。②新型危害行为固然侵害了社会利益,但“社会生活中的利益,无论是涉及个人、社会或国家的利益,并非全然为法律保护的客体,更非全数由刑法来加以保护……利益,须经审慎的评价后,方有可能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③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立法者应该以何种标准对一种新型危害行为“审慎评价”,继而判断其是否应当入罪?
二、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理论之思辨
关于犯罪圈的范围界定问题,往往要追溯到刑法规范之保护法益的目的。当一种新型危害行为侵害了法益或者造成侵害法益的危险时,就有了将其入罪的必要性。换言之,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的危害行为,便不存在讨论入罪问题的前提。但是,鉴于刑法在国家对公民权利的所有干涉中是最严厉的一种,因此“犯罪化,仅有必要性尚不够,还应具有立足于刑法的补充性、不完全性、宽容性即‘谦抑主义’精神的正当根据”。④因此,将法益作为刑事立法的界限,谦抑主义作为刑事立法的原理,二者结合即可确立刑事立法的边界。
这种德日刑法中主流的刑事可罚性理论在我国也具有普遍影响,但精妙的理论在指导刑事立法实践中却有些力不从心。由于“‘法益’的定义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成功而明确的说明,因而不能提供一个可以在法律上作为基础和在内容上令人满意的界限。”⑤一种行为是否达到了威胁或侵害法益的程度只能由立法者来判断,“立法者在做出决定时的裁量范围,比自己受到约束的范围要大的多”。⑥因此,法益作为刑事立法界限更多的是规范上的意义,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谦抑主义作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⑦具有根本指导性地位,“不仅关于刑法的解释、适用,关于立法,也应该考虑刑法的谦抑主义”。⑧但谦抑主义丰富的内涵同样只是在宏观层面给刑事立法奠定基本的立场,微观层面的入罪标准问题依然要在其指导之下作具体的探讨。
行为入罪的标准应当是具体且可操作的,美国刑法学者帕克在其《刑事制裁的界限》一书中为刑事制裁的最佳使用所设立的标准就是一种全面具体且颇具实用性的理论体系。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包涵六个条件,只有全部满足这些条件的危害行为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1)行为须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显著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不专属于任何意义的社会阶层;(2)将该行为纳入刑事制裁不会违背惩罚目的;(3)抑制该行为不会约束人们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4)须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处理;(5)通过刑事程序来控制该行为,不会使该程序面临严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负担;(6)没有合理的刑事制裁替代措施来处理该行为。⑨
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与帕克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入罪标准体系。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只有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被规定为犯罪:(1)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行为都是侵害或者威胁合法权益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并主张以刑法进行规制;(2)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代替刑法,只有动用刑法才能抑止这种行为,才能充分保护合法权益;(3)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不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4)对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能够进行客观的认定和公平的处理;(5)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符合刑事责任的目的,即具有预防或抑止该行为的效果。⑩还有学者认为刑罚制裁仅仅在下列情况下才是合理的:(1)从民意来看,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某一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国家与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国民情感与精神上均不能容忍这种行为;(2)从效果来看,以犯罪化来限制某一行为自由,符合刑事法律目的,并且不会因此而禁止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能够收到明显的抑止该行为的效果,可以预防行为人和其他人再度实施此种危害行为;(3)从效益来看,以犯罪化来限制某一行为自由,值得启动刑事诉讼程序;(4)从有无选择性来看,以犯罪化来规制某种行为必须是没有其他社会调整方法能有效控制和规范该种行为。(11)
上述三种具体的入罪标准理论在内容上有很大重合,实际上都暗合了德日刑法中法益理论与谦抑主义的内涵,其中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最为详尽。我国的两位学者在帕克理论之基础上作出取舍,张明楷教授与帕克的观点基本一致,但结合我国现实作出了更具体的分析,例如在第四个条件中要求“对犯罪行为尽量采取客观的记述规定,从而使司法人员能够客观地认定犯罪”,(12)强调了立法对司法的影响;谢望原教授则舍弃了帕克理论中“须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处理”这一条件,认为“对某一行为能否无区别地加以处理,与该行为应否作为犯罪来用刑罚加以禁止完全不是一回事”。(13)通常而言,刑事程序的公平性是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不关涉刑事立法之事,但是,由于对新型危害行为能否公平认定和处理经常要受到侦查、检测等技术手段不足的客观制约,这种情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的调整来实现程序公平,只能在刑事立法之时便未雨绸缪,以免仓促入罪造成各种理论争议和实践难题。因此,具体到新型危害行为的入罪标准确立时,还需仔细考察新型危害行为的特征对其入罪问题的影响。
新型危害行为因其“新型”二字,常常涉及新型的科技手段或新型的社会关系。公众对这种新型危害行为往往一知半解,也正是这种不甚了解使得公众更容易对这种行为产生恐慌,产生“生活中突增了额外风险”的焦虑;加之媒体热衷于追逐这些新型危害行为来获取关注,大量的聚焦与渲染将公众的焦虑又加深一层。此时一旦有个人或群体提出应将新型危害行为入罪的建议,便极易获得公众的附和。面对公众的呼吁,立法者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大局考虑,频频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新罪。刑法学界也出现了刑法应当对法益提前加以保护以回应“风险社会”、我国应当规定相当数量的轻罪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等推进犯罪化进程的观点。但这些新型危害行为入罪的支持者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迥异于传统犯罪的行为入罪后给刑法的具体实施造成的各种难题。鉴于上述情形,笔者认为关于新型危害行为的入罪标准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强调:
问题一: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是否需要达到“多数人”难以容忍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
帕克与我国两位学者的入罪标准理论中都强调了对某种行为入刑需要“多数人”难以容忍其社会危害性并主张以刑法对其进行规制。这个标准是“立法应当遵从民意”的一种具体表述。“一项法令的真正制定者,不是立法者个人,而是群体,立法者不过是这个群体的忠诚或不够忠诚的代言人而已”。(14)法律不是立法者个人的意愿,立法者只是代表社会群体来行事。但作为民意代表者的立法者在代表民意的同时必须善于分析真正的民意并对民意中的非理性层面进行引导。真正的民意需要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来获取,但我国立法者用来采集民意的几个渠道却非常不科学:(1)媒体反映出来的民意,但媒体有其立场和倾向,并不能代表人民;(2)网络上的意见,但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很少有社会底层人士和社会主流人士,无法代表全体人民的“民意”;(3)召开座谈会,但参与者多是由组织者精心挑选,不具有广泛代表性。(15)因此,通过这些方式取得的民意不能用来作为立法的参考,更不能作为论证某一行为是否应当入罪的社会基础。
即使面对真正的民意,立法者也不应一味盲从或附和。民意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其对立法的意见不可能绝对正确,法学领域的专家有责任以理性和专业知识向人民作出解释,以引导民意向正确的方向转变。(16)我国当前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型危害行为层出不穷,这些由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社会带来的风险使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而信息时代的媒体导向和网络为全部入刑,并认为刑罚是消除社会风险最有力的手段。但“暴力手段虽然是实现秩序和扩传播也使得这种焦虑变本加厉。感受到强烈威胁的国民本能地倾向于将新型危害行展秩序最直接的手段,但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17)刑罚本身作为一种“恶害”,必须是别无他法之下所为之选择。
民主立法要求立法摒弃神秘主义,让国民参与立法的过程,充分体现全体国民的意志和要求,但是“国民价值观应经由民主的程序,形成多数的共识(即制度化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立法的内容”。(18)即使是通过科学调查方法获得的民意也不能不经合法的立法程序而直接决定一项行为的入罪与否。民意可以是一种新型危害行为入罪的重要参考指标,但刑事立法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在遵从社会正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判断,“多数人”的意见显然不能直接作为新型危害行为的入罪标准之一。
问题二:已由行政法规进行规制的新型危害行为是否仍需入罪?
刑法作为最后手段法,在其他法律制裁手段不足时才能动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由行政法规进行规制的危害行为不存在入罪的可能。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是相对的,“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和社会伦理取向及价值判断标准的改变,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可能相互转化”。(19)对于已经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且适用行政制裁对其已然威慑不足、收效甚微的违法行为,适时地将其入刑正是刑法第二次法性质的体现。但这种犯罪化必须在恪守刑法谦抑的立场上进行,不能为了打击违法和防卫社会而盲目推进。
学界有观点认为我国应当实行犯罪分层化,一些具有一般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应被作为“轻罪”入刑,在降低犯罪门槛、扩大犯罪圈的同时也将刑罚的严厉程度相应降低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通过犯罪分层,将占犯罪总量绝大多数的轻微案件(例如我国的治安案件)纳入法制化的处理轨道,不仅有助于扩大法官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与权限,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而且通过为相关当事人提供必要的司法保障(如独立、公平、公正、及时审判,辩护权等),有效地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20)而且,将本来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罚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一种形式上的犯罪化。由于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被法律所禁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受到比刑罚更重的处罚,因而并不涉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剥夺。(21)我国行政机关既可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也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权,特别是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的期限最长可达3年,加之我国行政处罚的调查、决定与执行权都由行政机关行使,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因此形式上的犯罪化不仅不会侵犯人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保护人权。(22)
上述观点强调了刑事程序更有利于人权保障,却忽略了将危险驾驶这样的一般危害行为入罪后,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权力实质上被公安机关把握,这与主张犯罪分层的学者提出的防止行政权滥用以保障人权的初衷显然不符。另外,刑罚资源的有限性也限制着犯罪圈向行政违法行为扩张,“案多人少”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实际困难,自“醉驾入刑”之后,大量的醉驾案件使得办案任务本就繁重的司法机关雪上加霜,某基层检察院在醉驾案件高发时期要专门安排两名公诉人员负责醉驾案件办理和与公安机关联系。(23)有限的刑罚资源被投入到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就意味着无法集中起来打击危害严重的犯罪行为,不恰当的分配降低了刑罚资源的使用效益。
问题三: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是否需要考察刑事程序问题?
帕克与我国学者在入罪标准理论上最大的不同即帕克更加强调刑事侦查等刑事程序对行为入罪与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其理论的第四和第五个条件之中。第四个条件旨在说明只能将那些容易被警察侦查到的行为入罪,因为不论是对惩罚这些犯罪可能带来的预防效果而言,还是对警察公平执行法律而言,这都是有意义的。第五个标准要求某一行为的入罪不会使该程序面临严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负担”。所谓“定性的负担”是指在调查犯罪过程中出现令人反感的警察行为,例如不法搜捕和抓捕以及其他形式的警察圈套等;或者是警察的工作会促成贿赂和腐败;而“定量的负担”是指该行为的入罪会给刑事诉讼程序造成数量上的压力,而且实际情况中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与该罪在数量上的压力之间成反比。(24)
“犯罪现象是统一的整体,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学科划分只是研究主题分化的结果,不能因此而割裂对犯罪现象的研究……”,(25)涵盖实体和程序的刑事一体化研究更有利于深入全面地解决实践问题。上述两个涉及刑事程序的条件既关注刑法适用的公平性和效益性,又强调了刑事执行过程应尽可能少地干涉公民自由,注重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新型危害行为入罪后,公安司法机关通常要采取一些未曾使用过的侦查手段或取证方法,甚至对犯罪成立的认定要完全依赖某种科学仪器的检验鉴定所提供的证据,新型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取证环节设计的不严密都会导致刑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以及增大警察权力寻租的空间;另外,一些新型危害行为本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轻微违法行为,随着数量增多而有了将其入罪的必要,但入罪之后因其基数众多还是会对刑事程序造成数量上的负担。因此,帕克理论中的这两个条件对于确立新型危害行为的入罪标准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刑事立法是刑法运行的起始环节,作为起始环节,立法的好坏势必会对之后的侦查、起诉、审判及执行各环节产生连锁反应。例如“醉驾”在舆情激愤中匆忙入刑后,一经司法实践便暴露出种种问题:未建立查处醉驾的常态化机制、各个地区量刑不均衡、对醉驾的查处没有划分交警与刑警的工作权限、血液检测的鉴定人资格问题以及犯罪嫌疑人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实质上难以操作等等。因此,一种新型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入罪,须考虑该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消极效应,如果这种消极效应受客观条件制约而难以通过制度设计予以克服,犯罪化的立法便不宜操之过急。
三、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立:以反对“毒驾入刑”为例证之分析
通过上文的理论辨析,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不仅详尽具体,且兼顾刑事立法和刑事程序两面,更能切中新型危害行为入罪问题之要害。笔者拟在其刑事制裁界限理论之基础上,结合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尝试提出一个不够全面却有针对性的具体入罪标准,以期为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提供参考。为了便于观点的展开,同时体现该标准的可操作性,下文将以近来呼声极高的“毒驾入刑”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分析。
“毒驾”应否入刑的讨论早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征求意见之时就已兴起,然而当时学界对于醉驾入刑尚存争议,相对发生率较低而检测成本和难度又高的毒驾行为就没有进入刑法修订的正式议事内容。但随着近两年毒驾行为的增多,并出现了江苏“422”特大交通事故以及全国首例网络直播毒驾案“四川杨博案”等引发了媒体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的毒驾案例,作为危险驾驶行为之重要类型的毒驾行为就被视为危险驾驶罪的“漏网之鱼”。媒体纷纷建议将毒驾行为入刑,“对毒驾行为必须重拳治理,要像醉驾入刑一样实施毒驾入刑,对毒驾零容忍,对毒驾的宽容就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26)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危险驾驶罪还应包括吸毒或服用过量镇定类药品等其他不能自控的情况下驾驶,这些情形也具有极度危险,往往不亚于醉驾的危害性”。(27)目前在我国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对毒驾的处理分为两种情况:毒驾造成相应危害后果的,依其犯罪情节与伤亡程度以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毒驾未肇事的情形,就依《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相关规定予以罚款、拘留、吊销驾照等行政处罚。对于毒驾“不肇事不担责”的立法现状是否放纵了大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毒驾行为,将毒驾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中以刑罚予以规制是否确当?对此,笔者将在下文采用具体的入罪标准予以讨论。
(一)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28)我国通说亦认为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正是由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才使得犯罪得以与一般的违法行为相区别。(29)因此,立法者在决定一种行为是否应被纳入犯罪圈时,首先需要对其社会危害性进行判断。
然而,以社会危害性作为入罪标准通常被认为是难以贯彻实施的,因为社会危害性具有相当的抽象性,难以具体认定。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危害性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变化,又“因为社会危害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物质,而是具有一定的世界观的社会人根据自身的情感进行评价的结果,而人的发展本身尽管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但并非是机械的反射,而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是带有自身思维的产物,或者说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情感评价”。(30)诚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范畴,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危害性作为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且能被具体判断的。另外,作出这种具体判断的主体只能是某种行为发生所涉及领域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刑法理论专家。对新型危害行为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则需要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因外行对其知之甚少,只有通过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才能从各个方面把握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或侵扰状况。
在呼吁毒驾入刑的文章中,对毒驾社会危害性的衡量多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以“毒驾危害甚于醉驾”来论证毒驾入刑的正当性。毒驾危害甚于醉驾的“共识”得以形成往往是因为一些毒驾引发的交通事故伤亡较醉驾更为惨重,但仅从个案中得出的结果并不足以说明毒驾的社会危害性大于醉驾。任何一种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不同个案中都有轻重程度的差异,因此,社会危害性要求行为对社会利益的侵害具有高度盖然性。醉驾入刑是以醉酒驾驶对道路交通安全存在超出个案的一般危险性为前提的,因此,毒驾行为若要被纳入危险驾驶罪之中就需要证明吸食毒品能够对驾驶行为普遍产生消极影响并显著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澳大利亚国家药物与酒精研究中心的学者将1980年以来欧洲数个权威机构针对药物对驾驶的影响所做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这份综述总结了在实验室、模拟器、公路驾驶等各种研究中酒精、大麻、苯二氮卓类药物、鸦片、兴奋剂和混合毒品对驾驶的影响。各项研究结果都一致给出了酒精能对驾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也普遍显示酒精与毒品结合会对精神造成更大的损害,但除此之外,针对各种毒品的研究结果却模棱两可。譬如实验室研究证明大麻在高浓度情况下能对驾驶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但在驾驶研究中却无法得出相同的证据,对发生交通事故的司机进行调查也发现体内含有大麻活性成分的司机并不必然比体内未检测出毒品的司机承担更多的责任;低剂量的安非他命对于服用者的认知功能几乎不产生有害影响,并且可能增强其工作性能;对鸦片而言,鸦片的类型、服用的途径以及个体耐受性的差异都能引发不一致结果的产生。面对各种相互矛盾模棱两可的研究结果,文章最终只得以“尽管毒品和交通事故风险之间相关的证据稀少,但我们可以假定所有毒品在高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作为结论。(31)
由于毒品种类繁多,服用途径以及摄入剂量的不同都能左右毒品对人体的作用;另外服用多种毒品后毒品之间的相互反应难以把握,且毒品在人体内的代谢受年龄、性别、体重、精神状态等的影响,因此吸食毒品后个体的精神受损状态差异很大,关于毒品对驾驶能力具有消极影响的研究也只能得出一个平均的或者假定的结论,不能排除实践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例外个案的发生。在吸食毒品与驾驶风险之间的普遍联系尚未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之时盲目将毒驾入罪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难题,也将挑战刑法责任主义的根基。
(二)行为入罪后,能够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一种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固然可以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多方位的评判,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将其置于司法实践中进行检验。新型危害行为由于其“新型”,在入罪标准确定和侦查取证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专业知识或新型技术,司法实践一般采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不成熟的借鉴和过于大胆的尝试增加了刑法适用的不公平。
在毒驾入刑的讨论过程中,毒驾的入罪标准难以确定以及检测毒驾的技术不够完备是司法实践面临的最大难题。尽管有观点认为“毒驾入刑已为欧盟、美国、加拿大等诸多国家地区普遍实行,我国公安部门现已掌握了相关技术手段,在20分钟内便可鉴别吸毒者,因此,在执法操作层面上已经没有更大的障碍”,(32)但经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毒驾入刑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难题。
在确定毒驾入罪标准的问题上,“零容忍”的态度备受推崇。所谓“零容忍”即指只要在驾驶者体内检测到毒品,不论含量大小,不论驾驶能力是否受损,一律入罪。“零容忍”要求的入罪标准很低,被视为最有利于打击毒驾行为的方式。但在我国一旦实施对毒驾的“零容忍”,就意味着所有查处到的毒驾行为都将入罪,这就在实质上彻底架空了行政法的规定。在我国区分刑罚与行政罚的惩罚体系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并不存在界限鲜明的质的差异,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危害性与伦理可责性的严重程度不同。对于社会危害性及伦理可责性极其微小的毒驾行为(例如喝了含咖啡因的功能性饮料后驾驶汽车的行为)也适用刑罚会使得刑罚打击面过大,因此毒驾入刑需要确立一个标准作为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
然而,若像醉驾入刑一样设置一个客观的入罪标准,那么且不论针对每一种药物设定受损害标准之困难,即使确立了一个所谓的平均标准,也难以解决混合毒品和毒品代谢物的问题。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吸食多种毒品的人受到的损害明显增大,假如设置了每种药物的限定标准,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个驾驶者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其体内的每一种药物含量均未达到法定标准。(33)药物摄入人体之后就被分解为代谢物,有些代谢物在药理上具有活性,能够影响人体不同器官的功能,还有一部分代谢物不具有药理上的活性,因此对人体没有影响。如果检测结果显示驾驶者体内的代谢物已失去活性,就证明在检测时刻驾驶者的身体未受到毒品影响,至于驾驶者何时吸食过毒品,何时在毒品影响下驾驶汽车都是无法确认的事实,对驾驶者是否定罪也就充满了争议。(34)
为避免客观标准存在的实质不公问题,很多国家采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毒驾,但以不良驾驶行为的影像资料与警察对驾驶者进行的损害测试结果作为证据的主观标准也面临着可靠性的质疑。美国洛杉矶警察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设计实施了DRE(Drug Recognition Experts)程序,(35)授权警官通过实施程序中的十二个步骤对驾驶者进行药物损害的识别。在DRE程序的推广使用过程中,明尼苏达州的实践结果表明DRE程序对兴奋剂、抑制剂和麻醉剂的识别率总体上只能达到55%到66%,警官作出的药物损害认定中有将近50%与药物测试结果不符。还有观点认为DRE程序中的第二个步骤“警官与嫌疑人面谈”是整个程序中的结构性硬伤,使警官可能在获得嫌疑人坦白的基础上进行后续步骤,从而对模糊不清或处于临界的受损害特征高度敏感,整个检测将丧失中立性。尽管该程序还包含客观的药物学检测步骤,但该种检测不能衡量驾驶者遭受药物损害的情况,只能证明药物或其代谢物存在于驾驶者体内,因此药物测试的辅助只是减轻了对DRE测试精确性和可靠性的怀疑。(36)
尽管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即使结合使用也难以做到精准可靠,但境外与我国港台地区都在适用这些标准,因此毒驾入刑的支持者一再强调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做法。但对我国能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笔者持保留态度。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严格区分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而国外刑法一般不区分“违法”与“犯罪”,即使极轻微的违法行为也要由刑法进行规制。相应的,国外的惩罚体系也不区分行政处罚和刑罚,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毒驾行为初次被查获时,若驾驶者无异议,警方就可以不经过法院审理,以发布交通侵权通知的方式对其定罪,并处罚金及暂扣三个月驾驶执照。(37)这与我国定罪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不同,且判处刑罚的严厉程度也只相当于我国的行政处罚。因此,我国毒驾未入刑并不是法律的缺失,而是由于我国有行政法规来分担对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行政处罚相对刑事处罚,既节约高效,又避免了监禁刑的交叉感染以及犯罪标签对行为人回归社会造成的阻碍。尤其在我国,大部分关涉职业资格的法律都有禁止犯罪人终身或一定期限内从事某种职业的规定,犯罪将使公务员、司法人员、教师等群体面临职业前途尽毁的严重后果,刑罚之恶的突出决定了我国对待入罪问题应当慎之又慎。
关于毒驾的检测方式,目前我国执法人员基本只能依靠目测进行粗略筛查,对超速行驶、左右摇晃等驾驶情形异常的车辆或发生严重事故的车辆在进行酒精测试无果后再进行毒品测试。在当前没有建立路旁毒驾随机筛查机制的情况下,即使毒驾入刑,也难以达到威慑效果。尽管我国已有科学工作者发明了用于路旁毒驾随机筛查的唾液吸毒检测产品,但其只能检测出冰毒、海洛因和摇头丸等几种常见毒品的有效成分,且“唾液测毒”成本很高,现在普及尚有难度,同时“唾液测毒”只是粗筛,并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使用。(38)在欧洲,虽然一些国家已经使用了毒品检测设备筛查毒驾,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设备足够可靠,一个有经验的警察对司机的观察总体上仍然是最可靠的筛查驾驶者是否吸毒的方法。(39)因此,在进行路旁毒驾随机筛查时,依靠授权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损害测试是相对最可靠的措施。但毒驾现场损害测试比唾液检测更耗时耗力,结果精确与否仅仅取决于执法人员的专业与经验,因此拥有训练有素且数量充足的执法人员是执行这一筛查措施的客观基础。我国执法人员的素质与资源配备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极不平衡,这种现状必然导致毒驾筛查在一些地区能顺利推进,在一些地区却困难重重,执法水平的差异将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我国在毒品缉查工作中,排查嫌疑人员是否吸毒的常规检验方法是尿液测试。但采用尿液检测的方式为认定毒驾提供药物检测证据已经很少被各国采纳,因为“我们都知道违禁药品及其代谢物存在于尿液中的时间要长于其存在于血液中的时间,这也正是立法要求违禁药品要在血液中发现而不是在尿液中发现。只有这些药物存在于血液中时,才会对人的大脑和肌肉产生影响”。(40)因此,通过血液检测认定毒驾更为可靠,但血液检测需要由执法人员指明的注册医师或注册护士在排除嫌疑人存在因医学上的理由不能或者不应当抽取血液样本的情形之后,再进行血液样本的抽取。(41)而在我国为道路执法配备指定的医护人员很难实现,尤其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具有资质的医护人员较为稀缺。如果不能当场抽取血液样本,嫌疑人血液内的毒品含量就会在去往抽血场所的途中随着体内代谢而逐渐减少,无法为认定毒驾提供确实证据。
“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项法律被制定并不意味着当然地发挥作用,法律的实施必然受一国当下的科技水平、执法能力、司法资源等各项因素的制约。“……如果一个时代,条件尚不具备,则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经由立法来确定诸种法律概念,如若径行其事,则其效果对于后续时代不无伤害”。(42)
值得一提的是,毒驾行为人在庭审时能否受到无歧视的公正待遇也值得关注。由于吸毒本身的违法性与悖德性,毒驾嫌疑人无法获得公众的同情,可以预见在司法审判中被告人很难获得公正的待遇,“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微弱的辩护声往往为公众的道德口水所淹没”,(43)在保障公共安全以及满足公众报应心理的考量之下,存疑的案件也极有可能会被定罪。没有可靠的检测技术与严谨的执法程序作为基础,盲目将毒驾入刑势必会越过人权保障的边界。
(三)行为入罪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
“刑罚通过制定、适用与执行,对犯罪人本人及周围的一般人产生影响,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结果,乃是一种符合社会大众心态的普遍的历史事实。因此,预防犯罪,理所当然地也应成为我国刑罚的目的。”(44)将一种新型危害行为入罪的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抑制该种行为的发生,也即要达到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
在呼吁毒驾入刑的文章中,刑罚具有一般预防效果是最常见的论点,而支撑这个论点的论据往往是醉驾入刑后各地查处醉驾的数量大幅减少,刑事立法的震慑效果十分显著。有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上海等地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分别在50%、70%以上,酒驾、醉驾“双降”,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明显下降。2011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2.3%;截至2012年4月20日,上述指标的同比降幅为28%。(45)但刑罚的威慑预防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功用?毒驾入刑之后能否如醉驾入刑一般取得显著效果?
“威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有证据表明其有效性非常变动不居。它很可能只对两种情况下的行为才最有效:被抓获可能性大从而使得行为人有可能斟酌风险以及风险虽低但行为人十分惧怕刑事定罪。换句话说,高风险的预谋犯罪和由守法者实施的犯罪才是最有可能被刑事制裁威慑住的犯罪。”(46)
醉驾入刑的威慑效应显著与醉驾被查获的几率很高密切相关,便捷廉价又精准可靠的酒精呼气检测技术使道边随机筛查酒驾成为可能。相较之下,我国对毒驾的查处机制尚不完善,缺乏查处毒驾的常态化规定,在依靠执法人员目测进行筛查的情况下,驾驶行为没有明显不良表现的毒驾者被查获的几率很小,因此毒品测试通常都是在违章行为甚至是肇事行为发生之后进行的。“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47)现有的检测技术客观上限制了查获毒驾的高效性与准确性,难以消除毒驾者的侥幸心理,刑罚的威慑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另外,刑罚的威慑力建立在对方是守法之人的假设之上,但作为潜在毒驾人的吸毒者却多是漠视法律之人。吸毒与饮酒不同,饮酒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不具有任何的道德谴责性,因此醉驾遍布于普通民众之中,一旦醉驾入刑,法律禁止醉驾的规范意识即迅速在民间形成,遏制之效立竿见影。但吸毒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涉及普通民众,吸毒者多是自我约束力较低,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妄图挑战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之人。这样寻求刺激与冒险,具有反社会性与侵略性的群体又怎么会被危险驾驶罪的拘役、罚金之刑所震慑?众所周知,毒品具有吸食成瘾的特性,一旦停止吸食会使吸毒者痛苦难耐,而且毒品对驾驶者的影响比酒精复杂的多,会令人难以自抑地去飙车以寻求刺激,或是陷于幻觉之中兴奋地撞击行人车辆。吸毒成瘾者沉迷毒品难以自拔,靠毒驾入刑的威慑力无法杜绝其吸毒的可能性,也就无法对毒驾行为防患于未然。
将毒驾行为入刑,对于毒驾行为人本身,尤其是吸毒成瘾的毒驾行为人,也难以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吸毒成瘾的毒驾者不同于普通犯罪人,戒除毒瘾是对其进行改造的首要任务。对于达到强制戒毒条件的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对其作出强制戒毒的决定,根据戒毒人员的戒毒情况,强制戒毒的期限至少要达到一年,最长可以达到三年。而如果按照毒驾入刑支持者的意见,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之中,那么对吸毒成瘾的毒驾者最多只能处以半年拘役的刑罚。一般而言,半年时间难以达到戒除毒瘾的效果,刑罚执行完毕后毒驾者还是需要继续接受社区戒毒或者强制戒毒。显然,对于吸毒成瘾的毒驾者,强制戒毒比短期自由刑更为治本,更加有效。
(四)没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可以代替刑罚
“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但是还有其他多种社会控制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当其他社会控制的量减少时,法律的量就会增加,反之亦然。”(48)近年来,毒驾在我国呈现爆发态势,恶性毒驾案件频频见诸报端,但毒驾情形恶化并非刑事法网不严之过,而是公安交管部门疏于监管以及抑制新型毒品扩散不力之过。
有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在册的十二万吸毒人员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一比例在武汉已达到三分之一;长途货运司机、夜班出租车司机以吸食毒品来提神解乏几乎是其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北京某区检察院共办理过五起毒驾案件,其中有三起案件的驾驶人是“的哥”。(49)据某地客运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出租车司机吸毒的话就肯定不能上岗,但怎么确定即将上岗的出租车司机是否吸毒要由公共交通治安分局进行检查,而公交分局则表示在出租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车辆上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等由公交分局介入调查,出租车司机的选拔和培训全部由客运管理处负责。(50)这种相关管理部门互相推诿的做法对“的哥”毒驾愈演愈烈的现象显然难辞其咎。为了应对大量吸毒者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形,2012年10月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2条规定:“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三年,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解除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然而,有交管人员表示交管部门与禁毒部门之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交管部门无从知晓每一位申请驾照者是否有吸食毒品的历史,要求申请人去禁毒部门开相关证明更不现实,因此该条款目前尚难以操作。(51)在立法已然表明了打击毒驾的决心之后,交管与禁毒部门各自为政、相互脱节,使得立法难以取得预想的成效,无法从根本上防止吸毒人群与驾驶人群的交叉融合。
另外,新型毒品的泛滥亦是导致毒驾行为猖獗的重要因素,毒驾案件涉及的药物多是K粉、冰毒、摇头丸等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从药理与毒理机制来看,传统毒品海洛因和新型毒品给吸毒者带来的药物反应和体验截然不同:前者以放松、舒缓为主,而后者以亢奋、激动为主。(52)因此,吸食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后,使用者喜欢滞留在室内“腾云驾雾”,不愿外出;而新型毒品的使用者会在吸食之后出现亢奋、精力充沛的症状,喜欢外出寻求刺激,致幻类新型毒品的使用者还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常有被害妄想。近年来出现的多起恶性毒驾案件中,毒驾者产生被后面车辆跟踪、被车内乘客胁迫、身处竞技游戏中等种种幻觉的情形十分常见。同时,新型毒品服用初期产生的高度兴奋、食欲减退、不知疲倦的效应也使得长途货运司机、夜班出租车司机等群体将其作为提神药物来服用。新型毒品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价格低廉且获取渠道广泛等特点迅速扩散,根据《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2011年)》,2011年新发现的药物滥用者中传统毒品与新型合成毒品滥用人数的比例为1∶2.2。另外,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于新型毒品的认识也存在种种误区,有新闻工作者曾就吸食新型毒品的青少年对新型毒品的态度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你对新型合成毒品有何认识”这一问题时,80%的被调查者认为吸食合成毒品只是一种普通消费方式,对自己因吸食新型合成毒品被强制隔离戒毒不理解。(53)新型毒品吸食人群的增长与我国驾驶人群的增长导致二者的交叉群体,即毒驾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加,通过公安机关打击贩毒渠道、截断毒品源头以及禁毒部门开展毒品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对新型毒品的警惕才是解决毒驾问题的根本之道。
“……犯罪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决定的社会现象。因此,犯罪问题仅依靠刑罚是难以解决的,只有消除导致犯罪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条件,才是治本之道。”(54)“就许多风险或者危险而言,采取其他措施预防可能比单纯的法律禁止更为有效”。(55)毒驾的日益严重需要禁毒以及交管部门在源头上进行管控,而不是等到毒驾行为已然发生后再由刑罚介入。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方法之一,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刑事制裁予以解决,过分迷信刑罚不仅会引发犯罪圈的不当扩张,还将造成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萎缩,进而致使公众和国家管理者将刑法视为“救命的稻草”紧握不放。这样恶性循环终将导致对刑罚的滥用和对自由的压榨,不仅与刑法谦抑的立场背道而驰,也与建设法治国的目标相距甚远。
四、结语
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入罪后能够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入罪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没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可以代替刑罚这四个条件分别针对新型危害行为入罪过程中出现的以“民意”代替专家来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直接推动立法、为安抚公众而草率立法以致个案显失公平、“刑罚万能”思想备受推崇、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被忽视等问题而提出,虽有了无新意、老调重弹之嫌,但立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还是在时刻警醒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这些标准背后蕴涵的刑法谦抑、人权保障思想更是需要被反复言说、上下求索、铭刻于心!
注释:
①参见谢望原、卢建平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
②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③高金桂:《利益衡量与刑法之犯罪判断》,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69页。
④[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⑤[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⑥前注⑤,[德]克劳斯·罗克辛书,第22页。
⑦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⑧[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⑨参见[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94页。
⑩参见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4期。
(11)参见谢望原:《作为刑罚价值的自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2)前注⑩,张明楷文。
(13)前注(11),谢望原文。
(14)[法]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5)参见王政勋:《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16)参见孟勤国:《专家不能代替人民立法》,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
(17)田宏杰:《“风险社会”的刑法立场》,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18)前注③,高金桂书,第74页。
(19)梁根林:《刑事政策:扩张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20)卢建平:《犯罪分层及其意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1)参见陈兴良:《犯罪范围的合理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2)参见欧阳本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刑事政策分析》,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
(23)参见楼笑明、雷小强:《浙江义乌:“三高一低”特点显著》,载《检察日报》2012年5月9日第5版。
(24)参见前注⑨,[美]哈伯特·L.帕克书,第297页。
(25)叶小琴:《论刑法的趋同》,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
(26)刘武俊:《毒驾猛于虎》,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29日第2版。
(27)赵秉志、赵远:《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
(28)参见[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29)参见苏青:《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反思与改造——以法益视角为进路》,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3期。
(30)苏惠渔、孙万怀:《论国家刑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31)See Erin Kelly,Shane Darke,Joanne Ross:A review of drug use and driving:epidemiology,impairment,risk factors and risk perceptions.Drug and Alcohol Review(September 2004),23,319-344.
(32)游伟:《“毒驾”入刑的呼声应当正视》,载《法制日报》2013年3月7日第3版。
(33)See Make drug-driving illegal,but prevention is better,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1359-make-drugdriving-illegal-but-prevention-is-better.html.
(34)See Matthew C.Rappold,Evidence of Inactive Drug Metabolites in DUI Cases:Using a Proximate Cause Analysis to Fill the Evidence Gap Between Prior Drug Use And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32 UALR Law Review.535,536 2010.
(35)DRE程序包括:酒精呼吸测试、与逮捕警官的面谈、初步审查、眼睛检测、注意力分散检查、生命体征测试、黑屋子测试、肌肉紧张度测试、注射针孔检测、嫌疑人的陈述和其他观察结果、鉴定人的意见、药物学检测。
(36)See Jeffrey M.Morgan,The Admissibility of Drug Recognition Expert Testimony in The Prosecution of Individual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Controlled Substance:State v.Klawitter,518 N.W.2d 577(Minn.1994),18 Hamline L.Rev.261 1994-1995.
(37)See Drug driving penalties,http://www.vicroads.vic.gov.au/Home/SafetyAndRules/RoadRules/Penalties/Drug Driving Penalties.htm.
(38)参见翟兰云、张灿灿:《治理“毒驾”入刑与源头管控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12年6月26日第4版。
(39)See TISPOL Alcohol & Drugs Driving Policy Document,https://www.tispol.org//policy-papers/alcohol-drugs-driving/tispol-alcohol-drugs-driving-policy-document.
(40)See John B.Mancke,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DUI)off Drugs Law Update,Pennsylvania Bar Association Quarterly July,2009.
(41)参见《香港道路交通条例》。
(42)[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43)杨志琼:《美国醉驾的法律规制、争议及启示》,载《法学》2011年第2期。
(44)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
(45)参见李飞、杨永强、刘德华:《毒驾:是“明知”还是“恍惚”?》,载《检察日报》2012年9月27日第5版。
(46)前注⑨,[美]哈伯特·L.帕克书,第266页。
(47)前注(28),[意]贝卡里亚书,第72页。
(48)[美]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9)参见前注(38),翟兰云、张灿灿文。
(50)参见潘从武、黄英:《毒驾药驾危害等同酒驾却未被重视——对吸毒和服药后驾车的检查机制和法律责任凸显空白》,载《法制日报》2010年11月18日第7版。
(51)参见张蕾:《“毒驾入刑”,还有多远?》,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6月25日第5版。
(52)参见夏国美等:《社会学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53)参见周跃五:《勿陷新型毒品误区》,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29日第19版。
(54)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55)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