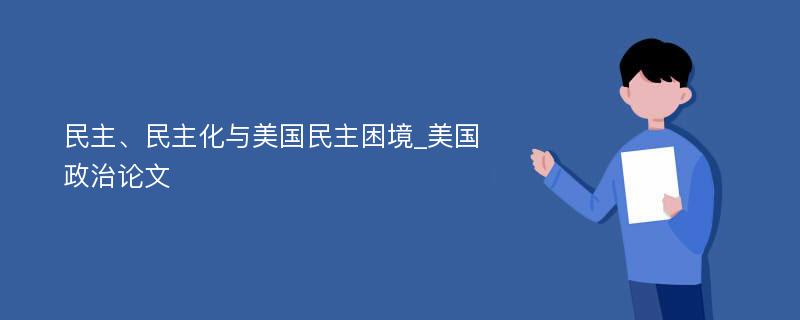
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美国论文,化与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苏联解体和东欧民主化变革使福山进一步完善了其“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的终结,更重要的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然而,冷战后全球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如福山预测的那么乐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重新走向新形态威权主义;在中东,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和“阿拉伯之春”后出现的叙利亚内战,导致了“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中东地区陷入了势力均衡被打破后的极端混乱;在欧洲,难民问题促使保守主义兴起,欧盟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危机;美国本身则陷入前所未有的党争、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出现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危机。尽管福山依然没有否定其“历史终结论”,但是他不得不修正以前过于乐观的看法,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福山认为美国已经形成否决性体制,从而导致美国民主出现衰败。 为什么冷战后民主化浪潮趋于失败?为什么美国民主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困境?本文将从民主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民主巩固、民主与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一、民主与民主化的失败: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转型。美国前驻俄国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将这一波民主化转型称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麦克福尔认为这次民主化浪潮的特点是:一些国家成功转化为自由民主国家,一些国家重新走回专制体制,还有一些国家则“卡”在了自由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中间。①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区域出现了这种特点:地理位置靠近西欧自由民主国家的东欧国家,民主转型比较彻底,例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地理位置远离西欧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的陷入无休止的首脑更迭,例如乌克兰,有的则重新走回威权体制,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有的虽然具有民主选举的全部规则,却是事实上的威权体制,如俄罗斯。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是一种政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首脑经由大众选举且竞争对手能够有机会获胜。②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摒弃了过多的规范性价值判断,将民主定义为“可以重复的有失败者的竞争性选举制度”。③根据这种定义,俄罗斯等国民主化不彻底的民主体制可以被称为“混合民主”(hybrid regime)。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斯蒂文·列维斯基(Steven Levitsky)和卢肯·威(Lucan Way)认为,在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体中留下了专制体制的残余,从而成为麦克福尔所说的“卡”在自由民主政体和完全的威权体制中间不动的特殊政体。④ 民主与民主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概念。民主是一种目标体制,而民主化则是达到这种目标体制的过程。实现民主必须依靠民主化,但民主化并不必然走向自由民主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关心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出现民主化。政治经济学流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引发民主化的主要动因和民主化的起点。其中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自由民主体制紧密相关,这是民主化成功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利益多元化,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促使社会变革,进而产生对民主体制的诉求。⑤根据这种逻辑,经济发展迫使原有社会必须要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现代化,而权力高度集中无法满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从而成为民主化的起点。⑥ 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危机将会导致寡头集团内部分裂,从而出现政治反对派。⑦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政治经济学流派的观点。这些国家因市场经济改革遭遇严重困境,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后,国内反对派对原有政治体制合法性进行挑战,进而加速了原有体制解体和崩溃的步伐。但是民主化的起点并不必然走向自由民主体制的终点。俄罗斯的民主化过程表明,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体制不稳定,但是却走向新型的威权主义。因此,政治转型流派认为,经济发展或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虽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危机催生政治不稳定,但同时也会“侵蚀民主体制”,反而朝着更加官僚化的威权体制发展,甚至导向更加专制的军政府和一党体制。⑧ 对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化,民主体制是社会阶级之间权力的均衡状态。是否走向民主体制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如何分配来决定。⑨因此,新型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愿意形成制约国家的力量,反而有可能顺从甚至积极支持威权体制。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中产阶级、大财团、大财阀依然要依附于军政府体系。银行、财阀成为维护军政府统治的强有力的联盟力量。⑩ 从民主转型的结果来看,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并未走向自由民主体制。麦克福尔认为,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政体转型基本颠覆了以前对民主化的认识。这是因为各个加盟共和国当权者及其挑战者处于一种不均衡的权力分配中,进而形成了“非合作性转型模式”。在这一转型中,如果民主派占据优势,那么将完成民主转型,如波兰和匈牙利;如果旧制度掌权者完全处于优势,那么将仍然保留专制体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白俄罗斯;如果旧体制掌权者和民主派挑战者势均力敌,权力分配相对均等,那么这类国家的民主转型就会“卡”在自由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中间,如俄罗斯和乌克兰。(11) 斯蒂文·列维斯基和卢肯·威将这种“卡”在民主化道路中间的体制定义为“竞争性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体制虽然具有自由民主制的主要特点,如定期的选举,且在总体上看选举程序没有大规模公开造假,但执政党却对竞争性政党及其支持者进行恐吓,阻止他们获得媒体支持,甚至动用国家机器逮捕、驱逐甚至暗杀反对党领导人。然而,这种违反民主精神的做法却是在“合法”的程序上进行的。从本质上而言,“竞争性威权主义”利用民主程序巩固了旧有的专制体制,但又不像旧有专制体制那样完全不遵守民主程序。(12) “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不仅仅是从专制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过度时才会出现,已经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也会衰败到这一体制,因为当政治或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后,新任领导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获取国家最高权力,进而破坏自由民主体制的规则,形成事实上的专制体制。藤森统治下的秘鲁和查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即是如此。(13)由自由民主制衰败而成竞争性威权体制,在本质上和纳粹德国不同,因为这种体制依然在形式上必须合法地遵循自由民主体制的规则。 这些国家的政体变革表明,民主化并不一定出现民主体制,民主与民主化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历史并未从此“终结”。在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无论最终形成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竞争性威权体制国家,还是重回专制体制的国家,它们在总体上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经济依然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发展,这与原来这些国家具有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旧体制掌权派和挑战者在总体上能够形成妥协,国家政权及社会并未被极端左翼或右翼势力控制等因素紧密相关。中东北非国家的民主转型则没有这么幸运,它们的民主化刚刚开始就陷入宗教控制或者无政府状态。 二、民主与民主巩固的失败:中东北非民主化 在“民主和平论”的影响下,“促进民主”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理论指导。(14)“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军在伊拉克直接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2010年,“阿拉伯之春”进一步改变了中东北非的政治秩序。长期统治突尼斯的本·阿里被迫流亡海外、埃及的穆巴拉克锒铛入狱、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在北约军事打击下彻底崩溃、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内战。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从军国主义成功转化为自由民主体制的经验,并未能够在伊拉克重复,反而让美军陷入战争泥潭而不得不从伊拉克仓促撤军。 “输出民主”理论认为,通过国际压力和外部环境,可以在非民主国家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传染/多米诺骨牌效应、控制和准许。(15)传染效应是指从地理角度而言,当一个国家开始民主化后,就会成为这一区域其他国家“民主化的传播源”,民主化就像传染病或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向周边国家传播。历次民主化浪潮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就印证了这一观点。“控制”是指通过国际压力,无论是军事占领还是国际制裁,直接促使非民主国家领导人放弃独裁统治而实现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及南非的民主化就是这种形式。“准许”是指通过国际压力、国际援助或者建立安全联盟,迫使非民主国家接受民主原则,建立一套适应民主规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而逐步完成民主化的各项议程。例如,1998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经济援助为交换手段,迫使苏哈托放弃独裁统治,印度尼西亚从此向民主体制转变;欧盟要求土耳其按照民主原则改造其政治、社会体系,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条件。 “输出民主”并未促使中东北非地区出现自由民主体制国家,反而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政治平衡和势力均衡状态。由于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该地区因此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并最终促使了“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输出民主并未给中东北非地区带来和平,反而让欧洲面临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压力,直接威胁到欧盟的安全与稳定。 巩固民主需要五大国内要素:(1)政权在地理、宪法和政治传统上具有合法性;(2)各方都能接受和遵守民主规则;(3)反对党能够接受政策约束;(4)较低的贫困程度;(5)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分歧不大,并且能够相互尊重。(16)根据这五大要素,中东民主化失败的根源是国家建构和民主体制建立的顺序发生错误。亨廷顿认为,国家重要政治分野,不在于政体形式,而在于政府有效性。(17)这里的“有效性”是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国家不但能够合法使用暴力,而且能够超越宗教、党派、利益团体形成有效的现代治理机制。虽然苏联东欧国家中有很多民主化不彻底或者重回专制体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建构先于民主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日本从军国主义改造成自由民主体制,成为输出民主最成功的例证,不过当时日本已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而且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体制改造。但中东北非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和独立建国后,由于美苏冷战的需要,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外部支持下,纷纷建立起强人政治。根据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国家向法理国家变迁的“三阶段论”,这种强人政治本应成为“魅力型领袖”阶段,即通过创造出新文化,彻底根除传统社会中因为种族、宗教带来的分裂因素,从而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然而,这一区域的强人政治是依靠外部军事支持和内部暴力震慑来维持的军事独裁体系,缺乏对法律权威的服从和对规则的遵守。现代文明并未取代传统的宗教和种族意识,国家认同没有代替种族、宗教认同。由于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一区域的独裁政体通过外援或者石油资源即可解决国家财政支出,并不具有建构完整的现代国家经济体系的动力。 很多民主理论信奉中产阶级是维护民主体制的中坚力量,但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力量。当中产阶级并未完全世俗化、宗教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时,一旦中产阶级和宗教势力,例如当政治伊斯兰主义和民主相结合后,宗教动员就会代替国家动员,这将对现代国家建构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中,中产阶级成为突尼斯和埃及专制统治的主要社会力量的原因。(18)这种环境下,民主体制优先于国家建构,其结果就是社会陷入混乱、领土陷入分裂,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当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和分裂后,社会各方希望通过强势集团重新稳定社会。极端宗教势力满足了这一需求,并由此而成为“伊斯兰国”建立的社会基础。 当国家内部缺乏巩固民主的各类要素,缺乏法治传统和国家认同,当国家建构并未完成的时候,外部军事占领、国际制裁或者通过政变等扶植新的统治者,强行在这类国家建构民主体制必然会导致国家失败。当极端宗教势力取代国家成为社会动员的唯一力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就变成了国家和极端宗教相融合,其结果不仅仅是民主的失败和国家的失败,它们还会生产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极端宗教主义怪胎。输出民主的结果是打破了原有脆弱的政治平衡,使这些国家从此走向混乱或者出现超越极权主义的恐怖国家形态。“阿拉伯之春”后混乱的中东及“伊斯兰国”的崛起,标志着输出民主的失败。 三、民主发展与现代治理:美国民主的否决体制 当代西方民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输出民主的失败和西方社会自身的治理问题。与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相比,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最严重的一次,却成为当代美国民主困境问题的引爆点;随后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国社会因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引发社会抗议运动;奥巴马医改加剧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国会内以及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成为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标志。而2016年总统选举,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参选引发的“黑马”效应,将长期以来因“政治正确”而压制的社会矛盾话题全部点燃。福山认为,美国民主体制出现了“衰败”,虽然他依然坚持其“历史终结论”,但不得不承认美国民主自身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美国民主的困境或者说民主“衰败”,本质上是民主政治与现代公共治理出现了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麦迪逊式共和体制造成的行政僵化;通过立法程序来实施行政权力导致的党争;联邦税制与贫富分化;福利国家与“美国梦”;国家间经济竞争。 (一)麦迪逊式共和体制造成的行政僵化 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后,在如何建构美国政体方面,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美国建国之父并不相信纯粹的民主能够带来国家统一与繁荣。联邦党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派系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利益、意识形态和情感基础上的。(19)联邦党人一直不断强调的一点是“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保证公民自由的基础,保卫公共利益是需要依靠有效率有权力的政府,因此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权威。强大的中央权威与权力相互制衡并不矛盾,高权能和高效率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专制政府。 联邦党人认为,党争(faction)会导致国家分裂(美国南北战争就是党争的产物),而解决党争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大的联邦政府并非专制政府,因为可以通过权力制衡的方式来防止其走向专制。联邦党人认为,只有强大的中央权力,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民的自由。(20)当今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强大中央权威,已经远远超过联邦党人的预想。由于美国幅员辽阔,社会管理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联邦体系,所以促使美国朝着独立于立法监督之外的大行政方向发展。战争、国际卷入、经济危机等因素都支持行政独立于立法控制这一主张,从而使得美国联邦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21)美国行政体系内部也彻底接受了麦迪逊式共和体制理念的影响:为了防止某一个部门过度拥有权力,必须设置一个新部门形成一种制约。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一共拥有65支独立的联邦执法体系。(22)联邦执法权力被不同机构分割,虽然形式上各司其职,但在执行时职能交叉,从而造成巨大的行政资源浪费。 麦迪逊式共和体制与预算为主导的政府管理体系相结合,造成的结果是一旦新机构成立就很难被撤销。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巨额财政支持,政府预算由此逐年递增。国家行政权力被众多部门详细分割,虽然能够实现机构内权力的相互制衡,但也造成职能重叠和机构臃肿。有利益的时候,机构之间你争我夺;需要负责任的时候,却互相推诿。例如,不同执法机构各自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情报体系,使美国一共拥有16个不同的情报部门。为了获得更多预算和权力,各情报机构长期以来缺乏统一协作机制。“9·11”恐怖袭击之前,很多执法和情报部门已经获得相关信息,但是机构臃肿且互相推诿,导致惨剧发生。“9·11”事件暴露了美国行政机构长期存在的弊端。 这种既要拥有强大行政权力,又要通过设置机构来互相制衡的行政体制,在对待突发性事件时候,缺乏灵活应对和统一协调的机制。麦迪逊式行政体制构造了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在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管理,尤其是应对全球化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越来越僵化。这种僵化并非民主的结果,而是制衡民主的结果。 (二)通过立法实施行政:政治极化与利益集团 福山认为,联邦行政权力急剧扩大,同时又为了防止专权而设置繁冗的机构和程序,使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衰败,因为其传统的制衡体制日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极端化越来越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但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23)只有通过复杂的官僚机构保障,才能实现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和权力制衡。因此,威尔逊认为,美国政治史不是一部行政发展史,而是一部立法监督史;不是改进政府组织的历史,而是推进立法和政治批评的历史。(24) 为了防止强大的总统制走向绝对专制体制,美国总统行政决策被法令化,公共决策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法案的方式推出。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缺少外部强大竞争对手的状态下,美国越来越强化通过立法来实施行政的模式。这种机制为党争、为利益集团把持和影响公共议题提供了政治机会,社会抗议成为弱者唯一的武器。民主的本质是竞争性集团之间的妥协,三权分立的本质不是三权对立,而是实现三权制衡下的合作。美国一旦出现社会危机,联邦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对社会实施高效的行政权威。而当社会处于平静,同时又缺乏外部威胁的时候,党争又开始影响联邦政府的行政效率。 这种行政决策法令化的决策模式,为“否决性体制”奠定了基础。美国国内重大公共政策都受制于这种决策模式。这些年,在医疗、教育、移民、反恐、涉及严重伦理问题的科技研究等领域,总统行政权力受到极大牵制,严重影响了联邦政府行政效率。例如当代美国最受争议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昂贵的医疗费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初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自1965年起建立针对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制度,美国社会从此有了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障。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收入相对均等、医疗费用合理。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美国医疗体系全面私有化。医疗集团、制药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三大集团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铁三角关系,急剧推高了医疗费用。商业集团铁三角成为“政府—国会—利益集团”传统铁三角关系中的一角。高额医疗费用不但给个人,同时也给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25) 沉重的医疗负担推高了企业成本,并由此而成为美国制造业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时期是美国冷战后经济增长蓬勃的时代。克林顿政府曾尝试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在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下,这种尝试刚刚进行就被迫叫停。小布什执政八年间,美国的重心被放到对外进行反恐战争上,只有部分地方政府如马萨诸塞州进行了医疗改革尝试,再加上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是坚信自由主义经济学,医改更是遥遥无期。 奥巴马上台后,把医疗改革作为其竞选时承诺“变革”的主要工作之一,力图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际上,奥巴马的医改蓝本参照的是马萨诸塞州医改的经验,也就是共和党人罗姆尼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推行的医改方案,而罗姆尼与奥巴马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是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奥巴马用的是共和党人的医改方案作为其改革蓝本。然而,奥巴马医改成为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核心。2013年10月,两党就医改问题的斗争达到了顶峰,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未能就医改达成一致,暂停对联邦预算进行拨款,结果导致白宫不得不临时关闭联邦非安全部门。 奥巴马医改方案将两党政治推向极端化。福山认为,民主政治不是用来结束冲突,而是要通过商定规则来化解和减少矛盾……好的政治体制减少潜在的极端化,鼓励出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方案。当极端化碰上了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26)正是这种制衡政治体制,迫使总统行政决策法令化。总统的任何重大社会公共决策,都要以法案的形式通过才能实施。“在美国历史的较早时期,一旦某个政党取得支配地位,这个体制就会被用来平抑多数人的意志,迫使它给予少数群体更多关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更加平衡更多竞争的政党体系出现,美国体制变成了通往僵局的灵丹妙药。”(27) 实际上,美国医改的核心,本应该是打破因大规模私有化而造成的医疗、制药和保险业形成的利益集团,真正降低医疗费用,而非通过增加联邦支出和增加中产阶级税收来补贴医疗保险。无论两党如何争斗,其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打破这个铁三角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正是利用行政决策法令化的制衡体制,轻而易举使改革偏离初衷。而“近来国会在立法设计上的变化,强化和扩大了有组织者的优势”,(28)进一步为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便利条件。 2004年,美国政治学学会发布了“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美国政治学会特别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国会内部的新发展更加精准地把政府的好处发放给了狭窄的小团体。由于两党已经两极分化为冲突加剧的部落,国会多数党把更多的国防合约、交通资金、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向拨款及其他项目等,留给了本党人士控制的选区。国会议员则进一步将流入自己选区的政府资金,注入投票率更高和给自己提供最大支持的特定选区。(29)这种决策方式会造成严重问题。例如,F-22“猛禽”战斗机是美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其生产本应该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系统工程。但是,为了让国会顺利通过F-22战斗机的采购预算,迫使F-22战斗机制造商将零部件的生产分散到20多个州,这不但增大了战斗机的制造成本,而且由于零部件生产地过于分散出现质量控制难题,使得F-22战斗机的维修费用非常高,出现了“造得起,用不起”的矛盾。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这种利益集团和国会的“猪肉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否决性体制和“猪肉桶政治”这两种极端政治行为影响了美国的行政管理能力,政府本应该成为超越利益集团、维护国家利益的最高权力组织,但现实是利益集团约束甚至绑架了行政权力。联邦党人在最初“顶层设计”时所担心的党争变成了现实。机构间相互制约本应防止政策出台过于专断,在实际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福山才认为“如果美国改成更为统一的议会制,许多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30) (三)联邦税制与贫富分化 1862年,南北战争时期临时实施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1913年,美国正式确立了这项税收体制。个人所得税从此成为联邦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标志着联邦政府将国家权力延伸到美国境内的每一个自然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4年美国联邦财政总收入达到历史新高,其中80%来源于个税(其中46.5%属于个人收入所得税,33.5%属于社会安全保险)。(31)以加利福尼亚州一户收入16万美元的家庭年为例,在扣除联邦税、州税、社会安全保险及401K(政府担保的养老保险)后,家庭净收入只剩下9.28万美元。48%的家庭年收入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拿走。而2014年联邦财政支出中,用于支付社会安全保险的比例只占25%,用于支付老年医保(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其他健保的比例达到25%。(32)虽然美国经济开始重新增速,但是2014年联邦财政赤字依然达到4830亿美元。(33)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由于享受不到医疗补助保险,美国中产阶级个人赋税额和回报率严重不成比例。由于美国企业税很低,只占据联邦财政收入的7.9%。而制造业外流,损失的不仅仅是就业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联邦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率意味着联邦财政收入降低,社会福利支出增大,进而联邦财政赤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联邦任何增加支出的计划,只能从中产阶级家庭攫取,因此,中产阶级对于税率的任何变动都极其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医改遭到了巨大社会压力的重要原因。联邦政府用于军费、反恐的开支逐年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巨额社会福利支出,中产阶级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压力。 另外,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计算,2012年美国1%的人口掌握了25%的国家财富。(34)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很多年没有上涨。由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虽然20世纪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打破了美国看得见的种族藩篱,然而,财富不平等却加剧了看不见的种族和阶层隔离。例如,通过学区制,根据财富的拥有程度确定公立学校的质量和入学标准,使得低收入者永远处于社会最底层。 美国政治评论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认为,早年美国根本没有阶级意识,富裕阶层并非高高在上,甚至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还和富人住在同一高级住宅区中。当代美国“机会平等”的立国根本被打破,问题不在于贫富差距,而在于出现了阶层固化导致的阶级意识。富裕阶层逐渐脱离美国平等社会,并且出现了对普通美国人的傲慢和不屑一顾。(35)社会观念的变化比贫富分化的现实更能加速社会分裂,默里称之为美国社会的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99%”这种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其说是抗议财富不均等和机会不平等,不如说是抗议富裕阶层逐渐对自由平等传统的不尊重,这也是“特朗普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 (四)福利国家和“美国梦” 奥巴马医改的社会阻力表面上来源于增税,本质上则是福利国家和“美国梦”的对立。早期美国是通过先民辛勤劳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立国和发展的源泉是“不养懒汉、勤劳致富”。在新大陆勤奋开垦与工作,从此告别饥荒、疾病、贫穷,同时免于宗教迫害和政府干涉,这是“美国梦”的核心。因为美国国土面积广大、劳动力短缺,因此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任何身体健康的人不需要依靠国家福利就能保证基本生活。这也导致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后,原有部分公共事业部门被大规模私有化,尤其是美国医疗系统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助推了美国医疗成本急剧上升。 社会福利的本质是“救急不救穷”。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逐渐开始建立社会福利体制,林登·约翰逊总统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但美国并未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奥巴马上台后,民主党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了社会福利覆盖范围。据美国专门研究医疗保险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家庭”(Families USA)统计,目前有1/5的美国人使用医疗补助保险,医疗补助保险本应该是维护美国贫困家庭稳定的基本保障,然而每一个州都出现骗保情况。(36)此外,1/6的美国人依靠“食品券”生活,而“食品券”由联邦财政负担。(37)由于联邦制的结构,地方政府为了加速本地零售业发展,甚至鼓励本地居民申请“粮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 民主党支持的扩大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美国保守主义传统。“茶党”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奥巴马医改引发的税收争议。保守主义者越来越对美国走向福利国家(或保守主义者称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担忧。同时,因反恐需要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因“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的对本国公民大规模监听丑闻、奥巴马政府在控枪问题上的支持态度,以及长期的“政治正确”而无法自由表达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让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者感觉来自联邦过于强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联邦权力已经损害了美国人民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对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对民主党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抗衡能力非常失望。 美国政治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在联邦层面,两党政治极化引发的党争不断加剧;但在社会层面,保守主义者却认为共和党无力抗衡民主党。这种现状的本质是党派利益纷争忽略了来自于民间尤其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需求,因此特朗普变成了一匹黑马。他代表了一批曾经支持共和党,但又对共和党相当失望的保守主义群体。无论特朗普是否能够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或者能否赢得总统大选,其本身已经成为共和党衰落的标志。现代美国的核心问题是民主被党争利用,麦迪逊式的民主制成为激化党争的体制根源。 此外,正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争论美国是否“衰落”一样,仅仅就美国民主发展本身,很难简单定义美国民主体制是否“衰败”。是否“衰败”不完全取决于美国民主本身的发展,更取决于其他非民主国家或者民主程度不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民主理论通常将民主与富裕、民主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尤其是在2008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美国陷入金融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反而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时对其出手相助。这种不同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在一定程度上修订了民主理论的常识。这也引起了对西方民主的反思。 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主转型中,俄国民主化走向了“竞争性威权体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则重回专制体制;“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北非彻底陷入前所未有的内战分裂与极端宗教主义统治之中;美国麦迪逊式的共和体制在全球化时代陷入公共治理困境。这三种类型的民主困境分别代表了民主与民主化、民主与民主巩固、民主体制与现代公共治理所面临的矛盾。民主是民主化的目标,民主化是实现民主体制的过程;民主体制是一种非常精致且需要随时调整的政治体制。民主巩固需要国家建构先于民主体制建立,只有如此,才能够为民主体制奠定基本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基础,否则,国家很容易陷入混乱,进而导致国家分裂和国家失败,甚至出现内战或超越极权体制的极端宗教统治。 麦迪逊式共和体制在设计之初就为政治极化埋下种子。冷战后美国缺乏外部军事威胁,由此导致国内政治优先于外交政策,民主的低效率导致重大公共议题争吵不断。而当美国两党政治极化不断加剧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在快速发展,从而引发了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争论。如中国的成就是依靠威权主义,还是从过去高度集权模式向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平衡点转换的结果?事实上,民主制度本身与发展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富裕国家通常是民主国家,不是因为民主体制是专制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民主体制更容易在富裕社会中生存。(38)当代美国政治极化并非是由民主体制“衰败”引起的,其在本质上是传统的麦迪逊式权力制衡原则与现代更为复杂的公共治理之间的矛盾,从而在现实中出现了走回亨廷顿式“强政府与有效治理论”的趋势。 笔者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任何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Michael McF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World Politics,Vol.54,No.2,2002,p.212. ②Robert 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2. ③Adam Przeworski,et al.,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16. ④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2,2002,p.51. ⑤Seymour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75. ⑥Seymour Lipset,et al.,“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45,No.2,1993,p.12. ⑦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7. ⑧Guillermo ODonnell,et al.,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M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Scott Mainwaring,et al.,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2; and Yossi Shain and Juan Linz,Between States: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⑨Dietrich Rueschemeyer,et al.,Capitalist,Development,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47. ⑩Richard Rose and DohChull Shin,“Democratization Backwards:The Problem of Third-Wave Democracies,”p.338. (11)Michael McF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World Politics,Vol.54,No.2,2002,p.212. (12)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No.2,2002,p.51. (13)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p.52. (14)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15)Laurence Whitehea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 (16)Anthony Butler,Democracy and Apartheid:Political Theory,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Modern South African Stat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8,p.98. (17)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1. (1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3页。 (19)Hamilton,Madison and Jay,The Federalist Pap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41. (20)Ibid.,p.13. (21)Richard Stillman,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epts and Cases,7th edition,Wadsworth Publishing,1999,p.445. (22)Larry Gaines and Victor Kappeler,Policing in America,7th edition,MA:Elsevier,Inc,2011,p.21. (2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第458页。 (24)Richard Stillman,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epts and Cases,p.9. (25)美国医疗补助系统(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财政共同负担。 (26)[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毛俊杰译,第447页。 (27)同上书,第449-450页。 (28)APSA Task Force Report,“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Perspectives on Politics,December 2004,Vol.2,No.4,转引自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29)同上。 (30)[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毛俊杰译,第460页。 (31)CNN,“U.S.Tax Revenue at Record High,Whos Paying,”http://money.cnn.com/2015/08/14/news/economy/us-government-taxes-record/index.html,2016-04-08. (32)Romina Boccia,“Federal Spending by the Numbers,2014,”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4/12/federal-spending-by-the-numbers-2014,2016-04-08. (33)Jonathan House,“Budget Deficit Returns to Prerecession Levels,”http://www.wsj.com/articles/u-s-budget-deficit-in-2014-narrows-to-lowest-level-in-six-years-1413385493,2016-04-08. (34)[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35)[美]查尔斯·默里:《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出现的社会根源》,http://cn.wsj.com/gb/20160219/opn155639.asp,2016-03-20。 (36)Elizabeth Hagan,“Medicaid Suspension Policies for Incarcerated People:50-State Map,”http://familiesusa.org/product/medicaid-suspension-policies-incarcerated-people-50-state-map,2016-03-20. (37)“食品券”(Food Stamp)是联邦政府为保证低收入家庭或个人提供的一种食物补助,使用者申请到这种食物补助后,用联邦政府给的一种电子购物卡就可以去指定的超市购买指定的食物,以保证基本生活。 (38)Adam Przeworski,et al,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37.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医疗体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中产阶级论文; 联邦政府论文; 医疗论文; 联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