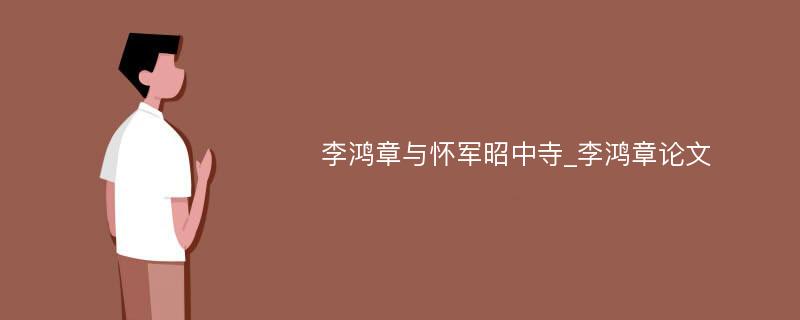
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鸿章论文,淮军昭忠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71—12
淮军是19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一支军事力量,在近代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参加对外反侵略战争及安定国内、筹备海防的过程中,淮军及淮系集团成员有数以千计的官将兵丁死于战场或积劳病故于任所,清政府对他们实行的褒扬祀典制度,除去遵循惯例外,并允许建立了数处淮军昭忠祠。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淮军昭忠祠制度并未引起重视,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将叙述晚清淮军昭忠祠的修建、建筑特色、管理制度、祀典制度及兴衰过程,以期对淮军昭忠祠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背景和目的
淮军的总首领是李鸿章。这支军队于同治元年(1862)在安徽组建成军后,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主要驻扎于直隶各地及山东、奉天沿海地区,成为拱卫京师、防守海疆的重要力量及北洋海军的官兵来源,后来又参加了保卫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抵抗八国联军之役,成为继湘军之后和清末新军兴起之前40年间承前启后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长期转战各地、参加国内外战争及守卫海疆的过程中,淮军有大批将领兵丁战死于沙场或积劳病故。为了褒扬、祭祀这些将领兵丁,同治三年(1864)湘军刚刚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李鸿章即奏请清政府修建无锡淮军昭忠祠,以后又不断地在各地修建淮军昭忠祠。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之所以热衷于修建淮军昭忠祠,其背景及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从清代祀典制度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遵奉了清政府表彰阵亡及积劳病故将士的定例,从思想观念上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服务的。昭忠祠制度是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所首创的祭祀制度,主要祭祀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官员将领及八旗兵丁。根据清代礼制,昭忠祠制度属“群祀”之一种①,被祭祀的人员分为正祀、袝祀。正祀一般祭祀官吏将领,袝祀(附祀)一般祭祀兵丁。雍正帝在雍正二年修建京师昭忠祠的上谕中指出:“朕惟《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烝,祭法曰:以死勤事则祀之,凡以崇德报功,风励忠节也。”自太祖以来,特别是圣祖在征讨三藩之乱、平定西藏、统一台湾等战争中,“虽天戈所指,如疾风振槁,而师旅之臣,捐躯马革,及守土之官,见危授命者,所在多有。……将士奋勇前驱,亦有殁于行阵者,此皆尽忠报国之臣,朕甚佳之,亦甚悯之。当于京城建立祠庙,春秋妥侑。其偏裨士卒,力战敌忾,舍生取义者,亦附列左右,用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②。京师昭忠祠亦称敕建昭忠祠,建祠地址选在崇文门内,雍正帝还钦定祠名为“表奖忠勋”,并御书匾额③。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工竣,建成后将雍正帝的御书匾额择吉悬挂,并规定了“将文武诸臣之位,安设正祠,偏将士卒之位,安设两庑”的祭祀规制,其祭祀行礼仪节等,“均与祭贤良祠同”④。其后,嘉庆七年(1802),因剿办川楚白莲教起义,阵亡将领兵丁颇多,京师昭忠祠不能放置众多牌位,嘉庆帝又诏建各直省府城昭忠祠(也称直省昭忠祠),其总体规定是“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其春秋祭品仪节,与直省祭贤良祠同”⑤。后来又允许修建特殊地区或特殊军事组织的昭忠祠。清政府对京师昭忠祠的建筑规制、入祀人员神牌的制作、生前的官职品级等也有规定。这些制度和规定,是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主要依据。李鸿章在他的奏摺中也表明修建淮军昭忠祠是为了“以彰恤典而尉忠魂”⑥;张树声在《请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也讲明在苏州建立淮军昭忠祠是为了“称朝廷励节褒忠之典”、“慰斯民报功崇德之心”⑦。由此可知,修建各地淮军昭忠祠,目的之一是为了表彰淮军在征战中战死的将士,为后来者树立榜样,使人们更进一步效忠于清王朝。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及其它昭忠祠的修建,是淮军修建昭忠祠的现实依据。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曾谕令,待江西湖口石钟山湘军水师昭忠祠工竣之后,“即著各该地方官,照各府昭忠祠之例,春秋致祭,以褒忠节”;曾国藩等在湖南湘乡捐赀倡建忠义总祠,清政府也“准其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⑧。其后,曾国藩又捐建湖南平江忠义祠,在江宁城内建立昭忠祠,“专祀湖南水陆各军阵亡员弁”,并建立江宁官绅昭忠祠⑨,清政府均予以允准。这些事例,都为李鸿章提供了具体和现实的依据,使他认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阵亡的员弁兵勇“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⑩。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也表明:“拟仿湘乡县及洞庭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11)。
第三,淮军将领的要求,是促使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重要推动力。从社会风俗来讲,中国的习俗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与祭祀,对战死忠魂更应妥善祭祀与慰藉。如果条件许可,应尽可能将死于外地的人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军队将士死于征战之中的异地他乡,属于孤魂野鬼,其尸骨应得到妥善安葬,其魂灵也应得到适当、长期的祭祀,以使其不至于在冥间有“衣食之虞”,其魂灵也有固定之所,不至于到处游荡,或为害阳世生灵。李鸿章及淮军将领们对此也非常重视。淮军在各地征战的过程中,不可能将战死将士“马革裹尸”,魂归故土。太平天国及捻军平定之后,淮军将领要求在各地修建昭忠祠。早在同治八年(1869),淮军将领刘盛瑺胞兄刘东堂“以升用道候补知府需次鄂省,购义地于永隆河掩埋忠骨,倡义建淮军昭忠祠”(12)。同治十二年(1873),盛军即在直隶青县马厂购置民田,作为义冢,后又提出为盛军建祠,“妥侑已故弁勇”。盛军将领周盛传在上李鸿章的《盛军建祠请奏禀》中不无伤感地说:盛军弁勇“随征驻防先后二十余载,积劳病殁,归骨无期,情事至为可悯”(13)。其后,盛军将领周盛波又提出在保定建立淮军昭忠祠。李鸿章提出修建巢湖淮军昭忠祠,也是在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等人的联名呈请之下促成的(14)。对淮军将领的这些要求,李鸿章也颇有同感,他也曾非常伤感地回忆自军兴以来,“淮军将士之捐躯命而膏原野者亦较众,其得裹尸而葬与夫闻于朝而与于昭忠之祀者,盖千百之一而已,予愀然伤之”(15)。李鸿章在《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也指出,修建保定昭忠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庶足妥侑毅魄,激劝方来”(16);在《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中,他指出捐建巢湖淮军昭忠祠的目的是“用申报飨,庶以妥侑毅魄,昭示来兹”(17)。这些都表明,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既是为了遵从民间风俗习惯,也是李鸿章顺应淮军将领的要求,使为国捐躯者得到应有的祭祀,使生者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
第四,从政治上来讲,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是为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地位服务的。李鸿章与淮军及淮军将领是休戚相关、不可分离的。李鸿章因有淮军这支武装以自重和显荣,淮军将士也因有李鸿章这个总首领而得到生前的荣誉地位及身后的褒谥祭典。就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登高一呼,部下群起响应,在淮军的兴起之地、转战之区和管辖之所修建昭忠祠、义阡享堂、公所、会馆,并编修《昭忠录》,为部下撰写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在他的光绪年间的奏稿以及《光绪朝硃批奏摺》中,保留着不少他为淮军旧部请求死后恤典、修建专祠、袝祀淮军昭忠祠、国史馆立传、封妻荫子的奏摺(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来强化淮系集团内部及后代的乡土意识、宗族观念及地域情结,提高他们对自己的感恩戴德意识和崇拜之心,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来进一步维系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淮系集团影响力,并不断发展、更新淮系集团的势力。在同治十一年他所写的《安徽义阡享堂记》中即表明了这种意愿。他指出,“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则生之聚也益坚”,他引用管子“轨里连乡之制”的思想,认为“使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祭祀同福,死葬同恤,此其平日之相恤也”,“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则军法在其中矣”,“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莫之能御,则所及者远矣。后世召募乡勇,殆师其遗意焉。粤、捻之兴,扰乱徧南北,治之者曰楚军,曰淮军,皆用乡人以治四方之事。”之所以在直隶省城保定购地建安徽义阡享堂,实为祭祀淮军将士,“今义阡之设,推古人族葬之法,以联乡里之情;而享堂之设,又推国家昭忠之意,以慰英毅之魄。……予既重乡人之笃谊,又伤夫将士之致命,遂志而不及见大功之成也,为之记,以志予慨。”(18) 李鸿章主持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在这篇文字中已表露无遗。总之,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不但向世人展示了李鸿章及淮军政治力量的存在,也反映出李鸿章与淮军旧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是李鸿章登上政治巅峰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各地淮军昭忠祠的兴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章及其他淮军首领根据清代祀典制度和湘军先例,先后奏请清政府允淮,在淮军的征战之地和主要活动地区,建立过以下几所淮军昭忠祠。
最早的淮军昭忠祠是同治三年十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清政府,由淮军公议捐助饷银,在江苏无锡县城外惠泉山麓天下第二泉之侧修建的惠山昭忠祠。李鸿章在奏片中称:淮军自同治元年组建以来,“迄今两载有余,肃清苏省,兼复浙境,计先后大小数百仗,……所有阵亡员弁兵勇,其约数千人,例应于各府城暨阵亡地方建立昭忠祠,设位致祭。惟分地建祠,经费无措。查无锡县城外惠泉山介在苏、常之间,上年进剿锡城,与忠、侍大股相持数月,鏖战尤苦,死事尤众。其地素号名胜,自被贼扰,绀宇琳宫悉成瓦砾,兴复无期”,故选址于此,“查明历次阵亡员弁兵勇,分别设位,由地方官春秋致祭”(19)。清政府于十一月初二日允李鸿章此奏之后,淮军即捐资并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在原惠山寺的废墟上修建了惠山昭忠祠。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惠山昭忠祠也称淮湘昭忠祠(20)。辛亥革命后,惠山昭忠祠改为“忠烈祠”(21)。
第二所淮军昭忠祠是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后修建的武昌淮军昭忠祠。武昌淮军昭忠祠位于湖北江夏县(今武昌县)保安门内墩子湖旁,祠内祭祀百余阵亡的淮军将领、湖北地方官及淮军兵丁等(22)。
第三所淮军昭忠祠是同治十三年(1874)在江苏苏州修建的苏州淮军昭忠祠。湘淮军将士死于平吴之役及闽浙粤东者,原来曾入祀于苏州昭忠祠(23)。约同治十三年正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淮军宿将张树声领衔,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经羲联衔向清廷上《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奏摺中讲明苏郡绅士冯桂芬、潘遵祁等呈请在苏州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阵亡的程学启等淮军将领兵丁建立昭忠祠。在此之前,苏州虽已为程学启建立专祠,但阵亡于江苏的淮军将士未能附入,出师他省并捐躯殒命的淮军将士也没有祠祀祭典,“既无以称朝廷励节褒忠之典,亦无以慰斯民报功崇德之心”,因而呈请在程学启专祠之西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一所,并请奏列祀典,归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昭慎重而垂久远”,所需工费已由李鸿章与周盛传、吴长庆、刘盛藻等相商,由淮军公助银两,“以伸袍泽之谊,毋烦绅民筹措”(24)。此奏摺于正月十三得到清廷允准后,淮军即在苏州南显子巷程学启专祠之西(民国属元和县境)修建了苏州淮军昭忠祠。
第四所淮军昭忠祠是刘铭传在台北修建的淮楚昭忠祠。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1885年9月6日),淮军宿将、台湾巡抚刘铭传向清廷上《请恤战死将士建昭忠祠摺》,奏摺中说,淮、楚军在台湾战守经年,据查死事员弁已达1600余人,他们或杀敌致果,临阵捐躯,或伤重殒身,或积劳病故,“均属戮力疆场,殁于王事,……迹其忠烈,实足哀矜。生既莫邀懋赏之荣,死宜共沐褒崇之典”,请求在台北府城建立淮楚昭忠祠一所,“将基沪经年战守以死勤事各员弁列祀祠中,官为致祭,以彰忠荩而肃观瞻。如蒙俞允,其列祀员名、建祠经费再由臣等妥筹,以彰圣明激善褒忠之至意”,清廷同意刘铭传所请,刘即在台北修建了淮楚昭忠祠(25)。
第五所淮军昭忠祠即保定淮军昭忠祠。保定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源于淮军在保定建成义阡享堂和盛军统领、湖南提督周盛波等人的要求。就任直隶总督之后,李鸿章有感于自军兴以来,淮军将士在各地捐躯命于原野而不能裹尸还葬,亦不能享受朝廷昭忠之祀,“予愀然伤之”,遂用安徽同乡人捐输银两,命候补道叶伯英、总兵叶志超在保定城西土桥邨卜得一块44亩风水之地,“缭以周垣为享堂,以祀淮军将士之死事者,为屋以停旅榇之可归者”。义阡享堂于同治十一年落成,李鸿章并写了《安徽义阡享堂记》以记其事(26)。同治十二年,周盛传也在青县马厂附近购置民田,作为盛军义地,后又提出在此地为盛军积劳病殁的将士捐建祠宇,“妥侑已故弁勇”(27)。周盛传病逝后,周盛波又重提此事。淮军将士的要求,促使李鸿章决定在保定修建淮军昭忠祠。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初十日,李鸿章向清廷上《保定请建昭忠祠片》,申明自同治四年(1865)淮军北上平捻,“方事之殷,将士日驰百数十里,不得一饱;夜即枕戈露宿,或竟疾趋达旦。祁寒暑雨,未能少休。仰仗国威,歼平巨寇,而良将猛士锋镝疾疫死亡已多”,后来办理海防,拱卫畿疆,仍多淮部,请求在省城保定由淮军将士集资捐建昭忠祠,以祭祀淮军北上平捻和后来防守海疆中战死及积劳病故的将士,“凡阵亡伤病文武员弁兵勇分别正祀袝祀依次列入”(28)。得到清政府允准后,李鸿章派盛军将领卫汝贵(字达三)、贾起胜(字制坛)回省城保定,选定保定旧城西南隅的原西大寺附近基址,李鸿章及淮军主要将领大力捐款,其中李鸿章独自捐银15000两,刘盛休、周盛波、周馥、叶志超等也各捐银3000两到50两不等,总计有64位淮军将领等共捐银55000余两(29),然后动工修建,光绪十七年(1891)竣工,这座昭忠祠定名为保定淮军昭忠祠暨公所,习惯上称为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
第六所淮军昭忠祠是建于安徽巢湖的巢湖淮军昭忠祠。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李鸿章根据统领武毅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的联名请求,向清廷上《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表明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和淮军将士的故乡,自淮军创建之后,“戡定全吴,肃清二捻,战伐之迹遍于浙闽江皖鄂豫直东各省”,“迄今拱卫畿疆,东至营青,南迄闽广,屹为海防得力之师”,但“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祠祀至今缺然”,“庐州为各将士故乡,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捍卫之绩,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长往不返,岁时霜露,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祀,而本郡独无”,请求仿湘乡县及洞庭湖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府城东南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30)。清廷允准之后开始兴建,祠成之时,李鸿章特命安徽桐城派名士吴汝纶为之作记,吴汝纶即作《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回顾了清代军制的变革及淮军的兴起,以及清代昭忠祠制度之起源、淮军昭忠祠的兴建等(31)。
第七所淮军昭忠祠是光绪十八年后在天津修建的天津淮军昭忠祠。当时,北洋海防事务次第举办,淮军将领议建天津海防公所,后复议增建淮军昭忠祠于内,“以祀淮军积劳病故诸将士”,到光绪二十一年工程基本结束,“详请北洋大臣衙门立案”(32)。天津淮军昭忠祠在金刚桥北岸迤西。与前几所淮军昭忠祠不同的是,这一昭忠祠可能未经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天津淮军昭忠祠应是淮军所建的最后一处也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淮军昭忠祠。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病逝后,由周学熙主持,“就天津金刚桥北岸迤西,原建淮军昭忠祠基址,庀材鸠工,营建专祠”,即李文忠公祠,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正式建成,“迎主入祠”,直督袁世凯并上奏清政府(33)。原天津淮军昭忠祠即后来的李文忠公祠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天津市第33中学即其旧址之一部(34)。
还应提及的是,其一,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铭军士兵袁定邦战死后,即“祀铭军昭忠祠”(35)。铭军昭忠祠于何时建于何地?与淮军昭忠祠有何关系及不同?尚待查考。其二,据周盛传叙述,盛军在移防直隶青县之后,曾在同治十二年前后修建盛军弁勇昭忠祠(36)。其三,据《清史稿》记载,“苏州、武昌、保定、庐州、巢湖、济南、无锡各地淮军,使凡转战糜躯者,莫不馨香而食,其为昭忠一也”(37)。如果此记载无误,淮军除修建以上七处昭忠祠外,还应在庐州、济南各建昭忠祠一座。雍正之后,安徽庐州府辖合肥、庐江、舒城、巢县和无为州,笔者查阅了光绪年间《续修庐州府志》、《重修安徽通志》、《续修舒城县志》,民国《安徽通志稿》,以及新版《合肥市志》等地方志,均无庐州淮军昭忠祠的记载。仔细分析李鸿章的《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及吴汝纶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则可发现,李鸿章在此摺中称,“各省皆有祠祀,而本郡独无”(38)。吴汝纶在文中记载“合肥则淮军本所自起,祀典不可阙也,今奏立昭忠祠巢湖脽上”(39)。由他们的记载可知,在巢湖淮军昭忠祠建成之前,淮军未在安徽及庐州修建过昭忠祠。巢湖淮军昭忠祠大约建成于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1893),此后一两年即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战后,从政治声望、地位和时间、财力等方面来考察,淮军和李鸿章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求在庐州境内建立另一所淮军昭忠祠。1901年李鸿章辞世后,更不可能有其他淮系人员提出修建庐州淮军昭忠祠。吴汝纶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文章标题即将这座昭忠祠称为“合肥淮军昭忠祠”,而李鸿章的奏摺则将其称为“巢湖淮军昭忠祠”,由此看来,合肥、巢湖淮军昭忠祠应为一处,名称可以互用。总之,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分析,淮军不可能在晚清时期于庐州府境内建有另一处昭忠祠。至于济南,笔者查阅了晚清、民国山东有关地方志包括吴树梅修《续修历城县志》、杨士骧修《山东通志》等,这些地方志有关于淮军将领李鸿章、周盛波、周盛传专祠及济南两处昭忠祠的记载,但无淮军昭忠祠的记载(40)。在没有查找到相关历史材料的情况下,笔者对济南是否建有淮军昭忠祠这一问题暂时存疑。
三、各地淮军昭忠祠的选址与建筑特色
李鸿章与淮军在各地修建的淮军昭忠祠,从选址、建筑特色等方面考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各地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选择在风水较佳或旧庙宇的基址上。根据中国民间习俗和风水观念,昭忠祠属于祭祀型建筑,在风水学上属于虚空的、精神上的,具有阴性场气,这类建筑应选择在远离居住区的较为幽静的场所,基址不要太高,特别是不要修建在高于一般居民房屋的基址和环境,以免以阴压阳(41);最好选择在旧庙宇的基址或周围有祭祀型建筑的环境,这样有利于超度亡魂。各地淮军昭忠祠的选址基本上体现了这些观念。如无锡淮军昭忠祠修建在无锡县城外惠泉山麓天下第二泉之侧,坐落于著名的惠山寺的基址之上,惠山寺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仅存寺门匾额”,淮军即于同治四年在原“惠山寺”的废墟上修建了惠山昭忠祠(42)。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惠山昭忠祠即淮湘昭忠祠“在惠山寺内,割寺之大雄殿以后至大悲阁止,旁及竹罏山房遗址为之”(43)。惠山昭忠祠的选址可以说占据了风水之地。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坐落于保定城西南角,西南属坤位,该处也是庙宇(西大寺)故址,西北侧是三皇庙,北侧有清河道署、育婴堂、清苑县治所,附近并有护城河及荷花塘、环境幽静,与无锡淮军昭忠祠一样,是超度亡魂的理想之地(44)。巢湖淮军昭忠祠则建在巢湖中庙隙地,坐北朝南,附近有著名的中庙(又称忠庙,此前由李鸿章捐修),南面为碧波万顷的巢湖,并与巢湖小岛上的圣姥庙隔湖相望,更是风水极佳之地(45)。当然,淮军昭忠祠能选择这样好的基址,与李鸿章的权势和淮军当时的威名是分不开的。
第二,从建筑规制来讲,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遵循清政府的定制。京师昭忠祠的规制较高,为“正门五间,左右门各一,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正室七间,……后正屋五间”,并有祭器库、宰牲房、治牲所等附属建筑(46)。各地府城昭忠祠的定制是“盖屋三楹”(47)。以保定淮军昭忠祠而论,其建筑格局为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总祠(正室)七间(正房三间,左右耳房各两间),这些都没有超过规制。
第三,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采用徽式建筑形式和风格,体现出徽派建筑特色。以保定淮军昭忠祠为例,她堪称近代北方地区徽派建筑艺术之精品。徽派建筑讲究风水、空间、结构、马头墙、雕刻之美(48),这些在保定淮军昭忠祠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从建筑空间来讲,大门及外部空间为错落有致、青砖灰瓦砌成的优美的马头墙,“可起到围隔空间、使之自成门户体系的作用”(41),马头墙与防火道相隔,既利用了空间,又美丽壮观;二门房脊使用北方少见的透风脊,给人以新鲜之感;内部空间以走廊、门厅式过道相通,给人以舒展之感;戏楼是徽派建筑中的祠堂、会馆不可或缺的建筑物,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戏楼,作为整座建筑群的主要建筑物,将昭忠祠与祠堂、公所与会馆的戏楼合二为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打破了京师昭忠祠等祭祀型建筑不设戏楼的常规,使其更具有地方性特色和娱乐、祭祀功能;将昭忠祠与公所合二而一,建在一处,也为首创,使之既便于管理,又方便祭祀;整座建筑群随处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尽显徽派建筑的“三雕”之美,加上戏楼大量的彩绘,更使身临其境的人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第四,淮军昭忠祠的有关碑刻等文字材料也出自淮系集团成员之手。截至目前,笔者只发现了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及安徽巢湖淮军昭忠祠的部分碑刻等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均出自淮系集团成员之手。如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总祠、大祠、戏台、公所的楹联及戏楼匾均出自李鸿章的幕僚、安徽桐城派名士吴汝纶之手(50),在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进院落西厢房的西廊壁上至今保存完好的名为《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的碑刻,也是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建成后,光绪十七年七月由保定营务处会同淮军各统领公议,经李鸿章批准后,同年十月刻石于此(51)。安徽巢湖淮军昭忠祠建成之后,李鸿章命吴汝纶为之作记,吴汝纶即作《合肥淮军昭忠祠记》,“汝纶则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俾后之谋国者有考焉”,该长文回顾了清代军制的变革及昭忠祠制度之源起,对李鸿章及淮军学习西方、因时而变并能立于不败之地等加以颂扬(52)。
四、淮军昭忠祠的入祀人员及祭祀制度
各地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时间虽然不同,建筑风格也会有所区别,具体入祀人员也因地区、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对入祀人员的品级规定、入祀类别、祭祀制度等应是相同的。各地淮军昭忠祠都遵照京师昭忠祠的规制,实行列祀、袝祀制度。列祀也称正祀,是淮军昭忠祠祭祀仪式中享受最高标准的原淮军将领,这些将领在同治元年至八年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阵亡病故,或此后死于战阵,他们的神牌尺寸较大,被安放于昭忠祠的显著位置以供祭祀。袝祀也记为附祀,是昭忠祠祭祀制度中较低的一种,一般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中阵亡病故的淮军下级将领和士兵,以及同治八年后经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允准附祀的非阵亡的淮军将领。
首先,各地淮军昭忠祠的列祀(正祀)人员都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有的保存在要求建祠的奏摺中,有的保存在昭忠祠建成后的碑刻或其它材料中。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及考证,现将各处淮军昭忠祠的入祀情况简述于下。
无锡惠山昭忠祠。根据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可知,惠山昭忠祠应主要祭祀“肃清苏省,兼复浙境”的淮、湘军中的“所有阵亡员弁兵勇,其约数千人”(53),《无锡金匮县志》则记载为“祀淮湘诸军克复江苏全省阵亡将士”(54)。这两条记载稍有不同,按一般常识,无锡昭忠祠应主要祭祀在江浙一带与太平军交战时阵亡病故的淮军、湘军将士。这里所称的湘军将士,即李鸿章组建淮军时,曾国藩从湘军中拨给李鸿章的数营兵员,实际上他们也应属于淮军。在这所昭忠祠列祀的淮军将领,应包括《昭忠录》卷一至卷四“湘淮将士传”所有的将领,其中较重要者有程学启、张遇春、何安泰、陈忠德、江福山、赖荣光、韩正国、潘承恩、张行科、尹连升等(55)。另外,孙益孝(56)、徐万银、苏得胜(57)、石胆成、胡永泰、许成宗(58) 等也应列祀于此。
苏州淮军昭忠祠的列祀标准即张树声奏摺中所称“凡淮军统将奉旨建立专祠者列于正祀,各部将士以次附祀”(59),《苏州府志》则记载为“祀淮军东征殁于王事者”(60)。根据这些记载,程学启、张树珊、唐殿魁、刘朝煦(61)、刘克仁(62)、张遇春、何安泰(63) 等应列祀于此。
武昌淮军昭忠祠主要祭祀淮军平捻时死于湖北境内的淮军将士,包括正祀张树珊、唐殿魁,记名提督吴宗国、雷仁美、郑海鳌,记名总兵谢连升,副将郭芳鉁;左祀湖北督粮道、安徽桐城人徐丰玉,黄州知府金云门,以及地方官员李公榞、俞舜卿、何开泰、胡文烺、朱开泰;右祀副将龚兴祖等46人;又左祀副将柏云章等;又右祀副将余春华等68人;其左右厢祀黑龙江甲兵及勋字营、铭字营、树字营等淮军兵丁(64)。值得注意的是,徐丰玉、何开泰并非淮军将领,而是安徽籍湖北地方官,咸丰三年后在湖北与太平军交战时自杀身死或战死(65),但也入祀于淮军昭忠祠,另外五名地方官员也能入祀,这说明,有些特殊人员能入祀于淮军昭忠祠。
保定淮军昭忠祠是重要的淮军昭忠祠,与其它淮军昭忠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淮军处于鼎盛时期修建的,人祀人员要多于其它淮军昭忠祠。保定淮军昭忠祠未保留入祀人员名单,这给研究带来了难度。李鸿章于光绪十四年五月向清廷上《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指出,设立此处淮军昭忠祠是为了列祀同治四年以后淮军在直隶、山东等地平捻阵亡及积劳病故的将领,并附祀后来防海而伤亡病故的将士。光绪十七年昭忠祠建成后,在《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中更明确规定,这所昭忠祠“奏明列祀自同治四年以后淮军剿捻阵亡、伤故将士;同治九年以后分调淮军来接海防,间有在北洋积劳病故人祠拊祀者,因其先在淮军著有劳绩,是以奏明柑祀。其余北洋各营未与剿捻之役者,虽在海防积劳病故,如非奏明有案,不得拊祀,以清界限而符原奏。”(66)根据这一标准考证,保定淮军昭忠祠列祀的淮军将领应当有:记名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唐殿魁、副将刘登朝、郭有容(67)、湖南提督杨鼎勋(68)、记名提督陈振邦、总兵衔副将刘正同、游击衔都司鲁朝斌(69)、提督衔记名总兵方有道(70)、记名总兵张遵道(71)、记名提督胡良作(72)、记名总兵胡家让(73)、副将加总兵衔周行发(74)、提督衔胡克让(75)、总兵程广和(76)、总兵衔副将尹昌景和副将龚兴祖(77)、总兵衔副将郭文武、副将姚长庚、曾文益(78)、提督曹仁美、总兵谢连升、王定祥、袁光明、记名提督吴宗国(79)、五品衔江苏候补知县黄振楚、副将刘斌等(80)。提督刘盛璋于同治八年“率兵驻防直东,卒于军”(81),他也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总兵衔张佩芝“历剿发捻有功……同治十二年在营伤发病故”,李鸿章“奏请旌恤”(82),他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另外,甲午战争及反对八国联军战争中捐躯的淮军将领戴宗骞、周盛忠、聂士成等也应列祀于保定、天津淮军昭忠祠。
巢湖淮军昭忠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建于淮军的创始之地和淮军将士的故乡,根据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所叙述的淮军转战南北各省的情况来分析,这里应是各处淮军昭忠祠的总汇,即列祀、袝祀于其它淮军昭忠祠的淮军将士,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同的祭祀。至于天津、台北淮军昭忠祠的入祀情况,限于篇幅,不予叙述。
其次,各地淮军昭忠祠的袝祀人员。清政府关于京师及各地昭忠祠的袝祀制度的规定是“其偏裨士卒,力战敌忾,舍生取义者,亦附列左右”,“偏将士卒之位,安设两庑”,“兵丁等位,于两旁群房内作五层安设”(83)。在各地府城昭忠祠,“各省驻防兵丁出师阵亡,准于驻防省分之昭忠祠内设牌袝祀,其牌位列于绿营兵丁之上”,“兵丁安设两旁”,“如同府兵丁人数众多,则相度祠屋之宽狭,酌量人数之多寡,或百人或数十人合一牌位,镌刻名姓,设于龛案致祭”(84)。淮军昭忠祠与各地府城昭忠祠的规定基本相同。苏州淮军昭忠祠所称“各部将士以次附祀”即指兵丁,武昌淮军昭忠祠“其左右厢祀黑龙江甲兵及勋字营、铭字营、树字营等淮军兵丁”也属附祀(85)。保定淮军昭忠祠袝祀的淮军将士,其必备条件一是参加过平捻之役阵亡的兵丁,二是参加过平捻,同治九年以后参加过防守海疆的官员及将领。对于北洋各营未参加平捻之役,但在海防积劳病故,如经奏明有案,亦可袝祀。符合以上条件的淮军将领,包括刘铭传、李昭庆、吴长庆、周盛波、周盛传、唐定奎等。一般地说,淮军将领必须由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后方能袝祀。据笔者察考,这样的人员,包括赵长发、李胜、吴毓芬、徐道奎,他们都由李鸿章奏请清廷,可以袝祀于保定及各省淮军昭忠祠(86),郑国魁可以袝祀于苏州程学启专祠及无锡、庐州、直隶淮军昭忠祠(87),阮炳福“附祀程学启专祠、淮军昭忠祠”(88),遇缺题奏提督江西南赣镇总兵王永胜附祀于苏州淮军昭忠祠(89)。徐文达、张树屏经奏准亦可附祀各省淮军昭忠祠(90),潘鼎新、刘瑞芬附祀于淮军昭忠祠(91),并非出身于淮军的提督衔记名总兵刘祺也可以“附祀淮军昭忠祠”(92)。
除以上淮军将领外,丁寿昌、吴毓兰、黄桂兰、朱焕明、苏得胜、吴育仁(93)、戴春林(94),以及丁德昌、骆国忠、郭松林(95)、刘克仁、郑国榜、刘东堂、吴秉权、王德成、张光亮、潘国扬、潘鼎立、王占魁、周志本(96)、宋先聘、李先谟、程守沛、段先春、朱先民、赵延训、程孔德、彭克勤、李大霆(97)、刘盛藻等也应袝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其三,各地淮军昭忠祠入祀人员的神牌制作,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正面各依官职之大小序定位次,兵丁安设两旁”,有官职者每人可以有一神牌,兵丁可以50人合一牌位,镌刻姓名,设龛致祭。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规定,入祠神牌样式,要按照礼部公布的则例、尺寸来制作,以后如有续入袝祀者,由各营查明亡故人员的职衔、营名、籍贯,文移祠中总理知会值年照式制牌。各家不得私自送牌、上龛,更不能任意逾制制造大牌,有乱体制(98),这一制度应适用于各地淮军昭忠祠。
其四,各地淮军昭忠祠的祭祀制度,一是按清代礼制,与江西湖口石钟山水师昭忠祠和湘乡忠义总祠相仿,“照各府昭忠祠之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祭祀仪节“与直省祭贤良祠同”(99)。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所谓“春秋致祭”即“岁以春秋仲月诹吉,遣官致祭”(100),每年二月和八月,选择吉日,由府县官员亲来昭忠祠上香祭祀,被祭祀官将兵丁的亲属亦可参加。京师昭忠祠的祭品为前正殿七案,后正室五案,两庑各三案,附祀兵丁共36案(101),淮军昭忠祠应与此相同,或稍低于此制。二是根据《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的规定,保定淮军昭忠祠的祭祀制度还有淮军同寅及安徽同乡的祭祀,包括春秋二祭及正月团拜,仪式结束后还要观看演剧及饮酒赴筵以联络感情。这种祭祀类似于家族中的祠堂祭祀,更能体现出淮军的地方性和集团性。三是日常的祭祀活动,包括每日早晚香灯、朔望香烛、逢节纸錁贡品等(102)。按照保定淮军昭忠祠的祭祀制度,每日早晚由司祠燃点香灯,每月朔望由总理及正副值年轮流进香,每逢节令要焚烧纸钱、摆设银錁贡品。此外,皖籍人士、入祀人员的家属及其他人员专程或经过保定,也可随时祭祀。这些制度,也应适用于其它淮军昭忠祠。
五、淮军昭忠祠的管理制度
笔者未能掌握各地淮军昭忠祠管理制度的材料,只与黎仁凯教授于十几年前在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进院落西厢房的西廊壁上,发现一通保存完好的名为《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以下简称《章程》)的碑刻,它是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建成后,光绪十七年七月由保定营务处会同淮军各统领公议,经李鸿章批准后,同年十月刻石于此。该章程是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保存下来的重要史料,记载了这座淮军昭忠祠公所的修建情况,规定了淮军将领兵丁列祀袝祀的条件、程序、神牌样式等。根据其记载,可以了解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各种管理制度。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由于建成较晚,规模较大,其制度应较为完备,其它淮军昭忠祠可能没有如此详细、完备的管理制度,但其总体制度应基本相同,由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管理制度可以推测其它淮军昭忠祠的大致的管理制度。
首先,关于祠所的人事管理制度。《章程》第三条规定,昭忠祠公所仿照保定两江会馆章程,设总理一名,由在直隶的安徽籍有文武职分的实缺候补人员且职务较高者中遴选,总管祠所一切事务。设正印二员,佐职二员,称为正副值年,每年秋祭时在安徽同乡候补正佐各员中公议推选,轮流掌印,也可派两江会馆安徽值年或其他人充任。以上人员如补授或署理官职而离开保定,要公议另选接替人员,“毋许私相授受”。新旧人员交接时,要将银钱、帐目、文契、折据等与司祠一起照帐点交,不能稍有亏短(103)。《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总理、值年均有经管银钱之责,有稽查祠事之权”,应公正廉明,如“有徇情挪移、侵蚀冒销等事,应准同乡同寅揭禀,分别撤换罚赔,以重公项而免废弛”(104)。
《章程》第四条规定,除总理、值年外,昭忠祠公所还设司祠一员,“择安徽士人谨愿可靠有家属者充之,祠中一应诸事皆归其经理”,包括对长班夫役的管理,对屋宇、戏楼的检查,对灯彩、陈设的保管收藏,如不胜任,“即由总理、值年辞退另延。如果勤谨将事,秋祭时公议,仍准蝉联接管”。昭忠祠公所另雇长班夫役10名,负责巡更、看门等具体事务(105)。
其次,关于祠所的银钱管理。《章程》第四条规定,祠所每年正月团拜及春秋二祭的祭品、演戏、席资等费每次只准用银200两,“不准多支”。早晚香灯、 朔望香烛、逢节纸錁贡品及窗纸、扫帚等项杂费津钱贰十千文(应为每月)(106)。 第六、七、九、十、十二条规定,祠所岁修经费及司祠、长班夫役的薪水等,经李鸿章批准,由淮军行营银钱所拨湘平银3万两,存天津汇丰银行生息以支付。 不足之数,由盛军在天津小站一带屯垦的五处苇地共6000余亩移交祠所作为永远产业的苇课收入中支付。盛军将领将每年苇课收入银两移解祠中总理、值年时,由值年回明总理公同拆封,择殷实可靠商典寄存,不准私存寓所。需用时由值年书票,凭折支取,同盖图章。所存银钱每月要互相检查,年终时由值年折报总理核明转报,并于正月团拜时,将上年出入各款另具清册,公同查核,张榜祠墙,以便公阅。以上收入如有余款,应提存作本生息。如有额外及紧要用款,要禀请李鸿章核实才准动支。淮军文武各大员参与捐款修建祠所,以后其子弟路过保定入祠致祭,可以查考帐目。如总理、值年紊乱规条,越例徇私,准其揭禀(107)。
第三,关于祠所物品及戏楼、公所的管理。《章程》第十三、十四条规定,祠所内置备的各种器具及铺垫、灯彩等皆载入清册,存于值年和司祠处,并立粉牌悬示祠中,随时查点,以防遗失。如遇公局铺用,司祠应当晚点收,倘或短少,应回明值年查究,如不回明,事后查明由司祠赔偿。祠所一切器物概不外借,如司祠徇私外借,查出立即辞退。凡有喜庆等事借用祠所演剧开筵,要酌收香资一千到八千文,年终时由司祠呈报值年入帐。不准在祠所从事赌钱等事(108)。关于公所,《章程》第五条规定,“祠所后另建屋宇,原为淮军将士致祭时公聚之所,无论外省、皖人、现任、候补及旅游斯土者,概不得租借久住,如有徇情私借私租者,查出议罚。”(109)
第四,关于对保定周围安徽义地的管理。保定附近有四处安徽义地,一是南门外纸坊头20.8亩,为乾隆年间方观承任直督时购置;二是东门外丁家园45亩,为咸丰年间吴廷栋任直隶按察使时与清苑知县丁学易(安徽怀宁人)等购置;三是南门外八里庄124.3亩,为同治年间直隶按察使张树声与周盛波等购置;四是西门外土桥155.3亩,为李鸿章倡率淮军各营陆续捐置。以上四处义地共345.4亩。《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过去义地由两江会馆安徽值年经理,现在由昭忠祠公所正副值年代管。正副值年要按章程管理,用款各归各帐,不能与祠所帐目相混(110)。
六、简短的结论
从最早的无锡淮军昭忠祠到最晚的天津淮军昭忠祠,其修建年代至今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光阴荏苒,人事沧桑。昔日的各地淮军昭忠祠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李鸿章病逝后,保定、天津淮军昭忠祠改为李文忠公祠,其它淮军昭忠祠也各有变迁。据笔者考察,目前保存的尚有保定、天津、苏州、无锡、巢湖淮军昭忠祠。其中巢湖淮军昭忠祠已对外开放,保定淮军昭忠祠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无锡淮军昭忠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各地淮军昭忠祠的兴衰及李鸿章主持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相关史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各地淮军昭忠祠及公所的修建,帮助李鸿章巩固了地位,发展了淮系集团势力。就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一是大量任用淮军人物及皖人以扩充、发展淮系集团势力,盘旋在他周围的人员大半是淮军出身或安徽大小同乡。在《光绪朝硃批奏摺》中,保留着一些李鸿章将在各地候补的淮军将领留在直隶“分别备补”的奏片(111)。据后人回忆,当时合肥城乡民众多有步行二千余里来直隶投效李鸿章者,李鸿章都尽量任用(112)。他自己也承认,“同治中某移督畿辅,僚吏之在官者,将率之在军者,吾郡人为多”(113),后人因而评论他是“任用私人”。二是李鸿章不但为一些属于他管辖范围的淮军病故官员将领要求恤典,而且为不属于他管辖的淮系人员请求赐谥封爵,有时为一人而屡上奏摺。三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以清政府恤典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尽可能地为淮军修建昭忠祠、义阡享堂、公所并编修《昭忠录》,且这些建筑基本上都由李鸿章首倡,由淮系人员捐赀修建。这些作法,一方面反映出李鸿章与淮军上下的非同一般的乡谊隶属关系及淮军的私人性质,内部的上下齐心,一呼百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鸿章的任人唯亲和不辨贤否。正是用这样的手段,使李鸿章达到了巩固自己地位,维系淮系集团利益,发展淮系集团势力的目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李鸿章与淮军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更不否认淮军将士及淮系集团中有作为的人物和爱国者。
其二,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在所有淮军昭忠祠中最具代表性。在晚清,它坐落于直隶总督衙署西南约一华里处,位于保定城内西南角,其西面、西南及南面半华里处是保定府城城墙及护城河,这里环境幽静,是修建祭祀型建筑的极好场所。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是现今各地淮军昭忠祠保存较完好的一处,坐落于今保定市体育场东面,基本上保存着原来的格局,占地面积约40亩,现存保存完好的各类楼堂房廊近百间,约5000平方米。从建筑规制和占地面积来看,此处应是较大的淮军昭忠祠公所。从入祀、袝祀人员之多来讲,根据淮军后期主要在北方活动的事实来分析,这里应是较多的。而且,其管理制度在当时是相当完备的。入祀、袝祀人员有严格的上奏批准制度,管理人员的遴选、任用有一定的规章。从祭祀制度来讲,分为官方的祭祀和内部的日常祭祀,可谓香火很盛。物品、银钱的管理也有严密制度,并有淮军提供正常的经费补贴。更重要的是有李鸿章作为后盾,由此而使昭忠祠香火日盛,公所行旅不断。
其三,淮军昭忠祠可以说是淮军盛衰的历史见证。以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为例,该祠所修建于淮军在北洋各地发展,李鸿章的政治地位扶摇直上之时。淮军的鼎盛时期是19世纪70、80年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淮军驻扎于各地,淮军将领或掌控军队,或出任地方大员,北洋海军又编练成军。此时的保定,从活动场所来讲,既有两江会馆,又有淮军公所。从军政机构、人员来讲,上有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下有一批皖省官吏,还有淮军营务处,包括莲池书院山长吴汝纶亦为皖人,诚可谓淮军及皖人在保定及直隶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数年之后,由于淮军能征惯战的宿将周盛波、周盛传、刘铭传等相继凋谢殆尽,二由于淮军先后败于甲午和庚子,三由于淮军总首领李鸿章的撒手归西,四由于淮军后起将领聂士成等也战死沙场,使淮军失去了政治依托、得力将领及军事实力,完全失去了昔日雄风,基本上已不复成军。李鸿章的病逝和淮军的衰败,也直接影响到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祠所的主要事务失去了决策者,必然使祭祀、管理逐渐废弛。这与杜春和先生所讲的北京安徽会馆在庚子之后,“因遭受侵略者的破坏与失去李鸿章的依助,从而步入衰败时期”的变化如出一辙(114)。
附带需要指出的是,旅游文物部门及学术界应当加强对淮军历史文物的保护与研究。据笔者所知,现在全国尚存的淮军昭忠祠有保定、巢湖、无锡、苏州四处,另有北京安徽会馆等建筑。在这些遗迹中,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产,是研究李鸿章与淮军历史、晚清祀典制度及会馆制度的极好的实物史料。但有些建筑如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虽然早已被确定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保护区内的房屋历经百余年的风雨剥蚀,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由于住户谋生的需要,这些房屋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李鸿章与淮军在近代史上有不光彩的一面,李鸿章更是毁誉歧异、盖棺不能论定的历史人物,但无论如何,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和佼佼者,在近代史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现代的人们不能由于对李鸿章的如何评价而殃及淮军的历史遗迹及近代优秀建筑遗产。应当妥善保护,尽快修缮,早日开放,加强研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近代的历史与祖国优秀的徽派建筑文化。
注释:
① 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祭祀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种。大祀即天坛祭天、地坛祭地、祭祖;中祀即祭日坛、月坛、先农坛,祭孔子庙、关帝庙、文昌帝君、太岁、前代帝王等;群祀即祭群庙和群祠,包括先医庙、火神庙、都城隍庙、东岳庙、龙神祠、龙王庙、仓神庙、贤良祠、昭忠祠、功臣专祠等。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光绪己亥刻本,卷35,“礼部·祠祭清吏司一”。
②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5,《清实录》总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390—391页。
③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光绪戊申年商务印书馆版,卷449,“礼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页。
⑤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⑥⑩ 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卷7,第49页。
⑦ 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1,第5—6页。
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1页。
⑨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2、4页。
(11)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页。
(12)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卷48,“武功传三”,第9页。
(13) 周盛传:《盛军建祠请奏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金陵版,卷9,第8页。
(14)(17)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3—4页。
(15)(18) 李鸿章:《安徽义阡享堂记》,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2册,第9—10页。
(16) 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页。
(19) 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第49页。
(20) 裴大中修、秦缃业纂:《无锡金匮县志》,清光绪辛巳镌版,卷12,“祠祀”,第8页。
(21) 无锡地方志、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2辑,第56页,1984年印刷。
(22) 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民国十年版,志27, “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第14页。
(23) 冯桂芬:《移建昭忠祠碑记》,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清同治刊本,卷36,“坛庙祠宇一”,第8页。
(24) 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卷1,第5—6页。
(25) 刘铭传:《请恤战死将士建昭忠祠摺》,《刘壮肃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卷6,第15页;《清史稿》卷87,“志62·礼6·吉礼6”,中华书局1998年缩印版,第1册,第711页。
(26) 李鸿章:《安徽义阡享堂记》,李国杰编:《合肥李氏三世遗集》,第2册,第9—10页。
(27) 周盛传:《盛军建祠请奏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卷9,第8—9页。
(28) 李鸿章:《保定请建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2,第38—39页。
(29) 捐银材料源自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西路第一进院落东厢墙壁的《建立淮军昭忠祠暨公所捐资文武衔名》碑刻,此碑刻现保存完好,但由于此房间年久失修,极度危险,不能进入,此材料由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原馆长衡志义先生提供。
(30)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4,第3页。
(31)(39) 吴汝纶:《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光绪甲辰刊本,卷2,第34—38、38页。
(32) 沈家本修、徐宗亮纂:《重修天津县志》,清光绪戊戌刊本,卷24,“舆地六·公廨”,第17页。
(33) 袁世凯:《故督臣李鸿章天津专祠请列入祀典片》,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164—1165页。
(34) 王者师:《李鸿章及天津李公祠》,《天津河北文史》第2辑,第13—17页,1988年印刷。
(35)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36,“忠义传二”,第76页。
(36) 周盛传:《本籍敬节育婴义塾牛痘诸堂局恳奏立案禀》,周家驹编:《周武壮公遗书》卷9,第5页。
(37) 《清史稿》卷87,“志62·礼6·吉礼6”,第1册,第713页。
(38)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李鸿章全集·奏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册,卷74,第2112页。
(40) 吴树梅修、张子杰纂:《续修历城县志》,民国十三至十五年铅印本,卷14,“建置考二·坛庙”,第32—33页。
(41) 亢亮、亢羽编著:《风水与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58页。
(42) 《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2辑,第56页。
(43) 裴大中修、秦缃业纂:《无锡金匮县志》卷12,“祠祀”,第8页。
(44) 李逢源修、诸崇俭纂:《清苑县志》,同治十二年版,卷首,“直隶省城图”。
(45) 戴巍光编著:《中国名胜大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46)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己亥刻本,卷58,“工部”。
(4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48) 《参见王明居、王木林:《徽派建筑艺术》,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49) 王明居、王木林:《徽派建筑艺术》第69页。
(50) 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全书·诗集》,“附录联语一卷”,第79页。
(51) 见黎仁凯、傅德元整理:《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载《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8页。
(52) 吴汝纶:《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2,第34—38页。
(53) 李鸿章:《惠山建立昭忠祠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卷7,第49页。
(54) 裴大中修、秦缃业纂:《无锡金匮县志》卷12,“祠祀”,第8页。
(55) 《昭忠录》,清同治苏州忠义局刊行,第1册,卷1—4。
(56)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36,“忠义传二”,第82页。
(57)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38,“忠义传四”,第35页。
(58) 吕林钟修、赵凤诏纂:《续修舒城县志》,清光绪丁未刻本,卷37,“人物志·忠义”,第59页。据沈葆桢修《重修安徽通志》记载,许成宗为“从祀无锡昭忠祠”,见该书卷211,第20页。此处从《续修舒城县志》的记载。
(59) 张树声:《请建淮军昭忠祠摺》,《张靖达公奏议》卷1,第5—6页。
(60) 李铭皖修、冯桂芬纂:《苏州府志》,清同治刊本,卷37,“坛庙祠宇二”,第48页。
(61)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48,“忠义传2”,第89页。
(62)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36,“武功传3”,第5—6页。
(63) 张、何均入祀京师昭忠祠,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0。传记材料参见:《重修安徽通志》卷233,“人物志·武功”,第15页;卷211,“人物志·忠节”,第20页。
(64) 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第14页。
(65) 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光绪三年本,卷203,“人物志·忠节”,第3—4页。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卷121,“职官15·传”,第27页;卷122,“职官16·传”,第3页。
(66) 黎仁凯、傅德元整理:《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第64页。
(67) 李鸿章在《保定请建昭忠祠片》中特别指出:“当捻寇蹂躏各省,总兵张树珊、唐殿魁先后死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62,第38页),二人均阵亡于剿捻战场,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与张树珊一起战死的他的部将、副将刘登朝、郭有容均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也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都司马寿文、同知衔升用知县李辉麟等(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卷3,第10页)应列祀或袝祀于张树珊神牌之侧。
(68) 杨鼎勋同治七年病死于直隶南部军营,李鸿章上《杨鼎勋请恤摺》,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4,第13—15页,他符合入祀条件,应予入祀。
(69) 陈振邦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长垣、滑县一带与捻军作战时负伤旋身亡,应予列祀。与他一起战死的部将总兵衔副将刘正同也应列祀。游击衔都司鲁朝斌、铭军马队守备高峻岭等一起战死,他们应袝祀于陈振邦神牌之侧或列祀。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3,第30—32页;《淮军平捻记》卷8,第12—13页。
(70) 方有道,安徽太湖人,约同治六年在山东鱼台县与捻军交战时阵亡,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03,“人物志·忠节”,第27页;《淮军平捻记》卷3,第4—5页记载。方有道已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也应入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守备袁正泰与方有道一起战死,应入祀或袝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71) 张遵道,湖南永绥厅人,同治六年四月战死于湖北黄安。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8页。他已入祀京师昭忠祠。
(72) 胡良作,湖南郴州人,同治七年六月重伤后病故。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51页。他也入祀于京师昭忠祠。
(73) 胡家让于同治七年三月在河南滑县阵亡。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51页。
(74) 周行发,合肥人,淮军盛军将领,官至副将加总兵衔,同治七年在直隶宁津、吴桥交界之毛家庄与捻军作战重伤身故,奉旨优恤。参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1,“人物志·忠节”,第23页。他也入祀于京师昭忠祠。
(75) 胡克让,安徽霍邱人,总兵,同治七年在山东与捻军作战阵亡,赠提督衔。参见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15,“人物志·忠节”,第22页。
(76) 程广和,安徽合肥人,同治七年病故于湖北防次。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45页。
(77) 尹昌景于同治七年二月在直隶安平阵亡。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8,第8页。
(78) 郭文武等于同治七年四月在天津杨柳青一带阵亡。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9,第3页。他入祀于京师昭忠祠。与郭文武一起战死的姚长庚、曾文益应入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79) 以上5人在剿捻时,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在湖北臼口阵亡。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67、150、170、172、176页。曹仁美、谢连升均入祀京师昭忠祠。王定祥等三人皆为湖南人,也应列祀于保定淮军昭忠祠。
(80) 黄振楚、刘斌于同治七年五月在山东乐陵、直隶吴桥一带阵亡,应能入祀。与他们一起阵亡的游击万得胜、都司龙得福应入祀或袝祀于他们神牌之侧。参见周世澄编:《淮军平捻记》卷9,第9—10页。
(81) 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合肥市志》第4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页。
(82) 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32,“人物志·武功”,第22页。
(8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49,“礼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页。
(8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85) 张仲炘修、袁祖光纂:《湖北通志》,志27,“建置三·坛庙一·附祠祀”(江夏县),第14页。
(86) 详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李胜请恤片》;卷74《再请优恤吴毓芬片》;卷74《徐道奎请恤片》。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中华书局1995年版,“军务·人事”,第41辑,第735、681—682页;第42辑,第531—532页;第43辑,第139—140页,李鸿章关于以上4人的摺片及硃批。 赵长发材料见吕林锺修、赵凤诏纂:《续修舒城县志》卷38,“人物志·武功”,第13—14页。
(8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军务·人事”,第40辑,第78—80页。
(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军务·人事”,第41辑,第365—366页。
(89) 李鸿章:《王永胜请恤片》,吴汝纶编:《李鸿章全集·奏稿》卷57,第7页;《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9页。
(90) 《徐文达请附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29—30页;《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卷291,第871页。《张树屏请恤摺》,《李鸿章全集·奏稿》,卷71,第40—43页;《清德宗实录》卷296,第928页。
(91) 《潘鼎新请祀昭忠祠摺》,《李鸿章全集·奏稿》卷63,第30—32页;《清德宗实录》卷259,第479页;《刘瑞芬请付史馆摺》,《李鸿章全集·奏稿》卷74,第41—42页;《清德宗实录》卷312,第60页。
(92) 参见《光绪朝硃批奏摺》,第42辑,第184—185页,《直隶总督李鸿章片》。
(93) 以上6人的传记,见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合肥市志》第4 册,第3394—3398页。
(94) 沈葆桢修、何绍基纂:《重修安徽通志》卷233,“人物志·武功”,第15页。
(95) 详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47,第19—20页:《丁德昌请恤片》;卷22,第6—7页,《骆国忠请恤片》;卷37,第14—15页,《郭松林请恤摺》。
(96) 黄云修、林之望纂:《续修庐州府志》卷48,“武功传三”,第5—31页。
(97) 吕林钟修、赵凤诏纂:《续修舒城县志》卷38,“人物志·武功”,第1—15页。
(98) 黎仁凯、傅德元整理:《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第64页。
(99)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2,“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二”,第1页;卷451,“礼部·群祀·直省昭忠祠一”,第1页。
(100)(10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49,“礼部·群祀·昭忠祠一”,第1页。
(102)(103)(104)(105)(106)(107) 黎仁凯、傅德元整理:《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第65—66、64—65、68、65、65、65—67页。
(108)(109)(110) 黎仁凯、傅德元整理:《淮军昭忠祠公所善后章程十六条》,《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第67、65、67—68页。
(111) 如《光绪朝硃批奏摺》第40辑第557页有李鸿章将记名总兵刘盛枫等6员“留于直隶分别备补”的奏片;第583、835页又有两个这样的奏片。
(112) 费泽甫:《李鸿章轶事》,《合肥文史资料》第1辑,第139页,1984年印刷。
(113) 光绪二年秋吴汝纶代李鸿章撰:《庐州会馆记》,见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全书·文集》卷4,第82页。
(114) 杜春和:《李鸿章与北京安徽会馆》,《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标签:李鸿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光绪论文; 吴汝纶论文; 程学启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