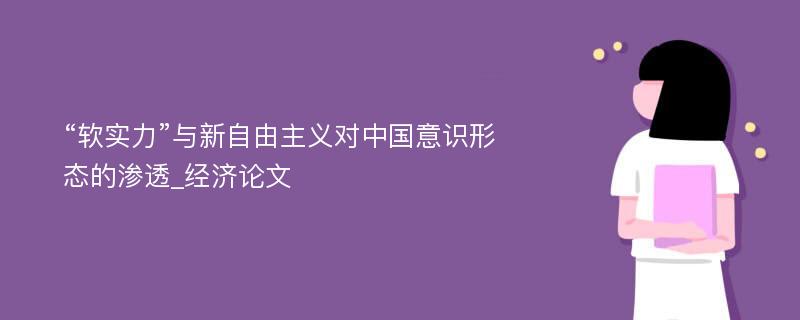
“软权力”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权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软权力”思想的实质: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软权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随后这一概念风行全世界。这一名词的产生与流行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在当今世界拥有绝对的“软权力”,也是其“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约瑟夫·奈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硬权力”指的是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而“软权力”则指的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并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一般来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胡萝卜”或者“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行为。“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吸引力,也就是文化的普适性;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可见,“软权力”真正起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非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与“硬权力”的手段和形式不同,美国“软权力”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温和的、无形的,但它的内容却比“硬权力”更为丰富和复杂,它的影响比“硬权力”更为深刻和久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美国凭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高科技实力向世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是其“软实力”倾销的一个有力见证。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方面拥有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多种传媒,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想方设法来维护它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在理论层面上它们主要是向不发达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终结论”,试图让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实现其对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然而,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的终结”来体现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如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进入90年代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提出了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主要冲突的观点。与此同时,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理论。其实,无论是“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战而胜论”、“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这些论述都直接或者变相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意识形态真的已经终结了吗?按照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论述,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否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制度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也就必然会有差别。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制度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仍会存在。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的一体化。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推行文化霸权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从而使整个世界的发展朝着更有利于它们利益的需要来重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并使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当代得到彰显。全球化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软权力”思想的推出,从这种视角上看,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
第一,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新自由主义者便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已全线崩溃,大肆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1],从此,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迈进了最为完美的“后历史时期”。在美国人看来,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的暂时失利,这是美国长期奉行“冷战”政策的胜利,也为美国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牢固确立自身的全球霸主国地位扫清了障碍。一些西方雄心勃勃的思想家们开始大胆地描绘未来世界的新格局和新秩序,他们炮制出各种形形色色的全球主义理论,并且将之辐射到世界每个角落。
新自由主义者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令人信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要尽早融入西方文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确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是极度的不平等,这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并且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最好映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继续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必然使民族性、国家性、社会主义性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衰微,民族认同遭遇困境,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以及发展合力,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抨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根基在于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它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和自我。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已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个人主义在社会过程面前的态度是谦逊的,而对其他意见的态度则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对立面,而想全面指导社会过程的那种要求的根源,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傲慢自大”[2]。这是对集体主义的严重歪曲。
新自由主义主张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制,否定计划经济。他们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就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只有市场竞争制度才能提供技术进步所必需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而国家对经济进行过度干预和计划调节,会引起一系列如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增多等诸多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就认为,计划经济是自由主义的重大障碍,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他还列举了计划经济的三大弊端:首先是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其次是不尊重消费者主权,不利于消费者愿望的实现;再次是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导致政治的集权,最终造成独裁统治,使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和奴役。可以说,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过分调节,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曾深刻地指出:“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其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3]
第三,取消公有制,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是新自由主义又一理论本质和核心观点。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以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4] 因此,不能搞公有制。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5]。可见,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私有制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是极力主张私有制的。他们的根据有:私有制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基础,它能够使个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具有最高的效率;私有制能够保证每个人致富机会均等,使每个人通过努力就可能致富,因而具有最充分的动力。新自由主义虽然以经济理论的面貌出现,但它绝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中起作用,而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比如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釜底抽薪”。有鉴于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并不是把新自由主义单纯看做一个经济学流派,而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要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规范拉美国家改革的政治取向。新自由主义与‘历史终结论’所鼓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最终胜利可谓‘异曲同工’。”[6]
作为当前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无疑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制和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来中国布道,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搞垮国有企业,造成失业问题从而引发动乱,最终使中国肢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张五常就是这种传教士之一。在中国经济学界曾一度掀起一股“张五常热”,其原因在于他的理论逢迎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另一重要方面是我们自己忽视了自觉运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他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然后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的经济意识形态。吴易风教授在《略论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一文中剖析了这种危害:“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7]
第四,抹煞民族主义,鼓吹经济全球化。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是新自由主义,其推动者是西方大垄断资本及其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国公司。这些超国家的国际管理机构一般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西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面对全球化,民族经济、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趋于消亡,资本已摆脱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控制,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巨型跨国公司手中。全球治理是人类未来政治的基本走势,“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8] 的呼声此起彼伏。人类已生活在民族国家主权逐步消亡的“地球村”中,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让渡主权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是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
世界主流媒体不厌其烦地鼓吹一些术语,如“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自由贸易”等,其真正意旨是为新自由主义“复辟”制造声势。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打着“自由化”的大旗,企图重新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倡导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逻辑。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符合中国人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正如学者王立强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从80年代到今天,民族国家的主体已经被美国肢解殆尽。美国在民族国家主权的废墟上建立起美元的金融霸权,使美国拥有了大规模巧取豪夺其他国家巨额物质财富的手段。美国控制世界的基础已经奠定,它治理世界的计划正在从思想变为现实。美国把整个世界作为它治理的目标。拉美也好、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都只不过是美国要治理的一部分。”[9] 可见,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如何疯狂扫荡民族国家主权为其资本拓展活动空间的。面对今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虚伪,我们必须坚决抵抗。因为它不是基于对世界各文化传统多样性的尊重,而是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这样很容易造成“国将不国”的信仰危机,真所谓“世界主义,误国殃民”[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