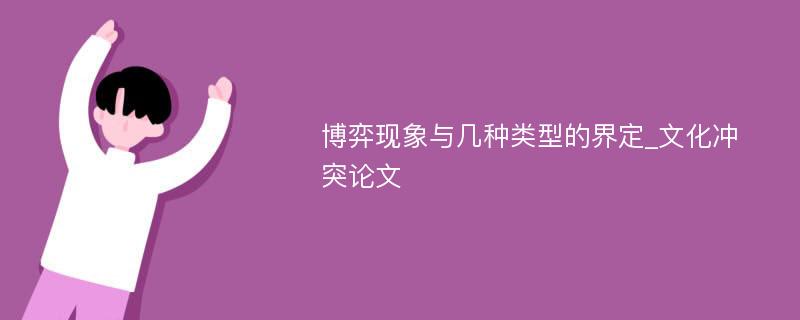
游戏现象与几种类型的定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义论文,现象论文,几种类型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游戏先于文化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① 赫伊津哈这句话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论断:由于游戏先于文化,所以我们不能把游戏研究放置在“文化”这个概念之下。它表明了一种考古学式的时间态度。“先于”,首先意味着时序上的先后,意味着游戏在考古学上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文化。这即是正本书试图表达的核心——由于游戏的出现,人类的文化才逐渐开始成型;也正是因为游戏是文化的根源,我们才能在人类所有文化形式之中找到游戏的根。 这首先标明了一种维度:文化是固定的,是对自然、社会、科学等等概念对立而又叠加方而存在的。但游戏却比它更古老,其形式是作为一种“基因”,嵌入在文化的诸多形态之中。我们当然能够找到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稳定的游戏,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在人类文化之中找到其“本源性”的基因。这造成了当前游戏学研究中两方面的问题:当我们使用文化的概念对游戏的考察的时候,我们无疑是在用“现在的眼光来检讨过去”;当我们认为游戏是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则消解了“游戏先于文化”的这一本源性的事实。尤其是,研究游戏学使得我们的工作有着巨大的风险——我们有可能冒险把和游戏毫无关联的观念和活动系统说成是游戏,或者也有可能会忽视许多游戏事实,体会不到潜在的真正的游戏性质。 因此,赫伊津哈所进行的研究是可以被称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游戏学研究。在这个层面上,其他研究无出其右者。根据我们的观点,在基本游戏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与游戏相关的原始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如何从游戏的框架中被分离处理,并发展成固定的生产组织方式,并最终形成文化与制度的。②因此,这是个理论偏差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所有其他问题之前来矫正这个问题。 我们并没有幻想去即刻获得那些能够真正解释游戏性质的深刻特征,只有在研究结尾,我们才能确定这些特征。不过指出游戏的某些外在的和易于识别的标志,倒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样做,将会使我们在遇到游戏现象的时候就能够把它们识别出来,不至于把游戏现象和其他现象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立刻着手进行这项准备工作。 不过,要想得到这个预期的结果,我们必须首先摆脱所有先入之见。当人们开始反思“游戏是什么”的时候,都潜在的包含着一种希望。当我们在谈论游戏时,我们希望它与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不同,甚至是相反。我们希望它为人们提供的是欢乐,而不是生活中的愁苦。这种情绪带领着我们,对游戏不断做出判断,把生活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包含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但是,这些先入之见由于包含了大量情绪,所以显示出的答案是杂乱无章的,都是根据生活的环境和机遇而形成的,所以它们很难令人信服。在下面将要进行的研究中,我们要坚决地把这些成见撇在一边。我们决不能从我们的偏见、情绪或习惯出发去寻求我们对游戏定义的要素,相反,我们应该从实在本身出发来定义游戏。 这种目标要求我们暂时从所谓“游戏的共性”中抽身出来,在具体实在中考察各种各样的游戏;只有我们发现了游戏本身,才能用它们的特征来给游戏下定义。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将利用一切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游戏,无论是现代的还是过去的,无论是最原始的游戏还是最精致的当代游戏;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合乎逻辑的方法把一些游戏体系排除在外,而把另一些游戏系统保留下来。对于那些将游戏完全看做是人类活动的自然体现的人而言,所有游戏无一例外,都是让人获得快感的;但反过来,快感并不能成为游戏的定义,因为所有游戏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玩家在其中的乐趣,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理解人性中被称为快乐的部分。 由于常见的游戏概念颇具权威性,可能会对辨别真相产生妨碍作用,为了使我们从这些概念中摆脱出来,在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最好先检验一下某些最通行的游戏定义。 一 存在论的游戏定义 关于反思游戏为何这一主题的著作,最早的倾向即是对游戏本质属性的定义。这种定义认为,游戏与生活的关系是对立的,而游戏内部的复杂性几乎让它无法被人们理解。这些论题在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一书都有所涉及,也在维特根斯坦的关于语言的研究中得到回应。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种完全有意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不当真的,但同时又强烈吸引着游戏者的自由活动;它不与任何物质利益相联系,无利可图。”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定义的几个部分进行逐一讨论:“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不当真”、“强烈吸引着游戏者”、“自由活动”、“不与利益相联系”与“无利可图”。 1)“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 这一描述将游戏与日常生活放置在对立的关系上。因而,就游戏的本质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自由领域,它源于何处并不是关键,重点在于它具有一种强烈地区分性。当人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不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确切地说,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具有神秘性。用这种方法对游戏进行描述更接近于一种宗教化的描述方式。而这一点则在黑塞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描述的更加详尽: 游戏的规则(游戏的符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有许多种学科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确切地说是音乐科学)——综合而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近乎所有许可之间建立起从内容到结果相互联系的关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全部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为对象的游戏,情况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产生的一切知识、高贵想象与艺术作品,直至继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以及他们转化成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③ 小说中的游戏人物事实上正是过着一种宗教僧侣式的生活。而这部小说本身就是按照歌德式的成长小说的写法完成的,小说最终事实上已经与游戏没有太大的关系——游戏在那里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纯粹的、唯一的精神世界是能够在通过智性训练之后而获得的。尽管小说并未对这种玻璃球游戏的细节进行更加深入的描述,但是就我们的观察而言,这种游戏的描述方式与作者对一种泛人类的新式宗教的观点不无关系。但是,宗教的体验最本质和核心的部分是人们对仪式及其神圣性的感受,而游戏的核心部分也被放在这个框架之中。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游戏,倘若被描述为能够承载神圣的话,将会产生许多矛盾性的观点。如果我们因为宗教中那些晦涩的部分也同样带入到我们对游戏的研究中,那么将会扰乱我们对游戏定义的追求。如果我们放弃掉对一般宗教的固有观念的话,那么问题就可能变得十分不一样了。因为宗教所试图涵盖的无疑是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起码在这一点上,游戏与宗教就具有可类比性;另外,将游戏放在这个高度来研究还有另一重考量,那就是较为全盘的对游戏进行总体性的研究。这种总体性的研究和我们上述的“游戏的共性”是不同的——后者意味着通过综合的方式,对游戏的现象进行把握;前者则意味着我们分析的起点就是总体性的,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置身于生活之外”的说法来描述游戏,是研究者对事物与生活神秘性的一种总体性反映。这种思考方式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受到了其他观念的影响。置身事外,首先并没有清晰的说明玩家的身体究竟是处在生活之中,而心灵在生活之外,还是二者都在其外。假如赫伊津哈的描述是前一种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护这种说法。它说明了一个道理:玩家的注意力与感受力事实上是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分离的。他在我们的面前进行游戏,但却同时并未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这种思路如果继续下去,就会让我们的工作进展到一个不断细分的全局性研究中去——究竟哪些游戏会既保留人的身体,又将人的思想带领到另一个世界;或者,游戏的哪些方面能够起到这种如同塞壬一般的魔力。许多研究确实是如此展开的,并使用了大量的实验来证明了塞壬的魔力事实上能够用科技的手段实现它。④这些研究时常会遇到一个难题:游戏整体的魔力到底来自于作为整体的游戏,还是来自于每一个部分的功能性协作?这种整体与部分的研究,是在总体化的研究中经常会被询问的。因为逻辑演绎的起点的唯一的,而过程又却不断细分,于是当需要对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就必须使用“系统”或“有机整体”这一的说法来解释。然而系统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协作?单独拿出来的部分可不可以获得需要的效果?答案时常会否定当初所定义的那个整体的魔力。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仅仅是在人们进行游戏的时候才会发现,“他”其实并不在这里。他的心在别处,他这一刻的生活也在别处。因而问题可能需要这样来询问:如果他没有在游戏的时候,难道他的注意力就一定在这里吗?游戏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我们发问时,作为一个人所外显的注意力的载体而出现的。假如我们没有发现他在游戏,那么我们是否还能肯定地说,他是置身于生活之外的? 并且,即使是在游戏中,玩家依旧可以在生活之中。赫伊津哈所提到的生活事实上指的是那些构成我们生活中劳动的部分与庸常部分的那些时间——也就是减去了游戏时间的剩余部分。这样的论证是循环的。我们不能在讨论某个概念之前,先使用减去这个概念的剩余部分来证明这个概念的存在,就好像我们不能让一个缺席的人来为他没有到场而举手一样——因为游戏不包含在生活之中,所以它在生活之外。而我们只要更改一下生活的概念,就可以将游戏的人也包含在其中。因为如果一个玩家是专家的话,他可以同时既在玩游戏,也在和别人聊天。 但是,存在论的哲学命题恰恰需要这样的循环论证。因为论证的起点必须是它自身,而不能是它之外的任何事物。因此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将赫伊津哈的这一游戏定义划归到存在论的范围之内。并且,在我们的研究中需要继续使用他所进行的循环论证来为我们的定义找到一个稳固的逻辑起点。 2)“不当真” 这一词语的含义,其实是对前一句的“生活”一词的进一步注解。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活动都是“当真的”。恰如赫伊津哈在论证游戏和法律的关系时,必须加上一句“两者看似如此截然不同”的话。“当真”一词所指涉的,是指法律中的判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游戏中的判决则似乎并不涉及任何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生活的本质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游戏正是在这一点上,让自己远离了生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生活的定义,赫伊津哈保持了一种谨慎而睿智的态度。 但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一点上否定了他对游戏的定义。正如许多游戏研究者所言,玩家们在游戏中常常是十分“当真”的。伊拉斯謨就曾在《对话录》中写道:“游戏必须赌点什么,不然就没意思了。”⑤如果游戏一旦涉及赌博,难道就算它的规则毫无改变,也都不再是游戏了吗?因此,“不当真”这一说明只是在说明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因为涉及死亡,涉及利益,所以生活必须当真,必须承受一种压力。而在游戏之中,则完全不同。游戏可以不当真,游戏可以成为生活日常烦恼的一个避难所。这些推论都建立在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定义之上。因而对游戏的定义,通过我们的研究就会发现,时常表达的是其范围之外的意义。因此,对游戏的研究的困难在于,我们必须首先将自己置身于生活世界之外来考量它的意义。不然的话,就会始终纠缠在游戏与生活的边界问题,以及生活本身的定义等问题之上。 3)“有意的” 这个词是对“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进行修饰的,似乎应该最先被讨论。但问题在于,只有我们弄清了“不当真”的问题,才能说明这一词语的涵义。有意的,指的是玩家在奔向那个不当真的领域时,所表现的坚决态度。赫伊津哈认识到,只有在玩家是清醒的时候,他所从事的游戏才是有意义的。由于“生活”是充满痛苦与压力的,那么坚决的向着反对生活的方向前行,就包含着一种伟大的精神特质。 有意而为之,意味着玩家的主动性,意味着这是他的选择与判断。这一点就将他从日常生活的散漫状态中区分了出来。这更加明确了我们上述的论证过程的正确性,游戏恰恰是作为区分日常生活中注意力是否集中的重要指标而出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可以走神,可以心不在焉,但他并不是在游戏。游戏首先需要的,是“有意的”,甚至是“刻意的”从日常生活之中抽身而去,也就是有意的拒绝生活中那些让人烦闷的庸常事物。当然也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一种逃避。游戏就是逃避日常生活的现实与当真的状态。但这无疑是一种庸俗化的对游戏的理解。如果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劳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游戏,那么人们选择进入游戏,就是对生活中的无聊与琐碎表示拒绝。 这种特质反过来可以回应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为何在赫伊津哈与黑塞那里所具有如此崇高的价值。因为正是游戏所具有的这一特质,包含了一种崇高的可能性——如果世间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游戏,那么这种态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世间的痛苦、压力与无聊都统统清除出去。“游戏人间”,在佛教的原始含义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是菩萨才具有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因为游戏中的人并非心不在焉,而是将他所珍视的价值放置在另一个层面上——于是世间万物随着这种视角的变化,开始瓦解掉它坚固的外壳,开始逐渐进入“无”的领域。 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将游戏的这一特质宣扬为一种宗教的智慧。而是说,伴随着研究者对游戏不同的理解,其分析路径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是大相径庭的。 4)“自由活动”、“不与利益相联系”与“无利可图” 我们直接将分析指向后三个概念。因为“强烈吸引着游戏者”只是对游戏者心理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只是指涉了游戏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游戏之上,而不构成任何我们可以得出游戏定义的含义。而这三个概念则十分不同,因为它们暴露了赫伊津哈的研究所依存的背景。关于这三个概念,首先是在康德关于“美”的概念那里得到阐述的。这一论述十分经典,因此在这里也不再赘述。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研究事实上在延续着康德对艺术以及判断力的研究。而《游戏的人》这一著作,也正是在人类学或文化学的层面上,对康德的理论进行深化与拓展。但是,康德事实上在他的论证中,是使用“游戏”来论证“艺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未曾知晓游戏的定义,那艺术的定义又何来只有?赫伊津哈恰恰是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才进行的关于游戏定义的研究的——在艺术史领域贡献如此卓越的他,势必需要将回答这一问题作为他重要的任务。 然而,这段论述同样也显示出了一种循环论证的特点。游戏的定义在于它是艺术的,而艺术的定义又在于它是一种游戏。存在论的论证方式再次显示了逻辑的原初形式——就如同在黑格尔的《小逻辑》中所表现的那样。 但是,根据海德格尔的研究,康德关于美的这一定义事实上是被后人误解的。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提到,“(康德笔下的)功利[interesse]一词,原是拉丁语的mihi interst,意思就是:我关心某事。对某事感兴趣的意思是说,想拥有某物,亦即利用、使用、支配某物。当我们对某物感兴趣时,我们就把它置于一种针对我们所企图和意愿的东西的目的之中。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始终已经鉴于其他某个东西而被看待了,亦即着眼于其他某个东西而被表象了”。⑥因此,如果我们说不与利益相连,也即不功利的游戏,表明了我们不愿利用、使用与支配的态度,意思并不是我们不关心是否在玩游戏,而是说,游戏所具有的这一属性,导致了它与生活的根本差别:同一件事物,在生活之中需要被利用、被使用,在游戏中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换而言之,同一件事物,使用生活的角度去观察,与使用游戏的角度去观察是截然不同的。这与上述的论证是完全一致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游戏中感兴趣的东西,并没有因其他东西而被看待,也不存在着为某种目的而被表象。它就是它自身,游戏就是事物自身的状态,游戏中的意义也来自于这些事物原初的本真状态。这种角度与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起源的论证是一脉相承的。 但我们依旧可以争辩的是,游戏常常是涉及功利的,游戏中的玩家在关心着某事。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常常是如何胜利,如何赢,抑或打出全新的积分。因此,这种争辩将会带着我们走出关于游戏定义的循环论证,而关注到游戏本身所组成的元素之上,也就是那些基本游戏的要素之上。在基本游戏中,目标与元素是清晰明确地。符号——行动的循环反馈环路不仅重复指向着游戏本身,甚至连“胜利”这种元素都是不需要的。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将在有关游戏的定义分析之后再来展开。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的对赫伊津哈的定义做一个恰当的评价。他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对游戏的本质属性进行研究。也正是由于他所关注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游戏的深度与广度也得到了重要的拓展;也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在有限的世界中才发现了无限的游戏。 二 系统论的游戏定义 前面已经提到过,使用系统的方式对游戏进行定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系统性难题:游戏的整体效果究竟来自于整体还是部分?每个部分在系统中组建的方式和机制是如何的?如果每个部分单独成立,那么是否并不需要组成一个整体?这些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始终困扰着西方哲学。而这些问题出现的起因在于,逻辑的推论是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大集合的问题无法通过数个小集合进行倒推,除非这些小集合的问题是大集合的子集。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游戏的魔力”而言,如果倘若真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游戏元素能够证明游戏的具有使人“在生活之外”的魔力的话,那所谓的系统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就十分可疑了。 但为什么我们又必须在这里探讨系统论观念下的游戏定义呢?这是因为“系统”的意义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同的。按照卢曼的系统论学说,每一个系统都可以独立存在,大系统则由许多个小系统所组成;每一个被分割的小系统也都可以独立的存在,并且也包含了大系统中的所有要素。⑦这使得问题从集合论的层面,转化为了一种如万花筒般的类比关系。那么游戏所构成的某种魔力,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要素中获得相对清晰的验证。因此,与存在论的游戏定义不同的是,系统论的游戏定义不会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只需要指出系统中得每个部分是什么,就能够相对清晰的勾勒出游戏的定义。我们下面就可以简要地叙述一下几种系统论的游戏定义。按照泽尔的归纳主要有几种观点⑧: 克劳福德认为,⑨游戏有四个共同的要素:再现(在一个封闭的正式系统内,主观呈现一系列真实),互动,冲突和安全(游戏的结果总是不如游戏的模式严酷);赛伦与齐默曼认为,⑩游戏是一个让玩家进入一个认为的冲突系统,有规则限制,并有可计算的结果;阿维顿与史密斯认为,(11)从最基本的层面我们可以将游戏定义为自愿控制系统的运用,其中存在各种力量的对抗,由一定的程序和规则限制以产生非平衡结果。 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被总结为,游戏是一个系统,维系这一系统的主要是游戏的规则;在这个系统之内,可以实现再现、互动、可计算等三种功能;而更主要的是,这个系统的内部是相互冲突的,玩家可以经由一些要素在这些冲突中进行对抗。当我们暂时将几种功能性的描述放在后文中叙述,就可以发现,系统论的游戏定义事实上可以被简化为“游戏是由规则构建而成的具有内在冲突的系统”。这种描述具有较高的准确性。通过对基本游戏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在最简单“捉迷藏”的游戏中,依旧能够发现规则与冲突。首先,规则告诉我们在游戏中不可以做什么。它定义了游戏的边界问题——只有捉和藏才是符合游戏。只要提的人不去寻找其他人,或者其他人不藏起来,那么这个游戏就已经终止了;其次,它还定义了角色问题——一群人必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扮演捉,一部分扮演藏;并且,由于捉与藏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此游戏才具有冲突性——一部分试图解决冲突,一部分人则负责为冲突增加难度。因此,它构成了一个二元的系统,而规则即是对这个二元系统的定义。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二元系统中继续简化为更加小的系统。所有人都可以只是捉的人,而藏起来的可以不是人,可以是一个物品。于是,这个游戏就从二元的“捉迷藏游戏”转化为一元的“寻宝游戏”。并且,即使是一元的寻宝游戏,冲突和矛盾依旧存在的。因为构成捉迷藏的冲突的载体是空间,人们会尽量躲在难以发现甚至难以到达的地方。而作为子系统的寻宝游戏,其难度也正是在这里。所谓的寻宝地图,事实上或简化或升级了游戏的难度。地图对空间进行组织,并通过一张张新的地图与符号,来标识出游戏内在冲突所导致的麻烦。因此,这种系统化的游戏定义十分精确地将游戏与游戏之间的转换关系解释清楚,并且能够经由这一定义,衍生出其他种类的不同游戏及其玩法。 并且这种冲突与规则的系统论定义,还可以在叙事学的层面上得到回应。普洛普在对民间故事的形态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故事都起源于一个“否定性事件”。(12)这个否定性事件标志着主角在开始始终保持的那个状态被打破了。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顺利地将火柴卖掉,小红帽成功地将食物送给了奶奶,王子或公主没有收到女巫的诅咒,于是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发生。这种否定性事件与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游戏的冲突十分相似。如果游戏不具有冲突,不具有对游戏角色产生障碍或威胁的元素出现,那么游戏事实上只会保持在同一个状态中,而无法进行下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论,正是由于规则的出现,才保证了游戏中的冲突不会快速消失。规则是游戏冲突的保证,但同时也正是规则需要保证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能够解决。正如所有街机游戏那样,冲突可以一直延展下去,角色最终必须死亡。但规则必须能够保证其在一定时间内的冲突,是可以被解决的。随着游戏难度的不断加深,时间持续的越长,玩家获得的紧张感与快感也就越大。 我们很难说究竟是规则还是冲突,维系着游戏系统得以成立。因为在这一定义中,规则是冲突的外显方式,是对冲突的组织结构的描述;冲突则是规则是内在基础,是玩家必须在游戏中体验到的否定性力量。因此,只要冲突具有某种独特的结构性,可以被归纳为游戏者都认可的规定,那么就可以被称为是游戏。 这一论证过程让系统性的游戏定义的边界开始变得有些含混了。在人类社会中,究竟什么样的冲突,又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下可以变成游戏?不伤害生命的?不涉及利益的?这迫使我们需要对冲突的结果做很多伦理上的判断。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如果必须要用理论才能对游戏与生活的区别做出解释的话,那么游戏学就应该被归类在哲学学科之下。因此,认识到冲突及其系统对于游戏的重要性固然十分必要,但这并不能解释游戏之所以是游戏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在贬低系统论的游戏定义对我们这项研究的价值。因为系统论对于游戏元素的组织结构问题的把握之精准,事实上已经在上述的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恰当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将游戏描述为一个系统是否具有严格的必要性。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证明,所谓游戏中的冲突,是由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构成的。游戏中的冲突,最低只能在二元游戏的层面上获得充分的解释。在更加简单、基本的一元游戏中,冲突是由于游戏中的物与人的关系所造成的。就如同在寻宝游戏中,冲突是由空间对人的阻碍而造成的。因而正是这个“阻碍”或何为游戏中的“阻碍”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 功能论或目的论的游戏定义 研究了系统论之后,让我们再研究一下另外一类的游戏定义。刚刚提到了,在系统论的游戏定义中,出现了关于实现“再现、互动、可计算”的三种游戏功能,关于再现的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再做详述。在这里我们需要率先进行分析的,是用功能论的方式对游戏进行定义,是否可以满足研究的需求。然而在分析之前,我们还是先梳理一下有关游戏活动的几个定义。 按照卡洛斯的研究认为,(13)游戏活动必须包括:自由(自愿),独立(时空上),不确定性,无收益的,规则设定,有信任;凯利的研究则表明,(14)游戏是一种一系列规则组成的娱乐方式,有明确地目标和达到目标所允许使用的手段;泽尔(15)则提供了一个更加精致而复杂的定义,他认为游戏需要包括几个特征:规则、多样且可计量的结果、赋予可能出现的结果以价值、玩家花费的精力、玩家依赖结果、可协商性结果。这些定义有一部分来自于赫伊津哈的对游戏的描述,有一部分则来自于研究者自己的发挥。但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并梳理一下为何我们会将这些定义归类到功能论或目的论的范围之内。 功能论这一提法,是相对于自然论而言的,是认为某一事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意义源于能够实现诸多的功能。那么,当我们对这些功能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这件事物的定义。这种方法否定了一种十分日常的提法,既认为游戏的出现是先验的,是自然的。通过研究游戏的现象及其属性,我们能够使用人作为尺度,来衡量游戏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在玩家与游戏之间所构筑起来的关系网络与结构是如何发生的。以这种方式作为定义的研究,能够避免赫伊津哈式的自我缠绕的论证。更多地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赫伊津哈在假设游戏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于是遵从这种假设,拿着放大镜在生活中寻找每一个细节,力争能够将这些细节与游戏的结构进行比较,以此寻找能够被称为游戏的生活细节。因此,对游戏定义的研究如果采取这种方法,就必须试图追寻一个问题,游戏究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在这些定义中,最具功能论典型特征的是凯利的定义。游戏是一种娱乐方式,是由一系列规则所建立起来的,有明确地目标和手段。(16)这一定义没有注意到一些事实,即游戏可以称为一种娱乐,但也同时可以成为别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对游戏进行描述,事实上是将游戏的范畴狭窄化了。当我们将自己的目的放在生活的其他层面的时候,就会发现游戏能够提供教育、咨询、社交,甚至是治疗与安慰的功能。这会让游戏最初的那些研究中,十分珍贵的地方被抛弃掉了。当我们认为游戏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时候,游戏所承载的是生活中所含有的全部意义。游戏就是生活,但却是与生活的复杂性不同,它更加清晰、更加具有理性,能够通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就可以完成,或者是达到它的效果。赫伊津哈同样有这样的倾向。他认为“游戏即是规则,规则即是秩序”。(17)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游戏提供了规则这一功能,而规则则带来了秩序。规则并不是在游戏之内的才能够成立的东西。而是说,游戏只有提供了规则,才能够在游戏中保证公平。这种功能与玩家在游戏所体验到的感觉是不同的。因为除非是那些必须要获得极高成绩的玩家,其他的玩家只是在游戏中体验游戏的元素所带给他们的感觉。在寻宝这样的游戏中,规则可以随时变化,却不影响快乐。我们的研究将会证明,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其他的东西,而不是秩序或规则本身。 因此,功能论的定义常常伴随着一种目的论的倾向,即认为某事物的目的是高于一切的。我们不能在游戏中获得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么这个游戏就是毫无意义的。为了避免这样的论述,研究们使用了“有明确的目标”、“可计量的结果”与“可协商性的结果”等等词语来修饰游戏的目的。但问题在于,目的到底是在玩游戏之前就设定好的,还是需要玩家在游戏中不断获得的?泽尔也提到了,模拟城市、第二人生这类的虚拟游戏,事实上是不提供任何目的的。玩家在游戏中,几乎是被抛掷到这一虚拟的空间之中,需要用身边的一切工具和资源来为自己寻找游戏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游戏称为“玩具”,但如果我们将这些游戏视为基本游戏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许多的大型游戏中找到它的影子。许多即时战略游戏,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达成“赢”这一目标。但是其制造建筑和利用资源来生产等活动,本身就具有娱乐的效果。 使用目的论对游戏进行定义,就时常会出现有意的将游戏的范围狭窄化,将游戏的意义狭窄化的倾向。即使我们对目的的描述可以不那么清晰,却依旧不能为游戏的研究提供一种价值。但这种研究的起点是有裨益的,会让我们的视野更加集中在关于游戏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层面上。游戏的目的,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同样需要在游戏的各个要素之间获得回应。这也是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 四 效用论的游戏定义 效用论的游戏定义,事实上不能翻译为游戏,而应该翻译为“博弈”。因为它所描述的是游戏过程中,玩家完成游戏时的状态。这一定义以舒茨的定义最为典型。 舒茨认为,(18)玩游戏就是进入一种特殊事件状态,只运用游戏规则所允许的手段,选择较低效率的手段,规则就会禁止高效率,这种规则仅仅因为可以使该活动成为可能而被接受。也就是说,效率是评价游戏的重要指标。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玩家在游戏中得效率,这一定义十分具有指导意义。游戏是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它描述了游戏玩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博弈论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进行描述的。认识到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将会认识到游戏活动并不是一个充满乐趣与和谐的领域。在它之中充斥着精心的算计,对他人的琢磨,对对方行动的策略性反应。因而经济学的问题,也同样是游戏中的主要问题。但是游戏中的经济学问题,其路径与作为日常的经济学有很大差异。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首先依赖于对生活世界的描述,对资源数量、人群动态的掌握。但这些因素在游戏中,尤其是基本游戏中是人为设定的。当然,如果我们把游戏中的资源设置在一定范围之内,确实可以增强游戏的可玩性,但更大的问题在于,究竟设置成何种方式,才能将游戏的乐趣最大化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围棋中设置19条线与设置18条有多大的差别?这些问题正是是我们需要证明的。 由于游戏中的资源是可以任意设定的,所以具体的设定方式,常常是按照一套玩法来推理出来的。首先,这会让对游戏内玩家可用资源的设计独立于游戏整体设计之外,成为一种特有的计算方式——游戏数据策划就是完成这项任务的。这再次证明了我们亟需将大型游戏在基本游戏中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它真实的意义;其次,这种思考可以证明,玩法在游戏的设计中常常是先于规则设定的。因此,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需要重新回头审视规则对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玩法可用先于规则,规则定义了资源的数量与种类的同时,导致了新的玩法。但规则究竟如何导致新玩法的诞生?抑或规则这一概念只是一个不严格的说法?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后文中尝试解决。 再次,反过来我们可以不可以说,生活中的经济学困境也是人为设定的呢?它是否由于我们已经在这套生活方式中,固定了某些玩法、某些价值属性,才会被设计出来的呢?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能够在本次研究中完成的。它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计划。 让我们回到效用论的游戏定义。博弈是对生活的一种拖延,是通过各种手段让对方无法完成独自就可以更好完成的使命。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解释围棋游戏的重要特点。对于围棋而言,与象棋(无论哪种)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只有最为简单地任务,即是“填满所有格子”。如果没有对手,那么这个游戏并不存在。但问题在于,围棋的规则并未设置任何棋子布局的限制,所有的下棋步骤都是在推论与推算后,得到最佳的答案而进行的。即使这些推算具有很大误差,但它始终试图选择最优步骤。而当我们开始用这种效用论的角度来质询这一游戏的竞争关系时才会发现,这种竞争关系事实上取决于格子对游戏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说,围棋事实上是一种关于“如何占领资源”这一生活主题的抽象化。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能够得到很多有趣的结论。而我们在这里最为关心的,是围棋这一基本游戏是如何将占领资源这一生活事实,抽象化、逻辑化为一种游戏的。看上去游戏似乎在描述生活中的某个层面,而一局围棋则是对这一生活现实的一次叙事。因而,我们不但能够从中获得某种知识,更重要的是,游戏玩家在这里的意义开始成为了一种叙事的写作者。当然,这种叙事是不直接的,需要通过阐释的方式对一场游戏进行表述。但是,它又同时证明了研究方法上得某种不能性——如果我们仅仅将游戏本身视为一种叙事,而不考虑到游戏要素与要素之间所构成的那种叙事的话,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困境。 因而,博弈论的游戏定义事实上在向我们说明的是,游戏的玩家才是游戏的作者。博弈论所使用数学模型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于决策中的玩家而言,每一盘游戏的意义才是游戏的核心。这让游戏研究无法以通常的研究方式进行,而必须在游戏的要素之间找到某种能够激发游戏叙事的结构,才可以对其进行更加清晰的研究。 ①[荷]约翰·赫伊津哈著,《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这种提法非常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探讨方式。但与常见的马克思研究相比,我们这一研究更加贴近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阿尔都塞式的研究方法及其形态。 ③[德]赫尔曼·黑塞著,《玻璃球游戏》,张佩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④关于这类论文可以参见Mark J.P.Wolf and Bernard Perron,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1-2,Routledge,2003. ⑤[法]乔治·维加雷洛著、乔咪加译,《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⑥[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8页。 ⑦Niklas Luhmann,Art as a Social Syste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33. ⑧[丹]贾斯珀·泽尔[Jesper Juul]、关萍萍译,《游戏、玩家、世界:对游戏本质的探讨》,载《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三期,第220页。 ⑨Crawford Chris,The Art of Computer Game Design,MNOL,1982. ⑩Salen Katie & Zimmerman Eric,Rules of Play—Game Design Fundamentals,MIT Press,2003. (11)Elliott Morton Avedon,Brian Sutton Smith,Paul G.Brewster,The Study of Games,Ishi Press International,2015. (12)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 (13)Caillois,Roger.Man,play,and Game,the Free Press,1961. (14)Kelley David.The Art of Reasoning.W.W.Norton & Company,1988. (15)同注⑧。 (16)Kelley David,The Art of Reasoning. (17)同注①,第82页。 (18)Suits,Bernard."Tricky Triad:Games,Play and Sport" in Morgan,William J.& Meier,Klaus V.(eds.),Philosophic Inquiry in Sport.2nd ed.Human Kinetic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