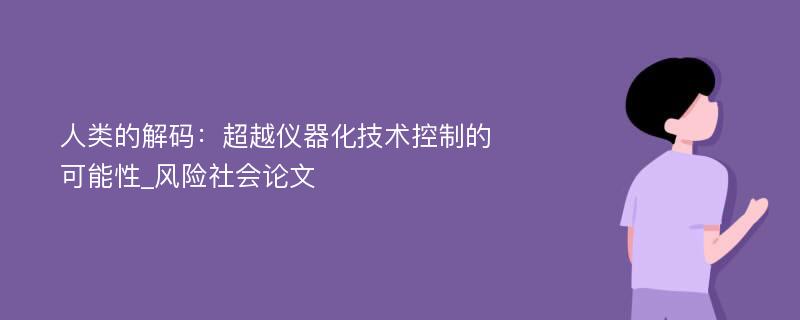
人之解蔽:超越工具化的技术宰制之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宰制论文,工具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6-0042-06
一、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
人在一般的意义上指人类物种的成员,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生物。人自身的整体性,体现的是人自身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的融合。人是不能割裂的存在。这种整体性既是一种人之共同性展现,也说明了单个的人也是一个不可抹煞的整体。人自身的整体性,也在于与他人相交往的主体间性中表现出其个体存在的完整性。其中的个体存在,既是一种自由意志的整全式表达,更关键的是它融合了个性与共性的平衡。个体在此既是一个独立的分子,又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人所具有的不可复制性在此是显而易见的。在一般的意义上,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个性化存在。这种个性化存在,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的例外。例外是相对于人的普遍存在、人的一般化意识以及整体化的社会情境而言的。“例外虽然屈服于普遍之下,本身同时却又负有一种任务,即要成为某一一次性实现的道路,这条违背着普遍走向的道路即使不是它所愿望的,毕竟是它所必需的。”[1]例外,不是单纯的变异,而是体现了人的一种独特性。在共同意志的盲说之外,对例外的宽容与敞开是对人之个性的尊重。
人的精神属性来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人的内在价值,是人的目的所在。基于人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新教伦理学家弗莱彻罗列了以下的内容:自我意识、自我控制、未来感、过去感、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关心他人、交流能力、好奇心。这并不是在生物学层面上来使用“人”这个概念,而是从人的精神特质的层面来解读人的秉性。
人之生命是一种有尊严的存在。它包含人格、福祉与自由意志。人格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与格局,福祉体现了人之生存的利益与幸福,自由意志体现了人在这个世间的主观意愿与自主式的存在。
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人所特有的,那么人作为自由的创造物,自由就是人存在的基本向度。人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并且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保持智慧的思维存在。“人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是变化的产物,在人的身上,从来就没有预先给定或确定的东西。历史既没有来由,也没有终点。人身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人类在漫长时间中创造出来的。”[2]在历史长河中融会成的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产物。人有能力把自身看做是在时间中存在的独特实体,因为其所存在的愿望,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与权利。
但作为现代人基本特征的自由特性并非是一个无拘的诠释。在自由的为所欲为的背后,人类之间的斗争乃至相残,乃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所在,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最大不幸。
因此,现代人的自由作为一个自我存在合法化的可能,并不会轻易被他者或外界所否定。但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对自由之有限性的省悟。这种自由之有限性在属人的层面上折射出人之有限性。
人之有限性,不仅表现为人之能力的有限,更关键的是人性的局限。人性的局限是人不能克服自身本能式的恶的弊端与私欲的爆发。这里的有限性,重要的是人之理性的有限,是人之道德意识的不完善。尽管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备理性,但欠缺也在于人并非拥有全知全能式的理性。
人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自我意识并扮演一定社会角色的主体。它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清晰地勾勒出来,也从另一个认知维度说明了人自身的渺小不能掩盖其所存有的伟大。“在如此怪异无情的世界中,像人这般渺小的生物怎样才能不泯灭自身的进取精神呢?万能却又盲目的自然界,在宇宙的深渊中急步匆匆,周而复始,不停转动。……生命虽然短暂,人却可以自由地审视,自由地批评,自由地求知,自由地发挥创造性的想像力。在他熟悉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人享有自由。不可抗拒的力量统治着人的外部世界,但人却比外力更强大,因为他拥有自由。”[3]
因为身心层面的自由所赋予人的精神格局,使人的有限性存在,不仅构不成对人的贬损,相反却成了对人真实内涵的精神赞誉。这种有限性的存在,在保罗·蒂里希看来是结合了人所具有的两种气质表现着自身,“它表现为焦虑(anxiety)和勇气(courage)的一种始终不稳定的平衡。人的存在,由于非存在,由于有限,由于面临着威胁,人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处在焦虑之中。它肯定自己,承担起自己的焦虑。……人的存在接受自己的焦虑,不企图否认或无视焦虑,而是相反,他的行动完全符合‘勇气’一词所表达的含义,这就是说,它无视非存在的威胁而肯定存在”[4]。
如果说焦虑是人之有限性的常态情感,是对未来之不确定所存有的一种恐慌,那么勇气则是理性赋予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它折射出人证明自身存在的努力。在跳脱人心邪恶或人性软弱的困境中,勇气也正是给予人精神动力去触及善恶之知、去除无端焦虑的精神武器。它力图借助价值的创造去探寻生命意义的来源和确证。
二、人的问题:自迷与异化,以及丧失勇气
人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外界,更关键的是来自人自身。首先,人的问题在于自迷。人的自迷,是人的自我困厄,是人不能够对他的行动承担责任。其原因在于人不能切实地认识到人的有限的自由的这一面。有限意味着人的生存受到非存在的威胁。在一种有限自由的状态中,人面临着非存在的威胁——死亡以及导向死亡的一切偶然事件,还有以错误和罪过为表现的迷惘状态。
如果人所立足的自由出了问题,人的自迷将难以挽救。对于每个身心正常的人来说,自由是人之自然所图。自由被认为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人往往看重自由的魅力,却忽略了自由的限度。自由可以作为任何事物的基础,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未经反思的自由是一种矛盾,如同无度的自由不仅毁灭的是自由,而且是人本身。作为观念的产物,自由过甚的结果也构成了另外一种压迫。人的自迷由此在自以为是的陷入中越来越甚,人自身不仅不能被超越,而且很可能被解构。
自迷还在于人具有突破道德规范的潜在冲动。道德是一套社会规范,也是一种价值德性,或者说道德是善恶之别。人之生命及其意义所在是道德价值的标准:凡有助于生命及其意义所在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而当人的自迷进入深度昏昧的时候,一些人挥霍欲望的理由,使道德怀疑主义的声浪也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善恶不分的状况也使道德虚无主义的观念成为社会无序、人心沦丧的根源。美国学者爱因·兰德认为:“是的,这是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你们的道德准则已经达到了顶点,走到了其发展的尽头和死胡同。如果你想继续生存的话,你所需要的不是回到这种道德之中去,……而是重新发现一种道德。”[5]
其次,人的问题在于异化。异化,是人真实存在的异化,是来自外物挤压或促逼的结果。这种外物不仅仅是在后工业化社会在诸多领域操控生产与生活意志的信息技术,而且也是主宰商品制造与交换的市场逻辑。它们所构筑的社会合理化逻辑是对人之自主性的强大扭曲。“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合理化逻辑对个人意识和行为的穿透程度之深,已远远超出了韦伯的想象,而日益走强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只可能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尖锐。我们被抛入日益膨胀的信息流中,而这些信息自己则被不断地编码与再编码以适应财团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利益和公共管理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期望以及意识都被深深地结构化了。”[6]
异化是来自物的异化,更是来自技术的异化。异化导致人作为行动者却不具备自由意志,其行动本应具有的可供取舍的可能性消失殆尽。在此状况下,新的电子媒介环境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技术知识的增长对人的挤压也是空前激烈的。当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极权时,人一方面顺服技术所规定的工作流程,另一方面成为工具的附属物。人的外在附属物对人的奴役,在以某种看似合理化的形式支配着人的存在。人的异化在此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被技术所操控的人自身的痛苦在选择过程中也频繁地出现了。在置身于不同情境的迷惑与影响下,人所受到的诱惑与人当下所具有的能力之间处于一种抗衡状态。心灵枯竭干涸的人是异化的,在不断的社会分层中被重新部落化,在此个人被个人主义的印刷品分离,是丧失了社会共同理想的无根的局外人。人所扮演的工具般的角色,在一种物是人非的境遇中,构成了人的无能为力。
人的异化来自时代的异化吗?当然,人的异化是基于多元文化时代的个体性与破碎性。也有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我们更应将这个时代称之为‘漂泊不定’或‘无家可归’,而不是‘异化’。事实上,‘异化’以一个总体性的世界、一个总体性的人格为前提(这些人格尽管彼此疏离),但是,多重网络社会既没有提供多少机会来经验这一总体性,它的‘组合化’成员也没有多少机会来发展其总体性人格的自我意识。”[7]与此相关,如若异化是以整体性的人格为前提,那么人的异化是总体的人类的异化,而不是个别人的异化。而人类的异化,无疑昭示了人作为类群体的整体迷失。
再者,人的问题在于自身失去勇气。这里的勇气指的是基于道德意识的果敢,以及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理念。勇气的渐失,是对应于焦虑的增加。焦虑表现为对处境的担忧,对前途的惶惑,特别是对丧失未来可能性的顾虑焦灼。因为失去勇气,人在这个世界无目的、无意义。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人失去勇气,导致人之想像也被耗竭。这种耗竭既是一种能力的耗竭,也是一种结果的耗竭。人慵懒地失去了生活的兴趣,欲望的驱使至多只是形而下的所为。人期待着在未来超越那些被给定的命运,实现那些实际上构成人的本质的可能性。
三、人的状况:风险生存
尽管人对自身的善,有时的感知是明确的,有时却也是隐蔽着的。明确,因缘于对道德之源的把握是清晰的;隐蔽,是因为迷惑于个人之利与社会之善的平衡。在此,人所陷入的知与不知的矛盾,使人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有可能被扬弃。可见,风险生存成为人在无根时代的基本状况。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不是我们所能补救的,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甚至在以更大的规模来重新创造不确定性,通过我们补救不确定性的努力来创造不确定性。[8]
无根时代,一般意义上被解读为精神匮乏的时代,也被诠释为空心人的时代。它缘自对人之本原的逼近,是对人之心灵的叩击,也是对人之生存根底处的追问。但出于人的有限理性,尽管人始终不渝地想去认识自我,但自我认识的结果存在偏差,“人的天性本身是多么统一和完整,多么尊严啊!我们的思维并非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向和倾向而以自身为基础。人并不是由两个独立并存的部分组成的,人是绝对统一体。我们的全部思维都以我们的意向本身为根据。一个人的倾向如何,他的认识也就如何”[9]。
对自我认识的检验是需要一种上帝式的全知全能来作为依靠的。当上帝式的全知全能,在目前看来只能在信仰领域被明证时,大多数人的自我认识充其量也只能是自我的认识,而不能成为全体人类的认识。
而个人化的体验是容易受到外界误导的。因为在商品主义与技术主义的物质喧嚣中,它容易在多样性存在的选择活动中被外物所遮蔽。人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人对多样性的态度上,是宽容的接受,还是狭隘的拒绝。毕竟作为组成社会群体的个体,人对时空维度的变化是否接受,关键是自身对这种复杂性的评估与认识。
人的风险尽管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但也成为当下的一个问题焦点。如若主体只是被理解为一种并不完善的虚构,现代人置身于一个历史的悖论上,他并不能看清人自身的未来。人只是一个有限知识的获得者,也只是一个有限能力的发挥者。其由人性所带来的脆弱性是与生俱来的,其心灵的广阔性也在遭遇有限性存在的挤压。“我们可以将当今人类的痛苦描写成一个孤立和疏离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的疏离。正如前面所解说的,科学和研究,尤其是数学—实验研究给人类丰富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是由无数的个别项目或实在的个别侧面所组成的,而非人对实在经验的整体性的知识。以这种知识为目标的哲学家反而被看轻,被人冠上梦想家或是怪人的头衔,因为他们的意见不能通过数学—实验过程的考验,也无法得到科学证明。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人再也看不到世界和自然的奥秘和神秘性,人和最高的真实失去了接触。古人经由神秘知识,诗人经由想像,哲学家经由他们整体性的理解,都和这最高的真实有所接触。”[10]
人与其本质的疏离,更加说明了人的风险生存也在于存在者的蒙蔽状态。蒙蔽,既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不自知,也是一种被技术操控的失措。蒙蔽状态,在人的生命流程中或长或短地出现。因此,与之相抗争的解蔽是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成为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迷失者,人才成为自由的。蒙蔽与解蔽的此消彼长总是贯通并且支配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然而,蒙蔽绝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的风险生存是归属于命运领域的蒙蔽。
如果说技术的滥觞是我们时代的命运,那么解蔽则是破解命运的关键。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走上了何种歧途?我们要追问的是技术,而现在却到了。αληθετα[无蔽]那里,到了解蔽那里。技术之本质与这种解蔽又有何干系呢?答曰:关系大矣。”[11]风险生存来自技术对人的遮蔽,建立在技术对人的操控的基础之上。如果现代技术是一个合目的的手段,那么对现代技术的适当使用,必须符合人为之所设定的目的。
唯技术社会构造了一个新的统治体系。技术的控制能否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可能在一个无技术的时代,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人陷入的是无可操控的徒手运作社会。但当人高扬工具理性,高奏技术无往而不利的凯歌,技术便化身为无所不在的中介环节,并且成为宰制人类生活的魔咒。在技术结构与技术效率的要求下,人是隶属于既定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技术成为指向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一种通用符号,并在一个贯通社会生活的流程中诠释着技术统治的另类理念。技术的合理性,融合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体系。它的存在决定了社会的存在,它的进步决定了社会的进步。“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12]当技术成为这个社会新的颠覆性力量,它隐含着这个社会正在剧烈发生的变化趋势。在公共社会的治理领域内,它增添了政治合法性的技术内涵。
解蔽是抵制唯技术主义或技术至上主义的解蔽,是还原人之主体性的解蔽。解蔽是一种去除风险生存之思路的澄清与贯通。它需要不断审视人所置身的社会状况,持续反思人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并有效纠正个人抉择的所作所为。“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这种促逼之发生,乃由于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是解蔽之方式。可是解蔽并没有简单地终止。它也没有流失于不确定性之中。”[13]解蔽,也伴随着心灵良知的质问。人所置身于这个世界的根本价值是否会被诸如技术为代表的历史替代品所抹煞?解蔽是一种自明的抉择,需要在一种心灵的转向中逃脱技术专制主义的统治。
在这样一个偏重实利的现代世界,如果人的风险生存被作为一个事关人类境遇的问题提出来,它也往往只是说明物质生存的风险被重视,而精神生存的风险则被忽略。尼采的告诫在此异常有力:“我只想成为明智的人,而不要这个充满混乱和对抗的制度,正是这些对抗构成了‘现代世界’。”[14]然而,明智从何而来?风险生存又如何摆脱?在这个混沌的现代世界,人们如何保全自己?人需要从一种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个体状态中走出来,人的精神力量的每一次提升,都体现为追寻自我存在真实性的一种质问。
人们目睹一种以技术化与物质化为主导的生活秩序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工具化的人,是一个精神空壳的人,是一个没有主动感与自主意识的人。他生存在充满风险的境遇中,被虚拟化与客体化的地位使人之灵魂不知被置放在何方。人们需要明确人的生命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存在,而不是为了他物的存在。人的价值概念源于人的生命意义,并依赖于人有效的目主的生命活动。人不能成为技术宰制世界的牺牲品。人对自然、社会与世界的改造是需要自主权利与自我意志的存在的。
〔收稿日期〕2007-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