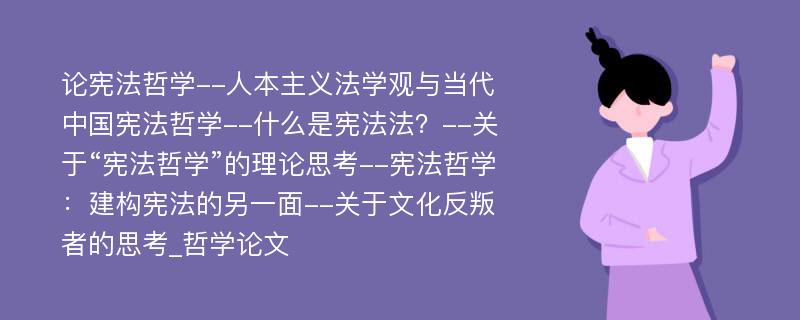
宪法哲学笔谈——人本法律观与当代中国宪法哲学——宪法学是什么?——关于“宪法哲学”的一种理论思考——宪法哲学:构建宪法的彼岸世界——英美宪法哲学刍议——论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对宪法知识的文化重构——以语境论为分析工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哲学论文,刍议论文,笔谈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本法律观与当代中国宪法哲学
李龙,张薇薇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人本科学发展观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而人本法律观则是科学发展观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在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实质是依宪治国。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基本内涵、价值目标及实践价值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以人为本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基本内核与根本理念。人本法律观,对于让宪法回归服务于人自身、重塑宪法哲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人本法律观基本问题阐释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解放、人性回归的历史。以人为本,关注人本身是人类的职旨与永恒追求。作为理念的“以人为本”源远流长。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都有相类似的说法。我国春秋时期法学家管仲就曾经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在西方,人文主义学派主张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个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当然,中国古代的人本观以及西方的人文主义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本观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以人为本”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活着的现实的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本位”,更是“根本”,是人的价值与人的意义之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以人为本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1] 所谓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实现为内核的基本精神。其核心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即是我们所主张的人本法律观。为了准确且完整地认识人本法律观这一法律理念,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法律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理解。我们认为,法律观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即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和人本法律观。[2] 其中,神本法律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盛行。在古希腊、古罗马,学者们将法律与神等同起来。中世纪时期,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学科几乎都受到神学的支配,成为神学的附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律被物役,物本法律观的出现成为必然。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揭示了法律的奥秘。揭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任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为指导,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即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揭示了法律产生→异化→回归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法律观也随之变化,即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可见,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对法律文化遗产的科学总结和对传统法律观的反思与超越。
人本法律观是以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保障人权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根本目的的科学体系。具体来讲,人本法律观的科学涵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法律活动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与归宿,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全过程。第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弘扬人文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强调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和谐一致,强调法律同经济、社会、环境等安排协调发展。第四,在法制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的自然权利。总之,人本法律观,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权利为尺度,实现法律服务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体系。人本法律观强调法律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
人本法律观的确立,既是法律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和实施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人本法律观是法律从异化再到回归的必然过程。人本法律观的提出必将引起中国法律观和法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人本法律观是直接影响中国法学走向的重要因素,代表并反映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二、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学科定位
哲学一词在英语中即“philosophy”,来源于希腊语,它常被解释为“爱智慧”或“爱真理”之学。宪法哲学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① 应该说,他们都从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他们对宪法哲学的认识。在我们看来,宪法哲学是对宪法基本问题形而上、一般性的概括与理解,是隐含于宪法文本背后的价值与准则。它重新审视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目标指向,探讨宪法的伦理价值与正义性问题。换言之,宪法哲学是运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和研究宪法和宪政问题的一门理论宪法学学科,它揭示了宪法和宪政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宪法哲学既有利于我们高瞻远瞩地把握宪法和宪政实践的全局性问题,又便于我们深入认识纷繁复杂的宪法和宪政问题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哲学既不属于哲学,也非政治哲学。宪法哲学属于宪法学,是法哲学。它关注的是宪法和宪政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宪法哲学是站在法律的立场而非政治的立场来考量宪法的,是以法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的视野来审视宪法和宪政问题。由此,我们说,宪法哲学应当具有独立的法学品性。在当代中国,学者们对宪法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宪法哲学的发展也相对薄弱。这些都已构成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瓶颈之一。当代宪法哲学理论基础的匮乏造成了宪法理论上的尴尬与实践中的失范。宪法是人权的保障法,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要充分发挥宪法的功能,必须树立科学的宪政理念,加强对宪法哲学的理论研究;必须转变宪政理念,充分认识人权在宪法中的价值和宪法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功能。因此,我们认为,宪法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宪法和宪政建设而言,具有根本决定性的意义。
三、人本法律观与当代中国宪法哲学
人本法律观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法治始终的生命线。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本法律观,以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于人的功能。[3] 由于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在发展进程、基本内涵、目标宗旨及实践价值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以人为本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的宪法哲学的基本内核与根本理念。
首先,从历史发展进程角度看,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具有同步性。如前所述,人类法律观经历了从神本法律观,到物本法律观,再到社本法律观,最终回归人本法律观的演进过程。在西方的历史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使人重新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开始了“以人为本”的历史演进。从宪法发展史的角度看,宪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反特权为使命,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为目标。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与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一部近现代立宪主义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权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宪法史,就是人权保障史。[4](P118) 保障人权、促进人权是宪法的首要功能与终极价值。离开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引,宪法就将失去其存在的根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其次,从基本内涵方面而言,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具有一致性。如前所指,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价值、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的实现为内核的基本精神。其基本内涵在于尊重并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权为本”。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价值,确认并维护人权是宪法的首要价值和根本功能。就宪法基本内涵讲,它包括国家权力的配置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毕竟,国家权力配置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遭侵害。归根结底,宪法是研究国家权力如何为公民权利服务的。保障人权是宪法的首要内容和核心所在,宪政制度的规定从根本上讲应该服务于人权保障。由此,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是宪法的真正本质和核心。宪法的理论基础应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构成了宪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再次,从价值目标的层面说,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的指向具有同一性。人类宪法和人权保障制度的历史表明,宪法与人权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宪法的人权保障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宪法文明发展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宪法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正如美国学者费里德里希所指出的,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是宪法的首要价值。[5](PP14—15) 在我们看来,宪政的终极关怀是人权,其根本意义与根本目标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障。真正的宪政在于一种特定的精神上的追求,一种尊重与维护每个个体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因此,当代中国宪法文化和宪法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重铸宪法的人文精神,完善宪法的人权保障机制和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历史性过渡。
最后,从宪政实践的维度讲,人本法律观作为法治的核心理念,是解决宪法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内在诉求,对于中国宪法学走出困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哲学获得较大发展,但仍面临诸多困境。其深刻的缘由在于宪法与部门法学对话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直接切入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公民权利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等几个方面。[6] 要走出现实困境,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和要求,构建宪法哲学理论。这要求我们的宪法理论与宪政实践都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人权。以人为本正是重构我国宪法哲学的基本原理,它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根基。
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以人为本业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业已发展成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业已成为各项工作发展的基本理念。宪政规律告诉我们,人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宪法的根本价值与功能所在。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并保障人权。这既是人本法律观的要义,也是当代中国宪法哲学的精义所在。作为法治国家的核心理念,人本法律观为也必将为中国宪法哲学走向成熟提供精神动力,为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构建贡献理论支撑。唯有坚持人本法律观,并将之真正贯彻到宪政实践过程中,宪政中国的实现必将不再遥远。
注释:
① 相关论文参见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范进学:《宪政与方法:走向宪法文本自身的解释》,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江国华:《宪法哲学:自由的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袁贵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J].求是,2005,(22).
[2] 李龙.人本法律观简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4,(6).
[3] 李龙.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中国法学的全局[J].武汉大学学报,2005,(4).
[4]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 [美]卡尔·J·费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C].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6] 刘茂林.中国宪法学的困境与出路[J].法商研究,2005,(1).
责任编辑 晨晓
宪法学是什么?
——关于“宪法哲学”的一种理论思考
周刚志
(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宪法学理论界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乃是如何摆脱左倾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重构宪法学的科学品格。宪法学者对宪法基本问题的深入追问,以及对于宪法学之学科性质与内在体系的深入思考,都已经切入了哲学方法论的理论视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宪法哲学”概念逐渐成为宪法学人所广为讨论的一个话题。本人认为,宪法学是一个具有开放性但是有相对自足的知识理论体系,宪法学者对于宪法规范与宪政规律的深入研究,必将触及到一个认识论层面上的哲学问题:即人类何以认识宪法、人类如何认识宪法。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宪法与宪法现象,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哲学”。
一、宪法学是一种关于宪法的知识体系
宪法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质疑的问题。根据我国宪法学权威教材的观点:“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是区分不同学科的基本依据。正是由于各门学科都已具有矛盾特殊性的特定客体为研究对象,才使各门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宪法学是以宪法和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1](PP1—2) 换言之,宪法学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因为宪法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现实:宪法学所研究的对象,即所谓“宪法、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同样也是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甚至经济学同样关注的问题。既然如此,宪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究竟何在呢?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对于学科的形成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学科的划分其实不过是学术制度运作的结果,它牵涉到学术机构、学术权力与学术资源的设立与分配,涉及到不同学科从业人员的共同利益,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我们知道自从全世界的大学中有各种学院的系科以来,就存在各种学科、这些学科的毕业学位以及这些学科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者联合会。这就是说我们政治性的知道不同的学科存在。它们建立了拥有界限、结构和人员的组织以保护其共同利益并确保它们的发展”[2](P165)。当然,沃勒斯坦质疑学科划分的真正目的,是旨在论证其所谓之“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体系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分工,在今天这个知识高速发展的时代,依然是理论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失的条件。但是,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其实宪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存在,确实是与我们现行的专业设置、学科分工的学术制度具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而并非其拥有一个排他的研究对象。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学术分工的制度体系,以维护各个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与自足性呢?除了知识分工与维护学术共同体利益的需要之外,沃勒斯坦似乎并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在笔者看来,沃勒斯坦的观点比较清楚地解释了不同学科形成的直接原因,即学术制度体系的存在,但是并不能进一步说明现行学术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其实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分工体系的存在,主要是基于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教育的发展又是基于社会化大分工需要不同专业人才的社会要求。以法学为例,宪法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宪法教育的需要,而宪法教育又是基于培育法律职业家阶层、巩固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需求与政治需求。我们可以从法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发现这一规律。何勤华教授就曾经指出,在法国宪法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宪法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791年宪法公布之后的第23天,法国政府就宣布要在大学中进行宪法教育(事后未能实现)。1819年,在大学中开设了“公法”讲座。1834年,法国在巴黎大学正式开设了宪法学讲座。[3](P152) 其实,不独法国如此,其他国家如英、美、日的宪法学理论都是在高等学校宪法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近现代宪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如拉邦德、耶利内克、施密特等人都是高等学校的著名教授。正是因为宪法学在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是与民商法学等私法学科等截然不同的一门重要的法学课程,正是因为宪法观念的传播与宪法技艺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才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独立地位。所以,从直接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宪法学”,乃是在宪法学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关于宪法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括:近现代宪法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过程,世界上几个重要国家的宪法典的结构、体系与内容,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与基本制度,本国宪法如何实施的法律技术等等。
二、宪法学是一种关于宪法的认知实践
宪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这也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在我国的学科体系中,法学无疑应该属于社会科学。但是西方学术界一般将所有的科学学科依据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归结为三大门类,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中法学传统上属于人文科学,而不属于社会科学。例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主流》一书中,即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列为社会科学,而将法学、哲学、史学、艺术学列为人文科学。[4](P188)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其主导原则,以实验为其主要形式而与人文社会科学风格迥异,此为学界之常识,自不待笔者多言。唯西方学界关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在我国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在此先作简要介绍。在西方学者看来,社会科学偏重于从自然科学中移植的实证方法,旨在通过对于社会的实证研究改进社会管理,其客观性比较强;而人文科学则偏重于“理解”方法,旨在通过内心的体验把握过去的生命与精神,建构一种价值观念来满足自身与人类的精神需求,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① 的确,法学诠释学与神学诠释学是古代西方最早出现的两门诠释学,而作为现代法学源头的罗马法学其实质正是诠释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5](P3) 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是以诠释学的方法研究与阐释古罗马法及本国制定法的学科,强调解释者的主观认识与法律文本之间的一致与融合乃是传统法学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而言,宪法学作为法学体系的一部分,似乎当然应该列入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应该以传统的法解释学方法为主要方法,摒弃立足于社会宏观视野下的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此种宪法学学科观念已经为当今某些宪法学家所主张。例如,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林来梵教授就认为:“必须让宪法学返回规范,确切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的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立足于这一立场,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他宪法现象则只是为完成上述任务的次阶任务。”[6](P4) 的确,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片面引用前苏联的国家法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存在很大的理论缺陷——“政治色彩过于浓厚,缺乏宪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其研究成果基本上属于宣传性、注释性的研究”[7]。而这些理论缺陷之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宪法学自身学科定位不明,没有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所致。中国宪法学欲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在传统法学体系中谋取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上找准自身的位子。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政府职能的重新调整,我国社会变迁的速度正在加快,传统的宪法制度正在面临深刻的挑战。传统的法解释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囿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与注释,真的能够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真的能够解决我国制度变革的重大时代课题吗?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认的。正因为如此,宪法学借助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必然成为宪法学研究领域内的一种潮流和趋势。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变局之下,宪法学者不能再如同“密纳发的猫头鹰一样,只在黄昏时才鸣叫”(黑格尔语),而是必须学习报晓的雄鸡,在黎明之前发出准确的呼喊。为达成此种目的,宪法学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静止的关于宪法的知识体系,而且应该被视为一种动态的关于宪法的认知实践。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法解释法学方法和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社会实证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宪法学所用,成为我们构建新时期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工具。
三、宪法学是一种关于宪法的哲学反思
宪法学是哲学吗?或者说,作为宪法学之构成部分的宪法哲学是哲学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江国华博士认为:“作为宪法基本问题追问之学的宪法哲学,既是关于政府应当如何行动的学说,也是旨在引导人们如何理解政府的哲学。它从哲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哲学思维的提炼,对宪法进行总体的根本性的考量和把握,从而提示宪法之本原、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李琦教授则认为:“宪法哲学不属于哲学而是宪法学,它是宪法学的一种面相,一种宪法学必须具备的面相,而不必是宪法学中的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所要追问的是:什么是哲学?为什么宪法学研究需要引入哲学的视野?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和基本问题,是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8](P219) 显然,从哲学家们所界定的“哲学”概念而言,江国华博士与李琦教授所探讨的“宪法哲学”,其实只是“宪法政治学”,或者说,是“宪法的政治哲学”。坦率地讲,笔者认为这种层面的所谓“宪法哲学”还不是真正完全的宪法哲学。
宪法学为何要引入哲学的研究视角?或者说,在宪法学的研究中为何需要引入“思维与存在”的重大问题呢?笔者以为,这就必须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上进行深入反思。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来看,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或者说,“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矜持,是哲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范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立足于“此岸世界”去把握“彼岸世界”,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力图立足于“彼岸世界”本身去把握“彼岸世界”,两种方法同样具有局限性,其区别也是相对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命题作为前提:即“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者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哲学命题本身无法通过实证方法所证实。进一步说,不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是有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区别也是相对的。虽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大量地使用实验或者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试验或实证方法得以正确运用的前提却是借助于深刻的理论思维提出的“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种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的同类的事实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9](P138) 所以,不论社会科学的“说明”方法如何客观完备,也不论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如何深刻,它都无法脱离对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关系的前提性把握。我们真的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吗?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在现时情境之下无法完全地认识与把握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最珍视何种制度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建构一个理性的政治制度?这些看似离奇的问题,实际上是宪法学者在研究宪法时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构成了近现代立宪主义运动最深刻的理论背景,也是近现代以来两大立宪主义模式——即“经验式的渐进主义模式”和“建构式的革命主义模式”产生的最深刻的文化根基。而20世纪兴起的风靡全球的某些宪政理论,如哈耶克的宪政理论,正是立足于这种意义的“宪法哲学”基础之上。总之,宪法学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求宪法学者对自身,乃至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哲学反思,对于我们建构合理政治制度的各种努力进行哲学反思。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宪法学得以成为一种关于宪法的哲学反思。
注释:
① 参见欧阳康著:《社会认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洪汉鼎著:《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参考文献:
[1] 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M].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4]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5]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 韩大元.宪法与宪法学的回顾与展望[A].张庆福.宪政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晨晓
宪法哲学:构建宪法的彼岸世界
刘连泰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任何法现象的哲学都无法游离正当性追问这一命题,因为关于法的哲学其实就是对法的寻根之旅,而法的根就是法的正当性。部门法的寻根之旅很容易结束,因为“我合宪,所以我正当”——部门法的正当性其实就是部门法的合宪性。宪法的正当性依据在哪里?我们如何论证宪法的正当性来源?这就是宪法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但由于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特质,我们无法在法学本身的框架内完成宪法的正当性证立。我们被迫游离宪法的此岸世界(规范的世界),去宪法的彼岸世界寻求证立宪法正当性的精神资源。从西方宪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基督伦理和自然法理论是宪法学者最经常的精神诉求,这两者与宪法存在价值上的暗合。
一、宪法的彼岸世界之一:基督伦理
宪法“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1](P1)。 基督教的教义具有不同的解读方法,但基督伦理对上帝的理解、对人的认识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基督教对人的认识表现在人之有限和追求超越这种张力之中。基督教对人的认识可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人是受造物,其特点是具有时限性,被动、相对、受到束缚和局限、软弱、无能、无法超越自然生命之生长的过程;其次,人乃“上帝的形象”,在具有受造物的一般特性的同时亦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因此,人有别于其它自然受造物,其精神特性可以使人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相对中向往绝对,在时空中体悟永恒;这种精神特性亦可使人具有灵性之光,成为精神和德性之子;再次,人因堕落而与上帝疏远,自我救助之路从此堵塞;最后,人靠上帝的恩典能够得到拯救,从此,人之生命的深化和超越获得了超然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基督伦理对人的理解归纳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本体上的有限性——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这种源于受造的有限性是人本身无法突破的本体上的界限;二是伦理上的有罪性——因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而归算到每个人身上的原罪和每个人生来就在心思意念与言语行为上违背上帝律法的本罪。这就是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如果没有人类的堕落,那么基督教的全部历史的编造,目前的基督教的宗教热情和道德所根据的原罪和赎罪的原因这段故事,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2](P1059) 人在本体上的有限性和伦理上的有罪性反映到宪法理论中,有限政府的观念脱颖而出。
1.权力的界限之一:权力的派生性。权力来源于上帝,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派生的。《圣经》中,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是真正的救世主。从这一观念出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的授权。[3] 国家不是救世主,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上帝。
2.权力的界限之二:世俗权力只及于“属人”的外在的世界。在对《圣经》的阐释中,神学家很早就造就了“两柄剑”理论:即精神之剑和世俗之剑。这一理论将世界分为属人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世俗国家的权力(即世俗之剑)仅及于属人的世界,而且要受到属灵(精神之剑)世界的监控,王权在理论上不具有“神圣”
性。这样,国家权力的边界被划定。马丁·路德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更为质朴。“人的制度,绝不能把它的权力扩张到天国和灵魂方面,它仅仅属于这个世界,属于人与人的外在关系。”“灵魂并不在恺撒的权力之下,恺撒对于灵魂,既不能教训,也不能领导;既不能毁灭,也不能养活;既不能捆绑,也不能释放;既不能审判,也不能定罪。”[4] 这样,世俗国家干涉公民信仰的精神暴政在理论上就被排除了,宗教信仰自由得以在世俗国家确立。①
3.权力的界限之三:只有正当行使的权力才是上帝赋予的权力,人类不服从不道德的权力。《圣经》将世俗权力解释为神授的同时,对权力的行使作出了限制。可见,“一项不道德的法律在良心上并不认为具有拘束力,而且可能不服从它乃是一项绝对的义务”[5](P203)。
4.权力的界限之四:人类的立法不是恣意的,受制于上帝的律法。人类的立法不是主观的创造,是发现——对上帝旨意的发现。“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是神赐予的礼物——明智者的戒规。”宪法不是人类制定的,而是人类发现的神的本性。“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它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浸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相对于这些原则而言,当人法除某些不相关的情况而有资格受到普遍遵行时,它只不过是这些原则的记录或摹本,而且制定这些人法不是体现意志和权力的行为,而是发现和宣布这些原则的行为。”[6](P5) 既然人类的立法只不过是对上帝旨意的发现,那么,上帝的律法就绝对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不仅是基督徒个人生活的标准,也是社会立法的标准。
二、宪法的彼岸世界之二:自然法理论
基督伦理构造了有限政府的理论,但人权观念的产生要归功于自然法理论。尽管在基督伦理中,人是有灵的,但人的有灵是相对于动物而言的。人的个性的张扬,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在基督伦理中是无法产生的。人因悖离上帝而有罪,“悖离上帝意味着转向自我或事物,即崇拜自我或崇拜世间的人或物;疏离‘存在’意味着迷恋‘存在物’,即沉迷于世上的人、物或自我,以这些东西为人生的终极关怀”[7]。既然迷恋自我是“罪”和苦难的根源,人权的概念当然无从说起。
不同时期的自然法理论仍然有共通的内涵,那就是作为终极道德和政治权威的力量。西方学者托尼·本斯认为这一定义具有七大特征:第一,存在着某种不依赖于任何特定国家之实在法的自然法或自然正义原则;第二,通过人的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第三,存在着一些本质上可以被定义为坏的或非正义的行为;第四,自然法是不可改变的;第五,实在法的惟一功能就是以其强制性认可和执行自然法的原则;第六,自然法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或外在的解释;第七,自然法中包含着对实在法正义性评估的批判性标准。[8](PP16—20) 作为实在法的批判性力量,对人类理性的信赖,一直是自然法理论的品格。但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变迁则是从中世纪才开始的,从自然权利中延伸出人权的概念,则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硕果。
近代自然法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人权的产生准备了土壤:第一,自然人性是近代自然法的基础,为弘扬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准备了条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人作为主体的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神性作为人与上帝沟通的纽带功能被削弱。“自然法并非隐藏在宇宙的‘幽冥之处’,而存在于自然人性之中。”[9] 第二,自然权利的概括,为自然权利向基本人权的转变准备了条件。人之为人所拥有的平等、自私、自主、自尊和自卫之类的“自然本性”,因为源于自然,又为人的理性支持,被近代自然法学家宣布为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出自“本性”、“自然”,来源于超验的自然法,因而实证法不得剥夺和践踏。又因为“本性”是人所共有,表达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性,因此,自然权利或本性权利就是人权。[10](P128) 第三, 自然法关于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阐释, 提供了政治正当性的标准——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的,为处理人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准备了理论工具。在近代自然法学家看来,国家不过是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权力的根本功能是保护原子化的个人的自然权利。近代自然法学家“渐渐发现,法律不仅是抑制无政府状态而且也是抵制专制主义的堡垒”[11](P63)。
三、构造的彼岸世界与思辩的此岸世界的意义
我们一直都在用叙述的方式描述宪法的彼岸世界。这种自说自话的方式很容易遭到诘难——为什么不用思辩的方法呢?只有思辩才是正统的法学思维呀!只有思辩的东西才能称为哲学呀!主张用思辩的方法去解决任何问题,显然是对人类思辩能力的致命自负。思辩的方法本质上是科学主义的,但科学从来就没有彻底解决过(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芸芸众生的苦难。
宪法的彼岸世界为宪法的此岸世界提供了价值基础,此岸世界的经验则为彼岸世界的价值提供了实现的路径。康德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在科学意义上的关于上帝存在、自由和不死的知识”,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证明。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前提来推演,从而得出如何行动的结论。[12](P187) 尽管我们无法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观察和研究彼岸世界,但彼岸世界仍是必要的。因此,人类行为的最终合法性其实是一个不能追问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彼岸世界。
此岸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宪法的此岸世界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我们把法律理解为对世界的一种阐释方法,不同的人们必然会有不同的阐释体系。当然,任何阐释都是有前见的阐释,对宪法现象阐释的前见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和基本人权的理论。政府为什么必须是有限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基本人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人权就是人权,恰如上帝就是上帝。我们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宪法的彼岸世界。
既然我们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研究彼岸世界,宪法的彼岸世界可否从我们视野中消失?或者一概称之为迷信?如果宪法的彼岸世界某一天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将宪法彼岸世界生发的有限政府理念和基本人权理论抛诸脑后,我们用什么评价此岸世界的宪法制度安排?用什么评价宪法的正当性?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宪法就是主权者的总命令。这样推演的结果:宪法是权力的婢女。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宪法学理论,宪法学就会沦为权力的附庸,最终丧失对权力起码的批判能力。如果说,宪法的彼岸世界过于玄妙,实务部门甚至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只能关注宪法的此岸世界的话,那么,法学的研究、特别是宪法学的研究则不能不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彼岸世界。
将宪法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理论应用在方法论的层面,我们会发现: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庞德概括的多种法律解释路径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的多个世界存在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进路,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会割裂法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庞德归纳的法律解释方法我们可以在宪法的解释中应用。从这个角度看,童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赵先生的研究方法都会肢解宪法的整个视域。童之伟先生用的分解、相加、再还原的方法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的产品,而科学主义的方法只能用于研究宪法的此岸世界。康德认为通过经验的知识是有限的,分析在认识领域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理性之一切理论的学问皆包含有先天的综合判断而以之为原理。”[13](P35) 赵世义先生的研究方法在否定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同时,将价值构造的方法推到极致,这同样会将宪法学的研究引入歧路——宪法学的研究和神学的研究有何区别?② 经验给我们提供了知识的质料,没有对于经验的分析,抽象的综合和价值构建是没有意义的。
就宪法的此岸世界而言,科学主义的方法的确大有用武之地。波斯纳的宪法经济学、法律的博弈论都可以采用,甚至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也可以变为数学模型推导出宪法的许多制度安排。童之伟先生的分解、相加、还原的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宪法的此岸世界。但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推及宪法的彼岸世界,几乎无法在逻辑上一以贯之。以童先生的方法为例,如果我们把宪法看作是“分配法权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法律形态,[14](P443) 是不是任何分配方案都正当?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必然是摈弃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客观和价值中立是科学主义研究的基本立场,而宪法学的研究恰恰不能摈弃价值判断——宪法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部门法确立基本的价值底线。其实,童先生也承认:“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一国的全部法权都是属于社会成员的,因而国家权力也理所当然是属于社会成员的。他们只是将全部法权中的一部分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这部分法权就转化为国家权力。”[14](P444) 这个价值前设就无法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推导出来。
构造的方法可以适用于宪法的彼岸世界,这种方法提供了宪法的基本价值预设。但价值的方法同样不能推及宪法的此岸世界。价值的方法不顾及此岸世界的差异,其价值观是普适的。如果不研究普适性价值的实现机制,不观察普适性价值实现的差序格局,宪法就无法解决芸芸众生的苦难。将宪法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理论用于观察中国的法治进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和法治的本土资源理论都有用武之地。关于法治的普适性价值是宪法的彼岸世界生发的,我们无法追问为什么。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我们怎么样实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在实现法治的普适性价值进程中,我们无法回避本土资源。
法学研究中的“折衷”经常被人鄙夷,往往被指责为“什么都没说”、“剑走偏锋”式的片面做法一般被称作得出“深刻结论”的不二法门。令我们无奈的是,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折衷的。就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就中国的法治资源而言,我们的结论几乎是“无可无不可”。没有不能运用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宪法的不同世界。普适性的法治价值和中国的本土资源都可以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出力,普适性的法治价值来源于宪法的彼岸世界,中国的本土资源来源于宪法的此岸世界。
注释:
① 基本人权体系中,精神领域最重要的人权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物质领域最重要的人权形态应该是财产权。
② 与之类似的还有伯尔曼和泰格、利维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不同解释进路。伯尔曼关注教会革命,而泰格、利维则关注市民社会阶层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用我们的观点看,伯尔曼实际上关注的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彼岸世界,而泰格、利维关注的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此岸世界。正如泰格、利维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保证自己理论逻辑上的自恰,泰格、利维不得不故意对大量的史料视而不见。应该说,这两种单一的解释进路都在阉割西方法律传统的完整视域。同样,德沃金和波斯纳的争论实际上未必构成真正的论争,他们诉说的是两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C].周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2]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M].吴文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Rousas John Rushdoony,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Order,p.53.转引自王志勇:《浅释加尔文论公民政府》,2003年3月10日在公法评论网上搜索。http://www.gongfa.com.
[4] [德]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2003年3月23日在公法评论网上搜索。http://www.gongfa.com
[5]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6]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强世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7] 何光沪.马丁·路德的遗产[J].读书,2003,(3).
[8] Tony Burns,Nature Law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M].Avebury Publishing Ltd,1996.
[9] 黄颂.自然法:充满歧义的文化理念[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2,(2).
[10]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1]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13]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14]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晨晓
英美宪法哲学刍议
许炎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英美宪法学者看来,宪法不仅是一种塑造着国家历史的重要工具,而且像民众的某种宗教信仰一样,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超验的、无所不在的品质。尽管英美国家的法学家较少专门研究概念上所谓“宪法哲学”的问题,但类似的宪法理论却十分丰富。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这些学说适应宪法总体结构的方式。这些理论既非自足的,也非静态的,相反,他们随着时间而相互交叠,循不同方向演进。实际上,英美宪法哲学理论对宪法的认识和理解充满可争辩性,在学者中一直是激烈论争的领域。了解英美宪法哲学的相关问题,或能对我国当前宪法哲学的构建与发展有所借鉴。
一、英美国家关于“宪法哲学”的概念
与中国宪法学者所提出的“宪法哲学”概念相对应的英美宪法理论主要是关于宪法的政治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前者如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后者如哈耶克的认识论哲学,构成了其宪政理论的基础。
(一)宪法的政治哲学
自然权利与自然法则奠定了英美宪法的政治哲学与道德推理。[1] 以美国为例,这些观念解释了制宪时代美国人民对于政府的认识。正如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所述,基督教传统上的自然法由渊源于神的启示的命令与禁令组成,诸如《十诫》。[2] 但宪法的制定者是洛克派哲学家,而非托马斯主义者。[3] 对他们而言,真理来源于人的理性而不是神。[4] 他们认为存在一个人类与生俱来的伦理体系,仅仅只能被人类理性所发现。约翰·洛克想象,在自然状态下市民社会与政府均不存在,个人是其本身的君主。托马斯·霍布斯把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描述为“孤独的、贫穷的、肮脏的、粗野的和短暂的”[5]。于是,通过社会契约产生了市民社会:个人同意建立政府并让渡出一些个体自由给社会以保护自身追求幸福的权利,包括获得并享用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能使其个人独立并能自由行使其他权利。因此,自然法则构成连接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或自然权利与政府的纽带。政府确实并未赋予人民任何权利——他们与生俱来、不可分割。在美国最初的居民看来,“新世界”类似于自然状态,他们有义务签订一份社会契约。于是,从“五月花号协议”,到《殖民地宪章》、《独立宣言》以及导致1787宪法制宪会议的早期州宪法性文件,美国人在宪政实践中逐渐提出了其宪法的政治理论。《独立宣言》催生了美国宪法,因为平等赋予所有个人的权利必须有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来维护法律与秩序。宪法制定者们认为整个宪法就是某种权利法案,限制政府对自由施加的任何威胁。[6] 在宪法实施之后不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开始争论,能否根据自然法运用司法审查撤销制定法。理论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否定这一观点,其判决仅依据对宪法的正式法律解释;但实践上,法庭对宪法的解释通常似乎与法官对宪法文本所加入的标准与价值密切相关。
从英美宪法产生的根由上看,宪法的意义在于确立制度安排、限制政府的权利和保护个人的自由。宪政主义者们认为,每个人周围有不受公共权力干预的自治领域,它划定个人的隐私与尊严,免于政治权力(政府)的干预。当代英美宪法学者们对宪法的认识也多着眼于宪法的实质内容,从权与法的关系分析宪法。[7](P22) 他们认为,宪法含有三层意思:第一,指各种强制性规范,强调对政府活动的限制,给予公民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指用以体现或不得体现这些规范的一种基本性文件;第三,指政治团体的实际组织,对政治制度的概述。[8](P266)
(二)宪法的认识论哲学
如果说英美宪法的政治哲学确定了宪法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其认识论哲学则要解决宪法应当如何的问题。尽管英美宪政发展的纷繁复杂各有不同,但其核心价值基本相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限制权力与保护权利。伴随其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如何看待宪法在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域与私域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也成为一个认识发展的问题。
17、18世纪英美自发的市场秩序表明,这种经济运行能使分散的个人利益得以和平地协调,政治决定在资源的组织、分配和生产过程中影响较小,从而大大限制经济生活中政治决策的范围,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侵犯。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家干预不得不成为必要,从而开启政府权力扩张之门。正如经济学家布坎南所发现,政治活动家们并非不带任何私人利益的个体,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和规模,超过任何可以想象的“公共”界限。只有政治的、集体的、政府的或国家的活动范围受到可强制执行的宪法的约束,才可有效阻止这种过分的扩张。[9](P121) 在哈耶克看来,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对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最可欲和最有效的规则体系的问题,比如应该为财产权利划定什么样的范围和限度的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他认为,并非单靠经济学上的财产权制度就能解决这类问题,经济学关注的应是宪政分析,即对各种规则体系中的综合运作特性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局促于特定政策的具体效果上。通过提供各种供选择的规则体系所可能产生的行为模式之综合性特性的比较性分析结论,宪政经济学可为宪政政治学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唯有依靠这样的宪政政策,才可能“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也即我们更愿意生活于其中”。虽然哈耶克与布坎南是经济学家,但他们均十分重视宪法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对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的影响。两人分别代表宪法理论的两派:行为选择学派(哈耶克)和社会契约论(布坎南)。[10] 哈耶克认为人群正常地形成一个社会,是源于他们服从相同的行为规则,而非授予他们自己一些法律。此即所谓多数之权力被共同接受的原则所限制,合法的权利不能超越这原则。这一原则是尊重个人选择自由的原则,不同于布坎南的契约式的议价原则。布坎南将所有待集体决策解决的问题分成两类:宪法类与一般法律类。宪法类包含在多数之下的少数人所受伤害甚大的问题,如政府权限、自由、权利与义务等,以及未来议会通过一般法律类规则的制订规则。
总之,英美宪法认识论哲学的目的致力于如何从宪法着手保护个人自由和维护市场秩序。立宪主义的精髓也就在于,宪法是权力之源。
二、英美国家研究“宪法哲学”的诸种学术派别
有学者认为,“解释”是现代宪法理论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词。[11] 对宪法解释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反映了当代宪法哲学中几个突出的根本原则,即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男女平等主义理论、批判的种族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源于启蒙时期,强调个人权利。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但与此同时构成实现和行使权利的最大威胁,因此需要通过宪法约束政府权力。现代立宪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但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分支,如法律实证主义、基于程序的法理学、新共和主义、法律与经济以及实用主义等等。[12] 这一过程中不同观点之间论争激烈,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未受管制的市场不能满足公众福利,政府有必要纠正不平等的财富与权力分配;但其他学者认为个人权利的领域必须尽可能地免于政府干预,以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治。他们一直强调公民自由与公民权利在取得社会正义上的优先性。
正如现代自由主义理论追随洛克的自由主义而走向左倾,现代保守主义宪法理论则走向右倾。[13](PP507—510) 与制宪者同样,他们保护财产权并承认财富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对宪法的认识上保守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的采取探究宪法原初的办法解释宪法,有的则倾向于文本主义,较先例原则更注重历史与传统分析。保守主义者尽管尊重司法特权,但不同意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主张多数人理论。在保护个人权利上,他们质疑非文本的宪法分析,但在实施分权与联邦上他们热衷于非文本的结构解释。实际上,保守主义涵盖了许多法律与经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原则去描述或预测政府决策者的真实行为,包括立法者和法官。[14] 然而, 保守主义理论否认自由主义的信条——宪法应与时代协调且法院主导,相反,他们坚持法官应与时代协调以符合宪法。[15]
男女平等主义理论把妇女权利保护整合、统一进宪法。批判的种族主义理论致力于分析白人主导的法律体制下种族与民族问题,努力公然地或隐讳地对抗种族控制。后现代主义理论则是一种反对理论的理论,质疑整个法律解释学①,质疑内涵或意义的意义,否认推理;通过否认任何根本性的东西颠覆哲学权威。但尽管遭到许多学者批评,后现代主义仍成为法律学界的主流理论之一,并对司法产生影响。它削弱对宪法解释的传统理解,认为是解释者的理解,而不是法律文本有意义。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菲舍,坚持法官不能局限于理论或外部规则中,而应以其本身的方式行为,因为他们个人深深地植根于法律和裁判的环境中。[16]
应当承认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但试图以一概全并非正确之举。其实并无必要权衡比较出优劣,如此之多的理论本身已说明,宪法在个人生活、市民社会以及国家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三、英美宪法哲学对我国宪法哲学研究的启示
从英美宪法哲学可以看出,宪法的作用在于限制权力、保障私权、巩固政权并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我国,学者们对于宪法的研究与宪政实践的发展相联。20世纪30年代主要集中在比较法学层面,在整理宪法知识的过程中注重了宪法文化特性的研究,但因宪法实践是党派政治理想和主张的表述,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宪法实践上,宪法自身的逻辑规律与历史传统被否定;80年代后宪法逻辑学的思考方法逐渐为宪法学者认可,宪法学研究体系呈多元化趋势。[17] 但对中国而言,摆脱工具主义的立宪观,实现以限制权力、保护权利这样的价值取向来行宪,仍然是其奋斗目标。英美宪法哲学之于我国而言,至少具有一点启示,即强调法治社会中宪法对权力的控制与约束,使政治关系置于宪法的支配之下。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如何维护宪法的至上性是其重大理论课题。一方面宪法要积极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以宪法的规范性约束社会的现实性。社会变革时期容易出现合宪性危机问题,因而更有必要维护宪法权威,根据宪法规范及其确认的原则判断变革的需求妥当与否。[18] 宪法哲学以权力和权利为研究范畴,两者间的关系构成其关系网络。[19] 有鉴于我国宪法文化传统上对权利的忽视以及现实生活中权力的膨胀,本文认为我国的宪法哲学应以保护权利与自由、维护公正与秩序为基本的价值目标进行构建,以引导中国能尽早走向真正的宪政之国。
注释:
① “[T]here is really no identifiable hermeneutic party in current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ory.”John T.Valauri,Interpretation,Critique,and Adjudication:The Search for Constitutional Hermeneutics,76Chicago.-Kent LawReview 1083,1086(2000).
参考文献:
[1] 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7.
[2] Michael V.Hemandez.A Flawed Foundation:Christianity's Loss of Preeminent Influence on American Law[J].56 Rutgers Law Review 625,634—38.
[3] William J.Stuntz.Christian Legal Theory[J].116 Harvard Law Review 1707 (2003).
[4] Robert Lowry Clinton.God and Man in the Law:The Foundations of Anglo-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M].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1997; Ellis Washington.The Inseparability of Law and Morality:the Constitution,Natural Law,and the Rule of Law[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2.
[5] Thomas Hobbes.Leviathan[M].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C.A.Gask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651).
[6] Alexander Hamilton.The Federalist No.84[M].ed.By Clinton Rossiter,New York:Mentor Books,1961.
[7]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8] Jean Blondel.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Government[M].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9]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黄春兴.经济学者的修宪论:哈耶克与布坎南的争议[J].当代(台湾版),1992,(5).
[11] Paul Campos.Three Mistakes about Interpretation[J].92 Michigan.Law Review 388(1993).
[12] Thomas Grey.Modem American Legal Thought[J].106 Yale Law.Journal 493 (1996).
[13] Walter Betas.Conservativism [M].in 2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eds.by Leonard W.Levy & Kenneth L.Karst,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 USA,2000,2nd ed.
[14] Daniel A.Farber & Philip P. Frickey. The Jurisprudence of Public Choice[J].65 Texas Lan,Review 873(1987).
[15] James A.Dom & Henry G.Manne Economic Liberties and the Judiciary[C].Virginia: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87.
[16] Stanley Fish,Fish v.Fiss [J].36 Stanford Law Review 1325(1984).
[17] 莫纪宏.论21世纪的宪法学构建基础[J].法学杂志,2000,(2).
[18]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J].法学评论,1999,(4).
[19] 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J].政治与法律,2003,(1).
责任编辑 晨晓
论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对宪法知识的文化重构
——以语境论为分析工具
张烁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宪法学界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不能单独的移植和研究原生于西方价值系统中的“constitution”,而应该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构建中国的“宪法”。也有学者看到中国人在接受宪法概念和理论时把西方宪义转变成为国人所接受的范畴。这种词与物的不对应影响到我们对宪法的认识与相关制度设计。笔者也坚持这种思考角度,并且认为:如果把西方宪法界定为关心秩序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知识体系和制度设计的话,那么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也一定存在着某种知识和制度①,它解释了人类秩序的产生和状态,回答了个人为什么在社会、国家等秩序现象中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它应该是一套与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语境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系统,尽管它可能未能抽象出西方式的尊严、理性、人权等范畴,尽管它回答问题的思路可能与西方文化中的解读有着天壤之别。这种知识赋予了我们在社会、国家等权力组织中生活的方向、勇气和自信。
但本文并非想完成概括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基本法知识② 的任务,而是希望利用西方知识传递与接受的有关理论去描述近代中国基本法知识变迁的一个重要过程,即在近代语境中,西方世界的宪法知识作为一剂药方被引入国内以期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它与作为国人头脑中的“前见”知识的儒家文化思想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两种不同源流、内容的知识在语境的支配下,曾产生了冲突、交织和整合,西方化的术语和范畴被吸纳,而自由与秩序、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念却在两种知识力的作用下得到了重构。国人正在这种重构后的观念进行着近代宪政运动。而关于文化重构的反思对于目前宪政建设的重要性则往往被现代的研究者所忽略。
一、宪法知识传递中的“前见”和“语境”
人们在知识的学习和传授过程中,都希望用确切的、固定的语言词汇进行表达,然而“词语意思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③ 是虚幻的”。因为“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到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1](P2) 当人们用一定语言进行思考时,必然受前人对一定词语中注入的意思的影响,但是后人只能用从小在文化中习得的固定词语去认识和表达事物,故这种前见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对宪法理论的研究也不可能不受到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描述、说明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时候,学者们必然是在依赖自己以往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的基础之上进行观察分析论证的。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由于这种“前见”作用机制的存在,因而在某个理论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问题、该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以及对问题的研究结论如何作用于社会现实从而使之由理论上升为实践等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后者对前者的承继性。
由于知识传递中必然存在这些“前见”和“偏见”,才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形成所谓的派别、谱系。在学术谱系之中的学者们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通常会因为使用了熟知但却具有指示意义功能的概念范畴,而造成在分析角度、论证过程以及结论上有着连续性的继承。就宪法概念这个问题而言,虽然90年代后宪法概念的研究视角出现了多维度的发展趋势,然而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上的承继。如新的概念定义仍然将宪法看作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然而论证这个问题时,仍是采取旧有的思路: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根本依据,所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超越其他法律的最高效力。虽然采用了西方法学界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范畴,但并未像西方学者那样以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来论证宪法的最高效力问题。因为我们用以论证问题的词语和范畴本身是带有“前见”的,它们指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对类似问题的价值排序和意义安排。我们在使用这些词语说明问题时,也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种意义指示和思维定势。我们既然用了“根本大法”去解释了宪法,所以我们必然会用“最高法律效力”去说明它的效力地位。因为,在我们的“前见”中,“根本大法”和“最高效力”已经连接成为无须逻辑证明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不会因为定义内容已经从“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演变为“宪法规定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发生任何改变。
目前的宪法概念问题研究中常具有这样一种学术策略,即汇聚所有时间空间的人们用“宪法”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抽象得出一个研究该现象的宪法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宪法学理论。然而概念的不周延性和不完整性使得“它们无论单个的还是综合在一起,都无法克服这样一个根本缺陷,即无法在必要的抽象程度上概括出不同历史类型、不同国别的宪法所共同包含的最基本的内容或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2]。自然, 这种“科学主义”意味很浓的分析路径也是历史形成的结果,与具体的社会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要想在这个研究课题上有所突破,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学术策略有着必要的反思。
中国目前的“宪法”作为一种描述制度的知识体系,它所包含的“前见”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西方世界中的“宪法”理念和制度体系;二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基本法知识;三是马列主义和前苏联以及日本的宪法观。需要考查的“语境”除了东西方各自原初的社会宗教文化之外,尤其应该注意中国近代时期对宪法知识的移植与重构。因为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学和社会科学皆产生于本世纪初,它们同是文化移植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语言变革在内的极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移植’的发生乃是我们探究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学术发展时需要面对的最基本事实。‘移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变形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外来的与固有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情感的与理智的、习惯的与创新的、观念的与行为的、思想的与制度的,各种因素彼此纠缠、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形态。处于这种情态之下,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3](P6) 在这个时期,各种“前见”交互作用,知识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互相影响,使得国人在用“宪法”一词接受西方文化中的“constitution”时又不得不变更它的具体内涵,刻入中国文化的痕迹。
二、西方宪法传入近代中国时面临的语境
在19世纪中叶前,儒家的政治控制模式和理念并未发生危机。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社会各方面逐步陷入了危机状况:儒学在应付社会危机和外来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思想上的匮乏和无力解释,也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传统价值失范的局面。知识分子只能继续前人的思路,在传统思想资源中一面寻找改革弊政的良策,一面努力寻求文化汇合时心理平衡的支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忧患,使得末世儒生们逐渐意识到现实国家秩序中确实有些不适应时局的方面,而在传统儒家自身学说框架中,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只能被迫将目光投向“敌人”的文化,开始漫长而痛苦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④。中国人在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解读和重构西方文化,学习其中的方法和策略来追求国家独立和富强,开始自己的近代化进程。
在一种直观感受的牵引下,民族的悲惨命运必然引发知识分子对中西方各国军事、经济、制度、国情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比较。比较的结果则得出“中国的积弱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的经验教训,所以“强兵富国”成为重要的价值追求⑤,而从西方文化中寻求富强的方式以为我所用则成为主要的应对之策。
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语境: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当作最高价值被突兀出来,成为国人批判传统和评价现实的主要标准,也是审视西学和学习西学的根本依据。国人们言必称“文明”、“进步”、“自强”,而在这一种充斥着西洋话语及其价值判断的语境中,“富强”无疑是平复民族创痛、强化民族自尊心的最具号召性的词汇。所以“追求富强”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又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性。西方文化中的种种要素必须与国家富强这个目的联系起来才能进入人们的讨论范围,而且,那些被认为能够有效地、迅速地提高国家实力的要素,则很快地成为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中心议题,并得到改造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当中。先是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引入,而后才是民主、宪政等制度文化的移植。
宪法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来的:据考,清朝末年的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制定宪法的主张。1908年9月, 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才成为我国官方的正式用语。[4](P16) 在这种语境中,对西方宪法文化的研究则必然地转换成为在宪政和富强之间探寻因果关系的实用性思考。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沙俄的事实更是让舆论界阐释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当时的《东方杂志》称:“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说曰: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而日本“以小克大,以亚克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5]。 国人在惊叹之余反思本国的改革,将当时改革的种种挫折归因于没有实行立宪,并真诚地认为如果能像日本那样实行立宪政体,则中国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欲救其弊,固非改政体不可,则立宪之说是已。……故立宪政体之于国,犹舟之有指北针也,否则迷阴而丧其行矣。”[6] 立宪成为国家自强的代名词。
语境决定着在中国的宪法知识一开始就不具有在西方文化中那样的独立的价值地位,是作为一种救亡的手段被迫引入的,故它从属于更高的价值范畴,而“作为西方文化的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地从‘道’变成了‘器’,从‘体’变成了‘用’,由一个形上的文化问题变成形下的功利问题”[7](P10)。
三、对西方宪法知识的重构途径
王人博先生在《民权词义考论》一文中用了物境、联想和记忆三个很有意思的
术语来描述词义是如何发生文化重构的,认为“近代中国的物境(circumstances)使中国的知识者对西方因民权而强盛的成功经验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不管西方的强盛真的是否由民主所致),民权便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可替代性方案。为了医治由联想可能出现的自卑感和挫败感,中国的知识者便从民族的‘民本’记忆中找到了灵丹妙药。民族的民本记忆无疑是缓解由西方民主的诱人联想可能产生的疼痛的一剂解药”[7](P30)。他看到了近代“物境”中最主要的两重性,即在民族危机下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文化移植时保持对传统文化的自尊的重要性。并且发现了文化重构中“联想”和“记忆”这两种心理过程对于物境满足的功能。这的确是对文化重构现象和过程的最形象的描述,然而,运用该方式解读的文化重构过程似乎更具有主动性,参与其中的人似乎都很明确地在为重构西方文化努力;它忽略了重构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重构方式是在文化“前见”的作用下形成的,而这种作用大多发生在人们心理的无意识领域之中。
语境本身是“前见”处理的结果,它与表示客观实在的“物境”略有区别,是人们对客观实在归纳抽象出来的理解。近代中国语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政治上国家的富强独立;二是中西方文化的定位,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定位。在传统儒家“时”的观念的作用下,产生了“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话语: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时局的要求,成为人民进步和国家发展的最大阻碍,而西方文化则被视为救世良方,一切对改革有利的因素都应该被整合到文化重构中去。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传统的最高价值被“富强”、“进步”、“文明”等西语范畴所取代,但是将一切价值都置于最高价值之下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近代中国被看作古代“一乱一治”模式的延续,而政体之变只不过是一种“治乱之道”,一种强盛追求的“术”而已。同时,语境又是文化重构的前提,它限制了重构的目标和内容。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一切吸纳和重构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强盛,所以西方文化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导致国家强盛的因素才能进入知识分子重构的框架之中,如军事技术、经济制度等等;还有些因素则必须在解读中与最高价值目标联系,才能被人们所认可和学习,如西语中的人权思想只有被解读成“民权”(认为它是民族独立权利的始源)与民族独立相沟通才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那些无法与当时的国富民强任务相联系的因素则进入不了文化者的视野,如宪政文化中的“有限政府”观念。内外交困的境况使得人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以限制自己权力的政府的出现,故这种观念就没有被解读出来。
重构是在“语境”和“前见”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语境决定了重构的价值方向和目标,而前见则为重构提供了思路和思想资源。与传统儒家寻找事物合理性的方式一致,近代国人们也是在虚构的历史叙述中寻找理解西学的线索,也满足了心理的平衡。如康有为更是虚构出“孔子是天下改制第一人”的论断来支持维新变法的主张。
另外,重构后的思想和观念通常用中国旧有的词汇和叙事方式表达,也传递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排序和思维定势。如代替人权思想的“民权”。由于在传统观念里,“民”是与“君”对立的,因而旧有的君民对峙的关系也被传递出来。人们仍然在一种对峙框架中,把西方的主张人的理性和自然权利、追求个人独立和尊严的带有平等意味的“人权”解读成旨在重新安排君、民顺序的“民权”观念。
四、对西方宪法知识的解读个案
在语境和前见的作用下,近代知识分子解读了西方宪法知识,并加以文化上的重构。
在宪法法律效力问题上,我们是用古代的“典”对宪进行重构。这样虽然解读出来宪法的根本法、大法的概念,但是有关法的效力位阶问题是无法涵概和理解的。宪法只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发挥着古代典象征的功能,但在现实中是被虚置的,没有形成宪法规则对于其他部门法规则的统摄。
在权力的政权正当性问题上,首先是用古代的“命”对宪法进行重构,使得统治权的天命论证被宪法的正统和稳定性所取代。整个近代中国出现的政权都在努力地论证自己的正统性,其主要的标志都是宣布对约法的尊崇,通过宪法形式上的稳定来表明授权的正当。这仍然是古代中国用以论证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性命之学”⑥ 中表现的基本思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宪法的稳定性确实能得到维持,但是宪法内容本身的正当性是被忽略的。而且,只作为证明“命”存在的宪法原则是可以被具体规则所突破的。其次,中国式的“君为天,臣为民而政”话语解读了西方宪法文化的契约话语,以合意对契约精神进行重构。如国民党时期形成的党治,就是以党员大会虚拟公民大会,希图通过所谓精英分子的意识整合来模拟西方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但党内部的组织逻辑与向下负责的代议制逻辑恰恰是相冲突的,也就是说,实质上是以行政专制性的合意替代社会契约论中的合意原则。
在权力的分配与运作规则问题上,是用传统社会的分工原则解读了西方用以维持法治体系的分权原则。即权力总是集中于一处,其他只是分工配合而已。另外,西方宪法中的正当程序观念也没有被解读出来。传统的实益公允原则使得我们无法认识到程序自身的价值。程序性的设计和运用都可以用一些正当理由予以践踏。
在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上,虽然接收了国籍、公民等这些西宪中的范畴,但是在传统社会有关“民”的知识的影响下,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思想很难被近代知识分子所理解。中国式的公民始终要分层次的,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分为“敌人”和“同盟者”。不同层次的人在权利义务配置上必须区别对待。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立法中公民法律待遇的区别可能已经淡化,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微妙态度将长期彰显着这种区别。
从时间层面上看,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宪法知识解释与重构过程已经结束了。重构后的宪法范畴与制度理解也随着实际发生的法制建设过程得到很大程度的整合。可以这么讲,我国的国家基本法知识已经发生了更新,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体系内的自治。这种知识体系已经构成了我辈学者理解宪法概念、思考宪法价值和设计宪法制度的一种“前见”。因此,对于这种前见的反思的重要性,在此不再赘言。
当然,完成关于宪法知识的文化重构现象的理解工作,非作者力能所逮。希望能通过本文唤起学术和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注释:
① 因为秩序现象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着的。
② 为方便研究,描述东方时使用“国家基本法”与西方“宪法”相对应。这一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创设。
③ 即主张语词自身有固定不变的意思。
④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是一个对西学价值判断不断抬升的过程。
⑤ 其实语境也是由前见形成的:这里“积弱”和“富强”的对应关系就表现了传统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是“乱—治模式”在近代中国的表征。
⑥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形成的道德之学、性命之学或正统之学就是论证政权正当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刘星.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民主的一个叙事立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童之伟.论宪法概念的重新界定[J].法学评论,1998,(3).
[3]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 吴家麟.宪法学[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
[5] 中外日报,1905—08—22.
[6] 南方报,1905—07—23.
[7]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晨晓
标签:哲学论文; 宪法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法律学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宪政论文; 以人为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