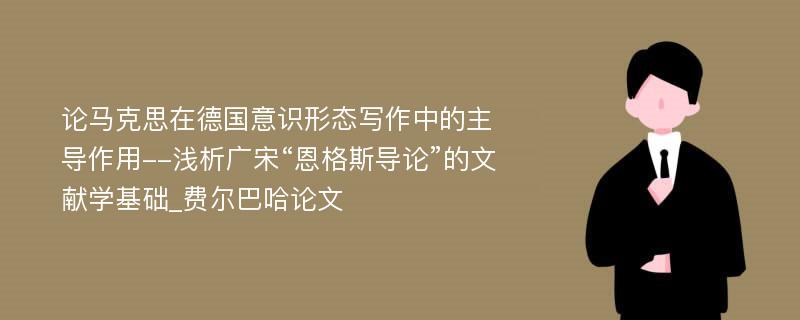
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析广松涉“恩格斯主导论”的文献学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德意志论文,马克思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主导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在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考证过程中,作为副产品提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地位问题。他认为,与通常人们形成的观念不同,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论据,其中文献学方面的依据首先和主要来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写作过程的考证。①
我认为,广松涉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的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启示;但对其基本观点却不敢苟同。他的文献学考证存在着根本缺陷。
一
首先,广松涉的论据仅仅是建立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已有不同版本考证和主观猜测基础上的。且不说涩谷正已经通过对原稿的直接调查,否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生产力”这一德文术语缀词法上的不同②,即使作为广松涉的论据的主要之点,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所谓“基底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这一公认的确凿事实,也是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广松涉猜测的主观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手稿{10}c=[25]页中恩格斯与马克思笔迹交替出现这一事实的解释上。他武断地说:“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的证据。”张一兵已指出了广松涉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推断”③。
在文献学考证方面我只想补充强调两点:一是手稿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笔迹的文字和符号确凿无疑地表明,尽管马克思直接动笔较少,但他对文章的内容、结构乃至于表述方式都具有不容怀疑的最终决定权;二是“基底稿”最后马克思所写下的供进一步修改手稿用的“纲目”(新MEGA Ⅱ称为“笔记”,广松涉称为“备忘录”),以及最后写下的“序言”(这两者均是马克思的笔迹),也都确凿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手稿写作过程的主导者和最后的定稿者。
二
更为重要的是,单纯文献学技术考证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只有将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结合起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费尔巴哈”时已有的明确署名文本或有把握确定作者的文本出发,将其同“基底稿”联系起来进行“互文式”的比较解读,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各自达到的思想境界,从而准确判断“基底稿”思想的原始提出者。
从这一观点出发,并利用新MEGA Ⅱ的考证成果,本文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进行三个方面的“互文式”解读:“第一卷”内部三章之间的比较解读、“第一卷”与“第二卷”之间的比较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比较解读。这种比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对施蒂纳的评价
主要是恩格斯于1844年11月19日和1845年1月20日在《致马克思》中论及施蒂纳的两封信与第一卷第三章的比较。
恩格斯在前一封信中对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原则具有“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我们应当“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④而在接到马克思回信后的第二封信中,恩格斯则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⑤
由于马克思的回信没有留传下来,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的具体观点。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现存手稿对施蒂纳的评价,恰好与恩格斯原有的观点相反。这一章认为,“‘施蒂纳’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⑥“他把费尔巴哈的这些变为主词的宾词神圣地奉为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的个人,他把这些有关各种关系的词句恭顺地看作是现实的关系,并给它们加上‘神圣的’这个宾词,又把这个宾词变为主词,变为‘圣物’,这就是说,他所做的同他责备费尔巴哈所做的完全相同。在他用这种方法完全摆脱了这里所谈的那种确定的内容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斗争,即放肆地‘仇视’这一‘圣物’,当然,这一‘圣物’永远是依然如故。……虽然费尔巴哈过分强调了反对这种幻想的斗争的意义。而在‘施蒂纳’那里,连这种意识也‘全部完了’,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⑦ 这就是说,施蒂纳不仅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甚至比费尔巴哈倒退了。
上述文本的比较解读表明,第三章批判施蒂纳的手稿体现的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回信中提出、后来又进一步发挥的思想。联系到陶伯特从写作风格角度作出的文献学考证,即“手稿恐怕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其篇幅在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长。此外,马克思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⑧ 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尽管这一部分的手稿笔迹是恩格斯的,但其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原先构成第三章一部分、后来转入第一章的“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的真正作者是马克思。
2.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评价
这集中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与第二卷对赫斯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通过对两卷文本的阅读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最初大概拟题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基底稿”(除了后来构成第一卷三章的内容外,还包括后来抽掉的赫斯所写的批判“格拉齐安诺博士”即卢格的部分),到后来的整个第一卷的三章中,尽管多处提到赫斯,但总的态度是肯定(两处)和中性(多处),只有一处有所保留,即声明“‘莫·赫斯’(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⑨。但是,第二卷从一开始的导论性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到第一章(“莱茵年鉴”)和第四章(“评格律恩”),即除了赫斯本人写的第五章(“霍尔曼”)之外的整个第二卷,却把赫斯及其著作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总代表进行直接(点名)或间接(不点名)的批判。
上述文本学的比较解读,得到了文献学考证的印证,这就是陶伯特文章提供的有关1846年2月底马克思同赫斯、恩格斯发生分歧与冲突的资料。据陶伯特文章说,“马克思在1846年2月底肯定写过一封信(此信没有留传下来),其中谈到一些明显的分歧,并怀疑赫斯和恩格斯是否有从事严肃的科学工作的能力。在一封同样没有留传下来的写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此信写于1846年3月23日的前两天或前三天,1846年3月23日寄给特利尔)中,马克思又一次谈到这些冲突,谈到他同赫斯在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由于这些冲突和意见分歧,燕妮称赫斯为‘纯粹的玄想家’,并谈到导致赫斯动身离去的“彻底决裂”。赫斯至早是在1846年3月22日、至迟是在3月29日动身离去的。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同魏特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引起了轰动)。”⑩“不早不晚,也是在那个时候,即1846年2月底至3月底,第二卷的计划也拟订好了,该卷分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诗歌、历史编纂学和预言等内容。”“魏德迈1846年4月中旬离开布鲁塞尔。那时已经确定出版两卷著作,其中第二卷的内容是评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11)
陶伯特的考证与我对文本的比较解读结果之间只存在一个差异:那就是陶伯特认为两卷的写作计划是在批判施蒂纳的“旧约”和“新约”之间(12);而“新约”(13)和“2、批判性的评注”(14) 的文本表明,其中对赫斯的态度并没有变化。(15) 因而我甚至推测第二卷的计划也有可能是在整个批判施蒂纳的手稿,即不仅包括“旧约”,而且包括“新约”甚至“2、批判性的评注”完成以后才制定的。这样一来,“三、圣麦克斯”就应完成于1846年3月22日—29日即马克思同赫斯冲突之前,而如此篇幅庞大的手稿就不大可能象陶伯特所推测的“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的”(16),而很有可能是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维干德季刊》发表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前,就作为独立的著作开始写了。这里有两个文献学证据:其一是“1846年3月24日,燕妮询问批判施蒂纳的著作写得怎么样了,进展如何。她没有提及其他手稿。”(17) 其二是马克思1844年12月在《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中也表明他在那时就曾经有一个要出版批判施蒂纳的书的打算。(18)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它同陶伯特关于文中标注的考证、特别是同“新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节正文中出现的 “这就实现了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虔诚的愿望”(19) 的证据相矛盾。但是,从这一点来看,起码迪特·戴希塞尔关于第二卷第四章“格律恩”可能写于《圣麦克斯》之前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一章开始不久就点名批判赫斯。(20)
联系到“1846年3月7日,丹尼尔斯在信中谈到马克思关于重新出版所谓的《德法年鉴》……以便‘审查’共产主义的哲学的计划”(21),以及马克思一贯的写作风格,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的第一章为马克思所写,更不用说后来明确署名马克思而公开发表的第四章了。至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本的结构和第二卷的思想属于马克思,这一结论可以说已得到基本确认了。惟一需要消除的疑问就是:赫斯是第二卷第五章的作者,如何解释“赫斯既是批判者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赫斯为什么愿意处于此种尴尬境地?
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第二卷导论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中。那里说:“由于德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中那些不久前写了我们在下面所批判的文章的人,究竟是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还是已经前进了。我们一般并不反对个别人,我们只是把刊印出来的文件看作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必定会产生的那个流派的表现。”(22) 这就是说,对赫斯为总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马克思自觉地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已经前进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正在前进着”,只有赫斯(尽管主观上想前进)最终没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实际上“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3.对费尔巴哈的评价
主要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札记与“基底稿”特别是“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比较。
由于“大束手稿”的二、三两部分已在前面讨论过了,这里只就第一部分进行比较。据陶伯特的考证,“这篇手稿是对鲍威尔进行批判的那篇文章的草稿,它没有完整地留传下来。此文批判的是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从留传下来的几张手稿看,对鲍威尔的批判是按照鲍威尔文章的结构展开的。留传下来的第6—11张的内容是针对鲍威尔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一部分而写的(鲍威尔在这一部分批判了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其内容主要是讨论费尔巴哈的‘感性’范畴。”(23) 与之相关的、有明确归属的文本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的札记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费尔巴哈”札记的写作时间,MEGAI编者曾推断为1845年秋,俄文第二版编者也曾推断为1845年11月,广松涉则推断为恩格斯1846年逗留巴黎期间,应马克思之约作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素材而写的。(24) 从这一文本的内容,特别是所反映的恩格斯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广松涉的推断是正确的。因为,一方面,其中的第3点(马克思改为“e”)关于“存在”与“本质”、“鱼”与“水”的论述,几乎完全再现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最后和巴纳1962年新发现的“半张稿纸”中。但另一方面,整个札记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全盘否定的,这显然与第三章既批判费尔巴哈又承认其历史贡献的基调不一致:后者强调“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25) 而我们知道,“大束手稿”的二、三部分原来正是属于第三章的。特别是札记中的最后一点即第6点(马克思改为“b”),更是全盘否定了费尔巴哈关于没有抽象的“自我”,个人总是男人和女人,并由此进一步引出人的类本质这一观点,不仅认为“如果费尔巴哈指的主要不是性行为、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人就是自我和你的统一”“这句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甚至说“正是因为人=头+心,为了创造人而需要两个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一个作为头,另一个作为心——男人和女人。否则就不可想象,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26)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直接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7}a=[12]页关于“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的论述相对立的:那里恰恰强调这种关系是从“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发展到“社会关系”的。(27)
上述情况表明,恩格斯的札记应写于1846年2—3月马克思同赫斯与他的争论之后,处于前面指出过的“正在前进着”的过程中,他直到此时的观点仍然与“基底稿”中以他的笔迹出现的思想有距离。
三
在明确了上述三个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以后,我还试图进一步说明恩格斯的这些转变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只要在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恩格斯观点转变的“断裂性”和马克思观点演变的“中介性”比较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主要涉及马克思《评李斯特》、《笔记本中的札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爱北斐特的演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有关书信、其他文章等文本的比较解读。在施蒂纳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是直接在马克思影响下转变的,前面已经说明。这里只简略地就后两个问题作一些比较。
在对待赫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表的态度上,恩格斯的转变有着明显的“断裂性”。恩格斯从1843年11月初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第二部分中,认定德国的“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赫斯“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28) 之后,一直“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写完《神圣家族》中他所分担的部分返回德国以后,他一直和赫斯等人一起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这在他的《大陆社会主义》、《爱北斐特的演说》(两次)和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如1844年9月20日写道:“在爱北斐特,大约有我的六个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29) 1844年11月9日又写了《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1845年3月17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30) 直到1845年10月恩格斯还为德国“共产主义杂志《莱茵年鉴》”和在瑞士的“德国的共产主义作家奥·贝克尔先生,以及属于同一党派的西·施米特先生和库尔曼先生”呼吁。(31) 而这些人正是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在“书信”中对赫斯态度的改变,根据我所掌握的极不完备的资料,首见于1846年7月17日和8月19日《致马克思》的两封信。(32) 最为明确的是1846年9月16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写道:“赫斯老爷子。……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我自然完全不理睬这个笨蛋……”(33) 并将赫斯的思想和著作称为“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34)。恩格斯公开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第二篇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分别载于1846年夏天出版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1846年卷)和1846年年底出版《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俄文第二版编者分别推断为“写于1845年底”(后改为“1845年下半年”)和“写于1845年年底”,我认为是错误的,这两篇文章都只能写于1846年2—3月马克思同赫斯决裂以后。(35) 这里有一个佐证,就是恩格斯以《德国状况》为总标题、用书信形式连载于伦敦《北极星报》的一组文章的突然中断。恩格斯在前两封信中叙述了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直到1815年拿破仑垮台得以“光荣复兴”的德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演变,从“第三封信”开始,转入研究“‘革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第三封信”写于1846年2月20日,载于1846年4月4日该报第438号,其中叙述了从1815年到1840年间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状况,并在结尾处预告“将在下一封信里谈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但是,恩格斯应允的最后一封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而是突然中断了。(36) 由于原定要写的“第四封信”的内容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到下面我要说到的马克思1846年1月的《声明》和前面已经说过的1846年2—3月马克思同赫斯和他的冲突,其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同样,在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上,恩格斯在1846年2—3月前后也出现了“断裂”。直到1845年2月2日,恩格斯还在以《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为总标题的第二篇文章中写道:“但是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欢呼:“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末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37) 但是,在前引的《费尔巴哈》札记中,他已经对费尔巴哈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了。
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之前的恩格斯书信和著作中找不到任何预示后来观点转变的蛛丝马迹相反,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看到观点演变的明显轨迹。在《神圣家族》和1844年8月11日《致路·费尔巴哈》的信中最后表现了“费尔巴哈崇拜”之后,通过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问题和英法社会主义文献,马克思开始怀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特别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更促使他重新审视费尔巴哈哲学以及从鲍威尔到施蒂纳的整个黑格尔哲学余脉。我作出上述推测的文本依据是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马克思的两部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两个计划(“现代国家”和“社会主义者文丛”)、两份札记(“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和“笔记本中的札记”)。重新审视哲学的成果,就是从《评李斯特》开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的颠覆旧“哲学范式”的根本思想革命。
陶伯特等人依据“在写有《提纲》的笔记本中,在《提纲》第一条前面有四行文字(即《笔记本中的札记》——引者)”,将《提纲》的写作时间推延至1845年7月以后(37),我认为有道理;但因此而指认马克思的《提纲》“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就失于片面和武断了。诚然,这“四行文字”的内容同《神圣家族》中“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直接相关,紧接着的《提纲》从论题上看也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论题的延续。(38)但是,《提纲》的写作意旨特别是立场、观点、方法却是对《神圣家族》同一论题阐述的否定和超越:费尔巴哈不再被看作终结了“概念”和“实体”的争论、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人,而是与包括法国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起成了批判的对象;原先肯定大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现在被认定为“抽象的人”,并以马克思自己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取代了。联系到在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费尔巴哈被授予‘实体’的骑士的称号”、施蒂纳的“唯一者”被称为“最强硬的实体”(40),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批判施蒂纳和鲍威尔一样是用“概念”来反对费尔巴哈“实体”,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以及边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不再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前提、而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四行文字”和《提纲》正是构成《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过渡的“中介”。我甚至推测其不仅写于马克思读了施蒂纳《唯一者》之后,甚至更晚,有可能《维干德》第三卷(1845年11月)以后,因为只是在这一卷,论战的各方才全面卷入。陶伯特等人认定《提纲》与《神圣家族》有关,其实不但不能否定、反而更加证明了《提纲》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联系,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动因恰恰来自鲍威尔和施蒂纳对《神圣家族》的批判。
从上述对这一文本的解读来看,“四行文字”和紧接着的《提纲》,正是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特别是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的思想提纲。而马克思写于1846年1月18日,发表于1846年1月26日《特利尔日报》的《声明》,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战争宣言。因为正是在这一《声明》中,马克思第一次宣布了他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彻底决裂:“我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41)
通过上述研究,我的结论是:尽管后来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基底稿”的笔迹主要是恩格斯的,但其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口授记录说”固然难于成立,但马克思叙述后,至少是在马克思主导下两人讨论后,再由恩格斯复述性地写下来的推断,应该说是合理的。
当然,认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键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应有地位,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广松涉《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一文的历史和理论贡献。不过,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注释:
①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375页。
②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③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2—263页。
⑧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页。
⑩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1)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2)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6—52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2—53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3、387、391、486、524页。
(16)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7)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4页。
(20)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21)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页。
(23) [德]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24)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2页。
(26)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27) [日]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299页。
(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36页。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0页。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1、676页;并见第6页、第35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6—653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595页。
(38) 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39)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1、53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7页。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读书论文; 神圣家族论文; 鲍威尔论文; 声明论文; 燕妮·马克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