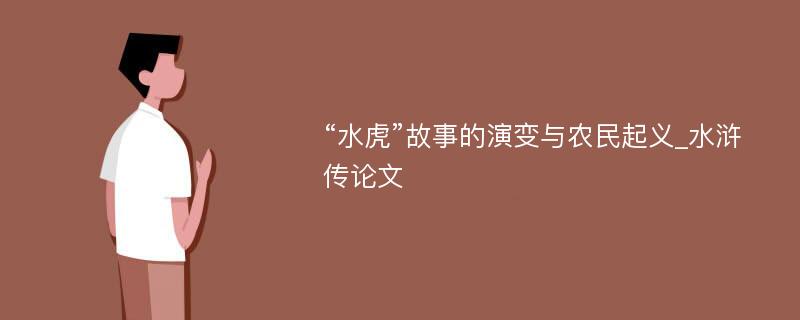
《水浒》故事演变与农民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起义论文,水浒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3—0132—006
我们在阅读《水浒》、研究《水浒》时,总有一个问题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事实上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也已提出,只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那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却只有在正史上并无详细记载、规模也并不很大的宋江起义产生了这么多的故事传说,以至于汇合、集纳为一部恢弘壮阔的《水浒传》?又为什么自古农民起义的领袖都被视为“匪”、“盗”,而宋江却终于享有了“忠义”的名誉,如元曲《同乐院燕青博鱼》中燕青语:“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宋江与方腊明明是同一时代的农民起义领导者,有何不同?论规模与影响,宋江甚至远不如方腊,为什么对宋江就要特殊看待?
要弄清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发掘有限的史料去再现历史中宋江其人及宋江起义的原貌是不够的。因为各种史载关于宋江起义的地点、活动范围、结局以及是否征方腊等多有分歧,相互矛盾,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印象。我们只能根据这样几条记录来判断一下宋江及宋江起义的情况:
《宋史·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这些记载给我们的印象是,宋江大约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至少能笼络、团结一批人在他手下。他及他手下的头领、队伍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宋江“勇悍狂侠”的形象特征与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宋江形象迥乎不同,这里面应当经历了一个对宋江形象的改造过程,实际亦即《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对宋江起义的性质与结局不断进行加工、增饰的过程。
一、前人的研究及“简先繁后”的误区
较早提出这一问题并进行研究的是李辰东与聂绀弩。李辰东《三国水浒与西游》[1 ]一书中“水浒研究”部分在谈及作者“同情心的建设”时认为,作者为力求作品得到读者之同情与喜爱,必然从各种途径对作品题材进行改造。如宋江起义之类在封建社会里总会被认为是“匪”、“盗”的行为,非用特殊的手法则只会引起读者的憎恶而非同情。那么作者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李辰东认为,第一,作者“将宋江等之为盗,改作被官吏压迫,非出自愿”;第二,作者“将许多好汉写成义士”;第三,作者“不仅让这些好汉为民除害,而团结起来的时候又为国家除害。‘忠义’二字由此而来。”李辰东在这里将宋江起义的性质的改变归于作者有意识的改造行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是有这样几个问题:
1.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起义活动中独独将宋江起义改为“忠义”类型?
2.《水浒》故事的演变以至成书应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性质的改变,即由自发的造反转而为被迫的落草并终于招安为国家出力,不会是某一个作者一时间的突然改作完成,而是在民间有一个传说故事不断被繁衍、流传、演绎、放大的历程。李辰东的结论显然没有顾及这一点。
这里还须分辨一个事实,即一些研究者认为宋江起义之改为“忠义”是文人士大夫所为,体现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而非民间的感情与趣味选择。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在封建社会,“忠义”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 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草野民间在这一标尺上总是一致的。事实上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都遵循着一个总的道德原则即“忠”、“义”,反官府不反朝廷,反奸臣不反皇帝,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同时从作品的流传看,没有这些道德色彩的添加,它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以至保存下来。
聂绀弩《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3]一文认为,《水浒》中的人物,尤其是宋江,是有一个逐渐提高的改造过程。在《宣和遗事》以前的宋末传说里并无宋江的名目,罗烨《醉翁谈录》里即无宋江篇段,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中只说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从《宣和遗事》起将宋江“杀惜”的原因与“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突出他“义”的一面。元杂剧中又突出他“度量宽洪”这样一种领袖人物必备品格的一面,慢慢地构成今天《水浒传》中宋江的整体形象。在艺术上由于繁本对简本的精细加工,不但对人物的性格刻划有提高,如“移置阎婆事”的成功,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一点在郑振铎先生《水浒传的演化》[4 ]一文中也有大量的“繁”“简”文本比较的例证。此外《水浒》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的方面还应包括:(1)加入王进、林冲的故事,从而将史实上并不恶迹彰显的高俅、 蔡京人格上加以贬低,证明“乱自上作”;(2)改造“招安”, 把史实上可能的宋江因“势穷”而降以及《宣和遗事》中所称的张叔夜招降改为宋江主动追求“招安”,突出其“忠义”主题。聂绀弩先生的这些意见都是很精辟、足以服人的,但其中也还有一些问题:
1.聂先生还是没有回答为何要将宋江起义作为“集中悬拟的箭垛”,从而汇合集纳为后来辉煌的《水浒传》的问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水浒是怎样写成的》[5 ]一文中也认为:“宋江他们的故事在人民口头流传的时候,人民口头流传的故事,不只宋江他们的故事一种,而是许多种类似的故事同时在流传。”那为什么独独宋江起义的传说故事得以流传与光大?
2.如聂绀弩、严敦易等先生认为,宋江起义得以格外的流传是因为民族战争的爆发,金人南侵,宋江余部参与了这次斗争,同时寄寓了人民的爱国感情与对朝廷昏聩的失望。这从当时朝廷的“忠义巡社”制度可看出来,《水浒》中亦有内证,即第七回回末:“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这两句诗显系指“八字军”。另明·吴从先《小窗自纪》所载一种“稗史《水浒传》”,内容与今诸本《水浒》均不同,除“四大寇”之名有明显差异外,宋江起义的时间亦与金人南侵同时,并载有宋江语:“宋江流离,金人相陒,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誓清中原,长江击楫,水惊波撼,将军用命”等自誓之词,显见至少在民间的故事传说中,宋江起义与金人南侵后发生的民族矛盾的斗争关系甚为密切。但是,如果因为宋江参与了抗击金人就选择他作为一部大书的主角,似乎也不足以成立。为什么不选择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呢?他也是从一个起义领袖转而为与朝廷合作抗金的。而从现行《水浒》看,也的确很少有关于抗金事迹的遗痕,惟有“征辽”或可说明这一种感情,即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所言“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3.聂绀弩先生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先生一样,都是从“简先繁后”的角度,认为《水浒》故事经历了从民间传说的萌芽到《宣和遗事》初具雏形、元杂剧又加以增饰敷衍终至成书这样一个过程。依照这样的创作过程与规律,且不论元杂剧与《水浒》成书的关系究竟若何,我们的确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宋江起义成为核心,具有了流传繁衍的源动力的。从成书的渊源上说,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水浒传》中仍存留着这么多的“说话”痕迹,显系不同的话本凑拢而成。
二、宋江品格的美化与拔高对《水浒》成书的重要作用
在《水浒》成书问题上,亦即《水浒》故事的发展演变上,研究者们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宋江成了一个代表性人物,而宋江在历史上明明并没有很大的规模与影响。也许宋江或其部属参加了抗金斗争,与朝廷合作,那又为什么不选择更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来作代表?严敦易先生《水浒传的演变》[6 ]一书将《水浒》故事的演变划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时期“萌芽茁发期”中,严先生认为,“宋江,无疑地是宣和二年以后,京东、淮南以至河北广大地区内的农民起义最有力的一位领袖,‘转掠十郡’,正足以形容他的发展和膨胀,他俨然已具有这许多地区‘群盗’所率相尊奉,与秉承号令的‘共主’资格。”由于具体史料的缺乏,这个判断也多具悬测的性质而无实在的论证。欲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我们仍非从记载宋江及其头领绰号的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与记叙梁山泺聚义始末的《大宋宣和遗事》入手不可。
实际上,《水浒》故事最初的渊源,选宋江作为一领袖式的代表,可能并不与抗金有关,而且也不会是文人士大夫有意美化与增饰的结果。宋江首先在民间一定是有了一些特别的气质与品格,并因此放射出夺目的光华,成为了一部大书的核心与故事发展的源动力。是民间的选择,民间艺人的铺衍深入人心,树立起了宋江的形象。非如此我们无法解释宋江何以成为主角,宋江起义又何以成为一部大书。孙楷第先生的结论可说是非常坚实的:“以今考之,自张天师祈祷瘟疫至打东平府东昌府止,盖为宋人旧话而盛演于元人者,方腊故事,当亦甚早。”[7 ]那么在民间的塑造过程中宋江的形象渐渐具有了哪些特质呢?南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所著《癸辛杂识续集》中所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为我们分析《水浒》故事的源起及宋江的超出众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序》中有两段话非常重要: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
“宋江事见于待谈巷语”,说明关于宋江的传说故事很早即已流传。龚开大概是个画家,在寻找绘画题材,“高如李嵩辈”画家传写的图画已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年少时壮其人”的龚开更想“存之画赞”。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为什么“士大夫亦不见黜”?龚开又为什么“年少时壮其人”?这可见宋江事虽无明确详细的史书记载,但在民间的传说中已具有了相当的魅力与传奇色彩,这种魅力与传奇色彩可能并非宋江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与他的部下、头领们的事迹传说大有干系,是共同形成的。如宋·罗烨《醉翁谈录》所载《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小说”篇段的名目,它们一定是《水浒传》所汇拢各种话本短篇的前期阶段。而宋江作为一个领导者,更多的应是具有领袖气质,它表现在龚开所言的“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及“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的坦荡豁达。
从龚开《宋江三十六赞》的赞语中我们很难找出人物具体的事迹,但我们应知道,这些赞语不是从“讲说故事”的角度来写的,而仅是为“刻划摹写”人物形象的图画所配的短语。虽然如此,从“呼保义宋江”条可知,“不假称王,而呼保义”正是他最突出的品格。为什么不“僭越帝号”就是最突出的品格呢?这正证明在古代农民起义中领导者最终的理想与抱负几乎都是要对皇帝“取而代之”,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支撑他们反抗的精神信念与思想基础。这反过来突出了宋江“不假称王”的可贵。“保义”是宋时“保义郎”的称谓。据程穆衡《水浒传注略》[8 ]释“呼保义”:“《辍耕录》:武正八品曰保义校尉,从八品曰保义副尉。言吏员未职,已呼之为保义也。又宋时相呼曰保义,似亦通称,如员外之类。”邓广铭先生释“呼保义”中的“呼”字与“不假称王”中的“称”字都为动词,[9 ]以“保义”相称应属一种很平易、通俗的叫法。龚赞“呼保义宋江”条中还有很有意思的两句:“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谓宋江只称呼“保义”而已,决不“称王称帝”,僭越名份,哪里像那些狂妄的人“专犯忌讳”!这对于宋江形象的树立并最终为士大夫阶层及人民百姓接受是很重要的。
但是,仅仅不称王称帝,也还不足以形成强大的人格力量,因为韬光养晦式的“缓称王”往往可能包藏更大的野心。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与龚赞差不多同时的《大宋宣和遗事》了。目前二者孰先孰后尚难断定,如果从龚赞对《宣和遗事》中人名的更易上,如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作阮小二等看,龚赞当在后;如果从龚赞中并无林冲、《宣和遗事》十二指使中已有林冲,以及龚赞中有五次提及“太行”,却从无“梁山泊”字样,《遗事》则已将“太行山梁山泺”合称看,龚赞当在前。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水浒》的题材内容的确是在不断吸纳各个渠道的传说中发展壮大的。而《宣和遗事》恰恰进一步明确了宋江在民间的形象,那就是玄女娘娘天书末所附一行字“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晁盖的梦中亦有“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之言,这就提高了宋江起义众头领的思想境界。《宣和遗事》应如鲁迅先生所言“由钞撮旧籍而成”,[10]或如严敦易先生所言,其中“梁山泺聚义始末”应系“从当时的水浒传话本来缩写的概要”,而决不是“水浒话本的萌芽和开始”。龚赞与《宣和遗事》都明确了三十六人的范围,并给出了大致相仿佛的名号。这说明在龚赞与《宣和遗事》的阶段,宋江的领袖形象由于其“不假称王”的“忠”与“私放晁盖”的“义”得以确立,这一点到元杂剧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元杂剧中“水浒戏”与《水浒》成书的关系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与《水浒》成书的关系究竟若何,如从“简先繁后”的观点来看,元杂剧应是对《水浒》题材的进一步铺衍:如从“繁先简后”的观点来看,元杂剧应只是对《水浒》题材的借用,其内容及所反映的人物形象并不与通行的《水浒》同。从现存的几种“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等看,关目的产生均由宋江的放众头领下山而起,除“李逵负荆”显系《水浒》故事的搬演外,其它均表现为杂剧的情节特征而与《水浒》的故事发展并无关涉。我们很难得出元杂剧是《水浒》成书中重要的一环的结论与认识,而应承认的是,在元杂剧兴起的时候,一方面“水浒戏”的搬演扩大了宋江起义的影响,深化了其“忠义”的主题,另一方面《水浒》故事自身在不断的繁衍壮大中也确实到了一个归纳、总结的时期。这从宋江在现存六部“水浒戏”中的自白可以看出:
1.宋江的出身经历与形象趋于固定。
以《还牢末·楔子》为例宋江[白]:幼年郓城为司吏,因杀娼人遭迭配。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某,宋江是也,山东郓城县人。幼年为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路打梁山泊所过,有我结义哥哥晁盖,知我平日度量宽宏,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及时雨宋公明。今晁盖哥哥并众头领,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之后,众兄弟让我为头领。”
这段楔子、自白在现存元曲“水浒戏”中大同小异。惟从中我们可知道:(1)“忠义”的名号已然确立, 不管是叫“顺天呼保义”也好,还是“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上面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也好,宋江实质已成为民间百姓某种心灵意愿的代表。如《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中关胜与李千娇语:“我不是歹人,我是梁山上宋江哥哥手下第十一个头领,大刀关胜的便是。”倘若梁山的声名不济,关胜必不会出此语;(2 )宋江的品格在元杂剧前的龚圣与《赞》与《宣和遗事》中并不具体,这里有了“平日度量宽宏,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便助他些钱物”这一句,不管这是之前民间传说的产物还是元杂剧所加,宋江之形象趋于完整、丰富可无疑矣,也因此具有了领袖的气质与底蕴。
2.除了《争报恩三虎下山》杂剧言“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及《还牢末》楔子[末]言聚义英雄数外,其它数种都很明确地提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概念,这个“伙”姑不论是指“一伙人马”或“一个头领”,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百零八人的节目已生出。
3.所有的宋江自白均言晁盖为三打祝家庄时而亡,这与后来流传的《水浒》不同,但我们注意到打曾头市起因仅为很小的一件事,即段景住马匹被盗,在这两打曾头市的战役中梁山并未增加一个头领,此应为后来传说节目的增添,而不影响《水浒》实质的内容定型。
由上述我们可以认识,元杂剧不是《水浒》故事演变与成书的一个环节,但它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表明,在元杂剧时代,《水浒》故事的流传更为活跃,并已到了宋江形象定型与“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明晰化的阶段,相关的故事内容虽并不与曲艺搬演的内容同,但一定是丰富多彩的。遗憾的是这时没有产生一部能对《宣和遗事》有所进步、发展的类似《三国志平话》的“水浒传平话”,使得《水浒》成书的历程在从元至明初的阶段(约一百多年)呈现空白。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一文即在考察元代“水浒戏”的基础上提出:“当时(指元代——笔者注)一定有一部水浒传,有一个完全的水浒故事,所以他们不妨零星取用,不妨各奔前程,专写小说中一部分的事以自名家。水浒剧本,其所叙的事实,与小说愈趋愈远,而这部水浒传却是与今本水浒传愈走愈近。”“这一部元代水浒传,我们很希望能够如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一样的突然出现于世”。这个看法虽仍是出于悬测,却不无其道理,在逻辑上与创作规律上是讲得通的。
四、“招安”的结局是《水浒》成书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宋江的形象定型以后,他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天下的英雄们发生联系了。民间塑造了宋江“忠义”的形象,“忠”的思想既使宋江“士大夫并不见黜”,又引起人民的同情;“义”的性格则改造了宋江“勇悍狂侠”的气质,使其向领袖型的人格形象转化。这又可说是文人介入的功劳,因为在《三国》、《说唐》、《封神榜》之类的讲史小说中,总要有如刘备、李世民之类礼贤下世的“明主”来做核心。他们不一定要有高超的武艺与绝顶的智慧,但只要“礼贤下士”、“宽厚仁爱”即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王道”总是胜于“霸道”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宋江之德虽不足以“据有天下”,却也已足以据有梁山泊、统率一群差不多已是国家最精华的人才了。
而当这一切都已成为定型的东西后,宏大的构思与磅礴的气势却不能由此戛然而止,正如海纳百川的大河终至奔腾踊跃之势时必须找到宣泄的出口一样,梁山义军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这也就是《水浒》中另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即对“招安”及“打方腊”的认识问题。
“招安”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作者有意地营造悲剧气氛?它符合宋江等众头领的思想与性格吗?如何区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招安”对《水浒》的成书有什么影响?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如何看待、认识宋江打方腊这一问题?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圆满的回答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及是否征方腊的历史真实性问题,由于相关的史料记载歧见互出,真假莫辨,笔者无意在这里进行很可能徒劳无功的考辨工作。对这一问题有着详切精当的认识的文章,我们可以参看陆树仑《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两三事》(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2、3期)与邓广铭《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或《邓广铭治史丛稿》)。 这两篇文章从对《折可存墓志铭》、李若水《捕盗偶成》诗等材料的分析,基本肯定了宋江的确受了招安,但并没有从征方腊,而是在方腊反后的一段时期复又叛乱,因此宋·范圭《折公墓志铭》中有“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的记录。
就艺术的真实而言,“征方腊”作为《水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形成的时间也较早,这从征辽、征王庆与田虎的战役中梁山不曾损折一个好汉可得到证明。“招安”的结果必是“征方腊”,即鲁迅先生所言“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1]倘若不接受“招安”,宋江的革命性与立场坚定性是没有问题了,但《水浒》能否流传与保存又成了问题,这大约是删去包括招安等情节的金圣叹所始料未及的。
从今天的认识角度与眼光出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体现在《水浒》中的“招安”与“征方腊”结局,实际亦即如何理解以宋江起义为代表的古代农民起义的结局问题呢?
首先,农民起义虽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代表着群众自觉的反抗意识,对旧有的统治秩序与社会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并对后世农民起义发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如《水浒》就被后世起义者从军事上学习,从组织形式、绰号等方面加以效仿,但农民起义总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无外镇压、招安及作新的皇帝这三条路,即使作了新的皇帝,也只是旧的制度的翻版,并不能产生本质的革命。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已有精辟的论断。
其次,从百姓的实际需要看,既需要起义英雄反抗官僚恶霸,一伸胸中冤气,又在朝廷无力抵抗外侵的时候需要这些英雄转而与统治者合作,这就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对立统一。“忠义”之“忠”是忠于朝廷,但在特定时期它符合人民利益,如鲁迅先生所言“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12],统治者同样也会产生这种需求,只不过统治者往往是从自己的利益而非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因而常常是妥协的、投降的势力占上风。统治者既然能利用“招安”收买起义者,并利用他们抵抗外敌的侵略,当然也能利用他们征讨别的“不遵王化”的起义者,因此历史上的宋江可能没有打方腊,但这样的事实并非没有,从艺术的反映来说是真实的。
第三,从传奇的角度看,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总是有一个道德上的准则,即“忠”、“义”,反官府不反朝廷,反奸臣不反皇帝,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一方面从作品流传的角度看,不加上这些道德色彩作品就难以保存和传世,另一方面从“王权永祚,不得篡夺”的观念出发,如萨孟武先生所言:“所谓‘正统’和‘篡夺’只是法律上的名词,不是道德上的名词”,[13]年代久的朝代总会享有“神器”不得侵犯的特权,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古人乃至有一定层次的知识阶层赞扬、支持农民起义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宋江受了招安就是“投降派”呢?曹操本人并未作皇帝尚受民间这么多的诟议,无非刘备是汉室正统而已,何况宋江的确是一介“草寇”呢?倘若宋江不“忠”,僭越,他就不会成为《水浒》故事的核心人物,而“忠”的结果必是受“招安”乃至主动追求“招安”,这是我们阅读《水浒》时所不能不采取的一种态度。
收稿日期:2001—1—5
标签:水浒传论文; 宋江论文; 宋朝论文; 方腊宋江起义论文; 历史论文; 方腊论文; 元杂剧论文; 南宋论文; 野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