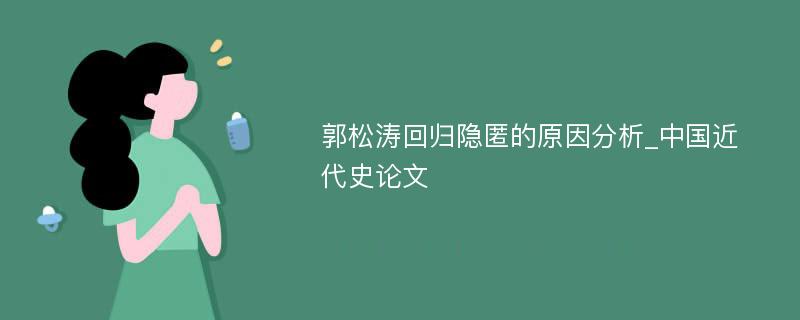
郭嵩焘归隐缘由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缘由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0117(2004)01-0035-04
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然而,这位显赫的钦差大臣却前前后后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
科举出身的郭嵩焘饱读儒家经典,无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归隐这种“出世”是建立在建功业的“入世”基础上的,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就无所谓息影林泉的归隐。郭嵩焘的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归隐时期他眷恋不舍的依然是其忧虑的时局和洋务,积极上书朝廷,执教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大力传播王学,王闿运佩服他能得“船山之要”,希望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
“归”即归来之意,“隐”即隐居之意,“归隐”就是退出官场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归隐”在历朝历代儒学士人中古已有之。北宋范仲俺脍炙人口《岳阳楼记》,流传着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不计自我得失,忧乐俱在天下的宏伟抱负,显然是对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的扬弃和发展。原来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当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时,则应有所节制,可屈可伸,可进可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固然是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积极入世而以善于自保的高尚品德,尽管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教,但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蕴含着具有永恒力量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经世传统中的“穷独达济”的文化心态,给人一种“清高自持”和“善于自保”的消极因子。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归隐是竹林七贤。
(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沿袭千百年来仕人的道路,郭嵩焘通过寒窗苦读儒家经典,历经数次科举落第,29岁前后终因十年不屈不挠奋斗而荣登进士之榜,走上了出世为官的人生道路。“三十而立”,立起了事业的支柱。然而,这位湖湘弟子置身官场,却如坐针毡。官宦之士前倨后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为名为利争相攻击的肮脏灵魂;正直之士一心为国弹精竭虑却屡屡反遭迫害的失意心态……一切的一切,久久萦绕于心,久久难以释怀,于是,一次又一次归隐故园。然而,时局的艰难,国事的剧变,又怎能让一个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的人平静地度过息影生涯呢?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烧灼着他的心,边疆频频告急的情报常常让他感时伤怀。郭嵩焘又一次一次走出湘阴家园,去救时挽局,去实现一个伟丈夫的非凡抱负。就这样,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郭一直在“仕”与“隐”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交错行进,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构成晚清仕人中一桢别样而独特的风景。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起义前夕,既是同乡又是至交的郭嵩焘与左宗棠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社会动乱即将来临,因此“为山居给邻之约。”[1]850年2月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湘阴首当其冲,郭氏被迫举家避乱,“离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2]梓木洞人心风俗醇厚,又有山水朋友之乐,的确是个避兵佳处,归隐到1853年3月,为期三年有余。农民战争的烽火愈燃愈旺,严重威胁清王朝的安全,更危及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利益,郭嵩焘“出山”来匡时救世,在湘军幕中充当摇羽毛扇的角色。
郭嵩焘以一介书生,第一次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亲眼目睹伤亡以及行军景象,“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屡战又多不利,困厄之感在所难免。何况他离家已久,千里乡愁,使他益感归心似箭,“湘岩故息壤,吾甘死耘锄”的心情呼之欲出,遂于1853年9月26日回到故乡。然而,战友江忠源突然在庐州阵亡。郭极为悲痛,作诗《哭江中丞》:“七叶两京廑北顾,九州一柱竟南倾。孤臣闲退今华发,日倚柴门涕泗横”[3]悼友感时,痛大将之亡,哀乎于辞。郭嵩焘难以隐居,江忠源死后不到一个月,1854年1月,郭嵩焘前往衡州,帮助曾国藩商定水师营制,匆匆结束了为期仅有三个月的第二次归隐。
1860年1月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前往山东,检查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有无隐匿侵吞,他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力争废除二百余年的积习,可为国家课税三百万,为此跑遍了山东沿海,走访每一海口,将他收集与见闻一一记录,拟定章程,资料汇集七巨册之多,利弊情伪均在其中,如要整顿,实举手之劳。但他历尽艰辛,结果因僧格林沁蜚语弹劾,“忍苦耐寒,尽成一梦。”[4]不仅使规划山东全局的计划“溃败决裂。”而且殃及无辜。他在山东专心访求有声望、有才干的士绅,反让诸绅横遭查询之祸,他的同年萧氏更因此丧命,郭的“私心痛惮”,岂待言哉?他一心想替皇帝办事,为国家开利源的雄心壮志,竟因不知官场的险恶,成为泡影。他的失望与挫折感,久久不能释怀。“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5],于是从1860年4月至1862年5月进行为期二年的第三次归隐。“微才多病甘归隐,愿睹唐虞酿太和”[6],郭嵩焘再次出山,是应李鸿章所请。1862年4月中旬,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保郭嵩焘司道实缺。同月下旬,诏受郭嵩焘苏松粮储道。此时李鸿章组建淮军,初生之犊,豪情万丈,很想大干一番,也因而极需人才。他在上海常与洋人周旋,颇需擅长洋务的人才。他还要带兵打仗,更需要能筹饷的人。既懂洋务又能筹饷者,在他看来,除了郭嵩焘之外,实无别人。郭并非轻易会改变归隐的初衷,正如美国史学家汪荣祖分析,同治改元,多少给郭嵩焘带来一点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在李邀郭之前,郭已慧眼识英雄,认定比他小五岁的李鸿章犹如黑暗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必将大放光芒。郭并非一定会预见李将位至相国,而是觉察到李将有一番作为,令他感到惊喜。[7]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屡遭阻扼,曾奏请开缺;但他的请辞,似不无以退为进之意,以冀有所作为,何况他上疏乞休,并未被批准。真正导致他离职的乃是同里故友左宗棠的恶意相倾,一心欲将亲信蒋益澧取郭而代之。郭知之甚稔:“左季高三次保蒋公,必得此席而后已,可谓全力以争矣,终亦不能测其为何心也。”[8]如此罢官,不能不令他感到窝囊,甚至愤恨。更让郭伤心的是,1858年他在南书房成为皇帝秘书,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开脱推卸责任,在那场弹劾案中,才使左免遭杀身灭顶之灾,反而因祸得福,从此受到朝廷器重,仕途平步青云。左竟然恩将仇报,让郭至死都不能谅解,在他七十几高龄时,他的少年朋友左宗棠荣归故里亲自登门拜访,被拒绝,可知郭嵩焘当时心情是泣泪噙血的。1866年5月14日,郭离任返乡,开始连续八年的第四次归隐。郭嵩焘每天除会客著书外,即督促仆役种菜、植茶、养鱼。闲时便与西枝、东枝慧灵等和尚谈诗论佛,听乡民拜香求雨,看家人请巫治病。生活似乎平静,郭嵩焘的心却一刻也静不下来。国政的得失,官吏的升降,无一不在他牵念之中,偶然中听来的国事传闻也常使他增加无穷的忧惧。同治十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兴师进犯,三月在台湾琅桥登陆。海疆多事,清廷六月初八诏命郭嵩焘、杨岳斌、曾国荃、于日昌、鲍超等来京陛见。显因国难当头,招集干才能吏赴京商讨国事。郭嵩焘家居八载,渐趋平淡;诏命突至,不免吹皱一池春水。他对官场早已灰心,但对朝廷与国家的忠爱之心,并未稍减。他仍期盼清廷能改弦更张,希望提倡自强的洋务派有所作为。正当台湾、新疆警报迭传时,西南边陲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滇案”使清廷更惊慌失措,应英国强烈要求,清廷屈从其威逼,派遣郭嵩焘前往英伦“谢罪”。“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大,下及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9]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毅然挑起这幅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郭嵩焘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他的高尚情操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
作为中国第一任外交大使的郭嵩焘,最初出洋的目的是全面考察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然而三年任期未满,他就一再请辞,缘于他难以忍受封建保守势力对他严厉的攻击。副使刘锡鸿得到大洋彼岸的清廷权贵李鸿藻等撑腰,一意相倾,列举十大罪状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阴影始终笼罩他整个出使期间,大大影响了他的情绪与工作。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同时召回郭嵩焘、刘锡鸿,分别以曾纪泽、李风苞继任英法公使和驻德公使。1879年5月5日,郭钦差驾到长沙,码头上冷冷清清,巡抚及下属文武百官“傲不为礼”,没有一人出来迎接。“欢迎”他的是贴满大街小巷的揭贴,上书郭嵩焘人名,“指以为勾通洋人”[10]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公使,就这样背着千夫所指走出国门,又迎着辱骂回归乡里。从此,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再也没有走出过湖南,开始了孤寂的晚年生涯,直到十二年后离开这个世间。
从1840年9月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入幕时算起,直到1891年逝世51年时间,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归隐漫长,整整等同官宦时期,难伸经天纬地之才,酿成个人的人生悲剧。山东之行,郭全力为清朝空虚的国库增加财源,反受降职处分,归隐使其前功尽弃。粤抚任上,郭尽职扑灭起义余火,结果反遭撤职,归隐使其难展封疆大使之志。公使期间,郭全面引介西方先进科技与制度,最终任期未满被召回,从此决裂仕途,归隐使其超前的洋务思想只能与他同进棺木,不能实践。
二、宦海、战乱和家庭风波是其归隐的外因
(一)宦海风波是几度归隐的共同原因
1859年10月,任职南书房成为皇帝秘书的郭嵩焘奉咸丰之命前往山东,以钦差大臣身份检查海口贸易税收。郭氏施行霹雳手段整顿税收,剔除中饱,侵犯当地官坤既得利益,积怨甚多。李湘芬再从中推波助澜,气氛更加紧张,终于闹出福山县商民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乱子。僧格林沁据此为词弹劾郭嵩焘,山东巡抚文煜亦因他自以为是,颇为不满,自然站在僧氏一边,结果郭费力不讨好,回京后得了个“降二级调用”处分。这是他努力行事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交卸辞行,在返回北京途中饱览世态炎凉,朝廷旨意不过“交部议处”,并没有明令罢官撤职,众人嘴脸顷刻变得冷若冰霜,与来时的热情恭敬形成尖锐对照。“炎凉”二字,郭嵩焘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过,情之所至,信笔成诗:“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11]山东之行失败,也是他进入官场后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思想上所受刺激很深:“自有山东之役,即办事之心亦隳”,[12]郭嵩焘难平胸中愤懑之气,遂告假还乡,郁郁寡欢在故乡度过两年岁月。
1863年6月,郭嵩焘初接广东巡抚时,雄心勃勃:“谓庶儿吾志一行也。”[13],两年多的粤抚生涯却使他苦不堪言,他几乎到处碰壁,主要原因是其不得当官要领秘决:多叩头,少说话。郭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面前,经常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持之甚坚,不知尊敬顶头上司,甚至公开讥讽。结果他自然遭到厌弃与攻击,又萌生退志,“堪笑先生好归隐,尘埃苦耐鬓毛侵。”[14]在权力的角逐中,他再次败下阵来予以撤职。郭嵩焘自叹“一日去官而身为轻,固知非功名中人也。”[15]称假回籍,甩手不干了。
1876年9月25月,郭嵩焘从北京启程,前往英国担任公使。驻外三年,他本想努力探求西方强盛之由,将大洋彼方之长引介到国内,但他的理想无一不破灭。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将其主张斥之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16]实际上给郭嵩焘戴上了一顶投降主义的政治帽子,《使西纪程》中的“并不得以和论”一语表明,他对此早已有思想准备,但何的奏参对他的打击还是如雷灌顶。副使刘锡鸿的构害,气焰极为嚣张,无中生有编造罪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锡鸿曾是广东巡抚郭嵩焘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如今却公开叫板攻击了。郭返国时身体状况,自亦不会严重到不能赴京供职,主要还是“政治病”——他固然不愿与刘锡鸿同朝列班,也极瞧不起当国权臣如李鸿藻、沈桂芬之流,实耻于其下。如果郭嵩焘勉为其难,仍然会因言论贾祸,不但无补于事,反而自取其辱。他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才会有誓墓的决心,一切的一切,让他心力交瘁,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人,与昧愚偏见战斗了几十年,实在感到毫无希望了,惟有引身自退。从此,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直至撒手人间,再也没有走出湖南,去施展其济世才华。
(二)战乱风波是前两次归隐主因
父亲病逝,郭嵩焘按照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父母离世,不管官位多高都必须在家守丧三年,以示哀悼之孝心,称为“丁忧”。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连克湖南江华、嘉禾、桂阳。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地主富豪纷纷逃命。
郭嵩焘有感于父母双亡,内乱遍地,不免感到心灰意冷。他屡试求得进士,自有浓厚的功名之心,然既得之后,碰上乱世,加以天灾家变,“遂不复以仕宦为志”。[17]于是隐居玉池山,希望了此一生
郭嵩焘首次出山,亲赴益阳劝捐。4月南昌告急,在江忠源一再函摧下,郭氏与夏廷越、罗泽南等统率1400余名湘军,向江西进发。“十年偃赛校书郎,鸣镝弯弓赴敌场。乱余身已非全物,死去魂应识故乡”,[18]但他追随江忠源,与太平军战于南昌、九江、湖北田家镇等地,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在南昌,他就写诗向江发过牢骚:“觅得疲驴试短衣,尺书屡召敢频违?此生戎马真非分,半夜星辰尚合围。”这时,他决计归家,无论江忠源怎样劝留,道是“不能终执戟,扫荡妖氛挣”,长揖而别。
(三)家庭风波使其无心留恋官场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最遭舆论谴责的是莫过于他的家庭纠纷,其家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但“粤民非之,”而且“事为通国所知。”[19]原配夫人陈氏温文尔雅,与郭嵩焘感情甚笃,不幸于1861年病逝。陈夫人去世后,他虽有小妾邹氏相陪,但不是正室夫人,在一般人看来,他没有妻室。1863年他任苏松粮道时,经冯桂芬做媒,与太仓富户钱氏订亲。他对媒人讲的条件很简单:“不求关,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20]钱家能攀上官府,自然十分高兴,双方一拍即合。10月3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之夜,郭嵩焘大失所望:“新人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应然耶?”[21]
10月14日,郭嵩焘携新夫人赴广东上任。从上海登轮船始,钱夫人就大闹不止。“终日喧闹,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22]
内战显然在急剧升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按曾国藩所讲,郭对钱夫人有大错:新妇入门,郭的小老婆都乘同样的绿呢大桥。结论是:郭嵩焘不守封建千百年来的礼规,不近人情,荒谬至极,挨千人万人骂,活该!难怪钱夫人大骂特骂,决绝而去。郭在广东劝捐,触犯了富豪的利益,闹得香港报纸评论,北京传说纷纷,清廷下令查办。曾国藩把郭嵩焘的家庭风波与劝捐相提并论,认为这是造成民怨沸腾的两大基本原因,因家事引出一场轩然大波,乃至构成他政治上倒台的一个原因。
隐居期间,郭家连遭不幸。1868年4月郭嵩焘的大女儿病故,翌年12月,孙女夭折。1870年1月长子刚基死于喉症,年仅21岁。连续换医诊治,最后“屡进参汤”,也未能挽救年轻的生命。刚基为陈夫人所生,自小聪慧过人,不但善诗文,而且书法绘画皆精,郭嵩焘视为掌上明珠。曾国荃曾致书郭嵩焘:“诸侄女中,四侄女(曾纪纯)相颇贵,其夫若子,皆当位至侍郎。”[25]这样一位贵相的儿子突然逝去,给郭的打击比一般的丧子之痛更沉重。他伤心长子之死,时常独洒思儿之泪,经久不稍减。光绪六年自海外归来,十二月初四是刚基忌日,虽已历经十二年,仍然“念之凄然”。[24]
刚基死后,郭府凶讯频传。1870年2月,郭嵩焘的第八个女儿因喉疾卒死。三个月后,久病的邹夫人也撒手归天,她是1856年被纳为妾的。1860年陈夫人逝去后,郭视其为正室。回籍以后,他不顾舆论,把邹氏扶正,两人相爱甚笃。邹氏偶尔外出,郭便感到十分寂寞。儿子死后只有邹氏是他的一点安慰。这样一位贤妻良母病逝,使郭悲怆万状,几乎了无生趣。1872年五女婿左浑(左宗棠侄子)夭亡,女儿痛不欲生,不久郭的小儿子又夭亡。短短数年之间,死亡六口,真令嵩焘有鬼神都不饶他的凄惨。这一人生悲剧使他更加无心留恋官场,第四次归隐长达八年之久。晚年的郭嵩焘又丧儿媳曾纪纯,其遗留的两子本谋和本顺成了孤儿,抚育求学的重任只好落到年迈力衰的郭嵩焘身上,这份伤痛可想而知。人生厄运对其影响自不待言。
三、独特个性是其归隐内在的诱发因素
郭嵩焘生性耿直,与封建官场的虚伪圆滑格格不入。某天往访陈孚恩,陈家高朋满座,正在热烈地谈论“洋务”。满屋人一个比一个高声地大发“爱国”宏论,慷慨激昂,盲目论战的空气很浓。郭嵩焘心里鄙视众人蠢笨可笑,嘴里由不得发出声来:“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大家听到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像机关炮灭了火,一时都默然无语。不一会儿,人们陆续散去。陈孚恩把他拉到无人处告诫:“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会能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曾国藩最知郭嵩焘的性格,“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对曾反对李鸿章请郭出山:“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郭嵩焘回信李鸿章,坦陈自己性格的梗直,容易得罪人:“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快,则群小惊疑。”
边患告急,1874年郭嵩焘接旨进京。正北上途中,郭氏曾在家乡湘阴停留数日。临行前,县令冒小山对他说:“大人心地开爽无城府。然世途崎岖,人心叵测,一切愿求慎重。”郭氏闻此语“悚然”,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愚直。未敢以猜防人心待人,又意求利人,不为人害,凡君此言,深中隐微,当书伸以志之。”[26]可后来的实践表明,他并没有吸收这个教训;第二年十一月,这个新授的兵部左侍郎即向朝廷上了《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英官重案折》,郭忘记了离乡时冒小山劝他“一切愿求慎重”的忠告。正是这个“语言激切”的奏参。给他惹来极大的麻烦,以致“横遭訾毁”[27]有好心朋友告诉他,要想保乌纱帽,万不能事事认真。“漫言之而漫应之,最省事,若明其事,则纠结愈纷。”[28]郭嵩焘虽然感到这是“皆身世要语”却始终学不来。相反,他对官场上应酬非常厌倦,“诸客纷集,极苦疲倦。
收稿日期:2003-10-27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归隐论文; 历史论文; 江忠源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