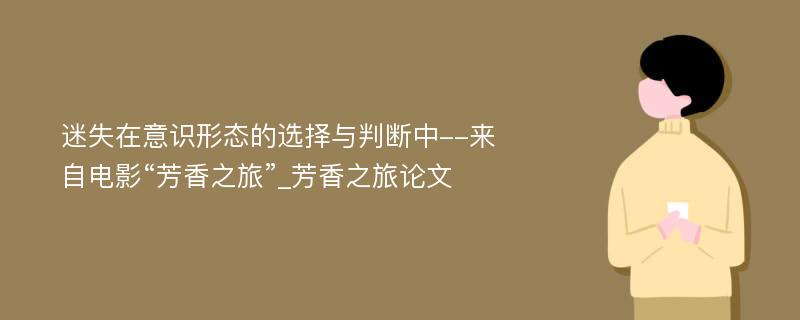
迷失在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中——从影片《芳香之旅》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开去论文,芳香论文,影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似乎是要写嗅觉
欲在银幕上写嗅觉绝对是一个冒险,更是一次对电影影像的挑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小说版《芳香之旅》和影片《芳香之旅》基本上同时出现,这是由诗人覃贤茂从电影重写的小说,显然是要加深或者拓展观众对电影《芳香之旅》的认识,在小说和电影之间产生互动。
“影视小说”《芳香之旅》,似乎是立志要写一部和嗅觉有关的小说,甚至是一部从嗅觉出发的小说。这个立意倒是很宏伟。因为嗅觉虽然微妙,但是若能成功地变成文字,在文字中看到、想象到“芳香”,这必然是件很有创造力的事情。万方曾经写过《香气迷人》,写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与众不同的嗅觉,能够帮助年老的金奶奶找到厕所,能够闻到海棠花的香味等,最后他成了一名品酒师。小说主要写他成年之后的事情,嗅觉的特异在成了他的职业之后,就没有什么特殊表现了。万方的文字很好,可是《香气迷人》的香气,似乎还是没有被写到完美的程度。
在“影视小说”《芳香之旅》中,油菜花的香味是浓郁的,进入大山之后的空气是清凉湿润的,而梨花的香味,则是清淡、素雅、若有若无的,但是从感觉上讲,则是执著而尖锐的。在这一切气味的基础上,作者写到:“只有亲自经历过那趟奇妙旅程的人们,才会真正知道,那确实是一趟奇妙的芳香之旅呵!即使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春芬都不会忘记,那种深处的记忆,嗅觉上特殊的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的减弱。”这个对嗅觉的珍视,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引发点,生理上的引发点,就像小说讲的,“嗅觉上特殊的记忆”,它有强劲的留存能力。
但问题是将嗅觉做电影的片名,其“芳香”到底怎样在银幕上显现?
对于从未在油菜花丛中漫步过的观众来说,他(她)是否能够在银幕上看到一片无边的油菜花的时候就想象出那浓郁的香气?对于甚至不能辨认梨花和杏花或者海棠花的观众而言,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梨花村的梨花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想象出那种梨花所独有的气味?也许,即使想象不出“芳香”来,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这是观众自身的知识有限所造成的。
但电影应该弥补观众的这个缺陷,既然写“芳香”是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既然电影以芳香命名。如果说,大片的油菜花和梨花的画面还不足以让观众感觉到“芳香”的话,那么导演应该在影片中挖掘更多的更深刻更隐秘的因素来写“芳香之旅”的“芳香”。但可惜的是,这个深刻、隐秘的因素在电影中很难发现。
银幕上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初中语文教材上,普遍选用了杜鹏程的散文《驿路梨花》,相信这一篇文章赋予了许多甚至没有见过梨花的人以深切的喜爱梨花的心情。在旅行者急切地想要找到歇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梨花,文章写到:“有梨花必定有人家!”只这一句话,人对自然的信赖,对人的信赖,对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深情厚谊,都在里面了。所以,当他后来写到梨花落在人的肩上,写在小屋子里看到了新鲜的水、米、盐甚至是生火的火柴和柴禾的时候,由这一切所带来的感动,都和梨花交织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中,梨花的芳香不仅仅是作为一类植物的芳香,它是人的复杂的情感和认识的综合。杜鹏程写《驿路梨花》的年代,正是《芳香之旅》那梨花盛开的画面所涉及的年代。所以,要说梨花的芬芳,《驿路梨花》的芳香更有历史的真实性。
在《芳香之旅》中,没有看到隐秘的、深刻的能够引动观众嗅觉“通感”的“芳香”,这应该与影片所描写的生活缺乏真实性,对真实的生活缺乏深切的感情有关。
从诸如《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一类影片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在一些新的电影导演的作品中,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看不到中国社会原生态中的人们的真实的感情。两个男知识青年,来到贵州的乡村,操着带有贵州腔调的“板正”的普通话,为乡民说电影、说小说,从而召唤了一个当地少女要去远行的萌动的心。这个故事本身没有问题。戴思杰对影片主题的解释也有道理:“不是写爱情,是写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是道理并不能掩盖问题。问题之一在于,“文革”当中年轻人阅读巴尔扎克,可否升华至文化冲突的高度?这是“文革”时代青年人的高度,还是数十年居留法国的中国作家或者中国导演的高度?问题之二在于,那些主要人物在影片的人群中所处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十分可疑。这些人物从学校来到了乡村,依然坚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阅读观念和生活习惯,并且在这一种观念中怡然自得。这也没有什么错,问题还在于,当时如火如荼的红色的革命生活对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强大于此的影响?当时代巨变开始之后,当新时期到来之后,知识和艺术重新获得它的社会地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劳动生活对知识分子产生不了重大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知识青年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可能是热切地想要融入到那种劳动者的生活当中去?作为年轻一代的并且长期远离祖国生活的导演戴思杰,他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当中所写到的“文革”,就不如经历过“文革”,并且一直热切关注祖国的历史和命运的导演谢飞在《我们的田野》当中对“文革”生活的表现,在真实性方面,在时代所赋予人的感情方面,更能够感染人。《青春祭》也是这样,李纯和《我们的田野》中的希南、七月、肖弟弟一样,全身心地想要融入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一样,千方百计要和劳动者脱开干系。所以,当人物的生活和人物的感情真实的时候,人物所闻到的气息或者芳香,才能够被观众闻到。
并不是说哪一种生活更值得人们去过,也不是要拒绝导演在电影中表达的判断,而是说当人们为自己的故事选定一个历史背景的时候,观众有理由对发生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的生活有属于特定历史的期待。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样的影片,基本上让观众的历史认知期待落空。而那些优秀的导演,他们为了将自己的人物放置在合乎历史的环境中,为影片的真实性所做出的工作,是令人惊讶的。马丁·斯科塞斯1993年拍摄了《纯真年代》,剧情描写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小说原作获得了 1921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为了让19世纪纽约上流社会的习俗在影片中真实再现,导演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花了7年时间研读原著,又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前期工作;服装、菜肴、住宅装潢、人物谈吐举止都非常考究,并且还聘请了12位以上的科学顾问,为美工提供咨询。这些数据和素材说明,这个导演为了获得环境和人物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花费了大量的超乎想象的辛苦劳动。反过来也说明,他相信自己的认识并不能代表另外一个时代的真实。
这就是新一代导演所拍摄的中国当代电影所具有的普遍问题:当导演开始写历史的时候,总是用自己的记忆,自己当下的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仅仅是一种假想,来代替历史的真实或者环境的真实。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芳香之旅》这一类电影和《我们的田野》、《青春祭》这一类电影的区别:一个是写经过记忆筛选的、由一些散落的点串联起来的生活,一个是写绵延不断的难以分割的生活。记忆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记忆不是生活?因为记忆总是记住美好的东西,而将那些和美好一起咬噬着人们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的东西遗忘了。像《青春祭》、《我们的田野》这样的作品,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未完成性,因为我们很难将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和生活本身的繁复性切割开来,这个未完成性是导演艰苦思考的痕迹,是敬畏命运的体现。但是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芳香之旅》这样的作品,则总想在一部不足两个小时的电影中,宣布一种对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的判断和认知。这种过度的认知自信,本身就是危险的。
还有片名,像《我们的田野》、《青春祭》,这些片名意味着对历史和人生或痛或喜的真实的情感。但是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芳香之旅》,就影片本身来说也是在写历史,但是其片名却明显地表现出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哗众取宠或者是言辞华美的一种不着边际。这个不着边际就意味着对历史和人生情感的不深切。一个时代可以是平庸的,是肤浅的,是不着边际的,但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却没有理由去屈就时代的平庸和不着边际。
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
也许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会被质疑,因为中文为《芳香之旅》的影片,其英文的片名是THE ROAD。这个片名似乎没有任何“芳香”的脂粉气,没有什么不着边际的嫌疑。并且似乎还隐藏着不少严肃的含义: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道路?是多年来一直变动不拘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路线?是中国人在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甚至思想路线过程中的心灵路线图?总之,这个THE ROAD比起《芳香之旅》来,多了一些象征和隐喻的抱负。
根据影片故事,我们知道片中主要有三个人的道路:崔师傅、春芬和刘奋斗,另外还有向阳号汽车。这三个人和一个车的道路,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经历过的大时代。在影片中,不仅车是符号化的,是概括和象征的,就连人也基本上是没有性格的:和刘奋斗恋爱时春芬的烂漫,和崔师傅结婚后春芬的沉闷,只有这两种状态,其中看不出春芬本人的性格。崔师傅,就是憨厚、老实、踏实肯干,本人的性格是什么?不知道。刘奋斗,就是英俊、青春,也没有性格。也许导演正是要利用这些概念化的无性格的人,来有效地将历史的多次变迁简明扼要地“拎”为一条线索。应该说,假如真的要使用这样的一个简明扼要的线索的话,向阳号汽车应该是最好的见证和承担者;奇怪的是,在多次的历史变迁中,向阳号仅仅被改过一次名字,那就是刘奋斗被发配到石灰场之前,改成了“反修号”,而且这似乎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刘奋斗社会地位的变化和春芬爱情的炽热。问题是在“文革”当中,向阳号仅仅只有这一次波折?新时期之后,向阳号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从未受到过冲击?在《芙蓉镇》、《小巷名流》中,我们看到的对十年“文革”的表述,也绝非如此简单。
为什么要将人物和历史都简单化处理?一个原因是导演不愿意将其复杂化。但是历史本来是复杂的。再一次问,为什么还要简单化?第二个原因是复杂化无助于描写美好的记忆。也就是说,为了保留美好的记忆,所以将历史的残酷性剔除。
第三层疑问:为什么那个时代是美好的呢?因为青春。可以这么说。但是只有春芬和刘奋斗是青春的,崔师傅的青春已经没有了。然而影片所描述的崔师傅也是美好的。崔师傅美好的原因是和毛主席握过手,他是劳模。因为所有的青春都是美好的,所以春芬和刘奋斗青年时代的经验不足为据。崔师傅的美好比较值得研究。一个像螺丝钉一样每天怀着同样高涨的热情工作的人,他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赞扬、认可,像雷锋一样,岗位是平凡的,但精神是伟大的。这是那个时代认可的价值观念。所以,崔师傅美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影片认为崔师傅美好,是因为导演认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的问题:当春芬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在对飞速发展的商业的、工业的、现代化的生活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看到了市面上售卖的毛主席像,她买了贴在家里,贴在崔师傅和毛主席握手的那张照片的下面。这样,我们终于为影片片头那春花烂漫的影像在意识形态判断的高度找到了依据,即影片编导是希望借助青春、爱情以及春天的魅力,来传达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怀念。
有意思的是,我们或许还可以从春芬饭桌的变化,感受到影片编导的意识形态判断的企图。当年,她和崔师傅跑车的时候,虽然她碗里的饭和崔师傅碗里的饭是有区别的,但是她可以吃到干烧带鱼、红烧肉;而在新世纪,影片展示给我们的春芬唯一的一顿饭,是她在给崔师傅上坟之前的寂寞午餐,白面条,凉拌黄瓜。这到底是两种写实的饭,还是具有象征意味的饭?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饭,因为只有这样理解,才会符合上文分析过的《芳香之旅》中人物和事物要素的概括性特征;也才会符合英文片名 THE ROAD所具有的哲学启示性,像费里尼的名作一样:《大路》!THE ROAD!够严肃。
所面临的迷失的可能
从《芳香之旅》整部影片的风格来看,它不是一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反讽任务的影片。这是由它在探讨春芬的青春流逝和意识形态变迁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严肃性所决定的。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影片中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细节,似乎又想要表达一种反讽的企图。
崔师傅和毛主席合影的那张照片,赫然挂在向阳号汽车的后视镜下面。这对于崔师傅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严肃的。但是这个严肃性在观众这里并不能成立。因为当观众的眼睛在面对崔师傅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所面对的是一个喜剧小品演员范伟。在影院中,观众因为看到范伟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快乐得笑出声来。任何时候,观众都具有笑出来的权力,但是假如上面我们讨论过的意识形态严肃性的问题成立的话,这个笑声对那个问题的探讨,就是一个损害。在很多影片中,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对西哈努克亲王来访的新闻片的借用,因为那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历史,所以有表达或者再现历史的效用。但是范伟和毛主席的合影,它的来自于数码合成技术的可随时更改的属性,使得这部影片所存在的历史基础,迅速成为虚拟的想象。这个虚拟性损害了意识形态讨论的严肃性,瓦解了编导在思想探索方面的抱负。
同样的问题还在于,春芬和崔师傅结婚的当晚,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新房中,放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主席像,是崔师傅的奖品或者纪念品。做爱时,主席像被撞到地上,碎了,小两口连夜偷偷将碎掉的石膏片儿埋到院里的树下。这个段落也让观众发笑。崔师傅有很多奖品是可以相信的,但是在新婚之夜,画面上出现很多主席像就令人发笑,我们权且认为是那个时代让人发笑。编导在意识形态中的迷失在于,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到,编导似乎倾向于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表示好感,那么这个干扰了新婚甜蜜体验的石膏像,这个在百姓性生活中被损坏的石膏像,它的象征意味又是什么呢?这里好像可以嗅到编导试图反讽的气味,只是不知这个反讽意欲何为。事实上,这个性体验的长期搁置,在影片最后的段落里似乎也有所回顾:春芬将旧的向阳号开到闹市,熄火了,她猛力拿起摇把想要把车发动,这时候我们想到由于崔师傅的阳痿症,春芬的性欲之花是从来没有绽放过的。一朵从未绽放的花儿就这样在时间中老去了。而且,她用摇把发动车的细节,使得她担任了人生中的一个主动者的角色,一个无作为的主动者。将这个细节和他们新婚之夜撞碎的主席像连接,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意识形态是毁掉了一代人的最基本的幸福的,为什么我们又在影片中不断看到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赞颂和迷恋?这就是又一次的迷失。
最后的一个迷失导致了剧作的可疑。崔师傅是一个热衷于写日记的人,像那个年代所有的模范人物一样,雷锋日记很有教育和感召的作用。崔师傅天天写日记不仅是春芬所熟知的事情,而且,从影片的要素上讲,是一个重要的要素,观众也已经熟知。崔师傅出事了,生死未卜,车队的同事送来了崔师傅的东西:裹在塑料袋里面的日记本。从此日记本消失了,直到最少十几年之后,社会上兴起了怀念过去时代的风气,人们来要崔师傅的“东西”进行展览,这时候,春芬才打开日记本,知道了出事那天的真相。从编剧的技术上讲,春芬晚一些看日记,观众就可以多一些时间被故事吸引。但是既然春芬在崔师傅出事的现场恸哭,恨不得和他一起去死,她又明知道崔师傅有写日记的习惯,难道没有想到去看看日记,了解一下真相?
可能编导会说,这是春芬在尊重崔师傅的隐私权。这个辩护肯定是虚弱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因为恋爱被发现,刘奋斗交代的录音中说春芬是资产阶级小姐,让她在丢掉名誉的同时差一点丢掉工作;由于新婚之夜的生理欢娱,撞碎了主席像,要偷偷掩埋;崔师傅患有阳痿症,所有邻居都用怪异的目光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于夫妻相互了解至关重要的日记本,居然可以被束之高阁十余年。况且,崔师傅的日记本从出发点而言是雷锋式的日记,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就预备着公开的,谈不到隐私。所以我们说,影片的编导又一次使用了当下自己对所谓“人权”的认识,来代替历史人物的行动逻辑。这难免又是一次迷失。很可惜。
小结
1995年,我们在论述“伤痕电影”时曾经说:“青春主题是一个开放主题。因它与人性的直接关系,在伤痕电影和以后的以‘文革’为题材的影片当中,它或隐或显地总会得到描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革’的表述也越来越姿态各异。难以用一种心情来评说人们——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革’历史的评价了。但有一点不容置疑:人们都是从关注青春出发,关注‘文革’这一段历史。控诉的声音越来越稀薄,反思的滋味也越来越淡,倒是怀旧的情绪越来越浓了。已经换了一批舞台面孔了,历史在朝前走着。《头发乱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显然有一种异样的声音,这一种异样的声音能被观众接受,绝非事出偶然:已经是由一批没有伤痕的人来讲述伤痕年代的故事了。”(饶曙光 裴亚莉:《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2-13页)令人惊讶的是,现在重温这段话竟然仍有一种历历在耳的感觉。历史在发展,电影的形态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当今或多或少涉及“文革”历史和生活的电影创作在不断远离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创作者大多是从一段甚至一点独特的情感记忆出发,展开无拘无束的艺术想象乃至文化想象。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吸引、打动当下观众(尤其是西方观众)。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艺术就是要诉诸人们独特的个人记忆、情感记忆;而且,对于电影来说,吸引和打动观众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对历史及其历史真实的尊重和供奉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超越了这个道德底线,个人记忆和想象、情感记忆和想象就会失去应有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最终成为一种悬浮在天空中的“漂浮物”。
中年和老导演在关注现实,年轻导演集体怀旧,是2005年中国电影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现在就断定《芳香之旅》、《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影片会对诸如此类的电影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随着最近几年与《芳香之旅》相近题材的增多,我们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历史成了一种仅供轻描淡写的装饰,当编导者将自己对青春的爱惜和那一段历史嫁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段历史也就变得没有瑕疵,叫人向往。如果真的能够从“文革”中抽取出一种精神上的成果,固然可喜,但是这些导演似乎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又在毫无顾忌地进行反讽。这就使得新一代的导演在书写“文革”和新中国历史的时候,迷失了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也迷失了基本的从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方法论。
标签:芳香之旅论文; 我们的田野论文; 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论文; 刘奋斗论文; 青春祭论文; 梨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