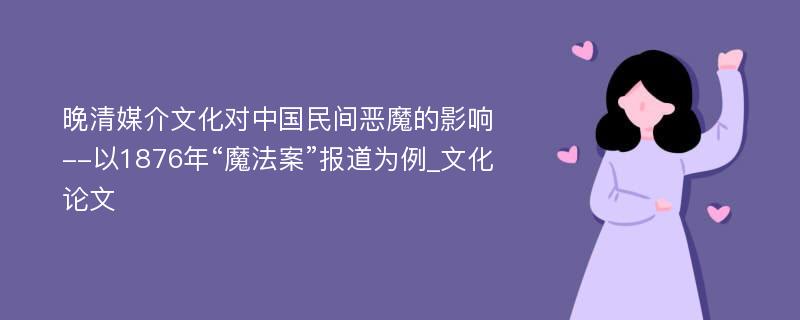
清末传媒文化对中国民间妖术的影响——以1876年《申报》“妖术案”报道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妖术论文,清末论文,为例论文,中国民间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古代,妖术的恐慌从未间断。1768年,清朝乾隆皇帝年间,江南地区引发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的“剪辫摄魂”的妖术恐慌。历史惊人的相似,1876年,清朝光绪年间,以“剪人发辫摄取魂魄”(以下简称剪辫叫魂)的妖术恐慌再次滥觞于该地区。而在1876年之前,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知”已经由传教士引入中国。早期的传教士出版报刊不仅宣传西方的宗教思想,而且在于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虽然其目的在于保护在华西方侨民的尊严和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渗入。科学文化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的民间妖术发生碰撞。《申报》作为当时的新式报刊之一,对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妖术案”进行了大篇幅的连续报道和评论,那么《申报》是如何呈现这一妖术事件的?同时,《申报》等近代报刊对中国民间妖术的传播和控制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将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一、《申报》的选择 “剪辫叫魂”妖术从现代的角度看是一种封建迷信。但在清期,“剪辫叫魂”被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统治阶层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清乾隆年间,民间尚无与统治阶层相抗衡的话语力量。“剪辫叫魂”妖术被统治阶层戴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剪辫叫魂”在当时并不解释为一种封建迷信,而在某种意义上与谋反相联系,“剪辫叫魂”兴起预示着清朝政治将发生异动。乾隆皇帝利用这次妖术事件对全国官员进行了一次大清洗,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1876年(清光绪二年),江南地区同样引发了以“剪人发辫以摄取魂魄”的妖术恐慌。但是,近代新式报刊形成了独立于官方的强大话语体系。当时的主要媒体《万国公报》和《申报》对此事的报道采取了不同的选择。《万国公报》明确表示不信此谣言,除了光绪二年6月17日,6月24日登载了江南地方官府的辟谣告示以外,对于谣言本身的内容和传播情况一概不予刊登,以防以讹传讹。而在上海的《申报》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在以“剪辫”“妖术”“打印”为关键词的搜索下,可以发现《申报》对此事的报道大约有100篇。这一系列报道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876年4月到1876年的12月,总时长约9个月。可以这么说,《申报》对此事进行报道本身就意味着新式媒体已经渐渐介入社会议题,打破了统治阶层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局面,对“剪辫叫魂”进行更深层次、更多元的解读,并把这种全新的解读带到民众和官员的视野中。 二、“妖术”的呈现 《申报》的报道内容是本文考察的重点,而一般分析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内容主要从新闻报道的频率、时效、形式和新闻框架入手。在所选取的报道中可以发现,1876年的5月、8月、9月为报道的高频率发布期。从新闻报道所提到的地点可以推断出妖术传播的主要范围,4月至7月,传播范围集中在长三角一带,“起于金陵后及于苏垣,今又至扬州。”[1]“金陵苏扬外由浙而至上海、杭垣、浙江绍郡。”涉及的主要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扬州及其乡镇。根据报道时间,谣言几乎传遍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时间大致是两个月。8月至12月,传播范围仍以长三角为中心,“剪辫一事初抵金陵、扬州、苏省上海渐及杭嘉湖等处,前月从皖南者及芜湖湾址经县宣州大通。”传播范围顺着长江流域扩散,安徽、江西、湖北也被谣言所波及。《申报》对此事的报道形式主要由新闻消息和新闻评论组成。一方面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对各地剪辫事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刊发了读者、本报刊对此事的评论。 对此事件最早的报道可追溯到1876年4月4日,“石工起造桥梁将须合龙之际,俗传叫魂之法。金陵城内人心惶惶,多将红布一角缝在小儿肩上。”[2]剪辫的场景通常为,“旋风一阵,风中若有一团黑影吹至面前不觉毛发森竖,风过处发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然至短亦连发梢一二寸从无仅失去发线者。”[3]被剪发之人“大半童子余则市井小民从未敢剪衣冠中人。”[4] 在“妖术案”初期,《申报》已经推断此事“均系异端邪教煽惑人心。连日城乡内外谣传颇多,若不严防密查从重惩办,恐奸民暗施邪术不免酿成事端。”[5]并且将“剪辫”一事作为普通的社会新闻报道,既然是新闻报道,那么《申报》在报道上就有较为严格的新闻把关和选择标准“择其有名姓可考者登之”,[6]并不是“有闻必录”。《申报》对收到来信中的事件要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信息要十分准确,有些报道的时间能具体到准确的时刻,如“初六下午四点钟时间有镇海人自鄞江北归至白沙地方忽觉头晕眼花恍惚中见有一人手拍其肩时身定举足微觉…”[7]从四月份开始,《申报》几乎每天都更新关于“剪辫”事件的报道,发布频率十分频繁,而且每篇报道都交代了详细而准确的事发地点。比如4月29日再述吴中剪辫、5月3日纪扬州剪辫事、5月16日纪上海亦有剪辫事、5月25日杭绍剪辫、剪辫到乡、5月30日杭垣亦有剪辫、5月31日吴中续有剪辫、6月3日双林镇亦有前辫、8月2日武汉剪辫事、8月15日南汇琐闻、8月16日昆陵异闻等。上海本埠以外的各地剪辫事的多由读者(报中所称友人)提供。如4月20日的报道《剪辫续信》中提到“昨接稣友信谓吴门近日亦传言纷纷……”,5月3日的报道《纪扬州剪辫事》提到“此事据扬友函称人所共见共闻……”,5月10日报道“日昨吴友函来又述及……”而在上海的信息大多由本报记者提供,“昨日报上万盛牲店内剪去辫子两人,昨晚又有店伙一人被剪连辫绳发辫一并剪去本馆分报人之人亲眼所见…”[8]随着谣言的进一步扩散,读者给报社的来信也越来越多“沪上近日到处剪辫报不一报已成案见不鲜矣…”“剪辫之说各处相传久矣,或曰纸人或曰妖术或曰即剪绺贼所之为众议纷纷究亦莫衷一是,此已数见不鲜,本可无容记及惟近据友人陆续邮示是亦不可不登报章也。”[9]读者提供的信息不仅丰富了《申报》的报道内容,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申报》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各地民众对此事件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民众的媒介意识苏醒,能够知道通过报刊寻求帮助。 《申报》在报道上不仅注重新闻的真实性,而且注重新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申报》在报道中对“剪辫”一事评论“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于剪辫一事乃见人人之俱为孝子矣。”[10]颇具黑色幽默。并且在报道中注重对剪辫过程的细节描写,通过不同角度的类似志怪小说式的叙事手法,再现还原剪辫现场。如描写“纸人”的样子,“纸人一个计五寸余长剪成武十像腰画书战裙着靴右手持剪左手持牌前胸画一太极图,后颈书三圈圈内写天地人三字,背上写大球贯出八十七号两足皆有符印,身上许多血点剪口亦涂红纸,此杨友所目见。”[11] 随着事件的不断扩散,“剪辫”谣言又向长江中游传播,皖南、武汉等地也出现了剪辫谣言。6月起,官府“各处巡查无不留心”抓捕“剪辫”之人。最早的抓捕行动从安徽各地开始,“官长及军民人等留心各处业已抓获四人,搜出发辫无数复有妖书数本。”[12]地方各省的剿匪也在陆续开展。《申报》连续报道官府拿获剪辫人的情况:“安徽之处亦有剪辫之事其处官长及军民人等彼此留心缉捕业经获得四人搜出辫发无数复有妖术数本,当即根究同伙,据供其党有数十人散处各省云云。现已咨会队封一体查缉矣,其妖人姓名并有司如何惩办容续探再登。”[13]从他们捉获的教民以及教匪口供得知:这些人供述自己是破钱教的教民,为了“祭活纸人七万可当千军万马炮枪不入,须得生人发辫两万条方始功行圆满。”,需要发辫配上纸人即能成为活人,一根辫子可以配三个人,共需要割两万余条辫子。[14]教匪中的教徒通常“按八卦之数皆扮游方僧道头领。”教匪陆续供述散处在各省的同伙。《申报》把关于与妖术有关的事件全部收录,比如妖人的长相,邪教的入教规则,各处邪教的地址以及教民如何传递信息。为了证实谣言乃邪教所为,《申报》在1876年8月18日的《拿货九龙山匪党》的新闻中,插刊了用木板雕刻的“九龙山匪党”臂章图样[14],这是《申报》创刊以来第一次刊登的新闻图片。 在官员缉拿妖犯的同时,由于“官办不如民办之速。”各地民众组织起自为团(“民间自为团练互相保护”[15]),对往来的可疑人进行身份的排查,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无辜的民众被误打或者被误杀。《申报》记录了这些被无辜杀害的事件。“因音同字异而身受剥肤之灾”一男子捡到一条辫子,因“捡”与“剪”同音,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暴打扭送官府,经一老人澄清此人才脱罪。[16]无锡贩猪客被民团搜出剪刀三把,被指为剪辫,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便将三人斩首其余两人交给县衙询问后得知此五人均是贩猪客,所带剪刀因买猪时须就猪身剪毛作记。[17]同时,由于民众怀疑的逃犯进入外国教堂获取庇护,“获到作法之人送县,经神甫讨出,于是民心愈不能平。”民众又把矛头指向外国教堂。“教堂作大会,神甫恐生事端,先于二十五日亲至锡(无锡)、金(金匮)两县,请官出示谕,以谣言惑众,例干严禁,剪辫厌人并无其事等语。并令两县派拨官亲随带壮丁及守备、千总、外委、营兵齐赴天主堂门前看守,酬劳犒赏。是日,教中集有三四千人,颇形热闹,然百姓见之,更忿形于色。”[18]而江阴县传来一则破除妖术的方法,即以白石灰画“十”字于街道地上,妖术立破。天主教神甫当然不依不饶,又到锡、金两县衙门咆哮,两县随即传谕各保,勒令将已画的“十”字务期洗刷净尽,并威胁尚敢再违,定干究办。民众的暴力添上了反洋教色彩。面对民众反洋教事件,《申报》迅速发表评论“前据庐州所获之教匪供词实系九龙山和尚主使名为半钱教与洋人无干或锡金之丝网船户明托天主教暗结半钱教则为可知,神甫不察力为教友袒护,人因是一疑百疑耳。”[19]面对妖术谣言带来的巨大社会恐慌和破坏,《申报》在详细报道各地剪辫情况及事件进展的同时也在零零散散的报道中多次辟谣。辟谣的方法一般为报道先描述剪辫或纸人新闻,然后指出错误。比如5月24日的《谣言失实》纸人乃是“童儒无知误听谣言遂哭告父母而人因信为妖法所致其实。”5月31日的《假纸人》“十余年前苏垣初复尸积人烟因有野狼出没噬人而穿窬者蒙皮效之人见而生步被逐攫取财物近有纸人剪辫之怪不意亦有假之以作奸者。”《申报》认为此事元凶并并非纸人而是真人假借纸人的名义趁机谋财害命。《申报》提醒官府要“留心民瘼”,“剪辫仍是人为之非纸人为之也,安得地方守令皆如安庆公之留心民瘼使黎庶安哉。”[20]另一方面,《申报》也告诫民众“勿惑邪说”。虽然官府在大范围得对谣言进行打击,但是各地谣言还是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了新的谣言内容,比如“阴兵过境”“复云打印”等,“昆陵民众买铜锣驱鬼,[21]常州府家家户户放炮以辟邪[22]。“妖魔鬼怪有其名而究无其实。前传有剪辫事先謂被剪辫者三日后必死,终謂一百二十日后必死,今已逾三月究问何人因剪辫而身死耶?”[23] 除了自身发表评论揭露妖术真相以外,它还引用他人对“剪辫“事件的看法,如全文转载钦差大臣晓谕“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近有匪徒以能用纸人剪人发辫为名妖言惑众迭经拿获正法枭示,然皆查有实据,訉有确供是以照例严办若仅因迹涉疑似不候官訉辄行聚众殴打甚至疑及教堂所为深恐藉端滋事酿成巨祸合行出示晓谕为此仰军民人等知悉此项匪徒向系白莲教党羽并与教堂无涉如果查有剪辫切实据无论平民教民均应听地方官查拿不得捕风捉影遂行滋扰如敢故违定即严拿惩办切切特示。”[24]晓谕中强调了三点,一、指出匪徒已经被抓获。二、此事与外国教会无关。三、民众不能捕风捉影,否则要受到惩。此外,《申报》还在评论中引用其他报纸的看法,如“字林报论及近日纷纷传说剪辫一事或请有妖法或谓有纸人是皆不足信…”[25] 针对此次妖术案,上层官员和地方官员对待此事的态度各有所不同。上层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对此事却格外敏感与愤怒,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匪徒作祟、乘机闹事。“剪辫”是一件谋反行为。恭亲王奕诉在美国使馆听到了京城剪辫之事后,立刻向何天爵询问剪人发辫的装订工真实姓名及其具体地址,并对他处以极刑。[26]而地方官员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呈《匪徒传习邪术现筹查办折》提到“该年三、四月间,金陵即有纸人剪辫之警,五月间遍布安徽庐州、池州等府,英山、霍山、建德、潜山、东流、石埭等县。自六月以后,沿及扬州、镇江、常州等处,并渐至苏州。城乡彻夜不眠,鸣锣巡警,或捕风捉影,妄拿无故;或逞忿挟嫌,栽害良懦,甚至觊觎孤客。”沈葆桢认为,白莲教是组织策划并积极参与剪辫等邪术活动的主要头目。[27]官员们认为此事是谋反和邪教所为。《申报》并没有对此事有过多意识形态的渲染,而是更多得以事实呈现的方式为民众辟谣。事件之初,《申报》指出“昔白莲教初期时,亦有纸人纸马邪法,以动摇人心。今海内虽云安堵,然盗贼奸佞潜踪草莽,狡马思逞者正不乏人,在上者不可不防微杜渐也。况近日剪辫已非一处,通都大邑之中皆有匪类出没,若不急为稽查,恐至酿成不测。[28]《申报》认为此次社会动荡的原因有三:第一、官府不作为:“地方之责者不得正本清源之道,一味养尊处优,随时自逸以不理理之,以致百姓疑官长庇护异类玩视民瘼也,官则似瞶如聋,徒示镇静。民则捕风捉影愈觉张惶,于是无辜受害匪徒漏网、上下相仇民教不和。…地方事务督抚司道可以镇静,守令丞尉不宜镇静也。”[29]其次,奸猾之人借谣言乱世。“城中奸猾胥役栽赃故智自作纸人择良懦可欺者,乡间杰悍之徒又藉团练盘查为名见过往行旅携有财物,口音稍异,回答稍迟初犹捆送官府终竟私行惨杀”。[30]最后,愚民的无知。“近来苏常两府属传纸人妖异,初则剪辫继之打印,复云压人甚且能化毒蛇异物,先謂九龙山匪党后疑及别教之民,究之其事固多诬妄其人亦无确凭而闻风谣乱一唱百和,举国若狂奸民四应以致野废耕盘市废贸易擅杀无辜酿成巨祸,光天化日之下有同异域蛮方尚复成何世界,究竟何妖之有,何邪之有,尽是无知愚民以讹传讹自作自受尔。”[31]最后一点是官员没有深刻意识到的,即使是奸人作恶,邪教所为,《申报》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愚昧和迷信思想。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申报》引用西人对此事的看法,西方自古也有邪术事,但是“及至物理与格致各真学兴于民间则邪术各虚传即为之止,盖真学渐兴而邪术则渐无矣。”[32]邪术传至上海,上海的西方男女皆不相信此事为真,因为“西国男女皆能读书明理故也至于华人之男女其所以深信不疑者亦有故,盖由于华人之男女能学者少,不学者多故至胸中全无道理专以道听途说者居多…”[33] 但需要指出的是,《申报》在报道此次妖术事件时,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它一面告诉民众此乃无稽之谈,另一方面也刊登各种辟邪办法。比如,金陵民众用黄纸朱书「哇喃咱叱吽」贴在帽子里,或者“等风来时急用污秽物等物抛向纸人”杭州人也用黄纸朱写辟邪字样贴于左门,或佩戴在身上等。谣言内容最初为”叫魂”和“剪辫”,随着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剪辫”又演变成复云压人、“阴兵过境”。《申报》也刊登了详细的出自《警富新书》的辟邪办法,“剪辫有药可以治其芳:朱砂、雄黄、金银花、青柯、蔴末、獨蒜子,又另写二字同药煎洗,洗时默念咒语三遍,咒曰割…..”[34]社会上也是如此,对于“剪辫”一事官员们的行为并没有比普通民众开明多少。根据美国传教士何天爵的回忆,据他观察,当“剪辫妖术”传播到北京后,北京的官员发布了许多通告,但“每张通告的内容与其说起到了消弭人心混乱的效果,倒不如说它雪上加霜,更增加了人们的骚动不安,这些通告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出门,不要与陌生人接触,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提供一些民间的巫术偏方保护辫子。”[35]可以看出,当时《申报》在抑制民间妖术谣言时所遇到的阻力。当时正处在一个从愚昧走向科学的过渡时期,《申报》直接向民众阐述此乃封建迷信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刊登辟邪的办法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 三、“妖术”谣言余波 1877年,京津地区又发生了剪辫谣言,《万国公报》对此事件只发布了一条消息“上年自江浙等省剪辫谣言甚重越传越开,究未见其实,在今春又传之京都自复稍息今忽后有谣言此剪辫事又于天津北京已及盛京各处皆有其实情仍然未经查确。”[36]而此次“剪辫风波”《申报》对其报道篇幅和字数也大大减少。“京友”来信称“灯节时某京堂之甥年十四岁在家读书时吟哦之际忽打一寒噤而辫已剪去举家皆之惊恐,然亦无甚病在后,辫仍送回并闻途中失辫者甚多。[37]最后此事的真相乃是小孩为逃学想出来的计谋。但是由于民众对剪辫的恐惧,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乞丐僧道一概不准过境,许多行路客为本地人活埋投水”但这些事立马被官府平息,谣言也随之而止。在此之后,《申报》几乎没有再对“剪辫妖术”的报道。再把时间延长到此次发生的三十几年后,在1876年至1900年间考察传媒文化对民间妖术的影响会发现,近代报刊都采取发布辟谣报道或者发表各种关于对妖术的评论“启迪民智”。比如万国公报曾在这三十几年发表过《谣言惑众》《谣言宜禁》等评论,并且指出民间妖术并非一次而人却屡为所惑“愚夫愚妇为其所惑推其受惑之故大抵由于不明其理,不信真道耳。”而创办于1897年的天主教报刊《益闻录》也曾多次发文《谣言可笑》、《谣言可恶》、《谣言惊众》等文章引导民众勿信妖术谣言,要相信科学真理。由于笔者的阅读能力有限且许多报纸已经查无记录,只能通过这些报纸的表现推测在此期间或许还有其他报纸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 《申报》首次详实、深刻地记录了1876年的妖术事件。相较于古代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谣言,谣言主要借助于人口自然流动和道听途说的方式,社会上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和流动速度决定了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38]。《申报》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在乾隆年间的妖术恐慌事件中,官僚系统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官员上达民情也得通过官僚系统。官员时常隐瞒实情,为事件的处理增加了难度,《申报》等近代报刊的崛起,形成了独立于官方的强大话语体系,并且形成了具有科学和现代性的文化与中国民间迷信文化相对峙的局面。《申报》对事件的报道,造成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提供了更多有效且真实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妖术迷信的瓦解。这场谣言历时9个月,而乾隆年间的妖术事件历时3年之久,而在这之后,剪辫叫魂谣言式微,虽然有科技进步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报刊在传播科学精神,抑制迷信方面也同样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