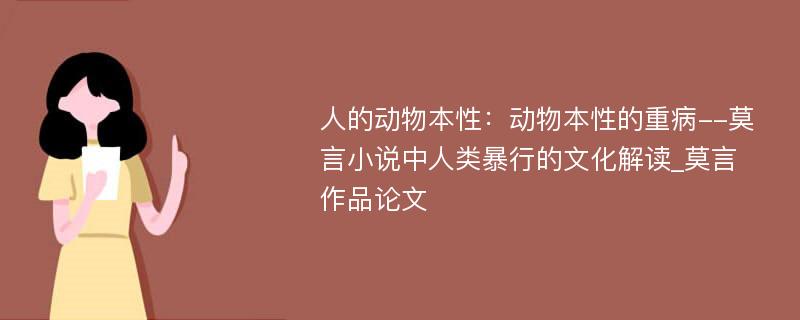
人类兽性:动物性的沉疴——莫言小说中人类暴行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疴论文,人类论文,动物性论文,暴行论文,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5)02-0042-08 对人类兽性行为的书写是莫言作品的重要特征。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灵巧技艺,到《二姑随后就到》中四十八种刑罚的名目繁多,再到《檀香刑》中“阎王闩”、“檀香刑”的复杂、精巧,甚至透着典雅的气息……莫言把人类兽行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描写可谓冷酷、血腥、灭绝人性,作者也因为对这些酷虐场景的过度铺陈招致诸多误解和非议。然而,莫言的精妙不止于描述各种酷虐场面的血腥、暴力,我们看到的,也不仅是人类兽性行为如何具体作用在一个个鲜活的肉体之上,感受由肉体之苦对神经的刺激;他要展现的,更是一场又一场关于生命的悲剧。莫言用最残酷的方式,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美好的生命撕碎、毁灭,传递给读者精神的战栗,让读者从灵魂深处发出对人类兽行的恐惧与拒斥。 有人这样谈论刑讯:“惩罚同类的肉体无疑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究竟起始于何时。该发明基于一个最为直接的观察:只有肉体的痛苦才是一件最具私人性质的事情,无法被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所分担,惩罚肉体也就最能达到惩罚者的目的,并让后者如其所愿地屈服。”①刑罚以对生命的戕害为目的,它是一个政权维护其统治的手段,统治者通过对反动作乱者、违反统治秩序者用刑,达到威慑百姓的作用,以顺其民。福柯说得很精妙:“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斗争,因为一切力量,一切权力和一切权利都属于一方。”②在莫言的作品中,“凌迟”是最能体现生命消逝过程感的刑罚之一。观者目睹了一个鲜活的肉体被一刀一刀脔割,生命被酷刑一点一点蚕食吞噬的整个过程。《檀香刑》中的钱雄飞拥有匀称健美的身体,这是有四十多年刽子手经历的赵甲第一次见到的完美身体。他两刀旋掉钱雄飞的胸肉,他“感到钱的肉很脆,很好割。这是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的犯人才会有的好肉。”③这样一个年轻、健壮、血气方刚的体魄,正值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在经过刽子手赵甲五十刀之后,两边胸肌刚好被旋尽,此时,“钱的胸膛上肋骨毕现,肋骨之间覆盖着一层薄膜,那颗突突跳动的心脏,宛如一只裹在纱布中的野兔。”④五十刀之后,钱雄飞依旧是一张悲壮的面孔,紧咬牙关,当赵甲割掉钱的舌头后,钱仍在用喷溅着血水的嘴巴含混不清的大骂袁世凯。三百七十五刀过后,钱雄飞的大腿、双臂、腹部、屁股部位都已被赵甲精准的刀法脔割殆尽,此时,钱雄飞的生命已经垂危了。在最后几刀分别割掉钱的耳朵、鼻子、眼睛之后,第五百刀切入钱的心脏,割下了心头肉,钱雄飞,一个健硕的身躯就这样消逝了。“凌迟”让人目睹了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在赤裸裸的脔割中,强悍的生命被一点一点扼杀,旺盛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残忍的过程。当作者把如此鲜活、强悍的生命放置在酷刑之下,使之消逝、殒灭,这不能不说是对读者精神的一大冲击,在这里,悲剧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酷虐的刑罚对人类强悍生命的剥夺,是发霉的历史文明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上演的,则是对稚嫩生命的屠戮。《酒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可爱的婴儿被高科技文明化的方式宰杀、烹饪,使稚嫩的生命最终成为消费者口中的美食。在宰杀之前,他们是那样鲜活可爱:“他的圆圆的、胖嘟嘟的、红扑扑的小脸正好侧对着学员们。”“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一个美丽、健康的小男孩。他的头发乌黑,睫毛长长,蒜头小鼻子,粉红的小嘴。粉红的小嘴巴嗒着,仿佛正在梦中吃糖果。”⑤这样一个惹人爱怜的小生命,转瞬间,在烹饪教授的指挥下,“被抬进一个特制的、鸟笼形状的架子上,架子上端有一个挂钩,可以与操作案板上方的吊环相连。”“肉孩在笼中,身体被禁锢着,只有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脚,从笼架下伸出来,显得格外可爱。”⑥等待着肉孩的,是被放出体内所有的鲜血,烹饪教授用一柄银光闪闪的柳叶刀,对着肉孩的小脚切开,“一线宝石一样艳丽的红血,美丽异常地悬挂下来,与他脚下的那只玻璃缸连系在一起”⑦。一个半小时过后,肉孩的血被控干,接下来,肉孩被尽可能完整的取出全部内脏,之后用70℃的水,除掉它的毛发……至此,一个粉嫩可人的生命被处理成烹饪待用的食材。 莫言塑造过太多美好的生命被人类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撕碎,他们强悍如钱雄飞、孙丙一样的英雄,娇嫩如《酒国》中的婴儿,还有一类生命,他们被扼杀在母体之中。在长篇小说《蛙》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妇产科医生,人称“送子娘娘”、“活菩萨”的姑姑,在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变成了人称“活阎王”的杀人狂魔。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基层执行者,在她手中,几年间,几千条未出母体的生命悄然殒没,这些尚未发出任何声响但同样经受了孕育过程的生命在人类的漠视中被扼杀。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凌驾于对一切社会道德、法则的遵守,是莫言一贯的价值诉求,《蛙》更直接抒发了作者对生命的敬畏感。作品以《蛙》命名,“蛙”与“娃”“娲”同音,女娲是造人的始母女神,娃是人类生命脱离母体之后的起始阶段,而“蛙”本身更作为多子的象征,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图腾,被人们崇拜。作者通过隐喻的方式,将蛙与生命连在一起。小说通过主人公姑姑的一段回忆,将蛙与人类生命的孕育过程建立起同构关联: 你出生的那天下午,姑姑在河边洗手,看到成群结队的蝌蚪,在水中拥挤着。那年大旱,蝌蚪比水还多。这景象让姑姑联想到,这么多蝌蚪,最终能成为青蛙的,不过万分之一,大部分蝌蚪将成为淤泥。这与男人的精子多么相似,成群结队的精子,能与卵子结合成为婴儿的,恐怕只有千万分之一。当时姑姑就想到,蝌蚪与人类的生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⑧。 姑姑这段话描述了人类生命的孕育过程,每一个生命都是经过如此艰难、悲壮却又十分幸运的过程产生,因而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珍贵,理应被尊重被敬畏被珍视。然而,生命曾经遭到无情的戕害,这是人类对生命的犯罪,是对自身生存的否定,是对生命逻辑原点的毁灭,这会使人类对任何价值的追求都失去真正的意义,而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人类本身,是“人兽性”。莫言用对美好生命的毁灭来引起人们对“人兽性”的强烈憎恶,进而思考其发生的根源所在,这是他煞费苦心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深意。引导人们一步步向兽性的发出点逼近,追问是什么原因让人变成野兽,或者,是什么原因让人将人看做野兽,这是莫言的小说极力思考与表现的主题。 人类兽行发出者表现出的“铁面无私”、“大义灭亲”令人印象深刻。《檀香刑》中的赵甲“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⑨我们对他从业四十多年的职业经验大致可以总结为:受刑者物质化⑩,施刑者神圣化。成为一名优秀的刽子手需要眼中无人、心中无人,即眼前的受刑者不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他(她)只是一个物质的人,与任何动物无异的血肉之躯;刽子手只需要按照具体刑罚的要求、步骤,把活干好即可;一旦把受刑者当活人来对待,就会影响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赵甲被钱雄飞健硕美好的身体惊呆了,也被他临刑前的表情和姿态威慑住了;眼前如此鲜活的生命、潇洒的模样,使赵甲居然无法进入“目中无活人,视人为物”的状态,直到钱雄飞“灰白的嘴唇颤抖不止”,他掩饰不住的恐惧恢复了赵甲的职业荣耀。看起来刽子手并不是天生残忍无情,之所以能够练就如此冷酷、铁石心肠的心理背后有强大的精神支撑,那就是对权力的服从,并使这种服从上升为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也是对施刑者进行自我神圣化的过程。福柯说:“在任何社会里,身体都要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11)的确,人的身体不断受到权力的干预、控制,使自身的各种力量被强加上一种驯顺的功利关系。这种干预、控制的手段基本体现为“纪律”,这是权力用来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强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12)“纪律”是任何社会实现对民众统治所使用的投入少、成本低却收益显著的重要手段,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之一。对纪律的是否服从,成为衡量体制内民众基本素质的标准服从纪律、对权力的驯顺行为被体制赋予有用、有价值;对权力的违逆,则被社会视作“反贼”、“反革命”等被消灭。“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是唯一的美德。”(13)赵甲的杀人行为是对国家权力的顺从,他也因此种行为变得对社会有用,他个人的社会价值是通过刑场的精彩表演来实现的。在拿起屠刀的那一刻,他感到“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道德法律之手。”(14)此时,赵甲的精神被王朝的荣耀胀满,如同鼓起的船帆,接下来的只是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完成他手中的艺术品,他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凌迟所需要的那五百刀…… 看起来,以权威、荣誉为代表的文明不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约束存在,“同时又作为一种内在化的力量,对个体施加影响,因为社会权威已被吸收进了个体的良心和无意识之中,并作为他自己的欲望、道德和满足的东西在起作用。”(15)更让人震惊的是,这种力量会内化为一种精神传递下去。由于权威约束机制的内在化,使赵甲对自己的职业产生由衷的热爱感和庄严感,他曾经对儿子说:“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就瞧不起了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猪狗没两样。”(16)既然眼前的受刑者不再是人,只是有生命的动物,赵甲杀人与儿子小甲杀猪、屠狗在本质上就是相同的。然而二者又大不一样:“同样是个杀字,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17)赵甲极力劝说儿子改行,跟随自己学习这门神圣的技艺,以光耀门楣。每当谈及自己的刽子手职业时,赵甲总是心怀神圣与庄严。历朝历代刽子手的行规:在行刑前用鸡血涂抹手脸,此后“我们是皋陶爷爷的徒子徒孙,执行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18)。站在刑场上的刽子手见了皇帝也不用参拜,可见此刻的至高无上性。他曾在面见袁世凯和慈禧太后时慷慨地说道:“小的下贱,但小的从事的工作不下贱,小的是国家威权的象征,国家纵有千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这一行。眼下国家动乱,犯官成群,盗贼如毛,国家急需手艺精良的刽子手……”(19)赵甲也凭借精湛的技艺被慈禧太后赞为“刽子手中的状元”,并带着太后赏赐的檀香珠和皇上赏的龙椅,以七品官的待遇告老还乡荣归故里。这次执行檀香刑是赵甲回乡后第一次出山,他把这次出山看做对皇上太后、国家的尽忠,看做对自己一世英名的完美成全,是自己事业的再次辉煌。在赵甲的意识里,我们看到一个生存在体制内的人,如何把体制加诸给他的纪律发展成荣誉,“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20) 国家赋予个人的荣誉,在个体的心中会上升为最崇高的规则与感情,甚至会使个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对组织的服从过程中,《蛙》的主人公姑姑的确做出了一定的个人牺牲,她的心理要比赵甲更为复杂。姑姑出生在旧中国,成长在新中国,父亲是曾经和白求恩一同工作过的党内军医,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姑姑放弃很多可以远走高飞的机会,选择继承父业留在高密东北乡,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工作的新技术妇产科医生。姑姑对工作极度热忱,对事业极其忠诚,凭借精湛的接生技术,被东北乡人赞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不久,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姑姑成为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为了开展计划生育,姑姑积极宣传:“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21)作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奉者,民众无法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姑姑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22)然而,姑姑不为所动,仍旧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宣传工作;面对恶意的指责、谩骂、攻击,姑姑无动于衷,她对侄子侄媳说: 我告诉你们,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对那些计划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23) 国家政策的变化,改变了姑姑的命运和性格,不变的是她对事业的忠诚。曾被男友在日记中称为“红色木头”的姑姑,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惜流血牺牲。随着计划生育的白热化发展,姑姑们的行为和手段日渐狠毒,她们从开始的宣传、教育发展到血腥的阻止,在这个对抗斗争的过程中,姑姑曾多次遭到被计划者的毒手。张拳是东风村无人敢惹的强汉,对公社的计划生育动员工作不以为然,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张拳妻怀有第四胎的肚子上,尤其是那些生了二胎就被强制放环被计划生育的、生了三胎就被强制结扎做了绝育手术的,更对张拳家怀了四胎愤愤不平,在周遭的压力和众目睽睽之下,对张拳家的计生工作更显得重要,对其执行政策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今后工作的开展局面。但张拳蛮不讲理的态度,动辄拼命的行为使公社无计可施。面对此种情况,姑姑直视张拳那张狰狞的脸,带着助手小狮子一步步向他逼近。首先迎接姑姑的是张拳三个女儿的死缠烂打,紧接着是张拳的当头一棒,血从小狮子给姑姑包扎的一层层绷带中渗出来,把周围人看呆了,张拳一家的嚣张气焰顿时被扑灭了,民兵们把张拳按倒在地,妇女干部们把张拳女儿一一制服。姑姑并不计较个人伤痛,她还是晓之以理的给张拳讲执行政策的必要性:人口不控制,必然会导致缺衣少食,很多孩子受不到应有的教育,人口素质难以提高,国家会陷入贫困状态,为了国富民强的国家大事,姑姑有甘愿献出生命的决心。张拳老婆后来死在逃离工作组被追捕的过程中,姑姑却没有因为一条人命的失去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不惜使用野蛮的手法控制人口的出生,她把逃避计划生育的群众当成敌人来剿灭,这里面包括普通群众,也包括她的亲人,在一场场斗争中展示了姑姑过人的智慧、胆识和谋略,更显示了她的“铁面无私”、“大义灭亲”。 当正常人在看到肉体受到折磨时都会自然产生动物性的同情,而施虐者之所以能够摒弃、抑制身体里面的动物性同情,凯尔曼给出了原因: 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24) 这是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之后,社会学家对暴行进行反思时的分析结果。无论对赵甲还是姑姑,施虐者能够战胜动物性同情,战胜世俗的不理解,首先皆源于第一种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对上级指令的服从,对组织福利的献身,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对文明社会来说,纪律的理想旨在与组织的完全认同,这反过来意味着要消除个人的独立特性、牺牲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与组织任务不相重合)。在组织的意识形态中,准备做这样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被表述为一种德行;准确地说,是被表述为注定要取缔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因此,用韦伯的名言来说,对这种德行无私地遵从乃是公仆的荣誉:“因为他尽心尽责地执行上级权威下达的命令的能力而被授予公仆的荣誉,就好像这些命令与他自己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使当这些指令在公仆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即使公仆们有所抗议,上级权威仍然会不屑一顾地坚持这些指令。”(25)对公仆来说,这种行为意味着“最高意义上的道德戒律和自我牺牲”(26)。 除去组织权威的精神支撑之外,施虐者理直气壮施暴的心理因素还包括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这一条件。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被意识形态浸透:世界上有两种生命,“有价值的生命”与“无价值的生命”,犹太人即为无价值的生命,“犹太人是‘粘菌’(虐原虫)无形的粘王,从远古时期就存在并蔓延到整个地球。因此对犹太人进行隔离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措施,只是通向最终目标路途上的一个站点。如果不把德国的犹太人清除干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结束。即使犹太人居住在离德国边界很远的地方,他们仍然会继续侵蚀和分解全人类的自然逻辑。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为了日耳曼种族的至高无上而战斗,他相信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以全部种族的名义、为按人种组织的全人类做贡献的战争。”(27)同大屠杀相类似,赵甲“目中无人”的境界即是这一说法的很好明证:刑台上陈放的只是一堆筋络、皮肉、骨架,他们丝毫不具备人的特征,他要做的,是按律例的具体要求分解这些皮肉组织;在《蛙》中,姑姑对超生孕妇穷追猛打,在她的思想中,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而在母亲身体里孕育的还只是块肉,同样是这一说法的很好证明;《酒国》中,烹饪学院的教授在宰杀婴儿时,不断向同学们强调: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人形小兽,更是很好的证明。 施暴对象的非人化特征使施暴者在施虐的过程中心安理得,如大屠杀一样,不仅兽行不会使道德背负起罪恶的负担,相反,它成为人类的正义事业供人孜孜以求。赵甲从事的事业是一个王朝兴衰的标志,当他把这个卑贱的行业与国家利益、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刽子手的行为立刻焕发出光芒,他会把这个与国运休戚相关的事业做到精益求精。姑姑在追逐、捉拿一个个超生者的过程中,除了服从党的指示、执行国家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心中,“计划生育”是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诸如此类种种都成为人类兽行发出的心理成因。 姑姑和赵甲等人类兽行的发出者不过是莫言虚构的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符号化人物,赵甲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舐犊情深、姑姑曾经的“送子娘娘”美誉,都表明他们和其他正常人一样,有爱心、有同情心,有常人的一切感情,并不是生就杀人如麻、嗜血如命,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冷血无情?我们可以回到人类本身的动物性上面来寻找答案。人类的动物性包括与生俱来的嗜血性;嗜血性在动物身上表现为弱肉强食、残酷的肉搏相争,当动物在攻击过程中把同类对手击败之后,就会收敛自己的攻击行为。这是极为原始的状态。然而在文明社会,文明会把这种原始的内驱力理性化,进而滋生出更为野蛮的行为举动。侵略性作为一种动物属性,是人与动物间相通的,然而它们却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动机出现在二者身上,对此,弗洛姆做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分析:动物的“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服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28)动物的侵略性是符合生理需要的一种反应,在人类的侵略性中包含来自动物祖先遗传下来的侵略性,它属于一种自卫本能,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它是生命应对外部威胁的一种直接反应同时人类还有一种独有的侵略性,这是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29)人与动物相一致的生理性的侵略性,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强烈”,“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记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30)这是弗洛姆对人类兽性给出的解释;人类的动物本质决定了人必然从动物那里遗传到一定的兽性因子,具有先天的侵略性,但这只是身体遭到威胁时做出的正常反应,不足以支撑人类的兽性行为。真正起到发扬、异化动物性侵略行为的,是社会存在本身。当人类体内的兽性因子被冠以文明范畴中的“正义”、“光辉”等名目后,兽性才会在文明社会中得到变本加厉的张扬和异化。从社会存在的权力、荣誉等对人的异化,到纪律等机制对人的驯服,再到社会存在本身对人类体内兽性因子(动物性)的催化和激发,使人成为制造惨剧的刽子手。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然而人的社会性往往会约束人的自然性,社会存在一方面压抑人类自然属性中的某些元素,另一方面,它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发展甚至异化人类的另一些属性。 人类兽性带来的酷虐手段与丛林中野兽的猛烈撕咬比起来,无处不闪耀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只有人类能够把身体内的动物性(兽性因子)发挥到如此“高度”,使人类成为最残忍行为的发明者和施行者。对此,莫言曾在作品中写道:“人,其实都跟畜生差不多,最坏的畜生也坏不过人。”(31)“一个人要是丧失了人性,哪怕是个孩童,也会干出比野兽凶残百倍的坏事。”(32)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莫言明确地说过: ……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33) 文明首先是为获取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工具的进步;社会进步使更多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但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34)“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35)弗洛伊德对此阐释得很清楚,他用本能理论、快乐原则,为我们说明了文明对人类动物性的压制和异化过程:“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36)人类的生物本能是动物性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论述了文明与本能之间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动物性作为原始、野蛮、落后的表征被文明压制,并且强调“压制才是进步的前提”,然而,长久的压制会带来稳定和谐的持续局面吗?文明意味着物质的丰富、精良的医疗卫生条件、庄严的宗教信仰、动人的艺术氛围和优雅的音乐旋律,同时也意味着奴隶制、剥削、战争和死亡集中营。文明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压制人类体内属于前社会的动物性,从这一视角考察文明,它与动物性、野蛮、原始是相对立的。然而,当我们反观文明时会发现,把文明和野蛮想象成对立面是错误的。“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7)当由于文明的压制而造成一种关于所谓野蛮的隐蔽历史时,另一种更为野蛮的行为在公开的创造着,尼采认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类最残酷的冲动还是确定不移地被减弱的,但是对自然冲动的弃绝并未导致一种伟大的改造。反而‘导致了一种变态’”。(38)尼采所说的“变态”,与弗洛姆所谈的“异化”有着异质同构性,它们皆由社会存在所致:当二者与动物性结合在一起时,都会产生令人无法想象的恶果。在弗洛姆的字典里,异化最初来源于人们对一块“木头”的崇拜:“对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像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像,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己。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39)无疑,皇权与国家政策等就是赵甲、姑姑们心中那块被崇拜的木头,在这里,社会存在的异化功能和文明社会伴随而生产出的所谓纪律、荣誉等规训机制同时发挥着作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一个有思想的人变成了杀人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自然会逐渐弱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由社会的本来主体沦为社会存在的附属品,当其所具有的思想、情感等独有因素逐渐萎缩,便丧失掉真正人的意义。莫言正是用一系列的人类兽行,诠释这一“变态”或“异化”的过程和结果,目的是指向社会存在本身。 有关于战争对人性的摧毁,有作家揭示道:“丧失了人的恻隐之心,变得冷酷而残忍。”(40)莫言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我想在当年的中国战场上,东南亚的战场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实际上是一些被异化的、在战争的大环境下变成了野兽的这样一批人,如果这批人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环境,那么他们很可能要忏悔他们过去的罪行。”(41)由此可见莫言对环境的强调,特殊的、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存在)会使人性中被压抑的部分极度膨胀,从而导致惨剧的上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已经解释了人类兽行的成因。作为一个写作者,莫言要做的,是对人性各侧面的深度挖掘,他会在作品中营造出极端的生存环境,刺激人性借以探求面临底线时的真实反应,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莫言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人性试验场。 收稿日期:2015-01-10 注释: ①敬文东:《事情总会起变化》,台北:秀威书局,2009年,第108页。 ②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99-100页。 ③④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第196页。 ⑤⑥⑦莫言:《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第214页,第215页。 ⑧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 ⑨莫言:《檀香刑》,第3页。 ⑩谢有顺:《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11)(1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55页,第56页。 (13)埃里希·弗洛姆:《生命之爱》,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14)(16)(17)(18)(19)莫言:《檀香刑》,第190页,第70页,第70页,第40页,第297-298页。 (15)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20)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21)(22)(23)莫言:《蛙》,第55-56页,第55页,第87页。 (24)转引自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第29页。 (25)(26)(27)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第91页,第91页,第92页。 (28)(29)(30)埃里希·弗洛姆:《生命之爱》,罗原译,第59-60页,第60页,第59页。 (31)莫言:《红蝗》,《食草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2)莫言:《生蹼的祖先们》,《食草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33)莫言:《恐惧与希望——2005年8月在意大利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34)(35)(36)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第1页,第2页,第7页。 (37)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第13页。 (38)詹姆士·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 (39)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罗原译,第111页-112页。 (40)赵文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41)莫言:《与王尧长谈》(2002年12月),《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