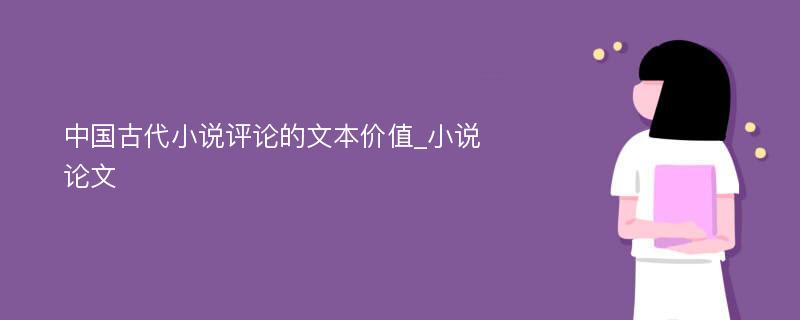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本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本价值的生成原因
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是指评点者对小说文本所作出的增饰、改订等艺术再创造活动,从而使评点本获得了自身独立的版本价值和文学价值。这一现象如果衡之以当今的文学批评观念乃不可思议,因为这已越出了文学批评的职能范围;而在中国古代也不多见,传统诗文在其流传过程中随着历史年代的变迁,其版本歧异容或有之,但同一作品经批评者的手定更易广为流传却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而在古代通俗小说领域,这种现象却屡见不鲜,且几乎与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相始终。
小说评点在小说自身的发展中能获得文本价值,其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因素约有三端: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是一种地位卑下的文体,虽然数百年间小说创作极为繁盛且影响深广,但这一文体始终处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之边缘,而未真正被古代正统文人所接纳。这一现象对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有二:一是流传的民间性,二是创作队伍的下层性,而这些又使得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得到社会的真正重视,也未能在创作者的观念中真正作为正宗的事业加以从事,就是在通俗小说进入文人独创时期的乾隆年间,人们犹然对吴敬梓发出这样的叹惋:“《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①a]通俗小说流传的民间性使其从创作到刊行大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抄本流传阶段,这样辗转流传,小说在文本上的变异十分明显,而最终得以刊行的小说,由于基本以“坊刻”为主,其商业营利性又使小说的刊行颇为粗糙。这在流传上的特色使通俗小说评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对小说重新修订和增饰的行为。而创作者地位的下层性又使这种行为趋于公开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说有大量的创作者湮没无闻,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书坊能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对象。因此小说评点能获取文本价值,其首要的因素是由于小说地位之卑下,可以说,这是小说在其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
小说评点之能获得文本价值与古代通俗小说独特的编创方式也密切相关。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在其发展进程中体现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个人独创型”的演化轨迹,而所谓“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不断累积、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这种小说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独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说发展史上,这种编创方式曾是有明一代最为主要的创作方式,进入清代以后,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虽然逐步向“个人独创型”发展,但前者仍未断绝。“世代累积型”编创方式的形成有种种因素,但最为根本的还在于通俗小说的民间性,明清通俗小说承宋元民间话本而来,因此宋元话本、尤其是讲史在民间的大量流传便成了通俗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或由雪球般滚动,经历了由单一到复杂,由简约到丰满的过程,最终成一巨帙,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或如百川归海,逐步聚集,最后融为长篇宏制,如《水浒传》等。这种在民间流传基础上逐步成书的编创方式为小说评点获取文本价值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前提,这我们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通俗小说文本的流动性”。正因是在“流动”中逐步成书的,故其成书也并非最终定型,仍为后代的增订留有较多余地,同时,正因其本身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故评点者对其作出新的增订就较少观念上的障碍。虽然评点者常常以得“古本”而为其增饰作遮眼,但这种狡狯其实是尽人皆知的,评点者对此也并不太在意。这一基本前提就为评点者在对小说进行品评时融入个人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便利,而小说评点本的文本价值便由此生成。
小说评点之获得文本价值与评点者的批评旨趣也有着深切的关系。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本无对文本作出增饰的功能,但因上述两层因素,故小说评点在批评旨趣上出现了一种与古代其他文学批评形态截然不同的趋向,即:评点者常常将自己的评点视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金圣叹曾宣称:“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①b]他批《水浒》虽无类似宣言,然旨趣却是同一的。他腰斩、改编《水浒》并使之自成面目,正强烈地体现了这种批评精神。张竹坡亦谓:“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②b]哈斯宝更明确倡言:“曹雪芹先生是奇人,他为何那样必为曹雪芹,我为何步他后尘费尽心血?……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因此“摘译者是我,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另一部《红楼梦》。”[③b]以上言论在小说评点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整体上小说评点并非全然体现这一特色,但在那些成功的小说评点本中,这却是共同的旨趣和精神。小说评点正因有了这一种批评精神,故评点便逐渐成了批评者的立身事业,他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乃至生命体验都融入批评对象之中,而当作品之内涵不合其情感和审美需要时,更不惜改变作品。于是,作品文本也在这种更改中体现出了评点者的主体特性,从而确立了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
二、文本价值的内在演化与表现形态
小说评点之文本价值就其历史演化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明万历年间、明末清初和清乾隆以降。在表现形态上则构成了三个层面:作品情感主旨的强化或修正;作品艺术形式的增饰和加工;作品体制和文字的修订。
就现存资料而言,通俗小说的评点萌生于明万历年间,在此时期留存的二十余种评本中,体现文本价值的主要有如下数种:《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卷楼刊本)、《水浒志传评林》(双峰堂刊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刊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刊本)、《绣榻野史》(醉眠阁刊本)。上述五种评本中,对文本的评点修订大多出自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之手,虽然后三种评本均署“李卓吾批评”,但真正出自李氏之手的实属少数[①c],《绣榻野史》之评点则显系伪托李卓吾[②c]。因此显而易见,这五种评本大多是在书坊主控制下从事的,其文本价值则主要体现为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如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周曰校“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③c],如《水浒志传评林》的“改正增评”[④c],如袁无涯本《水浒传》的增订诗词,订文酌字等都表现了这一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小说评点也开始出现了对小说内容的增删,余象斗《水浒辨》云:“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在《绣榻野史》评本中,评点者则将“品评”、“批抹”、“断略”融为一体,其中“批抹”即对文本的某些删改,“断略”则是评点者缀于篇末的劝惩性文字。[⑤c]尤可注意的是容与堂本《水浒传》,此书之评者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也作了较多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而是多设拟删节符号,或上下钩乙,或句旁直勒,并刻上“可删”字样,这一改定对后世的《水浒》刊本也有较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明崇祯、清顺治、康熙三朝)是小说评点实现文本价值的重要时期,是小说评点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成就最为卓越的阶段。其中体现文本价值最为重要的作品是一组“四大奇书”的评点本,主要有:《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明崇祯十四年金圣叹评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明崇祯刊本)、《西游证道书》(清初黄周星定本)、《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年间毛氏评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本)。以上五种评本,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小说评点已从书坊主人转向文人之手,故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在评点中有了明显的增强,表现在评点形态上,简约的赏评和单纯的修订已被对作品的整体加工和全面评析所取代。此时期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评点者对小说的表现内容作了具有强烈主体特性的修正,这突出地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之中。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由此,他腰斩《水浒》,并妄撰卢俊义“惊恶梦”一节,以表现其对现实的忧虑;突出乱自上作,指斥奸臣贪虐,祸国害民的罪行;又“独恶宋江”,突出其虚伪不实,并以李逵等真率之人为“天人”。这三者明显地构成了金氏批改《水浒》的主体特性,并在《水浒》众多刊本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毛氏评改《三国演义》最为突出的特性乃是进一步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其《读法》开首即言:“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足之”。本着这种观念,毛氏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用词(如原作中称曹操为“曹公”处即大多改去),毛氏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神加以改造。[⑥c]从而使毛本《三国》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中最重正统、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其二,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作了整体的加工和清理,使通俗小说(主要指长篇章回小说)在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宋元话本,因此在从话本到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明末清初的评点家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评点对象,故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小说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特性的《金瓶梅》由“说唱本”演为“说教本”。再如《西游证道书》对明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作品从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评改的重要部分,这一工作明中叶就已开始,至此时期渐趋完善。如毛氏批本《三国演义》“悉体作者之意而连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①d]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遂成章回小说之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遂达峰巅状态。
第三,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在艺术上作了较多的增饰和加工,使其益愈精致。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补正小说情节之缺漏,通俗小说由于其民间性的特色,其情节疏漏可谓比比皆是,评点者基于对作品的仔细批读,将其一一指出,并逐一补正;二是对小说情节框架的整体调整,如金圣叹腰斩《水浒》而保留其精华部分,虽有思想观念的制约,但也包含艺术上的考虑;再如崇祯本《金瓶梅》将原本首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让主人公提早出场,从而使情节相对比较紧凑,又如《西游证道书》补写唐僧出身一节而成《西游记》足本等,都对小说文本在整体上有所调整和增饰;三是对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的加工,此种例证也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总之,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对明代的通俗小说,尤其是“四大奇书”作了一定程度的总结。这种总结既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也表现在小说文本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此时期的小说评点是明代通俗小说的真正终结。同时,也使“世代累积型”这一明代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主体形式在整体上趋于收束。
乾隆以降,由于通俗小说“个人独创型”编创方式的日益成熟,也因为通俗小说中最富民间色彩的“历史演义”、“神魔小说”、“英雄传奇”等的历史地位逐渐被富于个体创作特色的言情小说所取代,故小说评点者对文本的增饰也相应减弱,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又回复到了以文字和形式修订为其主流。如乾隆以来,《西游记》和《红楼梦》曾一度成为评点之热门,但在众多的《西游》评本中,唯有《西游真诠》(乾隆刊本,陈士斌评点)一书,评点者对小说原文稍加压缩,而压缩之内容也仅是书中之韵语和赞语。在《红楼梦》的诸多评本中,亦仅省《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年间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一种对小说文本有较多指谬,但评点者不对文本作直接修订,而仅于书前单列“摘误”一段特加指出。此时期小说评本有一定文本价值的还有两种,一是刊于乾隆年间署“秣陵蔡元放批评”的《东周列国志》,此书乃蔡氏据冯梦龙《新列国志》稍加润色增删,并修订其中错讹而成。二是刊于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而所谓“增订”者也大多属形式层次,如“改订回目”、“补正疏漏”、“整理幽榜”、“删润字句”等。因此从整体上看,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经由明末清初之高峰后,乾隆以来已渐趋尾声。
从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而言,此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倒值得注意,这便是小说评点对“续书”的影响,如道光年间的《三续金瓶梅》,据作者讷音居士所云,其创作乃受张竹坡评本之影响,该书又名《小补奇酸志》,“奇酸志”一语即出自张竹坡评本中《苦孝说》一文。又如道光年间俞万春《荡寇志》,其创作也明显受金批《水浒》之影响。小说评点与“续书”之关系,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又一个值得考察的现象,也是小说评点文本价值的又一表现形态,限于篇幅,容另文申述。
三、文本价值的理论评判
小说评点体现文本价值,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确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作为一种批评形态,小说评点“介入”小说文本实已超出了它的职能范围,故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但评价一种文化现象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如果我们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那我们对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就有另一番评判了。
宋元以来,中国雅俗文学明显趋于分流,从逻辑上讲,所谓雅俗文学之分流是指俗文学逐渐脱离正统士大夫文人之视野而向着民间性演进。宋元时期,这种演进轨迹是清晰可见的。宋元话本讲史、宋金杂剧南戏、诸官调等,其民间色彩都十分浓烈,且在元代结出了一朵奇葩——元代杂剧。因而从分流的态势来看待俗文学的这一段历史及其所获得的突出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俗文学的成就是文学走向民间性和通俗化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民间性和通俗化诚然是俗文学在宋元以来获得其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雅俗文学之分流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俗文学失却正统文人士大夫的精心培育,而这无疑也是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损失。因此,如何在保持其民间性和通俗化的前提下求得其思想价值和审美品位的提升,是俗文学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宋元以后,俗文学的发展在整体上便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尤其是作为俗文学主干的戏曲和通俗小说,但两者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和平衡。对此,我们不妨对两者的文人化进程作一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来确立小说评点文本价值的历史地位。
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自元代杂剧以后并未完全循着民间性和通俗化一路发展,而是比较明显地表现了一条趋于文人化的发展轨迹。这里所谓的“文人化”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戏曲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强化,也即作家创作戏曲有其明确的文人本位性,突出表现其现实情思、政治忧患和文人的使命感;二是在艺术形式上追求稳定、完美的艺术格局和相对雅化的语言风格。这一进程就其源头而言乃发端于元代:马致远剧作对于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高明剧作中重视伦常、维持风化的教化意识。这两种创作意识为明代传奇作家所普遍接受,邱浚《五伦全备记》、邵灿《香囊记》等将《琵琶记》之风化主题引向极端,而在《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作品中,则是对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作了很好的延续。由此以后,传奇文学在表现内容和形式格局等方面都顺此而发展,至万历时期,文人化倾向更为浓郁,汤显祖“临川四梦”为其代表,一直到清初“南洪北孔”的出现,终于将这一文人化进程推向了高潮。当然,明清传奇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以上简约的历史描述却是传奇文学发展中一条颇为清晰的主线,这条主线构成了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一代之文学——文人传奇时代。
与戏曲相比较,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程度在整体上要比戏曲来得薄弱,其文人化进程也比戏曲来得缓慢。一方面,作为明清通俗小说之源头的宋元话本讲史,其本身就没有如元杂剧那样,在民间性和通俗化之中包涵有文人化的素质,基本上是一种出自民间并在民间流传的通俗艺术,故而缘此而来的明清通俗小说就带有其先天的特性,文人化程度的淡薄乃并不奇怪。同时,明清通俗小说与戏曲相比较,其文艺商品化的特性更为强烈,这种特性也妨碍了通俗小说向文人化方向发展。因此上文所说的通俗小说“流传的民间性”和“创作队伍的下层性”无疑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当然,综观通俗小说的历史发展,其文人化进程也还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它的两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康乾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以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完满的收束。但在这两端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却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缓慢的进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小说评点所体现的文本价值便有了突出的地位:
首先,在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中,小说评点者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通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正统文人精心培育之下的一种补偿,是通俗小说在清康乾时期迎来小说艺术黄金时代的一次重要准备。
在中国俗文学的发展中,明万历年间至清初,是通俗小说和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小说评点体现文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明末清初,大量出色的小说评点家与小说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说艺术审美特性的转型。他们改编、批评、刊刻通俗小说一时竟成风气,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种阶段性且集合性的小说评改使通俗小说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通俗小说至此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其次,在通俗小说的发展中,明代“四大奇书”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组具有典范性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四大奇书”的文化品位也是在不断累积中逐步形成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评点所起的作用毋庸低估,从万历时期“李卓吾评本”对《水浒传》“忠义”内涵的倡扬,到金圣叹评《水浒传》为“才子书”,再到明末清初评点家所标榜的“奇书”系列,可以说,“四大奇书”的文化品位在不断提升。如果说,在宋之前,唐代传奇是古代小说文人化的一个高峰,其标志在于唐代文人之“诗心”与故事题材结合中所表现出的灵心慧性,那么,在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小说评点家以其才子之“文心”对作品的增饰是通俗小说文人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四大奇书”便是这一环节中最为成功的例证。清人黄叔瑛对此评价道:“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作者”[①e],虽有所夸大,但也并非虚言。清初以来,“四大奇书”以评点家之“点定本”流行便是一个明证。
历来治小说史者,常常把小说创作与小说评点分而论之,叙述小说史一般不涉及评点对小说文本发展的影响(有时更从反面批判),而研究小说评点又每每过多局限于小说评点之理论批评内涵。于是,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也就成了一个两不关涉的“空白地带”,这实在是一个研究的“误区”。我以为,如果我们在小说史的叙述中适当注目评点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对其有一个恰当的评价,那我们所叙述的小说史也许会更贴近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原生状态”。
注释:
①a 程晋芳《怀人诗》之十六,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春帆集》。
①b 金圣汉《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
②b 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竹坡闲话》。
③b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评·总录》。
①c ②c 参见拙作《小说评点的萌兴》,《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6期。
③c 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识语”,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
④c 余象斗《水浒辨》,《水浒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本。
⑤c 见“憨憨子”《绣榻野史序》。
⑥c 参阅秦亢宗《谈毛宗岗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①d 毛崇岗《三国志演义·凡例》。
①e 〔清〕黄叔瑛《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雍正十二年(1734)郁郁堂刊本《官板大字全像批评三国志》卷首。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古代文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金瓶梅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绣榻野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