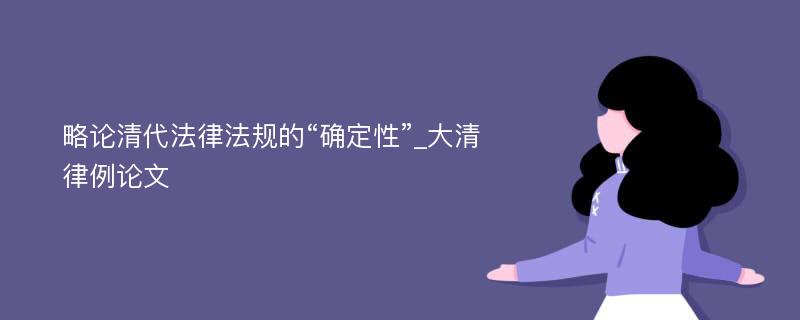
略论《大清律例》的“确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例论文,大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2)04-0094-14
提及《大清律例》,学术界最常用的一词即“清承明制”。就体例上而言,前者完全因袭后者。①就内容上而言,前者也有许多条文原原本本照搬自后者。明清律的继承关系至为明显,此点学界论著已多②,毋庸赘言。但是如果过分放大其继承性,则容易形成偏激的论断,比如钱穆先生即指出:“尤其是清代,可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③说“部族私心”并没有错,《大清律例》中,确有对满人犯罪的诸多优待的法律规范。但若据此判定“全无制度”,则亦非平情之论。对此,瞿同祖先生的评价则更为公允:“清律大体上继承明律,但有清一代的法律因陆续纂修条例而有相当多的变化。”④变化既然“相当多”,自然涉及方面较广,非本文一文可网罗殆尽。本文拟从《大清律例》的“确定化倾向”这一视角探讨这一“变化”,并期以此探析清立法者的立法宗旨与内在的“私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的“确定化”,不包括在司法实践领域当中的情形。法律规则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的规定应明确无误,尽可能地避免模糊性,以便于当事人准确地把握立法意图,从而准确地根据法律规划自己的行为。所以,本文的确定仅是指法律条款本身的文义确定性,故拟对《大清律例》的文本条款作出规范性分析,力图从文义上对《大清律例》作确定化分析。
清律条款的确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于有清一代的始终。清代立法者大致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使法律规范确定化。第一,在明律的基础上进行律文的增删;第二,持续地纂修律例,尤其是通过修例使得律义更为确定化;第三,在法律条款的要素上进行完善。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其实是一体进行的,我们只是为论述的清晰,而强分析之。
一、通过修改明律律文而使条款律义更为确定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明清律中相同律文中细节的不同看条款确定化的倾向。《大清律例》的四百多个律名大多沿袭《大明律》,在同一律名同一律文下,清律主要通过修改律文中的小注达到规范律义的目的。这种情形又可以具体分为增注、删注和完全改注三种情形。我们仅以明清律“名例”一篇进行分析。⑤
首先我们看增注的情况。瞿同祖先生在考察清律的继承和变化时说道:“清律小注多于明律,但往往只是加几个字,使语意更加明确,并没有因此而变动律文的内容。”⑥在这三类注释的方法中,又以增注的情况为最多。增注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律文中某个名词后加注,使文气贯通,指代明确,比如“流囚家属”条,明清两律律文为:“凡犯流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行者,听。迁徙安置人家口,亦准此。若流徙人身死,家口虽经附籍,愿还乡者放还。其谋反、叛、逆及造畜蛊毒,若采生折割人,杀一家三人,会赦犹流者,家口不在听还之律。”此条明律无注。清律在“迁徙安置人”之后注入“随行”二字,就将迁徙安置人什么样的家口说明了,避免语义不清,它又在“家口虽经附籍”中的“附”后面加入“入配所之”四个字,就将附籍的地方说清了,避免在运用此法条时产生“附原籍”还是“附配所籍”的争辩。另一种情况是在律文中某个名词或某一句、某一段后加,起到两个作用,一是补充说明律文意思的作用,以弥补律文言简之不足;二是解释立法意图的作用,以弥补律义不显之不足。前者的典型例子在“犯罪存留养亲”条,律文为:“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此条明律依旧无注,清律在祖父母之后加注“高曾同”,意为如果出现犯罪者有高祖父母、曾祖父母需要待养的,也符合律意要求。清律又在“父母老”之后加注“七十以上”,从而给“老”以一个客观标准,避免适用法律时主观擅断。又在“疾”后加注“笃废”,意为要达到“笃废”的程度才符合存养的条件。本条尚有其他类似的注,在此不赘述。这个注或者为扩大解释,或者为缩小解释,或者为字面解释,其目的是使律条更为清晰、明白,间接也促使第二个“解释立法意图”作用的发挥。后者的典型例子在“亲属相为容隐”条,清律在叙述完“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者,皆勿论”外,增加一注“家长不得为奴婢、雇工人隐者,义当治其罪也”。本来容隐就是儒家经义入律的典范。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⑦朱熹曾经注释道:“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⑧相隐源于父子之亲,后来作引申解释,将之扩大到夫妻、主仆,但是夫可以为妻隐,妻也可以为夫隐,那么主能否为仆隐呢?明律没有规定,清律为了使用法者别尊卑之义,防止照父子、夫妻关系类推,特别增加了这个注释,仆为主隐是为“义”,而主不为仆隐才是“义”,这就将立法意图讲明了。
其次我们看减注的情况。注也不是越多越好,当明律小注语焉不详或者没有必要时,清律就将这些小注删掉了。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明律的基础上直接删减小注,如“八议”条对“议能”的解释,明律解释为“谓有大才业,能整军旅、治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而清律则把“人伦之师范者”删掉了。因为“人伦之师范”不宜界定,不够客观,且与“议贤”之条似有重复,故清律将之删除,剩下的“能”则更加客观。又如“应议者犯罪条”,明律在律文后有这样一段注:“议者,谓原其本情议其犯罪,于奏本之内开写,或亲,或故,或功,或贤,或能,或勤,或贵,或宾,应议之人所犯之事,实封奏闻取旨。若奉旨推行者,才方推问。或取责明白招状,开具应得之罪,先奏请令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议,议定奏闻。至死者,惟云准犯依律合死,不敢正言绞、斩,取自上裁。”清律同一律条中则删去了这段小注,一是“八议”在前律条中已有明确解释,毋庸再在此小注中赘述;二是明清官制发生了变化,再用此注已经不合时宜;三是本注配合的律文已经很明白了,毋庸再作进一步规定。所以,清律一删,简明扼要之意顿显。第二种减注的情况是因明律小注语意繁复,在大体保持原注的基础上清律对之加以概括,可使律意更清楚易懂。如“犯罪时未老疾条”,明律在“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句后注为“谓如六十九以下,徒役三年,徒限未满年人七十,或人徒时无病,徒役年限内成废疾,并听准老疾收赎。以徒一年三百六十日为率,验该杖徒若干,应赎银若干,俱照例折役收赎”。可见清律直接将明律中繁琐的计算方法简化为“验该杖徒若干,应赎银若干,俱照例折役收赎”这三句话,同样是考虑到“名例”总则编的特色,再者,该如何赎刑,在律的前面有图表“徒限内老疾收赎图”如何决断,直接查表就可得知,无须再在名例篇中赘述了。其实明律后也附有这样的图,清律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弊端,所以作出如此删减。减注也可以看出清律法典编撰的水平进一步提高,逐渐趋向科学化、客观化、确定化。符合所谓的“复加损益,酌理准情”⑨的修律指导方针。
再次我们看完全改注的情况。所谓完全改注,就是在相同的律文下,从与明律不同的角度注释。这种情况极少,大抵在律文相同的情况下,清律发展明律用注多为上述两种。完全改注,以“五刑”最为典型。明律五刑的注释从赎刑着手,在介绍完每一种刑罚、量刑数量后,就举出该赎钱几何。比如它将流刑(加杖流)分三等:二千里杖一百,二千五百里杖一百,三千里杖一百。其小注中注明的赎钱数量分别为铜钱三十贯,铜钱三十三贯,铜钱三十六贯。而清律的小注中则完全没有任何赎刑的内容,有的只是先分析刑罚的意思以及采用这种刑罚的原因,然后再换算成行刑(笞杖刑)用板子的板数。比如在“笞刑五”律文后面,加入注释“笞者,击也。又训为耻。用小竹板”。然后又在“一十”这个量刑幅度后面加小注“折四板”。比照《唐律疏议》中“五刑”疏的解释:“笞者,击也,又训为笞。言人有小愆,法须惩戒,故加捶挞以耻之。”可知清律在注释的时候似乎较明律保留了唐律更多的成分。清代律学大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序中称:“(明律)其中仍照《唐律》者固多。而增减者亦复不少,且有删改失当者。”⑩那么此条可否作为删改失当的一条?因赎钱数目如上所述,明律后已附有赎刑图,那么又何必在此画蛇添足呢?清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删掉了赎钱数目,而庶几恢复了唐代的注疏。“可见,《大清律例》是沿袭《大明律》而远祧《唐律》的,而其终极目的,是‘合于古帝王立法设刑之’,正所谓‘准古酌今’”(11),改注也是法律进化的重要一途。
以上问题,均不属于瞿同祖先生所谓的“大体上”之列,但是因为律文小注同律文一样,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关系案件裁判中的实际援引,所以,清律通过修改小注,使得明律可能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确定化,从中亦可看出清代立法者的苦心孤诣。
二、通过纂修律例尤其是持续地修例使得律义更为确定
以上我们通过文本的静态分析看到了清代立法者通过修改律文小注的方式,从而使得《大清律例》条款律义更为确定。当然,即使在清代,这一律文文义的确定化也经过了前后百年的时间。清朝入关以后,由于“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为“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12),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员在朝廷上商议,对哈纳等校订,并以《大明律》作参考,多番修订之后才得以成书付梓刊布,并命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即为顺治三年(1646年)律。律文之后附相关条例430余条。康熙九年(1670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1670年)校订刻本传世。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由于发现后立之新法与原有之旧法有所冲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又再作修订,但直到康熙驾崩时,修订还未完成。继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员继续完成修订,“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13)。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开始,到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完成,并于九月初九刊行。此为雍正五年(1727年)刻本。乾隆初,又对原有律例逐条考正,进行总修,删除雍正律后的总注,于乾隆五年(1740年)编成《大清律例》,此时附例1049条。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订,这些订正增删改并,合计有1456条之多。此后对于例文又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最后一次大修时,此时附例更是已达1892条之多。
从修订过程上看,总的趋势是律例益繁,自然也明显地体现出了其确定化的倾向。具体的修纂和沿革过程,清代律学家所论至细(14),本文不拟详申。此处仅择《大清律例》“名例”篇中“徒流人又犯罪”这一条款的前后变化讨论确定化的问题。这一条款源自唐律“犯罪已发”条,明律改为现名。应该说并非清律的创造,但是两百年间,清立法者对此律不断加以改造,愈发精细。所谓“于细微处见精神”,其变化恰恰可以反映清立法者为法律确定化的努力。
顺治律所模仿的万历年间的此条律文原为:
“凡犯罪已发,又犯罪者,从重科断。已徒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后犯之罪。其重犯流者,依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若犯徒者,依所犯杖数,该徒年限决讫应役,亦总不得过四年。谓先犯徒三年,已役一年,又犯徒三年者,止加杖一百,徒一年之类,则总徒不得过四年。三流虽并杖一百,役四年,若先犯徒,年未满者,亦止总役四年。其杖罪以下,亦各依数决之。其应加杖者,亦如之。谓工乐户及妇人犯者,亦依律科之。”
原律文后附以下四条条例:
条例1:“先杂犯死罪运炭纳米等项未完,及做工等项未满,又杂犯犯死罪者,决杖一百。除杖过数目准钞六贯,再收赎钞三十六贯;又犯徒流笞杖罪者,决其应得杖数,五徒三流各依律收赎钞贯,仍照先拟发落。若三次俱犯杂犯死罪者,奏请定夺。”
条例2:“先犯徒流罪,运炭做工等项,未曾完满,又犯杂犯死罪,除去先犯罪名,止拟后犯死罪运炭做工等项。若又犯徒流罪者,依已徒而又犯徒,将所犯杖数,或的决,或纳钞,仍总徒不得过四年。又犯笞杖者,将后犯笞杖,或的决,或纳钞,仍照先拟发落。”
条例3:“先犯笞杖罪,运炭做工等项未曾完满,又犯杂犯死罪,除去先犯罪名,止拟后犯死罪运炭做工等项,又犯徒流罪,将先犯罪名,或纳钞,或的决,止拟后犯徒流。又犯笞杖罪,若等者,从后发落。轻重不等者,从重发落。余罪俱照前纳钞的决。”
条例4:“在京在外问拟一应徒罪,俱免杖。其已徒而又犯徒,该决迄所犯杖数。总徒四年者,在京遇热审,在外遇五年审录,俱减一年。若诬告平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者,比照已徒而犯徒,总徒四年者,虽遇例不减。”(15)
修改后的清顺治律,此条如下:
“凡犯罪已发未论决,又犯罪者,从重科断。已徒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后犯之罪。不在从重科断之限。其重犯流者,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若徒而又犯犯徒者,依后所犯杖数,决迄,并该徒年限议拟明白,照数决讫,仍令应役,通前亦总不得过四年。谓先犯徒三年,已役一年,又犯徒三年者,止加杖一百,徒一年之类,则总徒不得过四年。三流虽并杖一百,俱役四年,若先犯徒,年未满者,亦止总役四年。其徒流人又犯杖罪以下者,亦各依后犯笞杖数决之,仍旧应役。其应加杖者,亦如之。谓工乐户及妇人犯者,亦依律科之。重犯徒流,或拘役,或收赎,亦总丕得过四年,重犯笞杖,亦照数决之。”(16)
以上划线部分即为修改之处,是以增加小注的方式修改的。并没有改变明律旧意,但经此一修改,律义更彰。将不同种类的徒流人又犯罪的情况条分缕析,将所应加的刑罚明白昭示。更犯从重的原则在此得到确切的体现,且总数亦加以一定的限制,可防止司法官员任意出入。譬如增加“通前”一语,就让断狱官明白,此四年包括之前已经执行的徒役期,而非“又犯”后所加的徒役期限。否则,我们理解成如果该犯又犯,则再处其徒役,最高不得过四年,那么加上原来已经执行的天数,总数可超过四年。故加这短短的两个字,其实就使得律义得到澄清。这里的确可看出清初立法者在文字上的缜密之处。
然而文字上的缜密取代不了现实中的新旧杂陈,从顺治元年(1644年)一直到康熙初年(1662年),天下并不太平,政治制度也不稳定,很多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旋设旋废。甚至全国许多制度都无法整齐画一。所以,时人有嘲笑清律中出现了原本只有明朝才有的专门术语,故讥顺治律纯为“明律之翻版”,以至于出现重大纰漏而不自知。(17)其实若能结合清初的时代状况,会发现这种情形其实很正常。譬如,顺治律中亦有“巡按”字样,众所周知,巡按乃明代官制。其实清初亦有,只不过多有反复。巡按制度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始设,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废止,其间经过四次停复。(18)所以,在这样动荡的政治气候下,指望清律内容完全确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修律诸臣就草率从事。事实上,对于律文的精绎,从皇太极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顺治律序文中“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当是事实。
再看顺治律此条所附之例,同明律例文数一样,也是4条。但条例1将“赎钞三十六贯”改为“赎银四钱五分”;“收赎钞贯”改为“收赎银数”。条例2仅将“纳赎”改为“纳银”。条例3也仅将“纳钞”改为“纳银”。条例4则未加任何更改。说明顺治初这一条例的应用还延续前朝的惯例,只是因为明代的钞贯制度已经被废除,所以改成用银。这几条改动无关乎确定性与否,只是为了使律例适应新朝的情势。
康熙年间对律文未作改动。至雍正即位,此时大清已然一统,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各项制度相对成熟,于是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律。道光年间广东人潘德畲辑录的《大清律例按语》,应当是雍正年间修律大臣集体拟定的修律意见书。《大清律例按语》对于此条修改意见为:“原拟‘依数决之’下应注明‘充军又犯罪及重犯军罪,俱与流罪同科’,又‘工乐户犯罪留住’前条已拟删,应删去律文内‘依留住法’句。其天文生亦应加杖,末节注内应增‘天文生’字。”(19)
随后,《大清律例按语》还给出了对此条律文的释义。经过修改,在雍正五年(1727年)大清律中,“徒流人又犯罪”条律文修改为:
“凡犯罪已发未论决又犯罪者,从重科断。已徒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后犯之罪。不在从重科断之限。其重犯流者,三流并决杖一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若徒而又犯徒者,依后所犯杖数,该徒年限议拟明白,照数决讫,仍令应役,通前亦总不得过四年。谓先犯徒三年,已役一年,又犯徒三年者,止加杖一百,徒一年之类,则总徒不得过四年。三流虽并杖一百,俱役四年,若先犯徒,年未满者,亦止总役四年。其徒流人又犯罪,杖罪以下者,亦各依后犯笞杖数决之。充军又犯罪及重犯军罪俱与流罪同科,仍旧应役。其应加杖者,亦如之。谓天文生、工乐户及妇人犯者,重犯徒流,或拘役,或收赎,亦总不得过四年,重犯笞杖,亦照数决之。”
紧接着律文有一个总注:
“此是犯罪已发已决而又犯者之通例也,凡罪发未决而又犯者宜从重科断,若先犯重而后犯轻则科先犯之罪,后犯重而先犯轻则科后犯之罪。若二犯相等,则从一科断。至于流徒囚已至配所而又犯,或徒犯流,或流犯徒,则依律再科后犯之罪,其重犯流者,如再加流,则地过远,故决杖一百,止拘四年。重犯徒者,如再加徒,年数过久,故照数决杖,总徒亦止四年。徒犯又犯笞杖,则罪轻不妨全科,故依数决之。若充军人于配所又犯别罪,及重犯军罪,俱照流罪科断。其应加杖者,指天文生、工乐户及妇人重犯笞杖亦照数的决。”(20)
可以看出,此律文的修改及后面附加的总注,是完全按照《大清律例按语》的意见处理的。
我们对照上面的总注,再看雍正五年(1727年)律这条律文,其确定化程度的加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该总注将律文意思分析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总述犯罪已发但未处罚的情况,原则上是从重科断。如果前罪重于后罪,按前罪处罚,若前罪轻于后罪,按后罪处罚。如果前后两罪轻重相等。则从一科断。
从第二个层次开始,考虑犯罪已发已决的情况,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作出不同的处理。首先是流徒人至配所再犯流徒案件的。这里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所犯不同性质罪行的,如流犯至配所再犯徒刑,则科以后犯的徒刑;而如徒犯至配所再犯流罪的,则科以后犯的流刑。不需从重科断,实际上是按新犯罪对待。第二种情形是所犯相同性质罪行的,如流犯至配所再犯流刑的,则不能再处流刑,理由是流放太远,于是决杖一百,最多配役四年;而如徒犯至配所再犯徒罪的,则亦不能再处徒刑,理由是年数过久,于是按后犯的徒刑配以杖刑,徒刑年数不超过四年。
第三个层次则指出徒流人到配所又犯轻于徒罪的罪行,即笞杖刑,则科以后犯的刑罚,不进行合并折算。
最后一个层次则指出对于一些特殊犯罪主体,比如充军人、天文生、工乐户及妇人犯徒流罪后又犯罪的情形,可作特殊处理。因为这些人或者属于拥有特殊技艺之人,或者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处罚上应当变通处理。
可见,较之于此前的律文,雍正律解释得更为明确。且律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对于数罪间如何处理的问题,既给出了一般的处理原则,又分具体情形加以限定。笔者以为,如果按照雍正律该条律文,去适用于具体的徒流人犯罪的案件中时,法官几乎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乾隆五年(1740年)修律时,这一条变动较少。以“重犯军罪”已包在“又犯罪”之内,此注内“充军又犯”等二十字,俱应删去,改注“充军又犯罪,亦准此”字样。又因为“工乐户”有犯五徒,各依杖罪的决,并不同天文生加杖,且惟犯徒罪乃照依年限留役,流罪原不在内。至于徒罪不得过四年及笞杖的决之处,已包在依律科断之中,应将“工乐户”三字及“重犯徒流”等句删除,改为“天文生及妇人犯者,亦依律科之”句。(21)
因雍正律有律内小注,又有律后总注,乾隆官修以为繁复,使律典读之更像一部律学作品,而不似一代大典,故而将总注全行删去。因为文字层次已然分明,故而并未减弱其确定性。
至于原顺治律后所附4条条例,它们在雍正修律时,进行了一番改动,因为至雍正间,已经无运炭纳米做工之例,所以删除了含有这类内容的语句,其余条例均得以保存。
此外,雍正修律时在此四条例后又续增一条例:“凡宁古塔、黑龙江充发人犯在配所杀人者,仍由部具题行文该将军,于众人前即行正法。”(22)据《大清律例按语》中的理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内,刑部会覆配所杀人正法事,理类于此律。”故而在此律条后增设一例。
乾隆五年(1740年)该律文后附条例为5条。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列明,仅举大意申述之。条例1基本延续雍正律律文所附的条例1内容,并合并了雍正律条例2、条例3的内容,所以,前明的条例至此合并为1条,主要规定对“先犯杂犯死罪纳赎未完,及准徒年限未满又犯杂犯死罪”以及其他罪行的犯罪的处理措施。
条例2基本是雍正律中的条例4的延续,主要规定对在京外徒犯又犯其他罪行的情况的处理措施。
条例3由雍正律条例5发展而来,处理宁古塔、黑龙江发遣之犯又犯罪的情形。
条例4为新增例,规定对发遣人犯的分起解送的措施以及该人犯在发遣途中再犯罪时的处理措施。
条例5亦为新增例,规定对发遣黑龙江等地为奴人犯之妻女犯罪的行为的处理。
乾隆五年(1740年)之后,该律文条例继续发展。至同治九年(1870年),条例已增至13条。我们且略去期间各个版本大清律例该条所附条例,直接看同治九年(1870年)律该律文附例。
条例1与乾隆五年(1740年)律中的条例1同。
条例2处理“免死减等发遣新疆宁古塔、黑龙江等处盗犯”在配所犯罪的情形。此例原系2条,一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宁古塔将军题,发遣人犯骚达子在配打死齐兰保一案,议准定例,乾隆五年(1740年)修改。实际上是乾隆五年(1740年)律所附条例的第3条;一系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议覆宁古塔将军吉党阿咨免死盗犯刘五图等行窃一案,经九卿议准定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并,道光十四年(1834年)改定。
条例3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福建按察使张镇奏准定例。规定:“闽省沿海府属,如有金刃伤人问拟杖徒之犯,或在配所,或徒满回籍,仍执持金刃伤人者,俱发近边充军。”
条例4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刑部议覆山东按察史沈廷芳条奏定例(原奏与军犯脱逃系属一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修改。规定军犯在配所复犯徒流罪的处理措施。
条例5系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刑部议覆浙江按察使李治运条奏,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奏准,并纂为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嘉庆六年(1801年)分别修改,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定。规定寻常窃盗问拟军流徒罪,在配在逃行窃的处理措施。
条例6系乾隆三十年(1765年)黑龙江将军傅僧阿条奏定例。原载《督捕则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移附此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改,嘉庆九年(1804年)改定。规定旗下另户人等,因犯逃人匪类及别项罪名,发遣黑龙江等处,并奉天、宁古塔、黑龙江等处,旗人发遣各处驻防当差者,视情况而区别处理。
条例7系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刑部议覆广东按察使富勒浑条奏定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改定。改发极边烟瘴充军之窃盗,在配复犯行窃及其他罪行的处理措施。
条例8系雍正七年(1729年)定例,乾隆五年(1740年)修改,嘉庆六年(1801年)改定。规定发遣人犯,于经过处所再犯罪的处理措施。
条例9此条系嘉庆十九年(1814年)奉上谕纂为例。规定发遣吉林、黑龙江等处免死盗犯,在配偷窃官粮的处理措施。
条例10系嘉庆二十年(1815年),顺天府府尹审奏,窝窃回匪大李三等拟遣一折,奉旨纂辑为例。规定回民因行窃窝窃发遣、复在配行窃的处理措施。
条例11系乾隆元年(1736年)刑部遵旨议准定例,同乾隆五年(1740年)律该律文所附的条例5。
条例12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黑龙江将军永玮奏,发遣为奴之张二,在配行窃五次,拟以永远枷号一案,奏准定例。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改定。规定发遣新疆人犯并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在配行窃的处理措施。
最后一条条例13系咸丰元年(1851年)乌鲁木齐都统毓书条奏定例。规定乌鲁木齐地方遣犯,如有在配滋事犯法及乘间脱逃,并逃后另犯不法情事的处理措施。(23)
毋需对这些条文的内容一一加以分析,我们单从此条例发展的过程,即可以看出《大清律例》的确定化倾向,这个所谓的确定化倾向,实际上也正是一种具体化倾向。它试图想将整个社会中、整个国境内的一切徒流人犯罪的处理情况,都尽可能地加以规范。试图使之成为帝国国家政治、法律生活的指南。
三、通过对法律条款的要素进行补充使律义更为确定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法律条文比较、立法过程两个方面揭示清律确定化的倾向,虽然也涉及条款内容,但更多还是从体例与形式方面讨论的。以下我们就从法律条款的内容上分析《大清律例》的确定化努力。
规定非法律规范的技术性条款,虽然表述的不是具体的法律规则,但就内容上而言,它是确定的。比如,《大清律例》中“称期亲祖父母”条规定:
“凡律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称孙者,曾、元同。嫡孙承祖,与父母同,缘坐者,各从祖孙本法。其嫡母、继母、慈母、养母皆服三年丧,有犯与亲母律同改嫁义絕及殴杀子孙不与亲母同。称子者,男女同。缘坐者,女不同。”
这条律文确定地指出了什么是法律中的“期亲”及“祖父母”,从而将法律概念和生活概念区分开来,从此,“期亲”和“祖父母”就成为法言法语,它对于涉及这类亲属规则的适用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规则一般具有逻辑三结构,或者称三要素说,指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假定条件主要交待法律适用的背景情况,具体而言,就是要交代该规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样的人(包括行为主体和行为所针对的主体)、对什么样的物(犯罪对象)才具有适用性。行为模式主要交代该规则是可为的、禁为的还是必为的,因为《大清律例》中的条款通常是用禁为的模式表现出来,所以,更类似于刑事性条款。这样一来,具体又可以分成行为的动机和手段(起因),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过程和表现),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结果或程度)。至于法律后果,则是行为所招致的法律评价,作为刑事化条款,此结果便是制裁。
故而,我们以以上的逻辑结构,将法律条款分成时间、地点、人物、对象、起因、过程、后果、评价这八个要素,分析清律确定化的倾向。应该说明的是,这八个要素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世界中事实上就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将它们作为思想的工具,目的是使分析更为清晰。
我们还是以同治九年(1870年)《大清律例》的“名例”篇“常赦所不原”条为例。该条律文如下:
“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到事过钱之类,一应实犯皆有心故犯,虽会赦并不原宥,其过误犯罪谓过失杀伤人,失火及误毁遣失官物之类,及因人连累致罪谓因别人犯罪连累以得罪者,如人犯罪失觉察关防钤束及干连听使之类,若官吏有犯公罪,谓官吏人等,因公事得罪及失出入人罪,若文书迟错之罪,皆无心误犯,并从赦宥,谓会赦皆得免罪。其赦书临时钦定实犯等罪名,特赐宥免谓赦书不言常赦所不原,临时定立罪名寛宥者,特从赦原及虽不全免减降从轻者谓降死从流,流从徒,徒从杖之类,不在此限。谓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
该条款的要素为:(1)过程: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到事过钱之类。(2)起因:有心故犯。(3)结果:实犯。(4)评价:虽会赦并不原宥。严格讲,该条律文的中心要素就这么四条。在“虽会赦并不原宥”之后的条款“其过误犯罪及因人连累致罪,若官吏有犯公罪,并从赦宥。其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寛及减降从轻者,不在此限”其实是一条但书,特别指明即使有这样的结果也当赦宥的情形。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该条律文简化为一条法律原则,即只要有心故犯以上所指十数种犯罪,并实际已经从事犯罪的,虽会赦也不宽宥。不管在何时、何地、何人所犯,针对何人,行为结果如何。若按现代法律的普遍性看,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到《大清律例》时,我们不能执拗于这种高度的原则性理解。因为构成律条的,不仅仅是律,更有例。我们接下来看该条所附条例。
条例1:“凡杀死本宗缌麻以上尊长及外姻小功尊属者,俱不准援赦。”该条补充了“人物”这一要素——凡杀死本宗缌麻以上尊长及外姻小功亲属者。这样的人如果再结合上律文中规定的四个要素,则评价具体化为“俱不准援赦”。
条例2:“凡关系军机兵饷事务,俱不准援赦寛免。”该条补充了“对象”这一要素——关系军机兵饷事务的犯罪。
条例3:“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以其罪罪之。若干系钱粮、婚姻、田上等项,罪虽遇赦寛免,事须究问明白。应追取者仍行追取,应改正者仍行改正。”该条补充了“过程”这一要素:“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所告者)“若干系钱粮、婚姻、田上等项”,还补充了“评价”这一要素——“以其罪罪之”、“罪虽遇赦宽免,事须究问明白”,怎么才能算明白?即“应追取者仍行追取,应改正者仍行改正”。
条例4:“诬告叛逆未决应拟斩候者,不准援赦。又,捕役诬拿良民及曾经犯窃之人,威逼承认,除被诬罪名遇赦尚准援免者,其反坐捕役亦得援赦免罪外,若将平民及犯窃之轻罪人犯逼认为谋杀、故杀、强盗者,将捕役照例充军。遇赦不准援免。”同样补充了“过程”,即“诬告叛逆”、“诬拿良民及曾经犯窃之人,威逼承认”;补充了“时间”,即“未决应拟斩候”;补充了“人物”,即“捕役”;补充了“结果”,即“将平民及犯窃之轻罪人犯逼认为谋杀、故杀、强盗者”;补充了“评价”,即“将捕役照例充军”。
条例5:“凡遇恩诏内开有军流俱免之条,其和同诱拐案内,系民人改发烟瘴少轻地方者,即准援免,系旗下家人于诱拐案内发遣为奴人犯,亦许一体援免。”该条补充了“过程”,即此条开始的“凡……者”;补充了“人物”,即“系旗下家人于诱拐案内发遣为奴人犯”。
条例6:“直省地方偶値雨泽愆期,应请治理刑狱者,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内情有可原者,该督抚一面酌量分别减免省释,一面奏闻。”该条补充了“时间”,即“偶値雨泽愆期,应请治理刑狱者”;补充了“地点”,即“直省地方”;又补充了“人物”,即除犯徒流罪以外的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内情有可原者;还补充了“过程”和“评价”,即督抚一面酌量分别减免省释,一面奏闻。
条例7:“凡察哈尔、蒙古及札萨克地方,偷窃四项牲畜,罪应发遣贼犯遇赦,俱不准减等。”该条补充了“地点”,即凡察哈尔、蒙古及札萨克地方;补充了“对象”,即偷窃四项牲畜。
条例8:“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红阳等项邪教,为首之犯,无论罪名轻重,恭逢恩赦,不准查办。并逐案声明遇赦不赦字样,其为从之犯,亦俱不准援减。”该条补充了“过程”,即传邪教和“逐案声明遇赦不赦字样”;并补充了“人物”,即“为首之犯”、“为从之犯”;还补充了“评价”,即“不准查办”、“不准援减”。
条例9:“凡在京在外已徒而又犯徒,律应总徒四年及原犯总徒四年,准徒五年者,若遇赦减等,俱减一年。其诬告平人死罪未决,应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者,如徒役未满,遇赦减等,减为总徒四年。若再遇赦,仍准再减一年。如已到流配所,加徒役已满者,即照寻常流犯,减为徒三年。”该条放在此一律条下有点突兀,原先放在“徒流人又犯罪”一律内。但如果同样按照要素论分析,它补充了“过程”,更主要补充了“评价”。
条例10:“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之犯,遇赦准予援免。如数逾一万两以上者,不准援免。”该条补充了“对象”,即仓库钱粮;补充了“结果”,即侵盗银两数量在一千两以上及数逾万两以上。
条例11:“凡触犯祖父母、父母发遣之犯遇赦,查询伊祖父母、父母,愿令回家,如恩赦准其免罪者,即准释放,若祗准减等者,仍行减徒。其所减徒罪,照亲老留养之例,枷号一个月,满日释放,毋庸充配。傥释回后再有触犯,复经祖父母、父母呈送,民人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旗人枷号两个月,仍发黑龙江当差。”该条补充了“人物”,即祖父母、父母、民人、旗人、官兵;补充了过程,即“查询……”还补充了“地点”,即新疆、黑龙江;还补充了系列评价。
条例12:“凡宗室觉罗及旗人、民人触犯祖父母、父母呈送发遣圈禁之犯,除恭逢恩赦,仍遵定例查询办理外,若遇有犯亲病,故许令亲属呈报各该旗籍,咨明宗人府,并行知配所督抚、将军查核原案。祗系一时偶有触犯,尚无怙终屡犯重情,并察看本犯果有闻丧哀痛迫切情状,如系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奏请释放。如系旗人、民人,由各督抚、将军咨报刑部核明,奏请释放。如在逃被获,讯明实因思亲起见,又有闻丧哀痛情状者,即免其逃罪,仍发原配安置,不准释回。其逃回后自行投首及亲属代首者,遇有犯亲病故,准其察看情形,如实系闻丧哀痛,免其发回原配,仍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若本系桀骜性成,屡次触忤干犯,致被呈送发遣,情节较重之犯,俱不准释回。”该条同样在“人物”、“过程”、“地点”、“起因”、“结果”、“评价”等多有补充。
条例13:“文武官员、举人、监生、生员及吏典兵役但有职役之人,犯奸盗诈伪并一应赃私罪名,遇赦取问明白,罪虽宥免,仍革去职役。”该条补充了“人物”、“过程”及“评价”。
我们如果将律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而不将它分别看成零散的条文,则《大清律例》的确定化倾向至为明显。大体而言,律文和例文若干个条款共同构成了一项规则,这项规则一般就是律名所指出的那样,比如上述这条中,13个条例和1条律文共同构成了“常赦所不原”的规则。但是律条规定的是一项宽泛的原则,是“常赦所不原”的一般情况,并不意味着只要出现犯该律条规定的罪行,即一定会出现“常赦所不原”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只要不为律条所规定的罪行,常赦就一定会原。单凭律文是无法处理案件的,必须结合例将规则具体化。所以,条例实际上起着将规则确定化的作用。
如果分而析之,将它们看成是一组规则。则律表述的是一般性规则,而例表述的是特别性规则。这样一来,如果在审判中要援引法条,这个问题就转化为一般法和特别法的问题。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的,但在具体的律条中,则律文相对于例文肯定为一般法。一般法是指在一国范围内,对一般的人和事有效的法。特别法是指在一国的特定地区、特定期间或对特定事件、特定公民有效的法。在一般情况下,在同一领域,法律适用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这样看来,长期困扰我们的律例关系以及清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就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无论是“以例辅律”也好,还是“以例破律”也罢,讨论的都是一般法与特别法问题。《清史稿》谓:“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空文而例遂愈滋繁碎。”(24)这句话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即在律例皆有对某行为或事件作出规定时,则“有例不用律”,因为例更为确定,且属于特别法。各种审判官方文书上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例禁綦严”,也说明了例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说“律既多成空文”则纯粹是修清史者的外行之言,律作为一般法,是司法官员在遇到案件时的首选之法律渊源,他首先会查验律中有无规定,然后再查具体的例,这是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的,由粗到精,由一般到具体。所以,何勤华先生在考察清代法律渊源时认为:
“《大清律例》是清代法律的主要渊源,不仅在刑事案件中几乎百分之百地得到了适用,即使在大量琐碎的民事案件中也是得到贯彻的,那种认为《大清律例》只是具文,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遵守的观点是不对的。同时,在清代,律是基础,例是补充,一般情况下,当某个案子呈送到审判官面前时,他首先适用的是律,只有在律文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或没有律文可适用时,才会适用例。认为在清代,例的地位高于律、在律例并存之情况下首先适用例的观点,与清代的审判实践并不相符。”(25)
所以,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基本的规则还是由律构成,而例恰恰是将这项规则具体化的产物,它的作用是不断地补充法律条款的各种要素,从而使得律例构成一项确定的整体规则。
四、《大清律例》条款“确定化”的原因和效果
《大清律例》的律条数量并不是现存传世法典中最多的,但却是篇幅最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条例众多,一切皆源于此“确定化”的倾向。那么清代立法者何以如此强调“确定化”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制度惯性的力量。制度是有惯性的,一旦一项制度成熟且运行良好,则如果不经过断裂式的革命,则制度会一直延续下去。对于继承此一制度的群体而言,实际上后者已经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我们所说的“清承明制”,不仅是指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法律条文,而且还指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法律编纂模式以及立法方法。诚然,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后,可以设想一套完全不同于明代的法律发展模式,然而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设想从来是在经验的、传统的范围内,对设想目标的价值普遍认可之际,才能够如愿以偿。政治行政过程的每一细节无不随时地顽强流露着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无论参与行政的官员胥吏,还是预期管理的事务和群众,都无法逃脱思维模式的惯性和认识关系网络的历史。”(26)所以,清代人实质上还是按照明代的方式在立法,只是人员组织和机构构成不同而已。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就会不断地编例。其实这过程自明代弘治以后就已经开始,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朝陆续在进行律例的修纂。当原来的法律已然落后于时世,仅仅靠法律解释已经难以达到效果时,律例编纂就成为了一种需要,久之形成了一项定型的制度,在编纂之始,确定化的需求就内化在立法者心中。最后成为一种惯性,从明代延续到清代。
第二,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明、清两代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达到巅峰的时代,尤其是清代,更是如此。张晋藩先生在研究清代律学的兴起时,注意到:“清朝是极端专制主义的王朝,立法权、司法权高度集中,对于法律的解释权当然也不会漠视,由皇帝钦定某个私家的注律成果,恰恰反映了解释法律权的集中化与国家对律学宏观控制的加强。清代纷起的私家注律,实质上受命于国家,是为国家注释法律服务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的若干分支而已。”(27)这一判断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何以清律如此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因为法律越确定,给予解释者解释的空间就越小。这样司法官员执行起来的自由裁量权限也就越小。我们需要注意,《大清律例》主要是编给各级官员特别是审判官员看的,通过确定的文本,可以约束和控制各级官员的行为,而各级官员再推衍开去,以确定的法律理政治民,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专制的需要。而且《大清律例》还绝非一部法典那么简单,它更可被视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南。诚如美国学者钟威廉所论:“对中国人来说,法律就是靠严刑推行的命令,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潜在地、无处不在的、全权的政府的一部分。”(28)试问,若法律条款不够确定,又怎么会“无处不在”?
第三,与清中期盛行的“考据之学”的推动相关。我们看《大清律例》确定化的倾向,表现在例的不断编纂,其频率最高,数量最多的时期,恰恰是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这一时期学术界主流是考据学的兴起。关于其兴起的原因,历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传统意见大多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出现是清廷压抑思想界的激进政治诉求所导致的后果,学人被逼向了追求琐碎学问的狭窄空间。但近来又有一种意见认为,“考据学的兴盛应是官家正统观建立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后果,甚至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政治步骤”(29)。其通过乾隆时期收集天下书籍编纂“四库全书”这一工程而得到强化。“作为清朝文化的集中代表的考据之学,必然影响到清代的律学。在清代律学的系统中,以考证为特点的注律著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系统。这个系统致力于考证条文的沿革变化,并进行历史的探源溯流,通过历史的钩沉遗缺、参校得失,阐释立法的原意及变动的因由,使‘用法者寻绎其源,以明律例因革变通之理’。”(30)这些律学又反过来推动律例的编纂,力图将皇帝允准的敕制,通过类似于考据学术化的方式,编入《大清律例》中。
第四,与“文质之辨”及清“部族私心”有关。以上为清律确定化倾向较为显明的原因。但是在深层次中,还有一层隐而不显,却可能至关重要的原因。即清代的“文质之辨”及“部族私心”使然。“‘文质’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中一直具有相当复杂的涵义。表面上看,‘质’与‘文’按字面很容易被理解为‘原始’与‘文明’的差异,中国历史的文明和进化被描述为一个由‘质’而‘文’的过程。”(31)“文质之辨”又直接和“华夷之辨”挂钩。清代政权是被广大汉人视为“异族”的满人政权。满人自进关伊始,就始终承受“华夷之辨”的文化压力。“满人自居以俭朴强悍的风格夺到大明的天下,却又不得不面对所征服地区文人的轻蔑姿态与无声的非议,在心态上并无优势可言。‘质’的粗陋生存样态无法与‘文’的雅致生活风格相抗衡是帝王的一块心病。经过几代的努力,到乾隆时其‘文’的水平早已居于一般儒者之上,却仍一度难以消除如何保留满人习俗传统和认同汉人文化之间的形成的紧张感。”(32)诚哉斯言!《大清律例》就是融合满人习俗与汉人文化的一个奇特的复合体。而律典作为典章制度,本质上属于“文”的范畴,条款确定性与否,也是评价该典章“文”的程度的一项标准。占领了这个高地,可以很有效的消弭“华夷之辨”,从而改变广大汉人眼中的满洲统治者“勇武尚质”、“厚重少文”的印象。故而我们才发现自顺治朝至宣统朝,历代统治者无代不修律,无代不定例,如此孜孜不倦,大概可以反映出其隐藏的“部族私心”吧?
最后简要地考察《大清律例》条款“确定化”的效果,就积极方面而言,经过了长时间的对条款的确定化的努力,《大清律例》在律条方面叙述流畅,逻辑严密。较早将《大清律例》介绍给西方的英国人小斯丹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就曾经评价中国法律“非常严密”(33)。需要说明的是,小斯丹东译出的主要是律,而例只是节译一小部分,但仅从律文本身看,其评价确为至论。
同时,从立法者或统治者的眼光来看时,经过确定化,确实限制了帝国官员的司法权和法律解释权,把他们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压缩得极小。援引时若查不到确定的例,照例需要上报呈请,使得帝王能有效干预和控制司法活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物极必反,过分追求确定化,以至于事事皆欲用例确定下来,导致了条款的增多,律例益滋。乃至修史者发出了“律既多成空文而例遂愈滋繁碎”的感叹。外国人接触到《大清律例》后,也有此观感。如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即评论这部法律“关注一些琐碎细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不会发生实际的作用”(34)。
再者,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即为了寻求确定,而在律后附例,但是条例具体附在哪条律文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编纂标准,这一点造成立法者在修例时候经常显得很踌躇。从《读例存疑》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即一个条例在百余年修改过程中,经常从一律移至另外一律,或者拆开分别列入不同的律文下。即如我们上文中所引的乾隆五年(1740年)律“徒流人又犯罪”律下所附的一个条例,至同治九年(1870年)律时,已经被移进“常赦所不原”律内。如此,庞大的律典篇幅和变动的条例,给司法官员适用法律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咸同间“中兴名臣”胡林翼早年在贵州为官时,即写信给左宗棠感叹道:
“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35)
胡乃是一代“能吏”,都如此焦灼,何况平常庸碌之官!于是对《大清律例》普遍的感受即是律例难读、难懂。比如清代长期供职于刑部的官员徐宏先就谈道:“修律难,而读律更难。”(36)因为通读法律、通晓律意如此之难,使得原来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员对此望而却步,虽律载“讲读律令”之条,要求官员讲读律令,但现实中很难真正贯彻。
按照法理学原理,法律一般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或规范调整,而不作个别调整。但是,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为此规定人的行为规范,法律也不可能无所不包,特别是成文法的滞后性,使得任何法律都会有缺漏和盲区。由于出现了没有预见到或没有先例的情况,或者由于社会哲学、正义观念或态度发生变化等原因,实践中不存在或不可能有完全确定的法律体系。因此,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不完善,使得法律规则正义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这乃是法律本身的自然规律。如此看来,追求法律条款语言的清晰无可厚非,而试图用条例将天下事确定纳入,则注定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大清律例》的成功和失败,均应作如是观。
注释:
①《大清律例》不仅仅在分类上因袭《大明律》的七篇制、三十门的分类标准。而且在编纂体例上,也采用明律律例合编的体例。《大明律》一开始并未律例合编。至孝宗弘治朝将《问刑条例》附在全律正文后面,至万历年间,始将例文附在每一条律文之后,形成“大明律附例”形式,清顺治年间,即采用万历律例合编定本,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此后直到清末《钦定大清刑律》(新刑律)之前,这样的律例合编体例始终没有改变。
②关于此点,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7页;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第二章及第三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博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第24页。此外另有多篇论文涉及此点,兹不详举。
③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1页。
④瞿同祖:《清律的继承和变化》,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
⑤此处所比较的明清律的版本,为两朝的经典性定本: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大明律》与清乾隆五年(1740年)的《大清律例》,乾隆五年(1740年)后,律文(包括律文小注)迄清末修律前再未更改,所以,也可以看成为明代定型与清代定型的法律条文之比较。笔者所援引的两法典均为法律出版社1998年之版本。
⑥瞿同祖:《清律的继承和变化》,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文集》,第418页。
⑦《论语·子路》。
⑧朱熹:《四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⑨《清通志》卷七十五。
⑩薛允升:《唐明律合编》自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1)吕丽:《“准古酌今”的思想与〈大清律例〉的制定》,《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3期。
(12)《大清律例》卷前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
(13)《大清律例》卷前附《世宗宪皇帝御制大清律集解序》。
(14)若需要了解这方面细节,可参看的代表性作品有乾隆年间吴坛著:《大清律例通考》、道光年间潘德畲辑:《大清律例按语》、同治年间吴坤辑:《大清律例根源》、光绪年间薛允升:《读例存疑》等。
(15)以上律文与条例参见黄彰健编著:《明代律例汇编》(上册),“中央研究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刊,1979年版,第331页。楷体部分为律内小注,下引律文,小注均用楷体标出。
(16)《顺治三年奏定律》,收入杨一凡等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7)相关的情形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18)参见吴建华:《清初巡按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
(19)潘德畲辑:《大清律例按语》,海山仙馆藏版,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版,第76页。
(20)雍正五年(1727年)律《钦定大清律》,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21)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22)雍正五年(1727年)律《钦定大清律》,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3页。
(23)以上关于条例的沿革情况,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名例之三”。
(24)《清史稿·刑法志》。
(25)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6)李宝臣:《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7)张晋藩:《清代律学及其转型》,见何勤华编:《律学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19页。
(28)钟威廉著:《大清律例研究》,苏亦工译,见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页。
(29)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94页。
(30)张晋藩:《清代律学及其转型》,见何勤华编:《律学考》,第427页。
(31)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226页。
(32)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227页。
(33)张振明:《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4)张振明:《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
(35)《胡文忠公文集》,河洛图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页。
(36)徐宏先:《修律自愧文》,见《清朝经世文编》(影印清刊本),卷91“刑政”,世界书局1964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