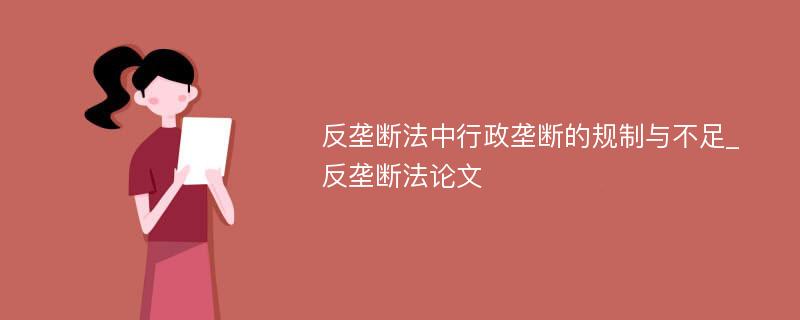
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与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制论文,反垄断法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从自由竞争逐步发展为经济型垄断的,而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业性垄断、地域分割走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通常,人们将行政机关及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称之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一个特有现象,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密切联系的。反垄断法不仅具有反对经济型垄断的一般意义,而且还具有反对行政性垄断的特殊使命,可以说,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中国反垄断法的一大特色。
早在1980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就已经提出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后来,国务院多次发布文件,禁止行政性垄断行为,如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禁止党政机关办公司的决定等等。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禁止行政性垄断。该法第7条对行政性垄断作了规定,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对于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后果,该法第30条规定。“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2001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对地区垄断作了禁止性规定,并详细列举了地区垄断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上述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的立法情况看,明显存在着不足: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立法比较零散、不完整和不成体系;有关规定多由国务院及各部委以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和意见形式作出,效力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各部委制定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还有相互抵触之处,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含糊、笼统,难以执行。
在反垄断法的起草过程中,行政性垄断是立法的难点之一,反垄断法是否应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是行政行为,和经济性垄断不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如果将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放在反垄断法中进行规范,那么所制定的反垄断法会带有浓重的行政法色彩,失去“经济法核心”的本来面目。况且,中国的行政性垄断有非常复杂的背景,行政性垄断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在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中,根本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很好解决的,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去逐步解决。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即使把反行政性垄断的内容纳入反垄断法,也起不了太大的实质性作用。行政性垄断涉及行政许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等许多问题,比较棘手,解决行政性垄断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各国反垄断法都主要规范经济性垄断行为,直接在反垄断法中限制行政性垄断的情况也较少。因此,不宜将行政性垄断的规制立法纳入其中。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反垄断立法应当将行政性垄断作为规制的重点。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一样,都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损害的是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行政性垄断具有转化为经济性垄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前行政性垄断现象极为严重,危害极大,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又缺乏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反垄断法应当对行政性垄断作出禁止性规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十分重视反行政性垄断问题,它们在反垄断立法时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果不涉及反行政性垄断,出台的只能是瘸腿的反垄断法,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永远不能走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反垄断法作为保护市场经济活动基础的法律,应该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做出相关规定。
最终,反垄断法以专章形式对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予以明令禁止。针对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反垄断法第5章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列举了行政强制交易、地区封锁(包括限制商品在地区间流通、阻碍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投标活动、以不公平方式设定市场准入等)、行政强制限制竞争等行政性垄断行为,比较全面地涵盖了我国目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反垄断法还专门针对含有限制竞争内容的抽象行政行为作了专门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的专章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但弥补了以往诸多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的缺陷,而且对具体行政性垄断行为和抽象行政性垄断行为均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解决了以往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彼此冲突的弊端,对于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问题专章作了规定,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在我国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反行政性垄断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其最终结果也是妥协的产物,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1.反垄断法并未使用“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只是提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因此,对是否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仍存在着争议。有人据此提出,中国不存在所谓“行政垄断”的问题,“行政垄断”的提法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垄断是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行为。行政机关并不是经营者,也不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不存在所谓“行政垄断”的问题。[1] 针对这种观点,多数人认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来自于政府,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人为地对市场进行“条”“块”分割,这是中国及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于是,人们将借助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称之为“行政垄断”。可见,“行政垄断”这个概念不具有行政机关从事经营活动特征。因此,以反垄断法第3条规定的垄断行为主体须为经营者为理由,指责“行政垄断”这个提法的科学性、准确性,进而否认我国存在行政垄断的事实是不科学、不准确的。[2] 可以预见,由于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缺乏明确界定及人们理解不一致,对今后的执法将产生消极的作用。
2.反垄断法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建立反垄断执法机关。当前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多头执法”的局面:发改委负责价格垄断和与价格有关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工商部门专门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其中可以涉及价格问题;与此同时,工商部门和商务部又可以同时审查经营者集中。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将执法权分割于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发改委,会造成权力分散,资源浪费,势必引起执法机关的扯皮,也不利于反垄断国际合作,因而权威性和独立性较低,与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的地位也不相称。反垄断法能否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与工作效能。
3.反垄断法对行政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关系规定不够明确。反垄断法的任务是制止垄断行为,理应关注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行业垄断企业。然而,这些国有企业一般都有一个强势的行业监管机构,现行保险法、银行法、电信管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明确规定,行业主管机关有权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应当包括垄断行为。在多头管辖的情况下,到底是“都要管”还是“都不管”,就成为法律尚需完善之处。在反垄断法草案的二审稿和法律委员会的审议稿中,原第2条第二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54条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调查处理的,依照其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3] 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垄断法将这些规定删除,却留下了悬念。由于没有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行为上的法律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对这些被监管的行业有执法管辖权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行业监管机构在处理被监管企业与其他企业或者与消费者的争议中,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维护被监管企业的利益,成为“监管者被俘获”。如果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没有权力处理被监管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这些行业的垄断行为将难以得到规制。
4.对抽象性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是反垄断工作的难点。反垄断机构只能建议实行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改变或撤销该行为,而无权直接责令其改变或撤销。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各种努力可能会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