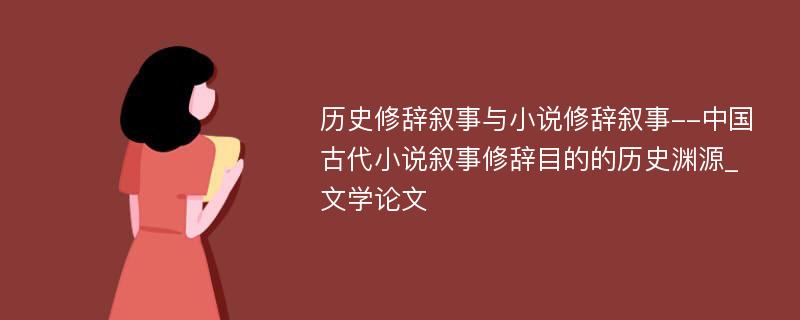
史学修辞叙事与小说修辞叙事——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修辞目的的史学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史学论文,目的论文,小说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3-204-04
中国传统的叙事概念涵盖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在这个大叙事中,中国古代历来有“史贵于文”的传统。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先秦有《春秋》、《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后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章学诚说:“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①,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叙事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处于正统地位的史学叙事,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制约。
为了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中国文人极力寻找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源性。所谓“稗官为史之支流”,小说是“正史之余”,“或於正史之意不无补云”②,都旨在强调小说与正史的相同之处,使小说的存在更具合法性。不过,小说作为稗史,虽稗史亦为史,但佳作不多。观鉴我斋在《儿女英雄传序》中曰:“稗史亦史也,其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也,何独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栋折轴,惬心贵当者盖寡。自王新城喜读说部,其书始浸浸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③只有那些言辞简约、文辞畅达,所写事情能够起到教化之功用,有着较为深刻的意旨的作品才能够算作为好的小说。
除了寻其同源性外,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也多向史学叙事看齐,在故事结构上或采用以正史为线索、囊括野史杂记和民间传闻而形成的带有补史性质的讲史平话、历朝演义和笔记小说;或仿照史书的体例,以编年记史,以纪传写人,以纪事录事;纵然是《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依然以纪传的形式“录述”了唐三藏法师的身世渊源;乃至章回小说的开场诗和结场诗,如《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等,都明显受到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的影响。
由于史学叙事与小说叙事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渊源,这里我们仅从修辞目的的角度,拟从道义到演义、劝谏到劝诫、发愤到泄愤三个维度发掘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与史学叙事承袭与发展的近缘关系,以便具体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小说修辞叙事的特点和局限。
一、道义与演义
所谓道义,便是对于义理的言说,道义是史书修辞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的史书不仅仅代表记忆和过去的史料,更处处或隐或现地保持着对于义理的言说,从而达成教化之功用,使得史书超越了故纸堆的学问,而具有鲜明的现实作用,颇为吊诡地契合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如春秋三传中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的描述。《春秋·隐公元年》言辞精简地将郑庄公与共叔段骨肉兄弟相互残杀的故事描述了出来,却绝非简单地复述或记录,而是寓藏明确的义理指向,叙述者通过“克”、“段”等词将自己的观点隐匿其中。《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时着力指出《春秋》中“克”与“段”的深意,指出二字中暗含着对于郑伯与共叔段的否定,并以此达成叙述者以言说义理为目的的修辞。《春秋穀梁传》的解释亦指出了这一故事包含叙述者的修辞指向:叙述者既认为郑伯的做法不可取,对待已经远逃的叛臣兄弟,应该以亲亲之道宽以待之;同时认为共叔段的错误更甚于郑伯,他失去了作为臣子和弟弟的道德准则,同样是站在明义理、崇教化的角度以传解经。《左传》进一步地发展了《春秋》中所蕴含的言说义理的修辞目的,更具体细致地讲述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续写了郑伯与生母姜氏和好的部分,将一种更为明显的贬讽贯穿渗透其中。如《左传》中郑伯在回答伯祭的话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其实便是叙述者借郑伯之口表达自己的伦理观念。这句话的意义还在于,郑伯已经预测到共叔段的后果,确立了共叔段有悖臣弟之道与他的下场之间的因果联系,“无道”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伦理逻辑,实现了史书叙事中修辞目的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新的发展。
在中国,史家对于叙事的修辞性有共识,他们认为,修辞是史书叙事的灵魂,失去了修辞,只把事件单纯地看成是事件,也就失去了史书存在的意义。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如是解释自己作《游侠列传》的初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④宋人吴缜认为作史三者为要,“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⑤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总结道:“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⑥,他在这里强调了史书所具有的以事载义、以事载理的修辞传统。余英时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也说:“历史叙事的作用,就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键找出来,使历史事件可以理解,离开这种解释,则历史学便不能成立,史籍也只能流为一种流水账而已。”⑦史载义理这一修辞目的,也就是余英时所谓的“理解”与“解释”。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继承史学以道义为目的的修辞,正如刘熙载所谓:“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⑧伯寅氏在《续小五义叙》中说道:“史无论正与稗,皆所以作鉴于来兹。”⑨小说虽为稗史,但稗史也应当具有“作鉴于来兹”这一教化功用,实现这一社会功用正是对于“义理”的言说。
义理的言说在具体的文学叙事中逐渐发展为对义理的演说,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演义这一小说文体就应运而生。应该说,“演义”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大量用于经典的阐释,如以像注经的《易传》,以事注经的《左传》以及以言注经的《公羊传》、《穀梁传》等。以言注经的“演义”逐渐被框定在语言学的范畴之中,大多偏重于训诂;以事注经的“演义”逐渐发展为文学独有的文体类型,宋元的讲史与话本成为了后代历史演义的前身。明清时期,史书的道义与以事注经的史书演义被文学叙事所继承,发展成为更具文学性的历史演义。
演义虽然与史学一样以阐发“义理”作为最终的修辞目的,但有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演”既有所本又有所生,如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就说:“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非无中生有者比也”⑩。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亦有语云:“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更为直接地剖析出了历史演义的“补史”之用。
在秉承“史所贵者义也”这一修辞目的同时,演义小说力求将“义理”以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出来,以“近语”编说古事。张尚德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11)。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亦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12),亦是强调以“近语”来表“义”的修辞目的。陈继儒在《唐书演义序》中更为直截了当地给历史“演义”下了定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又说“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13),也是肯定了以俗传“义”、以事演“义”的特殊性。以上这些对于以“近语”演古事的认可之语,说明了张尚德、陈继儒、蒋大器等人已经从语言上对史书与历史演义有所区别。蒋大器更是开创了所谓“事纪其实”派,主张在言说义理的前提下,演义之事只要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独特的文体形式进行了反思,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自觉与独立,而这同时又从反面证明了道义与演义的渊源关系,证明了古代小说叙事以及叙事理论中叙事修辞的史学渊源。
从道义到演义,史学修辞叙事与小说修辞叙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两者的修辞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人的伦理教育,不同的是,演义小说中的修辞叙事采用了更加形象化和通俗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去遵循忠孝礼义等礼节。郑鹤龄在《三续忠烈侠义传序》中说道:“见古人尽一忠烈,则尊之敬之;见古人行一侠义,则羡之慕之。读正史者概如是,读小说者何独不然”(14)观鉴我斋也总结道:“《西游记》为自治之书,邱真人见元门之不竟,借释教以警元门,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躯命本诚正以立言也。《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15)
二、劝谏与劝诫
劝谏同样是史学修辞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中的劝谏大多是通过对过去史料的记载,总结出治世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惩戒君王臣子,具有功利性特性。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采用过多种劝谏方式,汉代刘向《说苑·正谏》曾在孔子归纳的五种进谏方式(谲、戆、降、直、讽)基础上,重新划分成五类:“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班固则在《白虎通义·谏诤》中做了进一步修正:“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李贤在《后汉书·李云传论》的注解中具体指出了劝谏的五种基本形式:“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16),这些劝谏方式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忠君的品格和个人的胆识与智慧,同时又展示出了中国史书修辞叙事的风格。
史学叙事中关于劝谏的记载不胜枚举。就修辞目的而言,常见的有以“赞曰”等议论形式出现在史书中,或通过对事件的陈述来暗示其利害等。如《明史》在评价宋神宗时就写道:“赞曰: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17)直言不讳地将宋神宗的为君之过表述出来,以达惩鉴后君之目的。又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天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18)也是以直言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议论。史书中的劝谏还可以表现为对所录事件的刻意编排上。如《明史·本纪第二十三》中:“是年,革广宁及蓟镇塞外诸部赏。诸部饥,告籴,不许。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19)此处共录事件有三,一为庄烈帝朱由检革掉了广宁及蓟镇塞外诸部的赏粮;二为诸部粮草告急,朝廷不允许买入;三为诸部将空缺的粮草摊派到陕西饥民身上,流贼大起。史家在叙述这三件事时未使用表因果的关联词语,但通过看上去散漫的罗列而其本身带有浓厚修辞意味的编排,可以发现其隐藏的因果关系:流贼大起是前面两个事件的最终结果,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则要一直反推至君王政策的所失。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继承了史学叙事中以劝谏为言说目的的修辞方式,包括在叙述者的叙述和事件的安排上等方面也吸收了史学叙事的诸多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说修辞叙事中的叙述者与接受者的身份悄然发生了变化。就史学叙事而言,“谏”本身包含着说者与听者地位的伦理关系,是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建议、纠正、劝说。史书的隐含读者是君王臣子,“劝谏”的对象是那些位高权重之人。这种修辞目的到了古代小说叙事那里发生了改变,小说的隐含读者是下层,面对的是普通民众。因此,随着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位置的变化,“谏”这种特殊的针对于君王的政治文化术语就不再适用,“劝谏”的修辞目的就改写为“劝诫”,其对象成为普通民众。正如东篱山人在《重刻荡寇志叙》中所说的那样:“苟其持论新奇,意旨仍归于正大,则传诵者必多,其感人尤易入。”(20)其中,“传诵者必多”说明了小说与史书受众群体的不同,小说叙事的“劝诫”对象是众多的读者和听众。
与史学叙事相比,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中的“劝诫”不仅叙述者和接受者的位置有所不同,而且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写道:“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21)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则写道:“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22)在强调史学修辞时,吴缜使用的是“褒贬”二字;而谈到小说修辞目的时,静恬主人使用的则是“善恶”二字。笼统地讲,“褒”与“善”都是好的,“贬”与“恶”都是坏的,但以“善恶”来替换“褒贬”则是有深意的。从一定的角度讲,“褒贬”是针对“劝谏”而形成的,而“善恶”则基于“劝诫”,内含了修辞因受众群体改变而发生的微妙变化。“褒贬”是朝上的,是对君王的决策所做的评价,主要囿于儒家价值观。而“善恶”则是对于更为广泛的民众所言的,在“善恶”的评定标准中,儒经的价值观虽然占据核心位置,但也渗入了佛教、民间信仰等其他价值观的影响。由此,史学中以劝谏为目的的修辞叙事到了古代小说叙事那里,就发展成为受众下移且内涵更为多元的劝诫形式。
三、发愤与泄愤
言说义理、劝谏君臣是史书叙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集体性修辞,唯有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确立了以写史发愤为目的的个体性修辞,即“……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3)。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说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24)充分表达了自己因愤而著书,通过著书重新建构自己作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这一修辞目的。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获宫刑,是为官之辱,是史臣之耻,他的愤郁如是:“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25)在思索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后,司马迁坚持完成了《太史公书》,使史家个体的情绪融入到史书书写之中。但在后世的史学发展中,这种“发愤著书”的个体性修辞却被不断淡化、边缘化,不为史家所认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就直接否认了史家“发愤著书”的修辞目的,认为“后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潍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26)史论者们选择抛弃这种个体性修辞目的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自身的经学功用,个体性的言说自然要被不断淡化;二是除前四史外,只有《新五代史》为欧阳修单独所作,其余正史皆为集体官修史,故很难发出有关个人情绪的声音。
这种个体言说的修辞叙事在文学领域则得到了承继和弘扬。韩愈有“不平则鸣”,刘禹锡有“穷愁著书”,白居易有“愤忧怨伤”,欧阳修有“词穷而后工”,他们都在诗歌书写中沿袭了“发愤著书”精神内涵。至于小说创作,“发愤著书”的修辞也为古代小说叙事继承,并为小说叙事理论所论说,不过,古代小说叙事理论对“发愤著书”这一修辞目的的继承也并非完全照搬,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在排解愤懑的同时更注重的是重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他所举的周公、孔子、左丘等人带有自比性质,最终实现“成一家之言”。到了古代小说叙事那里,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诸如“经国大业”、“不朽文章”的言说目的逐渐隐退,而情绪宣泄、泄愤抒郁的言说目的则不断被强化。司马迁重在“立”,是“发愤著书”,立言以明志,通过立言重建自身价值;古代小说叙事则重在“破”,试图通过叙事来宣泄情绪,实现心理补偿,“发愤”的修辞目的也由此逐渐变成了“泄愤”,而这种“泄愤”的叙事也许更接近小说的本真状态。
古代小说叙事中这种“泄愤”在《水浒传》中特别突出。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水浒传》“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强调《水浒》是于叙事中表达叙述者对于南宋苟安的不满,以叙事泄愤。陈忱在《水浒后传略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水浒》,愤书也……愤大臣之覆餗,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佩蘅子也认为小说有一类便为“英雄失志,狂歌当哭,嬉笑怒骂,不过借来写自己这一腔块垒不平之气”。更为有趣的是,作为史家修辞目的的“发愤”到古代小说叙事那里,具有了宣泄的性质,个体价值建构的修辞目的让渡给了个体情感的宣泄和娱乐。金圣叹评《水浒传》创作时说:“(施耐庵)暖饱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他在《水浒传》第二十八回的总评又说施耐庵是“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表达了借泄愤而自娱的叙事目的。酉阳野史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27)他们都肯定了小说所具有的抒发愤懑的修辞目的,正可谓“泄愤一时,取快千载”(28)。
简言之,中国古代小说的修辞叙事既承袭并受制于史学修辞叙事的传统,又有所演变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风貌。我们在看到史学修辞叙事与古代小说修辞叙事的渊源关系的同时,还需要意识到史学修辞叙事中的“文以载道”功用、重史重实的传统以及叙事结构、叙述时间等方面的特质对中国古代小说修辞叙事的制约,关于史学修辞叙事对古代小说修辞叙事的消极影响还需要进一步专门研究。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页。
②③⑩(11)(12)(13)(15)(22)(27)(28)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263、267、268、578、382、111、104、268、578、429、171、173页。
④司马迁著,韩兆琦注:《史记·评注本》(下),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⑤(21)吴缜:《新唐书纠谬》,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⑥(2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史德),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6、812页。
⑦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91页。
⑧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
⑨(14)(20)高玉海:《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48、82页。
(16)范晔著,李贤注:《后汉书(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8页。
(17)(19)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2、792页。
(18)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5页。
(23)(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2736页。
(2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