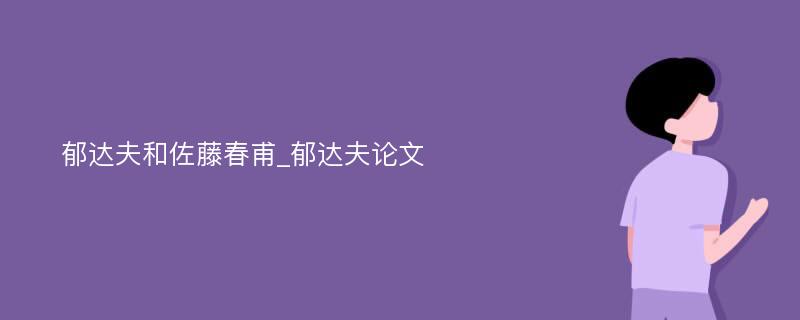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佐藤论文,达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3-0022-04
1923年,郁达夫在于北上就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途中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一封信里,曾谈到他索拜的一位日本作家。他说:“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郁达夫留学日本10年,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相当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但总的说来,他对日本文学评价不是很高,他觉得“局面太小,模仿大过,不能独出新机杼而为我们所取法”。但是,对于同是日本作家的佐藤春夫,他却如此称赞有加,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在郁达夫那些作家朋友中,有人还将他和佐藤春夫相提并论,并称他是“中国的佐藤春夫”;他们甚至当面对他说:“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1]而郁达夫在听到这一评价后的反映是:一方面很谦虚地说着“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的肩背”;另一方面,言谈举止之中,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骄傲与自豪。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郁达夫心目中,佐藤春夫的确享有非一般作家所能比的崇高的地位。
一
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佐藤春夫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他不仅以“私小说”作家而著称于世,同时还是著名的诗人、优秀的散文家和杰出的评论家。
在30年代中期以前,佐藤与中国文学界曾有过良好的关系。他不仅曾译过鲁迅的书,而且还翻译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他也十分关注。也许是因为这一缘故,当时那些留日的中国作家,大都对他抱有好感,而且不同程度地与他有过交往。其中,尤以郁达夫和他交往最为密切。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说:“在现代中国作家中,直接与佐藤春夫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人,当然应该首推创造社的郁达夫。”[2]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交往始于1920年。当时,郁达夫虽然还只是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一名普通学生,但是由于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时就已写出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因而他早就赢得了日本汉诗学坛的老宿们的垂青。而此时的佐藤春夫由于已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田园的忧郁》,也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对于本来就富于浪漫和感伤气质的郁达夫来说,佐藤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以厌倦、忧郁和厌世为基调的、颓废的诗一般优美的世界”简直太适合他的艺术趣味了,因此对佐藤的小说,他不能不为之心驰神往;同时,佐藤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善于将笔触“深入近代社会上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用复杂的忧郁情调,以及微妙紧凑的旋律,把人们的忧愁刻画出来”[3]的艺术天赋,也令他叹为观止。出于对佐藤春夫的仰慕,1920年,郁达夫通过田汉的介绍,结识了这位当时正在日本文坛崛起的文学新秀。在那以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不仅多次独自去拜访过佐藤,而且就是在回国以后,也仍然十分关注佐藤新作的发表。1927年4月2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还记下了这样的话:“……买了一本《公论》的五月号,里头有佐藤春夫的《文艺时评》一段,觉得做得很好。”
1927年7月,佐藤春夫偕夫人及侄女佐藤智慧子一行三人访问中国。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中国社会,了解一下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同时也会会郁达夫及中国文艺界的其他老朋友。7月12日,佐藤春夫一行三人抵达上海。第一个到下榻处来看望他们的,就是郁达夫。佐藤智慧子后来回忆说:“一到上海,郁先生立即到旅馆来看我们,而且差不多每天见面。在上海,除了郁先生之外,还见到了王独清先生、徐志摩先生、欧阳予倩先生等各位,但是郁先生对我们招呼得最亲切,因此印象最深,也最为怀念。”[4]的确,在佐藤春夫访问中国的二十多天时间里,郁达夫几乎一直伴随左右。他不仅陪同佐藤一起拜访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如胡适之、田汉、徐志摩、欧阳予倩、王独清等人,而且还在“功德林”摆酒设宴,邀请上海文艺界的名流作陪,盛情款待佐藤一行。7月下旬,郁达夫还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程陪同佐藤一行游览了杭州。一路上,他对佐藤的生活起居、旅途行程乃至文化生活等,无不悉心照料。
1936年11月,郁达夫因故再度赴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会上,他又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佐藤春夫。在欢迎会后,他还专程前往佐藤的寓所,看望了佐藤和他的家人。
自1920年初识佐藤,到1927年佐藤的中国之行,再到1936年的郁达夫访日,在16年不算太短的时间里,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由相识而相知,并且结成了一对跨越国界的文坛知己。他们之间的友谊,曾是中日两国文坛友好交往的象征。
然而,世事沧桑,谁曾料想,这一对交往多年、友情甚笃的异国知己,后来竟然会反目成仇!
二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关系的破裂,起因是佐藤春夫1938年3月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亚细亚之子》。在这篇小说里,佐藤春夫扮演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御用文人这一极不光彩的角色。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佐藤春夫逐渐暴露出其反华的嘴脸。他不仅自觉地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号筒,积极鼓吹“大东亚共荣”,而且不惜背叛自己昔日的好友与旧识,公开丑化和恶毒攻击与他友情甚笃的郁达夫以及郭沫若等中国抗日文化战士。他的小说《亚细亚之子》,即为阿谀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作。这篇小说由于在内容上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的需要,它一发表,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被搬上了银幕。
《亚细亚之子》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姓汪,一个姓郑,分别影射郭沫若和郁达夫。汪在北伐之后一直亡命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一起度过了10年的放逐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一个深秋的薄暮,他的一位姓郑的朋友,受了“最高领袖”的密谕,悄悄来到他的寓所,密谋请他回国抗日。汪遂抛下妻女单身回国,决心投身于反对妻子祖国的宣传工作。但是,回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来被人利用,他的郑姓朋友竟将他在北伐时所钟情的美人据为己有,并养于西子湖畔。为此,汪深感愤怒与失望。最后,他“幡然悔悟”,变卖了家产,来到“皇军”保护下的河北通州,在那里建立了日本式医院,并将日本妻子迎到通州,夫妻、父女得以重新团聚。
佐藤春夫的这篇小说,带有露骨的反华色彩,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治进行宣传。而这样的作品竟然出自佐藤之手,这不能不令郁达夫深感震惊和愤怒。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他绝对不能姑息迁就佐藤春夫这种为虎作伥的行为。1938年5月9日,郁达夫写下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刊登于《抗战文艺》第1卷第4期上。文章对于佐藤之流卖身投靠日本军阀的无耻行为进行了严厉地痛斥: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日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颂词。而对于我们的私人交谊呢,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太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人的丑态就暴露了。
在文章里,郁达夫毫不留情地将佐藤之流比作是在日本军阀后面摇尾狂吠的老犬,并且尖锐地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连娼妇也不如:
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老犬之一样。[5]
郁达夫对于佐藤的严厉的抨击,显示了一位正义作家在事关民族大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他的《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的公开发表,宣告了他与佐藤之间延续十余年的的友谊的终结。郁达夫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国立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郁达夫虽然在30年代中期以后断绝了与佐藤春夫的关系,然而在此之前的10余年里,佐藤春夫毕竟是他最为崇拜的日本作家,在创作上,他自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日本学者小田岳夫就曾指出:“达夫并不仅仅是崇拜佐藤春夫,在创作上也多受其影响。《沉沦》在很多地方与《田园的忧郁》相似,这就很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6]捷克学者M·嘎利克也认为:“佐藤的作品与郁达夫的相像,基调是抒情的,对国家的描写也是忧郁的。”[7]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评论家们对于郁达夫在创作上受到佐藤影响这一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1923年写的《海上通信》里,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小说给予过很高评价,对佐藤的成名作《田园的忧郁》尤为推崇。他说:“他的小说,周作人氏也就曾译过几篇,但那几篇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杰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最近发表的小说集《太孤寂了》,我还不曾读过。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以说是他近来的最大的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
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写于1917年,小说最初发表时题名为《病了的蔷薇》,翌年重新发表时,更名为《田园的忧郁》。《田园的忧郁》是一篇典型的“私小说”,它的大胆的自我暴露以及抒情式的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私小说”的特征。而被称为“中国的私小说家”的郁达夫在创作其“自叙传”小说时,无疑曾借鉴了《田园的忧郁》以及其它“私小说”的写法。特别是他写于留日时期的《沉沦》,更与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有着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对此,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也认为:“郁达夫的成名作,很明显是以佐藤的《田园的忧郁》为样板的。”[8]而小田岳夫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沉沦》与《田园的忧郁》之间的相似之处:“一、整体看来,可以说《沉沦》与《田园的忧郁》一样是叙述心境的小说。二、《沉沦》的主人公和《田园的忧郁》的主人公一样,具有忧郁症。三、《田园的忧郁》开篇即引用了爱伦·坡的诗句(原文和译文),《沉沦》开卷不久,就是主人公一边在原野里散步,一边读威廉·华兹华斯的原版诗并且由主人公自己译成中文。四、在《沉沦》里,遍布整篇的自然描写,非常倾注笔力。”[6]这些见解,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
考察《田园的忧郁》对于《沉沦》的影响,我以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郁达夫汲取了《田园的忧郁》中以身边事为题材、艺术地再现自我的方法。日本文艺理论家久米正雄曾把“私小说”称之为“‘自叙’小说”,也就是说,它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9]。而《田园的忧郁》无疑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篇小说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生活经历和内心情绪的真实记录。1916年4月,24岁的佐藤,带着两条爱犬和一只猫与他的情人远藤幸子一起迁居到神奈川县都筑郡中里村字铁(现在的横滨市北港区铁町)。由于母亲的帮助,他在那里买了一千几百坪土地。他想逃离令人窒息的城市,在这里喘一口气,结果却是失望而归。在《田园的忧郁》这篇小说里,佐藤春夫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在这一方面,郁达夫有意学习佐藤,他的《沉沦》同样是以他在名古屋八高上学期间的生活为题材,小说的内容基本上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沉沦》所记叙的,是郁达夫初到日本生活的一个片段。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与郁达夫在1936年发表的记叙这段生活的“自传”进行一下对比,就不难发现,作家的遭遇,以及所感、所思和所欲,与《沉沦》的主人公相合无间,甚至小说情节的推进都没有离开作家实际生活的轨迹。郁达夫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初到日本的经历:他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住满一年,尔后离开东京,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到名古屋后,“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10]。终于,在这一年的寒假,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他踏上了从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夜半时分,停车在一个小站,他飘飘然跳下车厢,直奔那弥漫着脂粉香气的日本妓馆,选中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妇,破了自己的童贞。第二天酒醒后,他无比悔恨,痛责自己“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读完郁达夫的这篇自传,再看他的小说《沉沦》,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事件,是完全按照作家生活的原貌如实地描写的,它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诚如夏至清所说,《沉沦》“可以毫无愧色地称之为作者的自传。作者和主人公的家庭教育背景几乎完全一致”[11]。
在日本现代作家中,佐藤春夫素以表现现代人孤独、忧郁和厌世等苦闷情绪而著称。他的《田园的忧郁》就是在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之下,分析了人生无法忍受的单调和疲乏,表现了一种奇妙的、近似于世纪末的颓废情绪。日本的评论家在评论《田园的忧郁》时指出,佐藤春夫“善于从内面观测自己的内心世界,擅长解剖自己的孤独、无聊和忧郁”,他的“作品里充满着一种由于精神的倦怠和神经或感觉过敏而来的世纪末的生活气氛”,他将笔触“深入到近代社会上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用复杂的阴郁情调以及微妙紧凑的旋律把他们的恍然刻画出来”。佐藤创作中的这一主题与情感取向也使郁达夫深受影响。他像佐藤春夫一样,把表现知识者的孤独、忧郁作为重要的审美目标。他也同样把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处,揭示其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在《沉沦》中,他以自我告白的形式,写出了一个青年的“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抒发了一个“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饱受歧视的孤独感和屈辱感,表达了作者自己那种怨恨祖国不强大,海外游子无可依靠的悲愤心情。
在写作手法上,郁达夫的《沉沦》也借鉴了佐藤的《田园的忧郁》。和所有“私小说”一样,《田园的忧郁》不是着眼于外部事件的描写,而是着意于心境的刻画。在这篇小说里,没有什么连贯的情节,也没有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者所着力表现的,是自我感觉、自我意识,是小说主人公的一种颓废的心境。那几朵败落的蔷薇花,正是主人公这种心境的象征。同样,《沉沦》的作者在小说中也没有试图去塑造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更没有去精心描写引人入胜的连贯的故事情节。整篇小说,就是一首哀婉的内心衷曲,一段艰辛的心灵历程。作者从小说一开始,就用充满浓郁感情的笔调,于事件的叙述中作极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自抒胸臆。而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就是那敏感纤细的个人感触、郁悒烦闷的情绪宣泄以及心理世界的细腻描绘。《沉沦》的这种独到的特色,恰与《田园的忧郁》十分相似。
日本的“私小说”在结构上往往独具特色。由于“私小说”以表现自我心境为主,它不需要虚构惊险传奇的情节,也不要架设巧妙周至的结构,只要把作者自己体验的生活直接写出来就行了,因而小说情节结构都较简单,不重技巧,笔法趋于散文化。西乡信纲认为:“日本自我小说表现手法的特点,是没有变化多端的情节,结构平淡,语言朴素,但要求毫不掩饰地描写。”[3]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在结构上即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有人曾经指出,佐藤春夫的小说“大多数都是一些具有随笔风格的东西”[9],这句话道出了佐藤小说体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随笔风格,是指作家不讲究小说的章法,不注重结构的严谨和情节的完整,而是有意追求结构的松散和情节的片段性,使小说带上了散文的特征。他的《田园的忧郁》就从盛夏的田园风光写起,写到阴雨连绵的晚秋,全篇的20节之间虽然彼此相连,但却十分松散,增加或减去一些章节都无损于作品的整体结构。这种松散的、趋于散文化的结构显然也被郁达夫借鉴并应用于《沉沦》的创作中。《沉沦》在结构上果敢地舍弃了传统的注重故事情节的小说结构模式,它以人物的主观感情的变化为小说结构的主线,叙事因素明显淡化,情节亦不再是构建、调节作品层次的链条。一切以人物心理情绪波动、心理情感逻辑来构筑作品的支架。它突破了时空限制与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以情感或心理线索获得艺术的统一感。郁达夫认为,一篇作品,只要能“酿出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地感受着这作品氛围的时候,那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贯不连贯,我就承认这是一部好作品”。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的小说一般都不大顾及结构技巧。他自己曾谈到,在“写《沉沦》的时候,……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忏余独白》)。这样一来,《沉沦》便呈现出了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面貌。为此,郁达夫还曾遭到过朋友们的取笑:“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当时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都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哪里有这种体裁?’”[12]而实际上,《沉沦》采用的这种体裁,正是受了佐藤的《田园的忧郁》影响的结果。
四
郁达夫虽然在创作上深受佐藤春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就《沉沦》而言,它也远不只是一部模仿性的作品,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思想内涵。诚如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所言:“《沉沦》虽然从《田园的忧郁》那里受到很多影响,但两部作品在根本上并不相同。后者的‘忧郁’产生于天下安泰的环境里,根源是人生固有的‘寂寞’,与国与民是完全无缘的。与此相反,前者的‘忧郁’却植根于‘祖国的劣弱’。”[6]小田在这里无疑指出了两部作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的确,从形式上看,《沉沦》与《田园的忧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部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及其思想内涵却有明显的不同。《沉沦》所描写的是一个身在异国的弱国子民生理与精神上的苦闷。作者从主人公灵与肉的冲突、爱与恨的交织中,揭示了一个病态青年灵魂深处变态的心理图景,从而揭示出了青年一代在“五四”前后这个特定的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氛围中,既因袭传统的文化与伦理观念,又渴望现代文明这样一种矛盾、痛苦和困惑的心理。《沉沦》中“我”的负罪感和忏悔、自省的内心表白,展现了新旧文化冲突中的人格分裂及其在文化归属、价值判断、情感协调、行为方式的选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彷徨、苦闷和困惑的心理现实。相比之下,《田园的忧郁》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悒郁和厌倦已经根植在他心灵深处”的厌世者,“他”心灵的窗户所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缺乏生机的寂寞和无聊。他颓废、消极和迷惘,企图逃避这个尘世而到“一个一切与这个世界组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去”。作品表现的是世纪末思潮影响下的人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倦怠。从形象的内涵和作品透视的社会意义来说,《沉沦》显然比《田园的忧郁》包含有更为深刻的时代、文化与人性的意蕴。
此外,《沉沦》和《田园的忧郁》还体现了他们的作者不同的人生态度与艺术态度。由于生活于不同的环境中,郁达夫和佐藤春夫在对待人生与艺术的态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佐藤生活于大正时期,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早已进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成为世界列强中的一员。对于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佐藤春夫来说,他感受不到民族与阶级的重压,生活悠闲而舒适,因而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不带丝毫的功利目的,而抱着一种纯粹的唯美的态度。在描写现代人的心境时,他也是用一种超然的神态欣赏着知识者的忧郁和苦闷。他“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烂熟的现实(不安、孤独和忧郁的现象),不过,他并没有探索这种不安、忧郁的根源,而是从唯美主义的角度加以咏叹”,他“一味地极大美化孤独和忧郁”[13]。与此不同的是,郁达夫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亲身经历了弱国子民受人歧视的屈辱,其经济地位远比不上家境优越的佐藤春夫,不论是在留学时期还是回国以后,他始终没有摆脱“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处境。这一切,都迫使郁达夫对社会现实始终保持关注的态度。因此在创作中,他缺少佐藤式的悠闲,无意将文学当作浪漫的精神之旅。虽然他与创造社同仁曾共同标榜过“为艺术而艺术”,但正如伊藤虎丸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也好,‘艺术派’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哪个派都可以说是以‘社会派’为前提的。”[14]正因为如此,在《沉沦》中,他不是像佐藤春夫一样用欣赏的态度描写知识者的忧郁和苦闷,而是写出了造成知识者忧郁和苦闷心境的社会根源。他使读者透过这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看到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收稿日期:2001-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