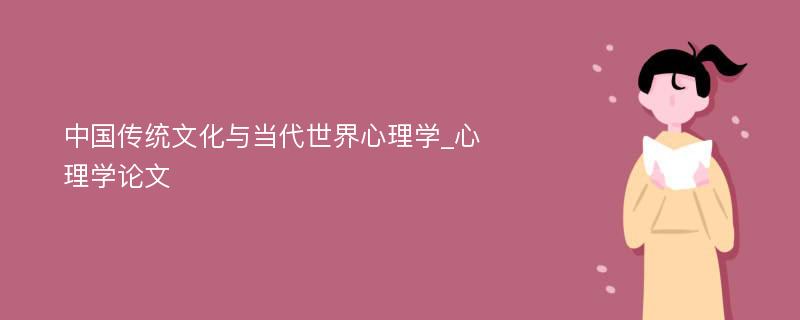
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当代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文化与论文,心理学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与传统文化
本文试图探讨: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的精神渊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对话的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世界文明生活中新的价值与历史地位;生活于文明飞速发展中的现代人,怎样汲取古老文明的精神营养,以滋补心灵,健全人格。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精粹文化与世俗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伴随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虽然在近代历史中,传统文化几经考验,一再接受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但终究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滋润与营养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魂灵与底蕴。
文化按照层次品位的高低,可以划分为精粹文化与世俗文化,每一个民族的精粹文化是由最能代表那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伟大人物创始的。从最早的文化源头上来讲,孔子、老子、庄子之于中国文化,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于西方文化,正是这种关系。以精粹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调一旦确立,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就会被后起的伟大思想家所不断继承与完善,形成流动着的文化长河。世俗文化则是每一民族的社会成员对于民族精粹文化的心理折射。精粹文化与不同地域条件、历史背景、文化领域的不同结合方式,便构成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形式。精粹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别在于,这两种文化创造者的品位不同,精粹文化的创造者,具有伟大的人格与超人的境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在纵向上,超越时代,走向后人。在横向上,跨越本民族走向全人类。世俗文化则是世俗社会的成员共同参与创造的,使得精粹文化的崇高精神扎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之内,参与创造世俗文化的人们在人格品位上是有残缺的、世俗的,甚或是堕性的、保守的,因此,世俗文化既辉耀着本民族精粹文化的光彩,又不可避免带有世俗社会的特有缺陷。我们把精粹文化与世俗文化区别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我们可以不因为世俗文化的缺陷而否定精粹文化的崇高品位与历史价值,出于愤世嫉俗的社会责任感,台湾的柏杨先生曾揭示出世俗文化中,中国人之“丑陋”,但这无损于孔子、老子的圣贤地位。鲁迅先生的无情的解剖刀也曾剖析过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但这也无碍于我们去体验中华文化源流中的精神凝炼力与生命纯度。在文化的析理中,保持一种理性的冷静。
(二)中国精粹文化的内在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部分,由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代表,这三家学说所代表的精神渗透于政治、宗教、艺术、哲学、民俗生活等诸多的文化领域。可以说儒释道精神构筑了中国人的“民族潜意识”。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圣贤文化,中国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圣贤人格的教育,这有别于西方以知识技能的培养为主的教育类型。中国文化注重德行,注重人格的完整性,主张以德至诚,以诚配天,成圣。天人合一,圆满祥和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概括地说,儒家学说的基本含义是:人怎样通过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人生的日积月累,完成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人生使命,达成一个圣贤人格的精神境界。《中庸》表述为“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大学》表述为“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自汉代董仲舒以来,与王朝政治关联密切。以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每以封建王朝为革命对象,儒家学说也同遭其难。假如我们跳出狭隘的历史局限,就儒家学说的跨时代意义来看,它的内在精髓恰恰是以治心为本,也正是在这一层含义上,它才能与释家学说和道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构筑中国人灵魂的精神要素,这使得儒家学说有可能突破特定时代所赋予它的僵硬外壳,成为跨越古今,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修心之法。近年来,海外新儒家学派正是本着这一宗旨,致力于挖掘这一古老学说的现代意义。修心养性之法是中国人的家宝。
释家学说为出世之说,诞生于印度,却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这种局面有它特殊的机缘,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的圆融之理,契合了儒家学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机制,而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也恰好吻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故此,禅宗初祖达摩西来,带来大乘禅法,至六祖慧能,契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气氛,立一代禅风,吹遍大江南北,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及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人文氛围,因而禅也就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在本质上,佛学是一种治心之法,世间之苦皆因妄念执着;欲要解脱苦难,唯有治心清净,去妄存真。佛学的这一义理与中国的修心养性传统有机融合,丰富了中国文化体系,中国的理学与心学大量吸收了佛学的治心之法,使得中国的儒学在宋明时期获得了更为完备的体系。
道家学说本为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想,后演变为一种本土宗教。作为宗教,就其对后代历史的影响力来说,却逊于佛教。这或许可以归结为道家的济世精神不及佛家之强,因之对苦难中的人们的感召力有程度上的差异。然而道家学说作为修心养性之道,作为一种哲学确实有其精妙之处,是中国古文化的灿烂瑰宝。在佛学兴盛以前,道家学说作为儒学的重要补充形式。儒道同为修养心性之法,儒家主入世,道家主出世。道家学说主张贵柔无为,道法自然,人与道合,成就至人真人之性。我国魏晋时期,儒学受到挑战,老庄易玄学代之而起,构成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儒释道三家学说相融并存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渗透于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人格修养的理想参照系,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当然历史也日益积淀出传统文化的种种负效应,演变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种种社会弊病,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些是世俗文化的产物。然而中国人对于精神的和谐与人格的完满带有深沉的信念,恰是中国精粹文化深入人心所致。中国文化精神以儒家的入世与佛道两家的出世作为互补结构,调整着中国人的处世态度的弹性与灵活度。
二、当代心理学的难题
(一)从意识分析心理学到精神分析心理学
心理学科的诞生,是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的莱比锡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冯特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是人的经验意识的构造问题,他在实验室里研究视、听觉、反应时间、注意、语词、联想及情感极性问题,由此他创立了侧重意识分析的经院式心理学。然而构造主义一经问世,就很快成为心理学界的众矢之的,其他心理学学派因反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原则而纷纷应运而生。在冯特的本土德国,格式塔学派以解释感觉的整体性原则来反对冯特的“砖瓦泥块式”心理学,冯特的弟子铁钦纳把构造主义心理学带入美国后,即刻在美国兴起了两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机能主义心理学以实用主义原则反对冯特的经院式心理学;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刺激——反应的客观性原则反对冯特的内省式心理学。在精神分析学派问世以前,以上这些心理学派的研究局限于人的表层感觉,外显意识及外在行为的解释之中,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问世及流布以后,人们才逐渐注意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与深奥。精神分析学象一股飓风,不仅卷动了整个心理学界,而且波及到各类人文社会学科,尤以文学艺术领域最甚。
弗洛伊德是一个医生,面对患者,他必须解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切实问题,使其拔出苦恼,得到治疗。因之,他切入心理问题的角度与一个经院心理学家切入心理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从今天的情形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点受到多方面的非议;然而弗洛伊德的伟大在于他提醒人们注意到一个长期以来被思想界忽略的问题:在人们的意识底层,有一种不为人们自觉意识到的本能驱力(力必多),它不适当地被压抑,是产生多种心理疾患的根本原因。潜意识问题无异于人们精神内部世界的新大陆,弗洛伊德正式把它揭开在世人面前。这改变了心理学的整体面貌:心理学从意识分析转向精神分析。心理学也就不仅仅是解释意识经验的构成,更注重解决人的心理问题。
(二)从病态人格心理学到健康人格心理学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很难完全协调统一在一起,人的本我真实力量总是受着自我与超我的压制不能完全舒展,因此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神经症。显然弗洛伊德的悲观性结论大大刺激了当代社会人们的人格自尊心。当然弗洛伊德对人格结构中生物性力量的偏执也很快受到后人的否定。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荣格,以他天才的敏锐,发现了人格深层结构中,除个体无意识成分外,还有一种更为深遂的内容,这便是集体无意识,这一观点为后来人格整合的健康心理学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大大突破了弗洛伊德在人格问题上的孤绝性视野。
当代卓有成效的精神分析学者霍妮,对神经症的主要症状——焦虑(包括莫名的恐惧、不安、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感觉等)也做了颇有特色的分析。她以为,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具有这样的心理结构:即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如“我应该是重要人物”,“我应该大有作为”等)与虚弱无效能的自我现状(如“我什么都不如别人”“我什么都做不好”)之间,处于严重冲突状态,使得人格发生分裂。这种分裂的人格会产生三种运动形式:(1)朝向人的运动,如对友爱与依赖性情感的需要;(2)背离人的运动,如对独立的需要;(3)反对人的运动,如对权力的需要。事实上这三种运动形式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对待他人的两极性心态,即依赖性与支配统治性。虚弱的自我力量导致对他人的依赖,而虚幻理想化的自我意向又导致人行使意志,支配他人的偏执。
把更大的兴趣放在整个社会风貌对个体人格结构的影响方面的,是德国的弗罗姆,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研究了德国社会特有的纳粹现象,归纳出纳粹现象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两种病态的心理模式——虐待狂(渴望统治与支配他人)与受虐狂(渴望被他人统治与支配),这种归纳与上面提到的霍妮对神经症病态需要的三种运动分析,有类似之处。在此基础上,弗罗姆进一步归纳出当代社会五种人格类型:第一种接受型,依赖与受制于外在权威者。第二种侵犯型,掠夺与统治外部世界者。第三种储藏型,保守封闭,以储蓄为僻好,缺少安全感,难于开拓者。第四种市场型,以交易为最高目的,人格商品化者。第五种生产型,富于创造力并敏于感受者。在这五种人格类型中,前四种均为病态人格,仅第五种是健康人格。
当代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在其重要论著《爱与意志》中,特别强调指出:“现代人的‘神经官能症’,其核心症结就在于意志的丧失,决策能力的丧失和个人责任感的丧失”。而人们用以填补内心空虚的唯一手段——性爱也日益变得官能化与技术化。在美国社会中,无爱之性随处蔓延。罗洛·梅所归纳的无意志的爱与无爱的意志,这两种极端的人格分裂类型,与弗罗姆所概括的受虐型与施虐型(或接受型与侵犯型),二者之间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综上,当代心理学家从不同侧面剖解了现代人的人格结构,竟也在一个焦点上达到共识:人格的基本结构——感受性与意志行为的分裂与冲突,带来病态心理的普遍蔓延,也构成了现代人的基本处境。这种状况也不约而同地表现于西欧存在主义的哲学与现代派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这样,当代精神分析心理学,存在主义哲学与现代派文学艺术作品也就共同创造了描述当代人精神现状所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难免让天性乐观的人感到窒息压抑,我们却不能否认它确实来自于厚重的社会基础。
在精神分析学派之后,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实现了心理学的从病态人格向健康人格的转化。由于不满于华生行为主义的人性机械化,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性动物化,马斯洛发起第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马斯洛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别于机械化与动物式研究的、使人更像人的本来面目的心理学体系。他通过大量收集生活实例,证实了健康人格与“自我实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马斯洛的理论努力证实,人的天性中本然就具有健康、快乐、自主、安详、创造成长与圆满和谐的成分,换言之人本来就具有圣性,关心人的“再圣化”是马斯洛学说的一大特色。面对大量的精神疾患,马斯洛本人也承认,能够达到健康成长、“自我实现”的人,在人群中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由于被各种“匮乏性需求”和生存困境所缠缚,不能完满实现自身的价值,就会导致各种心理疾病,但马斯洛不赞成以人的心理病态存在为由,就把人的基本结构描述为病态的,他宁愿以少数“自我实现”人格圆满的成功者的人格结构作为人的基本结构。在笔者看来,马斯洛的学说无异于中国的孟子“性善说”在美国的翻版。马斯洛实现了病态人格心理学向健康人格心理学的转化。换句话说,马斯洛实现了心理学上的世俗文化表达向精粹文化表达的过渡。
(三)精神分析学与人本学的困难
很显然,精神分析学与人本学是当代最能触动人的整体状态的心理学,因此心理学脱离开早期的经院式实验室分析,不可避免地再度与哲学携起手来,成为描述当代人生存状况的人生哲学的不同表达方式。但是,由于心理学科本身承担了更多的解决现实心理问题的使命,这两种学说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也暴露出它们自身的困难与危机。
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面对心理病患者的精神分析医生们越来越感到棘手的问题是:首先,患者自身的意志力衰退,对医生产生病态性依赖,不能在自己的基点上成长。其次,求治于心理医生的大多属于有钱而又有闲的阶层,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却因经济条件或闲暇不足,难于受惠于心理诊治。最后,精神分析者本人的博爱、真诚、智慧与意志力的综合素质,能否唤起他人的绝对信服,是诊治成败的最重要环节。在庞大的心理医生队伍中,品位高超令人敬服的精神分析者比例太小。
对于人本学来说,虽说人的本性中,自主、创造、和谐圆满的因素无可置疑。但何以如此多的人不能完全实现人性中这些优良的品质而带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障碍,处身于各种生存烦恼之中。让社会大多数人达到“自我实现”完成健康人格的可能性途径是什么?社会条件对人格发展的束缚是可以挣脱的吗?马斯洛在他的晚近理论中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这远非是一种乐观性哲学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这些问题在更大的比重上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这是人本学与精神分析学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的共有困难所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一个哲学上的根本矛盾:即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与缺陷残疾的现实环境之间的统一协调问题。
三、人格问题上的中西对话
在人格整合这个问题的焦点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以达成真正有深远意义的对话。
(一)精神分析与人本学者对古代文化的关注
颇富独创精神的精神分析学者荣格对古代文化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到非洲、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地进行考察,研究了这些未开化民族的原始神话,印证了他关于人格深层结构的独特发现。荣格注意到了人格底层的团体性因素,“集体潜意识”的表达,确实为个体人格在超个体的意义上,与更为广大深刻的民族意识达成整合做了最好的铺垫。这恰是荣格超出弗洛伊德之外,荣格的这一观点最为接近中国文化精神的观念,弥补了西方文化观念中个体意识或潜意识所特有欠缺——个体对集体的完全游离。弗洛伊德所理解的个体潜意识冲动的生物学化与孤绝化,恰好是西方文化中个体观念的特有折射。这种逻辑推导下来,便势必导致一个无可解脱的悲剧性结论:个体的潜意识冲动永远是反社会的,因之个体人格与社会伦理不能协调统一,人格分裂是必然的。
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弗罗姆曾于1957年与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共同举办了一个精神分析与禅的研讨培训班,事后合作出版了著作《神与心理分析》,禅者的智慧与人格整合引起弗罗姆的极大兴趣,他惊异地发现,禅者真正达到了人格的意识与潜意识打成一片,完全融合。所遗憾的是,禅者的这种人格整合是完全东方式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当弗罗姆尝试用西方语言来解释时,难免文化氛围与语言习惯上的隔膜。
人本学者马斯洛,格外在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中找到了默契。自我实现者与心理障碍者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自发性的品质。心理健康有良好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保证了灵敏、自主、独特的感受性与富有成效的创造精神,而频繁的高峰体验是健康者人格整合的最好标志,在“高峰体验”中,人与宇宙合为一体,人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觉知,进入宏大的融合之中,在此状态中,人似乎是被动的,无意志努力的,却具有最高的感受力与创造力。在这种人生境界中,真善美融合一体。马斯洛强调,这种自发性与高峰体验,最好的描述是在老子的哲学著作之中。“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便是人格高度整合的精神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一切心理症状荡然无存。
此外,当代著名的行为疗法创始人罗斯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老子思想与庄子思想的人格整合意义。
(二)中国文化传统历史演变中的两难问题
尽管中国文化传统是精粹的圣贤文化,然而这种传统却是在世俗社会的载体之上演变发展而来。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粹文化与世俗文化,既是相互映照、互相协调的,又是在层级品位上有大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西方文化所同样遭遇的困难,即理想境界与现实残缺的矛盾问题。
由世俗文化演变而来的中国式病态人格,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展示。《孔乙己》中孔乙己之迂腐;《祝福》中鲁四老爷之伪善;《伤逝》中子君之无聊;《阿Q正传》中阿Q之麻木。这些人格缺陷似乎潜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之中。鲁迅先生剖解中国人病态人格之深刻,真可谓入木三分。假如说,西方的世俗文化造就了典型的冲突、分裂、焦虑与难以整合的人格,那末中国的世俗文化则造就了表面和谐,内心却麻木、虚伪,失却真实完整感受的人格,同样也是病态人格。中国人的内心冲突会在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中得到缓解,表现形式上也远不象西方人那样激烈。这种文化格局影响于世俗社会的一般成员,极易发生埋没个体真切感受、走向虚伪庸俗的心理趋势。有感于此,当代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试图突破这种格局,找到人格成长的真实基点,于是从西方文化中大量引进了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并尝试以这种引进的价值体系塑造自己的人格。这种文化引进,虽然给世俗社会造成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却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与心理困惑。这种现状如同贾平凹《废都》中所描写的,那广做性爱尝试的庄之蝶,最终未能找到西方古典文化精神中性爱的那种壮烈与高贵,而走向无聊与幻灭。
与环境趋同,便有流于世俗,日趋麻木的趋势,人格得不到真实成长。引进当代西方价值观念,一味追求独特真实,又有人格分裂,心理失衡的危机。这便是中国文化传统在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面临的两难问题,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塑造自身人格价值取向上的基本困惑。
中国没有自己的当代心理学,中国人却也同样面临着人格整合的迫切课题,这种迫切性会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深入而更为突出。在上面所提到的两难问题中间,有无最佳途径可行?笔者以为,只有超越本民族的世俗文化,而与本民族精粹文化融和统一,才能避免流俗和分裂两个极端,超越世俗文化,沟通精粹文化达到人格升华整合,这中间的桥梁便是真切至诚的生活态度与严肃认真的责任意识。这个中间的过程是可以和西方的文化观念耦合的,但是终点还可回到中国精粹文化的圆满境界之中。这便是个体意识与荣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完全融合。人的个体意识是与世俗文化融合,还是与精粹文化融合,这取决于个体修养的精神品位,但这种融合却是个体人格和谐圆满的前题。中国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庞大的心理医生队伍,中国精粹文化系统本身就具有心理诊疗的特殊功能,这是众多被西方文化观念武装头脑的中国人最容易忽略的一点。
四、古文化与现代人
遥远的古代文明对于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早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中心。经济决定论者往往以人所享用与占有的物质生活水准,作为衡量人的生活状况的全部标志。却无暇顾及受惠于文明成果的现代人那一颗纷乱无序的心。富于感受的深刻思想家们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更为朴实的道理:心灵的整体状况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更重要的标志。古代文明透过重重物质文明之网,给现代人的启示,是人的精神整体与这个宇宙之间更为深遂与真诚的关系。古文化透出的完整、和谐、至诚与智慧的灵光对于麻木、平庸、分裂与焦虑的现代人,永远是一个温馨、振撼与魅力无穷的感召。
从中国文化源头来讲,三皇五帝、周公治世。孔子、老庄、释迦牟尼对学生与弟子说过的话,是怎样构筑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魂灵,又怎样由此演变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从西方文明的文化源头来讲,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们惊心动魄的爱恨交响曲,以及被钉上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又是怎样构筑了西方文明的魂灵,并由此演变出丰富多采的西方文化长河。这个视角不仅是文化史学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揭示中国人与西方人人格内在底蕴的一把钥匙。在此一条清晰的线索就显示出来了——文化之源与人格整合的内在关联。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心理学的考察,正是揭示这种内在关联的一个努力。
假如把中国文化精神再度简化,则可以概括为一个“诚”字。中国古圣贤境界是以诚事天,纯一无杂,它贯穿于儒释道三家心性修养的道法之中。相比之下,现代人的症结在于失诚,人与自己的生活世界失去了真诚关照的直接关系,外在世界的杂乱与内心世界的失调,便产生各种心理症结,程度严重者则走向病态。失诚则失圣,失圣则创造力低下,感受麻木。有一点勿庸置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实现圆满人格者总是少数。古之圣贤为数甚少,今之“自我实现者”为数甚少,无论古今,平民大众是社会的基本构成,然而今人的心理疾患何以如此之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如当代精神分析学者霍妮所指出的——源于现代人虚幻的自我意向。古代社会,贵贱有别,等级严明,各安其位,各事其政。而现代社会,个体从各种社会集团中游离出来,其有多项选择机会,近乎平均地享用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就造成了现代人虚幻的自我意象——人人都应该是成功者。而实际上成功者总是少数。“应该”与现状的巨大距离,便引起内心的冲突与失调,严重者则导致虚弱,人格紊乱。霍妮称之为“应该”之暴力。不能正视自身现实与虚幻的自负并存。自我愈是感到没有创造的潜能,他的虚幻的自负就愈是严重,就愈是对他人抱有敌意,而内心的虚弱却又促使个体从反向上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这也就是弗罗姆所谓“施虐”与“受虐”的倾向;罗洛·梅所谓爱与意态的分离。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至诚”精神可以上达圣贤帝王,下通平民百姓。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跨越时代,繁衍至今的生命力所在。诚字在儒家学说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便是不自欺(现代术语表达为正视自己),第二层含义便是不欺人(儒家所谓敬天事人),朱熹言:“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现代人有失于诚,恰好在于对内自欺,对外失敬。正视自己缺陷的勇气与敬重他人的德行是并行不悖的,愈是无视自身的缺陷以假象掩盖自己的虚弱,就愈是难于以诚敬待人,以责任处事,就愈是追求符合虚妄自我意象的外在效果,形成偏执型人格,爱与意志分离。
走向至诚是实现人格整合重要的途径。至诚需要正视自己、正视现实残缺的勇气;需要逆世俗而立诚的气魄;更需要敬德、敬贤、敬民族文化精粹的谦恭。至于现代生活中如何积小诚至大诚,实现人格完善,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操作性工作。正该另择文述及。作为有志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志士同仁,本该继承历代大德之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用心所在。
标签:心理学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马斯洛论文;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精神分析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精神分析学派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