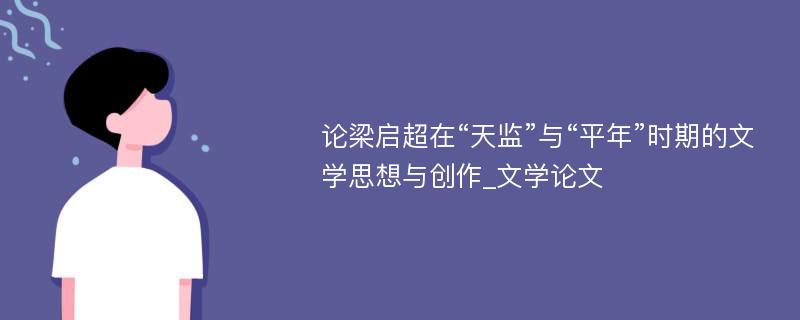
试论梁代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与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年间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梁代天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有一个时期常为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梁天监(502-519)、普通(520-527)年间的文学创作。在人们的意识中,齐梁文学的发展,似乎就是以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为中心,其实,在这两种文学现象之间,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也构成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这就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永明文学主要发生在齐永明年间(483-493),而宫体诗的实际发生影响则要到萧纲中大通三年(531)入主东宫以后,在这一段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京城文学活动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它与永明文学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萧纲到达京城不久所批评的“京师文体”到底何指?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创作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解决。
一
应该说梁初文学直接受到永明文学的影响,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如沈约、任昉、范云在天监初年仍然有文学活动,一些年轻的作家如刘孝绰、王筠等都是在他们的教导和提携下成长的,沈约并且还担任过太子萧统的老师。但是我们更注意到,这一时期永明作家的思想状态乃至诗风,都与永明年间发生了变化,年轻的作家并没有完全继承永明诗风,而是在新的朝代里提出了新的文学思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有必要对永明文学作一番考察。永明文学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代表作家即当时称为“竟陵八友”的沈约、谢脁、任昉、范云、王融、萧衍、萧琛、陆倕。“八友”之称见于《梁书·武帝本纪》,但这八友是否为经常性的文学集团,很值得怀疑。因为八人的年辈并不相等,比如陆倕,永明四年他才17岁,举为本州秀才,当他与张率前去拜访沈约时,沈约推荐给任昉说:“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是任昉与陆倕结为忘年交。至于萧琛,《梁书》记载他卒于中大通元年(529),时年52岁,这样比陆倕还小8岁。不过《梁书》又记萧琛曾为王俭丹阳尹主簿,时为永明二年,而这一年萧琛才5岁,于理不合。因此萧琛卒年52岁之说,很值得怀疑。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认为永明初年萧琛应为20岁左右。即使是这样,根据陆倕的经历,“八友’之聚最早也要到永明四年以后。永明五年萧子良正位司徒,于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八友”大概即于此时相聚,而得名或亦在其时。《梁书·萧琛传》说:“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可见萧衍是承认“八友”的说法的。从永明五年到永明九年,是竟陵文学集团的昌盛期,但能否说“八友”全部是中坚,恐还有疑问,因为从现存竟陵文学集团一些酬和作品看,似乎萧琛、陆倕与沈约、谢脁等相互酬和并不多。陆倕所存几首都是入梁以后作品,萧琛有一首《饯谢文学诗》,当是永明九年送谢脁赴荆州时作,但也仅有这一首,还表明萧琛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与他们相反,非“八友”中人的刘绘却参加了不少文学活动,他与沈、谢的酬和作品超过了陆倕和萧琛。因此所谓“竟陵八友”并不一定能反映竟陵文学集团的实际,这个文学集团的中坚并不是“八友”,而只是“八友”中的沈、谢、任、范、王等人。
沈约、谢脁都是永明文学的代表作家,对诗歌的声律化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他们能够突破前人樊篱,获得声誉(注:《南齐书·谢瀹传》记:“世祖(齐武帝)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诗?’俭对曰:‘谢胐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这说明齐初沈约尚未有诗名,他的得名晚在永明年间。),也正由于他们的新变体写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建武以后不再全力写作新体诗了呢?这一现象正说明了新变体在当时的局限。根据现在的研究,永明新变体诗主要发生于永明二年至九年,其内容也以咏物和赠答等应酬作品为主,这就表明新变体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只适合表现情感肤浅以应酬为主的内容。这一方面因为永明作家对声律的调谐把握还不能自由运用,对表达真感情的内容难以在新变体中使用;另一方面新体诗的讨论产生于承平时代的王府之内,而永明年间的统治者已十分明显地表示出对新体诗歌的喜爱,比如武帝萧赜喜爱《西曲歌》,并且仿而作《估客乐》;又如竟陵王萧子良与诸文士造《永平乐》十曲,这样由统治者倡导的新诗风,一开始就确定了写作的对象以应酬内容为主。但当永明末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作家的境遇改变、体会加深时,新体诗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相应的艺术经验,因此传统古诗形式即成为抒情的主要体裁。
沈约、谢脁诗风的转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建武年间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了整个诗坛的变化。永明年间以能文与沈约能诗齐名的任昉,这时却想以诗超过沈约。《南史·任昉传》说他“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注:钟嵘《诗品》亦有类似的说法:“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这说明任昉晚年写诗以使典用事为特色,想以此超过沈约。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任昉本不以诗名,他的不如沈约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到了晚年,却聊发意兴,想改变这种情况,超越沈约。问题是为什么任昉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以为这与永明末年诗风的变化有关。永明年间的新体诗写作,任昉未能擅名,但他并未想到要超过沈约,可能与他不如沈约娴于声律有关;至于永明末年,诗风变改,沈约、谢脁等人由新体转向古体,任昉则以事典入诗,因为这是他的强项。使事用典之风据钟嵘说始于颜延之、谢庄,其后的宋大明(457-464)、泰始(465-471)年间,文章殆同书抄。由宋入齐,承其风者有王融、任昉,钟嵘说:“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从这个批评看,任昉、王融的竞用事典,是从永明末年开始的,所以说是“近”。这股用事用典的风气,从齐末开始,一直漫延到梁代,史书所记沈约与萧衍争知栗有几事,以及萧衍召人编《华林遍略》等事都发生在梁代,说明这一时期的君臣都以博物博事自炫。
以上是齐末建武年间诗风变改的基本情况,沈约与谢脁是永明年间代表作家,同样也是建武年间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风影响并带动了齐末诗坛;与他们略有不同,任昉在永明年间不能说是写诗能手,但他在齐末以来却成为领风气的代表诗人,他倡导的使事用典之风,影响了齐末乃至梁初的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齐永明至建武年间文学发展变化的真实状态,构成了梁代前期年轻作家思想状态和文学创作的背景,对我们了解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梁天监、普通年间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既与永明文学不同,更与宫体文学有区别。从时间上看,应该从梁天监元年(502)开始,到中大通三年(531)结束。公元502年,萧衍代齐自立,是为梁朝,改元天监元年。这一年萧统二岁,被立为太子,萧衍为立官属,标志新文学时期的开始。中大通三年,萧统病逝,随着萧纲入主东宫,倡导宫体文学,宣布了萧统时期的结束。本文之所以采用天监、普通之名,一是因为萧统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普通以后,该集团成员基本解散;二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根据萧统生平和他的文学活动经历,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天监元年(502)至天监十四年(515)萧统加元服为第一个阶段;天监十四年至普通末(八年,527)为第二个阶段,这是萧统文学集团的主要活动时期。由于普通七年(526)萧统居母丧丁忧,而前此一年这一集团的主要作家刘孝绰亦被免官,所以萧统文学集团转入最后阶段,即从大通元年(527)至中大通三年(531)萧统逝世为止。普通七年以后,萧统文学集团事实上已经解散,其最主要活动大概就是将《文选》总纂完成,其它已无暇顾及了,因此本文的考察就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阶段。
天监元年萧统立为皇太子,武帝为东宫立官属,当时一些有名望的人如范云、王暕、褚球等都入东宫任职。其后东宫官属几经选择,如天监六年(507)诏革选家令,天监七年(508)诏革选中庶子(见《文献通考》六十),名德之人多入东宫,如沈约任太子少傅即是。南朝时东宫官属为四海瞻望(参《宋书·王敬弘传》),与西晋已有不同(《晋书·阎缵传》记缵上表陈选择东宫师傅,宜选寒苦之士)。《梁书·庾於陵传》载:“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地望。”因此萧统东宫可谓荟聚一时名贤。不过在第一阶段,萧统还很年幼,以他为核心的文学集团还没有形成,因为这一时期文学活动仍然以由齐人梁的作家为主,诗风也与建武以来的古体一脉相承。由齐入梁的作家有沈约、范云、任昉、陆倕、萧琛,这是永明文学集团中的“八友”阵容。除此以外,王僧孺、柳恽也是永明文学集团中人;至于在宋、齐年间擅名的江淹,到了梁代已经是“江郎才尽”,不再有什么创作了。以上的人员虽然都出自永明集团,但经过了建武年间的变化,不仅诗风已有改变,而且事实上他们在梁初诗歌创作的热情也不如以前了。如萧琛,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好:音律、书、酒,但年长以来,三好废弃了两好,惟有书籍不衰。这里的“音律”主要是指音乐,恐怕也包含有声律的内容,因为他是“竟陵八友”之一,早年曾经参加过永明声律的讨论,与谢脁等都有唱和,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到这时萧琛已不再写诗了。还有一些作家入梁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如范云死于天监二年(503),在新朝代中并没有来得及展现新面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代表作家的沈约和任昉创作上的变化。与永明、建武年间相比,沈约在新朝代中的写作并没有付出很多的热情,他主要写一些郊庙歌辞以及应酬的作品,但就是这些应酬作品也与永明年间不同了。永明年间的应酬作品以五言八句、十句短篇为主,这是典型的新变体;而梁初则以七言的民歌体为主了,比如《江南弄》、《四时白纻歌》诸诗都是。这个变化当然与梁武帝喜爱西曲歌有关,只是这样一来,永明体的影响就受到了限制。与沈约不同,梁初似乎是任昉的创作高潮期。从现存作品看,任昉的诗歌基本写于这一个时期,其中以《文选》所录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最为有名。此诗为悼念范云而作,诗中说“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可见二人感情的深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首
诗并不像钟嵘所批评的那样“动辄用事”,从形式上看,是典型的古体,用字也不避重复,与永明年间的诗歌大有区别。但就是这样的诗歌却被萧统选入《文选》,说明这一种诗风是被萧统集团认可了的。任昉以笔札名世,因此《文选》选录他的文章多达17篇,诗歌却仅有两首入选,而这两首诗歌又都写于天监年间,这一者说明任昉晚年诗歌确有成就,二者恐更说明了随着建武以来诗风的变化,引起了梁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观念的改变。正是在这个背景里,任昉萌发了在诗歌上超过沈约的念头。若以梁初诗歌论,说任昉赶上甚或超过沈约,也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一点说,任昉对萧统文学集团的影响可能要比沈约大。
沈约、任昉除了以变化了的诗风影响诗坛外,还把精力放在培养文学新人上。提携新人是永明作家的优良传统,如沈约、范云、任昉、谢脁等都曾提拔过许多新人,洎入梁以后,除了谢脁早死以外,沈约、范云、任昉更注重对年轻人的奖掖和提拔,如任昉在任御史中丞以后,刘孝绰、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仪、陆倕、到洽、张率等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而沈约对王筠的激赏,更是有名的故事。像萧统文学集团中的刘孝绰、王筠等就都得到他们的赞扬和提携。以上这些年轻作家基本都是萧统文学集团中人,这一个事实说明了萧统文学集团的形成背景,这个文学集团后来所提出文学思想和创作上表现的特色,都与这个背景有关。
随着年轻作家的成熟和新文学集团的崛起,沈约、任昉亦渐入老境,任昉先于天监七年(508)死去,至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也终于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人世。沈约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三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萧统于太极殿加元服,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正式开展了文学活动。
天监十四年刘孝绰、王筠并已35岁了,他们的成名很早,尤其是刘孝绰,少年时即被称为神童。他的父亲刘绘,曾预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游,也是永明体诗人,《南史》说他“音采瞻丽,雅有风则”。刘绘对声律理论应当很精通,而且具有批评意识,《诗品序》说他曾想著《诗品》,批评当时创作的混乱状态,可惜未能完成。刘绘的创作与批评意见应当影响到刘孝绰。除他父亲之外,他的舅舅王融是“竟陵八友”之一,对声律更有造诣。钟嵘《诗品序》记录了王融对于声律的一些意见,并说他想作《知音论》,“未就而卒”。王融对刘孝绰也尽栽培之事,在孝绰很小的时候就同车载他以适亲友,多加提携。而刘绘、王融的诗歌同志沈约,任昉、范云也都对他青睐有加,由此可以见出刘孝绰的文学思想及写作都与永明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刘孝绰相同,王筠也“少擅才名”,他出身于琅邪王氏,其从叔即是王融。从史料记载看,永明诗人中以沈约最为欣赏王筠。《梁书·王筠传》记:“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自谢脁诸贤零落之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谢脁是沈约的知己,其创作才能深为他所叹服。自谢脁、王融等人死后,沈约一直感受着寂寞的悲哀,他创作的《怀旧诗》九首就是这种情感的流露。当他于晚年得识王筠之后,竟能产生这样的欣奋,可见王筠的确继承了永明体的诗脉。同传还记王筠读沈约的《郊居赋》,音律正符合沈约的要求,把这位老诗人激动得“抚掌欣抃”。他说:“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正在此数句耳。”这都说明王筠深得永明声律的三昧了。从以上材料看,刘孝绰、王筠这两位萧统集团中的核心人物,都与永明作家具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但是直到天监十四年刘、王二人35岁之前,他们在文坛上并没有造成如他们父辈那样的影响,甚至连永明诗人津津乐道的声律理论,也未见有特别的宣传。这恐怕与建武年间以来诗风已经改变、文学思想也产生了变化有关。比如产生在天监年间钟嵘的《诗品》,就对声律理论持批评态度。这当然与钟嵘本人的思想有关,但若结合建武以来诗风变化的情况看,恐也并不一定是钟嵘个人的意见。萧琛所称晚年摒弃声律的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说明随着诗风的改变,人们对声律理论的热情已经衰减。以刘孝绰为例,从他现存的诗歌看,天监十四年以
前的作品多以长篇为主。如《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诗》、《太子汱落日望水诗》、《酬陆长史倕诗》、《答何记室诗》等,都是古体长篇。此外以代表萧统集团文学主张的《文选》为例,据刘跃进先生在《昭明太了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一文中分析,《文选》所收“竟陵八友”的诗,四句无一首,八句仅有4首,较多的是十句、二十句诗;而后来的《玉台新咏》所收,四句诗却有48首,八句诗有32首。再从律句和押韵方面考察,《玉台新咏》所收诗歌也都比《文选》所选在声律方面更为考究(注:《文选学论集》,赵福海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这说明萧统文学集团对永明声律理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从建武以迄天监前期,萧统文学集团就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中渐渐成长起来,至天监十四年以后,随着萧统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学主张和新的诗风就由这些新一代作家公开提出来了。
四
公开宣扬他们文学主张的主要是刘孝绰《绍明太子集序》和萧统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虽然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正式活动开始于天监十四年,但这两份文件却晚至普通三年(522)以后。这也说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文学思想才逐渐成熟。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当作于普通三年,因为文中有“粤我大梁二十一载”的话。《梁书·刘孝绰传》记:“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这一记载与刘孝绰的《序》是相符的。《序》中表达其文学主张的话是:“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浮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辞赋,曹祖劝其修令;伯喈笑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这段话前半部分表达了刘孝绰对辨体的认识,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观点相似。刘孝绰这里是赞扬萧统具有通才,诗、赋、书、铭、七、表等皆能曲尽文情。萧统是否通才暂置不论,刘孝绰这里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是“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典和野、远和放、丽和浮、约和俭,分别是四对相近的概念,刘孝绰强调前者,反对后者,表达了一种比较折衷的文学观。以“典”和“野”说,“典”指典正,“野”指质朴,《论语·雍也》有“质胜文则野”的说法,说明“野”指质过于文。 在六朝人眼里,典正不华丽,便容易流于野。钟嵘《诗品》评左思是“文典以怨……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可见左思的“野”是由“典”带来的。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文典则累野”,正指出了“典”和“野”之间的关系。再以“远”和“放”为例,“远”应该指作文不能太拘谨,“放”则有“放荡”的意思,与萧纲提倡的“文章且须放荡”意思相近。刘孝绰这里提倡要“远”而不“放”,文学主张与萧纲不同。根据刘孝绰的这个文学主张,可见他的理想与永明诗人(如沈约的“古情拙目,每伫新奇”)和宫体诗人都有区别,而较趋近于折衷。
和刘孝绰观点相同,萧统在同一年所写《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个观点很明显与刘孝绰完全一致。
从以上两份文件可以看出,萧统、刘孝绰旨在崇尚文质彬彬的温厚雍容风格。《颜氏家训·文章》以何逊与刘孝绰作比较,说明了当时的风尚:“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扬都指建邺,即梁时的都城,这个议论反映了当时人不喜欢清巧、形似的风格,这恐与天监年间安康、祥和的政治有关。刘孝绰帮助萧统编《古今诗苑英华》,仅收何逊两篇,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忌贤心理,另一方面也还因为何逊诗风不合当时的审美要求。人颜延之的话看,对何逊诗的批评,并不是刘孝绰一个人意见,颜延之本人也持批评态度,所以说“实为清巧”,表明“清巧”的诗风不好。这个批评很能反映时代文学思想的改变,因为从刘宋以来,“清巧”和“形似”一直是诗坛的主流。永明体在以四声裁诗的同时,描写上也以“清巧”和“形似”为主要特征,事实上何逊的诗风也与永明体一脉相承,因此扬都论者对何逊的批评,实际上已寓含有对永明体的批评。这一文学要求的形成,是与萧统、刘孝绰等人的提倡有关的。
除了上述两份文件外,以萧统为中心文学集团的文学主张还主要地反映在《文选》一书中。《文选》是萧统所编的一部诗文选集,选录从周秦以迄齐梁13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于它的去取精当,的确做到了如萧统所说的“集其清英”(《文选序》),因此自隋唐以来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选》学”。《文选》一书在后世产生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萧统文学思想的历史合理性。关于《文选》一书的编者,自南朝以迄近代,基本没有疑问,但近年来首先由日本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刘孝绰而非萧统(注:参见清水凯夫《〈文选〉的编辑周围》,此文最先于1976年发表于《立命馆文学》377·378,后收入作者《六朝文学论文集》,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但据中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萧统之功不可没,刘孝绰只是协助萧统编纂(注:参见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的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2页。)。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合乎实际的。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这里的“诗苑英华”就是指《古今诗苑英华》,萧统的意思很明显表示对它的不满意。为什么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时的文学思想还不成熟,编辑也不精当,故留有遗恨;另一种可能则是《古今诗苑英华》一书并非萧统所编,他的文学主张和编辑思想没有得到贯彻,所以他不满意。《古今诗苑英华》从何时开始编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它在普通三年以前已经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萧统的信可以作证。又萧统在信中说是“往年因暇”,我想一、两年以前恐不可称“往年”,细绎语气,似乎时间已经很长了,其书已在外面流传,因此《古今诗苑英华》应该在普通元年(520)以前,很可能是在天监年间编成。从《梁书》的有关记载看,天监十四年以后,萧统与东宫学士经常讨论篇籍,商榷古今,那么编辑图书应该是这以后的事,这也与萧统信中所说“谭经之暇,断务之余”相符。只是这个时候,萧统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文学思想的不成熟是必然的,因此《古今诗苑英华》一书可能全由刘孝绰编纂。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人才把此书径称为刘孝绰所著。比如《颜氏家训·文章》就说刘孝绰“又撰《诗苑》”,这里的“诗苑”即指《古今诗苑英华》,这是一证;二证是唐人刘孝孙《沙门惠净〈诗苑英华〉序》(《全唐文》卷一五四),称惠净“自刘廷尉所撰《诗苑》后,纂而续焉”,刘孝孙所编为《诗苑英华》,既是对刘孝绰的续,则见刘孝绰的《诗苑》就是《古今诗苑英华》。由这些材料可以见出《古今诗苑英华》的确是刘孝绰所编。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萧统对《古今诗苑英华》的不满意,与他没有直接参与编纂有关。基于这一事实,普通三年以后的编纂《文选》(注:关于《文选》的编纂时间,参见拙文《〈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萧统自然不会全由刘孝绰一人操作了。
与《古今诗苑英华》相反,萧统对《文选》表示极为满意,这从《文选序》可以看出。唐人元兢说:“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元兢这里首先提出《文选》是萧统与刘孝绰共同编纂的,与对《古今诗苑英华》的提法不同(颜延之、刘孝孙径提为刘孝绰所编),这也证明了萧统的确参加了《文选》的编纂。不过元兢说萧统和刘孝绰自称右以“毕乎天地,悬诸日月”并非事实,这本是《文选序》中话:“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明指周、孔之书,而非指《文选》。然细一想,唐人敢于把此语定为萧统对《文选》的评价,其潜意识中一定大量接受了萧统看重这部书的信息,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这一句话与《文选》联系起来了。那么萧统对这部书的满意主要指哪些方面呢?这当然与《文选》的最基本性质——作品选本有关。《文选序》说:“自姬汉以来,眇焉悠远,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很明显,《文选》不是一般的选本,而是在周秦以来将近千年的文章中选择出精华文萃,所谓“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应该是萧统的满意所在。与《古今诗苑英华》相比,萧统在编纂《文选》时,重新修改了体例,其中之一是将作家作品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它反映了萧统企图对前人文学进行总结的愿望(注:参见拙作《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文选》对《古今诗苑英华》体例加以修改的第二点,就是由单一的诗选变为赋、诗、文等符合文学内容的各体文选。就此说来,萧统的“遗恨”或许也含有对诗和文分开编集(萧统在天监年间集古今典诰文言编《正序》10卷,又集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古今诗苑英华》20卷)的不满,因为既是文学总结,当然不应限于诗,这样才更全面而具有权威性。要说明的是,萧统对《古今诗苑英华》虽然不满意,但并不否定,他编《文选》仍然让刘孝绰协助,便是明证。但《文选》从编辑宗旨到体例的许多变化,说明了他们文学思想的成熟过程。
《文选》编辑的基本思想,见于《文选序》,萧统在叙述了文学的由质及文的发展以后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这段话表明了萧统所持的进步的文学史观,这是他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关于《文选》的选录标准,一般认为是《文选序》所说“若夫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几句,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门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注:《揅经室三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朱自清先生据此说:“这样看来,‘沉思’、‘翰藻’可以说是昭明选录的标准了。”(注:《〈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国学季刊》6卷4期。)将“沉思”、“翰藻”理解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我以为是偏颇的。因为萧统这两句话本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等文体而言,若说它是《文选》选录标准的内容之一,是正确的,但决不就是这标准的全部内容。
《文选》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应该根据它收录作家作品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因为《文选序》的简单叙述还不能完全反映出萧统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文选》共收文体39类,主要分赋、诗、骚、文四部分。这四部分所掌握的体例却不一样,除骚收录《楚辞》以外,赋主要限在刘宋以前(唯一的例外是江淹,但他的两首作品《别》、《恨》二赋均作于刘宋末被黜为建安吴兴令时),似乎表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这一点与诗比较接近。诗的部分虽然收录了齐梁作品,但比重不大,也是详远而略近。文的部分相反,比较看重当代作品,表现出详远略近的特点。从收录作品看,赋的部分收录了先秦作家1人,作品4首;西汉作家4人,作品8首;东汉作家8人,作品12首;魏作家4人,作品4首;西晋作家7人,作品15首;东晋作家2人,作品2首;宋作家4人,作品5首;梁作家1人,作品2首。其中以先秦和东晋、梁最少,而以两汉和西晋最多,这个事实说明萧统对古代赋的评价明显高于近代。再看诗的情况,诗共收起汉迄梁155位诗人,339首诗歌,其中汉代7人,34首;建安7人,58首;正始3人,25首;西晋24人,126首;东晋4人,10首;宋11人,105首;齐3人,24首;梁6人,53首。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文选》收录西晋作家作品最多,其次为刘宋,再其次为建安。又根据作家入选作品的数量以及他们所占类别多少等综合考察,前10名分别为(1)陆机、(2)谢灵运、(3)曹植、(4)颜延之、(5)鲍照、(6)潘岳、左思、(7)谢脁、(8)王粲、(9)沈约、(10)陶渊明。这里前3名的顺序恰与上面三个阶段顺序相符,这不能说是巧合,只能说明晋、宋和建安时代的作家作品是受到萧统他们的高度评价的,代表了萧统文学集团在天监、普通年间的理想。至于代表着永明诗歌理想的作家沈约和谢脁,分别被排在第九位和第十位,这个事实反映了萧统对永明体的态度。与诗和赋不同,《文选》选文的体例比较注重当代。统计结果表明,《文选》共收录35种文体,76位作者,161篇文章(陆机《演连珠》50首按1首计算),其中先秦2位作家2篇作品,西汉14位作家26篇作品,东汉6位作家9篇作品,三国14位作家34编作品,西晋15位作家26篇作品,东晋5位作家6篇作品,宋7位作家18篇作品,齐4位作家7篇作品,梁7位作家29篇作品。从这个数字看,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宋、梁入选作品都不少,这个结果不能用详近或详远来概括。如果再仔细分析的话,这个“注重当代”其实是落实在任昉一个人身上的。我们替《文选》文类作
者排了一个座次表,除任昉居首外,另一位作者沈约仅居第四位,见表:
座次作家
一 任昉(9,17)
二 班固(5,7)、陆机(6,7)
三 曹植(3,5)、潘岳(2,5)、颜延之(4,5)、范晔(2,5)
四 司马相如(4,4)、陈琳(3,4)、曹丕(2,4)、应璩(1,4)、傅亮(2,4)、沈约(3,4)
五 刘彻(2,3)、扬雄(3,3)、吴质(2,3)、王融(2,3)、刘峻(2,3)
六 邹阳(1,2)、东方朔(2,2)、王褒(2,2)、贾谊(2,2)、蔡邕(1,2)、孔融(2,2)、阮籍(2,2)、嵇康(2,2)、干宝(1,2)、谢脁(2,2)、陆倕(1,2)
(注:括号中的数字,前者表示类数,后者表示作品数量。)
从此表可以看出,居前3位的作者,除任昉外都是汉、晋、宋作者,梁代其余作者均瞠乎其后,不可望任昉之项背。因此《文选》文类的注重当代,实际上仅重任昉一人。梁代作品一共入选29首,任昉一人独占17首;此外,他不仅入选作品多,而且所占的类别广泛,分布在九个类别中,其中有四个类别为他一人独占,即令、启、墓志、行状,这些都反映出编者对任昉在文学史中地位的肯定。任昉入选的比重远远超过了《文选》诗类对沈约诗歌的收录。在诗类中,沈约共入选13首,占五类,从入选的数量排位,沈约居第八位;从所占类别排位,沈约居第五位,在这两方面沈约都不如任昉在文类中处于第一的地位。这样说来,《文选》选文的注重当代,主要是为任昉所作的安排。这个现象说明任昉在天监年间对萧统文学集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沈约。
五
以上是天监、普通年间文学思想的大致情况,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以雍容温和为追求。从现存诗歌看萧统东宫学士中仍以刘孝绰、王筠、张率等存诗较多,其余如到洽、王规、王锡、张缵等人均存数首,这在南朝诗人中是很少见的了。甚至陆倕,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现存也仅有4首,而且也没有什么特色。他的写作恐怕还主要体现在骈文上,而这却是受任昉的影响。萧统身为太子,自为领袖,不仅文学思想的倡导是如此,创作上也完全符合他倡导的诗风。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萧统现存25首,其中《林下作妓诗》、《拟古诗》等,《玉台新咏》题作萧纲。徐陵是当时人,所说应当可信。而这两首又恰是萧统现存诗歌中仅有的艳体,这与他的立身行事和文学思想不相符合。当然,文学思想并不一定和创作实践一致,比如刘孝绰与萧统文学思想一致,但却写了不少艳体诗。不过以刘孝绰与萧统比较,刘孝绰的行为不很检点。普通六年(526)他受到到洽的弹劾,就被史书评为“中冓为尤,可谓人而无仪者矣”(《南史·刘勔传论》)。萧统的诗,规模较大,与新变体不同,显示了他作为储君的雍容风度。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搜辑,萧统现存诗有30首左右,大致可分为拟古乐府、咏物、酬赠以及佛会四类。前三类未见有什么特色,比较可读的倒是佛会一类。比如《和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诗》,这是一首颂诗,歌颂他的父亲梁武帝礼佛之事。据《建康实录》卷十七《武帝纪》,梁普通元年武帝置大爱敬寺,因此这诗当写于普通元年以后。全诗共四十句,记武帝游寺之事,气象氤氲,虽为颂诗,却规矩严整,颇具气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诗歌里,萧统写出了不少山水佳句。比如此诗的“丹藤绕垂干,绿竹荫清池。舒华匝长阪,好鸟鸣乔枝”,就非常清新。“舒华”两句化用了曹植的《公宴》诗“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诸句,比较成功。佛教与山水本来具有天然的联系,寺庙大都建于名山胜水之间,这也是南朝山水诗兴盛的原因之一。萧统性爱山水,如他在《钟山解讲诗》中所说“伊余爱丘壑”,但囿于身份,他只能在宫内和京内活动。他在《答晋安王书》中说:“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因此萧统的山水之游,主要集中在一些佛会活动上。除了这一首外,其它几首如《开善寺法会诗》、《同泰僧正讲诗》、《钟山解讲诗》、《玄圃讲诗》等,都有很精采的山水描写。如“落星埋远树,新雾起朝阳”(《开善寺法会诗》)、“涧斜日欲隐,烟生楼半藏”(同上)、“暾出岩隐光,月落林余影”(《钟山解讲诗》)、“霜流树条湿,林际素羽翾”(《玄圃讲诗》)等,写景状物都十分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句无论在声韵上,还是在辞藻上,都明显从永明体来,但由于放在长篇宏幅的佛会诗中,却显得淳厚而又有光泽,毕竟与永明体不同。萧统的这些诗大都写于天监末和普通年间(注:萧统的《玄圃讲诗》写于天监十七年,见萧子云《玄圃园讲赋》,《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九;《开善寺法会诗》、《钟山解讲诗》当写于普通三年以前,与梁武帝萧衍在开善寺讲经有关,武帝写有《述三教诗》一首,《广弘明集》卷第三十载有开善寺法师智藏和诗一首,智藏卒于普通三年,则此次活动在此之前无疑;又据《续高僧传》卷五《释智藏传》载,萧统礼敬智藏为师,曾游开善寺,赋诗而返,诗即《钟山解讲诗》,可知这两首诗都在普通三年以前。),正是他创作成熟期的作品,与他所倡导的文学思想是相符的。
就创作而论,这一集团的代表作家仍然是刘孝绰。刘孝绰名重当时,领导着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潮流。《梁书》本传说他每一文成,朝成暮遍,流闻异域;又说他与何逊齐名,时称“何、刘”。然刘孝绰仗气负才,多所凌忽,当时颇有地位的到洽、臧盾、沈僧杲等,都遭到他的轻视。而这三人受辱的原因,都出于与他同被主上恩遇的事实,由此可见刘孝绰是一个比较忌刻的人。基于此点,可知他对与何逊齐名会是多么地恼火,尤其这齐名还是“何”居“刘”前。因此,他不仅指摘何诗不成道理,而且在主持编纂《古今诗苑英华》时,仅收何逊两篇诗歌(见《颜氏家训·文章》)。不过从“何、刘”并称的现象,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事实:一、并称的时间当发生在二人为同事的时候,即天监十三年以后,二人同为安西安成王萧秀的幕僚之时;二、以刘孝绰与何逊并称,说明二人创作上的某些相近之处。刘孝绰今存诗约70首左右,大部分没有什么特色,与他当初的享名不太相符,但写于与何逊同时的几篇作品,包括与何逊的唱和之作,还是颇为可读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认为刘孝绰的作品没有特色,何逊的作品很有成就,这是我们的看法;事实上,刘孝绰在当时的影响却大于何逊,这说明刘孝绰的创作代表着天监、普通年间的诗歌理想。当时人对何逊的评价是“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颜氏家训·文章》)。这个“贫寒气”,既指内容上的叹卑嗟贫,也指诗风上的清巧。与何逊不同,刘孝绰尽管在用字遣词上颇为工整,但如“吾生弃武骑,高视独辞雄”(《答何记室诗》)的豪气,却是何诗所缺乏的。此外,刘孝绰诗宗古体,篇幅宏长,从容用笔,没有局促之感,这就是扬都论者所评“雍容”的具体内容。何逊的遭遇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的诗歌受到沈约、范云以及萧绎的称赞和喜爱,却不受“扬都论者”的好评,说明萧统和刘孝绰在天监、普通年间倡导的诗风确与永明体有一定的区别。
从以上所述看出,梁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是以萧统为中心形成了与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相区别的风貌。在文学思想上,他们提倡“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审美理想;在创作上,他们追求雍容闲和的诗风。这既与萧统本人思想、作风有关,也与天监、普通年间祥和太平的社会环境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作为这一集团文学主张的代表成果,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创作,而是以萧统署名编纂的三十卷本《文选》。公元531年,随着萧统的逝世,萧纲的入主东宫,这一集团所提倡的文学主张,立刻受到了以萧纲为中心新的文学集团的批评。新文学集团推选的宫体诗风成为当日文坛的主流,而且作为这一集团文学主张的旗帜,也同时作为与《文选》的对立,萧纲授命徐陵编纂了《玉台新咏》。这样,兄弟二人编于不同时期、代表不同文学主张的两部总集,实际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内容,这应是我们研究两部总集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