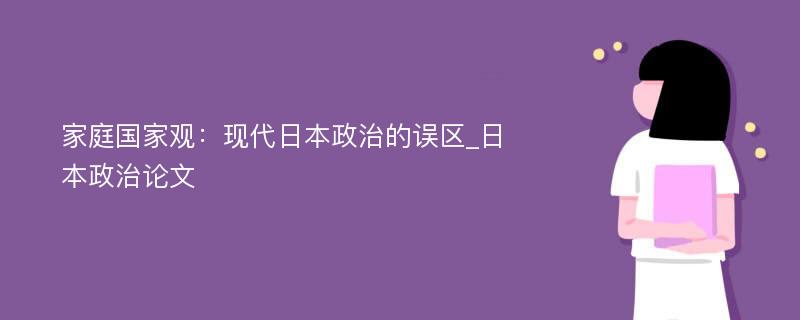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误区论文,家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利用了日本人在传统家族制度下养成的唯命是从的精神,驱使他们狂热地支持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和损失,也使日本民族几近毁灭。家族国家观及其实践实为近代日本政治的一大误区。
一、家族国家观的形成
家族国家观是日本近代的一种复古的社会思潮,是力图使天皇统治永久合法化的政治理念。早在幕末时期,就已出现了家族国家观的萌芽,一些主张“尊王攘夷”的后期水户学派学者宣扬“一君万民”的观点,提出“夫君臣者,父子也,天伦之最大者”。这一理论不仅对幕末的维新志士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近代以后家族国家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在维新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以天皇制国家对农民进行掠夺为基础、以保护特权商人和寄生地主的利益为前提的,因而,许多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立,都体现了新与旧、传统与近代文明的妥协。尤其是在政治结构上,实现了后期水户学派“一君万民”的政治构想,建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万世一系”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由《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明治民法》所构筑的日本近代国家,一方面呈现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貌,一方面保留了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封建遗制,因此有人称近代以来的日本是“家制立宪君主国家”。维新后不久,“文明开化”运动使西方近代思想如潮水般涌入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直接危及天皇的统治,明治政权执政者们为此大伤脑筋。在采取武力镇压的种种措施的同时,执政者们逐步认识到,仅仅用露骨的专制主义来强迫人们为国家尽忠和牺牲,未必能使人自发地服从,甚至还会引起反感。因此,在对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进行反思后,执政者经过谨慎的选择,终于从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的角度上,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已经明显贯穿了家族国家观的思想,敕语中将以“孝父母”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条规范作为“皇祖皇宗之遗训”,要求“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以达到“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最终目的。
《教育敕语》颁布后,哲学界权威、曾经留学德国的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受文部大臣的委托,撰写《敕语衍义》。在这部经过天皇内览、颇具权威性和正统性的敕语注释书中,并上哲次郎综合德国国家主义理论与日本的儒教传统,对《教育敕语》进行解释,指出敕语是由“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这两个要素构成的,“盖敕语之主意,在于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心,备不虞之变”[①a]。书中明确提出了家族国家观的思想,“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为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故我天皇陛下对全国呼唤尔臣民,则臣民皆应以子孙对严父慈母之心谨听感佩”[②a]。在这里,井上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孙的关系,将家作为国的基础,即家是一国之本。井上哲次郎又在1912年出版的《国民道德概论》一书中将他的家族国家观进一步系统化,提出“综合家族制度”和“个别家族制度”。他指出,日本家族制度的特色就是“综合家族制度”(也即把国家整体作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在“综合家族制度”下,把出自“个别家族制度”的孝的伦理推而广之,就成为“综合家族制度”中忠君的伦理。正因为日本有综合家族制度,才能实现孝与忠的完全统一,才有“通古今而不变的国体”。这就是井上哲次郎的家族国家观的基本思想,其中融合了日本传统家族道德、儒家的忠孝之道、天皇万世一系的神道思想和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观念,构成了“忠君爱国”的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忠孝一本”的国民道德论。
在井上哲次郎从道德方面宣扬家族国家观的同时,另一家族国家观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穗积八束也在从法律方面为把家庭作为服从意识的培养源、为家族国家体制的确立而努力。穗积八束是一个十足的国体论者和尊皇论者,在明治民法论争中,用家族国家观的理论攻击1890年公布的、稍有个人本位倾向的明治旧民法,提出“家之扩大成国,国之缩小成家”、“法制之源在家”的理论,力图利用日本家族制度中祖先崇拜的传统,以“祖先的威灵”为媒介,谋求家与国、臣与君之间的整合。不难看出,穗积八束所构筑的家族国家的模式是以家为国体和法律的基础,把在家庭中养成的最原始、最自然的“服从”这一“人道之教”,通过“祖先教”的纽带,发展成为国民的道德,使个人、家庭、国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孝悌的家庭成员”→“有用的自治公民”→“忠良的国家臣民”的国民道德的自觉升华,其国家理论和法的理论充满道德伦理的色彩。
自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经过天皇制政权的大力宣传,尤其是经过中小学修身教育的彻底贯彻,逐渐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当中。
二、家族国家观的极端发展
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显现了家族国家观的巨大威力。进入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为了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实现长期以来对外扩张的梦想,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蹂躏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同时,也将日本国民施上战车。在战争体制下,国家要求国民彻底抛弃个人的自由,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制统治。这了使这种体制正当化,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对家族国家观的宣传和鼓吹愈演愈烈。
1937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文部省思想局为强化国民思想统制,进行战争动员,发布了《国体之本义》;1941年文部省教育局广泛发行了堪称《国体之本义》之姊妹篇的小册子《臣民之道》;1942年,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又发表了《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在这些出版物当中,极力鼓吹家族国家是国体的精华,“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永远进行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而基于此大义,以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克忠克孝之美德,则是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是我国永远不变之大本”[①b];宣扬“所谓日本是家族国家,并非把家集中起来形成国家,而是国就是家,各个家族作为国之本而存在”[②b];强调天皇与国民是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和家族父子关系,“我国是奉皇室为宗家,古往今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君臣一体的大家族国家”,“皇室是臣民的宗家,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臣民以对祖先之敬慕之情崇奉祖先之皇室”,天皇与臣民的关系“义为君臣,情为父子”[③b]。法西斯军国主义者进行这些宣传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国民恪守“臣民之道”,就是要忠君爱国,舍我去私。这样,国民生活皆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服务于战争。《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被作为家族国家观的经典。如果说在此之前家族国家观是由官僚、学者积极提倡,并适应了天皇制统制,从而成为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念的话,这三种出版物所反映出的家庭国家观则完全是国家战时国民动员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战时国民思想统治的工具,经过国家舆论的广泛宣传,比过去井上哲次郎、穗积八束等人的鼓吹更直接,更露骨,影响也更广。这些出版物的发行表明,家族国家观已经由在意识形态领域教化国民的需要发展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并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中枢的位置。
自此以后,为了控制国民和进行战争动员,军国主义政权又接二连三地发布“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各种训令,令国民反复诵读,严格遵守,全社会都弥漫着家族国家的气氛,家族国家观被发展到极致。曾经有人撰文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认识到作为家族国家之家庭的伟大力量,作为陛下的赤子而生,被历代天皇之仁慈养育的日本人,只要不是持有极其错误的思想和不纯感情的人,都会自然地把日本人的思亲爱子的感情与思国爱国的感情联系起来,思家之心越深,当然爱国之情越甚,所以对如何喜欢疼爱的孩子,一旦应征,都能祝贺并鼓励之,并高高兴兴把他送上战场。只有作为家族国家的家庭,才能在世界各国的家庭中产生如此真正的模范,在感谢的同时痛感日本的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①c]这是当时日本人心态的真实反映。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人们将天皇奉为神和父亲,只要是天皇的诏敕和来自军国主义政权的声音,人们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服从与支持。当无数青年男子怀着忠君爱国的狂热在战场上虐杀、残害他国人民的时候,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动员了全国2000万妇女及其家庭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支援战争,承担后方生产的重担,连结婚、生育都被赋予“报国”的使命。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在战败前提出“一亿总动员”,“一亿玉碎”口号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家族国家观把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功能运用于国家政治,将家族道德作为促进国民认同国家权力的媒介和手段,使家族不仅仅作为血缘的关系而存在,还作为具有国家的政治关系、国家的伦理道德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法律关系而存在,位于这种种关系之顶端的就是集父权、君权、神权于一身的天皇。虽然家族国家观的论点未明文写进近代法律条文之中,却以伦理道德的体系确立了天皇的权威,使法律成为道德的一部分。家族国家观不过是天皇万世一系之国体观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大杂烩,其核心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天皇制统治和推行对外侵略政策。本来,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传统家族的本来面貌在迅速消失,在这种形势下,家族国家观反而甚嚣尘上,极大地毒害了日本人的思想,造成几代日本人的悲剧。
三、家族国家观与对外侵略战争
家族国家观是被蒙上家族外衣的、狭隘的国家至上的国家伦理观,在被运用于教化民众、维护天皇制统治的同时,也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作为侵略他国的理由和依据,不仅置其他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也将本民族的前途孤注一掷。
军队是侵略战争的急先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模仿欧美先进军事制度和军事科学技术建立了近代军事体系,而封建制度的残余与近代教育在思想教化方面的“成功”结合,造成了一支忠实于天皇的军队。军队被称作“皇军”,军人们头脑中被灌输的是封建时代武士的效忠精神。1878年,曾致力于日本近代军事改革的山县友朋发布《军人训诫》,声称“今日之军人,纵非世袭,亦与武士无异,故应遵循武门之习,效忠我大元帅皇上,报效国家。”《军人训诫》中还把“忠实”、“勇敢”、“服从”三点作为“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不难看出,近代国家的军队与天皇专制政权的关系和封建武士与领主的关系实际上如出一辙。在1882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军队世世由天皇统率”,要求军人绝对效忠天皇。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家族国家观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酿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就了无数愚昧无知的军人。他们只知效忠天皇,忠君爱国的狂热代替了理性,许多人都是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②c]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才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创造并推行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所谓“肉弹战术”、“沉船堵口”、“特攻战术”,这些曾为日本军人引为自豪的疯狂至极、惨无人道的战术夺去了无数日本军人的生命,把日本国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为了培养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行质素的军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完成了一项在世界军事史上标新立异的创造——将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导入近代军队的内部管理。1889年监军部(1887年成立,后改为教育总监部)发布监军训令第1号,指出“军纪恰如小儿之家庭教育,使其发育德育之心,在军队中也应形成此种家庭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教育敕语》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最高准则,以及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的家族国家的氛围,军队也成为贯彻家族国家观的重要一环,“军队家庭主义”开始流行。在1908年颁布的“军队内务令”中,明确提出“兵营乃共苦乐、同生死之军人的家庭”,“兵营生活为一大家庭,于融融和乐之间巩固全队一致团结、士气旺盛,勤劳于军务,上下敬爱,缓急相救,有事之日欣然而起,乐于为国事献身”[③c],将家族国家观与军队的教育训练结合起来。1912年,当时担任步兵第三联队长的田中义—率先在其部队搞起了旨在“兵营生活家庭化”的“改革”。按照田中义一的观点,“中队长是严父,中队附下士是慈母,内务班的上等兵是兄长,中队内的气氛若无家庭之温情味,就不能涵养真正的军纪”[①d]。这种“家庭化”的兵营生活很快在军队内得到推广,“严父慈母”也成了在军队内流行的口号,“军队家庭主义”从此成为日本军队的一大特征。
所谓“军队家庭主义”,就是运用家族伦理中的等级观念和孝与服从的伦理来维持军队内部的秩序,以培养军人的服从精神。而实际上,“军队家庭主义”只不过是掩盖军队内强制、暴力、惩罚的一个温情脉脉的光环,是暴力、惩罚合法化的代名词。有人甚至公开主张“作为家庭之父母的将校下士勉黾努力,借惩罚之威力改悛兵卒,以图治理中队家庭”[②d]。在“军队家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军人的尽忠节的本分、无条件服从的精神与封建家长制度、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及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混杂在一起,使日本军队的生活变得极其残酷与野蛮。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都有家长般的绝对权威,任何一点口实都会招致“违反军纪”的罪名而遭到辱骂、体罚。军队内的暴力行为不仅在“部下服从其上级不论何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这一铁的原则下被合法化,而且被所谓“军队家族主义”合理化,兵营因此被称作是“不可想象的、充满恐怖的、阴暗的精神世界”[③d]。由此可见,“军队家庭主义”无非是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对天皇的效忠一体化,通过残酷对待部下而培养造就出无数“虐待狂”式的法西斯军人。一到战时,这些军人就立即将平素所受的压抑转化成凶猛无比的战斗力,向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发泄,变成灭绝人性的、残暴无比的破坏行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在疯狂性、野蛮性、残暴性方面比起西方老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
家族国家观就是承认将公共权力扩大延伸到私人领域,那么,通过这条延长线,公共权力可以无限制地延伸到任何领域。因而,家族国家观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内维护天皇专制统治的舆论工具,而且被用于对外侵略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八纮一宇”(即天下一家之意)的口号,梦想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当时外务省的代言人在解释这一口号时,大谈日本的家族国家观,宣扬在共荣圈中,“以日本为本家是当然的”。日本的统治者还宣扬日本民族建设“共荣圈”的真正使命“不仅是大东亚现状的建设,还在于继承永远的家业,使其达于子子孙孙,使万世不朽的文化在大东亚全域内生生发展”。因此,他们要求日本人在“共荣圈”中发扬家族传统中祖先崇拜的精神,“继承祖先的遗业,把祖先之灵移至大陆崇敬之,誓在大陆从事大业”[④d],“坚持以‘家’为中心,在其土地上深深扎根”[⑤d]。这样,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被正当化,横行霸道、烧杀抢掠被说成是“爱的实践”,是“道义的普照”。比如,在侵华战争中一手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还在狡辩:“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本是‘亚洲一家’之内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人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⑥d]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以“家长”的姿态对“不服管教”的“子女”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仅中国就有数千万人丧失了生命。日本侵略者还以“本家”的身份大肆掠夺亚洲各国的资源,在语言、民族、宗教等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推行奴化政策。他们在被剥夺了主权的朝鲜实行“皇国臣民化”,逼迫与日本同样拥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朝鲜人“创氏改名”,此举意味着用以氏为中心的日本式家族制度取代以姓为中心的朝鲜家族制度,对朝鲜人是极大的侮辱。在菲律宾,“他们说菲律宾人是他们的兄弟”,但是他们疯狂地掠夺这个国家,强迫男人为日军劳动,女人遭其凌辱,许多无辜百姓惨遭屠杀,死者逾百万。在印度尼西亚,所有日本人都被称为“日本主人”,仅被“主人”强制抓走的劳工就死亡约200万人。这些事实无不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所鼓吹的家族国家观是地地道道的强盗的逻辑。
注释:
①a 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见《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1卷,《明治思想集》第2卷,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86页。
②a 同上,第91页。
①b 《国体之本义》,《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昭和31年版,第7卷360页。
②b 《家族制度》,《日本妇人问题资料集成》,家庭出版社昭和51年版,第5卷174页。
③b 《国体之本义》,《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第7卷373、377页。
①c 羽仁本子:《今日日本家族家庭的最高使命》,《妇人之友》1943年10月号。
②c 长岭秀雄:《日本军人的生死观》,原书房1982年出版,第159、175页。
③c 《军队内务令》,载《作战要务令·军队内务令·战阵训》,日本文艺社昭和37年版,第1~4页。
①d 《明治百年史丛书·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年版,第374页。
②d 武章生:《理想的军队家庭》,转引自藤原彰《天皇制与军队》第92页。
③d 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第90页。
④d 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从海外邦人言行看国民教育资料》,载《十五年战争极密资料集》,不二出版社昭和15年版,第182页。
⑤d 大政翼赞会调查会第五委员会:《关于[家]的调查报告书》,《资料·日本现代史·12·大政翼赞会》,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572页。
⑥d 田中正明:《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芙蓉书房昭和60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