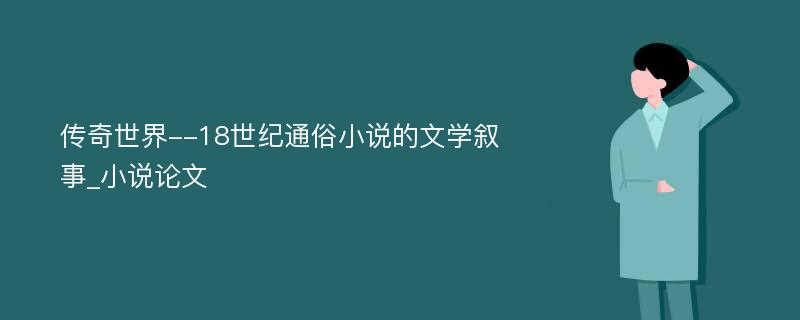
传奇的世界——18世纪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通俗论文,传奇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3)01-0135-05
18世纪,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给通俗小说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在对劝惩说、史鉴说的扬弃中,通俗小说抒情说逐渐成熟,通俗小说可以抒怀,可以“解胸中之闲垢”,与诗文同样为发愤之所作,因而也就同为立言之一种,同样可以传之后世以至不朽。创作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关注焦点的变化,从对外在社会现实的热情关注转向个人情怀、社会人生观感的抒写。而最深刻也最曲折的变化是叙事方式方法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创作观念,与小说的关注焦点息息相关,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蕴涵了18世纪的时代文化内涵。所有这些在内在精神上相通的通俗小说形成一个群体,被有的学者称为文人小说(注:关于“文人小说”,可以参考郑振铎《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4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屈小玲《清代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见《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而这些文人小说所采用的叙事方式方法也就可以称为文人化的叙事。
一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书坊商业性运作的操纵,个人情怀的抒写成为书斋化创作的核心。18世纪文人小说家更直接地借鉴话本体制,让叙述者更明显地介入小说世界,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以达到充分抒写自我的目的。与自我表现相关的是文人小说对人物形象的重视,有限的小说世界中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虽然不能说这些小说中的文人主人公就是现实中文人小说家的化身,但无疑这些倾注了小说家全力的形象身上寄托了他们的人生情怀,作家将自己的才华和学识交给了这些前无范例的完全虚构的人物,自己在现实中没有实现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由小说中的文人英雄们在虚拟世界中付诸实践。虚拟的人物、虚构的情节,决定了这些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传奇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是值得怀疑的,除了最基本的封建伦理准则——而这一点又不具有时代性,其他的如权奸误国、外敌入侵、爱情追寻等等都是缺少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情节要素,任何从中探求具体的时代信息的做法可能都是徒劳的,甚至包括像《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被一般的研究者认为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通俗小说,象征性的时空一方面使得这些小说获得了超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其历史、时代色彩变得淡薄。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通俗故事和历史演义中,历史演义在18世纪迅速衰退,一方面是对前代历史演义的改编和填充,另一方面则演变为“说唐”、“说宋”等一系列准历史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历史的中心由王朝的更替一改而为英雄家族的光荣史,权奸与忠臣的家事纠葛成为决定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和核心,历史在这些小说中被随意改造,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在文人小说中,历史退到了更靠后的位置,历史题材只有作为个人表现的材料时,才被文人小说家所接纳,历史被镶嵌在主人公的生活系列之上,甚至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比较典型的如《野叟曝言》,小说以明代成化年间为背景,对照真实的历史,就可以感到作者在有意识地改动历史来为主人公创造施展抱负的机会,因为作者对明代的历史很熟悉,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一介书生而拯救整个王朝和国家,有点像无稽的神话。相似的还有《绿野仙踪》,以明代嘉靖年间为虚拟的背景,主人公冷于冰成仙道路上的大功德之一是与奸相严嵩父子的斗争,还有对平叛、抗倭战争的参与,虽然一些人物形象的姓名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相同,但其事迹与历史相差甚远。再如,《蝴蝶缘》的开头说明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隋朝仁寿年间,但真正的故事与隋朝的历史事实几乎没有关系,直到临近结尾处,主人公蒋青岩才由一封信中得知朝廷的变故,韩擒虎战死,杨广篡位,奸邪横行,王朝濒临灭亡的边沿,在这样的情势下,蒋青岩和他的妻子、朋友决定隐居苎萝山。另外,如《快士传》中的明代宣德年间,《梦中缘》中的明代正德年间,《飞花艳想》中的明朝嘉靖年间,《二度梅》中的唐代肃宗时候,如此等等,历史虚化为一个年号,或者退为遥远的背景。至于《终须梦》将时间泛指为皇明,《凤凰池》只说是前朝,《水石缘》更完全隐藏了故事的历史背景,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所说,“问其年,年不知”。
不是将人物放到历史背景上塑造,而是让历史虚拟化来迁就英雄人物的事业,这正是文人小说和讲史故事的不同之处。这些小说中没有真正的历史时间,虽然其中常常充满了时间的概念。也正因为此,18世纪的文人小说与历史演义小说的时空有着本质的区别,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将绝对的过去作为描写的对象,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18世纪的文人小说则将描写的重心放在为着未来的现世,所有的叙述都围绕着还没有实现的胸中情怀,不是面向永恒,不是为了未来的回忆,而是为了当下的表现。
18世纪文人小说的时间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的长度与完整性问题。大团圆的结局向来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的特点之一,关于这种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文化根源和内涵,已经有很多人撰文论述过,作为优点或者作为不足。几乎所有的叙事作品都企图叙述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一生,结尾不留任何悬念,即使在小说的中间,叙述者也是常常忍不住很快将谜底揭出。这种不留余韵的做法,实际上体现了人本位思想,是对人生完满性的追求,也是小说以人物为线索组织情节、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必然结果。18世纪文人小说与此前的通俗小说和其他叙事作品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在这些小说中,一开始总要先交代主人公的出生和少年时代,在小说的结尾则是对主人公结局的概括性的叙述。《野叟曝言》的开头介绍了文素臣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母亲及儒教世家,文素臣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决定了他的人生志向,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文素臣的结果甚至他的后代的情况都作了交代,所谓的寿至百岁,六世同梦,万载常青,如此完满的结局使得任何形式的续作都非常困难。《驻春园小史》中的主人公黄玉史经过一番努力,得与心上人完婚,官至礼部,夫妇偕老。《终须梦》一开始叙述男女主人公父辈的交往,关于他们出生的预言,男主人公童年的教育和初显的聪慧才华,如此等等,在小说的结束处主人公蔡梦鹤荣归故里,夫唱妇随,优游卒岁,所谓“乐夫天命于无穷”。《梦中缘》从主人公吴瑞生的出生写到其后世子孙的繁衍绳绳振振,科甲不绝。《飞花艳想》在最后结尾处交代柳友梅五子登科甲,夫妇五人享受了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成为千古佳话。例外的只有《蝴蝶缘》、《蜃楼志》等几部小说,在《蝴蝶缘》的结尾处,主人公蒋青岩和妻子、朋友不知移居何处,最后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蜃楼志》的结尾,小说中惟一的文人李匠山告辞而去,留下了袅袅余音。
但是一生的描述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主人公成熟前的经历和理想实现后的生活,都只是极为简略的概述,是所谓的鸡头蛇尾,小说的绝对重心放在主人公的漫游上。当文素臣、冷于冰、黄玉史、黄逢玉、蔡梦鹤、蒋青岩等文人主人公步出家门,踏上追寻之路时,正常的时间流程突然被打断,在小说中虽然充满了时间概念,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但主人公似乎活动在时间流之外。比如《野叟曝言》中,朝廷和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酝酿了十几年的篡夺阴谋被粉碎,赤身峒的叛乱用多年时间才平定,还有剿平倭寇的战争,文素臣的儿孙们迅速长大,很快就能东争西战,建功立勋,而文素臣依然身体健壮,精神如昔,头脑敏锐依旧,在小说的最后一回,才交代了文素臣和他的母亲、妻子年岁的增长,文素臣突然之间就衰老了。在半神怪的《绿野仙踪》中,当温如玉经历人生的重大变故,沉溺于充满势利的温柔之乡而不能自拔时,当周琏与齐惠娘为肉欲之情而如痴如醉的时候,时间暂时陷入了停顿。这种半神话式的时间,在《希夷梦》中得到了更形象的表现,韩速和仲卿在华山希夷洞中入梦,到了浮石岛国,在岛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从梦中醒来时,已经是满头华发,而现实中的时间也才只是一瞬,当二人重游岛国,却又发现岛国功勋并非只是梦幻。这种百年一瞬的思想,并非只表现在神话小说中,在世情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时间词语就是“转瞬”、“转眼”、“不知不觉”,几个月、一年甚至数年常常被一笔带过,而实际上时间的变化也确实没有在小说人物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因为结束漫游生活的主人公往往还是年轻美貌依然。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时间观念,是因为文人小说采用的是传奇时间。这种传奇性的时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时间,是一些日子、时辰、瞬间的简单化的排列,虽然不能说这些时间序列可以随意改动,但是局部的时间顺序的改变对小说的主旨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确实造不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些时间可以说是没有内在限制的。不仅像《绿野仙踪》中温如玉、周琏的插曲可以移动到小说情节序列的其他位置,即是救助连城璧,金不换的觉悟,平定大盗师尚诏,抵抗倭寇入侵,赈济灾荒等等情节片段,在小说时间序列中的先后排列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像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完整的有机整体,在18世纪的通俗小说中仍然很少存在。再如《儒林外史》的前半部分,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没有很强的规定性。也许可以举出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红楼梦》的多线型结构,使人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不可作任何移易的有机整体,确实它的整体框架不能改动,贾府衰败的过程不能倒置,但除此以外,一次次的饮宴和节日庆典,一次次的诗会,都是以没有历史限定性的春夏秋冬和一年又一年、一天复一天的时间来描述,由于描写的地点限定在有限的空间,时间特别是季节的循环就显得特别突出,这种时间可以称为田园诗时间。在大多数漫游形式的小说中,时间的可移易性更为突出。小说主体部分的时间,比起开头和结尾交代的时间,实际上只可以说是一瞬或者很短的、其长度常常可忽略的时间段落,模糊的时间概念又使得这种时间难以捉摸,这些时间常常是不被计入主人公的年岁的,如《梦中缘》中的金御史休秩在家过了将近十年,翠娟小姐被贼人劫去了将近十年,而这漫长的岁月没有在女主人公的身上留下哪怕一点点的痕迹。而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极短的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决定了主人公的整个生活,也是作者要通过小说主人公表现的现实中的自己所渴望发生的变化。小说以主人公离开家庭开始,以回到家庭或者建立新的家庭结束,填充在这两点之间的是主人公的传奇性的漫游和追寻,是近于超时间的空白。
同样充满小说世界的是空间概念。比起这些小说中时间序列的可易性,空间上的可变性更为明显,故事发生在此地和移动到彼地并没有大的区别。比如《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在杭州斗孽龙、救弱女,在江西得重病,在京师进谏而被放逐,在往辽东的途中挫败叛党的暗杀阴谋、得知奸党的篡夺计划,在南昌救济遭受灾荒的百姓,在山东除掉景王的死党李又全,在广西平定赤身峒的叛乱,如此等等,这些事件和地点的联系本身就是松散的,空间的时间含义在这里完全缺如(注:这种缺乏有机统一性的现象,被浦安迪称为“缀段性”,他认为这是明清章回小说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参见其《中国叙事学》第56-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像《终须梦》、《玉蟾记》、《梦中缘》、《快士传》、《水石缘》等小说中,主人公更是信步走来,没有任何预先想好的计划,风物和事件有纷至沓来的感觉。时间和空间常常是擦肩而过,如果不是作者用心为二者安排了接触的机会,哪怕是抽象的机械的接触,这就是18世纪文人小说采用最多的道路和园林庭院两种意象或者说时空体。道路在小说中并没有具体的描述,但它连接着主人公活动的一个个点,相对于水路、旱路等具体的形象,抽象意义上的道路在小说中有着更大的意义,它与小说的追寻主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连接的不是一个个驿站和城镇,而是一个个目标,漫游的路途实际上是精神的历险。文素臣消灭了灭佛兴儒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越来越接近他的伟大事业的顶峰;冷于冰在修行的道路上每迈一步,离天庭仙班的距离就缩短了一步;蔡梦鹤、董闻、柳友梅等人的目标是显示才华、进入仕途、成就业绩、夫妇团圆、家庭美满、优游余生,这些目标作为他们追寻道路上的一个个点,一步步地得以实现。另一个时空体是园林庭院,这里是人物活动最集中的场所,不仅几乎所有才子佳人的密期幽约都在这里发生,甚至惩奸除恶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与道路相比,这里是时间、空间最接近的地方,迅速流动的时间在这里缓慢下来,场景得到初步的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人工的园林庭院相比,在18世纪的通俗小说中自然景物无法构成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背景,风景描写只是一些极为零碎的片段,可有可无的点缀,小说人物只是偶尔一瞥之,人物和自然之间缺少真正的交流。像《绿野仙踪》中的修炼在深山中进行,因而对山野风景作了稍微多一点的描写,但这些风景是作为人物的对立面来描写的,是不得不忍受的修行的考验或者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毫无感情色彩的静物。在大多数小说中,人物在园林、庭院、寺庙等建筑或者人工风景中活动,而这些建筑和人工风景也仅仅是提供一个活动的地点而已;虽然园林庭院的布局常常被不厌其烦地描写,但实际上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表现几乎没有贡献[8],如《红楼梦》和在一定程度上为它提供了范例的《金瓶梅》一样,对庭院建筑布局的描写,除了增加小说故事的真实性,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为建筑史提供材料了。作为精神外射的人物居所,在18世纪的文人小说中依然很少见到,像《红楼梦》大观园中各个女子的住所表现了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可能要算特例。通俗小说中的这种情况与前代诗文理论和创作中对大自然的关注和对情景交融、人与自然交流的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当与通俗小说创作和传播的环境有关。通俗小说创作最风行的时候,城镇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囿于城镇一隅的人,与自然的交流已经非常困难,而且18世纪文人小说中拥塞的人物把自然风景挤到了小说世界的一角,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小说人物的身上[7]。
使时间和空间接触交融,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时空体,以寄寓作家的文化人生感悟的成功范例,是18世纪的两部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将时空的主题表达深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泰伯祠和大观园这两个时空体意象不仅是两部小说主旨的集中体现,甚至成为两种文化人生的象征。泰伯祠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大观园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儒林外史》是对社会文化、对文运和士人命运的反思,泰伯祠表现了作者积极有为的济世态度,所以作者的感伤是济世努力失败后的无可奈何的感伤;而《红楼梦》的作者一开始就表现了对现实的逃避,大观园是作者精心营造的心灵逃避所,他的感伤是逃无可逃的感伤。这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虽然不能以优劣来衡量这两种态度。《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可以说是从精神上说的两种文人小说的代表,而泰伯祠和大观园也可以说代表了18世纪文人的两种精神世界[6]。
二
有必要谈谈18世纪文人小说的漫游模式,因为漫游模式是空间位移在小说结构形式上的体现。18世纪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很大一部分似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漫游模式来构造小说的情节,常常以一人为主线,将散漫的情节串连起来,这些情节由于地点的频繁变动缺乏集中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让我们联想到15至18世纪欧美的流浪汉小说及其他漫游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旅途上漂泊冒险,由蜿蜒曲折的道路连缀起来的驿站和旅店,是他们演出人生戏剧的舞台,一幕幕人生短剧,由漫游者联系成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人生之旅。但是中国18世纪的漫游小说与欧美的流浪汉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18世纪的漫游小说没有欧美流浪汉小说的广阔空间感和开放性的结构,有着完全不同的主人公,旅游的动机、方式不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18世纪通俗小说中的文人主人公不再是萎萎缩缩的小人物,他们不再将科举功名作为毕生追求的唯一事业,他们一方面希望人生的舒适,另一方面渴望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济世的抱负。在赞扬文人的同时,这些小说对轻视暂时贫困的才子,陷害文人主人公,阻挠文人主人公实现济世抱负的势利小人或奸臣贼子,给予严厉的惩罚。可以说,这是一种文人情结,文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些文人形象皆出自虚构,而虚构的目的则是借以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些文人形象肩负着文人小说家赋予他们的使命,踏上了漫游之途。
18世纪通俗小说中文人漫游的最初动机各种各样,或寻找佳人,追求美满姻缘,如《蝴蝶梦》、《水石缘》;或为避难而被迫出游,如《五凤吟》、《小野催晓梦》、《雪月梅传》、《希夷梦》;或是为了功名和事业,如《快士传》、《幻中真》;或是参透世事,对尘世功名心灰意冷,因而离家出游,或散心,或求道,或出家,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路》……但大多数文人主人公都一改最初的出游动机,将全部身心投入济世事业,如《水石缘》中的文人主人公石生与挚友设谋大败为乱之木客;《五凤吟》中的祝琪生率军出征,建立功勋;《雪月梅传》中岑秀以文官而兼武职,平定倭寇,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快士传》中的董闻消弥了中华与华光国之间的血雨腥风之战;《岭南逸史》中的黄逢玉,诛灭了叛乱的强盗,被封为安东侯。济世的理想主义支持他们不辞艰辛、无所畏惧地漫游于险情四伏的征途,深山丛林、强盗窃贼、恶棍无赖、忘恩负义、诬陷监禁……
采用漫游模式组织小说情节,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这类小说以叙述故事为主,着重的是人物行动、事件发展的客观过程,而不是行动的人,给人的印象,人物只是各种事件的串连者,把松散的故事连接在一起,这就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模糊,叙述者的讲述成了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包括主人公在内的许多人物都是受·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另一方面,虽然作家尽力将故事通过主人公贯穿起来,又努力运用伏笔、照应、草蛇灰线等等技巧使小说显得紧凑,但许多节外生枝的情节仍使许多这类小说显得散漫。许多文人虽然注意到了这种结构模式带来的一些问题,但还是采用了这种模式。这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传统和特点有关,也与现实生活中的文人漫游相关,更体现了文人在精神世界中的探索与追求。
以人物漫游为题材的小说,并非至18世纪才出现。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即有描写人物漫游奇遇的篇目,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传奇小说无法写出人物漫长曲折的旅程,而且游历在这些小说中并非主要部分,常常只是引出主要场景的引子。明代也有不少游历模式结构的通俗小说,如《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咒枣记》、《飞剑记》都是以人物的游历串连起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降魔除妖故事,但这些游历模式的小说毕竟只占极少的部分,而且主人公皆非书生,求道求经的题材与游历模式也是自然吻合。18世纪漫游模式的小说数量众多,漫游者都是文人主人公,漫游故事皆出自虚拟,漫游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经求道,而是出于尘世的动机。
18世纪的文人小说采用这种模式,应与小说家对小说结构艺术的探索有关。虽然明代即有不少长篇小说产生,但这些小说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虽有作家的创造性参与,但无疑结构问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文人大规模地参与通俗小说创作是在明末清初,而最受欢迎的体裁是短篇小说或曰话本小说。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短小,结构很容易驾驭,不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如由短篇转而创作长篇,结构问题即不可回避。18世纪的文人游历小说带有文人小说家的探索痕迹,虽然他们运用了穿插、照应等手法,话本小说的痕迹仍很明显,一是主体情节单一,近于单篇话本,似乎由话本故事扩展而成,属单线结构;二是这些小说由主人公将一些散漫的故事串联起来,又常常在主体情节之外,穿插一些相对独立的故事。一时一地发生的故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情节单元,不同的情节单元由一个人物联系起来,这种多场景的组合类似于传奇剧的出与出的连接,一生一旦串联起相对独立的各出。如《绿野仙踪》第一至十回写冷于冰得法术前的遭遇,等十一、十二回写冷于冰于湖南安仁县小试法术,第十三至十五回写连城璧故事,第十七至十九回写朱文炜故事,第三十至三十五回征大盗师尚诏,第四十七至六十回写温如玉和金钟儿故事,第七十九至八十九回写周琏和齐惠娘故事,而主人公冷于冰穿插其间,把这些故事串连起来。这种段落式的组合,类似于有的学者所称的“奇书文体”。
除了情节结构上的原因,文人小说家采用这种模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文人壮游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在那个诸侯割据称霸的年代,文人学士奔走于各政权之间,推广自己的王道霸术。由两汉至唐末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宽松,幕府辟召兴盛,文人学士不辞艰辛,游历各地幕府,寻求赏识自己才学的幕主。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幕府权力的衰弱,文人游幕之风渐稀,虽然仍有不少文人为求学或参加科考出家远游,也有少数文人为饱览山河风光而游历山川,但比起前后时期,文人游历现象不很突出。明清易代,许多汉族士人被抛出传统轨道,他们为了生计或其他目的,游历各地,寻找机会,至康熙时学者们纷纷加入到游幕者行列中,游幕之风再一次兴盛。而游幕之风的盛行是在18世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无数文人奔走各地,为幕主从事各种学术活动或助理公务,也有无数的士人为科考而奔波。18世纪的文人漫游之盛前所未有,给这一个世纪的社会文化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单就学者游幕来说,据《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史列传》所记学者生平,曾游幕者占将近百分之四十。文人学士漫游盛行的原因有多种,一是交通便利给他们提供了旅行的方便;二是乡试、会试等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他们不得不离家远游;幕府的增加,对学术文化的重视是学人游历的重要原因。
从文人角度讲,漫游则包含着无奈与辛酸。由于士人数量激增而科举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士人通过科举功名改善生活境况的梦想成为泡影,不习于农工商的士人,只好选择教书或游幕以谋生,清中期的学者传记中,多“家贫游幕”、“橐笔幕游”、“屡困场屋,橐笔远游”等词句。士人游幕还有另一重伤痛,那就是士人对社会的深厚关怀、积极的人世精神受到了前所未遇的挫折。士人要实现济世志向,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途径是进入仕途,而清中期科举制度的腐败,加上汉族士人所受的民族歧视,无数士人只好徘徊在仕途之外。他们在幕府中一边埋头于考据之学,又为经典中原始儒家鲜活的济世情怀感动不已。明清易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民族仇恨已经淡化,济世热情更加炽烈地燃烧。我们从他们的自述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矛盾而痛苦的心情。士人队伍的扩大,科举对士人精神的腐蚀引起士风的败坏,加上统治者对士人的各种各样的压制和打击,士人的地位实际上已下降,士气衰落。士人脱离了农工商,却又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保持的地位,这种无根的浮游状态时时引发士人心灵的伤痛。
所以,文人小说中所写的文人的漫游实际上是现实中文人心灵的漂泊。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的文人小说家也多为游幕者或曾游历过,如夏敬渠“幕游滇黔,足迹半天下”(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李百川曾漂泊陌路,周旋于扬州、盐城、辽州、梁州及河南等地,过着“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的生活(《绿野仙踪》抄本《自序》);《水石缘》作者李春荣因科场不利“负轻囊只身远出,历齐鲁,抵保阳,弃举子业,究习幕学”(李春荣《水石缘自序》,据清经纶堂刊本《水石缘》;《雪月梅传》作者镜湖逸叟曾“北历燕齐,南涉闽粤”(镜湖逸叟《雪月梅传自序》,据清德华堂刊本《雪月梅传》)……这些小说中所写的游历,既是现实文人漂泊生活的反映,更是他们心灵漂泊的象征,所以他们自己的抱负还没有在现实中实现,却为小说中的文人主人公安排了功成身退的结局。
总之,18世纪文人小说的时空运作,作为其叙事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具体的时空安排,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时空体的创造,以及叙事模式的形成,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与18世纪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而归根结底是由于18世纪文人的境遇以及基于此种境遇的文化心态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使得18世纪文人小说的包括时空运作在内的叙事方式不是简单的技巧卖弄,而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
收稿日期:2002-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