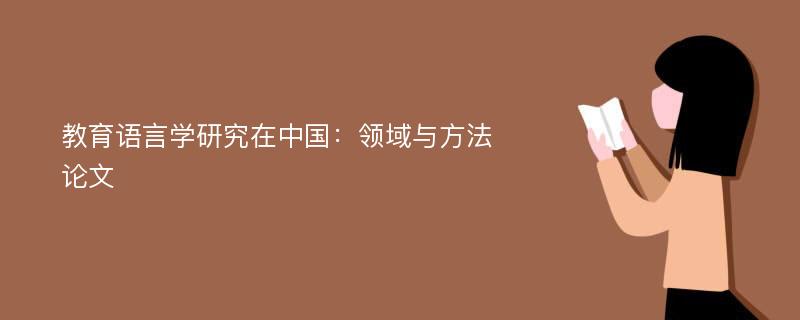
教育语言学研究在中国: 领域与方法*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金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梅德明
提 要: 教育语言学自1972年诞生至今,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相对于国外教育语言学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的迅猛发展势头,我国的教育语言学研究则存在研究领域单一、相关实证研究匮乏的窘境。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外教育语言学的发展概况,认为在面临战略转型的新时期,我国的教育语言学研究应聚焦于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以双语教育、语言服务、外语教学的生态观、移民/特殊群体的语言权利与教育、汉语的对外传播等话题为切入点,并对部分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教育语言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
一、 引言
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从产生到成熟,直至成为语言学领域的新兴学科,迄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教育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是教育中的语言问题,包括教育过程中的语言发展与使用、语言学习者的权利与文化认同、二语/外语的教与学、国家语言战略与规划等研究领域。以“Educational Linguistics”为关键词在Google Scholar检索发现,自1972年“教育语言学”诞生至今,国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已超过1 500篇,所涉及的研究视角包含学科综述、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测试与评价、二语/外语的教与学、多语地区的语言使用与权利、语言身份认同、语言的经济价值分析等多类话题。相比之下,国内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对该学科的综述与介绍阶段,所讨论的话题局限于二语习得、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师教育等视角,研究广度仍相对匮乏,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极度欠缺。本文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语言学习与使用情况丰富,适合我国语情特点的教育语言学研究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文章拟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外教育语言学的发展概况,着重讨论适合新时期我国语情特点的研究领域,并对与之相关的部分研究方法进行介绍,以期为我国教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思路。
首先,本实验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即不同电流大小、乳化剂用量、引发剂用量对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影响,然后得到最小分子量分布指数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制备条件如下:引发剂3 g,乳化剂4 g,电流0.2 A,反应时间8 h,反应温度30°C,分布指数1.946 86.
社会时代变更消费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下,出现了很多多样化的服务形式。企业多以顾客服务为中心,满足了顾客的利益和要求,才能提升企业的业绩。为此,企业需要不断创新营销方案吸引新顾客购买本公司产品,同时也要维系老客户与新客户之间的关系,建立长期的合作模式。
二、 教育语言学的学科概况
2.1 学科发展
“教育语言学”一词最早由Bernard Spolsky提出。Spolsky认为,应用语言学受其名称的限制,所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而缺乏清晰的研究主方向。此外,应用语言学中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语言教学过于关注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而对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与语言教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探索不足。怀揣着对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现状的不满与探索精神,Bernard Spolsky在1972年第二届应用语言学年会上首次提出“教育语言学”一词,随后在新墨西哥大学教育学院设教育语言学博士专业,并于1978年出版第一本教育语言学专著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教育语言学导论)。
同期(197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在Dell Hymes的带领下设立教育语言学博士专业,开设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与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等课程。本世纪初,该校Nancy Hornberger教授扛起美国教育语言学大旗,认为教育语言学已经具备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将教育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三点(Hornberger 2001): 1) 语言与教育相结合;2) 以问题为导向、以教育实践为出发点;3) 视语言的教与学为关注焦点。2008年,Nancy Hornberger主编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语言与教育百科全书)共计10卷本;2012年主编Educational Linguistic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教育语言学: 语言学的关键概念)共计6卷本,大量专著的出版为教育语言学在世界范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功能语言学派代表Halliday(1990)对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与范式做出进一步阐述,认为教育语言学不应仅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领域应以主题为基础(theme-based),采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式。Halliday(1990)通过教与学两方面对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举例,将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具体化。Halliday(1990)认为,从教学角度来讲,教育语言学研究可讨论教材的语言与语域问题、课堂话语研究、语类研究等;从学生的学习角度来讲,教育语言学可讨论语言用途、语言学习环境(尤指校外的语言学习环境)、功能语法及语篇等问题。
2.2 学科定位
目前,就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语言学界一般持以下四种观点: 1) 教育语言学等同或隶属于应用语言学,侧重对外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持此观点的学者多为教育语言学研究的早期引领者,相关研究成果多出现在教育语言学学科“身份未定”的时期。众所周知,应用语言学这门学科在成立之初即是以研究外语教学为主,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实际上就是指外语教学。从“教育语言学”的字面意思来看,这门学科所谈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教育当中的语言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焦点有相似之处。2) 教 育语言学是教育学与语言学两大学科的“交界学科”(interdisciplinary)。持此观点的学者(如Van Lier, 1994等)强调语言学与教育学之间的交互关系,认为教育语言学所关注的问题应包涵两大方面,即涉及语言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学问题、涉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语言学问题。这两大问题分别是教育学与语言学所关注的话题,因而教育语言学应为教育学与语言学的交界学科。3) 教 育语言学是教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相融合的“多界学科”(multidisciplinary)。该观点认为(如Splosky 1978),教育学与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并不足以解决教育语言学所涉及的全部课题,其研究问题还需要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补充,因此,教育语言学具有“多界学科”属性。4) 教 育语言学是基于且超越上述学科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教育语言学的研究特点是以问题为导向,即Nancy Hornberger(2001)所提到的“领域宽而焦点窄”,或Halliday(1990)所提到的基于主题(theme-based)的“超学科”研究。近几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也就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特性进行了探讨与展望。
1998年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兼并了贵州习酒总公司,这是当时国家白酒生产行业最大的资产重组项目,标志着贵州酒业集团化经营取得可喜进展。
4) 汉语的对外传播。当下,世界范围内刮起“汉语热”浪潮。在国内,各大院校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数额比例逐年上升;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英语的国际“霸主”地位,汉语的国际影响力仍亟待提高。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认同问题、母语对汉语的迁移问题、汉语教师的自身发展问题等,都可成为该领域深入讨论的话题。
1) Q方法(Q-Sorting Method)
2.3 研究领域
消费升级一般指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就是各类消费支出中总支出结构的升级以及层次的提升。反应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因此,消费升级理念对于整体的经济发展而言是重要的晴雨表。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整体的发展是由产品的总供给结构所决定的,消费结构对于整体的经济结构和需求结构而言有着重要影响。结合消费结构的实际升级来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集中体现了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对于生产的决定作用。
2.4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即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本质差别在于其理论欲求不同(张培等,2013)。质性研究的主要理论欲求是通过归纳,进而发现规律;量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欲求则是通过推理,进而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Bryman(2004)曾就归纳与推理作出区分: 归纳是数据在先,理论在后;推理则是理论(假设)在先,数据、结果在后。
三、 国内教育语言学研究展望
我国的教育语言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兴起。2010年5月,“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至今该会已成功举办七届。CSSCI来源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于2016年第三期特设教育语言学专栏,也从侧面体现出国内核心期刊对教育语言学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多以文献综述、外语教学、二语习得、教师教育等话题展开讨论,研究广度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例如,在2016年第七届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上,会议仍围绕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对符合国内语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发掘不够。
从教育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几位代表性学者对教育语言学研究的理解和关注点各有侧重。最早提出“教育语言学”概念的学者Bernard Spolsky利用新墨西哥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长期从事双语教育研究,对多语地区的语言生态与保护(Spolsky, 1970)、多语环境下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身份与认同(Spolsky, 1991)、多语地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Spolsky, 2009)等话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讨论;教育语言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Nancy Hornberger则擅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其成果多强调双语/多语教育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双语读写能力研究、语言的生态观等(Hult, 2011);Leo van Lier所从事的教育语言学研究聚焦于语言学习的符号与生态观,认为语言的教与学不应仅关注学校内部,而应从学校、社区、家庭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生态考量(Van Lier, 2004);无独有偶,英国的教育语言学家Stubbs也强调从社会、文化、历史视角来研究语言教育,用批判的眼光评价双语环境中所出现的语言权势问题(Stubbs, 1991)。近几年来,Francis M. Hult主编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教育语言学专著,为有志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例如,Francis M. Hult与Bernerd Spolsky合编的Th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2008)中涵盖了教育语言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即教育的语言与文化因素、语言教育政策与管理、双语读写能力发展、语言习得和语言测试;两年后,Dire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问世(Hult, 2010),该书从语言教育政策、语言多样性、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四大板块出发,对教育语言学的课题走向进行了展望;2011年,Francis M. Hult与Kendall A. King合编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Practice 一书,对双语/多语地区所面临的教师认同、课堂语码转换、学生的读写能力发展、难民家庭的工作语言、语言多样性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3.1 研究领域
Halliday(1990)提出,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应以主题为基础(theme-based),采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式;沈骑(2012)认为,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特性是以问题为导向,将实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是以问题为导向,但所探讨的问题终究不能广泛无边,正如梅德明(2012)所提,教育语言学的研究问题“若什么都可以,必然什么都可以不了;什么都能干,必然无一能干好”。本文认为,在战略转型的新时期,我国的教育语言学研究应始终围绕“教育当中的语言问题”这一核心,除涉及上文所提的传统研究领域外,或许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6) 语言能力测试与评价。作为外语人才的重要储备力量,我国中小学生的外语能力关系到国家的外语人才发展、国家外语能力的战略发展。然而,当前我国的中小学外语能力培养体系中尚无统一的外语能力标准,相关描述仅体现在不同阶段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之中,而外语能力标准不明确又间接导致目前中小学的外语评价体系相对混乱。由此,我国的中小学外语培养体系在纵向不能与大学外语教学进行有效衔接,横向又不能照顾到我国东西部师资、生源的差异,致使我国的中小学外语教学长期呈现“费时低效”状况。当下,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方针要求我国在培养外语人才的过程中,不仅应注重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等传统语言能力,同时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y)有了更全面的要求,外语人才的能力构成趋向个人综合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维发展态势。因此,关于中小学生的外语能力及评价体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 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双语教育。当前,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双语教育政策。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汉语的权势地位高于少数民族语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及其家长更倾向于增加汉语的授课比重,以提高学习成绩、高考录取率。然而,在课堂中过多使用学生并未熟练掌握的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是否会影响教学效果?国外有学者(如Mohanty, 1994;Tove Skutnabb-Kangas, 2008)认为,过早将儿童暴露在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中,儿童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会出现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不能完成学业任务等现象。再者,若盲目增加汉语授课比重而忽略本民族语教学,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未来出现转用甚至濒危的状况?诸如此类问题仍需我国学者进一步考证。
3) 语言服务。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语言是实现“五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沈骑,2015)。“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必将促进沿线国家之间人员的流动,届时沿线国家的交通、商业、教育、旅游等各行业之间的交流势必增加,与之相关的语言服务压力也随之提高。由此,李宇明(2015)提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然而,长久以来我国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过于单一,造成英语人才过剩而其他“小语种”人才短缺的窘境,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语言服务的人才尤为不足。如何充分发挥全国各地的地理、人文环境优势,培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语言服务工作的外语人才,无疑是近几年小语种人才培养战略的攻关课题。
冻脸效应: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会认为视屏中的人比同一个视屏中的截图更好看。研究者把这种静态脸相对动态脸没那么有吸引力的现象称为“冻脸效应(the frozen effect)”。
5) 外语教学的生态观。谈及外语教学,传统的研究话题往往围绕外语教学法、外语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外语教师教育等展开。外语的生态教学观则强调将学习者在校内、社区、家庭、学习者个体差异等因素视为一个整体。课堂中如何使用与调整教学媒介语;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电子游戏、新科技对外语学习的辅助性作用;学习者的社区、家庭生活对其外语学习有何影响(社区的语言景观、社会文化条件等因素);学习者自身的语言认同感等话题,是国内教育语言学研究的新突破口。
1) 英-汉双语教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贯彻施行“引进来”方针,国家、企业、学校和家庭各个层面过于重视英语教育,致使孩子接触英语的年龄越来越早。语言与社会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民族的知识与文化精髓。过早让孩子接触英语,而对母语教学关注不足,是否会使孩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认同感、甚至母语的使用(如语言磨蚀)等方面出现消极效果?新时期的中国已由“引进来”向“走出去”逐渐转型,将中华文化传向世界的历史重担在此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平衡国内学生教育的英、汉教学比重,无疑是当下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
7) 移民、特殊群体的语言权利与教育。目前,便利的交通条件致使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空前增大。我国东、南部发达城市(如上海、苏州、广州等)的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一方面,外国移民、留学生人口不断增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国务工群体也移居工作城市。因此,国内外移民子女的语言权利与教育问题已成为议题。此外,与国外相比,我国关于特殊群体的语言教育研究(如手势语研究、聋哑学生的语言习得等)仍十分薄弱,亟待相关学者的进一步探究。
3.2 研究方法
传统意义上的外语教学或二语习得研究,多从师生的教学/学习方法、情感态度、认知加工等方面入手,通过心理语言学相关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进行分析,运用测试、问卷等手段进行量化统计,质性研究方法多作为辅助手段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相对而言,教育语言学的相关课题在研究过程中采用质性方法的比重较大,研究更倾向于从社会文化、个体认同感、语言权利、语言生态等方面入手,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综合分析。从教育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几位学科代表人物均倾向于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开展教育语言学研究。例如,Bernard Spolsky多从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角度出发,提倡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语言教学与语言规划问题;作为资深的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研究专家,Dell Hymes侧重用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来研究语言教学问题,尤其关注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对双语学习者产生的限制与困境;随后扛起教育语言学学科大旗的Nancy Hornberger致力于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语言文化研究,同样倾向于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侧重对双语/多语地区的语言教学实践与语言规划进行讨论;长期从事教育语言学研究的英国学者Stubbs也聚焦于语言教育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常采用课堂观察、个案研究的形式进行资料收集。综上可见,相对于传统的外语教学或二语习得研究,教育语言学相关课题更加关注研究个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倾向于通过质的研究方法收集各方数据,运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分析,具有较明显的社会学转向。
传统的应用语言学倾向于以理论为导向,采取自上(理论)而下(实践)的研究范式,将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近似于Bryman所提的“推理”;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特性则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沈骑,2012)。这就意味着教育语言学研究并不以某一语言学理论为中心,通过理论解释实践;而是以语言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为研究中心,将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实践等融合在一起,近似于Bryman所提的“归纳”。如此一来,国外教育语言学研究多采用以质性为主的方法就不足为奇了。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的教育语言学研究可围绕前文提到的语言教育热点问题,从研究对象自身的内部因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两个路径予以剖析。现相应地介绍两种研究方法:
本文认为,首先,教育语言学在产生之初即是从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虽然其主要研究领域与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有所交集,但教育语言学除了关注外语教育以外,还对语言教育政策、课堂话语分析、语言身份认同、生态语言与保护等话题有所涉及,其研究领域与关注焦点更具针对性,因此,将教育语言学等同于应用语言学的观点有待进一步讨论。其次,不论是Halliday(1990)所提到的主题式“超学科”研究,还是Nancy Hornberger(2001)所提及的“领域宽而焦点窄”,均是在探讨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问题,而非学科定位问题。教育语言学的研究特点虽是以问题为导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辅助,但其研究焦点明确,关注的是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问题。若以上述第四个观点定位教育语言学,则难免将教育语言学陷入“多领域而无焦点”的窘境。最后,将教育语言学定位为交界学科或多界学科也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其特点。例如,若视教育语言学为教育学与语言学的交界学科,则既可将学科落脚点定位在语言学,称其为“教育语言学”,也可将学科落脚点定位在教育学,称其为“语言教育学”,致使学科焦点模糊(梅德明,2012);若视教育语言学为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界学科,虽可涵盖教育语言学的绝大多数课题,但同时令该学科从学理上过于宽广而缺乏界限。因此,教育语言学虽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点,但其核心课题应始终聚焦在教育中的语言问题,即学科落脚点应定位在语言学,仅对Spolsky(1978)、Nancy Hornberger(2001)等学者所提到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进行一定的借鉴。
该新工艺原料为玉米和小麦,花生粕为发酵提供了蛋白质,使用双菌种发酵用曲。该新工艺达到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且安全卫生。
在语言的教与学过程中,参与者自身的内部因素可通过Q方法进行剖析。Q方法首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心理学界。近几年来,该方法已运用于社会学、管理学、语言学(如Lo Bianco, 2015)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当中。与科学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量化研究相比,Q方法以“发现”作为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更加强调个体主观性与个别性的价值(赵德雷、乐国安,2003),其研究多用于理解“How”或“What”等问题,而非解释“Why”的问题。Q方法的操作过程拒绝了问卷、量表、测试等方法中对人群抽样的依赖,而选择对问题抽样,通过研究对象的主观排序(Queue)来获取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根据Q方法的操作特点,研究者可对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语言学习群体(尤其是移民、少数民族)的心理因素、跨国语言教师的文化冲突等相关研究课题取得更深入的突破。
2) 民族志研究
轮回理念不仅可以运用到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可以各种相关的人文概念中:善与恶,生与死,灵魂与肉体等等。
民族志研究适于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周围环境进行全方位考量。民族志研究最早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界(如Malinowski、Mead等)。数十年以后,该方法开始逐渐进入社会语言学、教育学者的视野。民族志研究善于从文化角度阐释个体的行为、互动及其周围的事件(Agar, 1983),从而达到在自然、持续进行的环境中分析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效果(Watson-Gegeo, 1988)。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与侧重点可对我国多元文化地区的双语教育、“一带一路”与语言服务、外语教学的生态观等研究课题进行更全面的解析。以多元文化地区的双语教育研究为例: 长久以来,我国绝大部分的多元文化地区受经济、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双语教育中“费时低效”的问题尤为突出。民族志研究方法可对该地区双语学习者的文化认同、语言使用环境(如语言景观)、学习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剖析,“自下而上”地对该区域的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提供研究素材。
社会文化视域下的教育语言学研究除了上述两种研究方法外,还包括其他研究方法,例如叙事研究、个案研究、话语分析研究、行动研究等,研究者在明确研究问题前提下合理选择不同的方法论。
四、 结语
在科技、交通日益发达的新时期,双语、甚至多语的语言社会环境日益普遍化,影响语言学习效果的因素决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内部,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开始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习者个体等课堂教学以外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倾向于从语言教学的社会文化视角入手,对语言的教与学进行综合考量的教育语言学无疑具有相当明朗的发展前景。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外教育语言学的发展概况,对适合新时期我国语情特点的部分研究领域与方法进行介绍,希望能为我国教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思路。
参考文献
Agar, M. 1983.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ryman, A. 2004.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90. “O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R. Giblett and J. O Carroll (eds.). Discipline -Dialogue -Dif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Language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 Murdoch: 4D Duration Publication.
Hornberger, N. H. 2001.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s a Field :A View from Penn ’s Program on the Occasion of Its 25th Anniversary .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1-2): 1-26.
Hult, F. 2010. Dire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 Heidelberg: Springer.
Hult, F. & K, King. 2011.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Practice .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o B., J. 2015. “Exploring language problems through Q-sorting”. In M. Hult and C. Johnso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 Oxford: Wiley Blackwell.
Mohanty, A K. 1994. Bilingualism in Multilingual Society .Psycho -social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 Mysor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Stubbs, M. 1991. “Educ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Multi- cultural rhetoric and assimilationist assumptions”. In F. Coulmas (ed.). A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Skutnabb-Kangas, T. 2008.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ume 5Bilingual Education . New York: Springer.
Spolsky, B. 1970. “Navajo language maintenance: Six-year-olds in 1969”. Language Sciences , (13): 19-24.
Spolsky, B. 1978.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Spolsky, B. 1991. “Control and democratization of sacred literacy”. In Samuel Rodin (ed.), Encounters with Judaism :Jewish Studies in a Non -Jewish World . Hamilton: Waikato University and Colcom Press.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L, L. 1994.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Field and project”. In J. E. Alatis (Ed.).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tabl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Van L, L. 2004. The Ecology and Semi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atson-Gegeo, K. A. 1988. “Ethnography in ESL: Defining the essentials.” TESOL Quarterly , (22): 43-59.
李宇明,2015,“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理论版)》, 2015年9月22日.
梅德明,2012,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当代外语研究》,第十一期: 32-37.
沈骑,2012,教育语言学何为?——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特性及其启示,《当代外语研究》第十一期: 38-42.
沈骑,2015,“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九期: 9-13.
沈骑,2016,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创新及对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学科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三期: 7-13.
赵德雷、乐国安,2003,Q方法论述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四期: 34-39.
张培、张昕昕、韩子钰,2013,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法类型: 2000—2010,《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一期: 66-69.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study in China: fields and methods
by YANG Jinlong & MEI Deming
Abstract: Since its birth in 1972,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subject. Standing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rapid growth and thriving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broad,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is meeting the dilemma of narrow research field and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By 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Linguistics research abroa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the present period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China could focus on studies on bilingual education, language service, language teaching study from ecology perspective, language right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of immigrants and special groups,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etc. Besides,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n introduc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Method
*本研究为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3年度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大中小学学生外语能力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ZDJ125-4)、国家语委科研基地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的阿拉伯语言服务调查——以陕、甘、宁回族聚居区的语言景观为例”(WYZL2016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地址: 400031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33号,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字编校: 汪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