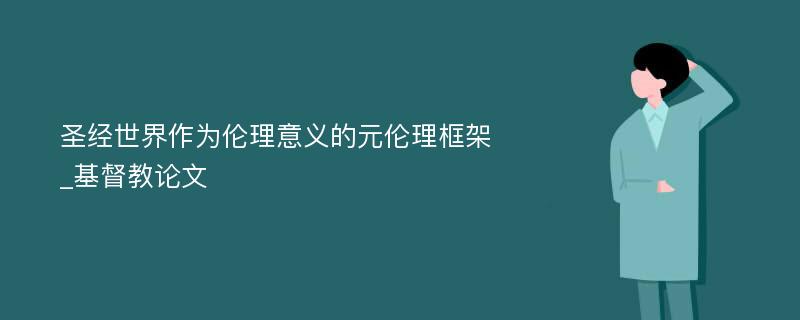
作为伦理意义之元伦理框架的圣经“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圣经论文,框架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天主教道德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低估圣经作为一种伦理资源的作用。教皇通谕常常将圣经视为教规的一种补充,而教规的基础则主要是自然法或个人化的论证。道德神学家们也趋向于低估圣经,尤其是倡导所谓“自律道德”的那些神学家,他们拒绝把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建立在外在于人类(自然,经文,教会,传统等等)的权威之上。他们的伦理体系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及人对其行为负责的自由之上,这种自由是服从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理性之表述的道德命令的。换言之,其理论的基石是人的自律以及道德规范的理性基础。麦克斯(K.Merks)把这种伦理思想描述为“理性洞见的道德学说,是托玛斯.阿奎那所建构的实用理性道德之类的自然道德学说的延续。”(注:麦克斯(Karl-Wihelm Merks), “从群体道德到世界伦理:道德神景观下的道德的普遍性”,载于慕辛加(Musschenga)(编辑),《宗教与道德有关联吗?
对道德独立于宗教的观点的再评价》(Dose Religion Matter Morally? A Critical Reappraisal of the Thesis of Morality's Independence from Religion,Kampen:Kok Pharos),1995年,19页。)(注:麦克斯,“自律”,载于威尔斯(J.P.Wils)和米埃特(D.Mieth), 《基督教伦理的基础》(Grundbegriffeder christlichen Ethik,Paderborn:Schoningh),1992年,269页。)
尽管“自律道德”的倡导者避免“宗教与理性相互排斥”这一提法,尽管他们把圣经视为道德判断中的一个来源,他们仍然认为圣经自身不足以裁定任何道德判断,构成某种权威。(注:麦克斯(Karl- Wihelm Merks),“从群体道德到世界伦理:道德神学景观下的道德的普遍性”,载于慕辛加(Musschenga)(编辑),《宗教与道德有关联吗?对道德独立于宗教的观点的再评价》(Does Religim Martter Morally? A Critical Reappraisal
of
the
Thesis
of
Morality's Independence from Religion,Kampen:Kok Pharos),1995年,10页)
并且,有些人否认圣经道德的原初性,从而使圣经相对化。例如,奥尔(Auer)认为旧约道德——尤其是十诫和智慧书中的道德观念——只不过是古代近东比较普遍的“世界伦理”(Weltethos)的一种代表。奥尔对新约伦理的看法与此相似:耶稣的训导引用了早期的圣著,他所建立的新律法并无原初性。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圣经对于建构伦理规范的独特贡献很难予恰当地认可。尽管奥尔承认圣经确乎有其影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籍以透彻地阐述伦理道德的全面的意义框架。他认为,圣经的信仰观至少有两重影响:在道德规范方面,它起到一种整合、激发和批判的作用;在道德实践方面,它起到一种推动的作用。(注:奥尔(Alfons Auer), “道德自律与基督教信仰”(Autonome Moral und christlicher Glaube,Dusseldorf:Patmos),1971年;荷兰文版,1973年,142—151页。)
然而,问题在于,奥尔的观点是否给予圣经伦理和元伦理体系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充分的认可。自然,不能否认,理性和自律的道德本身是相对于危险的不加批判的“他律”学说和不恰当地利用宗教与信仰的一种合理的回应。(注:麦克斯(Karl-Wihelm Merks), “从群体道德世界伦理:道德神学景观下的道德的普遍性”, 载于慕辛加(Musschenga)(编辑),《宗教与道德有关联吗?对道德独立于宗教的观点的再评价》(Does Religion Matter Morally? A Critical Reappraisal of the Thesis of Morality's Independence from Religion,Kampen:Kok Pharos),1995年,13页)倡导自律道德的神学家驳斥基要主义、信仰主义或启示绝对主义的观点,并且反对把圣经看作不可能用理性加以审视的绝对正确的道德规范。他们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对他们来说,盲从于与理性相忤的诫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那些诫命是上帝或者是自称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权威颁布的。尽管他们的这些倾向本意是好的,但不能否认,倡导自律道德的神学家,尤其是奥尔,对待圣经伦理的态度未免有失狭隘。他们过多地注意到道德规范的自律的基础,而对发现这些规范的创造性的时刻关注甚少。此外,他们忽视了圣经文本所激发的语义和实践上的创新,由此,他们低估了圣经伦理的原初性,而它则是那些具有广泛重要性的伦理探讨的泉源。(注:布格拉弗(Roger Burggraeve),《由〈圣经〉引起的思考:创造,受难,圣业,上帝之受难及其他伦理学的宽恕与自由:与莱维纳斯对话》(De bijbel geeft te denken.Schepping.Milieu.Lijden.Roeping.Gods passie en de ander.Vergeving.Bevrijding van de ethiek.In gesprek met Levinas,Leuven/Amersfoort:Acco),1991年,31页。)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明为什么道德神学必须更加重视圣经。这不仅是由于圣经作为一个“文本世界”(我将在后文中讨论这一点),而且,一种平衡的方法要求把信仰体系纳入思考的范围中来。按照这个方法(以德莫尔[Demmer]为代表),神学家不仅应考虑到理性相应于圣经伦理的批判和启示的作用,也应同样地考虑到圣经信仰相应于理性的批判和启示的作用。这种“相互启示的作用”应该是二者之间一种永恒的相互修正。(注:德莫尔(Klaus Demmer),(Leben in Menschen- hand.Grundlagen des
bioethischen
Gesprachs, Freiburg:Universitatsverlag/Herder),1985年,19页。)
并且,我们不能忘记,神学伦理学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不能仅仅被视作对人类行为的哲学阐释,或是具体伦理规范的理性基础。它不能只是哲学探究的一种神学翻版。它应是“信仰寻求理解”的一部分,因而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寻求答案:关切人类的上帝在人类行为中的处身意味着什么?它应该对基督徒响应上帝拯救人类,创制自由,关切自由的契始及其召唤的伦理行为的意蕴作出解释。
基督教伦理中的这种响应于上帝的特点意味着神学家只有深入于与他的研究相关的信仰关联中,才能充分地阐释基督教伦理。正如德莫尔所强调,基督教道德神学家不能放任自己以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相同的方式探讨伦理学(注:德莫尔,(Die Wahrheit Leben.Theorie des Handelns,Freiburg:Herder),1991年,14页。)。他应当把自己的理论植根于活生生的信仰之中。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并不仅仅倚赖于它是否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而是同等地倚赖于它是否包涵着一种永无终止的对象化的客体关联。这一客体究其根柢并非客体,而正是上帝。缺乏这种客体关联的理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伦理学。这意味着圣经不能被视为毫无生机的化石,而应当看作一个由喻意的及叙事的文本系统构成的中介质。它是先于理性反思的,其中记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使这种关系成为可能的意义体系。
即使神学家在信仰体系的基础上建构理性的理论系统,他也应当记住,道德神学作为对信仰进行理性反思的神学体系的一部分,它必须和其它理性体系一样,认真地审视其理论的文本根源。(注: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谁之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1988年。)
以上两方面中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以圣经为根基,对伦理学进行实际上的和意义上创新,这如何才成为可能?如何才能在认可自律伦理学说中合理的成分的同时又超越它的视界?
一、首先,我们应当看到,圣经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元伦理或超伦理体系。换言之,圣经与基督徒的道德实践的关联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考察语言的诗性维度。利科尔认为,诗性维度能将任何文本转换为启示的空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圣经能象其它文本一样任意加以阐释。二者有所区别:圣经的文本系统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独立于其作者的原意,其语言、风格和叙述模式变化多端,其潜在的意义如复调音乐一般丰富多彩。这一切都统一在上帝之中。采纳阐释学的方法来解读圣经,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个世界,其中上帝以其无限之恩典,成为这个世界中绝对的一端。他的恩典通过对日常语言的诗性强化传达出来,尤其是耶稣所讲的那些蕴义丰富的寓言。(注:托玛塞特(Alain Thomasset), 《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Poetique 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190—193页。)
圣经作为一个特殊的“世界”,使阅读它的人们身心彻底改变,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解释生活。圣经文本并没有提供新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但它赋予普通的伦理体系一种新的特殊的眼光,即,恩典与爱的复杂的救恩史。(注:托玛塞特(Alain Thomasset),《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
Poetique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459页。)尽管俗世的伦理规范不同于植根于恩典的伦理规范,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普遍的伦理义务在有信者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启示中同样存在。(注:施利比克斯(Schillebeeckx)的观点,参见奥尔(Alfons Auer),“道德自律与基督教”(Autonome Moral und christlicherGlaube,Dusseldorf:Patmos,1971年);荷兰文版,1973年,143页。)这样,这些道德原则就被赋予了新的形式的意义并且由此从义务的阶段(即服从于理性所要求的道德律)上升到绝对服从于爱的诫命的阶段。(注:托玛塞特(Alain Thomasset), 《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Poetique 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326页。)
然而,改变的不仅仅是伦理规范的形式的意义,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发生了变化。阅读圣经的人运用想象对之加以理解,经历一种向往基督的再生过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圣经更加关注的是人的新的存在方式,而非新的行为规范。它更多地蕴含着一种“存在的伦理学”,而非“行为的伦理学”。
这样一种改变人类的文本还有另外的重大意义,圣经作为元伦理体系,其“他律”并非对人类自由的阻隔,而是赋予人类在其行为中遵循一定道德规范的能为。圣经文本以上帝无限的恩典为其根基,使人类成为一种具有依照道德律生活的能力的新人(homo capax)。这意味着人的道德行为并非仅仅是出于其意志的选择,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所有的能力都参与其中(例如对道德的想象能力)。 (注:托玛塞特( Alain Thomasset),《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
Poetique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204页。)圣经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上帝要求人类如何行为, 而且是人类在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之中能够如何行为。
二、其次,我们应当考察圣经对人类成其为道德主体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道德并不只关涉到正确的道德抉择和与之孤立开来的道德行为,它首先关注的是二者在个人生活中的统一问题(注:参见德莫尔,“Die Wahrheit Leben.Theorie des Handelns,Freiburg:Herder),1991年。)。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他有责任使其作为人的生命禀得道德的统一感。赫维(Vaclav Havel)认为,这种责任是“我们用以书写人类历史中世界新生过程的笔”。
不过,如果不考察叙事结构的作用,就无法充分理解人的统一性。马可;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叙事是理解这种统一性的最为全面的方式……自我及其行为的统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叙事的统一。”(注:约翰逊(Mark Johnson),《道德想象:认知科学对于伦理学的意义》(Moral Imagination: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Eth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年,164页。)这是什么意思?它与阅读圣经是什么关系?保罗;利科尔对此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在《作为他者的自我》一书中,他提出,道德主体并不只是一个完全自律或自足的统一体,并不仅仅有同一,它在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中使自身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体。这个“他者”并不仅是具体他人的他性(注:参阅莱维勒斯(Levinas)的著作。),而且是文本的他性。它使人们运用想象充分体悟到圣经所暗示的存在和意义的可能性,从而不断地重塑自身。对利科尔来说,“理解就是面对文本的自我理解”。
人的“自我”的是人濡染于其中的文本世界(包括艺术和文化的创制品)的想象性的同化和结晶。针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徒通过阅读经文和崇拜活动而与圣经建立起活生生的关联,这种关联除了赋予他们以道德的洞察力以外,还使他们作为基督徒的道德主体,获得一种叙事的对自身的认同。换言之,情节生动的圣经文本使人们得以对能够转化为意义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想象的解释,从而以之指导其具体的行为, 并通过叙事式的方法, 塑造或者重塑自身(注:莫尼(Joy Morny),《对利科尔〈作为他者的自我〉的思考》,见库利(R.C.Culley)和克兰帕(W.Klempa),《三种爱:哲学、神学和世界宗教——麦克来兰德纪念文集》(The Three Loves:Philosaphy,Theology and World Religions.Essays in Honor of J.C.McLelland),1994年,85页。)。这一过程是以圣经为中介的,它使基督徒得以克服“某种本质主义或自我中心的矫饰以及解中心的后现代的偏逆之处”,后者全然失去了内在可能性的结构。(注:《三种爱:哲学、神学和世界宗教》,85页。)
对基督徒来说,阅读圣经,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活动,是建构其道德主体性的必要条件,是绝对必须的(尽管它不排斥其它的因素——如理性的作用)。
第三,我们应当考察圣经对基督徒的具体行为的更为直接的影响。
我们先考察圣经叙事的劝勉性质。
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叙事的劝勉性质。它有时明显地受到轻视(如布鲁诺·舒勒Bruno Schuller)。舒勒认为,圣经,尤其是福音书中并没有“一种对道德的确切的判断”,因为它是劝勉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劝勉本身并不提供道德的标准,因此,应当主要从圣经中劝勉内容对读者的影响,而不是从它们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其价值。(注:舒勒(Bruno Schuller),“关于基督教伦理性质的讨论的一些看法”,载于库朗(C.Curran)和麦克科米克(R.A.McCormick), 《基督教伦理的独特性》(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ristian Ethics,New York:Paulist Press),1980年,216—217页。)
舒勒的观点是典型的道德自发学说的代表,然而,问题在于,他的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圣经中劝勉内容的根本性。在这方面,鲁克·安卡特(Luc Anckaert)的解释与圣经更为吻合。由于读者与圣经文本世界所指示的对象——上帝具有某种三重的关联,这些文本的劝勉性质便使人类的责任根本化。有限的自律形式被打破,向着一种更为普遍的责任感,甚至向着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整个世界的责任感开放,这个世界的具体化就是向我们诉求的某个人的面孔(注:安卡特(Luc Anckaert),“上帝,世界与人类:介于西方哲学与圣经智慧之间与弗朗兹·罗森维斯的哲学、伦理学与神学的对话”(“God,wereld en mens in het tweestromenland.Tussen westerse wijs-begeerte en bijbelse wijsheid.Een filosofische,ethische en theologische dialoog met het ternaire denken van Franz Rosenzweig".Leuven),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94年。)。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道德传统自身的特殊性与伦理责任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到了超越,即,这种根本意义上的责任感克服了某种“小善”与对社会的整体性的责任感之间的张力。
这种向圣经的读者发出召唤的人类责任的根本性的“普遍化”,对职业伦理尤其具有意义。人类与圣经文本的三重关联使其超越了有限的由其功能区分开来的“角色责任”,获得一种真实的全球伦理意义上的责任感。由于这样的责任感,人类开始重视职业道德上的决断对邻域的后果,长期的后果,并且对开始关注那些具体的受害者,他们的眼泪常常被官僚和技术统治的思维方式所忽略。
我们接下来考察想象的作用。
在我以上对作为元伦理体系的圣经叙事文本的阐述中,我曾指出,讲述和阅读圣经故事可能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对自己的道德判断进行假设的实验。这种想象能够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它是“道德判断的实验室”。(注:利科尔(Paul Ricoeur),《作为他者的自我》(Soi-meme comme un autre,Paris:Seuil ),1990年,167,200页。)
确实,伦理行为不仅仅只是意志的行为或是在理性判断基础上依据道德规范而行动的事情,它同时也是一个更为自发和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们受到创造性的和再创造性的想象的作用。这种想象能够培育人们内心的情性,发展出新的行为模式。在这里,对圣经的想象至少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即它与效仿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对基督徒来说,希伯来文圣经的三个部分(摩西五经,先知书和智慧书)所教导的内容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最终的实现(而不是被否定),他就是基督徒的榜样与规范。对圣经的想象使得按照基督精神处世为人成为可能。这种想象使得基督徒通过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生,也使得他们发现新的做人方式和新的行为模式。当基督徒把自己设想为与基督同一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我转换成一种“基督式的自我”。这与勒内·吉拉(Rene Girard)所描述的被动的模仿和效法毫无关系。关键在于,这样的基督教徒从中获得了与使徒们同样的体会,当时的使徒们逐渐发现,基督是他们“内心的主人”。没有这种使徒的体会,基督徒不可能实践其道德生活(注:托玛塞特(Alain Thomasset ),《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Poetique 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208页。)。这种神秘的“如他那样行事”的经验以想象为中介,不仅使基督徒的观念得以根本化和人性化,也使得人们得以接受十字架受难的事实,理解那种自我牺牲的爱。
在这种效仿基督的过程中,转换为“基督式的自我”的基督徒具有某种世俗的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想象式的效仿基督是非理性的。对于这样一位接受十字架苦刑的人的生命意义的深刻反思,可以使人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基督的奥迹,并在“面临着放弃了神性的存在”之时,领悟到人的普遍本质(注:德莫尔,42页。)。用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话来说,“基督就是绝对命令的具体形式。通过其受难,……他强劲了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和他一起去实施圣父的意愿”。(注:舒勒(Bruno Schuller),“关于基督教伦理性质的讨论的一些看法”,载于库朗(C.Curran)和麦克科米克( R. A. McCormick ), 《基督教伦理的独特性》(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ristian Ethics,New York:Paulist Press.),1980年,218页。)
第四,我们应当考察圣经伦理的普遍意义。后现代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学说倾向于把圣经伦理私人化,或者把它看作一种笼统的道德规范,有待于约简为普遍性的秩序和原则,这样才能对公众有意义,才能为公众所接受(请参看罗尔斯(J·Rawls)的著作)。
这种观点就是对道德规范缺乏历史的眼光的表症。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认可或者可以认可的指导公众生活的普遍的伦理框架并不只是同一时期所达成的共识的产物,它同样也是一种永恒过程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道德信念和落实到实际中的特定的叙事及理性思考的传统拓展并丰富了普遍接受的规范。我们今天所认定为“普遍”的规范或习俗很多都是某种复杂的涵化过程的历史的产物,而犹太——基督教,或者进而言之,圣经的道德传统对这一过程具有赋予其位格观念的影响。(注:德莫尔,41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能够转化为审慎的信念和正确的行为的圣经在文本和实践中的创新作用,将继续丰富公众辩论的实质,对公众伦理施以影响。这种公众伦理具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而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的原则和秩序。它能够培育出具有实质内容的公共美德(如对正义与凝聚力的真正的理解)。
我们可以根据爱与律法的辩证关系,对所谓的“金律”进行阐释学的研究,以揭示公众伦理中具体性和普遍性辩证关系的“政治”意义。
表面看来,圣经中的爱和律法具有明显的差异。连语言的形式都是不同的:前者是诗意、咏唱、比喻的,后者是平淡、程式性的。在无限制的爱的原则(爱你的敌人)和均衡原则(金律)之间也有一种紧张关系。托玛塞特(Thomasset)受利科尔的影响, 认为这种差异不能解释为二者的对立。金律向来都具有双重的含义。它可以表示某种开通的自利或实用主义的原则,但也可以用超越自利的眼光来看。这样,它也就成为救恩计划的一种表现方式。爱与律法相互影响:爱之诫命拓展了金律,而金律则使爱之诫命在落实于社会生活的同时免于无序之虞。在此意义上,律法是爱之诫命的中介,而爱之诫命则是律法的活力的源泉。(注:托玛塞特(Alain Thomasset), 《存在的诗学与社会中的道德行为:保罗·利科尔对建立基督教景观之中的阐释及叙事伦理学的贡献》(Poetique de l'existence et agir moral en societe.La contribution de Paul Ricoeur au fondement d'une ehtique hermeneutique et narra-tive,dans une perspective chretienne,Louvain),1995年,463页。)
爱与律法这种关系的社会意义使我再次对圣经文本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思索。圣经世界丰富的语义能够触发新的想象,它不仅对基督教会,而且对整个社会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圣经世界使我们可能重新发现一些阐释范式转换的根本隐喻,一些新的视角,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这些根本隐喻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社会的种种矛盾。(注:汉迪(Charles Handy),《空空的雨衣:理解未来》(The Empty Raincoat: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London:Hutchinson),1994年。)它们使私利和“看不见的”利益机制与对共存的期待和“看不见的”合作机制形成一种张力。它们通过承担一种社会的契约而使契约人性化。同时,它们使人们为一种共同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其中包括为穷人提供特别的途径。它们使个人打破封闭的单维的技术——经济文化的视野。简言之,圣经所提供的隐喻使得人们解除对社会看法的神话观念,并努力克服其意识形态上的偏差之处。(注:佛斯特拉滕(Johan Verstraeten ),“对应用伦理学的叙事性及其阐释学的思考”(“Narrativity and Hermeneutics in Applied Ethics.Some Intro-ductory Considerations”),载于《伦理视野》(Ethical Per-spectives),1994年1期,51—56页。)
世界统治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作为邻居的全球》提出了旨在促进全球化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报告对于上述想象对圣经起范式转变作用的观点是个很好的支持,这一支持并非纯粹的巧合。用报告起草者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的话来说,“人们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学习、工作、相邻的地区,甚至国家和整个大洲,但还是保持我们原来的样子。但如果我们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一切就都能改变——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追求。在宗教的历史上,这种发生在人们的想象领域的剧变不断地发生,它标志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它是心灵的转向,是再生的过程。人们藉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用新的观念来理解事物,并开始新的生活方式。”
在与其它宗教的对话中,圣经的元伦理诗性文本世界确乎能够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