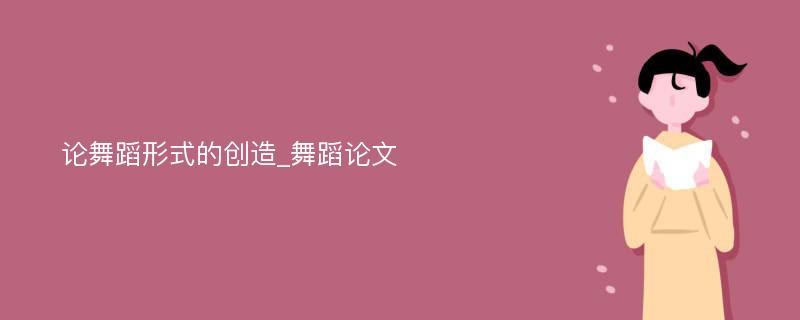
论舞蹈形式的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视为神秘的“艺术母题”——形式,在美学领域里占据显赫的席位。可以说,在众多的学科中,很少有像美学那样对形式给予特别关注的。在创作理论中,曾经认为形式置于从属地位的看法,是一种似乎经典的观点。而现今文学艺术界对形式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形式成为另一种感性的方式,同样担负起表现性的功能,荷载起作品理性意旨。强调形式的意义,总离不开对具体可感形式的探求与创造,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对舞蹈艺术而言,它以人体为工具,以动作为手段,形式就是人体的运动。换言之,舞蹈形式的创造,不外乎将既有舞蹈动作素材的结构重组;将日常生活动态的节律化和图式化;身体操练动作的情感化和寓意化,这就是舞蹈艺术形式创造的本质意义所在,可见形式对舞蹈艺术来讲是尤为重要的。尽管在舞蹈创作中,每每知道因难以找到完美体现内容的形式,而感到困惑和费神之痛苦,却偏要在舞蹈创作中,苦苦地在形式的沙滩上拾贝,在形式的海洋里撒网,孜孜不倦地渴求得到美的真谛。所以要求舞蹈家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热情睿智的眼睛捕捉生活现象,以生命的巨大能量,在历史的底蕴下,执著地现代追索,铸造足以显现舞蹈美的形式。
一、既有舞蹈动作素材的结构重组
舞蹈是人体动作的艺术。舞蹈艺术的美学特征,是以人体动作作为主要物质材料充分体现人体美为主要内容的形式美。舞蹈创作总是以动作为核心贯穿始终的。舞蹈编导头脑中贮存大量的动作素材,其中有前人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规范、风格化的动作,也有古今中外一切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动作,这些动作均称之为既有舞蹈动作素材。舞蹈创作的大忌,即将前人既有动作随意性地拼凑、堆砌,索然无味而不成其真正的“舞蹈作品”。文学家歌德说过:“对于每个人,素材摆在面前,似乎对内容有所把握,就能抓住内容,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形式是一个奥秘。”(歌德:《诗与真》)掌握挖掘、选择和发展主题动作,是我们舞蹈创作的重要手段。一旦从既有动作素材中找到合乎表现意旨,合乎音乐旋律,合乎逻辑发展的主题动作,可在动律上取舍,任意进行变形、扩展、升华,重新艺术地缝合变化。可在动律上加色彩,任选动作的一个部分给予精巧的特征性的装饰,使得动作更丰富多彩,起着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作用。可在动作力度上变化,使其动作在力度与节奏、点与线、刚与柔的对比上,形成各种质感不同的动作形式。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舞蹈编导,具有驾驭素材的功力,能运用一点点的素材,来提炼主题动作,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创作出一部精品之作。据我所知,舞蹈《黄河魂》的编导苏时进,为了寻找主题动作,历经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泡在排练厅全身心地无数次用自己的形体,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推敲、琢磨、筛选、提炼,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比较准确的主题动作。他在山东“鼓子秧歌”的动律上夸张、变形,突出男性的气质,将呈弧线形的身体运动与划船动作有机谐合,而产生了强烈的旋律感,使动作的过程加大幅度、力度,并融合现代舞的律动,塑造了独具个性、色彩鲜明的舞蹈形象,使人耳目一新,令人振奋,显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
二、日常生活动态的节律化和图式化
任何艺术,从孕育到形成的过程,无论你怎样精心设计,刻意求新,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所赋予它的胚胎和雏形。伟大的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看出美来。”在生活中,创造视觉艺术的人往往都是受到外界的影响才进入创作状态的,无论艺术表现的是什么感情,都是从日常熟知的物品、自然景物中产生的。舞蹈艺术形式的创造,从古到今,打开舞蹈动作的仓库,无一不是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的关联。舞蹈《再见吧,妈妈》、《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雀之灵》、《两棵树》、《小溪·江河·大海》等,要么是表现鲜明的生动的人物形态,要么是宣泄自然景物的情态,要么是展示自然动物的动态,并转化为动作形式,强调了以生活动作中的节奏和韵律加以衍化,艺术地在动作与动作过程中经过一定的路线形成图案,这中间也就是一个节律化和图式化的创造过程。
节律化
德国美学家艾·格罗塞说:“舞蹈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动作的有节奏的程序,没有一个舞蹈是没有节奏的。”舞蹈的基本原则就是表现身体有节奏、有规律的运动形态。在时代节奏,心理张力,情感底蕴,身心合一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时间关系,即运动周期的时值长短,能够给人以快慢有致、疏密有律,撒得开又收得拢,变化流动又统一凝聚,起伏跌宕又集中均衡之感。二是力度关系,即是周期性变化的强弱、流畅与顿拙,力度与速度,能量的大与小,有机无限组合,体现舞蹈动作节律的不同色彩和内涵。我们看到的舞蹈《海浪》中海燕的形象,不是一种自然摹拟,而是提炼节律化动作。海燕时而骄傲自由地抖动双翅,时而滑翔掠过海面,时而急速升腾上天,时而回旋俯冲而下,时而海浪翻卷逐浪高,时而细浪腾起珠花四溅。海燕的动作如两臂屈伸展翅,扦秧步,与表现海浪的倒踢大跳,连续卷体动作,成功地表现了节奏和韵律的强和弱、快与慢、扬与抑、高与低,二重叠合,跌宕交辉,错落有致。由于充分运用舞蹈动作和舞蹈结构节奏的变化,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生活内容的舞蹈形式创造。
图式化
创作舞蹈从生活样式抽象为舞蹈动作图式,通过舞台空间创造具体可感、直观运动的动作形式的组织。每个动作都占据空间,在空间中呈现具体动作的外观形态,构成一种图式。图式化不仅仅在局限单纯动作自身,它还在突出人物形象,渲染意境,张弛节奏,利用舞台移动线,在舞台空间进行以人体动作作序列的有组织的舞台画面的转换流动。其平衡与对称,分散与集中,单线与复合线,使构图合理组接,变化流畅。其动与静、正与反、明与暗、增与减,都使画面形成鲜明对比,使层次更加清楚,使主题更加突出,增强艺术表现力,铸就了作品的形式感和风格。近几年来,舞蹈艺术的风格注重图式化的追求,一代舞风渗入着一代文化气韵,淡化了传统动作的“小法儿”,强化了整体画面的运动。运用大写意的手法,营造了空间气氛,意蕴深邃,气势恢宏,折射着时代精神和风貌。例如,苏时进的《一条大河》,张继刚的《好大的风》,特别是房进激的《小溪·江河·大海》,用最简洁的圆场步,在舞台构图上运用横线与直线、平行线与交叉线、圆形线与曲线的移动,使画面似流水行云,水银泻地,又如曲径通幽,旋涡迭起,一幅幅绚丽多姿情景交融的画面变化,充溢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们带来一股清新、强劲的时代之风。
三、身体操练动作的情感化和寓意化
罗丹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艺术就是感情。”任何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现都离不开情感这个重要因素。舞蹈是一门情感艺术,情是舞蹈艺术内在生命的核心。它一方面是艺术家情感的独特体验,这是一种内心感受。是对客观事物敏感的情感捕捉和情感概括,是发自内心感情的激荡,将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印象物化为相对应的知觉意象,而将这些意象心灵化,以强烈的情感冲动传达人生的感受,凝聚到直观新颖、别致的艺术形象之中。另一方面是艺术形象中的情感流露,把人物内心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不同色彩的情感形象性地表达出来。这情感的魅力不是单一的平淡的感情,而是情感的张力——复杂情感的冲突和一致,紧张和松弛,激动和安静,上升和下降等物化于每个动作之中的。正如日本现代舞蹈家邦正美讲:“舞蹈不单是把舞步和固定的程式组合起来的机械的动作,更必须是用身体把人的内心表达出来的艺术。”因此,情感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艺术的表现内容,只有使操练动作充满着情感,才能使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
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动人心魄的作品,是从他心底流出的黄河儿女情,迸发着对生他、养他这片热土的爱,因此他的作品,充溢着鲜明的生活气息,蕴藏着浓厚的乡土情韵。像舞蹈《一个扭秧歌的人》,一曲原汁原味的秧歌调,唤起一位老艺人的回想。他眯缝着双眼,摇晃着脑袋,甜滋滋、美滋滋、嗲滋滋地追忆着伴随着他一生的秧歌,他心醉神迷,渗入骨髓,仿佛看到自己年轻时扭秧歌的火爆场面,如痴如狂,至死方休。一个活生生的秧歌艺人的形象,把情洒向观众,催人泪下,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舞蹈形式的创造区别于纯动作形式的杂技和体操。任何舞蹈形式不管它的节律变化如何生动,不管它的图式转换如何使人目不暇接,不管它的情感宣泄如何淋漓尽致,其实质是特定时期的社会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升华。确定动作之形及其表现功能,都应载负着动作的内容,使动作形象与内在意蕴相吻合,去构成对现实世界的象征观照。动作可以一般地去象征,也可以一般到个别去寓意,传达一定的文化意义。《荷花舞》中的清荷出水,寓意出污泥而不染,不入俗流,洁身自好的人生价值取向。满池盛开的荷花又寓意着祖国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小溪·江河·大海》通过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寓意着滴水汇成河,百川终归大海的哲理性主题。《黄河魂》通过一群船夫与惊涛骇浪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画面,寓意着我们伟大民族,不屈不挠,坚韧顽强,像东方屹立的巨人,震撼天地。
总之,艺术最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对舞蹈形式的探求和创造,应当成为创作过程的中心,应当根据自己采用某种艺术题材、门类的特征要求,不断创造、锤炼新的形式,以自己独具风格的劳动成果,为不断寻觅独特的舞蹈形式,而倾注独到的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