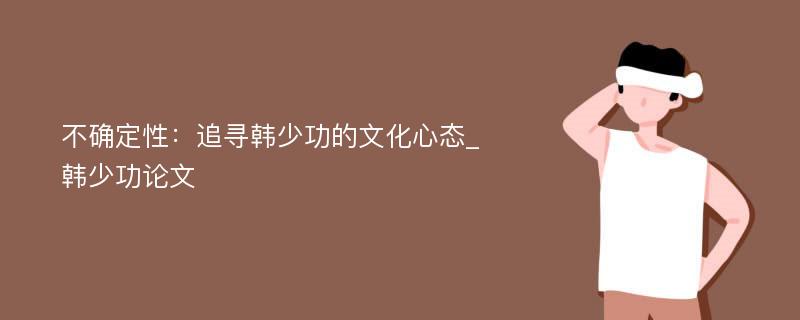
不确定性:对韩少功文化心态的追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心态论文,文化论文,韩少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次关于“九十年代的文化追寻”的对话中,韩少功用他构想的“过程价值论”对文化作了初步的阐说,其中有一段:“我反对民族文化的守成姿态,乡土也好,传统也好,民间文化也好,任何基于守成原则的相关研究都是没有前途的,都是文化‘辫子军’,而只有把它们当作一种创造的资源时,它们才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必须慎用。”〔1〕这一阐说很富理性味,可见, 文化应属韩少功自己所说的“想得清楚的事”,可是,我们也得正视这一事实,即对文化之事的言说构成了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这一小说族系中一条不隐的血脉,当韩少功声言“想得清楚的事就写成随笔”之后又说“想不清楚的事就写成小说”,可见文化又一直是他所“想不清楚的事”,那么,我们相信哪个韩少功呢?是写作文化随笔的韩少功,还是作小说演绎的韩少功?是“爸爸”“×妈妈”式取舍分明的韩少功,还是“栀子花茉莉花”式模棱两可的韩少功?文化到底是他想得清楚的事还是他想不清楚的事呢?其实,当作这种追问时,我们无意之中堕入了韩少功网取世界的不确定性圈套。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韩少功的文化心态。
一
不确定性不应被理解为认知主体的心智相对贫弱以致在面对认知对象时的无所适从,它其实是对象世界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一状态具有巴赫金所说的未完成性和不可论定性,这种特性是活生生的生活辩证法的精髓所在。对韩少功来说,不确定性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它也是其整个文学创作风格的美学追求与具体作品的构造术。
就其作为一种构造术而言,不确定性在韩少功的小说中也无一定的模式可循,它既可是《谋杀》中主人公对自己时空位置的疑惑,对自己所言所行的不确信,以致失去或放弃对自己言行及处境的言说权;也可是《梦案》中现实与梦幻间设防的坍塌,梦可成真,真可成梦,真与梦被置放在同一个层面且进行着互动性介入,韩少功认为这种真幻同眠正是艺术本身的需求,艺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梦幻中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2〕要在其间划界自守, 明确定性决非易事,也无必要。此外,作为这种互动性介入的纵向投影,是官修正史与民间传说的相互否证,《爸爸爸》中关于鸡头寨的来历,德龙的古歌唱得头头是道,不怕人不信,却被到过千家坪的史官轻易地否定,鸡头寨从此便游离于传说与信史之间,终无定所;《马桥词典》中的马桥更是因其史传品格的缺失构成了对信史独白式话语的一种质疑。当然,对诸种不确定性我们尽可作见仁见智的评说,但我觉得如下两点似应考虑到:
第一,不确定性是韩少功小说的一种创作策略,旨在拓展小说的话语空间。他认为传统小说太注重主线因果,结果,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读者的视野,人们只能在小说预先设置的情节,图式中被动地导入作品世界,作品提供什么,他才能感受什么,作品提供了多少,他才能感受多少。作品成了读者背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任何超出作品预设意义的阅读都被作品内在地拒斥。这样,小说话语空间的自我封闭与圈定在另一极上严重束缚读者的想象力和对作品的参与意识。韩少功的不确定性就是对传统小说主线霸权合法性的质疑,力求解放文本的同时也解放读者。《马桥词典》立体式的网状结构可以说是这样一次成功的尝试,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入口走进马桥,在无须路标的提示下,作兴之所至的随意游走。
第二,不确定性是韩少功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也是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有一段时间,韩少功曾被视为“怀疑论者”,他不仅怀疑除禅宗以外的所有宗教,甚至对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的“我”(韩少功本人)也颇生疑义,他对“我”是什么意思这一问题只能作出“多嘴多舌的沉默”,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来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某种代理,某种容器和包装。没有任何道理把我的心智注册为‘我’,并大言不惭的专权占有它。〔3 〕”如果说笛卡尔曾通过“我思”来确证“我”的存在,那么韩少功这里,越是“我思”,“我”就越不可被确证,就越具有不确定性,“我”的存在全然是“非我”的聚合,“我”与“非我”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我”命定要被注册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信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信码,我的品格在语言中得以充分的展示,因而对语言的清查就意味着对人清查,也意味着对世界状态的清查。
那么语言的真实情状又如何呢?任何语言都有“强以为名”的无奈与尴尬,它得用逻辑的形式表达非逻辑,用确定的形式表达非确定。“认识的主体在不断流变,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的流变,它们组成并不断转换着词的隐秘含义,层层叠叠,暖昧不清,它们只是在某种社会读解默契之下,才被人们有效的探明。〔4〕”因此, 语言符号与真实总有或多或少的疏离,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此外,语言在揭示人们已认知域的同时,也暴露着人们认知的盲区,而且,它同时寓有人们认知的成就和无能,共栖着真知与误解。语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了无歧义地直奔所指对象的。对语言的这一特点,韩少功是通过一种极端的语言现象——对义词与兼义词来透析的。所谓对义或兼义是指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共栖于一个词符或字符的现象,比如“不知好歹”中的好歹,比如“乱”可兼训“治”等,这一现象正应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洞鉴。语言背后澎湃着的生活激流,是充满丰富性与能动性的,它无法用逻辑来规范与驾驭,所以语言的陈述只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术,它近乎一种智性游戏。当这种游戏进行到一定程度,完全可能引起语言的“内爆”。正是在这种可能的“内爆”中,韩少功憧憬着一种新的语言观:“为了使心智从语言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应该视言语过程比目的更重要,‘说’比说‘什么’更重要。”〔5〕只有这样, 语言才能更好的诠释世界。此时,它将不再自诩能说什么,它对可靠的结论和终极真理也了无兴趣,它只关心过程本身,它明白任何对确定性的允诺都只能助长人们心智的惰性。在语言追随过程这一无限的朝向运动中,纯然的真实已被放逐,它无家可归,只能流浪在现实的此岸与虚幻的彼岩之间而无以登陆。如果说世界还有真实可言的话,那就是这种流浪者的不确定性。
通过对语言的清查,韩少功直抵生活的本质——不确定性,它在韩少功身上具体表现为一种流浪的心性,他说:“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6 〕流浪旅途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独处方式,每一次的出游都意味着精神之岛的又一次重筑。这里,我们无须指实韩少功的海南之行,也许更有意义的倒是他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回访故地”这一主题。
二
“回访故地”对韩少功来说并不是一种身体的放松或精神的休闲,也不是对尘嚣都市的逃避,更不是精英式的因愧疚底层民众而曾经有过的“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历史辉煌的昔日重现,而是一次次的精神历险与流浪,一次次文化信码的转译与破译,一次次对自我的追寻与体认,因而,其意义既不在离开寓居地时的莫名的焦虑,也不在顺抵故地时的释然,而在于回访过程中自始至终的一种临界状态,摇摆于都市的工业文明与乡村的农业文明之间,摇摆于市井文化与村俗文化之间而无以取舍,因为我对这两种文化有所同情的同时也有所苛责,哪一方都不可能成为我心安的栖居地,我被抛于城市与乡村的旅途。
一方面,随俗从众的心理使“我”在知青返城大潮中作别留有知青梦魇的汨罗农村,成为一个城市人,步入城市文化的共名状态,这种共名状态对一个普通的城市人来说也许无所谓,甚至还是他们的一种梦想,但对一个清醒的且具个性的文化人来说则可能会引发精神的苦痛,因为城市里“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色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几乎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理或名理,诸如后现代或后结构。〔7〕”另一方面, 曾经带着心灵创伤从那里逃离的乡村及其文化的那种无名状态通过远距离的观照后,又成了他们心仪的对象,那里,类似自然生命群落而呈现出质朴与原真的生命面貌,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特点足以抗击城市文明的矫饰与纤弱,乡村的无名状态也许更有助于“我”的个性的生成与展示。无名与共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共名通常以个性的丧失为代价,个性被抽象为空洞的形式并借助同样空洞的话语来支持;而无名则是个性显露之前的沉寂,它尚未获得话语能力,但作为另一种强大的未被认知的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它的存在无庸置疑,它迟早会得以正名并被纳入到可以对话的文化语境中。正是在为底层文化正名的胆识与才具这一点上,我们认识了两位当代作家:韩少功和张承志。
张承志的草原小说系列除了对蒙古知青生活感恩外,更主要的是为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正名,他以草原“养子”的身份开拓着文化正名的荒芜之路,以期真正的草原之子来成就这一伟业,因此,他的文化使命是抗击学术和文学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学,民族学领域中横行的无视民众主体,缺乏真实体验的某种殖民主义色彩浓重的风习,这种风习曾使游牧文化因受“警察式语境”的压迫而不具备与其它文化对话的基础,那些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对它更是一无所知。这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抗击激起了血性的张承志近乎宗教迷狂的文化激情,为找回失去的“索米娅”和“金草地”,他开始了九死不悔的流浪征程,尽管“索米娅”已永远地连同那绚美难再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太阳沉落于记忆之海,尽管“金草地”被永远阻隔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但那种朝圣者遥遥跋涉的悲壮却总令人激情澎湃。
张承志朝圣者式的不悔追寻也是通过“回访故里”这一主题来表现的,这当然不仅仅指白音宝力格的回访草原,也不仅指额吉的重返金草地,它还包括红卫兵们的漫溯长征路。但过于强烈的功利性和忏悔心态使每一次的回访都带有不欢而散的遗憾,在《黑骏马》中,我(白音宝力格)太想切入草原生活的内里,将回访的视角窄窄地对准索米娅,甚至为了这一视角的纤尘不染而一直排斥着黄毛希拉这类草原的烂仔,正如用显微镜来观察人的皮肤一样,曾经魂牵梦萦的草原也现出了粗糙的一面,我带着心安的失望离开了草原,我的养子心性也于此暴露无遗:“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之子,因而他们有可能在肤浅或隔膜的同时,也必然保留了一定的冷静与距离——这种保留,或者会导致深刻的分析和判断,或者会导致他们背离游牧社会。〔8 〕”背离总是伴以心灵与情感的创痛,伴以不堪回首的记忆,所以在《牧人笔记》小序里,张承志不无沉重与伤感地说:“这本《牧人笔记》恐怕是我此生关于蒙古草原的最后作品了。”可见,“回访故地”对张承志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与张承志“养子”身份不同,韩少功对故地的回访更多的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进行的,因而多了一份理智少了一份激情,这份理智使他能走进故地每一个甚至不美的角落,尤其是史遗风物对他有一种惹人心动的亲切感,方言古语,畸人畸行,在他看来都是一种文化的“活化石”,镌满着历史的沧桑,故地俨然一部文化大词曲,故人故物则是一个个蕴涵丰富的词语和文化信码,他的回访就是要读解破译这些信码,重构并激活信码后面的原生文化形态——村俗文化。这种文化在《马桥词典》里获得了较完整的表述。韩少功的每次回访仿佛都有所收获,因而要比张承志幸运得多,张承志总是迷失在文化追寻的路途,这也许可解释“回访故地”这一主题在韩少功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一现象吧。其实,他的每有所获还得归因于他与故地特有的关系——若即若离。在这种关系中,他的视野相对要广阔得多,不会注目于单个的某人某物,这使他能超越个人利害关系包括情感关系的考虑,他不会偏执地去辨识故地故人不变的一面,还会认可已变化甚至面目全非的一面。《归去来》中,我(马眼镜)的回访过程实际上是自我的追寻与确认过程,在故地,我无意中遭遇到一些似能确证我的人证物证,似曾相熟却又无法确信,但最终还是拼凑出一个面目模糊的“我”。尽管我一直在内心作顽强的拒斥与否认,但一种同样强烈的认同感也相伴而生,抵拒越强,认同感也越强。在某种意义上,《归去来》中的我可视为韩少功所有回访题材的主人公。所谓的归去来也不是传统语义学所说的复词偏义,如陶渊明的挂帽而去,而是一种对义,即来去两可的状态,这一状态有无限的延展性,我的时空范围被大大地拓展,凡是能叩动我的理智之弦的风物人事都在我的网取之中,因而每一次的回访都有每一次丰富,而且这种丰富拒绝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化,即拒绝被抽象凝固为一套规范的权威话语系统,因为韩少功更注重的是对民众心态及生活观念的体认,而不是对方志及史遗文物这类死的化石,标本的鉴定,更不用说通过这种鉴定来建立一套话语规范以剪裁其它异质文化。
可以说,韩少功的文化态度是宽容的甚至超然的。在诸种异质文化中,他不会臣服于任何一方,他像一个世故的老人有一种洞彻天机后的平和,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比如我们不能说可口可乐式的文化就一定比盖碗茶式的文化进步,因为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并无语种的高低贵贱,而只有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恶质化。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被韩少功在小说里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其实这也是寻根小说的一个共同的创作特色,具体表现为:石仁——鸡头寨(韩少功《爸爸爸》),鲍仁文——小鲍庄(王安忆《小鲍庄》),滨江大街的灯火——福奎的小草棚(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这种对立也就是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作者没有将情感投向任何一方。如果说作者在行文中无意地漫画了石仁,鲍仁文,对外来文化表现了某种不恭的话,那么,作者又通过鸡头寨的再次迁徒,鲍仁文作家梦的成真以及小鲍庄人喜剧化生活的渲染淡化甚至取消了土著文化虚幻的优越感。尽管创作本身要求作家择取土著文化的立场突出其对外来文化排斥,抵制,冲突的一面,但这种立场又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无意成为土著文化的捍卫者而是尽守中立。
在韩少功看来,异质文化之间这种取舍的两难,正是生活不确定性本质的准确体现,有感于此,韩少功在《马桥司典》里提出了“栀子花茉莉花”式的价值评判模式以修正隐含在《爸爸爸》中的“爸爸”“妈妈”这一非此即自的二值判断模式,在小说中,韩少功是这样解说“桅子花茉莉花”的:“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9〕”
三
这里,我们无意深究这两种价值评判模式所体现出的中西哲学与文化差异,只想说明韩少功的不确定性文化心态根植于物我一体,天人相应的东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钱穆先生认为,与西方文化起源于滨海地带及近海岛屿的商业活动不同,东方文化起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农耕活动。
商业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它起于内己的不足,内不足则向外寻求,自然就会养成一种战胜与克服欲,敌意成为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基本态度,在其心智上,无论世界观或人生观都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天人对立,人与人之间的敌我对立,哲学理论上的主客体对立,分析成为他们把握世界的技术性手段,“始,证,辩,结”的因果推演是他们接近世界的逻辑构成的必要步骤,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获致世界的确定性本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就内在地发育在这一追求中。
与西方文化重分析,主外向不同,东方文化重整合,主内敛。这与农耕生活不无关系,农耕生活通常是自给而无须外求的,对气候,雨泽,土壤,人们无能为力,这便养成了他们静守的心态,所能作的就是力行以德配天,求天人的和合,当以这种平和的心性处世时,就可少一份偏执,一份唯我独尊的霸气,成己即成人,成人即成己;当他们远瞻前路时,目力不会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而是时时顾盼已然的立足之处,形成一种潆洄委曲,绸缪往复,容与中流的回旋式节奏,所以,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无返,而是回旋往复的。”〔10〕也许这正是中国式的人生智慧,追求一种“未封”的境界,所谓“封始则道亡”。所以在庄周梦蝶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恐怕不在到底是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周这一疑难的最终解答,而在于庄周与蝶的关系,即物我不分的混沌情状,也就是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形成了中国哲学及文化诗意的一面,“天人合一本是一种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中国哲学大多是哲学家们对自己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或理性表达。〔11〕”它依据直觉所得到的模糊感受,完全不像主客二分式那样靠理性找概念的准确性,真正的诗意是藐视概念与法则的。
韩少功的不确定性文化心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意文化的现代版,他既不信仰任何终极真理,也不信仰决定论。他说,真理和理想不是体现在某个目的性结论里,而是体现在心智的求索过程中,因而不大在乎任何结论的可靠性。但他又没有投向后现代主义“怎么都行”的那种最虚无同时又最实利的状态中。恰恰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给了他的确定性另一种丰富的内涵。
后现代主义可视为西方文化史上出来已久的一股潜流的喷涌,其喷涌之速,之烈使其本身也乱了方寸,没了章法,显出一种恶质的不确定性。所以,韩少功不无调侃地说:“后现代主义——眼下一切不好解释的文化现象都可由其统称。〔12〕”这里,我们不妨对后现代主义试着追踪一下。
当西方主客二分式及主体性原则在近代获得相对完整的表述形态——认识论哲学时,世界在人们的眼里显出整一,稳定且充满智性图景,同时,古老的本体论哲学,又不时地给这一图景注入神秘性,二流交汇便铸塑了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由强调规整而来的等级制度,由强调历时关系而来的历史繁衍性,由崇尚权威中心而来的叙述性以及观察世界的形而上视角和解释世界的本体论信仰,整个社会被筑成了一个浑然结实的巨型金字塔,个性的人被再次势入阔大的共名场中,确定性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信仰。
对确定性的拆解便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怎么都行”这一达达主义的口号可以看作他们的行动纲领,“怎么都行”意味着对此时此地的现实全盘接受,原则性,价值标准在这里已无藏身之处,伊哈布—哈桑在谈及后现代主义时认为,后现代运动是朝着某种否定自身的艺术方向的冲击力,它表明了一种朝向沉默的运动,这一运动有两种特征:1 )语言的消极重复,自我破坏,恶魔般的,虚无主义的;2 )其积极的静止,自我超越,神圣的和绝对的。世界不再有中心意识和权威话语,只有“流行的时尚”及时尚后面的不确定性,所以,利奥塔德不无感慨,这个时代真可谓一个宽松的时代。一切在金钱与购买力这一低格的生存层面上相会并狂欢。艺术可用来自反自嘲,理论观点可以出尔反尔。一句话,人们尽可以在不确定性这一障眼术下为所欲为。
后现代主义这种恶质的不确定性及“怎么都行”的作派构成了韩少功文化关注的当然话题。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逆子贰臣,但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它在中国却不乏同道者。在韩少功看来,恶质的世俗化与反社会性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准确注解。首先,后现代主义者们亵渎了历史上旨在针对神权,以期结束压抑人性权利关系的世俗化,为沉迷肉欲,追逐物利的时尚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的世俗化是浅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它是掠夺者的世俗化,少数精英分子,强权者的世俗化,它既缺乏民众基础,又缺乏精神的尤其是审美的维度,长此以往,它最终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激起一种新的宗教迷狂。其次,作为这种恶质世俗化的必然发展,物化的消费社会使人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独处的幻想者,责任感不复存在,道义感不复存在,人际关系冷漠且脆弱。生活世界被各种人造的冰冷的构件如钢筋水泥,视听传媒,计算机及其它工业产品切割分块成一个狭小的单子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按相同的程序操作,按相同的规则游戏,情感钝化,灵性消失,人沦为机器的附件,“我们虽在不同的城市,但却在同一时间,相同的交通灯下驻足。绿灯一亮,我们都穿过街道。〔13〕”卡兹的这一说法形象地描绘了后现代者们的生存境况,除了“红绿灯”外,他们无暇顾及也无心顾及他人。所以,韩少功说:“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为哲学。〔14〕”社会性已遭放逐。
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还是在与他们所标榜的“内在性”相对立中获取其存在理由的,而不确定性与内在性的二元对立实质上仍是西方主客二分式原则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所以能在本世纪赢得人们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它奉行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激进的反叛策略表明着它与现代主义及前此传统的不同道。对韩少功的不确定性则不能这样看,它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诗意传统之中,既表明了他对世界的总的观点,也表明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而这一切最终都内化为他独具个性的文化心态。
注释:
〔1〕《九十年代的文化追寻》《书屋》1997.3。
〔2〕,〔3〕,〔4〕,〔5〕,〔6〕,〔7〕,〔14〕韩少功《完美的假定》第35,37,39。234,106页。
〔8〕张承志、《牧人笔记》第253页。
〔9〕《马桥词典》第362页。
〔10〕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 第440页。
〔11〕见谢龙《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第57页。
〔12〕韩少功《夜行者梦语》第11页。
〔13〕见佛玛克等编著《走向后现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