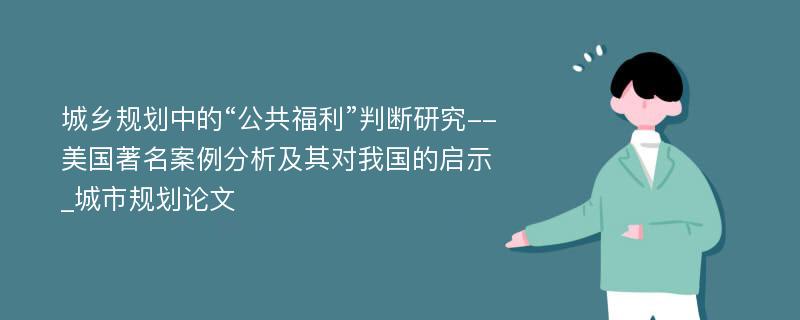
城乡规划中“公共福祉”的判定研究———则著名美国案例的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祉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著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78(2012)02-116-08
近年来,针对我国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问题,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在多地实施的备受关注的住房“限购令”。与之相对的是,自2006年起的住房供给源头上的调控,其中就有针对涉及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宅土地供给的住房建设规划,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对于城市规划的调控要求。在城市规划中保障中小套型可负担住房的调控思路:在城市规划中增加住房建设规划的编制,其中必须明确“当地新建商品住房总面积的套型结构比例”,也就是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住房不得低于商品住房总面积的70%(以下简称90/70要求),通过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居住用地明确提出住宅建筑套密度、住宅面积净密度两项指标来实现这一指标。①这一思路在此后的调控中多次被重申和贯彻。②
城市规划是空间资源如何分配和利用中的核心制度,法律规定其承载着维护公共安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③从宏观调控的诸多措施中也可以发现,在住房保障这一民生问题的解决中,城市规划也成为其中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对此现象,法律的逻辑首先并不在于追问这些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而是关注宏观政策本身及由此引发的行政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具体而言,每个城市一刀切式的90/70要求,以及被分解落实到城市中的各个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具体的住宅建筑套密度、住宅面积净密度是否符合了城乡规划法所要求促进的公共利益?
面对城乡规划中所应考虑的从生态环境到资源节约,从地方特点、历史风貌、民族特色到区域人口发展,从防止污染、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到住房保障等诸多要求,如何判断城市规划合理地权衡了这些因素,最终实现了公共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法律难题。
关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一般界定,法学学者从实体标准和程序装置等思路进行了卓有价值的讨论,④对于具体领域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也已有深入研究。⑤同时,关于城市规划领域中公共利益的研究也从多个角度展开。⑥
本文的研究在于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主要法律手段——区划条例(zoning ordinance)⑦司法审查中的著名案件“劳雷尔山Ⅰ案”(Mount Laurel Ⅰ)判决的解读分析,指出住房保障的规划考量是如何从“公共福祉”中找到合法性的基础,归纳法院关于“公共福祉”的判断方法以及其对于中国法的意义。本文的研究并不是要归结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的定义,也不是提出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判断的唯一标准,而是提供一种如何判定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的思路,以为借鉴。
一、劳雷尔山Ⅰ案的背景和案情
(一)全国范围住房供给的缺乏和排他性分区的存在
自1949年起,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与住房供给相关的法律,立法者已经意识到并试图解决日渐突出的住房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也已经在众多案件中表示出认识到住房供给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⑧当时,缺乏充足的住房供给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然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因素相比,区划法律制度更增加了住房压力。⑨区划(zoning)作为美国土地使用管制的主要手段,是实现城市规划的核心法律制度。州政府授权地方政府立法制定区划条例,大多数市镇议会通过各自的区划条例,设定多种综合指标(例如用途、建筑高度、容积率、地块基地面积和房屋底层面积等),对土地使用实行分区的无补偿的管制。在市镇的区划条例中设定的各种限制会影响甚至排除某些土地开发建设的方式。有时基于财政考虑,试图吸引更多的工商业,市镇在区划条例中对基地面积和住房底层面积提出尽可能高的要求,甚至规定一套住宅中卧室数量的限制或者彻底地禁止多户式或公寓等住宅类型。⑩有些限制使得低收入人群能负担的住房被彻底排除出了整个市镇。
这种排除特定的团体或者阶层的区划通常被称为排他性区划(exclusionary zoning),被认为筑起了种族和经济隔离的高墙。这种带有限制中低成本住房建设的地方区划十分普遍,并且基于各种理由得到了法院的支持。(11)
(二)新泽西州的处境与司法的立场
劳雷尔山Ⅰ案件发生在住房紧张突出的新泽西州,该州是当时全美最拥挤的州,每平方英里上的居住人口比例是最高的。更多的人拥挤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更容易产生土地使用的冲突。(12)该州存在着适合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承担能力的体面住房的极大需求,而这种庞大的需求甚至被认为已处于“危机”状况之中。(13)
早在1962年的维克斯诉格罗斯特镇委员会案(14)中,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霍尔(Hall)法官在判决的不同意见中就首次挑战了排他性区划,质疑了在整个市镇排出了移动住宅停车场这一用途的规定。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成为司法界的主流。
直到1975年南伯林顿县有色人种协进会诉劳雷尔山镇案(通常被称为劳雷尔山Ⅰ案),(15)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最终判定发展中市镇有义务通过它们的土地使用政策和规制来承担地区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的公平份额,并基于区划条例没有履行这个义务而判决排他性的区划条例无效。该判决的出现标志着住房供给问题进入了区划条例审查时法院考虑的视野。“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美国土地使用法在一些基本和重大方面处于转型期”,(16)劳雷尔山Ⅰ案正是这个时期的著名案例,表示法院“准备执行立场的重大改变”,甚至当时有学者认为它是“自欧几里得案件以来最重要的案件”。(17)
(三)案件的事实与争议
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是劳雷尔山镇,位于伯灵顿县的西部边缘。该镇由于高速公路网有一个极好的公路运输的战略位置,从1950年到1970年经历了城市和人口的飞速增长。(18)
根据该镇在1964年通过的区划条例,市镇29.2%的土地,大约是4121英亩被分为工业区,但在初审时只有不多于100英亩土地被实际用于工业用途。在条例中被规定用作零售商业用途的土地量也相对较小,有169英亩,大约是总数的1.2%。该区划条例规定了剩下的地区为四个居住区,分别命名为R1、R1D、R2、R3。所有的居住区只允许单户分离式的住宅,即每块土地一幢住宅。复合式的住宅、公寓(除了在农场上给农业工人居住的)和活动房屋根据该条例在这个镇全部不被允许。此外1967年后该镇批准了4个计划单元发展。在这4个计划单元发展中多户式的住宅以租用花园住房、中等或者高档公寓和连排房屋的形式在该镇第一次被允许建设和销售。但是严格限制了多于一个卧室的公寓;不多于两个学龄儿童的家庭可以居住在两个卧室的单元中;多户式住宅的每个单元中如果多于三个上学儿童,则要求开发者支付超出的教育系统的开支。1972年9月修订了区划条例,增加了一个新的区——R4区即退休者社区,在该区允许建立多户式住宅。但要求固定居民至少是52岁,最多只允许一个超过18岁的子女和父母一起居住,并且每个住宅内不得超过三个固定居民。
由南伯林顿县有色人种协进会等组织和个人组成的原告要求法院宣判该条例无效,并颁发禁止令禁止该条例的实施。
法官总结了劳雷尔山Ⅰ案的争点:像劳雷尔山镇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市镇是否能够合法地通过土地使用规制体系使得中低收入住房在这个市镇的提供变成实质和经济上的不可能;同时这个争点蕴含着更宽泛的问题——市镇是否有权限制住宅种类和使得住房种类的选择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的义务。(19)
二、城市规划的合法性基础——“公共福祉”的判定
在解决这个区划规制的合法性问题时,最关键的是审查条例是否符合联邦、州宪法以及州区划授权法。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这就要求“区划规范和其他任何运用规制权(police power)的法律一样必须促进公共健康、安全、道德或者公共福祉(最后一个词看上去如此广泛似乎可以包含其他三个词)”,“如果一个区划条例与公共福祉相悖,那么就是无效的。”(20)因此具体区划规制是否符合公共福祉,或者说“公共福祉”的判定成为了该案的关键。
法院遵循了先例——欧几里得案判决(21)的观点,认为区划规制的合法非法只是一线之隔,很难精确界定,是随着情况和条件而变化的。因此,其结合该案的土地使用规制的特定情况解释了促进或者说符合“公共福祉”在此所应该考虑的具体因素。
(一)“公共福祉”中“公共”的判断方法
1.不限于规划制定主体所辖范围。
法院在“公共福祉”中寻找土地使用规制的合法性时,首先指出确定“谁的公共福祉”的重要性。法院认为,通常地方在运用由州授予的规制权(police power)时,考虑的“公共福祉”仅限于制定规制的自治市的福祉,这在规制没有外部性时,基于制定地方利益的规制是正当的。但“如果规制具有‘外部性影响’(external impact)时,在自治市镇范围之外的利益不应该被忽视,而是应该被承认和考虑。”(22)
在法院看来,区划条例规制的范围是依据通常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划定的有一定偶然性的市镇边界,这些市镇边界的划定很多情况下基于地理、贸易或政治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并不涉及土地使用区划规制的问题,因此现实中确定区划条例适用于市镇这一行政区域边界并没有考虑与区划条例相关的因素,比如“居住区域的发展方向”和“工业的集中的发展方向”。(23)这些因素并不为人为的市镇的界限所左右。同时“交通方式的变革和居住条件的变化”(24)因素也造成了规制会对规制适用范围以外的区域造成影响,使得区划不再是一个市镇范围内的事务。
因此法院更强调一种“非地方的‘公共福祉’解释的路径”,更赞赏“区别于单纯狭隘的地方利益视觉的宽阔公共福祉的视角。”(25)
2.受规制影响的地域和人群的考虑。
更宽阔的视野对于土地使用规制合法性意味着什么?这可以在法院之后的论述,特别是市镇在土地使用的区划规制中具体义务的确定中找到答案。
法院认为正当的区划规制不能够仅限于市镇边界内利益的衡量,不能够仅考虑市镇居民从规制中将获得福利;考量的福祉范围从地域上说,应该扩展到“州内的地区”范围,从人群上也就是那些可能渴望居住在这个市镇内的各阶层人群。法院从地域和人群两个角度结合扩展“公共”的范围。
法院认为确定“地区”的范围是会“因为情况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每个案件的固定和便捷的规则”。法院划定了该案中的合适的“地区”的范围——从卡姆登市中心20英里左右为半径的半圆内的卡姆登、伯灵顿和格罗斯特县的部分——也就是其之前指出的“南新泽西大都市区”。
可能渴望居住在某个市镇内的人群,这依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法院是基于劳雷尔山镇当初区划的考虑进行了三次扩展来使得这个概念清晰化。首先要求打破“市镇内居民”利益考量的限制;其次是认为初审法院要求提供“现在受雇于或者合理期待受雇于该市镇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信息是中肯的,从而承认了“劳雷尔山镇相关”人群的利益;最后州最高法院认为其考虑的视角“更宽阔”于初审法院,也就是考虑到其划定的城市发展产生的“地区”的需求。
扩展的思考角度可以在法院的论述中找到理由。法院曾提到“这并不是说一个发展中的市镇能够忽视在其辖区范围内的那些穿梭到其他州工作的人们的住宅需求”。(26)这点结合之前对于外部性分析中考虑的“居住区域的发展方向”、“工业的集中的发展方向”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可以推断出:由于存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的现象,工商业发展和居住供给发展不仅在市镇内甚至在城市发展中一体化的地区内也存在不匹配的矛盾。
由此法院超越地方主义的规制思路,提出了“公共福祉”扩展理解的要求——打破以市镇界限为区分的内外部的观点,考虑土地规制引发的发生在市镇之外的地区人群的福祉的影响,即所谓“外部效应”;将土地规制影响所及的范围纳入规制主体考量的“公共福祉”的范围中。
(二)“公共福祉”中“福祉”的判断方法
在关于“谁的公共福祉”的理解上,法院采纳了宽阔的解释路径之后,接着需要确定的是土地的住宅性使用规制中如何理解“福祉”的要求。
1.绝对构成要素——人的基本住房需求。
在法院看来,住房的获得,作为公共福祉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问题。(27)因为“住房和食物是人的最基本需求”。(28)法院在评价一个公共团体的普遍的福祉时,着眼于组成该团体的个体的福祉,但其并没有去具体衡量每个个体的福祉,而是从阶层的角度,将每个阶层人的福祉总和作为普遍的福祉。正是依据这样的逻辑,州最高法院认为“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合理地提供充分的住房是促进公共福祉的绝对要素”。(29)
2.构成要素间的衡量——重要性和手段目标间的不可替代性。
各阶层充分的住房是公共福祉的绝对要素,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区划仅为了促进这一个要素而编制和实施的。在劳雷尔山Ⅰ案之前,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格鲁伯诉迈耶和力登镇镇委员会一案(30)的判决中认为“发展中市镇可以合理地区划和追求工业可课税价值以创造地方一个更好的财政平衡,这样合理行事构成了总体规划的合法的一部分”。(31)也意味着“公共福祉”可能包含着多种因素,而当多种要素彼此之间冲突时,如何解决冲突因素之间产生的规制的合法性,成为该案中法院说理的关键部分。针对被告提出的支持区划条例的规制的理由,法院指出了其考虑的因素和思路。
法院认为,各阶层获得合适住房机会与追求地方财税平衡冲突时,保证可获得住房的多样性是规制的合法目的。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规制目的的重要性,法院认为各阶层市民合适住房的机会具有“基础的重要性”,不能为了财税的理由,排除或者限制住房的种类;
二是规制目的实现手段的不可替代性,法院承认了地方的政府和教育开支引起的沉重的税收压力,但是认为这必须由其他的政府部门解决,也就是这样的规制目的是应该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达到的。
从反面理解法院的观点,也就是规制若排除住房的某些种类,这是不能够通过其他手段得以恢复的,也就是说,构成要素的价值位阶是与达成效果的手段的可替代与否相关联的。因此法院认为“市镇必须首先为了人们的居住福利而不是为了当地税率的利益进行区划”。(32)
在讨论基于环境的理由规划排除住宅种类的合法性时,法院延续了上述思路。劳雷尔山镇提出基于环境保护的因素,应当规定镇的相当部分的地区为一英亩半的最小基地面积。对此,法院确认了生态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这些地区是“平坦的并且易于安装市政设施”,(33)市镇能够要求开发者改进或者自己进行安装,解决可能带来的排污和供水的问题。因此这样环境的危险和影响就不再是现实的了。由此,法院认为实现环境保护不必排除某种住宅用途。
正是基于各阶层合适住房机会的重要性和区划对于实现该目的是不可替代的,法院在衡量财税收支平衡和所谓的环境问题与区划排除住宅种类的问题时,认为提供住房的多样性从而提供各阶层人群获得住房的可能才是体现了“公共福祉”。
(三)“公共福祉”实现的双重属性——私人和公共行为共同作用的需要
在确定“公共福祉”的范围和内容之后,法院为了促进“公共福祉”的实现,明确了市镇在区划规制中所应负有的义务。
法院在劳雷尔山Ⅰ案中认定该镇的现实状况是——市镇的区划条例由于住宅种类、最小基地面积、建筑物临路距离、建筑物体积大小等过高的要求,排除了中低收入可负担住房的种类;同时存在着持续强烈的住房需求,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缺乏。
因此法院推定被告市镇在区划规制中没有承担两个方面的责任:消极的责任是市镇不能够采取规制或者政策,阻止或者排除满足那些希望住在市镇中的所有人的需要、希望的住房合理选择和多样性的合理的机会;而积极的方面则是市镇应该通过土地使用规制,积极地规划和提供这样的机会。
法院对此提出了应负有的义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了一方面不能够排除中低收入阶层的机会,也就是允许中低收入者能负担的住房种类的建设,而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提供机会,具体而言就是至少是“承担现在和将来的地区需求的公平份额”。(34)
从法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福祉”的实现,存在着自我实现和政府干预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存在政府不干预而由市场或者通过私人行为实现的一方面,同样还存在政府的区划引导私人活动以及公共企业营建住房等政府干预下实现的一方面。
这样的双重属性也说明了现代社会“公共福祉”实现的复杂性。“公共福祉”的实现问题虽然在劳雷尔山Ⅰ案中提出,但并没有实际解决,这也为之后的劳雷尔山Ⅱ案等一系列后续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活动埋下了伏笔。
三、判决对中国法的启示
劳雷尔山Ⅰ案判决之后,该镇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该判决所判定的义务,(35)后续又通过劳雷尔山Ⅱ案、(36)新泽西州公平住房法(37)和劳雷尔山Ⅲ案,(38)大约经历了近20年的缓慢时间,中低收入住房建设的壁垒才逐渐消除,中低收入住房得以更多建设。
后续过程中从司法到立法、行政的重心转移可以发现现代行政的积极形成功能对于“公共福祉”实现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住房紧张、经济隔离和居住隔离等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正是劳雷尔山Ⅰ案使得上述问题进入了司法的程序,将区划规制和住房危机之间的关系带入了公众的视野;法院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就区划规制中合法性问题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对于区划合法性的核心概念——“公共福祉”的崭新诠释,增加了区划条例修编的考虑因素,为区划的更趋合理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城市发展中的住房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和可能。
劳雷尔山Ⅰ案的法官的判决思路对于我国城乡规划的检讨将有着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城乡规划制定应考虑利益的范围
城乡规划是以对公共利益维护和促进获得正当性的,《城乡规划法》第4条第1款(39)对于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提出了诸多原则,涉及了多重应权衡的因素、利益。然而这些应当被考虑的因素和利益究竟应该限定在怎样的范围内?比如考虑了“地方特色”是否会和“区域人口发展”的规划相冲突?“地方”和“区域”应该如何理解和确定?
劳雷尔山Ⅰ案的判决中提出了更广阔的“公共”范围理解的角度。提出了规制者考虑被规制对象范围之外的地域或者群体的利益,以减少或者消除规制可能产生的负面的外部效应。
基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使用的外部性,在土地使用规制中常产生对被规制对象之外的效应。比如A区规划设定了A区住宅品质的较高要求,这可能将推高相邻B区的土地价格,也可能由此改变B区的居民构成,甚至可能影响A、B所在的地区的劳动力的流动趋势。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将A区的利益视为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
我国现有城乡规划体系意图通过总体规划由编制主体的上级人民政府审批这一制度,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进行利益的调整。然而,直接涉及到具体土地使用限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是由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完成,因此劳雷尔山Ⅰ案判决中“公共”范围的确定方法,对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也许更有借鉴意义。
(二)城乡规划制定中考量因素冲突的选择
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需要公平和公正地权衡多方面的利益。劳雷尔山Ⅰ案判决中关于什么是具体规制中应该考虑的“福祉”的分析指出了:利益逻辑上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规划中应当被考虑。判决从因素的重要性和实现手段的不可替代性角度出发的分析,为我们确定关涉具体的土地使用的城市规划中的合法性目的提供了思路。
当下“土地财政”问题受到广泛的质疑和讨论,而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土地出让的依据,那么在其制定过程中考虑土地出让金的财政收入是否合法?进一步说,城乡规划的编制中财政收支平衡的考虑,对于GDP增长等经济因素考虑是否能够成为规划的合法目的?如果判定这些考虑合法,那么在这些考虑与其他被认为的公共利益的因素相冲突时,应该如何平衡?
从劳雷尔山Ⅰ案判决的逻辑来看,需要区分应当被考虑的公共福祉因素的重要性,而重要性并不是判断选择考虑因素的唯一依据,还需要在重要的因素之间分析土地使用规制对利益的实现而言,是否是不可替代的手段,由此来判断这些公共福祉的因素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制定中应如何平衡甚至取舍。笔者认为这对于解决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考量因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是值得借鉴的方法。
通过对劳雷尔山Ⅰ案判决中关于区划条例合法性审查的分析,笔者归结的其中的“公共福祉”判定标准对于中国法上“公共利益”,特别是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的确定或能提供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同时该判决也揭示了“公共利益”、“公共福祉”这样罗生门式的概念理解的复杂性,体现了对于类似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解释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为公共目的而设的大量的规制法中,也将大量涉及类似的社会公共利益(40)的判定问题。在不同的法律条文、法律领域中如何处理类似概念的判定,将会是一个庞大而又重要的课题,本文也仅是城市规划领域中这一问题的尝试性研究。
注释:
①参见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和2006年7月6日《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2006]165号)。
②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中的十一条调控政策(简称“国十一条”),其中明确规定:“抓紧编制2010-2012年住房建设规划,重点明确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的建设规模,并分解到住房用地年度供应计划,落实到地块,明确各地块住房套型结构比例等控制性指标要求。”
③《城乡规划法》第4条第1款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3条规定:“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④2004年行政法学年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参见陶攀:“2004年行政法学年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之议题研讨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3-139页。关于概念界定的主要观点类型,参见胡建淼、邢益精:“公共利益概念透析”,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3-8页;杨寅:“公共利益的程序主义考量”,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8-10页;黄学贤:“公共利益界定的基本要素及应用”,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10-12页;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15-19页;胡锦光、王锴:“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11-14页;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28-31页。
⑤参见宋华琳:“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28-40页;莫于川:“私有财产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3-10页;姚佐莲:“公用征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美国判例的发展演变”,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第107-115页;王利明:“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第22-34页。
⑥可参见何丹:“城市规划中公众利益的政治经济分析”,载《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2期,第62-65页;石楠:“试论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载《城市规划》2004年第6期,第20-31页;徐键:“城市规划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一个城市规划案引出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8-81页;李泠烨:“城市规划合法性基础研究——以美国区划制度初期的公共利益判断为对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第59-71页。
⑦区划制度是美国城市规划的核心法律制度。参见邢铭:“从区划法看城市规划控制方法的改进”,载《规划师》2002年第10期,第54页。其在我国的对应制度一般认为是控制性详细规划,而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现行的城乡规划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⑧See Toward Improved Housing Opportunities:A New Direction for Zoning Law,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21,1972-1973,pp.331-332.
⑨See Toward Improved Housing Opportunities:A New Direction for Zoning Law,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21,1972-1973,p.332.
⑩See 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11)See Bruce L.Ackerman,The Mount Laurel Decision: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Zoning Reform,U.Ill.L.F.,Vo1.1976,1976,p.1.
(12)See Norman Williams & Ayna Yates,The Background of Mount Laurel Ⅰ,Vt.L.Rev.Vol.20,1995-1996,p.687.
(13)See Bruce L.Ackerman,The Mount Laurel Decision: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Zoning Reform,U.I11.L.F.,Vol.1976,1976,p.1.
(14)Vickers v.Township Committee of Gloucester Township,37 N.J.232 (1962).
(15)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16)Norman Williams & Tatyana Doughty,Studies in Legal Realism:Mount Laurel,Belle Terre and Berman,Rutgers L.Rev.,Vol.29,1975-1976,p.93.
(17)Norman Williams & Tatyana Doughty,Studies in Legal Realism:Mount Laurel,Belle Terre and Berman,Rutgers L.Rev.,Vol.29,1975-1976,p.94; see Norman Williams,On from Mount Laurel:Guidelines on the "Regional General Welfare",Vt.L.Rev.,Vol.1,1976,p.25.
(18)1950年,市镇人口数是2817人,仅比1940年多出大约600多人。它在几十年前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没有大型的住宅区或者商业或者工业实体。平民都居住在散落于县道路两侧的个人住房内。1950年以后,住宅有所发展,并且许多商业和工业开始进入。到了1960年,人口几乎已经翻倍达到5249人,到了1970年几乎又翻倍到了11221人。
(19)See 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0)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1975).该规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里程碑式的案件——欧几里得案(Village of Euclid v.Ambler Realty Co.,272 U.S.365(1926))中确定的。关于该案内容和意义参见李泠烨:“城市规划合法性基础研究——以美国区划制度初期的公共利益判断为对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第66-69页。
(21)Village of Euclid v.Ambler Realty Co.,272 U.S.365 (1926).
(22)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3)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4)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5)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6)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7)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8)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29)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30)Gruber v.Mayor and Township Committee of Raritan Township,39 N.J.1 (1962).
(31)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32)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33)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 (1975).
(34)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67 N.J.151,336 A.2d 713(1975).然而正如之前所述,法院确定了“地区”的范围,却没有明确“公平份额”的数额,其认为这个应由市镇规划专家、县规划委员会和州规划机构来确定。
(35)See Alan Mallach,Do Lawsuits Build Hou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xclusionary Zoning Litigation,Rut.-Cam.L.J.Vol.6,1974-1975,p.653.
(36)Southern Burlington County NAACP v.Township of Mount Laurel,92 N.J.158,456 A.2d 390(1985).该案判决中,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市镇有义务采取具体的积极性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比如密度奖励(bonus zoning)或者预留部分(set-aside)以实现中低收入住房的建设,同时还通过建立“建设者救济”来鼓励劳雷尔山式诉讼,还建立了三人特别指派法官审理制度来确定分担地区中低收入住房的公平份额。关于该案的具体评析可参见Martha Lamar & Alan Mallach & John M.Payne,Mount Laurel at Work:Affordable Housing in New Jersey,1983-1988,Rutgers L.Rev.,Vol.41,1988-1989。
(37)该州法律的相关分析可参见Harold A.McDougal,From Litigation to Legislation in Exclusionary Zoning Law,Harv.C.R.-C.L.L.Rev.,Vol.22,1987,p.623。
(38)Hills Development Co.v.Township of Bernards,103 N.J.1,510 A.2d 621(1986).关于该案的具体评析可参见Harold A.McDougal,From Litigation to Legislation in Exclusionary Zoning Law,Harv.C.R.-C.L.L.Rev.,Vol.22,1987,p.623。
(39)《城乡规划法》第4条第1款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40)如《电力监管条例》第28条规定可以向社会公布电力企业等的违法行为,其中对于可以公布的违法行为限定的一个条件就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又如在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1月制定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的第24条规定了保险条款必须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