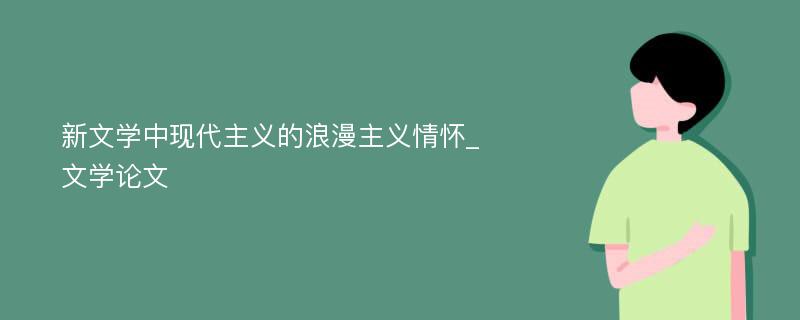
新文学现代主义的浪漫情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现代主义论文,情愫论文,浪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所共知,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各自都拥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内涵。但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文学现象却是那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许多浪漫主义作家创作了典型的现代派作品,许多现代主义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浪漫色彩,甚至对有些作家作品,也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例如,二十年代初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的叙说和理解,实际上就应该归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人们在谈论四十年代的徐訏、无名氏等作家的时候,也常用“后期浪漫主义”来称述之,而他们的很多小说又恰恰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作。——这大概就是新文学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在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之中难解难分地杂糅着许多浪漫主义情愫。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都不外乎要强调主观性、内向性、情感性,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为现代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在表现主观自我、强调情感体验等方面都与浪漫主义取得了相通之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条件,以及新文学作家自身的性格、气质、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质,使得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比较起来,现代主义不够真正的“现代”,浪漫主义也不够彻底的“浪漫”。因此,新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要想实现真正的“浪漫”,或者说要在对主观性和情感性等特质的追求上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程度就必然要走向现代主义。同时,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要想在审美体验和欣赏习惯等方面争取到更多的读者,也就必须汲取浪漫主义的诸多营养。
就浪漫主义而言,新文学浪漫主义受欧美浪漫派的影响极深。如梁实秋先生所说:“新文学即是受外国文学影响后的文学。我先要声明,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①]而欧美浪漫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是所谓的超越性。与欧美浪漫主义的这一特质相接近的新文学作家,应该是徐志摩、徐訏、无名氏这样一些人。他们崇尚西方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崇尚西方宗教的自然超脱、神人合一,崇尚以哲理的智慧和神秘的话语来建造一种超越现实的“西洋味”极浓的浪漫主义。徐志摩的散文《想飞》可谓是他们的宣言,他们是那么强烈地想飞,他们渴望凌空升腾地高飞于现实的庸碌之上。他们的理想是康桥模式下的自然、性灵,是由爱、自由和美所构成的单纯信仰,是一种自由驰骋的浪漫,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和永恒。
于是,追求超越与超越的无力和不可能,就使得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逐渐向现代主义分流。在新文学史上,诸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等许多浪漫主义作家,不管他们的理想境界多么美妙,也不管他们的主观情思多么炽烈,他们的思想基础都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坚实土壤,他们的创作宗旨都取源于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使命感以及积极入世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所以,他们既没有欧美浪漫派那样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和可以倚重的宗教哲学的精神力量,也就无法凭借着崇高的神秘感来俯瞰宇宙和人生,更无力超越现存的生活现实。
然而,作为浪漫主义的作家,所追求的又毕竟是主观思想和自我感受。于是,太强烈的追求与追求的无着之间的矛盾就使得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折磨。这诸多的无法战胜的矛盾和无法摆脱的痛楚,也使得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作家们不可能始终孤芳自赏地坚守浪漫。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其一,是放弃“浪漫”,去归入现实主义的洪波巨澜。例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尽管他们也是那么强烈地追求浪漫的理想、渴望超凡脱俗。但是,当他们“想飞”的情思与他们所置身的冷酷现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时,他们又情不自禁地要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其二,是执迷于“浪漫”,那么只能是到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中寻求精神慰借。例如,徐志摩、朱湘、林徽因、孙大雨等人的现代派诗,也都是由于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的太多的痛苦、战栗和无奈,这些痛苦的积聚和折磨使他们无所适从、孤独落魄,乃至绝望,就不由得与现代主义的“荒原”意识合流。前一种舍弃,是新文学作家们基于特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产生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后一种执著,也同样表现出浪漫主义经由理性升华的深沉与智慧,它布满了更多的磨难与艰辛,是固执在主观情感的世界里的挣扎、徘徊与寻觅,也是追求在“超越”的炼狱里的受苦受难的悲壮与华艳,更是一种寻梦于荒原的迷惘的灵魂的深邃。
就现代主义而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就在与它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寄植关系、依附关系。但是它又没有象国外现代派文学那样走向彻底的荒诞和抽象。于是,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就走着一条既相似于又相异于国外现代主义的独特道路。
一方面,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对国外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引进表现为积极的移植和大胆的尝试。这种借鉴的热烈和大胆,真有些史无前例。他们对有些手法,稍一小试,便弃之不用,可谓浅尝辄止。如完全否定理性的极度变形手法、过分追求抽象的“符号化”崇拜。对有些手法,则灵活掌握,充分运用,可谓深得精髓。无疑,这种借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尝试性的摸索中走着一条循序渐进的曲折之路。在二十年代,创造社的小说,李金发的诗歌,以及新月派的诗作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初步显示出现代主义的锋芒,但也明显地表现出借鉴的牵强和模仿的幼稚。到了三十年代,以施蛰存为代表、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派终于高举起自己的大旗,他们用急驰的旋律、缤纷的色彩以及各种倏忽多变的潜意识形态表现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②]然而,也许是政治风云和战争炮火的席卷,也许是单纯的非理性的表现形式不容易深入持久,他们都没能沿着自己的现代主义方向走下去。及至四十年代,经历了民族战争洗礼的现代主义作家们才开始迈进了一种理性沉思与自我体验相结合的更高层次。也可以说,徐訏、无名氏等人终于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包容了中、西浪漫主义多种特质的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主义在面对西方现代派的思想内容时又常常显得那么谨小慎微,即是一种谨慎的借鉴和有限的接近。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些现代派文学,真正使其成为“现代派”的,首先就在于它的反对理性、高扬感性,他们强调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人的精神世界的实质,就必须依靠情绪和体验、直觉和无意识等非理性的形式,于是他们振臂高呼重现感性的生命之光。而中国的现代派作家们,恰恰就在这一基本点上颇有些胆怯,他们小心谨慎地靠拢过去,却始终也割舍不断那条理性的根基。因为,中国的现代派作家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所选择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所承袭的传统的思维方式,都使他们不可能象西方现代主义那样对祖国的危亡与人民的灾难视而不见,乃至玩世不恭。他们只能在左顾右盼的政治斗争的夹缝中摸索前进,在多种艺术形式的兼容并包的积蓄中寻觅自己的艺术道路。
应该强调的是,正是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的这种探索性和兼容性导致它们在急切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路途中,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古代的浪漫主义抒情艺术的痴情,他们念念不忘怎样才能更积极地促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挥其自身活力。我国历史上的文学传统,大多偏重抒情,偏重于展示自我的主观世界。这一抒情模式,发展到唐诗宋词,便进入了顶峰状态。以后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回过头来仰视那一时代的文学精华,而无法超越那一时代的文学成就。新文学的现代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它突破了唐诗宋词的抒情符号系统,尽管这一突破是通过引进而获得的,但是它并没有背离自身文学发展的承继性。它初步建立起来的是一套现代的抒情符号系统,即现代生活和心理的节奏旋律、色彩音响、动势关系等等。这是既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本能、直觉、梦幻、潜意识等多种非理性的形式,也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所推崇的“意象”、“意境”、“性灵”等情韵的美学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学现代主义从问世到日臻完善,都不象西方现代派那样是一种顺逆对立、多向对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活力的激发,而主要是一种顺势的文化积淀。
首先,我们在新文学的现代主义中看见了崇尚自然、思乡怀旧这样一个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的经久不衰的主题。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作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表现都市文明的罪恶与田园乡村的清新两者之间的反差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施蛰存的小说集《梅雨之夕》、《魔道》与《上元灯》的相互对照,穆时英的短篇小说《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与《公墓》的相互对照,以及刘呐鸥的《风景》、施蛰存的《鸥》等一些单篇的小说中的对比描写,都明显地显示出城市与农村两种矛盾对立的环境氛围。在他们的笔下,现代都市生活的诸种光怪陆离的感官刺激都经过了作者的主观情思的浸润而被夸张地被推向了极致。也可以说,他们是在竭力地运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去强调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危机中的诸种堕落腐败、曲扭异化以及种种不可理喻。不知是为了维持心理上的平衡,还是为了寻求一种逃避和解脱,或者是念古怀乡的民族文化心理建构制约并调节着作家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使这些陷入困惑和无奈之中的现代派作家们,没有象西方现代主义那样走向荒诞和虚无,而只是把目光和希翼投向了乡间自然的清山绿水和未经现代物质文明污染的原始人性。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中的那种江南古城的书香和书斋绣房的儒雅,那些优美而感伤的故事中的一卷书画、一枚绢扇、一个淡青色的纱灯,都依稀可见陶渊明田园诗的情趣特别是一些晚唐诗的意境。但是,与古代诗人隐逸生活的悠然自得不同的是,施蛰存笔下的宁静与清新都是经过了自我意识的过滤而被渲染了,从而表现出对已经逝去的古风古习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田园牧歌的热望与幽叹。正是这种扯不断、忘不去的念旧怀乡的情思与希翼同他们自身经济地位的拮据、自我社会价值的曲扭以及个人情感取向的无所适从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的独特主题。
其次,在新文学的现代主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欧美现代派作品所没有的一种内省的、感悟的情致。这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种难以言传的既超感性也超理性的心理体验,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心领神会。例如,“一代才女”林徽因的小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灵感妙悟与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潜意识表现的美妙结合。她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学体系和浪漫情思中的那个源远流长的性灵说,强调文学创作是一种虚心纳物、妙悟人生的情感体验。在她看来,性灵的神韵就象在现代的客厅里,既有傲冰睨雪的梅花又有落满尘埃的蛛网,一切纯任自然,一切全凭造物主的神工。至于具体地表现性灵的手法,林徽因特别强调一种“忠于情感,忠于意象,更忠于那一刹那间内心整体闪动的感悟”。[③]它由感觉、意象和潜意识共同构成,是一种跟着潜意识的浮沉所创造的情绪、一种顺着直觉的体验和辨味所诞生的感觉、一种蕴藉着理性的情感与意象的融会。她的小说《窘》是一篇运用心理分析学说来表现中年人二重的性心理的代表作。作品一方面遵循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公式,写出了“里比多”与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模式。另一方面又使主人公内在的潜意识的流程携带着一种诗的节奏韵律,流淌着一种典雅的幽香与淡远。在这样的现代派作品中,没有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那种浮躁、喧嚣、庞杂与污秽,触目皆是敏锐的感觉,浪漫的情思,妙悟的参会和超越的心境。矛盾的性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玄妙飘缈的情绪的充溢和刹那间的感觉的振荡、牵引。它是那样的美,美得自然,美得飘逸,美得不可思议。
再次,新文学的现代主义艺术中也总是隐约可见一种儒雅的古风和婉约的美感。在徐志摩的一些现代派诗歌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种超然物外的豁达与闲适,一种自然性灵的妙悟。在闻一多的《李白之死》、《剑匣》等唯美主义的诗篇中,也可见一种雍容华贵、典雅精致的古风。当然,把现代派诗写得梦一般朦胧隐秘的还是戴望舒。他的作品的外在情境多是一种空蒙、寂寥、幽迷的象征性空间,其内在情绪又是一种隐约、飘渺、虚无的感觉性意象,两者的相会交融便形成了一种苦涩的、孤寂的、梦幻般的潜在感觉。其中浓郁的古色古香的意象、古风儒雅的风格,都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清幽婉约的诗风与欧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维的巧妙结合,是自我表现与隐秘灵魂的契合,是自然情绪的流露与微妙的象征暗示的结合,从而创立了建筑在现代情绪和现代手法基础之上的儒雅古幽的诗歌意象和风格。
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模式不仅有情理交融、含蓄蕴藉的美学传统,也有缠绵悱恻的肤浅和惰性。进入四十年代的徐訏、无名氏等人的现代主义创作的成就,就在于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那些空灵妙悟、华美绮丽的美学规范,也抛弃了其中的自然和谐、回避自我的世故与怯懦。它吸收了欧美浪漫派所携带着的诸种哲理性、神秘性、超验性的特质,并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流派中的诸多的表现形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由于欧美浪漫派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渊源关系,又使得这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充满了哲学思辨的穷究和理性审视的力量,从而把这种蕴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愫的现代主义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
其一,在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欧美浪漫派所蕴含着的那种浓郁的超越性和神秘感。他们追求神、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向往无限的、永恒的、神性的精神本体。例如徐訏,他一直“企图从对一种浩博宇宙观的追求中填补内心的空虚与失重感,其结果是将自己引向了神秘主义和宿命论。”[④]由于徐訏所追求的理想是欧美浪漫派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所推崇的那种超越的人与神之间的契合。所以,当他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面对上帝的崇高神圣时,当他们千辛万苦地寻求人与上帝的沟通、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契合时,只能过多地感受到沟通的艰难与无奈,只能戚戚然地哀尘世无净土。这样一来,徐訏作品中的这些困惑迷茫的现代派主题就都陷入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氛围之中。《阿剌伯海的女神》所创造的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象征性的世界,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和奇妙的梦幻情境。它描绘的主人公与海神之间的那些美丽神秘、浪漫风流的故事,不知是想以此探讨人生的命运,还是想追寻灵魂的感应?是要觅求宗教的信仰,还是要寻找人与上帝契合的途径?总之,人与鬼分辨不清,现实与神话混淆叠合,实感与幻觉交叉错置。读者感觉到的只是奇幻怪诞的情感魅力和空幻、飘渺的体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表现的是一种先哲的理想和命运。主人翁以耶稣式的博爱赤诚地去爱,也以耶稣式的救赎虔诚地去忏悔。结果,尽管他是那么竭尽全力地工作,那么热切地渴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在生命的奉献中得以升华,可幸福永远是暂时的。他在上帝与尘世之间的苦苦挣扎所能得到的,依然是“归途”就是“来处”的悲剧。
无名氏的两部中篇《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也都是在表现与徐訏上述作品相似的那种现代派所共有的苦闷、虚无、荒诞的情感体验。作品表面都是华丽繁缛的浪漫言情,都是在叙述主人公是怎样千方百计地追求爱情,可等到获取之时,又立刻抛弃了如火如荼的热恋,而后又是无尽的负疚与赎罪。作品又都以一种神秘的“石塔”理论作为结论,即“女人永远在塔里”[⑤],而营造这塔的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⑥],它们作为“一种坚不可拔的存在”[⑦]就象神话中的海狮的脑袋一样,砍掉了第一个,还会继续生出来第二个、第三个……作者以一种关于生存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存在主义的思考来解释这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即个体自我永远是孤独的,软弱的。尽管他们已经经历了生命炼狱里的各种考验,已经体验过了生命旅程中的一切大痛苦和大欢愉,甚至已经感悟到了生命本体中的一切玄奥和虚无,却仍然无法摆脱冥冥人生的那种神力和阻力。
其二,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又使自身走向了一种诗化的境界。他们刻意地追求一种诗情的美感、一种诗意的沉醉。他们的很多小说形式本身就象是一种抒情诗、散文诗、叙事诗,甚至是一种大型的西洋诗剧。也可以说,当他们面对那些无法超越的阻力和无法解开的生命之谜的时候,他们求助的是诗的媒介。他们企图凭借诗的语言和诗的表达方式更自由地去展示自己精神探索的历程,并且依靠着诗的想象去驰骋、去飞升、去超越。无名氏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用一种诗化的抒情形式来表现。翻开《野兽,野兽,野兽》,人们很难认定这就是小说,“全书近五百页,自始自终好象全是絮语和梦呓”[⑧],没有情节,没有对话,也没有人物的形象描写,有的只是一种狂风暴雨式的感情渲泄。它好象只是要表现生命在炼狱中的挣扎困惑,只是要倾吐自我的感情在凌迟碎剐中的被劫掠与被放逐,以及体验过生命的全过程之后的心灵的大彻悟与大虚无。
在四十多万言的长篇《海艳》中,无名氏也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点出发,认定只有主观感觉中的大海才是象征生命的诗,才能包容生命的一切行动和思想,也才能解释生命本体的多姿多彩。从文学的表面看,作品把大海作为一种诗化的叙述载体,作为一种“纯主观性”的意象,它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自由地追索它的无极和无限。从情感体验的线索来看,它遵循仍是西方现代派的寻找自我与超越现实的主题和“直觉”的、“本能”的表现方式。作品以西湖风景的如诗、如画、空灵、梦幻来象征“生命的最高圆全”。它以“蓝”的具体的“色”和抽象的“形”来象征生命的高贵、纯洁、灵幻。在主人公印蒂看来,追求生命“圆全”的途径只有一条,即一种非理性的感觉体验、一种生命冲动的诗。凡尘的眼睛不能射穿它,现实的生活事物无法企及它。就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进入到了灵与肉结合的灿烂之际,他们也就达到了生命旅程最辉煌的顶点,这是纯粹用“梦感梦觉”才能享受到的生命中的最艳丽、最豪华的大沉醉和大狂酣。然而,在无名氏的现代主义的“存在”观看来,当人的感觉和体验停留在一种原始的、混沌的迷蒙状态,他可以享受到超世的沉醉与诗的华艳。一旦人的意识由混沌转为清醒,一切超脱的美丽都会转眼即逝。于是,主人公在经历了瞬间的爱的狂酣之后,又不得不回到存在主义的孤独自我的出发点上。所以,诗的感觉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魔障。只有“孤独个体”才是一种永恒的体验,空寂和虚无永远是人生旅途上的真实存在。
应该说,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作家,从自己所置身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出发,从心系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出发,也从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出发,积极吸收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又最大限度地引进了欧美浪漫派的诸种艺术特质,使得新文学的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呈现出一种优美多情的浪漫风采。它既摆脱了西方现代主义的那些生涩怪诞、不可理喻的种种弊病,又使其直觉、本能的感觉表现层次深入到了一种理性思辨的深度空间,走进一个诗化哲学的世界。
注释:
①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
②施蛰存:《关于本刊的诗》,《现代》杂志1933年第4卷第1期。
③林徽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林徽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
④潘亚暾、汪义生:《徐訏简论》,《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⑤无名氏:《塔里的女人》,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4年版。
⑥⑦无名氏:《北极风情画》,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3年版。
⑧涪村:《编后絮语》,《野兽,野兽,野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