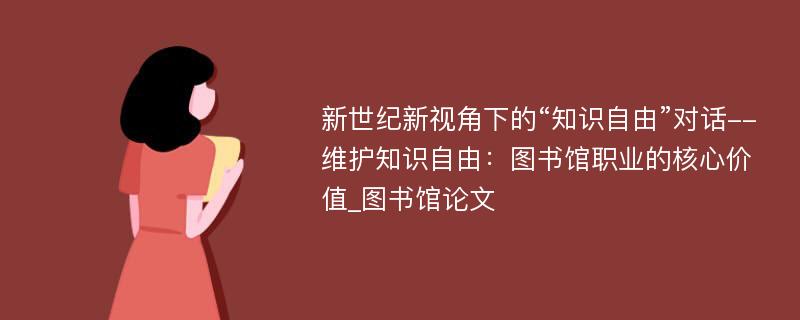
新世纪新视点三人谈之 关于“知识自由”的对话——维护知识自由: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知识论文,新世纪论文,图书馆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图书馆职业(本文所称“图书馆职业”,与“图书馆行业”、“图书馆事业”同义)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普遍的社会职业类型。那么,社会上为什么普遍需要设立图书馆职业呢?这就是图书馆职业的价值问题。笔者认为,社会上之所以需要普遍设立图书馆职业,是因为图书馆职业能够适应人们知识自由的普遍需要,或者说是因为图书馆职业是人们知识自由权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质言之,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1 关于知识自由
所谓知识自由,亦可称智力自由、知识平等,与其相近词汇有求知平等、求知自由等,是指人们对知识的自由生产、自由接受、自由交流、自由利用的状态,概言之,就是指人们自由从事或进行知识活动的权利。
知识自由是人权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人的身体自由、经济自由、精神自由一起,共同构成人权自由体系〔1〕。知识自由一般可区分为如下几种表现形式:
(1)知识生产的自由。即不受限制地进行知识生产活动的自由,主要表现为知识成果的发表或出版的自由。
(2)知识接受的自由。即不受限制地接受知识的自由,主要表现为接受教育和自主学习的自由。公民利用图书馆进行自主学习的自由,就属于知识接受自由的范畴。
(3)知识交流的自由。即知识在传者与受者之间不受限制地进行传递的自由,可分为正式知识交流的自由和非正式知识交流的自由两种形式。
(4)知识利用的自由。即不受限制地利用公共知识及其设施的自由。公民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就属于知识利用自由的范畴。
知识自由与知识限制、知识垄断、知识霸权以及知识分配不公等现象相对立。任何开明的国家和民族,无不承认知识活动的高尚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任何民主社会都应保障公民从事知识活动的自由。然而,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知识自由也如此。因而,人们在从事知识活动时,总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知识自由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
(1)物理障碍。即由于空间距离阻隔、社会所提供的知识资源及其设施数量不足(如社会教育资源、图书馆资源及其数量不足)、活动主体得不到必需的客观条件(如残疾人得不到特定设施及其服务)等原因形成的障碍。
(2)经济障碍。即由于经济支付能力不能满足知识自由所需的条件而形成的障碍。如社会上部分人群因经济贫困而不能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支付能力所限而不能享用有关知识设施,等等。
(3)技术障碍。即由于活动主体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或操作技能而形成的障碍。如在当今社会一些人不拥有计算机设备或不懂得计算机操作技能,就会失去利用互联网实现知识自由的机会,其典型反映就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技术障碍一般是由经济障碍所致,所以,技术障碍和经济障碍可以合称为“经济技术障碍”。
(4)政治障碍。即由于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势力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而人为实现有碍于知识自由的政策或做法而形成的障碍。如我国古代出现的“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文字狱”等事件以及当代“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查禁“反动”言论与书籍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知识自由的社会秩序。
(5)文化障碍。这里是指由于活动主体的文化层次偏低或所持观念的阻碍而形成的障碍。如果主体的文化层次偏低,必然影响其知识接受的广度与深度;主体所持的观念(如科学观念、宗教信仰、宗法观念等)必然对主体的知识活动产生选择性障碍。
2 知识自由与图书馆
知识自由是人类对自由权利追求中的一种普遍诉求,但知识自由的障碍也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随着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越来越重视,随着各国民主政体的越来越完善,各国都普遍重视采取消除知识自由障碍、扩大知识自由范围的政策和法律措施。从图书馆建设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所以普遍设立图书馆建制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建制,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图书馆能够保障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范围主要限于保障知识接受自由的权利,因为公民利用图书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知识接受的需要。公民的知识接受自由权利的实现途径不限于利用图书馆(如接受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毫无疑问,利用图书馆是一个重要途径〔2〕。
尽管图书馆诞生的原因并非在于为了满足公民知识接受自由的需要,但图书馆发展至民主政体时代,保障公民知识接受自由的权利已成为社会赋予图书馆的主要使命。而且,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已经把公民利用图书馆来实现知识接受自由的权利,纳入到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范畴之内,其主要表现是各国宪法中一般都列有国家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学习权(受教育权)、思想自由权、休息权等内容的条款,正是在这些公民权利中已经蕴含着知识接受自由的权利。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说,公民具有知识接受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具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而国家法律之所以规定公民具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知识接受自由的权利。
以上分析表明,图书馆事业发展至今,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其建制已受到法律保护(其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国家制定有图书馆法和相关的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政策),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这说明,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分配,以保障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制度。就像现代学校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出现一样,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社会的知识自由保障制度的形成〔3〕。
从维护知识自由的角度理解图书馆现象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因为从这一角度理解图书馆现象,能促使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设立图书馆建制是维护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需要,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充分实现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社会保障措施之一,因而也是完善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人权事业的重要体现。这就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政治意义所在。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有必要重温Michael Gorman的那句名言〔4〕:“图书馆是自由(社会的、政治的及思想的自由)的集中体现,一个标榜是真正自由的社会,如果没有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平等使用的图书馆,则是一种可笑的矛盾修饰法。”
从社会机构/制度角度尤其是从制度角度理解图书馆事业也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因为从这一角度理解图书馆事业,有利于促使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图书馆事业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为了满足图书馆机构本身的生存与扩张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制度完善的需要;重视发展图书馆事业,不仅仅是“应该”,而是一种“必须”。这才是图书馆事业应该得到重视的制度或法律基础。应该说,从制度角度理解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种新视野、新高度。
3 维护知识自由: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
图书馆职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其价值和核心价值是什么?这是从事图书馆职业的人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是指在众多的图书馆职业价值中,最能代表职业特征并对整个职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那些或那种价值。关于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Michael Gorman在2001年指出,图书馆工作的8个核心理念是:职责明确、服务至上、学术自由、方法合理、求知求学、求知平等、保护隐私、倡导民主〔5〕。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于1999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核心价值特别工作组),专门进行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并于2000年提出了10个有关图书馆核心价值内容的关键词,意在向人们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的概念范围,它们是:使用、协作、多样性、教育、智力自由、保存、隐私权、专业技能、公共利益、服务〔6〕。无论是Michael Gorman的8个核心理念,还是ALA的10个关键词,都对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作出了比较全面而又准确的概括和表述。笔者认为,在这18个词汇(两者加起来,其中有些是重合的)中,“知识自由”(Michael Gorman表述为“求知平等”,在学术自由”和“倡导民主”中也应蕴含此义;ALA则表述为“智力自由”)居于最高层,最具统摄意义,因为在笔者看来,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是现代图书馆制度的最高使命,而其他核心价值均可看作实现这一最高使命所需的手段或要求。笔者之所以把图书馆职业(制度)的最高的核心价值定位在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其根据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如上所述,在对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的概念表述上,“知识自由”最具综合性与统摄性,以“知识自由”为逻辑起点基本可以演绎出其他各核心价值的意义。如,“使用”、“协作”、“保存”、“多样性”、“方法合理”、“专业技能”、“职责明确”等,都可看作是实现知识自由的必要方法或手段;“隐私权”(保护隐私),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图书馆在履行维护知识自由职能时自然也要无条件予以遵守;而“求知自由”、“教育”、“学术自由”、“公共利益”等更是“知识自由”的交叉近义词。
第二,从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能看,将其核心价值定位在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能够阐明公共图书馆的形成、发展及其价值意义。
第三,如果从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的视角审视图书馆现象,就有利于引导人们从社会制度和法律的高度定位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从而有利于图书馆事业能够以无可置疑的理由得到社会和法律的支持,稳固其运行的社会与法律基础,再进而有利于维护图书馆事业的公益性质及其本位。
第四,用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来定位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符合国际图书馆界及其专业组织对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的定位要求,有利于同国际图书馆界保持一致。如IFLA于1999年就在“图书馆和知识自由权的声明”中指出:“IFLA支持、捍卫和促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论及的知识自由权的定义”,“IFLA声明人类拥有表达知识、创造思想和智力活动以及公开阐明观点的基本权利”,“IFLA表明履行知识自由使用的义务是图书馆和信息业的主要职责”,“IFLA因此而号召图书馆界及工作人员恪守知识自由使用、无条件获取信息、言论自由和尊重读者隐私权的原则”〔7〕。
图书馆职业为了真正充分体现维护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必须坚持贯彻以下三个原则:
(1)公益原则——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基础
公益性是社会对图书馆性质的基本界定。图书馆作为维护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社会机构与制度,是国家民主政体和人权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因而其运行成本是由社会支付的,实际上是由社会的全体成员支付的,这就是图书馆公益性的社会经济基础。坚持图书馆的公益性,要体现两个基本点,一是免费,二是平等〔8〕。关于这两个基本点,IFLA和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已作了明确阐述:“公共图书馆必须敞开大门,不分民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学历,面向所有成员免费、公开发开放。”〔9〕实行免费与平等原则,是图书馆职业的社会特征,这一特征为公民消除知识自由权利实现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障碍,提供了社会保障。
可以说,图书馆是带着公益性这一“护身符”降临于世的,而且这一“护身符”自古至今一直是图书馆之所以为图书馆的象征与标志。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人对图书馆的公益性提出了质疑。美国图书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哈里斯等人认为,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图书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图书馆死抱着过去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不作相应的变革,幻想在信息市场化的浪潮中保留那块远离商业化的“净土”的话,必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他们主张图书馆放弃公益性原则,走向市场化发展之路〔10〕。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向公众提供知识信息服务,既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也可以采取公益化模式。但从每一个民主化国家所应履行的保障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的责任和义务来说,以图书馆制度这样一种公益化模式来提供非市场化的知识信息服务,是国家必须采取的一种公共政策。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来说,市场调节也不是万能的,如公共政策调节、伦理道德调节等是市场调节所不能替代的〔11〕。据此,笔者认为,图书馆的公益化管理模式是国家公共政策调节的对象,而不属于市场调节的对象。同时,笔者还认为,放弃图书馆的公益性之日,就是图书馆的终结之日。
(2)服务原则——图书馆职业的理念基础
谢拉说,“服务,这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我国图书馆学家程亚男女士也指出,“服务是贯穿图书馆发展的主线,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12〕。如果给图书馆做一张“名片”,那么,它的“又名”应该叫“服务馆”,它的“经营范围”应该叫“知识服务”,它的口号(馆训)应该叫“服务至上”。图书馆职业工作者时刻铭记的最好的格言应该是“为您服务”〔13〕。
图书馆服务的直接目标是读者满意。读者满意表现在理念满意、行为满意和视觉满意三个方面。理念满意是指图书馆在服务理念、服务目标、服务精神、服务哲学等方面带给读者的心理满意状态。行为满意是指图书馆在全部运行状况带给读者的心理满意状态,包括行为机制满意、行为规则满意、行为态度满意等。视觉满意是指图书馆的各种可视性外在形象带给读者的心理满意状态,包括对馆容馆貌、馆徽馆旗、物品陈列、衣着举止、环境色彩等视觉对象的满意〔14〕。
在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和服务目标中,贯穿着一种核心精神,即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正是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支撑着图书馆人为维护读者的知识自由权利而浇注心血的崇高使命与高尚境界。
(3)自由存取原则——图书馆职业的能力基础
图书馆毕竟是以文献信息资源(包括网络信息资源)为基础来履行维护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职能的,因此图书馆对文献信息资源的组织能力,直接关系到图书馆能否维护好公民知识自由权利的根本问题。图书馆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的目标,是建立文献信息资源的自由存取系统。建立这种自由存取系统,是公民利用图书馆来实现知识自由权利的需要对图书馆提出的根本要求。
图书馆建立文献信息资源的自由存取系统,要具备三方面的保障能力,即文献保障能力、读者保障能力和技术保障能力。文献保障能力,是指图书馆所提供的文献信息的可获得性及其程度;读者保障能力,是指图书馆能够满足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的能力;技术保障能力,是指图书馆在技术手段上为读者提供支持的能力。这三方面的保障能力越强,就说明自由存取系统的“自由度”越大,亦即说明图书馆在物质能力上维护读者知识自由权利的能力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