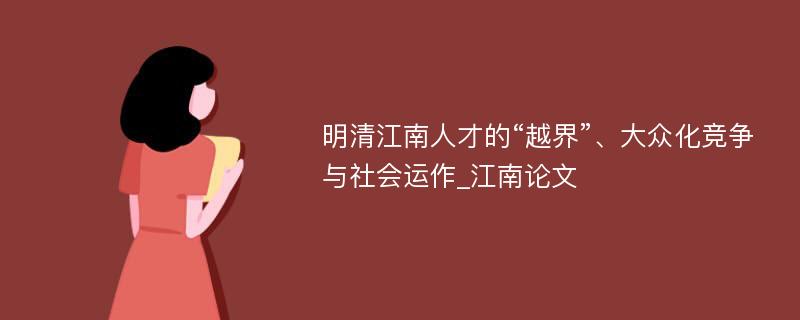
才女“越界”、声望竞赛与明清江南社会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声望论文,明清论文,才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5)02-0064-09 才女,在明清的江南社会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特别是在清代中叶迅猛发展。有些才女群体呈现出跨地域、跨血缘的特征,与明代以前才女以零星的个体面目出现迥然不同①。 才女往往是才德美兼备的闺秀,她们不仅相互唱和,还与男性士人发生诗文交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男女有别”“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秩序。对于这种才女群体的社会空间行动,研究者们从女性主义建构论的角度予以了较高评价,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主体性和空间能动性的体现②。 然而,如果将这种社会空间行为理解为一种对现有性别秩序的挑战与新的建构的话,也就意味着才女群体与男性士人的“越界”交往行为(本文的“越界”是指才女群体跨越内外有别的社会性别空间边界去与男性士人进行诗文交往)会给江南社会秩序运行带来威胁。但是面对才女群体的这种威胁,当时的江南社会却采取了有别于对待一般女子的策略。江南社会一方面要求普通女性遵守“内外有别”的社会性别空间边界,一方面又默认甚至鼓励才女们由“内”而“外”,允许他们同男性士人的“越界”交往。为什么才女群体由“内”而“外”的“越界”交往活动,会被当时的江南社会予以容忍呢?这种“越界”交往活动对于明清江南社会秩序运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从社会秩序运行的微观层面去重新理解才女群体在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叶的江南社会,可以由“内”而“外”与男性士人发生交往从而跨越社会性别空间边界这一历史现象?本研究拟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被以文学和历史学为主体的才女研究和江南社会研究所忽略的问题③。 一、才女“越界”交往与江南社会对才女交游的宽容 明清时期,封建礼教对女子和异性交往是严格控制的,对于性别空间秩序而言,男外女内、男女有别是最重要的空间秩序。然而,明清时期的才女群体和一般女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她们往往会通过群体的唱和活动由“内”而“外”,从而与男性士人群体发生交往。对于这种越出当时“女子”性别空间边界的行为,江南社会却多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④。这种将才女和一般女子区别对待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总体来看,在强调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对于才女群体也是强调德行和内外有别这样的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中的社会性别秩序的[1]。因而长期以来,在社会性别秩序中是贬抑才女的,即使是记诸史书的谢道韫、李清照、蔡文姬等才女,社会秩序维护者也是对她们大加驳斥,认为有亏妇德。“文学之妇,史传所载,班班脍炙人口。然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无论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贞辈,即回文绝技,咏雪高才,过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录,他可知矣。”[2](P116) 然而当时江南文人称赞才女时却多以蔡、谢比拟,“继祖母高明大学士文端公讳仪曾孙女也,相国和梅之裔,一代高华,大家起絮之才”[3](P181),并不将以谢道韫为代表的才女视为无德女子。 当时的江南才女也多以蔡、李、谢称誉或自诩,并不看重其德行有亏的一面。如徐媛在《屠母黄孺人墓志铭》中称颂黄孺人“其文才藻绘,上可方班姬,下亦不媿曹大家……诗才柳絮,宁让谢太傅之名,闺词觯色,丝不减蔡中郎之令女”[4](PP68-69)。墓志铭或有过誉成分,但这恰恰说明当时江南社会认为将有才有德的女子比作文学之妇是一种赞美。再如吴筠。“吴筠,字湘屏,号畹芬,上虞吴竹溪季女。适嘉兴李杏村。杏村好学擅诗歌,畹芬相与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赠杏村云:‘柳絮因风传谢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自负如此。”[5](P24)以谢道韫自诩,其实强调的是自己比丈夫强(谢道韫嫁王凝之,有“天壤王郎”之叹)。这并不符合明清社会“男高女低”“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秩序的要求,可见当时江南士人主要重视的是才女的“才”,对女才的重视程度高于女德。如晚明士林领袖钱谦益对明代末期叶绍袁家一门才女赞赏有加:“宛君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拟,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红而工子墨。”[6](P753)在才女群体的影响之下,才华而非女工成为当时江南士女的时尚[1]。 晚明时人曾记录当时江南社会对才女个体才华的器重。“近吴越中,稍有名媛篇什行者,人宝如昭华,琬能使闺合声名驾藁砧而上之。”[7](P179)而明末清初士人甚至以本地才女辈出作为江南社会的骄傲。顾若群在《卧月轩稿序》中说:“吾杭数十年以来,子萩田先生女玉燕氏则有玉树楼遗草,长孺虞先生女净芳氏则有镜园遗咏。而存者为张琼如氏之书。为梁孟昭氏之画。为张似音氏之诗。若文皆闺阁秀丽,垂艳流芬。宜马先生谓:钱塘山水,蜿蜒磅礴之气,非搢绅学士所能独擅。而马先生尤啧啧余亡妻黄字鸿氏所为闺晚吟,至拟之杜之北征韩之南山。顾谓吾姊(指顾若璞)氏之文,不徒以五言七字争奇于险韵,知言哉!”[8](P1647)顾若群的这番话充满了对其姐、其妻以及其他杭郡才女作品的自豪感。才女与家族认同之间的关联在男性文人的自豪感中微妙地展现出来。 对才女“越界”的欣赏和包容在当时的文人对传颂江南社会的才女记录中可见一斑。“吾乡多才女”[8](P128),“兰陵蒋氏多才女”[10](P118)。甚至有文人认为清中叶时江南文运钟于女子。“同时闺秀著名者,吴门有金纤纤、王梅卿、曹墨琴,棃里有吴珊珊,常熟有席佩兰、归佩珊,上海有赵韫玉,淛江有方芳佩、孙令仪,毘陵有钱浣青,皆卓卓可传者。相传乾嘉之间,文昌星扫牛女,度故闺秀诗词极一时之选。”[11](P29)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替才女群体张目的合法性话语策略。 可见,明清两代,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才女群体俨然成为“士”这个阶层争相赞赏的对象。固然,当时被视为才女的,基本上都是才德兼备的所谓“闺秀”,但是在其生命周期的青年阶段,作为才女,她们却是“动”的,呈现出一定的“越界”交往性。当时的江南社会对一般女子与男子的交往有着严格的限定,强调“男外女内”“男女有别”,而才女与男性的交游活动却与当时江南社会的这种性别秩序安排有一定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当时的社会性别空间边界。由于才女“越界”交往甚为普遍,以至于章学诚要发出感慨:“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12](P6) 为什么才女群体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被要求严守“男外女内”的性别空间边界,相反,其“越界”交往行为却被当时的江南社会的士人予以容忍和一定程度的鼓励呢?要想解释这个现象,必须要把才女“越界”交往这个历史现象同当时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联系起来。 二、才女“越界”与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 (一)才女“越界”与家庭社会地位提升 当时的江南社会,对于女子的要求普遍是强调德行。择妇以德,是封建社会家庭秩序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对女子德行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父子”关系逻辑——长幼尊卑秩序再生产的需要,是家庭秩序稳定的需要。江南社会的家庭秩序生产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空间生产。这种张力体现在江南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其秩序运行是稳定的,其秩序要求是强调把人固定在土地和关系之中,处于低社会流动的状态。这就要求人际关系重视先赋性关系。所谓先赋性关系,即血缘、姻缘、地缘等先在于个体的关系而非个体后天交往获得的关系。先赋性关系强调关系中的义务性和强制性而非选择性,强调关系的等级性而非平等性。这种对关系先赋性和稳定性的强调,就使得家庭秩序生产首先是一套对上下尊卑的义务性、等级性关系的生产。所谓“女德”本身就是对这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但是在江南社会内部,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秩序生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并不能保障家庭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江南社会中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存在。家庭在江南社会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从等级的角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是一个既定的等级社会,这是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一面,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其社会地位又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生变化的,这种可变性在明清就来自于科举制这种社会流动机制。 科举的录取率很低,使得即使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江南社会的精英——士绅群体的家庭,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而只有子代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才能使自己的家庭在江南社会中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家庭都必须尽一切努力提升下一代通过科考的概率。这是江南社会内的家庭竞赛。这种由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引发的竞争使得每个具体的家庭不仅要考虑家庭内社会秩序包括性别秩序的再生产,而且要考虑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再生产。 然而清中叶以后,科举录取的比例逐年降低。在科举竞争激烈的江南社会中,随着科举通道的日益堵塞,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男性士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因此,要想保障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再生产,男性之外的家庭成员——才女群体就为家庭的声望竞赛提供了新的资本:才女的才华转变成为家庭竞赛中新的文化资本,其与男性交往唱和所建构的人际网络也成为家庭声望竞赛中新的社会资本。 才女与士人的“越界”交往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这样的记载很多。“幼舆尝与渔洋诸公九日饮宋子昭小园,限蟹字韵,启姬代为诗,末云:‘予本淡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蟚蜞误为蟹。’一座大惊。”[13](卷4)才女的才气使得王士祯这样的诗坛领袖也为之叹服,自然增加了幼舆作为男性主人的声望。 除了与男性士人诗文唱和以外,才女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一个常见方式是通过拜师成为著名文人的女弟子。对于才女所属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其家庭通过才女进入一个新的人际与文化网络中,从而有可能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位置和声望,在江南社会的家庭竞赛中增加新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个动机,很多士人家庭容忍甚至鼓励家中的才女加入女性和男性的才人网络中,例如随园女弟子群体。 随园女弟子严蕊珠就凭借自身的才华而非传统的熟人介绍,让袁枚接纳了她。“吴江严蕊珠女子,年才十八,而聪明绝世,典环簪为束修,受业门下。余问:‘曾读仓山诗否?’曰:‘不读不来受业也。他人诗,或有句无篇,或有篇无句。惟先生能兼之。尤爱先生骈体文字。’因朗背《于忠肃庙碑》干余言。余问:‘此中典故颇多,汝能知所出处乎?’曰:‘能知十之四五。’随即引据某书某史,历历如指掌。且曰:‘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诗用典乎?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然非读破万卷、且细心者,不能指其出处。’因又历指数联为证。余为骇然。”[14](P1585) 从严蕊珠的事例中可见,才女加入文人领袖的门下,不完全需要如男性那样太多的门第、父辈等交往因素,而主要依靠自身的才华。即使与袁枚不认识,也可以直接求见纳入门墙。这种强调个体吸引的新型交往方式,为处于“士”这个阶层内的下层普通士人家庭的才女跨越社会分层的障碍,加入以袁枚这样的文坛领袖为中心的人际网络提供了便利。袁枚所到之处,才女们蜂拥而至,欲求拜入门墙,成为其人际网络中的一员。这种新型的人际网络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群体,它首先强调的是个体才华这样的个体因素而非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即如前述的严蕊珠,虽然其外祖父为吴江李宁人,曾做过按察使,但其父仅为诸生,未有功名,在江南社会的家庭竞赛中显然处于下风,然而,家里出了才女,严蕊珠在没有人介绍的情况下面见袁枚,凭借其出色的才华,成为袁枚的弟子和三大知己之一。另一个著名的随园女弟子骆绮兰也曾经自荐投袁枚门下,后经袁枚介绍转投镇江士林领袖王文治门下,成为两大文人领袖的共同弟子。很多出身一般甚至寒微的才女得以成为才女网络中的一员,从而提升自身和家庭的社会声望。如吴江另外一个出身商家的贫寒才女汪玉轸即是如此。 (二)才女“越界”交往与男性士人、才女的声望提升 当时的江南社会,不仅才女有走出家庭、“越界”交往的动机和需要,男性士人出于种种考虑,也乐于与才女交游。 当时的士人领袖收女弟子蔚然成风。“吴玉松太守云传载辞官逍遥里社,所受业女弟子多至数十人,年八十有余之。”[15](卷2,P29)“齐梅麓有女弟子张云裳襄,张丽坡参戎之女也。归汤价人观察之子,才貌双优,事梅麓如父”[15](卷2,P51)。“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华,为西河佳话。乾隆末年袁简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诗,当时有议其非,然简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树着花之诮,近有士子自负才华,先后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诗都为一集,其中有贵有贱,杂出不伦,或本人不能诗为代作一二首以实之。以夸其桃李门墙之盛,此虽从事风流而实有关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艳称其事者。”[16](P317) 可见,招收女弟子这种行为虽然依然受到江南社会秩序维护者的批评,但是在江南社会内部也不乏“艳称其事者”。这种羡慕的背后,恰恰说明才女群体的出现,无形中使得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的声望竞争方式变得多样起来。才女的鼓吹者和保护者身份成为一种新的提高男性士人社会声望的方式。这不仅给男性士人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还可以将男性士人自身的文化资本(文化场域中的较高位置)转换成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从而成为切实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社会位置的一种手段⑤。 在文化场域中占据较高位置的士人需要才女群体来实现其文化资本的转换,而处于较低层级的男性士人也同样可以凭借和有声望的才女交往来提升自身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清代中叶以后,科举录取人数大幅降低,大量的士人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沦为寒士⑥。科举正途以外的社会声望成为他们维系自身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的重要竞争方式。对才女及其作品的鼓吹成为部分男性士人维持和改善自身社会位置的新的竞争武器。“余在里门偶见装潢家有残画一束,中有黄皆令设色山水扇头,妍妙绝伦,余问肯售否?答云本系托销之物。余适有虞山之行,不及还值,且扇头单歇只署皆令二字,贾人亦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意此画未必遽有识者,终落余手耳。往虞山不数日,即归急觅之,则有客从吴门来,见之即重价购去矣。妙画不易得,交臂失之,是天下第一恨事。皆令名媛介,嘉兴才女,诗文书画皆佳绝,……诗笺未有刊本,余尝于友人斋中见之,今不能记忆矣。”[17](PP32-33) 黄媛介是明末才女,从这段男性士人对黄媛介的画欲得还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才女及其作品在当时江南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男性士人对于拥有才女作品的渴望。类似的还有清代男性士人对明末才女叶小鸾的接受与痴迷。 由于才女在江南社会中广受士人欢迎,以至于还出现假才女的事情。“昔船山太守寓吴中,眷莲缘校书绳之,甚至同时文士咸赋诗张之,其美丽可想。叔曾慕名往见,肥黑而麻,非但不美而已。吾乡女冠韵香能书能画,兰貌已容。为空山听雨图,梁山舟侍讲首题一诗,遂遍征名流题咏。享艳名二十余年。然其对客酬和之作,咸复壁中人为之。叔亦捉刀中一人也。忆余在装潢铺见便面上韵香自书诗词,曾录其采桑子词出以相质。叔曰,此虽不知伊谁笔墨,然韵香不藉词传,词或藉韵香传,又何必辨为非。”[18](P37) 借才女得以成名,恰恰来自于部分男性士人以才女自重,藉与才女的交往提高自身在江南社会中的声望与地位所致。也正因为此,部分男性士人不仅乐于与才女交往,而且还要大为宣扬。“纤纤题湘湄诗稿有云,江东独步推君在,天遣飘零郭十三。余嘱武林蒋山堂以落句作一私印,佩之终身以志知己之感也。”[19](P33)郭麐对苏州才女金逸的题诗如此看重,固然有个体情感(知己)的因素在内,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与才女的交往是当时部分男性士人在文化场域内进行身份区隔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吴江才女汪玉轸给郭麐的画题诗,“频迦因之更请叔美画万梅花拥一柴门图,名家题辞甚众”[11](P29),时人认为郭磨好事,确实也道出了文人利用才女提升自身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的这一面。 可见,与才女诗文交往成为当时部分男性士人在文化场域中身份竞争的新手段。“乾隆间闽中徐两松藩伯首唱素心兰四律,一时都人士次韵者至数百家,旁及闺秀亦有和章。先资政公本在方伯门下。因命先太夫人同作。时藩伯将和诗橐次成帙,属鳌峰院长孟瓶庵先生甲乙之。先太夫人诗中有三霄桂窟输清绝,万顷芝田伫后缘句,先生辗然曰,此两句居然诗兆梁氏之兴,未有艾也。藩伯以为知言。”[20](P18) 由于与才女的诗文交往在男性士人中日趋竞争激烈,部分男性士人甚至退而求其次,将编辑才女作品也作为自身在文化场域竞争的手段。“夔臣字山臞,以诗名,曾辑女子诗为《雕华集》。待梓,翁绣君女史以寄他氏,损增刻之,别立集名,夔臣抑抑病殁。文人好名之弊如此。”[21](P127)男性士人因为编女性作品集不遂,从而无法在江南社会的声望竞争中获胜,竟抑郁而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才女及其作品对于部分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声望竞争的重要性。 (三)独立声望:才女“越界”的内在动力 由于家庭和男性士人的鼓励,才女群体“越界”与男性士人交往的合法性得到确认。而在与男性的交往唱和中,其经常呈现出才华超越男性士人,与之分庭抗礼的现象。 “沈佩玉夫人,叶克昌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蛬吟深夜月,人卧一庭花。’十字颇为士林传诵。”[16](卷24,P359)“虞山王云上,名岱,能诗。家素贫,常出门负米。其夫人席氏亦工吟咏,有‘愁连双鬓改,贫觉一身多’之句,传诵艺林。”[16](卷24,P361) “《五色蝶次韵五首》,闽县汪淑瑞女士作。藻思绮句,传诵一时。”[13](卷2,P31)“蕙孙号散花女史,教授起凤女。善洞箫,制有《箫谱》。其所著有《绣余集》、《翡翠楼诗文集》。《浣纱词》尝有‘听残红雨到清明’之句,脍炙人口,咸称‘红雨诗人’。”[13](卷2,P33) 才女的才华被男性士人广为传颂,甚至得到了以往一般男性士人才能得到的评价(如“红雨诗人”的别号),这说明,在与男性士人的“越界”交往中,才女不再仅仅作为男性士人的附庸,而开始依赖才华赢得属于自身的声望。再如著名的才女王端淑。“玉映,名端淑,号映然子,王思任季女,宛平丁肇圣室。著有《吟红》、《留箧》、《恒心》等集。……负才荦荦,能对座客挥毫,而陈其年且称其长于史学。初得徐文长青藤书屋居之,后寓武林之吴山,与四方名流相倡和。毛西河选浙中闺秀诗,未及玉映,因奇诗云:‘王嫱未必无颜色,争奈毛君下笔何。’引用恰合,一时盛称之。……玉映善书作画,长于花草,有疎落苍秀之致。顺治中,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授诸妃主,玉映力辞乃止。卒年八十余。”[13](卷5,P110) 讥讽毛西河这样的文坛领袖而且“一时盛称之”,毛西河也作诗道歉,这充分说明了王端淑已经不满足于作为男性士人的竞争性工具和附庸,试图寻找才女自身在江南文化场域中的独立位置。而她被清室聘为教师,虽然可能为野史,但也说明江南社会对王端淑这样的才女在文化场域中占据独立位置合法性的肯定。前述的才女采石,在与男性才人的竞争中也处于上风。“署中东偏花畦中有白牡丹一株,郑夫人尝置酒招采石赏之。采石赋诗云:‘素心毕竟让花王,侍从多骑白凤凰。富贵自应留本色,天人原不要浓妆。馆陶仙子情如玉,虢国夫人影亦香。寄语谰言莫相戏,洗红久已谱清商。’幕中同人有拈此题者,见此诗都为阁笔。”[15](卷4,PP38-39)类似才女与才子同场竞赛,让男性士人拜服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清中叶吴江才女汪玉轸。“同人欲制挽联未成,适汪宜秋内史玉轸挽对至,众遂藉口阁笔。其词云:‘入梦想从君,鹤背恐嫌凡骨重;遗真添画我,飞仙可要侍儿扶。’”[13](卷1,P56) 可见,在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开始凭借自身的才华在江南社会的文化场域中建构自身的位置。才女群体成为江南文化场域中新的竞争者而不再仅仅依赖于男性才子的鼓吹和提携。 这种独立的场域位置无疑给当时的才女提供了新的“越界”交往的动力,所以当长辈劝说梁章钜的妇人郑氏学琴时,郑氏却说:“与其学琴,不如学诗,尚冀有片纸只字留示后昆也。”[20](卷3,P19) 当才女与男性的交往、竞争中获得独立位置后,才女的自我评价就不再仅仅依赖于男性士人的评价,也包括来自于才女群体内部的独立评价。这种对才女独立声望和群体内部评价的重视在骆绮兰的自序中和袁枚对其儿媳的评价中也得到了证实。骆绮兰在《听秋轩闺中同人集诗序》中道:“深悔向者好名太过,适以自招口实”[22](P696)。而在袁枚给骆绮兰的信中,提到“八月驾到,定到随园,得与所慕爱之儿妇相聚谈诗。渠读来书夸美之词,笑声不绝。甚矣!女子之好名更甚于男子也”[22](P790)。可见,成为才女,可能在江南社会中拥有独立名望,这也是众多女子成为才女的动力。“识字岂真忧患始,作诗宁冀姓名留。当时幸有怜才者,应愿将丝绣蒋侯。”[23](P1330) 影响所及,如果自身才华不足以在与男性的诗文交往中获胜,那么,对才女作品予以编辑也成为部分才女进行自身独立声望获得的竞争性手段。“合肥女史赵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读书。尝集古今名媛四百余人,各为小传,题曰《壶史》。又着《香奁杂考》一卷,征引详博。至于韵语,特其余事耳。”[16](卷24,P361)“严廷锳妻孙嫊,吴郡人,幼明慧,娴经史,兼工藻绘。早寡寒灯败帷,辛苦四十载,晚课女孙辑古名媛文百余首,细为评注,名曰古文鞶鉴。识者以为可补中垒列女传、汝南女典之缺,巡抚张伯行表其庐榜曰:独娴大义。”[24](P3202) 可见,在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和江南士人文化场域竞赛压力的合力下,由于才女“越界”交往对于家庭和男性士人社会地位再生产具有重要功能,才女“越界”成为江南社会容忍和鼓励的行为。而这种对“越界”的容忍和鼓励又往往会促使才女获得独立场域位置和独立声望,并成为驱动才女群体“越界”交往的内在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越界”交往对于整个江南社会的秩序运行而言,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面对才女群体的“越界”,江南社会是如何来予以规训从而保障其性别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的呢? 三、作为生命周期的才女“越界”:江南社会秩序对才女“越界”的规训 “马氏名间卿,字芷居,金陵人。陈翰林鲁南之继室也。鲁南丧耦,知其贤而有文,遂委禽焉。”[25](P3080)陈中之女“端容止,不妄言笑。女工精致过人,读《女诫》、《孝经》等,皆通大意。太平君(陈中)爱之,邑大家争聘”[26](P371)。 当时的才女在婚姻市场上较受欢迎,例如才女凌兴凤,当丈夫去世以后,大家皆欲聘,以为才女有利其家。才女之所以在婚姻市场上受欢迎,关键还在于才女的“越界”并没有真正冲击到“男外女内”“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秩序,而相反,才女的“越界”交往是建立在社会性别秩序对当时女性的规训基础上的。才女被社会性别秩序定义为“德才兼备”。德,作为才女群体的基本要素,始终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其生命周期的青年阶段,其个体才华得到承认和尊重,并可以凭借其个体才华“越界”与男性士人交往,但是这种“越界”依然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大多数才女与男性士人的交往依然是建立在诗文的基础上,才女在交往过程中,必须始终恪守女德。因而,女德,作为社会性别秩序的主要规范,始终是对才女的交往行动产生制约作用的。 同时,必须意识到,才女“越界”交往只是其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活动。如果说,在才女未嫁的青年阶段,“才”是评价才女的主要标准和声望来源,才女可以依靠其才华“越界”交往的话,那么,婚后,“德”就上升为才女的主要评价标准和声望来源,必须严守“男外女内”的性别空间边界,相夫课子⑦,其与其他男性士人的交往基本上停止。 在科举制背景下,课子对于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生产无疑十分重要。而才女的才华,对于子代教育来说,无疑大有裨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王凤娴“暇则拈书课其子女,吟咏自如”,丈夫卒于官后,“孺人茹荼十余年,卒教子伯元君以明经荐乡书。是时孺人昼则操管钥,课臧获,勤瘁于家政;夜则课伯元君学,非丙夜不休”[27(P91)。顾若璞,丈夫早逝,更是身兼严父慈母两职。“酒浆组纴之暇,陈发所藏书,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记》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二子者从外傅入,辄令篝灯坐隅,为陈说吾所明。更相率吚吾至丙夜乃罢。”[13](卷6,P143)桐乡孔继英,课子严而有法。“家贫不能购书,命长子启震借书抄读时,复代为手缮。”[29](P150)无锡杨氏幼时从叔父学习,“二子稍长,亲授句读,后虽已就师,每夜归必篝灯火与相对以助其勤。”[29](P302)苏州朱氏幼通《女诫》诸书,“教二子无所不至,家有塾师,而复自课不废”[30]。南京户部郎中陆恺的母亲李氏更是“教诸子甚严,自外传归,夜则课之”[31](P79)。 才女婚后不仅可以为“令子之母”,同时也是丈夫的陪读良伴,使丈夫的攻读更有效率,帮助其在家庭竞赛中获胜。如仁和郭素媛“娴女训,于归后佐其夫读书,恒达旦,以为常”[32](P2529)。王璐卿“江南通州人孝廉马振飞配。天姿颖异,读书过目成诵。于归后励夫子以读书,脱钗典衣以佐膏火,有不足则篝灯刺绣以继之。每遇花晨月夕,辄贯酒为欢,间制小诗则彼此酬和。”[33](P169)而常熟孙原湘与妻子才女席佩兰感情弥笃。其《示内》诗有云:“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34](P1),这种夫妻同读互动所产生的愉悦,会增强丈夫的攻读效率。同样的事例很多,如“周云英,字逸仙,宝山人。嫁竹旬里徐阶三。家贫不废吟咏。阶三亦工诗词,……著有《卫花居诗草》。……与逸仙诗同一潇洒,可谓纸阁双声矣。”[13](卷5,P124)“吴江张春水……续配陆璞卿女史,名惠,幼即明慧,并长诗画。春水丧偶,读其《绣余吟》而善之,遂倩人委禽焉。由是巡檐索句,刻烛联吟,殆无虚日。春水编其闺中倡和诸作为《双声合刻》,传为艺林韵事。”[13](卷5,P125) 因而,才女的“越界”交往被社会性别秩序规训为阶段性事件,才女在婚后和其他女性一样安于“内”,“女德”取代“女才”成为才女婚后的首要规范。这样,婚后的才女成为对社会性别秩序完全无害的群体。她们通过课子和相夫,帮助子代或者夫婿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对于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和社会秩序再生产有着显著的作用,并且,其才华又会让其夫婿产生建立在个体吸引基础上的愉悦感。因而,选择才女成为当时很多士人择偶的现实标准。 甚至当夫婿在江南社会中无法维持自身社会地位时,才女还可以由内而外,利用自身的才华,维持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位置,从而间接地对于江南社会的秩序稳定起到了维持的功能。如“采石,嘉兴人,归吾闽曾茂才颐吉。茂才游幕江南,寄孥吴下。采石卖诗画自给。”[20](卷2,PP37-38) 可见,才女不仅意味着有可能通过相夫课子等活动来帮助家庭社会地位的稳定和提升,也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丈夫无法承担“外”的责任)可以由内而外,保障其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生存和社会地位的维持。从而使得江南社会在总体向上流动性下降⑧的同时依然能维持其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再生产。 四、结语 明清的江南社会是由士绅掌握权力的社会。一方面它具有稳定性,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定性,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和各安其位是这种等级社会稳定性和秩序再生产的需要和表现。然而,与这种稳定性相对立的是,江南社会在微观的家庭层面,同时又是一个有着流动性的竞争的社会。由于造就士绅阶层的科举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要想维持和提升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就意味着江南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处于科举考试的高度竞争之中。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性不仅在士绅阶层中存在,随着明清江南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发育,上下有别的阶层界限开始模糊,僭越性开始显现,维持自身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再能够仅仅依赖江南社会自身秩序包括性别秩序的运行,而必须是一个动态的与其他阶层竞争的过程。如何让自身的家庭和家族在江南社会的竞争和流动中保持甚至提升其社会位置和社会声望,成为每一个家庭秩序维护者和运行者的首要职责。这就意味着,江南社会与家庭之间在秩序维护方面开始出现微妙的缝隙。对于江南社会来说,社会秩序必须优先强调非流动性和上下尊卑的家庭和社会等级规范,这样才能保障江南社会甚至国家的稳定性。而对于家庭来说,这些强调稳定化和固定化的社会空间秩序和技术虽然依然重要,但首要的紧迫性任务是如何让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再生产和声望竞争中获胜。因而,在晚明和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举制竞争的日益加剧,江南社会的秩序运行和家庭竞赛之间出现了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才女群体在江南社会中开始盛行。 才女的个体才华使得才女成为无法完全用江南社会中“女子”范畴来定义的对象,才女群体与男性士人的交往使得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男外女内”的社会性别空间边界,在与男性人士交往中,才女凭借其个体才华来提升家庭和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这构成了家庭和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竞赛的新的手段和文化资本。 正是因为才女之才有维持和提升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的功能,因而,江南社会一方面容忍和鼓励才女群体的“越界”交往;然而另一方面,通过种种规训手段来确保才女与男性的“越界”交往始终只是其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性事件,使才女婚后完全恪守社会性别秩序的规训,成为贤妻良母,不对社会性别秩序带来真正的威胁,其相夫课子的行为,又有助于家庭社会地位的向上提升,从而有助于江南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随着才女越界被定义为一个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事件,才女越界交往对性别秩序的威胁也就被化解,才女“越界”成为明清江南社会默认甚至鼓励的现象。才女群体的存在及其与男性士人的交游没有混淆江南社会的社会性别空间边界,相反,不仅使得社会性别空间边界更为明晰,也使得江南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更为顺畅。 注释: ①从目前学界研究情况来看,才女群体在明代已经出现,如晚明著名的叶氏家族才女群,但还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建立在地域唱和基础上的才女群体在清代远多于明代,如随园女弟子群、陈文述女弟子群、蕉园诗社、吴中十子等地域性才女群体,呈现出以江南地域为中心的唱和交往情况,互动频繁。 ②持这种观点影响较大者为曼素恩(Susan Mann)和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中强调才女群体作为社会上层群体,其动用的资源和与男性的权力关系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阅读女性群体的不一致性,进而讨论了中国社会的“内”与“外”不仅仅是一种性别压迫机制,同时也赋予了女性特别是作为上层的才女群体以一定的自由。而高彦颐在其影响很大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更是将才女群体的这种主体性演绎到了极致,认为才女群体事实上利用各种策略获得了行动和挣脱男权意义的自由。 ③目前对于清代地域性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在文学和史学研究领域,对于清代江南知识女性群体盛行与江南社会的微观运行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④关于这种宽容,详见张杰:《才女为何?明清江南社会对“才女”群体的社会认知和秩序生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⑤事实上,如袁枚等在文化场域中占据较高位置的士人,通过广泛吸收女弟子,从而可以将这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详见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⑥清代进士录取率呈现波动状态。据研究者李润强统计,自乾隆十三年至六十年(1748-1795)的22科。共取中进士3753名,平均每科录取170.6人,远低于清代单科录取平均值239.7人。而乾隆六十年递减至81人,为清代单科人数和每科平均人数最少的一个时期。见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⑦关于这一点,见张杰:《才女为何?明清江南社会对“才女”群体的社会认知和秩序生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⑧科举录取率在嘉庆年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而监生、廪生和捐官的泛滥使得低级士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的“寒士”。由于科举无望,同时又拥有流动的合法性,这些寒士对江南社会低流动性的社会空间秩序带来一定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