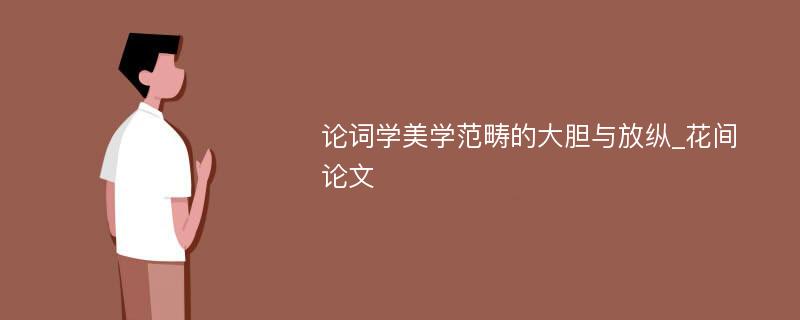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豪放论文,范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豪放”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司空图(837-908)首先提出的。他在其《二十四诗品》中以“豪放”指称一种诗歌风格,并以诗的语言对其加以描述:“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召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展现了一种阔大之境,豪迈之情。杨廷芝《诗品浅解》释之云:“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可谓中肯。
宋人普遍地将“豪放”用入了诗歌风格批评。欧阳修以李、杜诗格为“豪放(《六一诗话》):王安石以“豪放飘逸”评李白诗(见《滹南诗话》引);陈师道称鲍照之(《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见《升庵诗话》)。“豪放”风格受到推荐,甚至成为一时的风气。《东轩笔录》记载:“皇祐(宋仁宗年号,1049-1054年)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看来,宋人用于诗歌风格批评的“豪放”概念,当它表示正面推崇之意时,其内涵与司空图在《诗品》中的描述并无二致;但“豪放”过甚所产生的非美因素,也已如影随形般地出现了。
“豪放”进入词学批评领域是从苏轼开始的。由于词是一种有严格的形式要求的文类,所以用于词学批评中的“豪放”,其取义首先侧重于“放”的一端,即逸出规范,不受约束。苏轼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苏轼的这番话常被用来作为其词论为“诗化理论”的根据,这里恐怕存在某些先入之见或误解。平心玩味这段文字,苏轼是把词当作“小词”看的,也就是说,苏轼是重视词的体性要求的。所以他说陈慥的词是“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虽似褒扬,其中却含有的委婉的批评之意。而下文“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用一“但”字转折,更是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可以推测,陈慥的词是不大协律的,所以苏轼批评他“豪放太过”,太不合词的规矩。
苏轼自己的词也常得到“豪放”的评语。宋朱弁评苏轼的和章质夫杨花词“若豪放不入律吕”(《曲洧旧闻》卷五);陆游认为苏轼“所作乐府词多不协”的原因是“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沈义父《乐府指迷》云:“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故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也。”(《乐府指迷·豪放与协律》指出东坡、稼轩词并非一概豪放,也有协律之作。在以上诸家的批评语言中,“豪放”的语意也都侧重于“不协律”。
词在形式上的不协律乃是由于其内容的逸出传统范围而造成的。沈义父所云“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也”已经暗示了我们这一点。苏门学士晁补之对此早有议论:“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词话》卷一)正是由于苏词的内容“横放杰出”,以致“曲子中缚不住”,才产生了“不谐音律”的结果。换句话说,豪放的内容要求一种豪放的、不受拘束的形式来表达,词风的“豪放”是词的题材超越传统范围的必然结果。可见,“豪放”不仅包含“放”的一端,即形式的不协律,也包含“豪”的一端,即内容的宏阔有气魄。而词的内容又取决于词人的性情,所以,词人主体情性之“豪”是词体之“放”的内在原因。
这样,“豪放”就不光指词的形式不协律了。曾慥(?-1155)在《东坡词拾遗跋》中说:“东坡先生长短句既镂板,……传之无穷,想象豪放风流之不可及也。”(见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这里的“豪放”,因与“风流”连用,更能唤起读者对苏轼其人人格魅力的向往,而不仅指苏轼的词风。张端义(1179-?)评朱希真:“《月》词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贵耳集·朱希真词》)着眼的是词的内容所展现的雄伟气魄和阔大境界。所以,宋代词学批评中的“豪放”概念,其内涵在不断地丰富着:从最初仅着眼于形式因素,到涵盖了作家的性情因素,作品的风格因素。
明代张綖(生卒不详,正德八年—即1513年—举人)首次明确地将豪放与婉约对举,作为词的两种风格类型之一提出。他在《诗余图谱·凡例》后的按语中说:“词体(注:张綖所说的“体”,指风格,不指体裁。《文心雕龙·体性》提出文有八体,就是指八种风格类型。参见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169页。笔者注))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不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稍后的徐师曾在其《文体明辨序论》中论及“诗余”时,完全秉承了张綖的观点。
张綖的词论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把豪放作为一种与婉约并列的词学风格揭示了出来,指出“豪放”词的特征是“气象恢弘”,这是对豪放词风的整体的和审美的把握,而不是像前人那样较多着眼于词的形式因素、内容因素或作者因素的某一侧面。其次,张綖指出词风的豪婉“存乎其人”,即与作者的性情有关。秦词多婉约,苏词多豪放,正是由他们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第三,虽然张綖确认了豪放是婉约并行的词之一体,但仍坚持“词体以婉约为正”。明确地将豪放与婉约并列,是张綖词论的革命性所在;而“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则是其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局限性所在。
张綖以婉约、豪放二体论词,并非平空而来,而有其历史的渊源。张綖的贡献在于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对历史现象做了高度的概括。
词的创作实践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立足于张綖的时代,回望七八百年的词史,豪放词的创作虽然不占主流,但也代有作者,取得了足以与婉约词抗衡的艺术成就。北宋有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人;南宋有以辛弃疾为主的爱国词人群体;金人词“颇多深裘大马之风”(清贺裳《皱水轩词筌》)元;“虞、赵诸公辈,……以气概属词”(王世贞《艺苑卮言》);近代况周颐曰:“金元词近刚方”(《蕙风词话》卷三)。在金元两代的词创作中,豪放一脉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张綖看到了这些历史事实,并且以明智的态度承认了它。
除了创作上的依据外,张綖之论也有其理论上的渊源。当苏轼以其雄旷之作进入词坛时,其幕士即评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形象地道出了两种不同的词风,一为柔婉,一为雄壮。南渡之际的胡寅(1098-1156)在《题〈酒边词〉》中高度评价了苏轼革新词风的意义:“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见《宋六十名家词》)这段话的理论重心虽在肯定苏轼豪放词的历史地位,但其将苏轼的逸怀浩气、举首高歌与《花间》、柳永的绮罗香泽、绸缪婉转对比而言,实际上于无意中对词风作了豪婉之分。南宋朱熹(1130-1200)在《答陈同甫书》中说:“远寄新词,……两词豪宕清婉,各极其趣。”(《朱子文集》卷三十六)明确地以“豪”与“婉”对举评词,成为张綖之论的先导。
而清代有关“豪放”的词论又是在张綖之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在对豪、婉两种词风的评价上,清人有了更为客观公允的学术性的态度。《四库提要·词曲类》之总序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渊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从源流上确认了词体“以清切婉丽为宗”,以苏辛为“别格”的事实,同时认为苏辛虽为别格,其艺术上之“工”却不可否认,因此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风才得以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这种既承认词体有(正)宗、有别格,但又肯定二者各具独立的价值、不能偏废的观念,获得具有学者素质的清代批评家的普遍认可。
清初颇有影响的文坛领袖人物王士祯(“祯”一作“禛”)认为“名家当行,固有二派”,意即以苏为名家,柳为当行,二者之间无须强分优劣。他颇为自豪地声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不以优劣论豪婉,实际上就是肯定了二者具有同等的审美价值。陈廷焯也从自己的词学观念出发,批评了张綖的“当以婉约为主”论:“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认为只要“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则“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矣。”(《白雨斋词话》卷一)
沈祥龙从词的题材要求及声情一致的原则出发肯定了豪放之体的必然性。他说:“词之体,各有所宜,如吊古宜悲慨苍凉,纪事宜条畅滉漾,言愁宜呜咽悠扬,述乐宜淋漓和畅,赋闺房宜旖旎妩媚,咏关河宜豪放雄壮。得其宜则声情合矣。”(《论词随笔·词体各有所宜》)“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则情致绝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论词随笔·词有婉约有豪放》)“词调不下数百,有豪放,有婉约,相题选调,贵得其宜。调合,则词之声情始合。”(《论词随笔·词贵相题选调》)他甚至把豪婉两派词风的肇始上溯至唐人,说:“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二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于诗近江西;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华胜,于诗近西昆。后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论词随笔》由于对李白词的真伪尚存异议,所以从理论上讲,沈祥龙此论未免有些勉强。但从感情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欲从源头上为豪放词取得正宗地位的良苦用心。
清代词论更从创作的主体——即词人——这一本原上对影响豪放词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田同之(生卒年不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举人)认为词的豪、婉取决于作者性情:“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四圃词说·填词见性情》)此论发挥了张綖的“存乎其人”说,但立论的重心却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而与孟称舜的观点相似。张綖坚持“当以婉约为主”,以东坡词为“非本色”,田同之则认为只要能反映作者的性情之真,豪放、婉约都可以称为本色。由陈师道传至张綖的“本色”观,是立足于词体而言的,这个“本色”指的是词体的本色,即由《花间》、柳永等一系列的词人所确立起来的词学审美传统。田同之所说的“本色”,与孟称舜一样,指的是词人性情之本色。从对“本色”的不同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词学批评的重心从作品转向了作家。谢章铤说:“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赌棋山庄词话》卷九)对豪放词风的肯定,也就是对词的表现主体情性之功能的肯定。换句话说,只有词的功能从应歌转向自抒怀抱,豪放词风才能获得充分的肯定。
清代词论家进一步认为,词人的胸怀襟抱、学问、遭际与豪放词风的形成有关。彭孙遹曰:“稼轩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金粟词话》)楼敬思曰:“稼轩驱使庄、骚,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王士祯曰:“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词苑丛谈》卷四引)梨庄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卷四,按梨庄为清代词人周在浚,周亮工长子)陈廷焯曰:“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白雨斋词话》)这些议论可以说都是在张綖的“存乎其人”之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是张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其理论重心落在“以婉约为正”上,清人则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词人的性情、学问、襟抱等极为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反映了清代重学问、重修养的风气,一方面也反映出对中无所有,只对苏辛进行表面化的模仿的词风的批评。
以上诸论,实际上都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即论证豪放这种词风存在的合理性。既然词调的音乐风格有豪放与婉约之别;词的题材内容有豪放与婉约之别;词人的性情、襟抱、遭际等也有豪放与婉约之别,那么,词的文本的风格有豪放与婉约之别不是天经地义吗?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给豪放词一个充分肯定的正面评价?这就是以上诸论的内在逻辑。
谈到豪放词风,过去的词论家往往用的是一种否定、惋惜或辩护的调子,清人既然证明了豪放词风存在的合理性,就以正面的、积极的态度进入了对豪放词艺术风貌的探寻。
苏辛并称,前人多强调其豪放之同。清代以来的词论家则对苏辛之异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周济曰:“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之论虽有扬辛抑苏之嫌,却一语道破了苏辛之别,即苏词自在而不当行,辛词当行但亦偶有自在处。什么是自在?周济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介存斋论词杂著》)东坡自云“吾文如万斛涌泉,不择地而皆可出。”其作词亦然,晁补之谓其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不十分用力”,“横放杰出”,精神上无束缚,落笔自由潇洒,如涌泉自出,(胡仔语)这就是自在。“曲子中缚不住”,时时逸出词体的音律规范,当然难称当行。所谓“辛之当行处”,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提到:“(辛词)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此固是辛之当行处,但恐怕还不是周济所谓“当行”。周济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即收敛雄心,压抑高调,将温婉之音变为悲凉之调,虽悲凉而不失温婉的底子,这恐怕才是周济所说的辛之“当行”。谢章铤说辛词“豪放中见精致”(《赌棋山庄词话》卷一)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辛词固多豪放之作,但其“当行”处,是并不“放”,反而相当收敛的。冯煦谓其“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蒿庵论词》)“摧刚为柔”当是稼轩豪放词的特色所在。
陈廷焯明确地指出:“东坡稼轩,同而不同者也。”所谓“同”,即同属于豪放词人;所谓“不同”,即二人之“豪放”的内涵不同。他认为苏词是“王道”、“神品”、“仙品”,而辛词“兼有霸气,然犹不悖于王也”,是“豪品”。(以上所引均见《白雨斋词话》卷八)《白雨斋词话》对苏辛词作了多角度的比较:
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魅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卷八)
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卷八)
东坡……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卷六)
王国维对苏辛之异作了最简洁的概括:“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
台湾词学家郑骞对“旷”与“豪”作了如下解释:
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放。(《景午丛编》上编“漫谈苏辛异同”)
稼轩词所得评语如“悲壮激烈”《宋史》卷四百—辛弃疾传)“雄深雅健”(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激扬奋厉”(沈谦《填词杂说》)、“悲愤慷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东坡词所得的评语如“韵力高胜”(《魏庆之词话》引述黄庭坚语)、“清空中有意趣”(张炎《词源》卷下)、“丰骨超凡”(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卷五)、“高华沉痛”(邓廷桢《双砚斋词话》)等,两相比较,我们不难领悟苏辛“豪放”词风内涵的差异。
对于由苏辛词风产生的负面因素,清代一些词论家也进行了检讨。
周济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指出苏词有粗豪处,而一般读者往往不觉其病、反以为佳。
谢章铤说:“学稼轩,要从豪放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人打油恶道。”(《赌棋山庄词话》卷一)
陈廷焯认为稼轩有些词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以致“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有些词着力太重,不免剑拔弩张。(《白雨斋词话》卷一)“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白雨斋词话》)卷六)
王国维也指出:“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人间词话》)
各家之论,既对后世学苏辛者学而不得其要提出批评,也客观地指出了苏辛词本身艺术上存在的不足。正因为苏辛词确实有“粗豪”、“粗犷滑稽”处,从而给后世的“叫嚣者”提供了模仿的范本。由于苏辛的影响之大,学者之多,其词风的弊端也充分暴露。于是,“豪放”词风往往给人以复合的印象:它既有超旷、壮丽、雄豪、悲凉之美,又往往拖着粗鲁、粗莽、粗豪、粗鄙之类的影子,甚或可入打油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