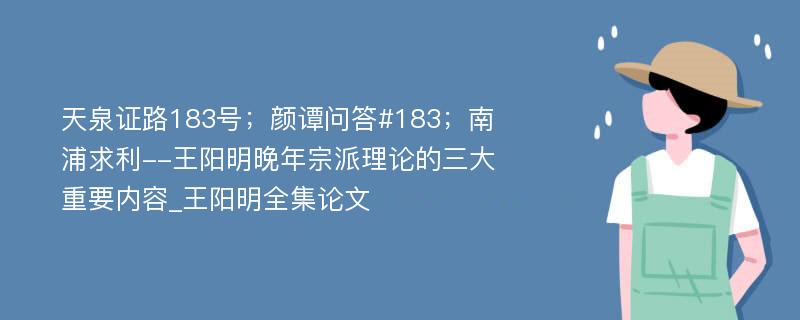
天泉证道#183;严滩问答#183;南浦请益——有关王阳明晚年宗说的三件大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泉论文,晚年论文,三件论文,问答论文,南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阳明在嘉靖六年(1527)九月八日受命赴两广前一天晚上,在会稽天泉桥向他的两位大弟子钱德洪、王畿解释他晚年讲学宗旨及教法,史称天泉证道。次日,这两位弟子送他,至严滩而别。阳明在严滩,“复申前说”〔1〕,并有严滩问答,进一步提出了“究极之说”〔2〕。十月,至南昌附近的南浦,其在江右及门弟子等候于南浦,向他请益。阳明向他们申述天泉证道,说其“向上一机”〔3〕被王畿发泄,可裹粮前往,质证于钱王两子。因此,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是阳明晚年在仅仅二个月中再三向其弟子阐述晚年宗旨的三次重要学术活动。不了解这三件大事,就不能了解他晚年的学术思想。然而,这三件大事,是否确有其事,或其内容究竟如何,是宗旨还是权法,却有争论。次年,阳明由两广归里,卒于途中,他本人已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企图对此作些考证,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天泉证道
记载天泉证道的文章,据我统计有六种之多,其所载内容及解释并不完全一致,甚或有较大分歧。今取《传习录》、阳明《年谱》及王畿《天泉证道记》为主,予以对校,以见其异同。至于对“四有”、“四无”和“四句教法”的分析,因篇幅有限,将在另文探讨。
《传习录》和阳明《年谱》,是王门的权威性经典著作,对天泉证道的记载,在主要问题上基本相同:一、“四句教法”,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四句,确是阳明讲学“宗旨”;二、王畿的“四无句”,即“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5〕,确为阳明所许可;三、阳明指出钱德洪与王畿之所争,是两种本体与工夫之争。“四无”之说属“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而钱德洪所说,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功夫熟后,“本体亦明尽了”,这是为“其次立法”的〔6〕四、阳明在认可这两种教法后,指出他们应“相取为益”,“相资为用”,但在相取为益中,他告诫王畿,“利根之人世亦难遇”,若“只在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7〕、故在相资为用中,他倾向于钱德洪,而以四句教法为宗旨。
然而《年谱》与《传专习录》所载亦有不同:一、《年谱》提到人心本体如太虚一段,《传习录》无,但关系不大,于天泉证道精神无损;二、《年谱》载阳明所说:“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而《传习录》所载是:“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这里的差异,涉及四句教是否属阳明一贯教法,还是他晚年的宗法?前者讲的是“始立”,晚年才立,后者讲的是“原有”,在居越以前就有了。我们如翻阅《阳明全书》、当以《年谱》所载为是。三、《年谱》尚载有阳明的一段语,此段《传习录》无,即:“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这段话很重要,对王畿来说,是致命的。《年谱》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而王畿早已在嘉靖十一年(1532)在北京殿试时开始宣讲他的“四无”说“此意”了。以后他林下、水边、车辙所至,无不在讲“此意”,如果指《年谱》所说,岂非违背了师说!师说是教他只能“默默自修”,是不能“接人”的。
这第三点的不同,反映了钱德洪和王畿的学术分歧在这三十年中有了发展。钱德洪在修《年谱》时曾说:“师殁后,吾党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吴时,见吾党喜为高论立异说,以为亲得师传,而不本其言之有自。”〔8〕看来,这一句是钱德洪为了纠正王讲学中的“高论”流弊而加上去的,王畿虽参予《年谱》的编辑,但不是主要的,这一段决非王畿之意。
王畿本人对天泉证道的叙述,则见于他的《天泉证道纪》一文中,此文由他口述,由其弟子笔录。此文与《年谱》及《传习录》所载,其主要事迹虽无多大出入,如阳明的四句教法,他的“四无”说及其得阳明的认可,关于两者相资为用,关于本体、功夫为两种人立教等等。然而在叙述中有很大不同、除王畿对“四无”说作了发挥为《年谱》及《传习录》所无外,主要区别有下列三点:
一、《纪》中并没有讲到四句教法是以后接人的宗旨。他只讲钱德洪的“四有”,即四句教与王的“四无”应“互相取益”。“四有”是接中根以下的,“四无”是接上根人的,然都不能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受,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受。”〔9〕这里那有四句教是接人宗旨之意?
二、《纪》以阳明所说:“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视人”句代替了《年谱》所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句。“保任”与“默默自修”含义不同。保任指悟道之后,仍须继续保持心中所悟之道,不使退转,然并不排斥通过外在践履,涵养维持所悟之道。如龙潭崇信问天皇道悟:“如何保任?”答:“任性逍遥,随缘放旷”〔10〕,这是一种以内为主,内外不二的修持方法。然“默默自修”,只讲内,而不讲外,如正觉宏智的《默照铭》:“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尔廓尔,体处灵然。灵然独照,照中还妙”〔11〕。默照是离开语言和行为的,宏智在《坐禅箴》里又说:“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12〕。这是一种割裂内外,脱离外界的内心修养方法。因此,保任是可以接人的,只是“不宜轻以示人”而已,而后者则绝对否定接人的可能性。王畿这一代替,为自己宣讲“四无”说找到了合法性和权威性。
三、《纪》中一字不提《年谱》和《传习录》中所载阳明对王畿“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的告诫。反而记载了阳明认为“四无”说是他“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踖等之病,故含蓄到今”的“传心秘藏”,而现在被王泄漏了天机而已。这样一来,“四无”说不仅为阳明所印可,而且成阳明的“传心秘藏”。这对王畿来说,自然极为重要。他在晚年多次对人说,他之所以到处讲学,因“师门晚年宗说,非敢谓已有所得。幸有所闻,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常年出游,虽以求益于四方,亦思得二、三法器真能以性命相许者,相与证明领受,衍此一脉如线之传。”〔13〕“四无说”成了阳明晚年宗说,并据以成他自己学说的基础和自己学派的法印了。
严滩问答
关于严滩问答,权威性的记载见于《传习录》下:
先生起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14〕。
王畿在《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中所载,与《传习录》基本一致,然有所不同:
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钱德洪)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两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工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致诘。“夫子莞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己见得,正好更相切mo,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二人唯唯而别〔15〕。
其中有无实幻、本体工夫之说,与《传专习录》同。但有三点不同:一,增加“夫子复申前说,……弗失吾宗”句,“前说”自是指天泉证道事,说明严滩问答是天泉证道的继续。
二,实相幻相的一问一答是谁主动提出的?据《传专习录》,是王畿提出的,而按《绪山行状》,是阳明先举这一问题乍看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其实大有意义在。按《传习录》,是王畿提出,然后才有阳明之答。因此,举这一“佛家实相幻相之说”而授佛入儒的责任在王畿,阳明不过因问而答而已。按《绪山行状》,这一“佛家”观点是老师复申天泉证道前说后“因举”的,师生之间十分契合。
三,增加了阳明对严滩问答的评语:“此是究极之说”,而且需“默默保任,轻勿泄漏”。这“究极之说”句在严滩问答中是原有的。还是王畿后来加上去的?应该说是原有的。嘉靖八年(1519),以钱德洪和王畿具名的《讣告同门》一文,先述天泉证道事,然后说:“冬初,追送严滩请益,夫子又为究极之说,由是退与四方同志,更相切磨。”〔16〕当时,钱德洪也承认有此“究极之说”的。
《传习录》为何要把这一援佛入儒的问答略去阳明“究极之说”的评语呢?这反映了钱德洪的观点,他在《传习录》所载的严滩问答后,自己作了这样的评语:“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这样一来,就把“究极之说”彻底否定了,阳明只不过在问答中偶然提及而已。
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实相幻相、本体工夫的问答?由于这是授佛入儒的命题,既有佛学的含义,又有儒学特别是王学的含义,所以比较复杂,我在这里据《传习录》所载试图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第一句:“有心俱是实”,为何是即本体证工夫?从佛学来说,“有”是幻相非实相,“无”是实相非幻相,所以这里有实幻无并非佛学意义上而只能从儒学意义一上来理解。“有心”,指心体的“有”,即“有善无恶心之体”,“俱是实”,指旨先天有善无恶的心体,流行于后天意、知、物之间,意为有善无恶之意,知为知善知恶之知,物为有善无恶之物,心、意、知物一齐皆“有”。这后天的功夫, 都是有善无恶心体流行的结果,其所表现的都是有善无恶的“有相,”这“有相”是人生的真实相状,都是“实相”,这即“是本体上说工夫”从这一命题来看,是儒家的观点。
第二句“无心俱是幻”,是承上句而来的。“无心”自然指心体之“无”,即“无善无恶心之体”。这“无心”的心体流行于意、知、物之间,自然是无意之意、无知之知、无物之物,心、意、知、物一齐皆“无”了。所以从“无心”的本体来看上句的心、意、知、物的“有相”,从本体到工夫,俱是“幻相”,这是“是本体上说工夫”的又一解。这是王畿“四无”说的观点。
第三句“无心俱是实”。这“无心”不是指心体,是指工夫。以无心应万物,即僧肇说的“虽观有而无所取相”,宋小招提寺僧慧达,把这句话解释为“造修”〔17〕,“造修”即工夫。用这工夫说本体,则俱是实相,亦即僧肇在《宗本义》所说的:“三乘等观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谓诸法实相也。”〔18〕无心观法,则见诸法实相。若在工夫上意、知、物一齐皆无,即“无所取相”,则心亦不可谓之有矣。心就成了无善无恶的心了。这是“是工夫上说本体”的一解。
第四句“有心俱是幻”。从工夫上说,“有心”自是指执有之心。心之执有,即用诚意、致知、格物(从《大学》本义上讲)的工夫,用此工夫说本体,是通过对治(去恶)面获得的“善”,(不是“至善”,王畿认为“无善无恶是为至善”〔19〕)是“有相”。僧肇说:“且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慧达对“有‘有’注释说:“妄有、计有,故云有‘有’。”〔20〕所以这“善”是“妄有”,是“幻有”。这是“是工夫说本体”的又一解。
上述四句解,都是从本体工夫合一上说的。
那末,为何说这是,究极之说”?这是因为在其中指出“即本休证工夫”的最上乘说,即第二句“无心俱是幻”,又指出丁“用工夫合本体”的最上乘说、即第三句无心俱是实”。从本体上的“无心”,到工夫上的“无心”、按王畿在《天泉证道纪》上的话说,即是“从无处立根基”。曾为阳明的弟子,后来对王学持反对态度的黄绾、在批评阳明时说: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学,有以致知为致为极其良知,……又今看六祖《坛云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21〕。
黄绾熟知阳明思想,阳明是以“无”为本来面目,他说过:”心之本体,原无一物。”〔22〕“佛氏说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23〕即以“无”为心体的本然状态。这本然状态是直超上乘,是良知的“至极”、是则严滩问答,岂非是阳明的“究极之说”!
严滩四句是“有”“无”相兼,是彻上彻下语,但其中的“究极之说”的上乘二句,与王畿的“四无”说相契合,这就难怪钱德洪在编阳明《年谱》中要略去严滩问答这一节、在《专习录》中要略去“究极之说”这一评语,而且还补上此仅是老师“偶读”面非“借此立”的话了。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严问答不仅是天泉证道的继续,而且是天泉证道的补充,是了解阳明晚年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而王畿正是在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中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南浦请益
严滩送别后、阳明即兼程赴江西转广东。十月、到达南昌西南的南浦,其江右及广弟子率众二三百人候于此地,向阳明请益,据王畿说:
(阳明)过江右,东廓(邹守益)、南野(欧阳德)、狮泉(刘邦采)、洛村(黄弘纲)、善山(何廷仁)、药湖(魏良器)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请益。夫子云:“军旅匆匆、从何处说起。我此意言之已久,不欲轻言,以待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虽出山,德洪、汝中与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诸君只裹粮往浙,相与聚处,当自有得,待予归未晚也〔24〕。
这就是“南浦请益”。请益的是什么呢?文中所说的“畜之已久,不欲轻言……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与王畿《天泉证道纪》中阳明说的:“汝中所见、我正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踖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是相符合的,所以南浦请益,请益的是天泉证道事,而主要说的是王畿的“四无”说。
问题是,南浦请益却不见于《传习录》和阳明《年谱》,是否是王畿捏造出来的?不是,理由如下:
一、聂豹弟子徐阶在其所作《龙溪王先生传》中也记载了此事,他这样写:“文成至洪都,邹司成东廓暨水洲、南野诸君,率同志百余人出谒,文成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近被王汝中指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吾方有兵事,无暇为诸君言,但质之汝中,当有证也。”〔25〕这一内容,王畿的同乡和弟子赵锦在《龙溪王先生墓志铭》中亦有记载。我们不能排除徐阶和赵锦参阅王畿之文而作的可能性。但徐阶在北都时,曾设讲会于灵济宫,主持讲会者就有欧阳德,故亦不能排除徐阶从他的口中获知的可能。徐阶位至大学士,一度秉国政,岂能随便听王畿一家之言而轻率写下此王门中的万世大事!
二、南浦请益第二年,即嘉靖七年(1528),当时尚未进入王学门的罗洪先,赵京会考,已听到王门弟子对钱德洪和王畿的高度评价:
嘉靖戊子,予计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闻阳明之门所评乎?“江有何王,浙有钱王”,盖指雩都何善山秦,黄洛村弘纲与绍兴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也〔26〕。
如没有南浦请益,王门弟子何以在第二年即对钱、王二人有如此高的评语?南浦请益中,阳明是高度赞赏这二位大弟子的,令江右弟子往浙江向他们质证天泉证道事。罗洪先后来为何廷仁(善山)作《墓志铭》说:“君以诸生事先生,在赣超赣,在南浦趋南浦,在越趋越。”〔27〕可见何廷仁确参加南浦请益。
三、南浦请益参加者黄弘纲和邹守益,后来对天泉证道亦有所讲述。罗洪先在《与钱绪山论年谱》中说:“天泉桥上与龙溪兄分辨学术,当时在洛村兄所闻亦如此,与龙溪兄《续传习录》(即《传习录》下卷)所载不悖。此万世大关键,故一字不敢改移。”〔28〕天泉证道时,黄弘纲不在绍兴,罗洪先所说的“当时”,应指天泉证道二个月后,黄弘纲在南浦请益时所闻。
邹守益后来在《青原赠处》中叙述了天泉证道的内容,但他把地址记错了,说是在富阳,而把钱德洪的“四有”首句写成“至善无恶者心”〔29〕。《青原赠处》作于嘉靖二十五年,当时《传习录》下卷及阳明《年谱》尚未刻成,其所说自是凭其记忆所及,而他的记忆,也只能来自南浦请益。
从上述三方面考证,南浦请益是可靠的。王畿是一位“天性温良,居常坦然平怀”〔30〕的儒者,他决不可能凭空提造此事。至于钱德洪为何在谢《传习录》和《年谱》中不载此事,可能南浦请益主要济的是王畿的“向上一机”,钱德洪印象不深,晚年忘了。况且语录和年谱,并不必事无巨细,一概录入,钱德洪因为与王畿观点分歧,认作小事而不载。
南浦请益的主要意义,在于证明天泉证屯之不虚,证明阳明四句教法之不虚,证明王侵“四无”说为阳明印可之不虚。明末,刘宗周就提出这一疑问,认为“四句教法”首句“盖阳明先生偶一言之,而实未尝箔之于书,为教人定本,龙溪辑欲以‘无’说笼罩前人,逐有天泉一段活柄。甚矣,阳明之不幸也。”〔31〕
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别怀疑“四无”说取得阳明的印可,他说:“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王级)言之也。”〔32〕
然而,从南浦请益来看,刘宗周和黄宗羲的怀疑不能成立。
注释:
〔1〕〔2〕〔15〕〔24〕《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十《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绪山钱君行状》
〔3〕〔25〕〔30〕同上书卷末徐阶《龙溪王先生传》
〔4〕〔6〕〔7〕〔14〕《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
〔5〕〔23〕同上书报三十五《年谱三》
〔8〕钱德洪《答沧题谱书》,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年谱附录二》
〔9〕《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天期证谴纪》
〔10〕《五灯会元》卷七《龙潭崇信禅师》
〔11〕〔12〕《宏贸值师广录》卷八,见《禅宗语录辑要》
〔13〕《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
〔16〕《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
〔17〕〔18〕《肇论中吴集解》卷上《宋本义》
〔19〕《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五《与阳和张子回答》
〔20〕《肇论中吴集解》卷中《论主复书释答》
〔21〕黄绾《明道集》卷一
〔22〕《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
〔26〕〔27〕《念庵文集》卷十五《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铭》
〔28〕同上书卷四《与钱绪山论年谱》
〔29〕《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三《青原赠处》
〔31〕《刘子全书》卷十二《学言下》
〔32〕《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