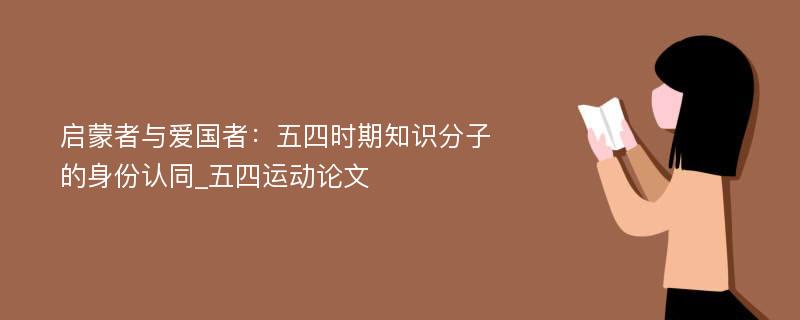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者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启蒙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103-05
五四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启蒙时代。其间,民国宪政失败的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患日亟的民族危机联翩而至。民初以来,中国一直笼罩在袁世凯专制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霾之下。1915年春夏,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袁世凯背叛民国而登基称帝。此宪政与民族双重危机,构成了《青年杂志》出世的严峻历史背景。在此危机中的启蒙时代,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人权和主权的双重挑战,此即中国现代性特有的“启蒙”与“救亡”问题。信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普世价值的启蒙者如何回应民族危机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在新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中如何处理个人、国家和人类的认同问题,是一个饶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
一、个人与国家:公民民族主义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旋律是崇尚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个人主义,那么这种个人主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其时,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尼采式贵族个人主义、易卜生式个性主义、泡尔生式精神个人主义和斯蒂纳式无政府个人主义风行知识界,各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汇成了新文化运动之个性解放的新思潮。陈独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伦理革命命题,其表征“人的发现”和自我的觉醒的启蒙精神,预示着现代中国以精神个体代替家族成员的人格转型。
另一方面,五四又是一个充满民族危机的时代,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救亡始终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力和思想主题。这也是中国启蒙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之特性。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既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者,又是抵抗外敌侵略的爱国者。他们面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
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早年曾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投身反帝宣传活动。但是,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陈独秀等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来说,其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启蒙价值的公民民族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而不是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主要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为认同的基础,而族裔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则分别以共同的族群、文化、历史为认同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中诸种民族主义往往多有交叉融会[1]。
陈独秀信奉公民民族主义或“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语),他坚持以“公民国家”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主张理性的、民主的爱国主义。对于陈这样一位启蒙者来说,爱国主义必须符合启蒙的基本价值。他的一篇写于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文章,以《爱国心与自觉心》为题,讨论了“爱国”与“启蒙”的关系。陈主张,国家具有土地、人民、主权三大要素,人民建设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此为立国之精神。而中国自古以来不曾存在这种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国家既然不合国家之义,亦无爱国可言。陈主张的“自觉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启蒙爱国主义。在他看来,爱国心是情感的产物,而自觉心是理智的产物。爱国,是爱其为保障人民权利和增进人民幸福之团体。自觉,是觉其国家之目的和情势。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盲目的爱国,难免为野心家所利用。陈甚至不无激愤地主张,国家若背离保障人民权利和增进人民幸福的目的,则国家存亡亦无所荣惜。而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反而残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甚至托庇于法治国统治下的失国之民,其权利亦非乱国之孑遗所可及[1]。陈对国家的批判性观点,表达了其对袁氏当国的悲观绝望,但其激进的公民民族主义国家观即使在进步知识界也广受争议。
在陈独秀看来,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偶像。一个国家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而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无国家可言。因而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它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国家,才有国际竞争。惨酷的欧洲战争,就是“国家”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2]。
关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陈独秀一直持理性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关于“爱国”,陈主张:“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3]
对于陈独秀来说,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主权,它建基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因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其说是领土,毋宁说是人民和主权。陈的这种“公民国家”想象,建基于其自由民主的启蒙理想。这种以公民国家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它显然既不同于梁启超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也有异于孙中山以族裔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新文化运动另一位知识领袖胡适亦信奉公民爱国主义。他留美时期崇尚卡莱尔(Carlyle)的爱国说,卡氏主张另一种爱国主义,即国家与国民和谐互爱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偏见之上,它将使国家对国民更加亲爱,而没有对国民的哲学的伤害;这种爱国主义将使国家爱所有的人,公正地奖励各个地区,国民也将不顾一切地热爱祖国,以及它那悠久的社会传统及道德生活[4] (P197)。
对于胡适来说,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赖以成立的惟一根据,是“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此为民族主义的惟一前提,否则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即不能成立。他甚至相信,若以袁世凯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令中国人选择,人们必然选择威尔逊。若以威尔逊为异族而选择袁世凯的人,必然是中民族主义之毒的愚人,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4] (P354)。
胡适坚持认为,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而必须以民主制度为前提,以人民主权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他强调:“‘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此共和政治之说也,而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4] (P355)显然,胡适的公民民族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与陈独秀的思想如出一辙。
高一涵以自由主义阐释国家之目的以及公民与国家之关系。他强调,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求得归宿之途径。人民与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二者互有权利和义务。人格为权利之主体,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无权利则不得为公民。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个人之权利,以支持国家[5]。高对国家和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表征着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和民主精神。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在这种以民主公民国家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中,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意义被弱化,因而它亦常与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结缘。
二、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另一精神面相,它与构成其时代精神的个人主义相映成趣。诚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6]。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多为世界主义者,康德的“世界公民”只是其“人是目的”原则的逻辑结果。而孔多塞认为,世界主义是个人解放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那些小群体融入越来越大的群体的过程,最终达致由一种普世语言和共同文化凝聚而成的全球社会[7]。
与欧洲启蒙运动相似,世界主义亦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思想特征。尽管身处列强瓜分的外患日亟的民族危机之中,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多为世界主义者。张灏关于五四思想之两歧性的分析,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荡的思想张力[8]。
陈独秀是一个崇尚人类大同的世界主义者,他对国家的怀疑和批判立基于其世界主义理念。与孔多塞一样,他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将最终趋向于一个大同世界,并且热心倡言世界语的普及,将其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工具。在与陶孟和讨论世界语的通信中,陈写道:“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共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9]。陈独秀相信,人类进化过程中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10]。
在《答半农的D诗》中,陈独秀抒发了他的世界主义情怀:
弟兄们!姊妹们!
我们对于世上同类的姊妹弟兄们,都不可此界彼疆,怨张怪李。
我们说的话不大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各有各的脾气,但这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会把我们连成一气。
连成一气,何等平安,亲密!
为什么彼界此疆,怨张怪李。[11]
胡适少年留美的经历使其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尽管他的世界主义并不排斥爱国主义。在他看来,现代的世界主义,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轻视和反对国家的世界主义。他主张:“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胡适很欣赏邓耐生(Tennyson)的诗句:“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4] (P79)
在胡适看来,当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即德国式的帝国主义。这种自私自利的国家主义在国际交往中不顾国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爱、和平,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即“国际大法”。要实现大同主义,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提倡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爱国是大好事,但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即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4] (P264)。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既倡言个人主义,又推重人类“大我”的价值。关于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他强调,自古希腊以迄近代的个人主义,无不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人类。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如家族、社会、国家,但因为要推翻这些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的“人类”。因而凡是个人主义思想家,无不承认个人与人类的双重关系[12]。
李大钊则将个性解放和世界大同视为民主的终极目的。他主张:“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13] 李的人道理想是超民族的,他号召青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4]。
蔡元培校长在为北大学生刊物《国民》杂志创刊号所作序中,倡言“博大”的世界主义。他强调:“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之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有利于国,而又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而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绝端利己的国家主义。”[15]
新文化运动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及其主笔的《新潮》杂志,亦以人道主义为启蒙理想,其人道主义则以人类大同的世界主义为鹄的。在个体与人类之间,傅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他主张:“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16]
在傅斯年看来,一个现代人具有民族成员和世界公民双重身份。他在《青年的两件事业》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这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傅斯年相信,世界是一个大共和国,人类未来可能趋于组成“世界共和国”,人道的事业需要人类的互助合作,目前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之事业,正是世界主义运动的两大趋势。
在世界主义风行的五四时期,甚至连维新宿儒梁启超亦深受此时代思潮的感染。梁一改早年的国家民族主义观点,转而主张超国家的世界主义。在《改造》发刊词中,梁主张:“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17]
三、救亡中的启蒙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潮,历来被政治家们归为反帝的“爱国运动”。而关于五四事件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演变,学界亦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论。这些看法涉及五四后期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于,“五四运动”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压倒了启蒙主义?其实,即使在举国爱国激情高涨的“五四运动”以后,启蒙知识领袖们并没有因救亡的时势而成为民族主义者。
耐人寻味的是,五四知识领袖们并没有将五四运动简单地视为一场爱国运动,而是从中看到了公民社会之公共精神和社会运动的民主价值。陈独秀在五四后仍坚持公民民族主义观点,他在评价“五四运动”的精神时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直接行动加以制裁,而不诉诸法律,不依赖特殊势力和议员[18]。易言之,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国民对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
与陈独秀一样,“五四运动”总指挥、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亦更看重五四运动的民主意义。他强调:“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19] 在傅看来,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其社会运动预示着中国人继国力的觉悟、政治的觉悟、文化的觉悟之后的“社会的觉悟”。“所以从5月4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20] (P353)
1919年春,罗曼·罗兰、罗素等欧洲著名知识分子在巴黎联合签署《精神独立宣言》,反思欧战中各国知识人囿于狭悲民族主义而背叛人道主义理想、为本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推波助澜的深刻教训。宣言沉痛地承认,欧战使知识分子陷入迷乱之中,大多数知识界的人都将其学术和聪明才智供其政巩之用。他们使思想沦为欲望之器,并且成了一个国、一个邦、一个阶级营私的工具。宣言坚持精神独立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宣布知识分子尊敬的唯有超越种级族类的真理,并且为全体人类而工作[21]。《精神独立宣言》同年秋由张申府(崧年)译成中文而刊载于《新青年》和《新潮》二刊,激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共鸣。
译者张申府在按语中强调,此宣言的主旨在于:“无论求学求术,除了为他自己外,都是为的个人:自己和自己以外真实存在的各个体——便是全人类——绝不是为的那一部分,绝不是为的私人徒党的营利射利,强加在众人头上的,像上帝,教会,国,把人压制,把人拘束,把人隔离分裂的东西。”[22] 张申府还在《少年中国》发表罗素的《国家》译文,他在前言中表达了罗素式的国家观,将国家视为拘束人、分裂人的不祥之物[23]。
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宣言》进一步激活了陈独秀的世界主义精神,他将其视为欧洲知识界由民族主义而世界主义的觉悟,这也使他更加疏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关于爱国问题,陈认为,中华民族自古闭关而独霸东洋,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国民性上缺乏爱国思想。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深厚,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欧洲有些思想高远的人,相信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而没有价值,并且目睹了许多以国家的名义所作的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3]。
与梁启超相反,陈独秀并不认为中国人自古缺乏国家观念是坏事。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学者和现代心地善良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观念,而不知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国家,闭口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班日本留学生从日本教科书上贩来的劣货。全人类的吃饭、穿衣、能哭、能笑、贸易、交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之名,才分裂了全人类互相亲善的感情,使人们无故猜忌,爱国主义最终沦为战争工具。陈独秀指出,“国家”本是近代欧洲军阀财阀制造出来欺人自肥的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入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和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拒斥国家主义的觉悟,如《精神独立宣言》的作者和武者小路等人。而中国人现在还欲创立过时的国家主义,是十分愚蠢的[24]。
在五四的启蒙思想世界中,“公理”不仅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是连接自由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纽带。“公理”是五四知识界极为流行的一个中心概念,所谓“公理”,即启蒙运动的普世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在宪政危机和民族危机并存的历史语境中,五四公民民族主义以“公民国家”连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启蒙价值的“公理”框架中处理自我与国族的认同问题,这一内争“人权”和外争“主权”的“公理”,成为启蒙知识分子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的普世原则。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将“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刊物的宗旨,他强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25] 对于陈来说,“公理”具有内外两层意义:对内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对外保障国家主权的自由平等。陈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因为威氏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坚持自由平等的“公理”。威尔逊主义之要旨有二:“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25] 陈对威尔逊的期待虽不免一厢情愿,但符合其一贯的公民国家观,即把国家视为内保人权、外保主权的公民共同体。
如果说陈独秀以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原则为“公理”,那么对于胡适来说,“公理”则更多意味着人道主义。胡留美期间,早在1914年底欧战爆发伊始,即有“以公理易强权”之主张。胡认为:“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之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此吾所以自附于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24]
胡适的这一“以公理易强权”的主张,在五四时期成为启蒙知识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诉求。五四可谓一个“公理”流行的时代。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反对日本瓜分中国的凡尔赛和约、吁求“民族自决”的理由,仍是《每周评论》的“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字,这也是启蒙者对欧洲大战的立场。因而,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更是启蒙主义、世界主义的。陈独秀主张:“……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24]
在五四后期的“社会改造”大潮中,个性解放的启蒙理想并没有被启蒙知识分子所抛弃,傅斯年主张启蒙与社会解放双管齐下。他认为,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个性的;二、社会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社会性发展。中国人在这个时候自然免不了加入最近的趋向,不过前一时代的个性发展,也是我们所必须要求的事情。不经个性充分发达的一个阶级,文化上必觉得干燥无味,而且突然转到社会性上,文化上又很觉得根基薄弱,所以中国此后的思想运动应该是双管齐下的[20] (P356)。傅关于个性与社会并重的主张,在五四后期启蒙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在五四运动以后,并没有出现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李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问题在于:一是将“启蒙”与“救亡”简单地对应于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骨干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从事爱国反帝运动的人结合而成,这种外在化的解释忽略了新文化人之启蒙者和爱国者复合的双重身份,以及五四思想结构中启蒙与救亡的内在张力。二是对“救亡”的定义过于宽泛含混,前文将“救亡”解释为爱国反帝运动,后文则将“社会改造”、“革命”等等统统归入“救亡”,从而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26]。实际上,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蜕变,民族危机、爱国反帝和民族主义并非主要因素,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毋宁说是启蒙的内在分化和自我瓦解,即启蒙运动由于其内部之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而走向分裂。此即唐德刚所谓列宁的半盘西化与杜威的半盘西化的冲突。
五四以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世界主义是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从孔多塞到马克思都是世界主义者,而且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最彻底的世界主义理想。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标签:五四运动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陈独秀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