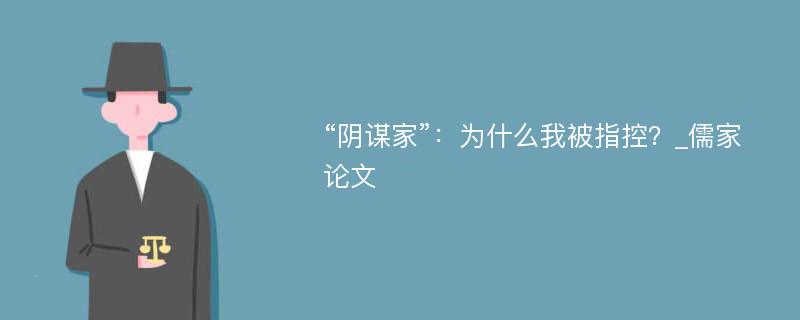
“阴谋家”:老子何以被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阴谋家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的误解和负面评价中,“阴谋家”堪称老子身后不幸得到的最大污名。①追根溯源,其所以被诬固然与《老子》文本的某些表达方式有一定关系,但就思想本旨而言,老子之学绝非阴谋术,老子其人亦绝非阴谋论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毋宁说,这一污名乃是在老学复杂曲折的衍变流传及其与儒家思想的相互激荡中历史地形成的。陈荣捷、陈鼓应等先生曾概要指出了其间的若干因由,以为老子辩诬。②但鉴于此类辩诬之论甚是简略,且只是涉及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而非全部,加之学界对此又多习焉不察或较少注意,所以,关于老子之“阴谋家”污名的历史由来问题尚有进一步澄清、检讨之必要。本文将在汲取前人洞见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深入剖析这一思想史现象。 一、易生歧解的《老子》文本 在古代,以“阴谋家”之污名抨击老子的主要是后世的儒家学者。从他们的立场说,指认老子之学为机谋诡诈之术绝不是凭空捏造,因为其书中原有支持这一污名的内证。综括来看,后儒经常援以为据的所谓内证大致有老子的如下一些说法: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以下引《老子》仅注某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二十八章)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 老子的这些思想常被儒家批评为权诈机巧的阴谋术,而这又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有直接关系。显而易见,上述文本包含着一系列可以相互转化的对反范畴或观念:雌雄、黑白、张歙、与夺、柔弱与刚强、后其身与身先、不自为大与成其大、无私与成其私、不争与莫能与之争,等等。怎样理解其间对立转化之关系的实质呢?客观地说,这确是一个易生歧见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老子之“阴谋家”污名的是非判断。 我的看法是,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应断章取义,仅着眼于前引文本,而是需从老子思想的全部内容和总体特征出发。具体来说,上述诸范畴之间的对立转化关系涉指两个层面。 第一,正如天地自然中普遍存在着对立转化现象那样,这种关系是作为史官的老子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既为规律,它无疑就是客观的或“自然”的。换言之,在社会生活及其演变中,原本存在着各种事物和力量的对立转化,老子所做的只是“秉笔直书”,即如实将此类现象不加价值判断地描述出来而已。这也就意味着,由雌而雄、由张而歙、由与而夺、由柔弱而刚强、由无私而成其私、由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等诸如此类的转化都是外在的客观现实,转化的过程都是“自然史”性质的,其间并无老子本人的私见和私意,当然更没有丝毫的阴谋术考量。 第二,“反者,道之动”兼涉天道和人道,落实到政治层面而为“术”,老子告诫君王应依道而行,遵循“弱者,道之用”的原则去治国理政。在此意义上,前述对反范畴之间的转化关系是指得道者采取的政治实践方式及其将会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老子之所以强调为政以弱而不以强、以与而不以夺、以无私而不以有私,是因为惟有如此方符应于天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之常则,上合天道、下合人道,所以必将产生积极、久远的政治效应,正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或“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这本是老子基于其对“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深彻省察而向为政者提出的箴谏之言,但在老学思想的历史流传中,这种政治理念却很容易遭到后世的无意误解甚或故意曲解,儒家以机权阴谋之名指斥老子即属此类。 详而言之,在前述范畴中,雌、黑、张、与、柔弱、后其身、不自为大、无私、不争等皆是为政者所采取的具体手段,雄、白、歙、夺、刚强、身先、成其大、成其私、莫能与之争等则是各种手段最终导致的政治效应。但由于言之过简且“微妙难识”(司马迁语,见《史记·老子列传》),两组对反范畴之间原本属于行为方式和客观效应的关系,却可能会被误解者或批评者颠倒过来,并将其扭转为内在动机或主观目的与为满足动机、实现目的而刻意采取的相应手段的关系。譬如,为满足成其私的动机而采取无私的手段,为达到莫能与之争的目的而采取不争的手段,动机是身先而手段却是后其身,等等。进一步,由于两组范畴各自都是前后对反的,而老子对其间的手段和客观效应的转化关系所作的又是几乎不带任何价值色彩的纯现象性描述,③以至于这种关系一旦被颠倒过来并被纳入动机与手段的框架中理解,老子力倡的为政理念便会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阴谋性或机权巧诈的特点。因为,从动机和手段的关系角度看,为政者表面上采取的雌弱、给予、无私等手段,与其意在雄强、夺取、成其私等内在动机或主观目的恰恰相反,所以如果施行这些手段,客观上既可对他人(尤其是敌手)构成误导,造成错觉乃至有效欺骗,又可以借此掩盖其潜在动机或真实目的。后文我们将会看到,儒家对老子之诡诈机权的责难正是循此进路展开的。 毋庸置疑,这种动机或目的与手段的理解进路背离了老子思想的本旨。细究其理可发现,即便责难者希望照此把老子塑造为“阴谋家”,至少仍另需两个关乎价值立场的前提预设:首先,为政者是无道之徒,其内心怀揣着不可示人的私利私欲,所以才要采取虚假的欺骗手段;其次,老子不仅不批判,反倒主动向无道的为政者献计献策,以助其取利逞欲。显然,这两条都与老子思想的价值品格不合。且看他对主政者逐利营私的批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六十六章);“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才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七十五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反乎此,老子的理想则是“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六十四章)、“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据此,如果说老子以权诈之术助无道之主逐利济私,显然与实不符,有失公允。 必须申明的是,对老子的“阴谋家”污名进行文本澄清,并不等于否认其思想实质是“君人南面之术”。事实上,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正如高亨、王博等学者所言,老子说话的对象始终是君王,而其思想的中心则是君王的权力使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与儒、墨、法等家相比,老子的深刻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仅批评君王独断专行、扩张放纵,更洞察到社会政治中“为人和为己的统一”,即君王只有“给万物和百姓空间”,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大的空间”。因此,在权力的使用方式上,“柔弱的态度要好过刚强的态度,无为的做法要胜过有为的做法”。④从这个角度说,所谓柔弱谦退、无私无为实际都是君王自我收敛、自我节制的权力使用方式,而并非诡诈机巧的阴谋术。 二、申韩与汉初黄老 以“阴谋家”之名斥老虽多出自后儒,但最先将老子之学往阴谋术的方向诠释的却是战国时期的韩非,而老子之“阴谋家”污名在儒家的异端批判话语中的坐实,韩非当亦难辞其咎。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是对老子思想的选择性阐发,而在后者以事释老或以事证老的叙述体例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渗透于其间的权诈阴谋气息,最典型的是如下几例: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损,谓“弱胜强”也。 句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 这两段话把老子抽象的张翕、取与、强弱之论与具体的历史事例对应起来,并直接将其由广义的社会历史规律和治国理政之道狭义地曲解为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运筹谋划、克敌制胜之术,其基本要领是假与真取、示弱致强、以柔克刚;相应地,其运用方式也由明转暗,由公开而潜隐(“起事于无形”),而其理论实质则已由权力的自我内向节制之道蜕变为君王向外攻伐取利的狡计。 除了敌我斗争,在君臣关系方面,《韩非子》亦多借引老子思想阐发其人主术。兹以《主道》《扬榷》二篇为例,⑤前者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后者云:“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万民一从。”类似表述在《韩非子》其他篇亦不少见。要言之,通过改造利用老子的虚静无为的道论思想和政治理念,韩非提出,人主必须采取以虚待实、以静制动、以暗执明的手段,确保其对臣下的有效驾驭。《难三》篇有云:“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可谓一语道破人主术深藏不露的特质。 韩非对老子的借重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其权诈阴谋源出自老。这种印象与老子思想的本貌无疑相去天壤。比这更糟糕的是,当韩非以老子之学为理据阐发其权诈之术时,其性恶思想也被暗中夹带给了老子,而事实上老子并没有人性恶的观念。但在韩非那里,人皆具有自私自利的天性却是其政治思想得以成立的人性论前提,正是由此前提出发,他才会基于人主立场,公然提倡权诈之术,以维护其专制权力和至高利益。这也就是说,在韩非性恶论的标杆上,人主克敌制胜、驾驭臣子的阴谋术都是正当合理的,权诈手段的外在有效性与人主内在的逐利动机恰相匹配。老子虽然并不主张人性恶,但其思想流传和衍变不可左右的结果却是,一旦老子之学经由韩非的借重、曲解而被视为阴谋之术,它也就同时被逆向地传染上了自私自利的负面品格,而这恰好因应了后儒斥老子为“阴谋家”所需要的价值前提预设。 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在汉代被称为黄老学或黄老术,兼取包括法家在内的诸家之长是其显著特点,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云:“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作为“西汉道家之渊府”(梁启超语),⑥《淮南子》正是一部兼采各家的黄老学著作。⑦就该书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借鉴来看,其中亦不乏近于《韩非子》的阴谋论成分。以《道应训》篇为例: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于干遂。故老子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亲之,故霸中国。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纣闻而患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以献于纣,因费仲而通。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杀牛而赐之。文王归,乃为玉门,筑灵台……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故老子曰:“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这两段话直承《韩非子·喻老》篇,二者不仅援引相同的历史典故,其叙说体例亦相一致:先述历史典故,最后以老子之言道出个中玄机。更重要的是,作者所强调的同样是老子之言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作为权诈之术的实际应用。按其叙说,勾践灭吴、文王克商皆堪称把老子抽象的刚柔荣辱之论具体用作阴谋术以欺骗敌手、暗中取利的经典案例。类似的叙说在《淮南子》全书虽不多见,且亦非该书释老的主调,但却继《韩非子》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给老子之学添加了更多的阴谋论气息。 此外,《史记》将老子与申不害、韩非合传,客观上也为后世将老子视为与申韩一系的阴谋论者提供了口实和进行理论拼接的历史线索。关于老子与申韩的思想关联,司马迁认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传末在简要评说申韩的思想大旨后,再次指认二者之学“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这是司马迁立足于汉初黄老之学的理论视野所表达的他对老子与申韩之间的思想源流关系的看法,⑧《史记》将三者合传的根据和因由亦正在于此,但道家和法家的后世批评者却可能从中虚构出一条并非实然的思想史脉络:老子是刑名法术之学的始作俑者,申韩则是其后继者。特别是在后儒的异端话语中,当道家和法家一并遭到激烈批判的情况下,老子更可能会被不加分辨地反向追认为申韩法术权谋之祸的肇端,例如南宋朱熹在以嘲讽的口吻指斥老子之学的所谓诡诈特点后,接着便说:“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此类批评之偏失在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固然被申韩借取以阐发其刑名法术之学,但如果因此而齐同“源”与“流”,把老子与申韩混为一谈却不察其异,并且反过来把申韩刑名法术之学的某些内容、弊害及其负面性的价值品格(例如阴险诡诈)径直移置或归因于老子,显然既不合逻辑,更有悖于思想史的本相。 应当指出,虽然《淮南子》的少数内容和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可能会被后儒援作指证老子为阴谋论者的凭据,且汉代道家亦讲求“治国用兵、取威定霸之术”,⑨但从总体上说,权诈诡计在当时却似乎并不被认为是黄老学的本有之义,由此可推,老子之学也未被视为阴谋之术。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好黄帝、老子之术”,其效命于高祖也,“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有些奇计因“颇秘,世莫能闻也”。所可寻味者,陈平作为“奇谋之士”非但没有津津自喜,反而坦言:“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陈平将其所擅长的阴谋奇计与所喜好的道家截然区分开来,且以前者为招祸自害之术,这说明汉初的一些黄老人物不仅不主张阴谋,反倒深切排斥之。另外,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这是道家尤其是老子之学呈现给汉人的基本貌相。从中可见,汉代学者对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之学褒贬兼有:谦弱自持是其所长,这与儒家的克攘之道相通;虚无放任、无所作为是其流弊,这与儒家的仁义礼智相悖。无论褒贬长短,汉人心目中的老子之学都与阴谋狡计无关。 三、黜老:儒家的异端话语 如同班固对道家思想的责难,由汉至唐,儒家黜老的基调是指斥其虚无放任、一味持守清静之弊,这可以说是针对老子薄仁非礼的反批评。例如,扬雄《法言·问道》:“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桓谭认为扬雄之书度越《老子》,理由是:“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汉书·扬雄传》)言下之意,老子的薄仁非礼之论诡于儒家圣道。王充则批评老子惟求全身养性而不济民于难的避世倾向,《论衡·定贤》:“(以)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是则老聃之徒也。道人与贤殊科者,忧世济民于难,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⑩谈及圣人和老子之于有无的问题,王弼云:“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此说虽旨在会通儒道,但内中也未尝不隐含着对老子沉湎于无的微词。裴頠的《崇有论》一方面肯定老子思想确有“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另一方面又批评道:“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晋书》卷三十五)东晋孙盛黜老,在其所著《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和《老子疑问反训》中,(11)仔细辩驳了老子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之说,其结论是:“案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骈拇枝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道宣《广弘明集》卷五)到了唐代,老子被帝王崇奉为先祖,但韩愈却直言不讳,在其名文《原道》中贬“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乃“小仁义”或“去仁与义言之也”,故其言仅是“一人之私言”,而非儒家“合仁与义”的“天下之公言”。(12) 简要回顾儒家黜老的历史可知,自《荀子·天论》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始,在此后由汉至唐的较长历史时期内,阴谋权诈之污名并没有被加诸老子。在儒家的异端话语中,以此污名黜老,当始于以排二氏、彰圣道为务的理学勃兴的宋代。 “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颐说: 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若言与之,乃意在取之,张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则秦之愚黔首,其术盖亦出于此。(《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52页) 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其初意欲谈道之极玄妙处,后来却入做权诈者上去。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然老子之后有申、韩,看申、韩与老子道甚悬绝,然其原乃自老子来。苏秦、张仪则更是取道远。(同上,第235页) 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本末舛矣。申、韩、张、苏皆其流之弊也。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后世犹或师之。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纵横,其失益远矣,今以无传焉。(同上,第1180页) 予夺翕张,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与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张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权诈之术也。(同上,第1181页) 程颐指斥“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的依据有三:一是他所建构的刑名权诈之术的异端学统——老子为源、申韩张苏为其流,二是他从动机(“意”)和手段的关系角度对老子所谓予夺翕张之论的臆解,三是他认为老子之学“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如前所述,这种批评的可辩驳处在于:其一,即便老子的某些思想被申韩张苏援引利用,也不应因此而混同本源与末流,径直把后者主张的刑名权诈之术反过来强加于老子;其二,老子的予夺翕张之论固然言之过简、易生歧解,但如若不结合老子思想之大旨,而只是断章取义,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潜隐的真实动机与表面的欺骗手段之间的关系,则显系偏狭武断;其三,正如陈鼓应、刘笑敢先生所指出的,先秦时期“愚”不等于“愚弄”,而《老子》六十五章所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及其他章中的“愚”字则是真朴或淳朴之意。(13) 与程颐同时代的苏轼著有《韩非论》一文,该文虽未批评老子之学“杂权诈”,但却从另一方面呼应了程颐所谓的异端学统,并与之相辅相成。苏轼认为,老聃、庄周之徒的“虚无淡泊之言”和“猖狂浮游之说”,“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但在后世,其绝弃人伦的虚无思想却势必被推重刑名的韩非等人所用,“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据此,苏轼断言:“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14)经此一说,除了权诈,申韩的所谓“残忍”之祸亦源出于老子,老子之罪愈发大矣。 平心而论,无论从内在动机的角度,还是以所谓“残忍”的后世流害责难老子,这类黜老话语实质上都已不再是客观公正的学理批评,而是基于儒家价值立场的道德讨伐。几乎可以看作是对程颐和苏轼之说的综合发挥,朱熹在指斥老子之学为权诈之术时便频出诛心之论,而他加诸老子的道德恶名则主要是自私与无情: 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问老氏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之说。曰:“它便拣便宜底先占了……”(同上) 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同上) 张文潜说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同上) 老子说话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奸……故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如申韩之徒皆是也。其后兵家亦祖其说,如《阴符经》之类是也。(同上)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欧公尝言,老氏贪生,释氏畏死,其说亦好。(《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关机巧便,尽天下之术数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数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同上) 这里提到的“占便宜”、“占得十分稳便”、“退步占奸”、“保全其身”、“贪生”等皆可归为自私,而所谓“忍心无情”、“便是杀人也不恤”也就是苏轼所说的“残忍”。其不同在于,苏轼认为“残忍”是老子之学在后世经由申韩而衍生的流害,而朱熹则将此罪名直接加诸老子。在朱熹看来,老子的自私和无情与申韩之徒是一致的,故其学必然流为变诈刑名。 朱熹把老子的诡诈手段概括为“反处做起”,而这种阴谋之术正是出自其自私无情之心。他说: “……天门开辟,能为雌乎?”《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说话都是这样意思。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都于反处做起。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之不已,其势必有时而屈。故他只务为弱。人才弱时,却蓄得那精刚完全;及其发也,自然不可当。”(《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谿,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你争。……只是他放出无状来,便不可当。(同上) 所谓“心最毒”、“设心措意”、“这样意思”都是朱熹对老子用心阴险的揣测和判定,其具体做法是以不争为争、以屈为伸、以柔弱胜刚强,即“反处做起”。朱熹认为,这种动机和手段相反的阴谋术之恶毒可畏在于其无形无状,“深藏固守,自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所以它一旦猛然发用,便使人猝不及防,无法抵挡。 朱熹黜老话语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对老子与刘汉政权的批评时常结合在一起。依朱熹之见,汉家取天下所凭借的全是老子的阴谋术: 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如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术,全是如此。……汉家始终治天下全是得此术,至武帝尽发出来。(同上) 在朱熹的天理与人欲、公私、王霸二元对立的历史视野中,刘汉政权属于负面的一端,而他将其与老子合在一起进行批评,一方面为老子的阴谋术提供了政治实践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也借此指明了老子思想的政治价值实质及其消极的历史后果。 综上所述,通过动机的揣测臆断以及由此展开的道德讨伐、由老子而至于申韩的异端学统的构建和具体的政治实践范例的提供,朱熹全方位、多角度地批判了老子的权诈思想。可以说,老子作为“阴谋家”的理论形象是在朱熹这里被清晰、完整地塑造出来的。而这一形象一旦被树立起来,便藉由程朱理学的广泛流行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甚至在后儒心目中从此变得根深蒂固。 朱熹之后,抨击老子思想为机巧权诈之术最用力者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在晚年所著《庄子解》中,船山不仅指认老子陷溺于“矫激权诈之失”,(15)更明确将其思想实质命以一险侧之“机”字: 老子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知者博大而守者卑弱,其意以空虚为物之所不能距,故宅于虚以待阴阳人事之挟实而来者,穷而自服;是以机而治天人者也。《阴符经》之说,盖出于此。以忘机为机,机尤险矣。(同上,第358页) 在批评老子基于二元思维的机权之术“尤险”的同时,船山称许庄子拔理于黑白雌雄虚实的老子之上,且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迥异于老:“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侧之机,故申、韩、孙、吴皆不得窃,不至如老氏之流害于后世。”(同上,第359页)这段话反过来说就是:老子之学必“启天下险侧之机”而至于寡恩刻薄、权谋巧诈,并终将流为申韩孙吴的刑兵法术,从而严重祸害后世。因此,船山在《老子衍·自序》中斥之曰:“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同上,第3页) 除了庄学和老学专书,其他著作中也可见船山批评老子的大量言论。这些著作的文本类型包括儒家经典诠释、史学批注、社会政治评论、思想文化短札等,不同语境下船山的黜老言论亦常有以权谋巧诈指斥老子之辞。鉴于船山的这类批评颇多,以下仅从几个方面各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首先,船山指斥老子佯装虚无、谦退、雌柔之貌,而其内里所蕴却是与之相反的实、进、刚: ……实以为体,虚以为用,给万物以柔靡,佯退而自怙其坚悍,则天下之机变刻深者,水不得而辞。而老氏犹宗之以为教父,曰“上善若水”,则亦乐用其貌而师之,以蕴险于衷。是故天下之至险者,莫老氏若焉。(《周易外传》卷二)(16) 以柔靡之假象掩盖其坚悍之内里,这种内外不一既是老子诈术的关键特点,也是其“至险”之所在。 其次,承程颐之说,船山认为老子的诈术包涵着愚弄和欺骗天下臣民的内容: 此之不察,则将为老氏“善下”之说,以济其“欲取固与”之术,以愚诱其民,则道裂矣。(《礼记章句》卷三十)(17) “广德若不足”……老氏之言此,欲芟夷廉隅而同于愚也。……“良贾深藏若虚”,贾而已矣;“盛德容貌若愚”,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贾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诗广传》卷四)(18) 照此,老子所谓“广德若不足”、“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云云,皆同于韩非主张的人主藏之于胸以潜御群臣的阴谋术,而老子所说的“圣人”则是愚弄天下、高深莫测的阴谋家。 再次,船山也像朱熹等先儒那样批评老子的翕张动静雌雄之术必然流为申韩之害: 若无忌惮之小人,如老聃之教……欲张固翕,以其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己愈退则物愈进,待其进之已盈,为物情之所不容,然后起而扑之,无能出其网罗者……故其流为兵家之阴谋、申韩之惨刻。(《周易内传》卷二上)(19) 若以轴喻,则脱然两物,故为不动以持毂而迫之转;则是有意不动,以役使群动。此老氏之所谓“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阳为静而阴挟之以动,守乎雌以奔走天下之雄。其流为申、韩者,正此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20) 与朱熹略有不同,船山有时又区分老子与申韩,认为申韩“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老子“贱名法以蕲安天下,未能合圣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驰也,愈于申、韩远矣”(《薑斋文集》卷一)。(21)但从其恶劣的历史影响来看,老子与申韩致祸虽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由此,船山把老庄与申韩、浮屠三者并称为“古今之大害”(《读通鉴论》卷十七)。(22) 复次,船山认为老子的机权之术常被后世士人用以避祸自保、逃避道义责任: 王弼、何晏师老庄之机械以避祸而瓦全之术,其与圣人知必极高明、礼必尽精微之道,天地悬隔。(《周易内传》卷五上)(23) 漠然于身,漠然于天下,优游淌瀁而夷然自适者……此其为术,老聃、杨朱、庄周倡之,而魏、晋以来,王衍、谢鲲之徒,鼓其狂澜,以荡患孝之心,弃善恶之辨……追原祸始,唯聃、朱、庄、列“守雌”“缘督”之教是信,以为仁之贼也。(《读通鉴论》卷十六)(24) 身陷明清易代之世,以“遗民”自处的船山多次借抨击老子的“守雌”和庄子的“缘督”等思想,把矛头指向历史和现实中士大夫群体因受老庄的影响而表现出的某种道家化的消极品性,尤其是那种惟思一己之自安自适而放弃其应有的责任担当的人格特征。在此意义上,船山批评的“守雌”已不属于老子,而是某些儒者机权保身的处世之道的代称。 最后,船山认为老子的机权巧诈若用于政治军事实践,只会使自己陷入凶险之地乃至自害自毙: 取安之书而读之,原本老氏之言,而杂之以辩士之游辞。老氏者,挟术以制阴阳之命,而不知其无如阴阳何也。……安是之学,其自杀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读刘安之书,可以鉴矣。(《读通鉴论》卷三)(25)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言兵者师之,为乱而已矣。……故奇者,将帅应变之权也,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赵充国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此之谓也。老氏者,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师之者,速毙而已矣。(《宋论》卷六)(26) 前段话涉及西汉刘安谋反自杀之事,后段话是对王安石用王韶之策出兵图夏的评论,船山批评此举无功而反有祸。在他看来,这两个历史教训都证明老子的机巧权谋只会祸害己身或国家。回顾前文,韩非亦曾以历史实例解老,但他对老子之术的实践效应的肯定态度却与船山恰好相反。船山是坚贞大儒,韩非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们对老子之术的不同理解和评价相映成趣,殊可玩味。 相较于朱熹等先儒,船山对作为阴谋论者的老子的批评,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还是在所涉社会历史的广度上,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时值明清昏乱之世,船山又以除尽异端、捍卫并挺显儒家圣道的纯洁性为己任,故其黜老言辞屡屡表现为颇具强烈情绪化色彩的冷嘲、热讽、怒责或痛斥。内中虽多有不尽合乎学理的偏颇、失实或不谨严之处,但却进一步强化了老子的“阴谋家”形象,为其添加了数笔浓墨重彩,使之变得更加丰满赫然起来。 四、现代余响 古人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而至于以假乱真或弄假成真,或许原是历史文化演变不可避免的一种荒唐而又真实的常态。由于宋以后的儒者基于排他性地挺立儒家圣道之目的而塑造的作为“阴谋家”的老子形象影响深远、彻人人心,以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一方面既有萧公权、(27)陈荣捷、陈鼓应、陈霞(28)等人着力于区分老子与申韩,进而为老子辩诬,另一方面,仍不乏有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老子思想视作机谋巧诈之术。兹略举三例: 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指出,《老子》一书的思想主题有二:道术和权谋,而“此两者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譬如,所谓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云云,“固是道术之辞,亦即权谋之用”。关于老子与韩非的关系,傅斯年说:“《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所释者,诚《老子》之本旨,谈道术乃其作用之背景,阴谋术数乃其处世之路也。”(29)不言而喻,这种老韩一贯之论沿袭了儒家构建的由道而法的异端学统。 1950年代,钱穆先生在《道家政治思想》中对老子思想做出了极为负面的理解和评价。他首先认定老子“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迹近欺诈”,其“所用则尽属人谋也”,“故老子教人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白而守其黑,知其荣而守其辱”,“伪装若无为,而其内心蓄意,则欲无不为”。相应于此,“老子心目中之圣人,乃颇有其私者。彼乃以无私为手段,以成其私为目的”。具体来说,“彼乃常求为一世俗中之雄者白者荣者,而只以雌以黑以辱作姿态,当作一种手段之运使而已”。钱穆的这些看法可谓朱熹以诛心之论黜老的现代版。近通于船山所说的“其哲亦愚人之哲”,除了黑白雌雄荣辱等诈术,钱穆还认为,“《老子》书中之圣人乃独擅其智,默运其智,而不使人知”,“玩弄天下人皆如小孩,使天下人心皆混沌,而彼圣者自己,则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些也不混沌。此实一愚民之圣也”,而老子的政治理想则不过是“聪明人玩弄愚人之一套把戏而已,外此更无有也”。括而言之,“《老子》书中之政治,则成为权谋术数,为一套高明手法之玩弄,政治成为统御……而实际意味,则落在黑暗之阴面。”(30)作为一位具有儒家襟怀的现代学者,钱穆几乎是把老子作为异端来看待的,而他对老子政治思想的批评,则堪称传统儒家黜老话语的现代形态,其中充满了儒家式的主观偏见和误解。限于篇幅,此不详述。 1980年代,李泽厚先生在《孙老韩合说》一文中提出,(31)老子思想是由长期的战争经验酿生的军事辩证法提升而来的政治和哲学的辩证法,老子之“道”所具有的变易灵活和不确定的神秘特色,亦“与其来源于兵家的‘诡道’不无关系”。因此之故,总体来看,作为君人南面术即政治辩证法,老子思想承继了军事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即:“以现实利害为依据”,高度冷静、排除情感的理智态度;“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式的矛盾思维;“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相应地,老子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也就表现出了兵家的诡诈机谋的特点。例如,“与《孙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兵家‘诡道’一脉相承,《老子》大讲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等等,其中的‘若’字便也可释作‘好像’。所以有人认为‘实质便不外一个装字’(32)‘以为后世阴谋者法’(33)”;其所谓“守柔”、“守雌”,“除了教导统治者要谦虚谨慎”之外,“主要是要人们注意到只有处于‘柔’、‘弱’的一方,才永远不会被战胜”,所以“不要过分地暴露自己的才能、力量和优势,要善于隐藏优势或强大”;而作为一种“君道”,老子之“无为”的涵义则是“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上却无所不管。”至于老子与韩非的关系,李泽厚认为,老子上承兵家的“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和“周密思虑具有异常明确的功利目的”,后来韩非将其“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并“把它发挥到自觉的极致”。对照儒家的黜老话语,可发现李氏所谓老子思想的“异常明确的功利目的”、极端冷静的利害算计和非情感态度,与宋以后儒家对老子的批评,特别是与朱熹所说的“自私之巧”、“其心都冷冰冰地了”极为相似,而李氏把老子之学定位为对军事经验的哲学提炼,(34)虽可谓别出心裁,但这一别出心裁之举却无意间从思想前源的角度更加坐实了儒家加诸老子的“阴谋家”污名,虽然李文并不是要对老子其人其学作道德裁断。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被后世无意误解或故意扭曲其本相的人物绝不只有老子。例如,商纣历来是众所周知的暴君,但孔子的门徒子贡却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其言下之意是说,纣的恶名或是“墙倒众人推”的社会风习的产物,其诸多恶行则是后人捏造、强加的。与此相类,以上的思想史考察表明,老子的“阴谋家”形象也是历史地、“累层地造成”的,其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乃至逐渐清晰、完整、充实丰满的漫长过程。全面考察这一过程,无疑既有助于学者拨开雾障以直面老子思想的真貌,进而从中开出新义,同时又能使我们从一个重要的细部深入理解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复杂性。 ①明人刘凤《严君平道德指归序》述及后世对老子之学的各种附会臆说,其首条便是“以柔弱胜刚强而为兵权之谲者,取彼险武附于诈谋”。(严遵著、王德有译注《老子指归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41页) ②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71页;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18页。 ③借用何炳棣的话说,老子的这种表达方式体现了一种完全撇开道德是非(amoral)的“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32页) ④王博《权力的自我节制:对老子哲学的一种解读》,《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⑤刘咸炘认为《主道》和《扬榷》篇“盖道家末流之通说”或“或申子之说”,郭沫若认为此二篇把老子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表现得极其淋漓尽致”。(傅杰选编《韩非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8、132页) ⑥转引自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06页。 ⑦冯友兰指出,刘安“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黄老之学”,“《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156页) ⑧通过分析比较,萧公权认为老子与申韩思想之根本迥不相同,由此他批评司马迁谓申韩之学源出自老的看法是“不揣本而齐末,取形貌而略大体,未足为定论也”。(《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⑨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86页。 ⑩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3页。 (11)僧祐、道宣《弘明集 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页。 (12)《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 (1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6-307页;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36-637页。 (14)《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103页。 (15)王夫之《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中华书局2009年,第150页。 (16)《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97-898页。 (17)《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225页。 (18)《船山全书》(第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65页。 (19)《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68-169页。 (20)《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98页。 (21)《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5、87页。 (22)《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51页。 (23)《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535页。 (24)《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13-614页。 (25)《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36页。 (26)《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68-170页。 (2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6-238页。 (28)陈霞《屈君伸民:老子政治思想新解》,《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9)《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30)钱穆《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6、143、137、128、131、132、139页。 (3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105页。 (32)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33)章太炎说:“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4)与李泽厚的观点相近,何炳棣直接指认《老子》的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在他看来,《老子》所谓“将欲翕之,必固张之”云云,“两千余年来被公认为最机灵诡诈的战术箴言,在词与义上都最肖似《孙子》”,而《孙子》的愚兵理论也被《老子》提升扩大成了愚民之术;另一方面,《孙》《老》皆“置道德是非于不顾”,只不过“前者语言坦率无隐”,后者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来柔化、缘饰其“冷酷”、“残忍无情”的心肠。(《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3、30-33页)标签:儒家论文; 韩非子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淮南子论文; 国学论文; 朱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