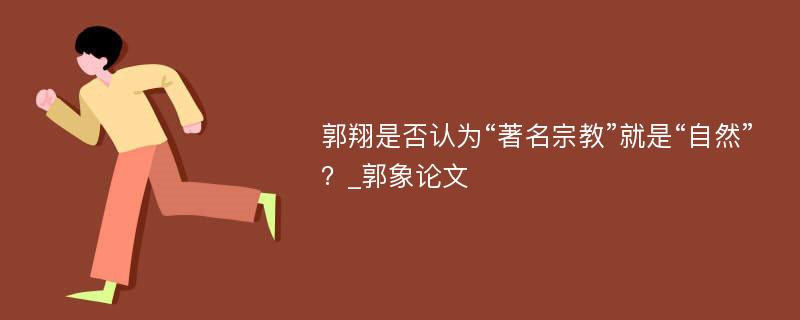
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教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家们所深为关注的问题。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进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前人的基础上,郭象对此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后人以“名教”即“自然”来概括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为任了自然,也就遂了名教,尽了名教规定的义务,亦尽了自然之性,并指斥他以此为腐朽的门阀士族制度辩护。对此,作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名教乃自然之迹
所谓“名教”,就是将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即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其具体内容表现为儒家的仁义礼教、三纲五常等一系列具体的封建道德规范和礼法制度。所谓“自然”,即道家所崇尚的天然、本然、质朴状态和无形无象的本体。而“名教”即“自然”,就是将封建道德礼法与“自然”这一本然状态或世界本体完全等同起来,将遵循、固守封建名教视为顺应本性自然的合理行为。然而,细究郭象的有关论述却难以得出这一结论。
以大道和自然为本是道家学派的基本思想,在这一问题上,郭象继承和发展了老庄和王弼的思想。将“自然”视为根本,而名教乃自然之迹。在《庄子·天道注》中,郭象赞同“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的排列顺序,认为其正确体现了“自然先后之序”,进而还依次阐明了这一先后之序的内在逻辑联系:“自然既明,则物得其道也;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适也;理适而不失其分也;得分而物物之名各当其形也;物各自任,则罪责除也。”(《庄子·天道注》)这说明,郭象不仅以道家自然为本的立场来理解自然与仁义礼法之关系,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他指出,仁义道德乃古圣因时而显的外在行迹:“圣人一也,而有尧、舜、汤、武之异,明斯异者,时世之名耳,未足以名圣人之实也。……虽有矜愁之貌、仁义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在宥注》)这就是说,尧舜等圣人皆抱道守一,全其本性,故其内在的根本主旨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等诸多条件的不同,而需要制订或履行与时相应的道德名教,这才形成了他们各自相异的外在表现和形名。他们的“矜愁之貌、仁义之迹”都不过是朴实之本性因顺时势而表现出来的外在形迹;而且,正由于他们是名实相符的圣人,故虽行仁义之迹,却仍然能保全其“所以迹”的纯朴之本性。这就透露出一个鲜明的观点:道德名教乃是自然本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体现,它们是自然之迹,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本体。
儒家经典是封建道德名教的理论依据和重要内容,它们与“真性”、“自然”之关系如何是必须回答的。对此,郭象通过发挥《庄子》“六经为先王之陈迹”的思想,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况今之人事,则以自然为履,《六经》为迹。”(《天运注》)在他眼里,《六经》并非千古不变的神圣经典,而是“任物之真性者”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行迹,“自然为履,《六经》为迹”。所以,统治者对民众应该采取“任其自化”的政策,而不宜实行强制教育,硬性地向他们灌输儒经:“若播《六经》以说则疏也。”(同上)因为儒家经典只是自然的派生物,拘泥于这些派生物,以此禁锢民众则是本末颠倒的不明智之举。
郭象不仅将俗儒眼中的神圣经典视为前人的行迹,不能体现大道的精粹,而且还认识到拘于陈迹的弊端,他批评那些明于诗书礼乐的儒生只是“能明其迹耳,岂所以迹哉!”(《天下注》)这些俗儒局限于古代文化的外在形式,而不明了其内在本质和精蕴,抱残守缺,这就将禁锢社会文化发展的活力,导致民族思维能力的僵化和文化的停滞。这一认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二、自然高于君命
三纲五常是封建名教的核心内容,而“君为臣纲”又是三纲五常的中心。故讨论“自然”与“名教”之关系时,这也是一个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在郭象的《庄子注》中,“自然”是置于君命之上的。他阐发庄子“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一段话语说:“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岂值(值,相当)君命而已哉!”(《大宗师注》)庄子的原意是说,人们之所甘愿为君主而献身,是由于君主超过自己(“愈乎己”),更何况那支配万物的“道”(真)呢(“而况其真乎”)?而郭象则进一步阐明说,“真”是不依赖于他物,自然而然、不可逃避和抗拒的一种客观必然性,服从自然的支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君命所不可比拟的(“岂值君命而已哉”)。
顺着这一思想理路,郭象阐发了“尽民之性”、反对“专制天下”的主张,认为实现社会管理与保持人性自然的统一,保持君主与“天下”相因相成的和谐关系,这是达到理想政治的必由之路。他说:“指麾顾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为”(《天地注》),“己与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专制天下,则天下塞矣,己岂通哉!”(《在宥注》)这里所凸现的不是封建名教束缚下臣民对于封建君主的绝对服从,而是强调君主不能“专制天下”,在统治和御使民众时不能违逆和压抑其自然之性,而应给予民众“自为”的空间,才能实现“圣治”。这些都清楚地说明,郭象并未将“自然”与“名教”等量齐观,“自然”高于一切的执着主张,促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冲击了封建名教的樊篱。这与那些力图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至高无上性、利用自然天理以论证封建名教之合理性的封建卫道士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指斥郭象维护封建名教时,人们还常常引用他的另一句话,即“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此语取自郭象阐发《庄子·天运》中关于人体百骸六脏之关系的一段论述,在这句话的前后,还有几句关键性的话语,故有必要将此段话完整地引出:“若皆私之(即对体内的百骸六脏不分轻重皆很珍爱),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他以人体脏腑四肢百骸的生理位置和功能与君臣上下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相类比,认为它们各自有着功能上的轻重之别,各有所司,既不可相互替代,人们对它们的呵护和关注也应有轻重之别、上下之分,从而承认君臣上下之分乃天理自然。但同时他又指出,这一天理之自然是以“贤”和“才”为内在根据的:“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是由“贤”和“才”所决定的。这说明,郭象虽然身为门阀士族成员,但却注重德和才的重要性,强调顺应时势、因时而动者则时人贤之,推之为君,才不足以应世者则只能为臣。德、才必当其任,具有“时之所贤”之德方可履君之位,具有为君之才方能承担为君之任,而不能任由私意;只有臣妾之才却不安于臣妾之任,以下冒上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一认识是对道家“物各有宜”、“因才而用”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朴素的社会分工论。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君臣上下的社会等级不是世袭或命定的,不是超自然的异己力量强制规定的,而是社会生活和历史潮流选择和造就的结果。
三、“以一正万,则万不正矣”
将“名教”等同于普遍人性,这是“名教即自然”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郭象却看到,仁义名教并非人的普遍本性。他虽然说过“仁义者,人之性”的话(《天运注》),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段话语及郭象的其他论述作全面考察,则不难发现此语决非论证仁义具有普遍合理性,其关键意义恰恰是强调仁义不是普遍的人性,而是因时代和主体的差异而在某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特性。因为紧接着郭象又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过去则冥,若滞而系于一方则见。见则伪生,伪生而责多矣。”(同上)将仁义这一“有变”、“古今不同”的人性“滞而系于一方”,必然产生道德虚伪等弊端。在《骈拇注》中,他更是系统地论述了仁义道德不能成为普遍行为规范的主张。他说:“多方于仁义者,虽列于五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与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因为人的个性品德是有差异的,如果人为地将曾、史二人品德结构中的仁义特性推广到其他人身上,或者将其视为普遍的人性,则必然产生各种弊端:“夫曾、史性长于仁耳,而性不长者横复慕之,慕之而仁,仁已伪矣。”“学曾、史而行仁者,此矫伪,非实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伤其德也。”“仁义连连,只足以惑物,使丧其真。”“矜仁尚义,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骈拇注》)总之,仁义既非千古不变的普遍规范,也非人人均具的本性,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主体的不同而改变的,将仁义道德作为普遍的道德规范或者以统治者一己之意作为“正天下”的道德标准,都是郭象所反对的。他说:“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各自有正,而不可以此正彼而损益之”,“以一正万,则万不正矣”(同上)。以具有特殊性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强迫众人恪守之,只能适得其反,导致道德虚伪和各种弊端。可见,“自然”与“名教”不能划等号,“自然”的内涵是自然而然,“各自有正”、“各得其正”,而仁义名教则只是“一家之正”,“古今不同”,不是永恒和普遍的法则。
四、名教不足固守
出于以上认识,郭象认为仁义礼法等名教不能固守,亦不足恃。在继承庄子思想的基础上,他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郭象赞同庄子视仁义礼乐为道德衰败、本性扭曲之产物的观点,并阐释《庄子·马蹄》中“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之语说:“凡此皆变朴为华,弃本崇末,于其天素,有残废矣,世虽贵之,非其贵也。”(《马蹄注》)仁义礼乐的产生是“变朴为华,弃本崇末”,是残害自然天性的。故世俗之人所尊奉的仁义礼乐不仅不足贵,而且将导致诸多弊病。
首先,他认为,仁义礼教将导致道德虚伪,徒饰外表:“礼义之弊,有斯饰也。”(《田子方注》)刻意地标榜仁义之迹则是节外生枝,将扰乱等级有序的局面:“令天下之人外饰其性以眩惑众人,恶直丑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据,而崇伪者窃其柄,于是主忧于上,民困于下。”(《在宥注》)因为“仁义有形,固伪形必作。”(《徐无鬼注》)具体的仁义道德规范有外在的形迹可循,若只注重于这些有形有象的仁义礼法,就为那些伪善者追求仁义之名提供了机会。“令饰竞于仁义而雕画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无以为安也。”因此,他反对以孔子倡导的仁义之行作为治国之本和道德典范:“慕仲尼之遐轨,而遂忍性自矫伪以临民,上下相习,遂不自知也。”(《列御寇注》)孔子的仁义之行有其特殊的时空条件,后人若脱离诸多具体的条件盲目效法或树立僵化的标范,必然导致以华伪之迹教民,使民众丧失自然本性而流于矫伪,故不足称道。
其次,郭象认识到,固守具体的礼法制度可能被暴君利用为害民的工具,致使统治者的权力绝对化,成为“据君人之威”以戮杀民众的独夫民贼。他发挥《庄子》中圣法为大盗之具的观点,揭露窃国大盗利用圣法残害民众:“暴乱之君,亦得据君人之威以戮贤人而莫之敢亢者,皆圣法之由也。向无圣法,则桀纣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侧目哉!”(《胠箧注》)
第三,郭象认为,具体的礼法制度皆有其局限性,不区分具体的时空条件而固守礼法,必然生弊。他指出:“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天运注》)顺应时势而制定和运用礼义制度则宜而美,执滞固守则令人生厌,“时移事异,礼亦宜变”,才能“不劳而有功”(同上),只有因顺时代变化和自然人性的道德礼法才是合理的,有实效的。他批评俗儒拘于名教礼法这些“先王之陈迹”而损害大道:“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外物注》)效法和固守古圣之陈迹是不足安天下、守天下的:“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所以守国而为人守之也。”(同上)执守圣人之陈迹而不知变,必然难以适应变化的时势,遂使国家为他人所有。这就得出了名教礼法不能固守的结论,也为后人因顺时代和人性,不断改革、更新现有的礼法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料和理论依据。
五、“天性所受,各有本分”
人既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又处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如何解决社会伦理法度与自然人性的关系?如何协调社会角色和自然人性的矛盾?特别是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这是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实质问题。郭象既克服了崇有派以抽象名教的合理性论证现实名教合理性的屈从和保守,又超越了贵无派以现实名教的不合理性,全盘否定名教之价值的偏激,而试图建立既不脱离社会现实而又顺应时代变化且合乎人性自然的道德礼法。
郭象虽然承认天地之间存在着“尊卑先后之序”,但我们认为,不能以此作为郭象肯定封建名教的论据。因为郭象此语只是对《庄子》思想的发挥,此后的成玄英亦有这一思想。郭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实施九品中正制的时代,否定了由出身门第决定尊卑之序的社会格局,在他看来,“尊卑先后之序”是建立在众生各自不同的自然本性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世袭或靠强制手段而获取的:“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他这种将人的自然禀赋差异固定化的看法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联系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则此论亦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当时实行的由门第高下决定尊卑贵贱的九品中正制度,是扼杀人才、压制进取精神的腐朽制度,而郭象以自然天性为尊卑等级的内在根据,则是试图根据自然禀赋的高下来确定社会地位,其合理性无疑超出以出身门第决定贵贱的现实社会制度。
因此,对于个体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符合和遂顺主体之真性的生活:“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齐物论注》)在他看来,世俗的尊卑贵贱并不足介怀,只要遂其“真性”,即使处于社会下层,亦可“自安其业”,自得其乐,而不须顾及世俗的毁誉评说。而作为统治者来说,能否因顺民众之本性而治之,这是社会达到整体和谐的关键:“因其性而任之则治,反其性而凌之则乱。”(《在宥注》)“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而天下无患矣。”(《在宥注》)作为管理者应当努力创造一个“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的环境,而作为被管理者则应当安守其位,不作非分之想,即不能“志过其分”。从外表上看,郭象这种任性自足的主张与遵循名教皆体现出对某种秩序的追求,这可能是人们将“名教”即“自然”的命题加在郭象身上的又一原因。但我们认为,二者在实质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封建名教秩序是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强加给个人的,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压抑和无可奈何的服从;而任性自足则是强调以自然本性为基础的自适,自用,自足的主体精神,力图缓解外在异己文化的压抑,追求顺应本性,安其性命之情。
郭象以上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万物独化于玄冥”(《齐物论注》)的本体论。他否定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认为万物不是“天”这一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主宰的产物,是不待外物而独化于玄之又玄、浑然无别的绝对的至无。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变化,都是无原因、无目的、无条件,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万物皆造于自尔”(《达生注》),“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齐物论注》),“无待”于任何力量的主宰。由此出发,他认为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力量,才能够“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惧得,泯然无迹。”
注重从内部寻求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突出主体自身的力量,这在封建社会中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思想。按照封建专制主义的逻辑,民众是必须依赖于君主的,君主是民众的救星,而处在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也盼望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从上面给他们施以阳光雨露。然而,郭象却由道家无为而治的原则出发,否定了民众对于封建专制君主的依赖性,强调“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尔,而莫知恃赖于明王”(《应帝王注》);肯定了万物的主体性,主张“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认为圣王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其有能力治天下,而在于他能够因顺民众之本性,任物之自为:“故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在宥注》)无为政治的核心就是让“万物各得自为”,他说:“无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万物各得自为。”(《天下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郭象的这种“各反所宗,而不待乎外”的思想有利于引导人们崇尚自我的主观努力,发现和肯定自我价值,从而有利于缓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自然的摧残。
六、“捐迹反一”的理想
郭象对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思考,乃是为了免蹈西晋统治者毁裂名教而又以名教禁锢天下、以名教杀人的弊政,试图弥合自然与名教的分裂和尖锐对立,重建合于时代要求和自然人性的道德礼法。在以上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郭象提出了“捐迹反一”的主张。
他认为,顺乎自然而行的举措是无外在行迹可循的。鸟行而无彰迹,因为其“率性而动,无常迹”(《天地注》)。而着意地循求外在之迹,则必然失其本然。他强调,作为圣人的黄帝并非刻意为仁义而行仁义:“夫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则后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撄也。”(《在宥注》)黄帝的仁义之举只是他与天下之民亲和冥合而自然显现出来的,如果缺乏与物冥合的真情,而单纯追求外在的仁义之迹,则反而扰乱天下。因此:“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万理皆当者,非为义也,而义功见焉;故当而无伤者,非仁义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驰,弃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扰世不由于恶而恒由仁义,则仁义者,扰天下之具也。”(《骈拇注》)自然无为则与物无伤,万理皆当,这并非为仁义而仁义,却自然显现出仁义的行为和效果。这才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为求仁义之名而奔走争斗,丧失自我本性,则反而扰乱天下,走向了仁义的反面。
他强调,礼义精意决不在于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必须由外在的规范培养出内在的道德情感:“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如果“矜乎名声,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大宗师注》)
通过发挥《庄子》中仁义残害天下的思想,郭象激烈地抨击了逐迹背本的时弊:“由腐儒守迹”,故导致了“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的惨祸。他们“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复攘臂用迹治迹,可谓无愧而不知耻之甚也。”(《在宥注》)他指出,不追求反本还原,专事效法外在形迹,“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其结果只会是“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谬矣。”(《缮性注》)这些充满愤懑的语调,鲜明地表达了郭象对于封建名教伤性害民这一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于“捐迹反一”、“返朴归真”社会理想的殷切期望。
* * *
我们认为,“名教乃自然之迹”或“捐迹反一”的命题较之“名教即自然”更能确切地反映出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郭象的“捐迹反一”,反映出玄学家对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认识的深化。其意义在于:①澄清了“名教”与“自然”是“迹”与“所以迹”(“本”)的关系;②从理论上指明了封建名教的局限性;③认识到封建礼法制度对于人性自然的束缚,试图调和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达到礼义忠信与自然本性的统一;④将道家的哲学本体——“道”、“自然”发展为具有绝对性意味的道德本体。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儒家伦理缺乏本体力量、无法形成超验的形而上学品格之不足,为中国伦理思想在理论上增添了极为有意义的活水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