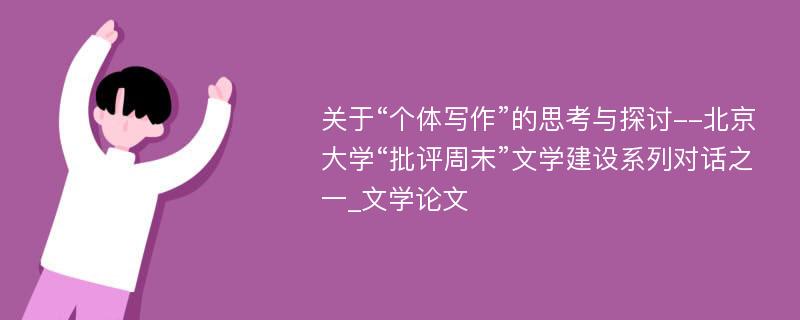
对“个人写作”的思考与讨论——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学建设系列对话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批评家论文,周末论文,系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人的文学和集体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人的觉醒有关。胡适进新文学革命的两项内容,一是“活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语言工具的革新,是建设和到达“人的文学”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乃是通过人的发现以建设人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前夜,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号发表振聋发聩的大文:《人的文学》。这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的文章指出,新的文学“须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他把这种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可见,新文学在它的发轫期就有很高的境界,即确认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个人,文学的灵感以及创造的全过程与个人性的感悟与劳作有关。文学当然要作用于社会和大众,但文学是生发于个人、并经由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社会和大众的。但是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却在新文学的发展途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左翼思潮,几乎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定位于集体。这种定位导致前述那种文学的个人创造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严重的贬损和否定。
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的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当今的中国作家已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世界和他人以及对自身的看法,而不受或很少受到干涉。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人终于在文学中得到突现。社会的开放和商潮的勃兴给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这种形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
但当前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使文学大幅度地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众承担。在一些作家(并非少数)那里,文学已沦为梦呓般的私语和自我抚摩,这些作家在自恋自慰的陶醉中把自己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加以隔绝。作家的这些追求要是鉴于以往“集体写作”的教训而清高自处,那也无可厚非。而事实却是,这些作家(不是所有)却几乎是无保留地以这样的“个人化”取悦于商业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对身边、窗外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丧失”保持警惕自有道理,但他们对现今的秩序却失去了警惕——这原是欲望和复制的时代!欲望使个人无限地膨胀,而复制则最后地消弭了“个人”。
显然,文学不能只关心自己。杰出的和优秀的文学总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社会。
个人写作:有价值的悖论
“个人写作”是九十年代最蛊惑人最让文学界受用的一种“姿态”,在主流之外,它几乎成了对各自的立场有着不同表述的作家们的共识,只有个别诗人(例如于坚)明确表示过拒斥。几十年来,由于“公有制”社会型态所决定,国家话语对“个人”是限制性的,提倡的是非个人的宏大叙事。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中,历来极少有“个人”甚至排斥“个人”。“个人写作”的提出,因而首先具有文学之外的价值和意义。
但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个人写作”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对抗,它同时也“暗合”了国家话语的某种变化。个人化写作时期到来的必然性,和国家把经济命脉的自主权逐步还给个人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经济领域,“个人”愈来愈合法化,写作者在体制外生存变成为可能,个人具体的生活方式蜕变和大背景转型,自然而导致“断裂”,摆脱了意识形态制约下宏大叙事的因袭。
复印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我觉得是两件最具象征意味的事物。前者表明商业化信息社会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而后者则体现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个人写作”是艺术家在此双重压力之下,以个性跟共性、自由对法则或许是堂吉诃德式的反抗,同时,写作者强调以“个人”身份出场,也是对“朦胧诗”、“第三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种种集体反叛姿态的反叛与调适。
而在女作家那里,情况又有所不同。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私小说”与其仅仅视为张扬“个人”,不如看作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了她们对个人空间的迷醉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自恋。她们锲而不舍地对小房间、浴缸的反复摹写,坦露了呈现幽闭的阴郁隐秘的个人经历的渴望。更年轻的一代则把叛逆理解为“酷”,她们自我感觉良好,敞开身体,并不拒绝男性的欣赏目光。她们崇尚个性,不爱听父母唠叨,也无年长一辈(红卫兵、知青)的集体经验,既无法也不愿意进行历史叙事,便关上房门写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以上种种“个人写作”的问题在于,当“个人写作”成了大家的共同追求,成为潮流,它其实已经异化为另一种集体写作行为,陷入“悖论”的怪圈。而寻找个人经验与时代语境相融入的可能,使“个人”与“公共空间”两个大小同心圆有相切点,对当下的写作尤为迫切。
对于“个人化”写作的具体文本阅读,看法并不统一。如有人认为或侧重于对压抑禁忌的个体、私人记忆的释放。也有人把解读重点放置于文本中人物的精神和肉体成长过程,而非仅存身体话语,相当一部分人持女性主义的阅读批评视角,还有人似乎更重视女作家的女知识分子双重叙事身份,这些批评视角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批评网络。
“私人化”写作为什么会出现在90年代,它与80年代的“女性文学”有何不同?更多的人认为是社会转型使男性精美文化撤离中心,使“无母无父”的女性写作在90年代获得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和与自己建立新的“历史档案”的可能。使80年代的“无性”或“中性”的女性文学从对自身世界的冷漠和逃避到90年代对“自足性很强”的女性的话语空间的涉足和“自我指涉”欲望世界的析筑。我认为是国内外的政治、历史、经济的变迁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文学界自身的变迁及外国文学的涌入,如西方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使得“双重边缘”得以产生,即个体话语相对于宏大的集体话语,女性话语相对于男性中心话语。而“私人化”写作正是在双重边缘的呈现。
一方面。“个人化”这个概念相当于“独特性”、“个性特征”、“个人风格特征”。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而它的价值、作家的价值在于“独特性”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权威的“知识”,对这个的文学“本质化”的“知识”和说法当然可以进行历史的研究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它会牵涉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西方文学中“独特性”的强调应该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因此,我们要警惕的是某种本质化的看法。
与上述看法相反,是理论上不可能存在一种“个人化”的写作,这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理论背景有关,和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有关。当然,我们不是在理论上来谈论问题,但不是说这些理论认识对我们的讨论就没有帮助,我觉得这种帮助是方法意义上的,可以作为我们具体讨论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在90年代的语境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把它作为指向真理或谬误的普遍性问题来讨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与90年代语境有密切关联的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来提出。
在我看来,个人化写作所表现出的可能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时代,或者说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才会显著地呈现出来。
参照角度:诗人的写作姿态
文学是一种天才的而不是匠人的事业。天才产生另类,或者说与众不同。这是作家安身立命的东西。九十年代发生在我们身边所有事物,其意义都不在开始,而是结束。“个人化写作”也是结束,结束伪写作的姿态和英雄主义的集体意识。所以“个人化问题”实际上是对现时文学情景与场所的一次大清理,让那些拒绝真实的个人经验写作退场,新感觉和新体验以现时的当下的在场姿态从不同的体式、视觉和特色全面进入文学。这是与时代的“私人”与“个体”相称的平民自我意识的复苏。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开始,而是结束。可以用一句这样的话加以概括:“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时代离“我”远去。所以现时文学不是“先知”的启示录,而是个体生命在迷乱时刻的梦游,找到的是文学的种种新的可能,也许不得真相,但它新鲜热辣。我认为这就是文学,本真意义上的中国九十年代文学。彭玉娟
九十年代诗坛可谓招牌林立,异彩纷呈,然我们在其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为标新而造新的矫情。诗歌那种激荡心灵让泪光闪烁的苦痛不见了,抚摸创痕让孤独栖息的温婉不见了,阅读的明亮与流畅不见了,使诗飞扬也使读者飞扬的韵律不见了。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一种辞不达意的烦燥与痛苦,一种没有在语言之路上与圣者相遇的晦涩与不安。由此,我们想起海德格尔的话:让语言说,让语言自身来说。
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似乎更愿意让“我”来说。个人化写作欲以个人的方式对诗歌的生存和死亡有所承担,并通过写作的方式来拯救自己。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肩头掮得起黑暗的闸门吗?不错,铁肩担道义。然这种担当用以支撑的是与天地同仁同德的自负与血气,天长日久,难免困乏与空虚。当我们灵魂里都还晦灭不明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透彻思想照亮别人呢?抛开诸多别的因素不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质疑:读者对九十年代诗歌的拒绝与背弃是否与诗人写作的姿态有关?是否正是那种救世的傲慢与创世的自负使我们与读者隔离?自《黍离》、杜甫以来对国家民族的忧思愤嫉,这正是今天个人化写作欲以消解的话语,而新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拒绝母亲的乳汁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与此同时,又仅仅是近现代的西方进入我们视野,各种主义和方法纷至沓来,而其身后——更大的背景——《圣经》传统——却未被我们透视,西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用以关注和批判当下的最高尺度——至真至善的终极价值——尚未进入我们的视界。
诗人的姿态中是否应该有一种向圣者敞开的顺服与谦卑,与那在十字架上受难和牺牲的悲悯者照面,在破碎自我的碎片中返照出自己真正的个性,而让个性自己欢唱出来。
是否,这才是真正的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转型的九十年代,人们更注重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精神的追求及生活的质量。因而,创作的个人化现象是必然的。但个人化又是局限性的,而社会化与现实化也是相对的过程,在个人化经验的发掘中,应强化历史意识,要有超越性的内在精神,这样才能较长地生存与被接受。
新的期待:重建公共理解的空间
90年代历史语境下诗歌中出现的个人化写作,使诗歌创作返回诗歌创作本质。告别了过去以“公共话语”为基础的集体写作。诗人以个人名义承担时代给予他(她)在此生活的细节和责任。个人化写作是对艺术独立性、独创性的维护,诗人的写作空间与读者的视界拓宽了,有了更多自由写作的天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文学完全是个人的”(马拉美),诗歌更是如此。诗人能够在众声喧哗中走向内心,以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经验和历史生存,潜心诗思于内心真实中开出被遮蔽的诗性之花。以个人视点切入历史,让诗歌回到诗本位,敞开一切遮蔽,这是一种伟大的可喜的进步。
我是非常赞同谢冕先生意见的。我认为个人话语对公共话语是一种疏离,一种对流行大众精神、主流意识的疏离与拒斥,消解了主流艺术的板结化。但极端个人化写作也是危险的,危险在于受方彻底脱离,割裂。过分拘于小圈子身体感情的封闭的个体写作经验:独白、私语、身体抚摸。完全排除受众的反映,导致公共表达空间的彻底缺失。这是整个90年代文化语境面临的某些困窘与尴尬,这是文学上一种自绝行为,失却与社会、历史交流功能。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曙光,诗歌不能变成孤悬空中封闭的圆球。个人化写作有待重整新的公共理解空间。
“个人化写作”的提法最先出自于女性书写,狭义范围内指性别意义上的个人写作,女性写作、私小说。这一类写作以女性生存为母题,彰显女性意识,对现有的男性叙述和话语秩序进行颠覆。“个人化”命题之所以能籍女性写作得到诠释,其共通处在于无论个人写作还是女性写作都在写作主体上有着被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所排拒的、边缘化的、弱势的实体的存在,这一实体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任何微弱的然而坚实的声音,都被另一种激越的、更具合法性的权力的同声合唱所淹没。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学反思运动消解了个人和历史,个体语言和标准划分的公共话话的界线,提供了众声喧哗的语言环境,也提供了个人化写作的契机。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进程当中,个人化生存和写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商业的渗透及至无所不在使人面临无可回避的生存压力,当这些因素介入到作家的精神情绪和写作状况的时候,一方面作家的处境可以形成新的生命体验,作为素材进入写作;另一方面又使人愈发得困惑:当我们面对批量生产、流水线操作的机械复制时代,写作以及其他的文化创造在多大意义上还能保有个人化特征,经验在什么程度上不会被重复,纯粹个人的精神和生命的空间能否依旧?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90年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变革,致使个人最深刻的变化,是自我认同,即身份的危机。普遍交换和它所强化的竞争机制,不仅把个人从集体统一性中剥离下来,而且使个人先天地失去了稳定感。稳定感的丧失,对于市场化中的个人,既意味着它变成了一个根本性的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又意味着它自身的内在统一性缺少基本保障,而时时面临着在普遍交换中被割裂和消解。自然,后一种危机是更根本、更严重的。如果说,8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努力达成的是对自我精神独立的确认,即寻求“我是谁”的解答,那么90年代文学后现代品格则表现在对个人身份崩裂之后的顾此失彼的自我退守。在80年代,时间是自我的希望,它向未来的不断延伸。对自我至少意味着可能;在90年代,时间变成了无处不在的诱惑,它不属于个人,却左右了个人的一切欲望。90年代是属于个人的时代,但在个人的时代个人却是以丧失身份的无名的方式存在的:90年代的文学是个人化的写作,但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主体却是自我分裂的个人。倘若不是着意美化和自欺,90年代文学应当追问和辨析的是:究竟什么是属于个人自身的?在这里,我们认识到90年AI写作作中文学视点阈限的强逼性退缩,即不断把视野压缩到个人自身,至多是非常有限的伸手可及的周围。
结束或开始:现象的悬置与梳理
从文学的一些基本范畴来看,任何一种写作都处于文类的传统、阅读的规范、时代的风尚与作家个体独创性的复杂的辩证关系之中,因而如果不考虑一种提法、一个现象的具体语境,以纯批评的眼光从脱离具体针对性的角度考察“个人化写作”,会很容易从两方面发现它站不住脚:个人性质的写作并非九十年代所独有,或者,被指认为“个人化写作”的许多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类同性。但如果我们从某种类似“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从对文学现象的悬置和梳理入手,辨析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领域内的特殊策略如何构造或曰制造出了“个人化写作”,我们就会不仅仅满足于对这一概念做简单的价值评判,而会更多地关注这一概念背后的“构型因素”,并从中“考掘”出更大的问题。
在辨析“个人化写作”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概念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各文类,作家群落之间“个人化”形成了很多裂缝和差异性,有些研究者试图从“人道主义话语”的流变、“主体性”的盛衰演化来整合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其有效性值得怀疑。事实上,单是这一概念之中的“个人”一词各类作家和批评家对它的阐述都不一样。在诗歌中,“个人写作”的提倡者们着重引发“个人”一词中的“个体理性”意味,它直接针对八十年代的集体对抗或集体狂欢写作。在先锋小说中“个人”更多地指涉了世俗的个人身体经验,以此与以往实验小说中浓重的技巧至上气息相区别。女性小说的“个人”则侧重于文化性别政治的个体实践,矫正前代女作家个人性别反思的淡漠。而一些批评家对“个人”的理解却往往着眼于市场社会之中的自由的经济学个体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洞察这些差异可能正是理解“个人化写作”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会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关键所在。
按照上一次的报告和我读的一些文章看来,所谓“90年代个人写作”好像是承80年代对自我发现的继续深化扩展,就是说先从社会的、或者说政治的控制摆脱,接着从所有的正统文学的规范中解放,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比如说在诗歌方面,80年代初期,朦胧诗打破了当代诗歌的规范,表现了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按着80年代中期崛起的实验诗歌活动,把它扩展为一种追求语言、与人的独特感受和精神境界的写作。
不过,在90年代,实验诗已经没像80年代那样给读者带来现多冲击,我觉得在诗坛出现了试图克服实验语言表象化的活动,就是说引发了世纪之交的“民间口语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前者继续追求语言本身的力量和纯度,后者不但依靠像前者那样注重产生“纯诗”的灵感,也重视“知识”,试图补上和克服“诗的语言”的危机。
这么想,90年代诗歌个人写作“个人化”这个概念,已经超于它本来具有的“独特性”、“个人特征”等等意义,包含着90年代一方面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从规范超脱,一方面寻找新的规范控制的这种文学现象。
另外,先锋小说也好,女性写作也好,虽然前者力图打破语言规范和有逻辑性的故事构成,后者把前者扩展为性别,就是说从男性和象征着男性的权力话语中摆脱,但并没有完全发展为无秩序的阶段,使人感到好像仍然有某种规范控制它们。
90年代,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进步,在对政治的关心越来越稀薄的过程之中,创作者和读者更关心个人的生活、精神活动,其结果迎接了“多元化”的时代,在这种现象中也许最适于产生“个人化”这个词。不过,如上所述,“个人化写作”这个词好像已经不能限于这个范围,越来越扩展,成为很含糊的概念。
“个人化”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在九十年代的小说界如先锋小说、女性小说,及诗歌、散文领域都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提法,从而形成一种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总的来看,它是在“话语转型”的过程中,针对以“社会化”、“群体化”、“主流化”的文学描叙前提而言的,它试图有意与“公众话语”、“巨型话语”拉开距离,强调写作主体独特感受和人生经验的重要性,以及文本自身的独立意义。因此,这种在特定时期寻求个人位置和视角的写作方式,同时暗含着写作者对文学的认知态度及价值取向。
从具体文本来看,所谓“个人写作”的作品只是初步探索,并且良莠不齐,但在总体上它可能会给文学发展带来一些影响,如:一、作家的审美表达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能够较集中地展示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二、加深对人丰富复杂性的呈现深度,拓展对其时空背景的对照视野:三、进一步促使写作倾向的主观化和文学风貌的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化”与“共众性”、私人空间与公众空间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微妙的相交关系,时代的、社会的影响对个人始终都有一种制约或渗透的作用,并且从文学表达上来说它也需要民族历史的非个人的思考的一面,当下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梳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提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文本上引发的,这种强调个体生命独特感受方式的写作,具有一种本真的意义,警惕简单地纳入社会观和道德观的批评范畴。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提出“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各自观点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包括着中国百年新文学传统“人的文学”这一位置的某种恢复,表明了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另一层面功能的逐步显现,可以说它本无多少新奇之处,如同对一个曾经缺席的姗姗来迟者的重申,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理性命题;也许随着语境的变化,它可能将失去其特定含义,或者窄化为一种更具体的写作形式,如“私人写作”,或者泛化为多元文学格局中的一类普遍现象,如与“官方写作”、“大众写作”相对应。但无论如何,文学对人,及其独特的经验和超验世界所能达到的深度探索,将永远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