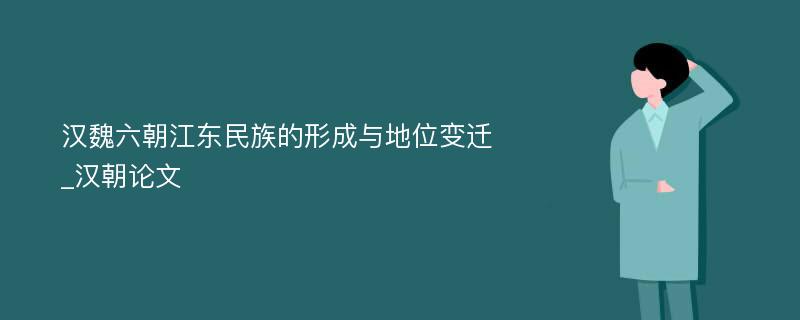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大族论文,时期论文,地位论文,江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4-0059-08
在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古代社会里,学术文化总是由少数上层贵族人物所垄断,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通常的现象。就中国古代上古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而言,主要是“学在王官”,春秋战国以降,特别是汉代以来,平民教育虽在不断发展,但不可能像今天所谓的“普及教育”或“义务教育”那样,这是不难理会的。自汉代以来,各地区的豪强大族逐渐开始在文化上接受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并且在汉代重视“家法”、“师法”的经学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道德文化相维系的世代相沿的“家学”,以保证世家大族的长盛不衰。这一情况在两汉时期已经形成,特别在东汉时期,世族及其文化已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以降,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坍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与垄断遭到进一步的削弱,特别是异族的内进,南北各地的割据与分裂,使得各地区的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条件。从当时的历史事实看,各地域的学术文化主要存续于各地的世家大族中,南北朝的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古世族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此,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有明示,并且一再申述,他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指出:
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陈先生指出: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星散于全国各地的世家大族,往往成为区域性的文化重镇,六朝统治的江南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有鉴于此,本文借助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地区世家大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略加考论,以作为深入研究江东世族文化的基础。
一、秦汉之际的江南土著“豪杰”及其文士代表
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土族”的产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同步。江南地区自三代以降,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与中原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吴、越诸国的著名士人大多来自外域,如伍子胥、孙武、范蠡等皆如此,江东才俊之士尚很匮乏,更无论什么名门大族了。直到秦汉之际,情况仍没有根本改观。《史记·项羽本纪》的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羽本临淮下相人,楚国旧将子孙,后因叔父梁杀人而“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由此可作如下推论: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已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力量有限,还没有出现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足以号召乡邦的名门与名士,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江南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说明江南地区在整体上仍很落后,社会分化尚不明显。
当然,仔细考察当时江南的文化发展史,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江南土著士人的活动,特别是西汉统一后,一些南士入仕朝廷,这隐隐约约地表露出江南地区的土著“豪杰”在文化积累上的历史印迹。较早以文化显名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在西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皆以文辩著名”(《汉书·邹阳传》)。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严助,《汉书》卷64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汉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汉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颜师古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教育机制。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个宗族还存在,直到西晋时,人们谈起江东“旧家”,仍列有吴地严氏,(《世说新语·赏誉》)但数百年间并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人物。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恐与其宗族文化特质有关。严助为“友婿富人所辱”,说明这个宗族尚未确立有效的宗法伦理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崇尚文辞,这也是当时南方的地域文化特征,但随着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与严助同时显名汉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64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从上可见,朱买臣的“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看不到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此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尽管有一种说法说东吴时期崛起的吴“四姓”之一的朱氏与朱买臣有关,但这一朱氏以“武”显,并非文化士族,且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确实的世系传承的依据。由上文考证可知,在秦、西汉前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总体上仍比较落后,社会发展尚不充分,还没有大量的培育豪强大族的条件,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豪杰”。降及西汉,在这些地方宗族中出现了几个以辞赋显名的文士,但并没有形成可以世代承传的家族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世家大族了。
二、两汉时期北方人士的南徙与江东儒学世族的形成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地方豪杰势力的日益壮大及北方学术文化风尚的南被,一些宗族正逐步向儒学世族转变,当然,这一成长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与此同时,不断有北方人士南徙,有的还是规模较大的家族式南迁,他们在儒学修养及宗族教育等方面,似乎比当地豪杰要优越一些,也更重视一些。因此,这些南徙大族在江东定居后,在宗族的繁衍、财富的积蓄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原来当地的豪杰。在汉魏之际兴起的所谓江南大姓,若追根溯源,主要是汉代南迁的移民。
见于正史的这类移民宗族,较早的一例是汉武帝时期南徙的会稽郑氏。《汉书》卷70《郑吉传》载吉为会稽山阴人,宣帝时期为西域都护。又据《后汉书》卷33《郑弘传》,吉为弘从祖。同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郑弘在东汉明、章时期颇有声名,历任尚书令、侍中、太尉等,这与其祖辈任武职大有不同,这表明郑氏入籍会稽仅三代,已完成了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又据《后汉书·王充传》及《论衡·自纪篇》,王充家族本魏郡元城人,祖辈“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后又因以武犯人,徙至上虞。这说明王充先世是因封侯入籍会稽的,家本崇武,到东汉前期王充时才转而尚文,入洛游学。
两汉之际,中原一度大乱,南迁北人之数量与质量都大有提高。从正史记载看,有些避难之士后来留居江东。《晋书·儒林·范平传》,范平,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至范平时,“研览坟素,遍该百氏”,成为著名的经师,并仕于东吴。又据《元和姓纂》卷5,叙丘氏时列扶风一望, “汉平帝时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属王莽篡位,后俊遂于江左居吴兴”。这说明吴兴丘氏是避王莽祸而居江东的。吴兴沈氏是显赫东晋南朝的江东“武力强宗”之一,据沈约《宋书·自纪篇》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沈氏先祖靖,西汉末为济阴太守,避新莽之祸而“隐居桐柏山”,其子戎徙居会稽之乌程。不过,沈氏一直崇尚武力,直到南朝后期沈约的时代才转为“文化世族”。及至东汉,由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迁徙江东的北士数量更多,其中尤以因任职、封侯南迁者为重要。如《后汉书》卷38《杨璇传》,璇,会稽乌伤人,“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当然,由于其他原因迁移的例证也不乏记述。至于东汉后期避祸南徙的北方人士,这已逸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赘。
由以上考述可见,在正史资料中确实可以描绘出一条自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北方人士南徙的清晰线索。从各族的发展过程看,大多是先世以武力显,后世转而尚文,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当然,进入正史记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南徙北人中最有代表性或发展最充分的家族。其实,有些南徙北人虽然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显名一时的人物,但在家族势力的积累,特别是在儒学文化的教养诸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及至东汉中晚之世,这一类儒学世族生机勃发,成为江东地域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人们熟知的所谓吴“四姓”——顾、陆、朱、张,会稽“四姓”——虞、贺、孔、魏等也大多如此。如会稽虞氏,《元和姓纂》卷2“虞氏条”曰:“秦有虞香。 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虞翻显名东汉之末,仕于吴,为虞香二十世孙,虞意为翻六世祖,以此推断,虞氏当在东汉中前期迁入会稽余姚。又据《三国志》卷57《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翻上《周易注奏》,虞氏在江东很快转化为儒学世族: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会稽贺氏也如此。《晋书》卷68《贺循传》:
贺循……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庆氏是如何迁入江东的呢?《元和姓纂》卷9 “贺氏条”曰:“齐公族庆父之后庆克生庆封,以罪奔吴,汉末徙居山阴。后汉庆仪为汝阴令。……(仪)曾孙纯,避汉安帝父讳,始改贺氏。”由此可见,贺氏当在西汉末迁入吴,东汉中后期再迁入会稽,世代以礼学相承。虞、贺二氏是会稽郡最显赫之儒学世族,有一定的代表性。
吴地最显赫之家族当属陆氏。关于陆氏的来源,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战国时齐国大夫陆发有二子:万、皋,“皋生邕,邕生汉太中大夫贾。万生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这是说吴地陆氏与西汉初名臣陆贾同族。另据《元和姓纂》卷10“陆氏条”,则称“汉太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史记》、《汉书》陆贾本传皆载贾为“楚人”。战国末江东一带曾为楚国辖地,故疑贾即为吴地人。若依此推论,陆氏当在西汉以前已迁入江东,故陆氏宗族根基深厚,至东汉时已称为“世为族姓”(《后汉书·陆续传》)、“世江东大族”(《三国志·陆逊传》)。
朱氏,据《元和姓纂》卷2“朱氏条”述吴地朱氏来源说, “汉功臣有都昌侯朱轸,轸至买臣,会稽太守”。这是说吴地朱氏是在汉初因功受封而来。又据《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6 “朱姓部”引《苏州府志·氏族谱》所载:“朱氏大盛有九族,吴郡居其一。郡之穹窿山有朱氏墓碣,字已漫灭,其可读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二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会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于吴。’此唐时子孙追述其先过江岁月也。”方北辰先生考证,由于此碑“字已漫灭”,因而误释。实际上所谓“平始三年”,当为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元年”,由唐武宗会昌壬戌回推842年,正好是汉平帝元始元年, 这说明“朱氏由下邳移居吴郡是在西汉末”[1]。由上述, 吴地朱氏南徙时间有二说:一是西汉初,一是西汉末。
张氏,按《宋书》卷53《张茂度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这说明吴地张氏乃张良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张)良字子房,汉留文成侯。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马金。金生阳陵公乘千秋,字历雅。千秋生嵩。嵩五子:壮、赞、彭、睦、述。……吴郡张氏本出于嵩第四子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又《文士传》载:“留侯七世孙张赞,字子卿,初居吴县相人里。时人谚曰:‘相里张,多贤良,积善应,子孙昌。’”(《太平御览·人事部》一三七“谚”条引)这三处记载都肯定吴郡张氏乃张良七世孙迁移而来。至于七世孙是张睦,还是张缵,记述不一。程章灿先生按文献学的标准,以为《文士传》最早,《宋书》次之,而《新唐书》最晚,故推论张缵为长沙太守,始迁吴,[2](p.90)时间当在东汉前期。
吴“四姓”中,只有顾氏为汉代以前定居江东的土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士传》:“(顾)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顾氏出自己姓。顾伯,夏、商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初居会稽。”这说明顾氏自见诸史籍以来便已著籍江东了。
通过以上对会稽、吴郡二地具有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来源的考证,他们大多是在东汉中期以前由北方迁入江南的。就吴“四姓”而言,正如台湾学者何启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可以知道顾氏以外的其他三姓,不是南方的土著,而是外来的。陆氏、朱氏在汉初,张氏在东京,从北方迁于吴郡,从此遂为吴郡人。”[3]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与东汉末特别是东晋以后大量迁徙江南的北方大族相比,陆、张、虞、贺等江东大族也是移民,只是早来了数百年而已。不过,由于这些家族在中古历史开始时,即东汉中期以前皆已著籍江东,故被称之为江东土著,以区别于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姓士族。在古代社会,士人往往是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世家大族的南移必然会带来儒学文化的南播。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繁衍过程中,这些宗族人口不断增长,普遍建立起庞大的田园,并且形成了乡里宗法组织,进而建立起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族普遍重视宗族内的儒学教育,从而用儒家伦理来规范宗族子弟的言行,这使得这些世族子弟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某些优良的道德行为,久而久之,在这些大族内就形成了一定的“家风”和“家学”,以维持这些大族的地位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坠。以往人们谈论中古大族,对其政治、经济特权比较重视,而对世族文化风尚在大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似乎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实际上,在地方仅有经济与武装实力者,只能是“豪杰”,如果他们不能崇尚文化,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所谓“世族”,也不能得到封建王朝在仕进方面的优遇,因为汉代是以“通经致仕”为正途的。也可以说,汉代这种取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方大族崇尚儒学。反过来,这些通晓经术的大族子弟,必然得到入仕的优遇,“出仕州郡”,前举会稽虞氏、贺氏、吴郡陆氏等,皆是江东地区“通经致仕”的代表。正由于此,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冠族”、“族姓”。因此,所谓“冠族”、“衣冠”、“族姓”,其核心不仅仅在于其官宦和世代承袭,也不仅在其宗族庞大,而主要在于维系其宗族长盛不衰与提高其宗族社会地位的家风与家学。对于东汉江南地方文化世族的出现,唐长孺先生早有明示:“江南地区从东汉以来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虽然较之中原还相对落后。同中原一样,各郡都有大姓强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东汉二百年来培养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名士,这些名士多半是由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姓中产生的。会稽虞氏自零陵太守光至玄孙翻五世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学。有名的党人名士,被列为八俊之一的魏朗是会稽人。吴郡陆氏是‘世江东大族’,自东汉陆闳至汉末陆康,有好几个名士、达官。吴郡顾氏,顺帝时顾奉官至颍川太守,是个名士。也有许多先世名位不见史传,但可以肯定是大姓的,如吴郡之朱、张、钱唐全氏、阳羡周氏、丹阳朱氏等,即使远郡桂阳也有谷朗那样的‘衣冠子弟’”[4]。
确实,全面考察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情况,他们在仕宦、文化业绩诸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先辈,不少人名闻遐迩,声震中原。而追究其出身,则大多来自那些“通经致仕”、“世仕州郡”的文化士族。这与汉代州郡大姓垄断地方选举的制度与风尚有关。[5]
三、东吴时期江东大族的全面得势及其门阀化
东吴时期是江东大族发展的黄金时期。汉末政衰,王纲解纽,天下分裂。孙氏父子据有江东,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关于孙吴政权之性质,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挠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6]就东吴历史的一般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但若就孙氏兄弟与江东土著大族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有一个由对立到结合的复杂的变化过程。孙策立国江东及孙权继立之初,他们与江东土著儒学世族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他们依靠淮泗军、政势力的支持,对江东大族采取了野蛮的诛杀政策,旧史上所谓“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三国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傅子》),说的都是这件事。对此,田余庆先生已有精湛的考证,可以看到当时江东盛氏、周氏等不少名门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虞氏、魏氏、陆氏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7]追究江东大族与孙氏兄弟间冲突的根源,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关键在于双方阶级观念与文化意识的差别。这一局面直到孙权亲政后才逐渐调整、改善,既往的“诛其英豪”的政策得到改变。此后,孙吴政权虽然实现了所谓的“江东化”,军、政大权主要归属江东大族人物控辖,但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
不过,从双方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来看,其间的关系当然还是以合作为主的。从孙权来说,他要稳定在江东的统治,必须要寻求陆氏、顾氏等江东大姓人物的支持,而从江东大族方面来看,他们要发展其宗族的力量,在天下分裂大势基本确立之后,必然希望缓和与孙氏政权的对抗,所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多进入孙氏幕中,推动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大致在黄武年间,孙权先后启用陆逊掌握兵权、顾雍行使相权,分居文武朝班之首,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
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大族的政治、经济力量急剧膨胀,其中尤以吴地顾、陆、朱、张四姓为突出。以陆氏为例,《世说新语·规箴》载: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人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刘孝标注引《吴录》云:“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这说明陆氏宗族之强大,连皇权也不得不有所惧惮。与此同时,东吴地方选举也基本上为江南大族控制,《三国志》卷56《朱治传》载治为吴郡太守,“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这里将“吴四姓”与“公族子弟”并举,可见江东大族子弟社会地位之高。他们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垄断了地方的选举权力。
与此相应,江东大族的经济利益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田园,还占有数量惊人的部曲、佃客,孙吴政权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赐田复客制、世袭领兵制等,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现实利益。对此,仅举《抱朴子外篇·吴失》的一段记载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势利倾于邦郡,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棁。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这样的记载甚多,充分说明了江东大族经济实力之强大。此外,东吴时期江东大族在婚姻、社交等社会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这虽与两晋时期典型的门阀制度相比尚不能完全划等号,但确实可以说当时江东大族已经初步门阀化了。
然而,西晋灭吴打断了江南大族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尽管晋武帝司马炎一度为了稳定江东局势,采纳了南人华谭的“先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轻其赋税”的建议(《晋书·华谭传》),对“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晋书·晋武帝纪》)。但总的说来,吴人已沦为“亡国之余”,其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时人刘颂便上书直言:“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时湮替,同于编户。”(《晋书·刘颂传》)当时不少江东大族人物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即使太康以后,陆机、陆云兄弟、顾荣等“南金”入洛求仕,但大多遭遇坎坷,不仅屡受北人的轻辱,而且“二陆”等还惨遭杀身之祸。顾荣虽未死,但也有朝不保夕之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任齐王主薄的境况说:“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正因为如此,西晋之世,江东大族“屡作妖寇”,图谋兴复孙吴之旧,并在西晋末年支持陈敏之乱。[8]当然, 当时的历史形势已不可能再回到南北分治的历史旧局中去了,江东大族只有与北方文化士族合流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四、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大族与侨姓士族的合作及其从属地位的确立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士庶纷纷南奔,并在江南重建东晋王朝。但是以司马睿、王导等代表的晋室王公和北方士族要在昔日敌国——东吴的辖境内创建新王朝,必须努力寻求江东大族的支持与合作。据载,司马睿初过江,“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司马睿本人也常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的感觉。对此,王导建议司马睿“虚己倾心,以招俊乂”,他们主动拜访了江东大族代表顾荣、贺循、纪瞻等。顾荣等入司马睿幕,任散骑常侍,他大力举荐南士,如顾氏、陆氏、谢氏、贺氏、陶氏、甘氏、殷氏等,其中有些是自吴亡后始终丧失仕进机会而又重新步入仕途的南士。(《晋书·顾荣传》)东晋建立前后,贺循、纪瞻、陆玩、顾和、陆晔等江东大族代表,皆位至卿相,这是西晋时期所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王导又主动向陆玩求婚,并刻意习吴语,做出了种种姿态,可谓用心良苦,表示与南人亲善。比之西晋,南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南人代表与流亡的北方士族共同拥戴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汉族政权,与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相抗衡。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江南的所谓“武力强宗”一再兴事生乱,反对侨人政权。但以顾、陆、贺、纪等“文化士族”出于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坚定地维护侨、旧合作。这对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东晋王朝的总体政治格局看,其中枢权力始终掌握在侨姓大族的手中,江东大族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即便是在南人仕进比较顺利的元、明、成等东晋前期诸朝也是如此。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统计东晋有尚书令15人,北人12人,南人3人;尚书仆射共30人, 南人仅占10人;吏部尚书共32人,北人占24人,南人有8人; 三公几乎清一色的北人,南人仅有个别人如陆玩侥幸点缀其间,还为北人讥笑倾危国家栋梁,又自嘲“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晋书·陆晔传附陆玩传》),其不自信竟如此。从以上数字比较,侨、旧士族强弱分明,南人仅为侨姓士族的政治配角。至于中央、地方的军事指挥大权,更是基本上为北人垄断,南人只有东晋初甘卓、戴若思、陶侃等少数人出镇地方,且一再受到排挤。江东大族的这种政治从属地位,一直持续到南朝仍无根本改观。尽管南朝时期侨姓士族日渐衰败,但仍压制南人,维持既往的侨、旧体制。如南齐高帝欲用吴人张绪为右仆射,侨姓代表王俭直言“南士由来少居此职”,坚决反对。当时褚渊在座,说:“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愤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南齐书·张绪传》)齐高帝无奈,只得弃张绪不用。从社会地位而言,南人也低人一等,如梁武帝时东魏降将侯景“请娶王、谢”,梁武帝应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愤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南史·贼臣·侯景传》)婚、宦二事是确立门阀地位高下的标志,当时的统治者极为重视。而在这方面,南朝时期江东大族显然处于侨姓之下。
当然,对这一状况南人是有不满情绪的。早在东晋立国之前后,“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驾御吴人,吴人颇怨”(《晋书·周处传附周勰传》)。如义兴豪强周氏的代表人物周玘便以“中州士人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他图谋生事未成,死前谓其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晋书·周处传附周玘传》)周勰后来果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直到南朝,仕途不畅的南人仍义愤难平,只是他们已无法改变侨、旧格局,故怨怪当初顾荣等不应接引诸伧南渡。如南齐时乌程人丘灵鞠曾愤恨地说:“我应还江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看,顾荣等南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抛弃狭隘的乡邦意识,接引北入南渡,实我国历史上之大功臣。不过,丘灵鞠的牢骚仍有其“合理性”,它表达了南人对两汉、特别是东吴时期相对独立发展和全面得势的黄金岁月的一种怀念之情,更表达了对两晋以降南人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相对失落的怨愤。所谓不平则鸣,说的正是这一道理。及至梁代,以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江东大族在政治上似有所上升,但侨、旧体制并没有根本变化。至于侯景之乱后,整个高门阶层衰败不堪,江南腹地的被称为“岩穴洞主”的土著豪杰崛起,造成了南朝政治新的变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收稿日期:1999-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