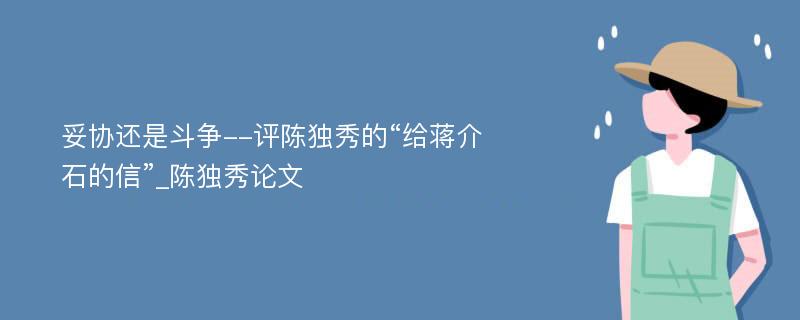
妥协还是斗争——评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信论文,蒋介石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后,6月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57 期上公开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信》)。过去,由于受到共产国际、苏联和对陈独秀本人评价的影响,对《信》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一直把它看成是陈独秀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依据。笔者经过考察这段历史和研析这封信,认为这个看法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拟从《信》的发表背景、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探析,不妥之处,祈请专家、学者、同行指正。
一
《信》写于26年6月4日,发表于6月9日,由于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均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和“整事党务案”之后,且此时正处于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氛围之中,所以,一些论者认为,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写信给蒋介石,无疑是对其妥协退让。我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考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中央、陈独秀当时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态度及立场,了解当时妥协退让的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结论。
1926年3月20日, 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和发展,篡夺统一战线的军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以往,人们一般认为“由于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篡夺阴谋得逞。”〔1〕似乎这个事件是陈独秀处理的。其实,事件发生时, 陈独秀不在广州,而远在上海,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而专程派人去来不及,”〔2〕故中共中央、陈独秀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消息。 既然消息都不知道,就谈不上处理,更谈不上什么“主张妥协退让”。
那么,事件究竟是谁处理的呢?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是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事件发生时,其所率的苏共高级使团正在广州考察,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当时在华的所有其他苏联顾问,“连鲍罗廷及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并接受其指示,”〔3〕所以, 他运用自己的权力一手处理了这一事件。当天,广州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被蒋介石派兵包围,布勃诺夫等人先是十分震惊,稍事稳定后,即亲赴蒋介石处磋商、询问,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明确答复后,布勃诺夫即于3月24 日上午开会决定处理事件的方针和办法。他认为事件的发生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错误有关,会议据此决定“不同意反击”〔4〕蒋介石, 并撤销为蒋介石所不满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以此向蒋介石让步。会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苏共高级使团于同日下午撤离广州,行前布勃诺夫再次向蒋介石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被解职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罗加乔夫等人也随团离去。
当布勃诺夫在广州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陈独秀对于“中山舰事件”还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3月末, 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就事件进行了谈话,这样,陈独秀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大概情况,但“其巨细颠末”还“未能详知”〔5〕。 在布勃诺夫等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下,陈独秀对事件性质一度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判断,并根据布勃诺夫的既定方针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的态度和立场。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6 〕这篇文章是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反映出中共中央、陈独秀此时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对策。随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介石采取友好的态度。”同时,又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7 〕然而,张国焘离开上海不久,4月中旬,陈独秀陆续收到周恩来、 陈延年等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在详知事件的“巨细颠末”之后,陈独秀异常愤怒,便一反“和解”立场,“主张和蒋介石斗争”〔8 〕: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让“国共两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问题”〔9〕; 另一方面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对抗、孤立、打击蒋介石的新政策,〔10〕并派彭述之前往广州,传达并执行中央的新政策。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却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反对。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于事件后作出的“利用蒋介石”和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11〕的决定及布勃诺夫提出的处理意见,首先做的就是反对中共中央、陈独秀的新政策,谋求与蒋介石的妥协。4月30日,鲍与蒋介石“商议党争,交换意见”〔12〕后, 即决心对蒋介石作极大限度的让步。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广东区委干部特别会议上,鲍罗廷一再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必要,为了合作,必须向蒋介石妥协。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也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会议在没有进行讨论的的情况下表决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13〕接着,鲍罗廷“与蒋中正先生会商国共关系问题,订定‘整理党务案’。”〔14〕蒋介石为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鲍罗廷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国共两党再次发生冲突予以同意,并且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办法。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蒋介石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后来写道:“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交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又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15〕不仅如此,鲍罗廷还积极协助蒋介石扶持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此,张国焘写道:“在三二○事件后,筹备二届二中全会中,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16〕正是由于鲍罗廷的妥协退让,结果,在5月15日至22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接连抛出了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对这四个暗伏杀机,“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17〕的反动提案,中国共产党内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廷的“竟然忍让”和压制,这四个提案终被顺利通过。
陈独秀在报端看到“整理党务案”发表后,非常愤怒,立即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明确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虽有约束力,而对于国民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18〕,公开声明不承认“整理党务案”。这一行动无疑是对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所执行的支持蒋介石、同蒋介石妥协政策的公开对抗,是对蒋介石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人反动行径的公开斗争。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是布勃诺夫、鲍罗廷等人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苏联对蒋介石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并在他们的操纵和压制下,形成了妥协退让的格局。而当陈独秀撰写和发表《信》时,妥协已经形成,退让已成定局。事实上,陈独秀“不仅思想上与之联系甚微,时空上也仅有相继关系”〔19〕,所以,不能因为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写信给蒋介石,就认为是陈独秀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何况,史实还向我们展示了重要的一面,即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都“恰好是主张反击,而不是主张妥协”〔20〕。
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挑起政治风浪,掀起反共浪潮,达到了初步的目的——打击和限制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发展。但是,蒋介石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继续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不过,这时蒋介石由于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谴责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由于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并施展其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玩弄自请处分、缩小事态、打击右派、嫁娲于人等骗局,以欺骗和麻痹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在舆论和理论上向中国共产党进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肆鼓吹和贩卖“一党专政”的反动理论。还在4月上旬,蒋介石就声称, 国民革命军以三民主义为主义,只能以三民主义者为干部,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同月20日,他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时发表讲话,声称:“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21〕不过,限于时机,他这时的话讲得还比较含糊。然而,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他觉得时机成熟,便直言不讳了。5月27日, 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22〕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讲话称:“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他接着声称:“如果一党中间,有另外一个小党的党员在里面活动,一班党员便起了猜忌怀疑之心,由这猜忌怀疑便发生一种恐惧,由这恐惧便发生冲突,由这种冲突便自己的势力互相残杀,同归于尽。”因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他还说:“一方面主张世界革命统一,中国革命要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一方面,中国革命是中国国民党来领导中国各阶级革命,要请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23〕6月8日,蒋介石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24〕可见,蒋介石兜售“一党专政”反动理论的目的和实质是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合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决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第二,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阴谋暴动”、“阴谋倒蒋”。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发动“中山舰事件”时就开始诬陷中国共产党“阴谋暴动”。事件后,蒋介石在某些方面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但在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方面,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从3月22日起, 蒋介石在多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训话,含沙射影、嫁祸于人地攻击和诬陷中国共产党。3月22日,他第一次就事件对黄埔军校官佐学生发表讲话。 在讲到他为什么发动事件时,他绘声绘影地说自东征胜利回到广州后,就出现了“倒蒋运动”,有人造谣“陷害”他,使他十分“痛苦”;说黄埔军校中有人攻击他是军阀,是应该打倒的段祺瑞;还说有人勾结在一起,早就阴谋推翻他,因而他采取紧急的严厉措施完全是被迫的,也是正当的。〔25〕3月24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给第4期的学生讲话。这时事件真相已逐渐暴露,而他在讲话中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漏洞百出。学生当场纷纷向他提出质问,他无言以对,便耍无赖地说:“你们若要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26〕4月20日, 蒋介石设宴送别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在宴会上又发表讲话。在讲到事件时,他故弄玄虚说“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现在“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讲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27〕除此之外,他在事件后还发表了两次演讲,也影射、诬陷共产党。关于这一点,国民党的党史资料中,在提及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讲演时加以注释说:“事后蒋校长曾为此事发表两次演讲,但为考虑当时国内外局势及当地复杂情形,不愿将事变底蕴立即宣布。”〔28〕实际上,蒋介石是“中山舰事件”的真正肇事者和阴谋策划者,事件的“底蕴”他当然是绝对不敢公布的,因而便采取这种诬陷中国共产党和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
由上可见,蒋介石在继军事上、党务上进攻之后,又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理论上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认为“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29〕于是,为了揭露蒋介石“以退为进”的骗术, 批判其“一党专政”的反动理论,驳斥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他拍案而起,奋笔写下了这封《信》。因此,从写作动机来看,他是为了维护我党利益和名誉,对蒋介石的独裁阴谋进行揭露和斗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信》是战斗的檄文,并非是妥协退让的依据。
三
有论者认为,《信》“写得非常软弱无力”,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坚决”与“自信”;甚至认为《信》在认识和评价蒋介石方面,说了不少“胡话”。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我们认真地研析,就会发现《信》不仅慷慨激昂,充满战斗精神,而且对蒋介石认识透彻,反蒋的态度、立场非常鲜明。
第一,《信》对蒋介石的假意“苦衷”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蒋介石在多次讲话、训话、演讲中,一再说他有许多“不能讲”、“不忍讲”、“不愿讲”的“苦衷”和“痛苦”,以混淆视听,掩盖事实真相,实则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其弦外之音谁都能听得出来。对此,陈独秀指出:“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蒋介石“说出的权利”,但若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则要求蒋介石“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社会自有公评。”〔30〕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心中有鬼,才不敢说出事件的真相,故意躲躲闪闪,制造疑案,这一点,陈独秀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并就此进行嘲讽挖苦。
第二,《信》对蒋介石诬陷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进行了揭露。针对蒋介石多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含沙射影、闪烁其词的攻击、诬陷,陈独秀给予了无情的揭露。陈独秀指出:蒋介石“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至尾,都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31〕为此,陈独秀严正声明:“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32〕在这里,陈独秀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阴谋者,也就肯定了蒋介石才是真正的阴谋者。
第三,《信》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进行了抨击。陈独秀在《信》中说:“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为。”〔33〕以前,人们往往根据这句话,认为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盲目肯定”、“吹捧”、“美化”,是为蒋介石“开脱罪责”、“公开辩护”等等。我认为,这是对陈独秀这句话的肤浅理解。恰恰相反,陈独秀在这里采用名褒实贬笔法(在当时国共合作至上,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进行了严厉鞭挞。说“三月二十日”以前还“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为”,言下之意“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乃至其后的“整理党务案”,则是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了,只不过前者是其走向反革命的第一步,后者是其第二步罢了。关于这一点,陈独秀以后的文章与讲话都证明,他一直把“三月二十日”作为蒋介石“‘反赤’运动最盛时期”〔34〕的起点。
第四,《信》对蒋介石举出诬蔑共产党的所谓“事实”进行了辩驳。蒋介石为了达到对共产党栽诬的目的,竟在他的训话中举出四个“事实”:即军官恐怖与自卫的问题、第七军名称搁起问题、高语罕说“打倒我们的段祺瑞”问题、北伐主张被根本推翻问题。陈独秀对此进行了逐一辩驳,认为:第一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只能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党分子之意志”;第二个事实“当然和我们无关”;第三个事实“绝对没有”;第四个事实则“只有缓进急进之分”而无“根本推翻”〔35〕之意。蒋介石企图泼给中国共产党的脏水,陈独秀又全部给泼了回去。
第五,《信》对蒋介石所鼓吹的“两个领袖”舆论进行了批判。针对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36〕的言论,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介石的别有用心,名曰国民党“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实则主张“有两个领袖”,为其企图当国民党的“领袖”制造舆论。陈独秀指出:“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生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总理,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然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37〕这就对蒋介石企图取孙而代之当国民党领袖的阴谋进行了迎头痛击。
第六,《信》对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团体两个主义不会成功”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蒋介石为了对其“一党专政”理论张目,大肆宣扬“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38〕的谬论。这个谬论是戴季陶理论的翻版,其目的就是认为“一个团体”(国民党)内只应该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即戴季陶所主张的“共信”),而不应该有第二个主义——共产主义(即戴季陶所主张的“别信”),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对此,陈独秀进行了严正驳斥。他指出:这完全是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的存在”,“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39〕
上述内容表明,《信》的主旨是揭露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诬蔑,戳穿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批判蒋介石的反动谬论。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毋庸讳言,《信》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错误。首先,错误地认为国共两党之所以产生纠纷,是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40〕。其次,错误地认为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分子不同,只指出了后者是“中山舰事件”的发动者。第三,错误地认为在“英日美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倒蒋,就是助长反动势力,就是反革命,等等。然而,这些错误毕竟不能影响《信》的主旨,其原则性、批判性、战斗性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总之,从《信》的发表背景、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三方面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信》是斗争的,而非是妥协的。
注释:
〔1〕《中国革命史》(南京七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第186页。
〔2〕《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第11页。
〔3〕《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3页。
〔4〕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5〕致中:《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6〕《中国革命势力的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向导》周报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7〕〔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8〕〔20〕郑超麟:《怀旧集》第144、236页。
〔9〕《郑超麟谈陈独秀》见《安徽大学学报》1981第3期。
〔10〕〔13〕彭述之:《评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前卫出版社,1957年版,第5—6、9—10页。
〔11〕格鲁宁:《论三二○事件后中共的策略问题》引自《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146页。
〔12〕《蒋介石分类日记·党政》1926年4月30日。
〔1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4章。
〔1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文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第42页。
〔17〕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2页。
〔18〕《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向导》第157期。
〔19〕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山舰事件》,《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5期。
〔21〕〔22〕〔24〕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第44、74—75、79页。
〔23〕1926年6月26日—30日《广州民国日报》。
〔25〕见1926年3月22日,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官佐学生的讲话》。
〔26〕见1926年3月24日,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官佐学生的讲话》。
〔27〕见1926年4月20日,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官佐学生的讲话》。
〔28〕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史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辑。
〔29〕〔30〕〔31〕〔32〕〔33〕〔35〕〔36〕〔37〕〔38〕〔39〕〔40〕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周报第157期, 1926年6月9日。
〔34〕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年),第172页。
标签:陈独秀论文; 鲍罗廷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中山舰事件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