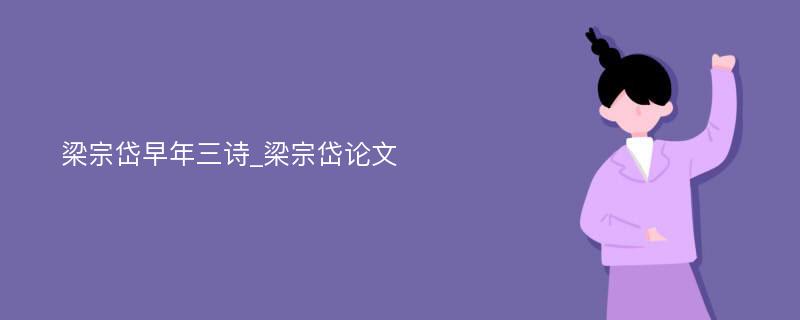
梁宗岱早年的三首集外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早年论文,三首论文,梁宗岱论文,集外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时事新报·文学》1923年8月20日第84期上,梁宗岱发表有《杂感》一文。此文为对创造社诸君之批评,其中,在批评“创造的诗”“泪浪滔滔”之后,有如下之语:
近人发表创造的诗或小说未免太滥了,有好些只是初学的东西便胡乱拿来发表,比方我二年前也曾把我最初学做的几首诗来发表——如《夜深了么》、《小孩子》、《登鼎湖山顶》……,简直不成东西。如今恩之,不觉汗流浃背!(固然现在作的也是幼稚的很;不过总不至那么坏罢了。)
在这段批评文字中,梁宗岱谈及自己“最初学做的几首诗”,引起了我的兴趣。以此文发表时间为1923年看,“二年前”即1921年,也即梁宗岱于1921年开始最初的新诗创作。同年,梁宗岱亦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梁宗岱的诗集《晚祷》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诗题来看,共收诗19首(至于为何是“诗题”,后文分晓)。这19首诗虽然收入的是他在1921年至1924年的诗作,但并未包括梁宗岱在《杂感》中谈及的“最初学做的几首诗”。
今之谈及梁宗岱的诗及诗论,往往是从《晚祷》这本诗集谈起,将梁宗岱早年所作新诗笼统论之,以梁宗岱《杂感》一文视之,实际上他此一阶段的写作还是有所变化,或者变化甚大。
梁宗岱的诗集《晚祷》于1924年初版以后,其后曾再版数次,据《梁宗岱文集·诗文卷·法译卷》中所录“晚祷”集的提示,除初版外,尚有1933年重排版。此外,我找到1939年版。从这三个版本看,其诗之字词有若干改动,但所收诗仍是旧有规模。
2003年,为了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同时有《梁宗岱文集》和《宗岱的世界》两部丛书出版。对于梁宗岱早期诗作的编排方式,均称是保持《晚祷》诗集不变,整体收入书中,其后再录入新找到的集外诗。
从诗题来看,《梁宗岱文集·诗文卷·法译卷》中的“晚祷”集收录梁宗岱诗19首,但在《宗岱的世界·诗文》中的“晚祷”集里,梁宗岱诗却有20首,其中多出一个诗题为《夜的梦痕》。原来,此首是从前一首《光流》中剥离出来的。在《光流》一诗的写作时间上有一个“编者注”,曰“原注把‘夜的梦痕’四字排在这日期之后,而下一篇则无标题,现分开排。”《光流》一诗,原载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其后诗集《晚祷》的1924年初版及1939年版均保持同样格式,《梁宗岱文集·诗文卷·法译卷》中的此诗,因编者说明中是以“后出版本”为准,应是按《晚祷》1933年重排版而定。在《宗岱的世界·生平》中,当作者谈及《晚祷》时,仍为“19首”,①而且在引用《光流》一诗时,也未将其分为两首。②只有《宗岱的世界·诗文》卷中,将《夜的梦痕》与《光流》分开,另为一个诗题,并未交代出处,或许是此书编者据自己理解而编排。
两书中所收写于1924年之前的集外诗,《梁宗岱文集·诗文卷·法译卷》设“集外”一栏,有《森严的夜》、《絮语》、《太空·五、十二》。《宗岱的世界·诗文》中“其他诗作”一栏,有《小娃子》、《哀慧真》、《烦闷》、《高兴》、《森严的夜》、《小溪》、《新生》、《感受》、《太空·一、六、十、十二》、《恐怖》、《旧痕》、《絮语》、《感伤之梦》。
以上两书所收集外诗情形不一,有的是组诗中曾节选数节选入《晚祷》,有的或改换诗题收入《晚祷》。总体而言,《宗岱的世界·诗文》所收集外诗较《梁宗岱文集·诗文卷·法译卷》要多。在《宗岱的世界·诗文》的“编后小记”中,编者称“个别早年的诗文,虽知其题目,但至今尚未寻得,深感遗憾。惟有寄希望于未来的《宗岱佚文集》了”。
梁宗岱在《杂感》一文中提及的几首诗,大概就属于“虽知其题目,但至今尚未寻得”之列了。恰好我因编选《现代诗论丛编》(1921-1923)卷的工作,查阅此一时段的旧刊时,记下了梁宗岱的这几首诗。
《杂感》中提到题目的有三首诗:《夜深了么》、《小孩子》、《登鼎湖山顶》,其中《小孩子》即《宗岱的世界·诗文》中所收《小娃子》,写于1921年7月15日,此时梁宗岱还就读于广州培正学校,算是中学时代的诗作之一。因《宗岱的世界·诗文》已收,故不再录入,惟此书并未注明此诗原载《太平洋》1922年第3卷第3期。
《夜深了么》刊于1921年11月30日《学艺》第3卷第6号,该杂志由丙辰学社编辑出版:
夜深了么?
为什么我底窗前却好像霜一样地亮着?
月亮儿从窗儿透过——
照著我底床;
映着我底眼;
令我睡也如何睡得下。
月亮儿啊!
你怎么这样地多情?
你怎么这样地缠绵?
你爱我么?
你恋我么?
你可怜我这个苦人儿。
在这静悄悄地深夜伴着我么?
只是伴着我,
倒令我一腔底伤心事从我底胸中涌出来了。
倒令我满眶底眼泪儿从我底眼里迸出来了。
况且你底光终是照不透我底心儿底幽暗的。
唉!…………罢了!
我也不睡觉了!
我也不瞌眼了!
就使我瞌着眼儿,
恐怕仍是见着那愁城苦海罢!
外面底风,你为什么只是呼呼地吹着?
远村底狗,你为什么只是汪汪地吠着?
树上底叶,你为什么只是莎莎地叫着?
树上底枝,你为什么只是格格地响着?
你怨么?
你慕么?
还是有什么伤心事,
要告诉给苦人儿听么?
还是我底爷,我底娘,我底弟弟,
忍不住我底苦,托你们来探问我么?
爷啊!妈啊!
你可迟了!
当日我不是苦苦地央求你么?
我底弟弟不是苦苦地哀告你么?
只是你以为这样就是爱我,
这样就是再大没有地爱我。
唉!你可错爱我了!
我也太随你摆布了!
本来呢,你家庭养育,恩情高厚,
我那里敢违背你!
更那里敢怨怅你!
只是——
你不该贪那人底富贵;
你不该恋那人底奢侈;
拆散我底好人儿,
弄我到这般田地!
我底好人儿啊!
你是在家中么?
你是在学校里么?
你是在念我,怨我么?
去年中秋底月下,
不是我们俩诀别底日子么?
恨只恨——
你还是不能自立底男子;
中国底社会,
又不能容能自立底女儿。
我要逃走么?
那里逃得去!
我要死么?
我底父母恩情,又那里报得了
只得拼着我一身,
做我父母底一个孝顺儿子。
谁知一错再错,
竟错到这般田地!
你可看见我在这里受痛苦么?
要是你看见我,
恐怕你也要怨恨我了。
还是不怨恨我,
还是怜悯我,爱惜我呢?
鸡叫了!
多情底宝月,也离我去了。
窗儿上已透出一片曙光
来替代那月亮儿底光了。
树上底寒鸦哑哑地乱叫——
天就要亮了。
我底心儿却仍是一样地幽暗着
我底手如雪冷!
我底面如黄蜡!
我底心似死灰!
我底湿透了我底双颊!
唉!我要离开你了,可怜底世界!
唉!可怜底世界,我要离开你了!
二一,一,十一,于广州培正学校
此诗大概是书写了一个反抗包办婚姻、追求爱情与独立并意欲自杀的青年女子在深夜的思绪,自是彼一时代之流行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学艺》和这份杂志的主办者丙辰学社。丙辰学社与少年中国学会相似,亦是彼时纷纷成立的青年团体之一,郭沫若诸人曾较晚加入这一团体,并在《学艺》上发表作品。不过,查阅《学艺》,并未发现梁宗岱的入社记录,发表作品也仅仅只此一次,或许仅是投稿。
《登鼎湖山顶》见于1922年5月5日《学生》第9卷第5期,这份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一
来到鼎湖山的白云寺住了六天了。
山的名胜都几乎游尽了,——
信女如云的庆云寺去过了。
飞流百尺的飞水潭也游泳过了。
林间飞鸣的鸟声,虫声,……听够了。
溪间石上看书,写信,也做够了。
但鼎湖山顶呢,
到过未曾?
还未曾啊!
这也配叫得做游山么?羞啊!
今天已是到山底第六天了。
倘再不达到彼巅,后天就要下山了。
不要辜负了这行么?
不要令山灵失笑么?
我们快登上山的极巅去。
二
到底壮志是多阻的啊!
挫折我们锐气的说话,就百出了,——
卖物的说:
“平时是可去的;但这几天淫雨霏霏,
路是很滑而难行的。
不要滑倒么?”
同行的说:
“山顶?是容易到的吗?
我们昨天还不过到山的一半,
已经费了两三点钟的时候。
你们若想到山的绝顶,除非明天绝早上去才得。
现在已是下午的两句钟了,
上了去今夜怎能回来呢?”
胆怯而不去的纷纷了。
剩下的人呢?
除了我外,
只有司徒乔曾恩涛二君。
我们三人也许是听从他们的话;
然而,不过是令我们准备得周到些罢了。
一枝万寿藤的杖,
一包杏仁制的饼,
一张洋毛的毯,
一个储满滚水的壶,
扶著,系著,挂著,背著,
便飞也似的向山顶跑去了。
三
从寺的左近一条小径上,
转了三个湾,
便有几间泥屋现于我们底眼帘了。
一个龙钟老迈的乡翁正在门口吸烟,
喷出的烟作一圈一圈地缠绕而上。
但是我们可迷了路了,
便走过去恭敬地问他一问。
他那温和地不愿意我们去而不得不说的话,
我们便依了他从屋后的小路上了。
四
小路真滑啊!
形势是很斜的。
走不上百来步便气喘喘地了。
两条腿也倦到了不得了。
然而最近的一个山峰已快到了。
登罢!登罢!
登上去,歇歇罢!
高过膝的香草从我们的胫上拂过;
但也不过令我们的呼吸更香些。
不上十来步便到了最近的一个山峰。
那不是几颗大石么?
且放下行李歇歇罢!
五
呀!歇了十分钟了,
快点起程登上山去罢!
于是第二个山峰又到了。
但是我们底呼吸可又不灵了。
歇歇罢!
呀!雨来了!
你看!山那边不是乌墨墨地云一团团打下来么?
团团地白云不是濛濛地向着我们进来么?
我们快向上跑去!
和他们赛个快慢!
六
但是我们究竟给他们战胜了。
白云已追到我们底脚下了。
我们底路快要迷了。
四围底景色都遮昏了。
三尺以外的景色都不见了。
肚可饿了。
口也渴了。
身也倦了。
然而不觉间又过了两重山顶。
迷迷濛濛的,那不是斜立的石壁么?
快走去躲躲罢!
除了身上的毯,
去了头上的帽,
揭开水壶盖,
放下毒藤杖。
充饥有芬芳可口的杏仁饼;
止渴又凉透肺腑的山溪水。
山谷间茂林荫著的溪水涓涓声势还可以听到的;
但微得要催我们眠了。
七
白云依旧密密地笼着;
雨点依旧疎疎地打著;
我们底心可不耐烦了。
我们要冲著白云,浴著雨点,望著山顶跑去了。
我们就跑出崖壁去。
哎哟!好险哟!
发发地狂风吹的好不寒,
险些儿就要把我们煽倒了。
但我们只把脚跟略站定,
便又望山顶飞也似的跑上去。
八
再上去路就没有了。
形势比前更加陡了。
然而管他什么!
跑得的就跑是了。
跑不得的就行是了。
行不得的就攀是了。
到底曾君跑得比我快些,
一眨眼已到了两山间的凸处。
“O Fine!……Come on!”他叫著。
我们便也向上飞跑了。
九
几重山顶已经过去,
看看快要到山顶了。
云渐渐的稀了。
雨也止了。
下望迷濛中只见些山坳间的树。
但路更没有了。
形势更加陡了。
巉岩的大石,
丛生的小树,
石罅的长草,
直立著,斜倚著,下垂著。
那里是路?——没有!
那里是地?——望不到!
我们就此止步么?
否,不行!
我们要攀著大石上去。
我们要扶著小树上去。
我们要缘著长草上去。
我们要直立著,斜倚著,下垂著上去。
鞋底脱了。
手皮剥了。
我们又到了一重山顶,
然而还不是最高峰啊。
十
白云依旧笼著;
雨却没有了。
我们依旧攀著,扶著,缘著,登著;
绕了几绕,便到了山巅了。
啊,到了山的最高峰了。
好美丽哟!
好灿烂哟!
照苏的太阳当顶射下来,
山下的白云一张一张的分开,
现出一个再鲜艳没有的世界。
远近山脚下的村落,都好像乱石般乱堆了。
出肇庆峡的西江,却像一条大的蚺蛇蜿蜿蜒蜒地。
啊!好美丽,好灿烂哟!
“可惜伊不曾同来哩!”
十一
哦,时候不早了。
天快黑了。
我们下去罢!
攀援而过了几个石崖。
飞跑而过了几个山顶。
背滑而下了几个斜坡。
看看到了山脚了。
但来时还没有滑倒过的路,
现在却噼呖拍勒地跌了好几跤了。
屋前一个衣衫褴褛的村童向我问道:
“不怕雨淋么?”
我顾了他一眼笑声说:
“好朋友,多谢你底盛意。”
便又飞也似的向白云寺回去了。
此诗很长,亦是彼时流行一时的一类题材——“游记诗”。在评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时,胡适指出“这一类的写景诗”,“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③而康白情的组诗《庐山纪游》,共37首,则被胡适评为“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④梁宗岱此诗后未署写作时间(或许是因篇幅关系,因此诗最后一行已是该页最后一行)。但必定是在该刊出版的1922年5月5日之前。
此外,梁宗岱在《学生》第8卷第10期曾发表所译泰戈尔诗《他为什么不回来呢》,目录中为汉译诗名,但正文却是英文诗。而在2003年出版的两部丛书中所选此译诗,都变成了汉语译文。
至此,梁宗岱在《杂感》中所提及的三首诗已交待完毕。但是,在1921年至1924年,梁宗岱的新诗创作想必会更多,譬如,我在1922年4月5日出版的《太平洋》第3卷第5号,就发现了梁宗岱的《深夜的Violin》一诗:
在那昭苏的春日载阳,
千啭的黄莺儿溜溜地歌唱,
心琴的回答,
也带着喜溢的声浪。
在那将曙未曙的清晨,
司晨的公鸡儿哥哥地骚动,
灵魂儿也会,
惊醒从沉沉地酣梦。
就是钢琴,当他叮咚地响,
也会引起人们进取的精神;
就是军乐,当他雄壮地吹,
也会令到人们有奋斗的心。
独你这哀吟的Violin,
偏在这静悄悄地深夜哀吟;
给我以无限的懊恼,
惊扰我不定的灵魂。
你究竟有什么伤心事?
究竟有什么事伤你的心?
为什么你只这样地悲咽?
为什么你只这样地低沉?
你有如此美丽的颜色,
冰雪聪明地天资,
难道也事非其主,
住不得其号伴侣?
还是觉得这世界的溷浊,
不圆满的事常引起你的愁恨;
特地里发出几声叹气,
来表示你的“哀矜勿喜”的怜悯?
Violin啊!
我恐怕你未能把这大地安慰,
你的琴上早已断了弦了;
那时任你用尽了你的哀矜,
恐怕也难再续那已断的线了!
到不如把你的歌声深深地收没了,
让这大地好过他的死寂地生活了!
二一,七,二二,于广州,培正学校⑤
此诗似乎较接近《晚祷》集中的风格,较为沉潜凝重,且以Violin为题,也有走向音形义“交响”之象征主义,而与前两首的“叙述”或“叙事”风格略有差异,虽这一读感亦是建立在对梁宗岱《晚祷》及其后诗歌的倒溯上,但上文所列三首诗亦能显露出梁宗岱早期诗歌创作的不同路向。
1921年至1924年期间,梁宗岱在广州参与主办了《越华报》的《文学旬刊》副刊,据说亦发表了大量文学创作。但在《宗岱的世界》所辑录的新诗中,除《晚祷》集外,梁宗岱此时的新诗却只有仅仅十余首。
再回到《杂感》一文,梁宗岱猛烈地抨击了创造社诸君所代表的诗歌风气,并以自己早期诗作为例,而在出版第一本诗集《晚祷》时,文中提及的几首诗也全都未收入。此亦反映了梁宗岱的诗歌态度和诗歌观念的变化。因此,找出梁宗岱的这三首集外诗,一方面似可说明,在1921年至1924年,以《晚祷》为代表的梁宗岱的早期诗歌创作,可以更细分出一个时期,即以《登鼎湖山顶》和《夜深了么?》诸诗为代表的诗歌实践。另一方面,这几首诗,亦能见彼一时代的诗歌流行风气之一斑。
在搜寻梁宗岱早期集外诗时,也曾发现梁宗岱发表于期刊上的诗歌,在收入《晚祷》集时,以及在《晚祷》集的再版中,都有程度不一的修订。对此仔细校订,又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但那也许是另一篇文章了。
注释:
①黄建华等:《宗岱的世界·生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②同上,第24页。
③胡适:《评新诗集(一)康白情的〈草儿〉》,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第1期。
④同上。
⑤本文所辑录的三首集外诗原文“著”、“着”同时使用,文中保持原状,未作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