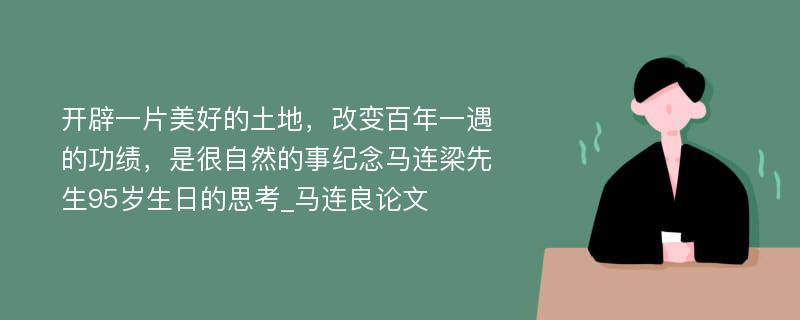
独开妙境饶新变 百炼功纯尚自然——纪念马连良先生95岁诞辰的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妙境论文,断想论文,诞辰论文,自然论文,百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剧艺术200年来,无数天才用生命投入,才使她登上了民族艺术峰巅,推开了世界的大门,并做为人类文明的瑰宝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物换星移,不少天才已走进历史,永不磨灭的是他们生前身后的辉煌。马派艺术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就是为京剧创造辉煌,并以他的艺术财富、艺术人格为起点,能使京剧再现辉煌的艺术大师。
一度迷茫之后,当社会文化心理走向成熟,文化观念、审美取向更加自觉的时刻,作为民族文化综合显示的京剧艺术,重受青睐、再振雄风的时机必然到来。值此,马连良先生95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缅怀先辈,寄情未来,希望旧曲精深人脍炙,新声隽永世争歌的京剧新天地早日到来。
一个剧种,表现社会题材的广泛性,反映社会层面的多样性,必须有成熟的老生行当,这已经成为一个剧种趋于成熟的标志,在京剧艺术史上,老生行当举足轻重,代有才人,各领风骚。程长庚、谭鑫培之后,生行流派纷呈,相映成辉。由于戏曲观众审美能力的成熟,有了更多的群众参与,20年代、30年代先后推举了“四大须生”,唯有马连良先生两兼“四大”,独获殊荣,以后更有“南麒北马”并峙菊坛南北,直至马连良盛年早逝,以至于今日依然无人超越,这在京剧生行艺术中堪称奇迹。戏剧研究大家张庚先生称马先生为“老生泰斗”,可谓独具慧眼,千古定评。
京剧艺术有着先天于南,后天于北的两种基因。有着受宠宫廷、重归市井的两种经历。马连良从坐科学戏到走上舞台,正是面对京剧改革相继,高潮迭起的特殊时代。马连良这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在于他的天赋与勤奋,还在于他不沉醉于一时成就,能摒弃自恋,放开视野,洞察京剧艺术发展的症结与契机,在传统的规范中去探寻京剧发展的趋向,迈着自己的脚步,拓宽着京剧艺术的路。读了马先生不少文章,深感马先生谈戏论艺、精湛独到,是以才、学、识所谓史家三长为根底,是立足于京剧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品位上,而不是拘囿于舞台上下有限空间,仅仅在唱、念、做、舞上毫分缕析。艺术观念化为一种艺术实践,马连良一生应是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不断革新的艺术大师。
应该承认,京剧艺术自身发展,必须在内部有一种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推陈出新的机制。京剧艺术的永不衰竭生命,主要来自京剧艺术工作者群体的活力。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作为京剧艺术的载体,推动京剧艺术向前发展的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京剧工作者,大多文化基础薄弱、文化视野较为偏狭,不能不承认京剧艺术发展滞后,终于跌入低谷,除了外部原因之外,这内部原因起着重要作用,马先生自律苦学应成为后来人的典范。
京剧艺术名角辈出,但堪称为表演艺术家者寥寥可数。他们往往缺乏革新意识、超前意识、艺术整体观念,只是继承师傅衣钵,言谈只是师傅传授,倘有所得,只是个人行当、有限剧目的点滴的表演体会,少有艺术底蕴的开掘、艺术观念的升华。有如珍珠熠熠光华,却不能贯散成统,难成系统,更与体系无缘。
马连良作为艺术大师,他艺术成熟的标志在于马派艺术的确立,倘以为马派艺术只是京剧生行的一个流派,无视于她已跨越行当,跨越剧种的广泛的指导作用、借鉴意义,是对马派艺术价值的低估。
马先生师承谭派,但无意自限,不以维妙维肖为追求目标,而是根据自身条件,立足于一,着眼于十,广采博收,在心灵中化合,在实践中创造,化育中一个新的艺术自我。风格是艺术家艺术成熟的标志,艺术家风格独特的艺术成就,其美学贡献,美学价值为社会、为公众所认同、所肯定,更有追随者积极参与,具有集体优势,特立于舞台之上,能打开新境界,别开新局面,这就是流派。艺术是大海,万派归之,任何一流一派,必定是有限的,必须是在流动中,不断吐纳。马先生正是这样看待流派,包括对自己的艺术,也从不尊为“止于至善”视为最高极限。他曾告诫自己的弟子切莫“圣行颜随,亦步亦趋”。他赞赏弟子言少朋在唱、念、表演中有“言家门儿”,高度评价弟子王金璐结合个人条件,勇于继承杨(小楼)派艺术。马先生这种见地、这种心胸,贯穿着他的学艺、从艺的全过程,并使他在艺术生涯的早期便脱颖而出。
近几十年来,提倡继承流派取得了成绩,却不见新的流派诞生,当是遗憾。这和某些流派创造者的家人、弟子,把某一流派奉为万古不变的圭臬,对外是门户,对内是拘限,不允许他人越雷池半步有关。本是一传、再传、三传的货色,已经陈旧,甚而变味变形,却视为秘室珍藏、奇货可居,颇有借死人以发迹之嫌。个人或有所得,然而却使京剧艺术陷入误区。京剧舞台屡见新人,却无新风格、新流派,只是人新艺不新,无疑将断会送了新人及整个京剧艺术的前途。创作上只是一味模仿前人,艺术最终将毁灭自己,这一说法绝非危言耸听。马先生从不以所尊的流派自限,更不以自己的马派自诩。着眼京剧艺术的命运,从艺不从派,这一精神财富的意义已超越了马派艺术的本身。
京剧艺术虽以演员为中心,以四功五法为表现手段,同样是以创造性格独特的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是其根本任务。马先生一生积极改革,从净化舞台,乐队退居边幕纱罩之内,淘汰“出将入相”守旧,到全场人物认真做戏、扮妆到位,小袖、护领、靴底三白,都在追求着一种有助于人物塑造的情境与气氛。一台无二戏,主要角色是戏魂所在、中心所在,恰似北辰居中,众星拱之,也须天宇澄净,众星灿烂,才得以使北辰倍显辉煌、光彩照人。一出戏是个艺术形象体系,从舞美、音乐到配角,都是形象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处薄弱、一处缺憾,都会使整个形象体系松散,甚而瓦解,主要角色,也因周遭的不协调造成了反差,使自己变得苍白。马先生非常重视合作者的选择,注重发挥他们的才智,从无夺戏之嫉。因而马先生的戏,台上人人尽职,个个好看,给了马先生创造自己的角色形象提供了极好的艺术氛围、人物坏境。
马先生对自己创造角色,用心极苦。他认为“演员就是演人物,不同的人物,就要有不同的演法,不能千篇一律。”演人不演行,虽是梨园名谚,做到这一点极难。由于剧本人物的类型化,演出模式的定型化,加上程式运用的技术化,以致演员难以在行当限制之内,创造出性格化人物。千人一面,千曲一腔,演员总是不断重复着自己,立得起演员,活不起角色,观众或许悦耳目,却难动心,这已是众多演员的通病。马连良会戏极多,对自己的每个角色都是用心开掘,把握住角色的性格基调,并和周围的角色交流中、冲突中,去深化他、丰富他,即或是角色的脚步也都是予以性格化。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清风亭》张之秀、《四进士》宋士杰、《甘露寺》乔玄,虽然都戴“白满”归属“衰派”,却因人物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处境不同,而脚步各有千秋。由此足见马连良从角色穿戴到唱、念、做、舞,无不追求着角色的真生命——性格。纵观马先生一生创造数百个舞台形象,都体现着马派艺术风格的同一性,却绝无人物的雷同。
马先生一生以革新为己任,有口皆碑。革新,不是迁就时尚,不是取媚低俗,而是为了使舞台形象更鲜明、更完美、更生动、更感人。这和当前某些剧种、某些剧目,忽略创造舞台艺术形象这一根本,生搬硬套,把出奇出怪,目为革新、艺术整体性的美,七零八落于异想天开的“革新”之中。
马连良艺术成就,千家评说,却不为千家说尽,我则以“独开妙境饶新变,百炼功纯尚自然”,从这一侧面作结。作为艺术大师,他的艺术财富,后世取用不竭,对他评价也将代有新说。
马先生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所欣赏的一句诗“壮志青云上”,恰如明人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马先生巨大成就的取得,在于他有不患得失、不计荣辱,誓为京剧艺术献身的精神,这是他志气的所由来。倘非“志在青云”之上,难挣名缰利锁,或是只有气而无志,必然是心中总不平,艺术总平平,即或天资与马连良比肩,终不过流水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