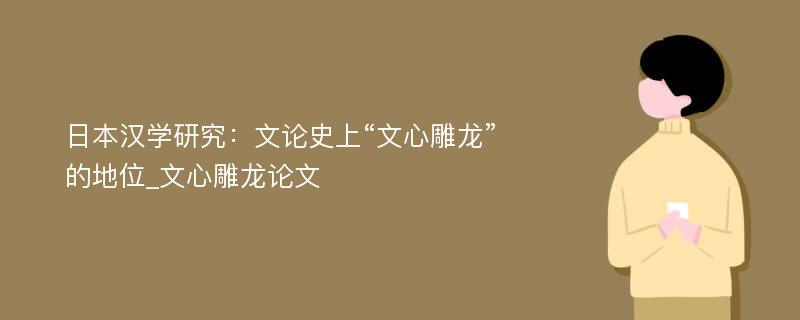
日本汉学研究——《文心雕龙》隐秀篇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文心雕龙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史上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心雕龙》第四十章隐秀篇,虽然其中四百多字可能是后代的补文,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发展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刘勰指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卓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按字来讲,“隐”与“秀”各有相反的含义。“秀”字本来意味着植物抽穗开花,后来引伸为所有引人注目的美好秀丽的东西。“隐”字意味隐晦于内、精微深奥,是“显”的反义。虽然如此,“隐”与“秀”却又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文学理论的主要概念。这里将一方面把作为文论辞汇的“隐”与“秀”的含义溯波索源地加以个别分析,一方面又围绕“隐秀”概念在后代文学理论上产生的意义进行一些考察。
“秀”在文论上是指一篇作品中最突出的地方,基本上继承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想法。换言而说,是一篇诗文中作眼目的秀句。刘勰在后面以王赞《杂诗》中的两句为例而展开议论说:“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陆云《与兄平原书》把相当于“一篇之警策”的概念叫“出语”。(“《祠堂颂》已得省。兄文不复稍论常佳,然了不见出语,意谓非兄文之休者。”又“《刘氏颂》极佳,但无出语耳。”)
与刘勰并时的钟嵘在关于文学的许多观点上持有与刘勰不同的看法,但是只就秀句的问题来看,他与刘勰的意见有不期而同之处,在《诗品》中经常运用秀句而展开评论。譬如说,他论谢朓诗云:“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这里所用的“秀句”一词,与《文心雕龙》所用的比较起来,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差距。现在试看《诗品》中一些秀句的用例。在序里,钟嵘对于过度用典故的作风加以了严厉的批评: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永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垄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这里所引四种古今秀句中,“思君如流水”是徐干《室思》的第二十九句,“高台多悲风”是曹植《杂诗》的第一句,“清晨登垄首”是张华《失题诗》的第一句,“明月照积雪”是谢灵运《岁暮诗》的第三句。钟嵘认为这些诗句是不用典故、直写所见而具有高度风格的典型。和刘勰不同,钟嵘引用秀句时,如上面一段所表示,总是不引一联而只引单句。现在列举诗人评论中引用秀句的例子。
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乘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永怀,非列仙之趣也。(中品郭璞评)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与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仁人德,世欢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中品陶潜评)
《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中品谢惠连评)
郭璞的“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两句,虽然是佚句,但据钟嵘说,有“坎壈永怀,非列仙之趣”,而代表了“辞多慷慨,乘远玄宗”的《游仙诗》的面目。陶潜的“欢言酌春酒”是《读山海经》其一的第九句,“日暮天无云”却是《疑古》其七的首句,钟嵘以为都是典型地代表“风华清靡”的作者诗风的佳句。至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谁不知是《登池上楼》中的名句呢?重要的是钟嵘不单举这些秀句为例,同时通过它们探讨作者的艺术风格。这种秀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钟嵘说“池塘生春草”之句有“神助”。刘勰指出秀句是“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又篇末的赞说“言之秀矣,万虑一交”。于是他们得到的结论显得不期而同一:秀句不是由努力所产生,而是只有通过语言不能表达的某种奥妙的途径才会出现的。
到了初唐,就出现了一本专以历代诗人秀句撰为一书的新型总集,即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二卷。该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但早已散佚,现在只有其序文收在空海《文镜秘府论》而传下来。著者在序文中就本书的编辑方针云:“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可知,该秀句选集是把自古诗到初唐上官仪的古今诗家将近四百人的诗华锦绣汇成一书的。此外,《新唐书》集部文史类还著录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由此可以想像出当时这样的秀句集锦相当流行。据元兢之言,秀句选集六朝时还未有,到唐代初期才出现。“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但他对《古文章巧言语》的选句方针并不满意,因此重新打定主意,开始编辑《古今诗人秀句》。元兢的以秀句为核心而欣赏整篇作品的理论基础,似乎可以回溯到《文心雕龙》隐秀篇。
收在《文镜秘府论》的唐代文论中,有不少作品是以摘取诗歌的精彩部分立论。例如被推定为王昌龄《诗格》佚文的文章(南卷)有如下一段云:
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此之例,皆为高手。中手倚傍者,如“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此皆假物色比象,力弱不堪也。
这里所引的两种秀句,一则谢灵运《登池上楼》,另一则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所谓王昌龄《诗格》的文章, 经常采取如此方法进行讨论。秀句在这些评论中,为阐明论点起着很大的作用。
所谓“唐人选唐诗”中,殷璠《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这两种诗集,是以诗评和诗选为两个组成部门而成书的。更具体地说,殷璠与高仲武都在各个诗人的作品前面,放着论他们诗风的简评。而且在这些评论里,秀句又占据中心的位置。例如:
(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浃,在泉为珠,著璧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至于“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又“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谁肯惭于古人也。(《河岳英灵集》王维评)
〔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矣。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同岑参评)
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艾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且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又“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中兴间气集》钱起评)
殷璠与高仲武基本上继承钟嵘《诗品》的手法,有效地运用各个诗人的秀句,以便生动精彩地刻画出他们整个诗歌世界的艺术风格。《文赋》既然说,“立片言居要,乃一篇一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如上引诗句本身也当然发挥着“一篇之警策”的妙处,同时又代表或烘托了作者的全体诗风。除此以外,尚有中唐皎然的《诗式》五卷中的“诗有五格”,以“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等五格分类诗趣,其中各类是专由摘取从古诗至唐代诗人的诗句而构成的。是把体现五类格的诗句按顺序排列下去,以具体地显示各类诗格的文学风貌。《诗式》序云:“今从两汉已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由此可以推定,《诗式》这书本来可能是以展示诗句为主要内容的诗论著作。
可见,溯源于陆机,深化于刘勰、钟嵘的秀句的概念,至唐代就为不少诗论家所注目,与那时的诗论蓬勃兴起的风潮结合起来,产生了把秀句融合在一起的新式评论。以后,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开祖的宋代诗话又继续沿袭和发展了这种方法。例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云:“梅圣俞云,作诗须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真名言也”(此话实际上根据《六一诗话》中的一文),然后他引梅尧臣《送苏祠部通判于洪州诗》的“沙鸟看来没,云山爱后移”二句、《送张子野赴郑州》的“秋雨生陂水,高风落庙后”二句,以此评为“状难写之景也”。下面又引梅诗《送马殿丞赴密州》的“危帆淮上去,古木海边秋”、《和陈秘校》的“江水几经岁,鉴中无壮颜”,以此评为“含不尽之意也”。葛立方举梅尧臣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佳句,具体指出了梅尧臣裁诗时,是踏实地实践了他那“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创作理论的。这可以证明把秀句融合在评论中的方法,到宋代以后也继续认真地贯彻和发展了下去。也可以说,刘勰早已奠定基础的秀句理论,在好几百年以后的诗论里着实地扎下了根。
2
“隐”的含义比“秀”似乎更复杂些。刘勰把它解释为“文外之重旨”,是正合适于神思篇所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的境地。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应当注意刘勰所谓“隐”的概念的背景,在中国传统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传)的思想。这句话指人在心目中的意思,不能全面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语言有很多限制,它只是个不完善的传达意思的手段。
先秦诸子中,《庄子》的哲学常常触及到这个问题。在天道篇,轮扁回答于齐桓公,论斫,轮之技术云:“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据轮扁说,斫雕车轮的技术是只有他自己的心和手才了解而用语言说不出来的,所以他自己也决不能把这秘诀传给他儿子。又在秋水篇,北海若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据他说,可以用语言辩论者,不过物之粗而已。然而物之精细则只能潜得默化于心,不能用语言辨析。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随着诗文与书画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兴旺,各个方面的文艺理论也空前发展。但理论家们有时还是不断议论语言表达的困难以及创作技术的奥妙性。譬如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站在与轮扁同一的立场上,主张作家各有各的本领,是不能传达给别人的。又《西京杂记》卷二有如下记述:有一人叫盛览,向他朋友司马相如问作赋之诀窍。相如回答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在书法的领域,王羲之《自论书》论书法的技术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对绘画理论来讲,南齐谢赫撰的《古画品录》在古今许多画家中,推荐刘宋陆探微为第一品,而极赞他说:“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地寄言,故居标第一等。”无论王羲之与谢赫,他们都以为最高的艺术成就是“事绝言象”。据谢赫的批评基准来说,艺术上的成果越高,对他的评价就越来越不容易用语言表达出来。由鄙见来看,像这样的想法不但继承《易经》系辞传、《庄子》等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言语道断”思想的影响。
如果一碰到语言的墙壁就束手无策,即无法发展文艺理论。所以若有意开展理论著作,不得不尽量扩展语言本身的能力,以突破语言表现力量的界限。陆机早已在《文赋》序中,为言语不能表达全部意思而发出叹息。他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陆机当然像轮扁一样深深了解创作技术只能得心应手,很难用语言表达详尽,但他尚尽量努力,凡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都要在《文赋》里写下去。
《文赋》本文用韵脚的变换分成二十个小节,基于陆机自己的创作体验,通过作家的心灵之窗,将有关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予以省察,并试图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予以归纳。在将近末尾的第十六节,他论述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创作妙处云: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里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文学创作好像跳舞和歌唱,其中奥妙复杂的技法都无法可传,美言道断。一看到这里,有人或可能怀疑作者又提到“言不尽意”的老套话,将要把创作理论困在神秘不可知的迷宫中。其实,据我来看,在这一节所用的轮扁的故事含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像陆机已经在序中说的那样,作者既十分熟悉语言的限制,就极尽笔墨之能事,从各个角度把创作上的种种问题理论化了。那里当然还剩下不少问题值得讨论,但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后生,期望将来他们能进一步探讨解决。
《文心雕龙》的以神思篇为首的后半部二十五篇特别受到《文赋》的影响,将陆机提出的各种命题开展得更加详细。叙述创作活动中想像力的神奇作用的神思篇,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章。上面已经引用的“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一节是置在该篇的最后地方。在这里,作者发出“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的叹息而结束一篇,是在构思上和内容上都继承上面所看到的《文赋》的方法。刘勰也在神思篇中,一边碰到用语言论述困难之处而犹豫不决,一边又为突破这个坚实的语言之障而奋起挑战,要试图建立空前无有的创作理论。
刘勰在五十篇最后一章的序志篇末尾发出感叹说,我在本书驰聘于文坛艺苑之中,有关文学的问题几乎都谈到了。继续又说:“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这里的感慨也可以说有和神思篇末段相似的积极意义。作者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都已在全书尽量阐明了。若尚有说不够的,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所以他最后很谦虚地说:“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与此相似的想法,在其他领域的艺术理论中也可以看到。例如梁姚察的《续画品》序,一开头即说:“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不过,继此就连绵阐述了很详细的绘画理论。作者先吐露语言的界限,然后开始展开论说。就书论方面说,可以举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为例。对三国时代的书法家钟繇的评论,是以“十二意”,就是从平、直、均、密、锋、力等十二个角度来试图分析钟繇的作品。作者先把这“十二意”名称一一罗列,逐次解释其内容,如“平,谓横也”,“直,谓从也”,“均,谓间也”等等。其下有“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二句,说这里也还有不能以文字表达清楚的神奇处。庾肩吾《书品》在开头的论中,以象微性的说法概括篆书、真书(隶书)、草书等各种书体的特征,接着又说:“殆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这句话也可以看作与上述几个例子有同样的意义。
《文心雕龙》隐秀篇所提到的“文外之纤旨”,是“言不尽意”思想向另一方面的开展。既然语言有界限,未能全面表达意思,就要追求超越字面意义的奥妙味道。换言之,以语言的不完备性为前提,要在文字之外别开生面。范文澜把“纤旨”解释为“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就是指这样的境界。“隐”的含义和“含蓄”、“余味”、“余韵”等辞汇比较接近,但不能说完全相同。物色篇的“物色尽而情有余”一句也与“隐”的意义有一脉相同的感觉。
在《诗品》中也可以找到近似“隐”的概念的想法。钟嵘在序里解释六义中的“兴”的意义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周礼》大师郑注引郑司农云:“兴者,记事于物。”孔颖达疏据此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发起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郑、孔着眼于表现技巧方面加注,钟嵘却着重“兴”所引起的兴致而立论。值得注意的是钟嵘的“兴”的解释与过去代表性的经学解释完全两样,而接近于《文心雕龙》所说的“隐”的含义。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周南关雎)云:“案,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提曰兴。”这也可能是继承《诗品》的解释的。(参照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
到了唐代,重视“文外之纤旨”的美学思想重新受到欢迎,并汇合成为一条更大的河流,一直延绵流传至宋代。现首先举皎然《诗式》中“重意诗例”一节。“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赌文字,盖诣道之极也。”“重意”指诗句里蕴藏着多重意思。皎然引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等句为二重意诗例,又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两联,各为三重意、四重意诗例。他又评他的十代远祖谢灵运的诗句云:“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据此可以看出皎然最尊重的,是“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而“情在言外,其辞似淡而无味”的诗境。这不正是符合刘勰所说“文外之旨”吗?
其后,晚唐的司空图也重视“隐”的境地。他的诗论特别强调“象外之象”、“味外之旨”。《与极浦谈诗书》引用戴容州(叔伦)之言,“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然后又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司空图有时又以味觉作比喻而论诗。在《与李生论诗书》里,他首先说:“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因为正如《吕氏春秋》本味篇云,“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那样,滋味是从古代以来一直被认为复杂微妙而难以语言说出来的。刘勰也在隐秀篇赞用滋味为比喻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司空图还继续说:“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江岭之人”与“中华之人”之所以不同者,只在知“咸酸之外”的“醇美”与否而已。在此书的最后一段,司空图鼓励李生这个年轻人又说:“足下之诗,时辈故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他的《二十四诗品》“含蓄”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也可以肯定涉及到这种境地。
在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介绍他朋友梅尧臣的诗论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然后他把温庭筠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之“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评为“道路辛苦,羁愁旅思”见于言外的秀句。司马光的《续诗话》也似相呼应地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此后,经过苏轼、姜夔等,严羽最后继承了重视“文外之旨”的诗境,而且把禅宗的“不立文字”的思想汇在一起,加以细密系统的理论化,建立了一种独到的文学理论。如此问题,现在不必一一赘述,只引《沧浪诗话》诗辩的一节作见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如上所述,《文心雕龙》的隐秀篇,给后代的文学理论开辟了“秀”和“隐”的两条道路。然而这“隐”与“秀”,一看好似两条相反的要素,但实质上深处结合在一起。它们实在可以说是既一而二,又二而一的。
标签:文心雕龙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诗品论文; 诗式论文; 刘勰论文; 杂诗论文; 六一诗话论文; 钟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