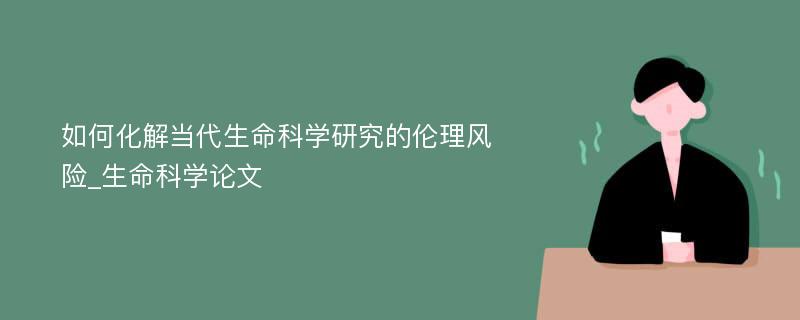
论如何化解当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伦理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科学研究论文,当代论文,风险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并通过生物医学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扩展了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然而,生命科学研究是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处于一种道德窘境(moral dilemma)之中。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领域,机遇和风险象在这里如此紧密相联。正如德国哲学家拜尔茨所言,“人们从现代生物科学的革命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其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业成果,而且还有其‘自我控制’能力的增长。在某些观察家令人愉悦的幻景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生物时代’的门槛上。在这个时代,人将一步步实现其对自身组织的完全控制。”[1]而对自身组织和进化历程的完全控制则意味着科学技术在生命领域的祛魅(disenchantment),生命的神圣、珍贵与尊严都将遭受严重削弱,人的生命价值也将被重新定位,这对于人类价值系统特别是道德价值系统的冲击与影响可谓大矣。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寻求解决之道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看法。
一、在研究自由与伦理调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自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永恒话题,它不仅是最深刻的人性需要,也是达成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同样,研究自由作为科学活动的重要基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它促成了科技的进步、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提升和社会福祉的增进。“对科学研究关上大门,不仅会妨碍认识的积极积累,而且意味着会使我们在可能的灾难面前失去抵抗能力。”[2]故此,我们应坚决捍卫研究自由原则。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包括生命科学研究在内的当代科学研究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在与尘世隔绝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工作,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正如“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控制论》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为善和为恶的巨大可能性,因而,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不能脱离社会上的价值判断。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亦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显然,以尊重人、关心人为要旨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也应是自由的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违背这一点,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爱因斯坦曾深刻地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4](P73)“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4](p73)故而,作为科技活动的主体、和晰成果受益或受害者和社会价值拟定者的人类理应自觉地承担起责任,在尊重研究自由的同时,对科研活动进行必要的社会伦理调控,并使二者保持一定的平衡。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科学研究的自由,而是要反对以科学凌驾人文,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最终使科学技术朝着道德化方向良性发展。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同样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能性,例如,被称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实施,一方面推动了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带动了农业和医疗保健业的革命性变革,具有极为重大的科学、经济与社会价值;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难题,如基因治疗的道德风险、基因歧视与社会公正问题、基因资源的争夺与国际合作中的知情同意权问题等。
对此,我们既不能置之未闻,极其片面地强调科学家的所谓绝对自由认知权,也不应因噎废食,停止甚至彻底放弃生命科学研究。现实中,要尊重研究自由,因为作为思想自由之组成部分的研究自由,对于知识的积累与进步是不可或缺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包括人类基因组研究在内的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能增进个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福祉。具体操作中,唯一合理可取的做法是:在充分尊重科学家之研究自由的同时,切实加强对生命科学研究的社会伦理调控,并力争在二者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二、强化科学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意识
一般而言,责任是指与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相对应的职责,或指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而必须承担的过失。责任与知识或力量成正向对应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掌握着特定知识、技能与权力的人,由于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和社会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负更多的道德与社会责任,需要有特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其行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对人类已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那么,科学工作者是否应有特定的道德责任?科学家是屈从于政治的淫威、金钱的诱惑,还是应服从于社会良心和道德责任感的召唤来从事自己的科研计划?
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科学工作者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他们比之其他人能更及时、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知识的应用前景,因而他们有责任去预测、思考和评估科学技术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萨姆·施韦伯所说:“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突现的复杂性和新奇。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述,我们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5]
同样的道理,对于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医学技术开发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由于他们掌握了生命科学知识与技术,较一般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对他人和社会乃至自然界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无法保持价值中立,不管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可能后果作审慎的道德考虑。“虽然他除了设计自己的实验之外并不设计任何东西,但他能为企图作恶或在应用上有明显危害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的设计提供基础概念。”[6]只要他们的行为是本着自由意志,他们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就应负一定的道德责任。
事实上,有关生命科学研究人员的伦理责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基因工程研究初期的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伯格将猿猴病毒SV40DNA与大肠肝菌质粒DNA通过剪切后拼接在一起,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另一位生物学家普兰克提醒伯格:SV40具有致癌性,带有SV40的细菌大量增殖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伯格接受了普兰克的建议,停止了自己的研究。但是基因重组的研究并未停止,于是伯格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伯格信件”,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明了或未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前,应自动停止生产巨毒物质基因以及自然界尚不存在的抗药性组合的基因扩增实验,应当停止致癌基因的扩增实验。尽管后来的实践表明伯格信件对基因技术危险性估计过高,但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议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充分发挥伦理委员会的评判与监督作用
当今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科学工作者承受了过去无法设想的巨大的道德与社会责任。例如,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和不道德的使用,许多美国科学家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道德窘境之中,后来,在社会良知的感召下,科学家们组织成立了一个致力于将科学发现用于建设目标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并创办杂志探讨有关核武器等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一些社会与伦理问题。该组织有效地行使了对科研活动和科学家进行道德评判、舆论监督与价值导向的社会职能,起到了专业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作用。
同样,为保证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能沿着道德化方向有序发展,我们除须强调科学工作者的个体自律,努力提高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意识外,还要不断加强对生命科学研究的道德评判与舆论监督,建立健全专业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以便任何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计划都在事先经受一个由多学科组成的独立的、多元性的伦理委员会的评判。正如德国学者赖特所言,“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及其日益增长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使人们在许多方面对生物医学行为的意义产生疑问。……决定个人伦理责任的许多传统原则开始动摇,个人良知出现普遍的不确定性。于是人们呼吁建立伦理委员会并就相关问题立法。”[7](P104)
伦理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可使针对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医学技术运用的道德评判与监督成为一项贯穿于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全过程的有组织的常规性活动。伦理委员会应保持它的各个机构的透明度,并审慎评判,其成员不仅应有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更应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律师、宗教界人士以及代表社区文化价值观的非专业人士。伦理委员会应立足于伦理、法律和社会的观点来审视被提交的生命科学研究计划。具体说来,它应根据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对有关的研究行为和技术应用过程进行独立的伦理审查与道德评判,并对伦理原则的贯彻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督,以确保当代生命科学研究活动符合伦理原则的要求。目前,国际国内相继成立了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中国人类基因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对生命科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约束作用,但其所为还远远不够,如何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应有的作用显然是当务之急。
四、加强生命科学伦理的普及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90年代以来,在遗传学和生物医学专业领域及公众中,对生命科学研究所(可能)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就已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对生命科学技术之美好应用前景的神往与对该研究领域的潜在伦理风险的担忧赫然对立。在10余年的时间里,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各有关团体则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甚至组建了一些专门的委员会,以期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无疑从另一侧面说明,在当代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内,多么需要一种缜密、规范的伦理考量与道德定位。
然而,针对生命科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全新的伦理问题,迄今为止已有的伦理学却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恰如赖特所说的那样,“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物技术危机,而传统伦理道德非但不能缓解这种危机,反而受到它的腐蚀。”[7](P105)因此,有必要在反思传统伦理的基础上确立并普及一种以公正、尊重、行善、不伤害为基本原则的生命科学伦理学。这种生命科学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其道德目标是要尊重生命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自由,保障人类的尊严和平等,倡导人类和谐与国际合作,最终造福全人类,其现实课题则是从理论上探讨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医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并提出在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些新的行为方式时所应遵循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及规范。
面对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中不断涌现出的价值冲突与伦理难题,我们以为,或许只有籍凭这么一种生命科学伦理学的创立及其基本原则、规范的深入普及,才能真正化解研究中的伦理风险,实现当代生命科学研究造福全人类的崇高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