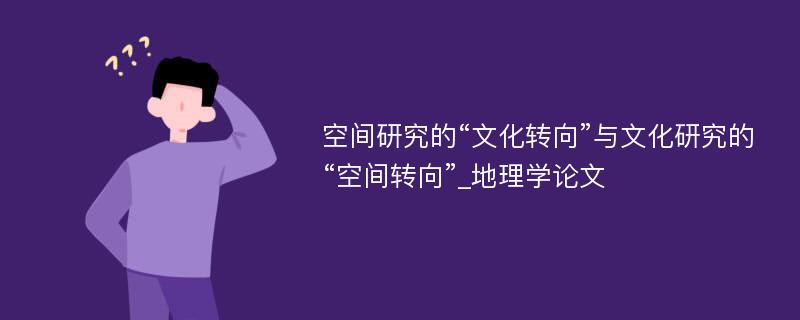
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08)08-0138-03
理论范式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演变而不断转变更新的。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科原有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逐渐失去其有效性,多途径的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去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以寻求合理的解释成为必然,这使得原来清晰的学科边界不断发生扩展和蔓延,各学科之间广泛地交叉融合,促成了学术范式的当代转型。
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倡导和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与既有的各种学科发生了粘连,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与日俱增地交叉渗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从文化的角度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成为各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和方法论基础。在这股大潮中,地理学的发展尤为突出,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关联运动”[1]。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著名的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就是“文化转向”。2004年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家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中,也用专门章节研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问题,认为当代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以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与考斯格罗夫首发先声,研究内容从传统的区域研究和空间分析转向解决现实性社会问题,提出要关注文化的生产运作、价值内涵与符号意义,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空间和地方的作用、文化政治、日常生活与消费等话题。
文化地理学的思想火花来源于16世纪的人类学。18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学家拉策尔的作品《人类地理学》的问世,开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先河,他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学说来分析不同文化之间为了生存和繁荣而互相竞争。这种文化领域的弱肉强食的思想有许多负面影响,与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有很大的联系,直接启发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以埃伦·塞坡尔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2]。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影响,地理学家索尔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提出解释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在他的带领下,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在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伯克利学派开始的[3]。
二战结束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在不断革新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50年代末,整个北美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地理学界先后掀起了“计量革命”,实证主义被广泛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的发展。60年代,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人文地理学产生了行为主义学派,开始对人的心理决策和行为认知进行研究。1976年,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上发表论文,以现象学、存在主义、理想主义为哲学基础,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4],把人的经验看作是有效的知识来源,注重从感应环境去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与地理学结合,出现了以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学理论,主张地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加以考察,把人文地理学研究引向了对阶级、财产关系、资本积累等深层机制的关注上,并开始用全球化的视角进行观察,为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工具。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文地理学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开始了对少数人群问题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地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兴起了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理解是新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对伯克利学派的文化概念的批评之上。新文化地理学认为伯克利学派预设了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代表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应该被扬弃。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视为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了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认为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3](P76)。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长期被忽略的具有不同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被纳入研究视野,许多被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空间场景(如少数族裔空间、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贫困者空间等等)成为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的重点。
爱德华·索亚的“空间三部曲”①堪称后现代地理学的经典著作。索亚主要致力于研究以洛杉矶为范例的当代后大都市如何从分散的城镇村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之一,以及在这种后现代空间重建过程中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揭示出当前城市重建的全球化浪潮是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的征服、边缘化和剥削,是由资本左右的、持续不断地对城市空间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其目的是为了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和经济的两极分化[5]。在研究中,索亚倡导理论界重新思考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将第三空间作为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表征或感知的空间)的本体论前提,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都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这两种空间概念,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索亚的研究中采用了语境分析和跨学科方法,展示出了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科,波及到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6]。
沙朗·佐京(S.Zukin)从另一个途径来勾勒后现代城市图景,把后现代城市描绘成日益商业化的新消费主义的场所。她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了这种文化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构性,以及它如何强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主流的社会科学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忽视了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佐京认为文化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佐京的研究深入发掘了空间维度的文化意义,使得都市空间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紧密联系[7]。
另一方面,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亦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它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关注各种空间议题,把以前给予时间、历史和社会的礼遇,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与空间相关的领域大量进入文化社会学科研究的主题,开始同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日益交叉渗透。
传统研究中,“空间”是实在的物理实体,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空间视为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客观容器,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的直观形式。19世纪以后,西方学界对时间予以了关注,认为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却把空间当作是刻板的、僵死的、非辩证的东西。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成是受条件限制的历史创造,对空间也缺乏重视和关照,使现代社会批评理论长期处于历史决定论的笼罩之下[5]。
20世纪20、30年代,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以芝加哥学派为开端,引入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成长的机制及其社会后果,研究为争夺有限资源发生的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分化过程及其伴随的城市文化问题。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标志着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书中列菲弗尔反对传统社会理论视空间为单纯、客观的物理空间,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认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空间由社会生产,同时也生产社会。一方面,空间是社会过程的结果,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每一个社会,每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间。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力量产生发展的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要素,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列菲弗尔在地理学及都市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思想使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受益匪浅。
1976年,福科发表题为《其他空间》的讲演,指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人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8]。在《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福柯更强调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力动作的基础。
空间、知识、权力的三位一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批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性的讨论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哈维在1990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讨论了后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空间问题。哈维认为“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像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9]后现代性是与“时空压缩”相关联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人与人工制品的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无地方性”都市环境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弗里德兰德和包登在《此刻在此:空间、时间与现代性》一文中也认为,后现代性改变了空间与时间的表现,并进而改变了人们经历与理解空间和时间的方式。后现代性是以即刻性和间距性为标志的,计算机、手机、电话等的发展使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与他人联络,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在场。人、事件、组织、全社会不再简单地与单一的地方或特定的时间相关联,空间和时间已经成了思考后现代性组织与意义的媒介[10]。
安东尼·吉登斯将后现代看成是高度现代性的阶段,而不是一个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阶段,不存在两者间突兀的转变。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认为“时空分延”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使空间与场所相脱离。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下,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被在时间一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取代,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的跨越的过程中被重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就是“时空分延”,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它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1]。
建筑与空间,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关键性纬度。以建筑艺术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上的民本主义,基本特征就是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空间是一种“超空间”,是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空间,它超越了个人身体和认知能力,被高度碎片化,并被加以多重符码化,伴随而来的现象是新的大众商业文化文本随意的、无原则地、充分地拆解了以往的一切,并把它们结合在新的整体性中。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里,人们的心灵经验和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支配着。这种都市空间的新形式,需要借助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即以当前的空间概念为基本依据的政治文化模式,来理解现代空间环境,恢复批判性意识。[12]
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这场跨学科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型。学者们对“文化”和“空间”的前所未有的重视,给文化研究注入了思想与阐释的新范式和新视野,有助于我们思考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当前社会是被空间化逻辑所主导的社会,通过空间结构的分析可以辨证地定义一般生产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介入生活、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和研究策略。
注释:
①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地理学》、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2000年出版的《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