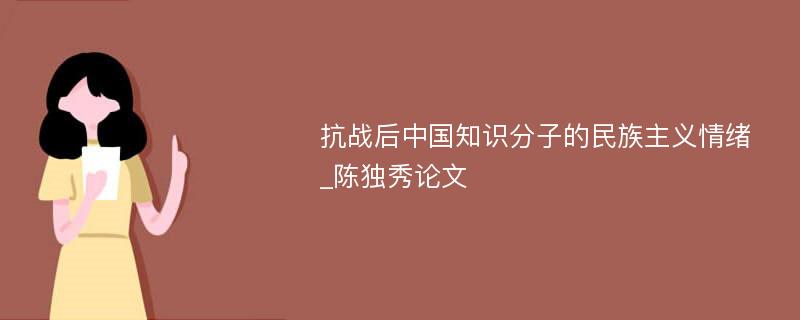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战后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内忧外患,创巨痛深。但是中国方面对于这种刺激的反应,上自九重之尊,下至黎民百姓,除了由曾国藩、李鸿章辈搞了一段时间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所谓“自强运动”,对创痛多少显示了一点迟钝的感觉之外,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以及“万国衣冠拜冕旒”一类昔日辉煌的回忆之中。其间一切改变都是被迫的。五口通商是被迫的,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是被迫的,甚至引进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按照当时国人的逻辑,但凡“奇技”,皆为“淫巧”,用之则不免坏了中国的道德人心。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以非常之举,实施全境对外开放。老沉持重的中国官吏们为此瞠目结舌,以为此乃致亡之道,窃喜自己继续紧闭大部分国门,未制订如此轻率的开放政策。
殊不知正是国门的一启一闭,拉开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湘淮陆军一溃千里,北洋水师葬身鱼腹。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重新安排了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使中国再次尝到了战败国的耻辱。大概近代以来中国多次打败仗,唯有此次才真正品出了屈辱的滋味。盖前此而来的列强如英吉利、法兰西等,或奉行“重商主义”,或看重基督教福音事业,虽以坚船利炮前来叩关,要皆不过胁迫中国“开放”。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斯时列强虽危害中国甚深,但却“不毁我宗庙社稷,不掠我领土人民”,中外兵刃相加之后,不过“金帛议和”而已,没有也不存在亡国之患。再说西方国家的底细中国人也实在弄不清楚,大概可以等同历史上乱华之“五胡”吧,与之交锋败阵,尚可用野蛮人的船炮厉害作自我解释。古代“文明史”上就有过汉族的王朝向“夷狄”俯首称臣的先例,因而虽惨遭失败,心理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
甲午之败则不同。此番不是败在西方列强手下,而是败在素来为中国人看不大起的“小日本”手下,因而产生了一种“辱莫大焉”的感觉。日本在30年前还只够得上中国的学生的资格,现在它能打败老师,一是靠变法,二是靠尚武,三是靠激发民族主义。17世纪日本的儒家学者山崎暗斋曾向弟子提出:如果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军攻打日本,日本的儒生应当怎么办。他并明确表示,如果发生如此不幸的灾难,希望弟子与他一道,武装抵抗,生擒孔孟,以报国恩[1]。 促使日本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将信仰和意识形态放在一旁的是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这是日本人所遵循的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在与日本人交战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察觉对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存在。而战败的奇耻大辱,终于将中国人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诚如时人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民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思想家、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福利爱所倡导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作为拿破仑发动大规模征服欧洲的侵略战争在政治思想上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固然没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 强调了“诸夏”与“夷狄”在制度上的文野差异。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认为能够“莅中国而抚四夷”[3],才算得上实现了王者的抱负。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夷夏之防”。不过,由于中国古人在地理上将中国等同于“天下”,加之“夷狄”环绕,四方来朝,周边没有真正能够征服中国的强敌,因而民族主义观念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也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4]。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之势,逐渐形成。1896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在经过社会政治学的重新包装之后开始传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中国知识界信奉的“天演”法则。亡国灭种的命运不仅为刚刚发生的割地赔款的事实证明并不虚幻,而且被“科学”揭示了所以会败亡的内在机理。这样,国运终于成为知识界首要关注的问题。以后几年里,中国的知识界精英投袂而起,发动了一场被后人称作“维新变法”的运动。其实这场运动的基本宗旨在于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口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会亡吗?“波兰分灭”是为前车之鉴。儒教会亡吗?耶教的咄咄逼人之势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并非杞忧。炎黄子孙会被斩尽杀绝或者会因种性羸弱而无法繁衍下去吗?中国人多达4亿, 显然是野蛮的西方列强想杀也杀不完的。但种性繁衍的优势要想保持殊非易事。近代国门初开之时,国人看见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无不视之为“蕃鬼”或“化外之民”,以为中国文明进化,在种性上便胜外人一筹。五口通商之后,各开放口岸仍严防金发碧眼的外国妇女进入,据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担心“蕃妇”前来“偷种”,使中国人从此失去种性上的优势。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曾设计出大规模移民巴西的计划,企图在南美洲去建立一个“新中国”,也是出于“保种”的考虑[5]。 由于爱国志士的大声疾呼,从乙未至庚子这五六年间,中国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萌发后的第一次救亡热潮。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是救亡图存,学习西方又被维新人士认定为救亡图存的基本路径,这就导致了西学的大量引进,国人亦因此以新的目光审视中西方文化,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优劣,从而使中国近代思想史出现了一段宣传民族主义与鼓吹西化并行的时期。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特别是经过被革命派人士称为“野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之后,“西化”加速,国人亦逐渐由仰慕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唯新是尚的程度。一时间,“西方”几乎成了“现代”的代名词,而且是越往西边走,就越接近“现代”。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生动记述了自己向西行的不同观感,颇具代表性:“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北美]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6]很快, 这种仰慕西方文化的心态便发展成一些现代西方学者称之为“反中国感”(Anti-chinesism)的心理情结。这在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明显的反映。谭嗣同是最早表露出这种“反中国”心理情结的思想家之一。面临清末社会的变局,他预感劫运将至;然而“劫象”却是通过比较国人与西人体貌看出来的:“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7]联想到国门初开,国人初见洋人,感到形容丑陋,鄙夷地称之为“蕃鬼”时的情形,其间感情的迁移,不可谓不大。逮至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批评更趋激烈。一般士人,稍稍耳食新学,则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8]。而中西学均有相当功底的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 李大钊、高一涵、吴虞等“新文化人”在这方面更是既开风气又为师,不仅起步较早,也走得较远。
鲁迅先生当新旧交替之顷,曾经在国内新式学堂和日本接受过近代教育,一生都在为破旧立新呐喊呼号。他的“反中国”情结集中反映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几乎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上。主张青年人多看外国书,少看或不看中国书[9],就是他这种态度的集中反映。 钱玄同少时尝参加义和团,民初在北京做教员时,却又加入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天主教。他的房间里还供有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或问其改信宗教的原因,他回答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10]由于信仰对象的转移,钱玄同的中西文化观亦发生变化,后来更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发展到连中国文字也主张废除的地步。陈独秀思想激越,不减鲁、钱,他的“反中国”情结主要反映在他就“爱国”所发表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上。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曾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就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爱国”口号,作了一番“理性的讨论”。半年以后,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学生踊跃参与,他又写了《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一文,再次对“爱国”口号提出商榷。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11]对于“国粹”,陈独秀亦持极端蔑视的态度,主张一概打倒。他甚至对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武打也十分反感,斥之为“乱打”,认为它“暴露了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12]。胡适沾庚款办学的光,赴美留学7年, 两个世界的观感在其头脑中形成的反差较之仅仅去了一趟“东洋”的鲁迅、陈独秀不用说更为强烈。他曾经坦率地承认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13],进而以此为理论张本,于20年代末,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对于本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胡适在大多数时间里均表现出一种冷静甚至超然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当国人义奋填膺谴责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时,他却表示说,中国面临困境,是由于“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的缘故。不久,“中国不亡,世无天理”[14]这句激愤的言词,也就脱口而出了。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新文化人”会具有如此激烈的“反中国”情结呢?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反中国”,乃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良心所做出的反省与自责,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自省的民族主义”,可以归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路径。既然要改造国民性,当然就要与造就了这种国民性的传统决裂,这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逻辑。
这样认识问题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却存在着将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思想及其表现形态简单化的嫌疑。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是近代社会造就出来的一个思想异常复杂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言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反省与自责,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思想追求,看到他们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组思想政治范畴的选择上犹豫彷徨、不知所从的困惑。认识这种困惑,是解析“新文化人”何以“反中国”的关键。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大同”的社会理想,19世纪末,国难当头之际,受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权衡轻重缓急,他们尚能将现实的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将“大同”理想的实施置诸遥远的未来。康有为写了《大同书》,秘不示人,而将救亡图存视为急务,即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中国知识界广泛服膺的时代,民族主义也是一种不难作出的抉择。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对作为西方近代思潮之一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灾难的思想政治根源。作为正在迅速膨胀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开始在欧美社会流行,并伴随着众多思潮一起传入中国。陈独秀、胡适等人以其对世界政治思想潮流流向变化的敏感把握,很快接受了这一新的主义。
既然受了“世界主义”影响,也就不能不与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下,陈、胡等人对“国家”观念提出了批评。陈独秀认为,人类生活本来是没有什么天然界限的,所谓“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认为国家的形成,无异在人类本来互相亲善的情感上,挖了一道深沟,砌了一道屏障,结果“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15]。与陈独秀思想十分接近的李大钊也颇不以“国家”为然。他认为人类进化是沿着“世界大同的通衢”向前行进的,预言世界人类的“大联合”,终将“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6]理想终将成为现实。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曾加入基督教,并一度加入费城世界主义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年会的代表之一。受这段经历的影响,胡适也曾给人留下“世界主义”关怀更甚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印象。他在1916年10月写道:“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葛得宏·斯密斯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17]在国家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时,胡适所持“不争”立场,与他所信奉的“世界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陈、胡等人领风气之先,他们倡言“世界主义”时,在西方已经开始退潮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尚呈涨潮之势,他们反其道而行,颇显出特立独行的思想品性。但他们并不是为区别于他人而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他们对“世界主义”是真正服膺的,这就使他们在理性上很难接受“民族主义”,在行为上也每每表现出超越的姿态。但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的民族主义关怀却是无法掩饰的。
在日本就“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胡适这样写道:“昨夜竟夕不眠,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能睡。五时起,下山买西雷寇晨报读之。徐步上山,立铁桥上,下视桥下……忽然有感,念老子以水喻不争,大有至理……‘上善莫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者’……以石与水抗,苟假以时日,水终胜石耳。”[18]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已经到了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地步,你能说这位“世界主义者”真的不爱国吗?昔孟子尝与淳于髡就天下沦陷应当援之以“道”还是援之以“手”作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讨论,这位“亚圣”是反对像“嫂溺”而援之以“手”那样去拯救天下的[19]。孟子与淳于髡的分歧不在于“援”还是“不援”,而在于怎样“援”。其实胡适与他的留学生同伴以及大多数同胞的分歧也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不是“争”还是“不争”,而是怎样争的问题。显然,他是主张“援”中国以“道”的,而他此时认准的“道”就是“世界主义”以及他认为奉行了这一主义的“国联”会对日本侵略行为加以干预。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批评胡适这一书生之见的迂腐和无济于事,但他的民族主义关怀,情发乎衷,溢于言表,他自己掩饰不了,别人也没有办法加以否定。正因为在他的情感和潜意识深处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怀,所以当1936年7 月他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时,他最终放弃了他崇奉了二十余年的世界主义,由“不争”转而“力争”,就是充当被后人讥讽的“过河卒子”,也义无反顾,在所不辞。
与胡适一样,陈独秀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时,尽管存在着意识层面理性的抑制,但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仍然时有流露。他向往世界大同,但是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他的“世界主义”理想也可以同信奉同一主义的康有为一样,暂时让位于民族主义。不过,也许是已经意识到了其间隐含的矛盾,陈独秀在价值判断上巧妙地采取了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折两分的做法。于是民族主义也就变成了扩张侵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自卫的民族主义两种。前面我们引述了他反对“爱国”的激烈言辞,这些言辞大多发表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之时,揆诸本意,显然并不是要反对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要谴责日本人近乎疯狂的民族主义躁动。因而在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他明确表示,“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民族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族生存,也没有什么罪恶”[20]。“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家金瓯残缺,山河破碎,陈独秀感时伤事,以《金粉泪》为题,写出七绝诗一组共56首,对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人以及沉醉于“六朝金粉”繁华古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抒发了自己的一片爱国之情。其中一首写道:“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依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度辽。”此时陈独秀已身陷囹圉,却将个人遭遇完全置之度外,所思所念,悉在国运,忧国之情,见诸梦寐,以致后来国民党政府在释放他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爱国情殷”[21]。
不过,也应当看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毕竟是两个对立的政治思想范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宗奉这两种主义,因而与陈独秀、胡适一样,所有服膺了“世界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尚存在民族主义的关怀的话,他们的民族主义大都只能表现为一种本能,潜藏于意识之下,对其思想政治行为起着某种支配作用。他们说不出何以如此行事,但却非这样做不可。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了,表现了他们忱挚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理智却告诉他们在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上泛滥成灾的现实情况下,与其出来唱慷慨激昂的“爱国歌”,不如对着头脑发热的人们泼点冷水,唱几句反调。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或先后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行为,两种政治行为的“作用当量”不可避免会因互诋而有所减弱,这应当不必讳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的伙伴及同胞对他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说这些批评并非全在理上,恐怕也同样不无道理。
除了游移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外,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难选择,也是造成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时而发爱国之幽情,时而哼“反中国”曲调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近代国人谋求的民族自立之道,曾被学者概括为“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曲。这大抵是不错的。但是“变奏曲”老是成不了“协奏曲”,其间的原因,颇值得深思。近代以来将两者奏出了相对和谐音调的恐怕只有戊戌前短暂的几年。斯时康有为辈通过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如议会制)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以及带有折衷色彩的君主立宪政治选择,化解了本来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紧张。不幸的是,戊戌政变以及庚子以后国人政治思想的激进化,将或许可以同时承担“救亡”和“启蒙”双重任务、具有中国传统中庸特色的变革路径切断了。作为激进化的一种表现,20世纪头20年,所谓“启蒙”,就是要宣传西方近代科学民主。传统中国的一切,均被视为封建专制时代产生并且只能为封建专制时代服务的“作品”,放在要打倒的位置。然而,被赋予了“救亡”重任的民族主义却不容许对自己民族既有的一切持如此轻率的否定态度。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自我认同的,而且是排他的,它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对于民族文化与民族声望的关怀”[22]。从走向上讲,民主主义是西向的,民族主义却是东向的。同时肩负了救亡、启蒙双重重任的激进的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胡适曾经将这种“两难”表述为是选择袁世凯还是威尔逊的问题。他在1917年3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王壬秋死矣。 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予妇书云:‘彼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吾尝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记此则以自赎。 ”[23]王壬秋乃儒学耆宿,精于帝王之学,汉满之见甚深,所谓“去无道而就有道”或许有站在汉民族立场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未必真如胡适之所诠释者。但胡适的这番话却无疑道出了晚王壬秋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双向选择上的困惑。
这种困惑又因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被人为地混淆而变得更加难得其解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同义语。前者可以界定为一种基于民族的同一性而产生的旨在促进社会生活一体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后者则是处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群人(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特征,一种情感的表露。对于近代民族国家而言,“国”与“民族”的界限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难划分,因而这两种主义每每被人混淆。尤为紧要的是,“国”尚存在着政治学含义上的“国”与地理、文化及社会学含义上的“国”的区别。前者大约相当于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国家(state),实乃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 也就是“政府”;后者则类似于祖国、宗国(motherland),亦即共同的地域及其所负载的除却政治制度之外的一切。在近代中国,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往往使人不知所从,人们对这种“国家”的感情也很容易发生转移。周作人回忆录记述了这样一种现象:清末一度使人肃然起敬的“国旗”黄龙旗,“式样并不难看”,但到民国建立、五色旗升起之后,人们意识到它“是代表满清势力的”,感情迁移,好恶变化,便觉得黄龙旗上画的龙“有些简直像一条死鳗”[24]。这很能说明国人“爱国”的旨趣及其转移的原因所在。在国家政权更迭不已的近代晚期,老百姓的“爱国”往往限于热爱祖国,当然也可能包括有政治的含义(如果他认同了某种政治的话);而统治者宣传的“爱国”则偏重于要老百姓拥护自己控制的国家政权。
由封建统治者倡导的“爱国”与中国传统的“民主主义”及近代民主思潮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清季以来,一些眼光锐利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1903年,举国上下庆祝慈禧太后万寿,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以为“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因试编《爱民歌》与之相对:“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使高唱《爱国歌》为慈禧祝寿的官民人等惊愕不已[25]。逮至民国初年,曾经被辜鸿铭揭示的“爱国”与“爱民”的矛盾被进一步揭示出来。陈独秀在“理性的讨论”爱国的思想行为时就发现,所谓“爱国”,至少可以区分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的”“爱国”以及官方“下令”劝导的“爱国”等若干种表现形态。他还发现,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作搜括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正是有鉴于此,陈独秀才对当时的“爱国”宣传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有时甚至出来唱几句反调。胡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18年6 月所作《你莫忘记》一诗, 借一位父亲临终前给儿子所写遗嘱, 控诉父亲过去20年教儿子所爱的“国家”的种种罪恶,宣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这位被假托的“父亲”所希望“亡”的“国”,显然是特指当时的军阀政权。
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反对笼而统之的“爱国”口号,并不表明他们不爱国。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言,“自然”的爱国心,“古今中外稍具天良者”,皆能有之,不必劳未必真正爱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军阀们去费心“发扬”。周明之先生在分析胡适《你莫忘记》一诗时认为,“胡适在此彻底否定了中国政府及其合法性”[26],可谓知胡适者。陈、胡等人的真实命意,是不想让军阀政府“爱国”的宣传妨碍了近代民主主义的实施,这是陈、胡等新文化人政治思想的价值所在。然而当其在“爱国”问题上与军阀政府作对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在列强入侵肆其暴虐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即便如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否与国民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信守“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等人,在面对这一难题时,甚至不惜暂时牺牲民主主义的追求而将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寻求与袁世凯之类的统治者“合作”,去尝试实施“开明专制”。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当然不屑于这样做。但在潜意识的层面这两类知识分子是靠得很近的,故胡适才会有不忍弃父母之邦的表示。他写道:“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吾亦未尝无私……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27]不过,“为宗国讳”与追求近代民主之间的分寸殊难把握,胡适等人在面临这一问题时常怀投鼠忌器的担忧,因而其言论及行为方式往往出现前后不能协调,甚至自相矛盾之处。研究胡适以及这一时期与统治者在“爱国”问题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甲午以后中国面临自有明以来数百年所未曾经历的巨大变局。历史的遗传性状,现实的致变因素,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情感的,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代异常杰出而又异常复杂的知识分子。处在变化的中国社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变化的;处在复杂的中国社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这给后来的人认识他们造成了某种困难。显然,“单线性”的思维方式将不可能认知复杂的社会造就出来的如同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近乎诡谲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近代社会固然也出现了几个丧失了个人良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读书人,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是真诚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在清朝封建政权和北洋政府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愿意附和着去呼喊几句简单的“爱国”口号,是因为他们肩负着历史赋予的推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民主主义的重大使命;在民族主义从一种思潮的鼓动发展成一场社会运动时,他们在情感上顺从它,但又努力在理智上超越它,这是因为他们几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利剑,既可以自卫,又足以自戕。他们不满足于普通层次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要进一步谋求爱国之道。他们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选择上表现得有些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而企图谋求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地。这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愈显示出它的可贵。1916年9月,身在美国的胡适因忧国而作了一首白话小诗, 暗示了爱国也有如何爱的问题。他写道:“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28]能读懂这首小诗者,庶几能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之心曲矣。
注释:
[1]查常平《日本历史的逻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0页。
[2]《论语·八佾》。
[3]《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梁惠王上》。
[4]梁启超对这一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是由于“天下”观念在作梗。因为“国家”乃是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概念,所谓“对外族而知有国家”是也。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则无所谓国家。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中国即“天下”(世界),“天下”亦即中国,这种观念阻碍了国家思想的形成。梁启超谈道:“(中国周边)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5]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33—34页。
[6]《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4页。
[7]《仁学》卷下,《谭嗣同文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194页。
[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一卷44页。
[9]鲁迅《青年人必读书》,《鲁迅全集》,第三卷12页。
[10][24]周作人《苦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1 页、257页。
[11]《独秀文存》卷2,“随感录”,80页。
[12]《独秀文存》卷3,210页。
[13]《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48页。
[14]《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期;《胡适的日记》,1933年3月2日。
[15]《偶像破坏论》、《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独秀文存》卷1,229页;卷2,81页。
[16]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12期。
[17][18][26][27]《胡适作品集》183页、第33册56页、121页、第35册60页,转引自(美)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
[19]《孟子·离娄上》。
[20]《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卷1。
[21]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81、201页。
[22]张晓刚《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64页。 引文系作者转述的马克斯·韦伯就民族主义所作的论述。
[23]《胡适作品集》第37册191页。 胡适在其自传中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是其对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内在矛盾的另一种表述。他并不反对五四运动,但却为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性质深感遗憾,这说明了他心中的困惑。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3—189页。
[25]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见《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17页。
[28]胡适日记,1916年9月6日。转引自罗志田《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31页。
标签: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民族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爱国歌论文; 历史论文; 甲午年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