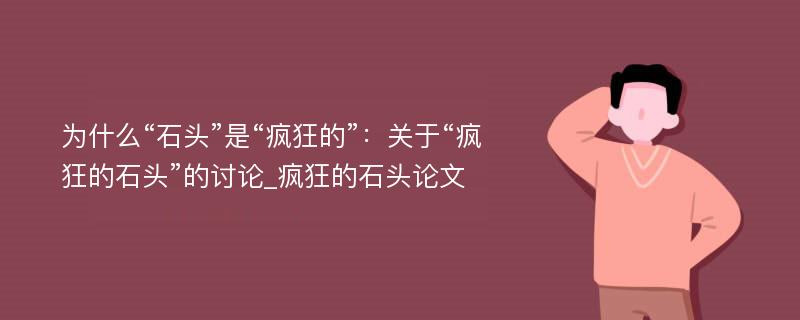
“石头”何以“疯狂”:关于《疯狂的石头》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头论文,疯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一群并非天王巨星级的演员,区区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却创造了石破天惊的票房成绩,真可谓点石成金,一石激起千层浪,石头果真疯了。围绕影片《疯狂的石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们在李今教授的指导下,利用掌握的文化研究理论,对该片的娱乐性以及隐藏在娱乐背后的表征和隐喻特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做了有别于专业影评家的新颖解读。
一、立足于大众的娱乐性
一部电影成功与否,观众心中有杆秤,票房则是最直观的指示剂,从这方面讲,《疯狂的石头》无疑是成功的;而其之所以能够抓住观众,则首先根源于其立足大众的娱乐性。
厌倦了矫情的说教与造作的煽情,对恣肆汪洋的电脑特技也已经审美疲劳,平时绷紧了神经的观众掏钱进影院,要的就是全身心的放松,花钱买的就是乐;可以说,一个“乐”字充当了影片成功的急先锋。
李今教授在《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上为我们介绍了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成为在此进行阐释和解读的利器。霍尔认为,“意义的获得”有赖两个过程,第一,作者通过建构将意义置于符号之中,第二,读者对这些符号进行解码而获得意义。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一点上与作者同样重要,从任何有用的角度来说,未被消化的接受和解释的各种符号都不是“有意义的”。电影的呈现也是一种符号。《疯狂的石头》是成功的,它的娱乐性立足平民,因而能够很顺利地被观众“解码”,使观众在会心一笑中真正从心底理解并接受。
第一,以重庆话为主体的大众化的语言。
在讨论中,大家都不约而同意识到了重庆方言在影片成功中的作用。来自成都的吴自强同学显然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指出,包括重庆方言在内的四川方言整体上属于北方语系,使用重庆方言能够保证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听得懂,满足了“解码”的基本要求;同时四川方言很早就走出盆地,在历史上很多影视喜剧中充当主要语言,例如《抓壮丁》、《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等,都曾在全国观众中产生较大影响,观众们都已有了欣赏以四川方言表演的喜剧的习惯。
事实上,近年来方言影视、曲艺剧目颇为走红。赵本山、潘长江等人的浓重的东北口音的小品业已成为春晚一道必备菜,以东北农家、市民生活为背景的东北味儿电视剧又风靡全国,雪村那句“翠花上酸菜”从东北一直唱到江南;前两年冯巩以天津卫的方言排演的喜剧电影《没事偷着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也深受观众喜爱。即使是冯小刚、张艺谋等大牌导演拍摄的所谓大片里,也不时有操方言的角色,调和一下全剧的口味。这一点也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齐有波同学的分析颇为透彻。他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不同地区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外地定居,面对一个有异于自己故乡的陌生环境,在影视剧中偶然听到家乡话或者类似家乡话的口音,会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同时,日渐剧烈的城市化越来越多地将人们从土地剥离,几千年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积淀的乡土文化心灵结构,也很容易被有着淳朴乡土气息的方言所激起。第二,单纯从语言的角度看,与方言相对的普通话,是在长期以来被定为官话的北京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既定为官话,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就必然会对其中相对粗俗但生活气息丰富、幽默诙谐的话语成分删削掉。重庆因地理的原因在历史上与中原相对隔绝,保存就比较多,尤其一些粗话,荤而不脏,幽默诙谐,我们在《疯狂的石头》中可以很直观地感觉到这种相对原生态的生活语言对感官的冲击力。而且由于这种语言观众听得懂但又不全懂,便如雾里看花,造成一种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理解的张力,有一种相对朦胧的美感,经得起观众回味。
第二,大众化的叙事方式。
你尽可以说《疯狂的石头》在表现手法上的前卫性,但他的叙事方式却并没有脱离大众的基本口味与套路。如今的时代,创新是顶时髦的词眼,但一味求新却也容易陷入窠臼,在影视界便表现为生产了一批与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不相符的所谓大片。创新是要立足于实际的。《疯狂的石头》在这一点上处理的就不错。
匪盗故事在中国的文学叙述、影视拍摄中一直颇受青睐,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题材。最负盛名的如《水浒传》,《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自不必说,即使一些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作品也有“盗”的一席之地。影视剧中此类题材更是不可胜计。《疯狂的石头》以对翡翠原石的“盗”与“反盗”为基本线索和故事框架,显然摸准了观众审美的先验心理结构,有助于观众的接受。
以匪盗故事为线,很容易便可以将人物分为盗与守两派,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塑造与观众的欣赏。中国的文学作品、影视剧习惯于将人物分为截然的两个阵营,从身份上分为贵与贱,从伦理上分为善与恶,从道义上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等等。对此,赵菁同学的论述显然颇具匠心,她甚至由此联想到了近来再度成为热点的红色经典:影片中的人物基本分为两派——好人、坏人,围绕一个宝贝展开激烈的争夺;最后,好人当然在历经险阻之后完成“护宝”的任务,坏人则一败涂地,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很类似于五六十年代以“三红一青”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最常使用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此模式的继承。
故事的发展情节曲折,扑朔迷离,但最终也没有背离中国式叙事的结局模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不少批评家对中国文学中存在的这种大团圆结局的传统颇为不满,以为此背后隐藏的是作家乃至整个民族痛感的缺失,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此一说法有道理,但不全面。大团圆的结局,可以看作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对于幸福的渴望与诉求,根源恰恰在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经历、民族心理;持此论者所持的标准是西方式的,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未免有些生硬,而实践上影响似也不大,对于读者、观众的审美趣味更是影响甚微——观众喜欢看的,还在于喜乐团圆。对此,来自外国语学院的张莹同学深为认可。她认为,影片的结尾,包世宏将真的翡翠给了那位善良淳朴的女友,让人感受到疯狂之外的真实的温情,与前面的搞笑、疯狂相得益彰,错落有致,对于常年生活于紧张、压力之中,厌倦了生活中的丑陋、欺骗的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还往往安排某一戏份不算轻的人物,充当插科打诨的“小丑”角色,例如《说岳全传》中的牛皋,《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八戒等等,这在西方文学中也有以呼应,称为“福斯塔夫式的人物”,有助于“造笑”,同时也可以缓和情节的紧张气氛。影视剧中这样的人物也颇为常见,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天地男儿》中的警员“三条四”、欧阳老师等等,深受观众喜爱。这种人物一般说话一愣一愣,做事鲁莽,大部分IQ略低,说话、行事有异常人,晕头虎脑,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逻辑,在不合适的时机、场所说一些不合适的话,做一些不合适的事,在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中营造一中幽默的氛围,令人忍俊不禁。《疯狂的石头》中扮演此一角色的是“黑皮”。此君操着浓重的鲁中口音①,袖子里总藏了一个榔头,说话做事“一愣一愣”的,动不动就要拿出榔头,砸了就跑。在信息化、自动化的今天,此君居然还试图使用这种原始的工具不假思索进行盗窃,本身便显得不合时宜,滑稽得够劲儿。
性与暴力是商业片制作的两大要素,《疯狂的石头》并不能免俗,但与时下的一般商业片制作相比,并不出格。暴力的描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并不被强烈排斥,读者并不排斥,甚至可以上升为所谓“暴力美学”;情色的、性的倒一直排斥于主流之外,不过近年来也有所变化,如今,绝对的洁本恐怕也难以为大众所接受,就如《林海雪原》这样的红色经典,为照顾普通读者的口味,也会加入诸如“蝴蝶迷”之类“擦边”的性的描写。况且,如果说五十年前对于稍有过火的男女亲热场面要捂住眼睛不看的话,恐怕如今都没法睁着眼睛在大街上走路了。暴力与性不值得提倡,但的确可以刺激观众引起感官的快感,为观众喜爱而成为影视剧的卖点,对此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加以制止,有其存在的逻辑。
影片不仅在叙事结构上颇合大众的口味,其笑料也多源自民间,大部分直接源于当下生活中流行的幽默元素。例如影片中秦秘书对冯懂的肉麻拍马,谢小萌装瘸子欺骗老爸,奸商作梗致使麦克功亏一篑等等,包括令人喷饭的一些经典造笑语言,例如“共公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侮辱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等等。另外某些严肃的话语被用在完全相反的语境中,通常会显得相当滑稽,营造特殊的幽默效果,例如盗哥称盗窃为“事业”,偷翡翠为“项目”,小军听到盗哥欲以谢小萌为要挟逼其父交出翡翠,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绑票啊,咱不专业啊!”这种亲民性使笑料从制作方对观众进行投掷时,不会突兀,而是自然渗透,使观众能轻容地接受。
与此相应,影片选区的场景,也颇为大众化,富于生活气息,对此刘波、罗晶等同学都有提及。全剧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传统企业的自救故事展开,其间各种矛盾交织,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制造了独特的娱乐效果;重庆,建国以来国家的重点工业基地之一,国有工业企业多,职工多,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生活和传统企业出现的问题在这里有着集中的复杂的表现,很好地支撑了影片的叙事与情节的展开。围绕这块翡翠原石,各个阶层、各种生存状态下的人物纷纷出场,极富现场感与真实感——改革开放里凭借不正当手段起家的流氓商人和哈叭狗腿子,在经济浪潮里濒临破产的传统企业厂长、职工,蟊贼与国际大盗,因生活所迫痴迷中奖的小市民,挂着艺术的幌子每天吃喝玩乐骗钱泡妞的浪荡子,当然,也有包世宏这样尽职守法的“蔫狠男人”以及他的女友那样的纯真女子。影片的主线是翡翠的“盗”与“反盗”,围绕这一主线还纠缠了许多其他的叙事,诸如权钱交易,社会上相当普遍的中彩票心里,小市民生活的艰难,以及形形色色的偷与骗,等等。这一些都深为观众所熟悉,笑过之后,不妨对号入座,嬉笑怒骂、个中滋味我自心知,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二、立足大众,但不囿于此,用一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以求平中见奇,朴中见色
如果说《疯狂的石头》对传统的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借鉴帮助观众顺利“解码”,帮助观众迅速“入戏”的话,那么其利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对传统叙事元素的超越,则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力和新鲜感。
影片的题材是传统的匪盗故事,但此匪盗却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的匪盗。在一般的文学叙述中,匪盗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另一类则可称之为侠盗义盗,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前者通常是狭义公案小说、警匪片中的反面人物,是为了衬托正面的大侠、警探的英武无敌的;后者则多多被叙述为因各种原因逼上梁山的好汉,在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影片中出尽风头,例如周润发领衔的《纵横四海》、《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等,至今依然颇受制片人、观众青睐。《疯狂的石头》中的道哥、麦克等人,所做依然是不乏暴力的诈骗、偷窃之事,但经过了影片的喜剧化包装,并非十恶不赦的罪犯形象:黑皮动不动就要拿出榔头“直接抢不就行了么,费那些事干嘛”,“一榔头砸开拿了就跑谁撵上了啊”,这哥们儿真是实在得可以、可爱,当盗贼也讲“素质”“诚信”“王法”“道德”,甚至请律师的时候,令人觉得滑稽十足,消弭了传统影视作品中偷盗场面的窒息、紧张气氛,令人耳目一新。《疯狂的石头》影片中的贼,不是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同时对于港台匪盗片中的义盗、侠盗也是一种颠覆。齐有波同学对此有十分细致的观察。放在一般港台的匪盗片中,像麦克这样身手不凡的国际大盗,定当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但影片却着意让这位大盗硬生生栽倒在三个土贼和一个学侦查出身半路出家的普通保安身上,再联系到这位先生开头是如何地意气风发、酷劲十足、信心爆棚,那种强烈的讽刺和幽默效果便跃然而出了。
另一方面,看守与匪盗之间,也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在我们的印象中,看守与小偷之间应该是一种严肃的甚至令人窒息的对立关系,但在该片中,却刻意被安排在隔壁房间,相互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刚刚还追个你死我活,马上就在澡堂子相逢而不相识。这是一种十分怪异的对立方式,双方互不相识,甚至直到最后,守方代表包世宏都不知道小偷是谁,自负无敌的麦克直到最后才知道,被自己杀死的原来就是自己的雇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恶搞,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恶搞,用夸张的手法着力展示社会生活荒诞的一面。刘彦欣同学应用施莱格尔兄弟提出的“戏剧反讽理论”对此进行了解读,“戏剧中存在着观众已知而剧中人未晓的情节”,这是表演的戏剧可以做到而静止的文本做不到的地方:第一,剧中围绕翡翠原石的几方都不知道翡翠的真假,所以认真地争夺,也因为其不知使情节戏剧性发展;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人物关系,盗与反盗双方互不相识,观众都对此看的一清二楚,因而能为其行为大乐。通过这种戏剧反讽增加了电影文本的独特魅力。
对传统经典的反拨,或称为恶搞。一些经典的影片、艺术节目会在观众心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当他们以完全陌生化的方式出现的时候,观众往往会因其荒诞性而忍俊不禁:一帮姿容不慎秀丽的男女排演千手观音,小军穿上一身并不合体的夜行衣,戏谑地称自己为蝙蝠侠,嘲笑掉在半空中的麦克“蜘蛛侠呀,够专业呀!”。张志勇同学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对于电影经典场景的戏仿,例如希区柯克《后窗》里把人装进大旅行箱,《肖申克的救赎》里在地道中的爬行,只不过这些都加入了十足的笑料,更增加了幽默诙谐的效果。
三、娱乐背后的深层象征与隐喻
李今教授充分肯定了同学们对于影片娱乐性的讨论,并引导大家透过现象挖掘其背后的深层象征与隐喻。她指出,《疯狂的石头》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影片。从情节结构来讲,作者编织了三组冲突线索,它们代表了几组对立的社会关系。1、兵与贼,以保卫科长包世宏为首,为保护能换来工人工资的翡翠与道哥三人盗窃团和国际大盗麦克之间的较量;2、觊觎翡翠的两方盗窃势力洋贼和土贼之间的冲突;3、凌驾前两组矛盾之上的港商冯董和厂长的权钱交易。最终港商通过贿赂厂长,买到了这块能为他带来一本万利的土地,使前几组兵与贼、土贼和洋贼的争斗变得毫无意义。至此,土贼与洋贼之于厂长与港商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后者是贼中之贼。
在这样一个大的隐喻结构之下,再来分析《疯狂的石头》的概念世界同样会发现其隐喻的性质。《疯狂的石头》的概念世界呈现出与文化价值的习惯意义,言说的习惯方法颠倒错置的特点。由此,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如贼的文化习惯形象,本来所指的是人中渣滓、破坏法律、没有礼义廉耻的概念意义,但道哥把自己的偷盗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事业”,偷窃翡翠行为是“项目”,还一再强调他们这个团队人员的“素质”,“专业”,甚至麦克也打出“诚信”的招牌……,这些在经济改革,引进外资的大背景下频频出现的热门词语被挂在“贼”的嘴上,从这种颠倒错置本身就可以阅读出对前面所说的大的隐喻结构进一步细化编织的旨意。
再如上面提到的麦克。从麦克专业的盗窃手段、敏捷的盗窃身手以及派出所听闻麦克潜入之后如临大敌的情状看,他应该是一个名声在外的著名惯盗,但最终却输在两个半土贼手中(本来是三个,但那时候黑皮被困在下水道里,只能算半个),实际上也是一种隐喻:不谙游戏规则,迷信专业技术在时下的社会只能碰个灰头土脸。
电影的题目中“疯狂”二字,也有隐喻的含义。疯狂的并非石头,也绝非与石头发生直接关系的包世宏们和道哥们冯董们,更是转型期社会一种近乎癫狂状态的隐喻和夸张反映。三宝仅仅从厕所捡到一个写有特奖的易拉罐环,就轻信地跑到北京领奖,并不是三宝没脑子,反映的却是社会上一种近乎癫狂的中彩心理。这种心理并非只是一种巴望天上掉馅儿饼的发财心思,看看三宝在棚户区破落拥挤的家,真真正正是“穷疯了”。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人的心理与性格存在多种可能性,置于特定的环境中,会产生特定的行为。对于影片中反应的癫狂躁动,显然不能简单视之,更应拨开这层外衣,去探寻其中隐喻的深层根源。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本或符号系统,《疯狂的石头》经常通过不断的重复手段,将大量的充满社会内容的场景、物品、人物贯穿动作等提升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如“厕所”,是保卫人员和小偷们不断出入,不断在此发泄、糟蹋和祸害的一个场所,一句“我们这也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抗议,使厕所这一场景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的某些具有类似性质的现象,各种不负责任的开发,污染,贻害的行为。
再如,“翡翠”在《疯狂的石头》中是启动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动机目的,其象征意义也是显然的。在具体的土贼、洋贼和权钱组合的权力“窃国”的隐喻中,赋予“翡翠”以国有资源的隐喻也是顺理成章的。
小偷三人团伙在作案现场关公、金刚塑像的一再闪回衬托下,很容易让人想到桃园三结义、梁山好汉在现代的境遇。黑皮一直重复说着一句话:“费那事干嘛?砸了就跑,谁能追得上?最后,他因在地沟里出不来,饿极了,终于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抢了面包就跑,从偷到公开地抢劫。从黑皮这一贯穿动作,似乎可以读出“人们被逼急了,会铤而走险的”警告。道哥的下场,也属于同类性质,最终用暴力抢夺翡翠,惨死轮下。
《疯狂的石头》主人公包世宏小便不通的病痛,同样是一种社会病症的象征,最终影片的“光明尾巴”:包世宏在上台领奖的召唤中,欣喜若狂地体验着畅快屙尿的快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创人员在对不满的现实恶谑、恶嘲、恶讽进行了一番“恶搞”之后,痛快淋漓的姿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疯狂的石头》赋予重庆某工厂改革开放中的社会现实以负面价值,根据表征的构成主义理论,我们所应发问的,并不是它扭曲了还是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的问题,而是它涉及或针对的是谁,为谁代言,以及赋予人物、行为、现实以什么意义的问题。《疯狂的石头》显然针对的是那些打着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搞活经济的旗号,而行“窃国”之实的腐败分子和国际资本,是为那些在改革中“下岗”,被砸了饭碗,“早死早超生”的弱势群体代言,正是这样的平民立场,使作者建构了与改革开放的主流话语之外的另一种话语体系,并以民间的智慧和方式对他们眼中改革开放的弊端、于狂欢中进行了插科打诨地调笑和亵渎。
搞笑的喜剧不能承受严肃分析之重,“石头”也不会一直“疯狂”下去。但在笑过之后,再来解码《石头》的内涵意义,会使我们在开怀大笑之后,再进一步共享它严肃的主题意蕴。
注释:
①不少评论以为黑皮讲的是胶东话,笔者却以为应是鲁中地方口音,因其与笔者一来自山东省潍坊地区的朋友说话语调、音位、音素相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