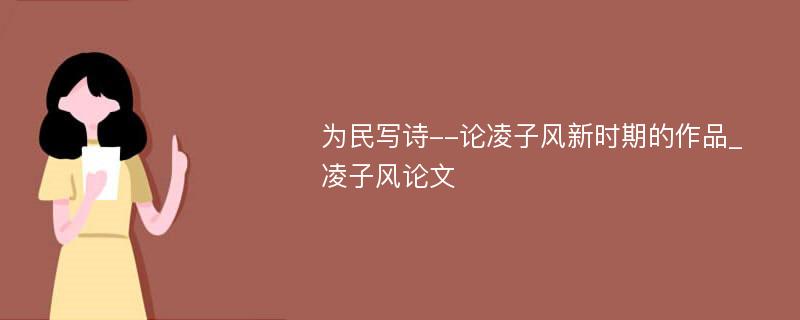
为平民作诗:凌子风新时期作品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平民论文,作品论文,凌子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凌子风驾鹤而去,中国电影痛失一个风格化的导演。在凌子风的创作中,他始终努力自成一体。而新中国电影中,他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如同其他跨越了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在凌子风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这个烙印有的时候使他的作品显得庞大、丰富,而有的时候,却也使他的作品显得犹豫、彷徨。在个人和时代之间,永远有那种探询、追问、回应、追随的关系。在凌子风身上,这种时代的烙印就更加明显。时代给予凌子风的,不仅是他的题材,而且,也是他的风格,他的叙事方式,他的人物,他的观点。从一个艺术家到他的时代、从他的愿望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结果。这就是本文研究凌子风的角度。
提笔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时,手侧放着一篇文章《“真人”凌子风》。像所有的艺术家传奇一样,凌子风在此成为了一个神话主人公,他游戏于时代浪巅之间而将历史变成一幕大戏的枯燥背景。于是,也是很自然地,在艺术家的肖像后,一种古典艺术家所特有的圆润光环散出灿烂光芒。“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用他们作代言人,……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向人说话。”(注:柏拉图《伊安》篇,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篇极为传神的艺术家小传和艺术家研讨会上种种“形迹”的述撰,使我们产生一种畏难情绪:在艺术家凌子风极富色彩的人生经历与同样丰富的艺术经历之间,到底哪一部分更应该成为理论和批评关注的对象。但注定要枯燥的理论最终只能以一种学究式的态度来拆解艺术家的作品,并在拆解中,将其与冷漠、外在的大时代背景比附在一起。但对于凌子风,由于有了前边提过的出色的小传和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将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人生联系起来讨论。这或许可以使我们在分析中不至于像法官一样只注重事实与例条。由此,艺术家也获得了一个与他的作品站在一起的机会。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凌子风是与新中国电影事业一起成长的。这不仅是指他是延安电影团最初的成员之一;同时,他的第一部作品《中华女儿》,既是他个人作为导演创牌子的作品,也是新中国电影创牌子的产品。凌子风与成荫不同,也与袁牧之等人不同。前者是完全在革命阵营中接受的电影艺术教育;而后者,在归附革命阵营之前,已经是蔚然有成的大家,领一时之盛名。凌子风在“国统区”开始他的艺术生涯,这使他无疑受到“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熏陶。而同时,他又是延安文艺运动的参与者。延安文艺的“民间化”过程,凌子风不但参与其事,而且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这就使他的创作之中,同时带有两种文艺的影响和主张。换言之,研究凌子风的创作具有一种考古意义。两种铸就新中国文艺的艺术运动都先后在他作品中留下年轮印迹,并使其作品由此成为一种标本似的存在。也就是说,凌子风及其作品可以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个体具体而又生动地讲述中国自30年代至今的艺术流变,它的彷徨无措,它的欣喜,它的困境,它的犹豫以及希望落空之后的虚惶。而这一切变化之根源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更进一步、更具体、更行为化地说清楚就是如何处理文艺与大众关系的问题。这又分解成几个问题:如何为大众讲述,如何讲述大众,讲述什么样的大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在新文艺中,“什么人”被界定为大众的艺术。而我们知道,在新民主主义文艺中,“普罗主义”也是以大众路线为号召的。于是,我们在“国统区进步文艺”和“延安文艺”中发现了同一种表述,这一表述便是劳动的大众。然而,在这种共同的表述背后,却隐藏着两个不同(只在很严格的意义上)的概念。而凌子风,从一个艺术青年成长为一个艺术家,先后两度被这两个概念所感召,并在二者之间徘徊。
在革命的人群中的一个平民诗人:革命的召唤和“大众”的概念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的一个主要口号之一曾是“普罗文艺”主张的中国化,即文艺之大众化。我们之所以提出“中国化”这个名词,乃是因为中国的所谓“普罗文艺”,是一种民族主义压力下的普罗文艺。换而言之,这一主张是与艺术家们对民族危机的深刻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历史。因此,当知识分子无力将对外洋资本主义的理智上的认同与对其侵略的感情判断上的仇恨联系,协调起来的时候,“大众”,这个巨大的异己群体,因其立场与利益的单纯,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标杆。从鲁迅,到曹禺、老舍、沈从文,他们一直“关注”地描写“大众”。在他们的讲述中,“大众”既是一块乌托邦净土,他们是联系自己与传统、与乡土的一条纽带,使他们不致完全迷失在现代各种思潮的洪流中。而同时,他们对乡土、对大众,又有一丝怀疑,一点陌生,有一种“间离感”。由此,“大众”在这些作家的讲述中,既是朋友,又是陌生人,既体认,又批判;既有一种距离感,又满怀温馨。“大众”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是那种不会触怒自己的朋友。在知识分子的目光中,他们随着知识分子心智的需要而显现出不同的面孔。于是,有鲁迅的浙江风情画,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老舍的胡同里的人们。于是,我们犹豫地将之称为一种“人本主义”的“大众”形象。这也许有违“人本主义”的本意。但我们强调的是,在这种观念中的“大众”,既没有成为须顶礼膜拜的神性的概念,也没被排斥为一种纯然的文化异在之物。凌子风的早期艺术生涯,正是在这样一种“大众”概念的熏染下展开的。从《“真人”凌子风》中我们看到,凌子风早期的艺术活动,是追随着“国统区进步文艺”的轨迹进行的。
历史和距离:在个人和革命之间,在批判和同情之间
进入根据地以后,像所有艺术青年一样,凌子风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这一洗礼的一个主要程序就是一个新的“大众”概念的培铸。虽然凌子风在1943年回延安只被延安风擦了一下,但新的文艺时尚与文艺思想已成为统率性的思想规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在这一口号下,“大众”已被表述为一种“革命的”大众,一个服务的对象。对于新文艺工作者来说,对于新的“大众”,他们惟一可选择的态度,便是体认与服从,并接受号召,服从召唤。大众成为解救民族危机的终极力量。因此,大众在此成为一个神性的概念,它不可怀疑,不容争辩,而且它天然地拥有一种思想与道德的优势。大众作为先锋,是引导革命的力量。大众的情趣,大众的判断,大众的道德原则,成了新文艺时刻必瞻的马首。与大众结合,其最终的目的是完全消除异在感,抹煞距离感和第三者的审视的目光。想大众之所想,做大众之所为。甚至“喜欢”这样一种感情反应也是不正常的。你必须脱下心事重重的思想外衣,一头钻入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其中一部分,消失于无形。在这样一种热潮澎湃的革命热浪的感召下,凌子风兴高采烈地投入到这一大众化过程中去。从《“真人”凌子风》来看,凌子风在民众中进行的艺术活动是大受欢迎的。而且“凌子风在敌后农村呆了六年,除担任边区剧协的常务理事,乡艺辅导校长外,还担任过武工队排长,为适应战斗环境和农村演出,他从街头剧得到启发,倡导不用布景利用田庄村头院落作为舞台取名‘田庄剧’,活跃在敌后边缘区,敌占区以及根据地腹地的农村”。(注:左舒拉《“真人”凌子风》,《当代电影》1990年第2期,第81页。)凌子风从事的解放区第一部故事片的摄制便是他上述活动的自然延续,而他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中华女儿》,也依然可以视做这一创作活动的延续。如同《边区劳动英雄》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部“采风式”的作品。它的故事来自斗争的第一线,有真实的生活事迹为依本。而且,在故事编排上,它也可以脱去原来旧文艺中旧神话的鳞屑,从而显现出全新的编排方式、叙事方式。影片中对残酷斗争环境的表现以及对群像的细致刻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凌子风后来的创作中,这些风格化的东西并未固化下来而形成一种写作风格。他的题材的不断变化,使其风格也随着发生变化,风格被掩盖在题材,故事的时效性与政策意义上了。艺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完全的追随与体认便无从有艺术可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凌子风,在完全隐迹于大众之中时,便也意味着一个艺术家身份的某种消隐。
进入诗体的平民:美化也是改写
《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狂》,凌子风在新时期的创作成就是辉煌的。在上面提到的几部影片中,有一些共同之处。首先,它们均改编自新民主主义时期进步作家的作品。另外,除《狂》之外,《骆驼祥子》、《边城》、《春桃》都获得了各种奖项。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劼人,这些名字使我们想到了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进步,然而不会像鲁迅一样呐喊着向对手投掷匕首、投枪。他们温和,但却时时行走在民众之间。这些作家的笔下,便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人本主义”的大众。他们比茅盾更有“土味”,而比鲁迅更少火药味。他们略带温柔地描写他们眼前的大众,但亦有柔和的批判。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批判与同情都适可而止,从而保持一种距离感。凌子风一连改编了四部这样的小说,可以说,在他新时期的作品中,有一种一贯的倾向。经过从1949年以来的种种风波与运动,这种对“旧”文学的温柔的回顾说明了什么呢?经历了种种历史风云之后,凌子风在投奔延安前的那个大众又开始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革命”的大众开始隐退了。凌子风曾在这个大众神话中生活了很久,也许这时他才发现,他其实无从了解,也无从融入这个大众。因为在革命的大众神话中,体认与服从并不要求认知。而且,随着革命的阶段性变化,政策、短期目标的改变,这一大众神话表现出的是极易变幻的面孔,它忽而是苦难的,忽而是仇恨在身的,它也许是冷静的,但有时却极端狂热而近乎失去理智。它有时宽容,但有时却表现得极为偏狭。也许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剧烈的变动会使任何一个艺术家头脑混乱而无从为新的大众画像。于是,凌子风将目光越过现在投向从前。那是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们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凌子风在讲述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时,都能勾出一大堆“自己的故事”。而且,由于历史所造成的时间间隔,无形中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发生了作用。老舍等人的故事在讲述中重新获得了灵气。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创作高峰期。因为在这一创作期中,凌子风显现出了一种与“作者”概念相符的风范,即在一系列的创作中,显示出了一种一贯性,一种一致的书写特征。在凌子风的温情的回顾中,旧中国显现了一种特有的魅力。那些大众,是平平凡凡的大众,游离于历史大潮,政治斗争之外的辛苦生活的大众。他们的面孔,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形象。从新大众的神话中脱身出来,凌子风开始焕发了惊人的艺术青春。凌子风关于改编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改编就是原著加我,别人怎么着跟我无关。”(注:左舒拉《“真人”凌子风》,《当代电影》1990年第2期,第85页。)这个中间的“我”, 便是使其创作显现出一致性的原因。
于是,这提醒了我们去寻找,在这些改编中“我”的成分、“我”的色彩是什么。
消失了的“大众”
在四部改编作品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主人公形象的美化。我们先来看《骆驼祥子》。老舍的这部小说,通篇色彩是对祥子的“哀其不幸”。祥子由一个纯朴的车夫,终于毙倒街头,是有一丝悲剧意义的。在这部小说中,老舍没有为祥子硬安上一个反抗过程。像所有悲剧主人公一样,祥子的人生悲剧,与其性格联系在一起。他过于善良,过于锋芒内敛,因而无法与命运的安排抗争。当一系列打击接踵而来,他的职业和家庭幻想均告失败以后,他自暴自弃地放弃了追求而堕落下去。事实上,小说最动人心弦的叙事安排就在于它的首尾的呼应。一个纯朴的年轻人带着尚很充实的人生理想来到城市,结尾时,他丧失了一切信念贫病交加地死去。但是,我们看到,影片中,祥子最终的堕落被删除了。无论如何,这一删除,是将小说的最精华部分给删割掉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损失。悲剧被截除了动人心魄的部分便成了一系列无意义的生活片段的展示。电影《骆驼祥子》偏重小说前段而将后边一个重要部分语焉不详,就好像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省略了他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几乎所有明眼人都看出在改编的《骆驼祥子》中,虎妞成了主角而祥子弱了下去。因为随着虎妞的死去,故事就草草地收尾了。而无论如何为艺术家辩护,这一故事的重心的转移是难以让人心服的。因为这对于名为《骆驼祥子》的改编,至少是文不对题。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来说,祥子的纯朴与追求,不过是为他戏剧性的死亡做铺垫,而在改编本中,只留下了铺垫。其实,凌子风本身,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他别有考虑:“不忍心让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祥子颓然堕落。”(注:俞小丁《反璞归真,如愿以偿》,《大众电影》1982年第10期,第6—7页。)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解释来说明重心的转移。为什么虎妞的性格、悲惨结局可以展现无遗呢?真正的原因是,凌子风在表现“旧”的大众的时候,“新”大众的影子下意识中笼罩了那原本纯然的形象。在新的革命的大众的学说中,大众作为革命的主体,唯物史观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推动者,是不能够以一种无助的、自决的方式堕落而无可救赎,并无从反抗。作为先觉的劳动者,一切堕落、自毁的原因必须是外在的。他每一个过失,每一次不值得称赞的举动,都必须寻找到一个外在于它,并逆历史主潮而动的敌手并将之归罪于这个敌手。因此,祥子的堕落在革命大众文艺的旗帜下,就必须虚写以维护革命大众的主体光环。这样,在凌子风的祥子身上,冷静的观察目光被一种过于投入,过于体认的“不忍”的目光所代替。这样,祥子既在影片中占据主要角色的位置,又在叙事上退居虎妞之后,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叙事格局。在几场主要戏的处理上,凡是有虎妞出场,影片就显现出耀人的光彩,而一旦虎妞不在,祥子就显得虚惶无主。这样,我们看到的凌子风的《骆驼祥子》就变得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多了一份温情而少了一份冷峻。俗谚说靠得过近就会看不清。凌子风正是过于力求靠近大众而局限住了自己在这里,作为对凌子风个人作品的分析,我们恐怕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特点。从大量的他的自我介绍及介绍文章之中,我们得知他从小即生活在祥子之类人的生活空间中,因此,对他们的生活及习性极为熟悉并颇津津乐道。但在此,我们毕竟无法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原因的解释。
《边城》使凌子风得到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作为新时期改编的一个热点之一,沈从文的小说颇受改编者的青睐。凌子风在这部影片里显示了娴熟的导演技巧。但同时,在流畅的叙事表面上,沈从文小说中湘西文化的那种异在感和独特的人际、伦理关系被淡化了。爷爷这一形象变得过于敏感,孙女的形象又变得过于清纯。在这种改编中,湘西那个多少有点蛮荒,宿命色彩很浓的世界消隐了,而爷爷、孙女之间的那种依恋的感情关系被夸大了。婚嫁死生,水涨风落的那种风情变成了一股淡淡的哀愁。故事中的爷爷和孙女,在影片中成了外来力量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他们仿佛迫于外力而不得不接受必将分开的命运。而在原小说中,这一切并无一种无奈的情绪,而是一种被文化所规定的宿命。这于他们,并不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对痛苦与幸福的体验是不同的。而在凌子风的改编中,他使爷爷的目光中,多添了许多失落和哀愁。而孙女,由于不再是一个“早熟”(按我们通常的成长分阶)的女性而被拉向外界,便有了一种被伤害的苦痛和恐惧。如果说在《骆驼祥子》中凌子风由于过于温情而丧失了冷峻的批判性的话,则在《边城》中,他又由于对“大众”形象的热爱与关怀不必要地添加上了一种冗过的批判立场。而归根结底,这一切的原因也是凌子风力图在一种唯物史观的人文背景中塑造他的“大众”形象造成的。这是一个颇为难以解说的困境,当他热切地将自己的主人公拉向主流历史,拉向一种大的人文背景中时,他的主人公却倔强地离他而去。凌子风第二次由于热爱他的主人公而失去了使他们更为不朽的机会。如果不是这份热情,他极为可能拍出比第五代更为惊世骇俗的作品。
《春桃》作为许地山的作品,有着许地山特有的“禅”味。《落花生》这篇小品文,可能更让人体会到许地山的这种“禅”味。生生死死,叶落花生,许地山作品中有一种奇特的冷静与从容。这种从容,是历经变乱之后的那种参透红尘的高远的视点。在原小说中,使我们吃惊的不仅是那个故事:一间屋子里住着两个男人,一个女人,而两个男人中,一个是女人的丈夫,一个是女人的情人。让我们更为吃惊的是那种冷静的叙述笔调,引痛而歌,遇难而不惊,正是在一个惊人的故事的平静的讲述中,将三人的苦难化为一种博大的佛境。
在影片中,三人的困境过多地被较为狭隘的“情”“理”冲突而被高度戏剧化了。残废的丈夫,在叙事中被安排上了一种社会批判色彩。于是,影片失去了小说特有的冷静与超然而变得像是一种社会控诉。换而言之,女人与情人的关系由于被美化而使残废丈夫的出现变成了一种较为一般化的戏剧关系。当情人毅然出走时,他的牺牲使他显得形象颇为高大,但却使整体受到了损害。在这一次的改编中,凌子风又一次由于“不忍”而使他予主人公过多的同情与认同。大众于是不再是冷静而多少有点参透红尘,冷漠的大众,而成了热情而痛苦的大众。也就是说,凌子风过多地以新的,代表主流历史推动力量的自觉而善良的大众的标准来美化了许地山的人物。这种美化的结果是使影片的戏剧性增强而失去了导演自己的观看视角。对人情关系的热衷最终挤掉了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生存心理的展示。
《狂》是一部难度较大的改编。其难处在于,原著的那种“恶”的细致刻画。一个女孩的理想——最初是去成都,一次次实现而又一次次落空,显示了极强的社会描写及心理刻画的深度。而在影片中,两性角逐的成分被较多地赋予了细致的描写。这也许是改编中不可避免地采取的一种结构的方式,但在这种结构中,作“恶”的快感变成了一种近乎痛苦的体验。而痛苦本身,变成了狂欢。主人公在痛苦与狂欢的交织中被原谅了,被理解了,然而也被一般化了。
结语:个人的故事完了,历史的……
说到这里,必须提的一句话是,我们通篇的长论,并不是在指责凌子风的改编。艺术家必须永远被责备然而又不应被责备。我们想要指出的是,艺术家的一种写作习惯,或一种强迫症式的书写方式其根源何在。当凌子风宣称改编是“原著加我”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那个“我”并不是艺术家个人的秉性、才情,而是那个“新大众”神话的影子。这一神话在他的改编中不断与旧的大众神话相遇并改写旧的大众神话。这种改写就是不断将旧大众拉向新大众,将主人公们从历史边缘拉入唯物史观的历史主流。因此,在凌子风的作品中,他的人物徘徊在两个大众概念之间而显得虚惶无主。他们反对主流的历史写作方式但又时常修改自己以适应主流历史写作。他们不时对主流神话构成威胁而最终又宣称自己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例外。
也许这一切都因为凌子风是一个热情而又真诚的艺术家。他的热情使他常常站出来为主人公辩护,而他的真诚又使他在两个大众神话交织的困境中无从解脱。
或许一种艺术理论能更好地让我们理解凌子风。这种艺术理论宣称:越是对世界的美化的描写,便越有一种社会批判力存在。因为那种与真实的世界异在的艺术世界,让我们越发体验到真实世界的丑陋与不完整。而如依此说,则凌子风的这种“美化”的改写,可被视为一种一贯的批判立场,一种贯穿的对世界的看法。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凌子风为我们显示了一种他自己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也许从一种文化的或艺术学的角度来审视都可以找出其偏颇之处。然而也正是这偏颇,让我们认识到了他的困境之后的那种人文背景。如此说来,则凌子风的改编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