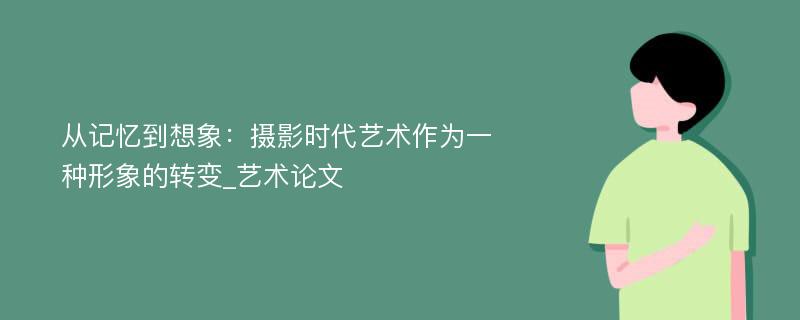
从记忆到想像:艺术作为摄影时代的影像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想像论文,影像论文,记忆论文,艺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催生了新型传播环境和影像文化生态,影响着摄影的创作与审美架构的重置。数字媒体成为当代艺术创作最热门的媒体,现代科技和人类艺术灵感高度融合而产生的影像艺术消解了传统的摄影艺术概念,无孔不入的后期加工挑战着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底线,摄影艺术的言教功能遭到普遍怀疑,这些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影像文化时代的来临。
一、摄影作为证据时代的颠覆
在传统摄影观念下,摄影被认为是一种精确复制客观对象的技术手段和逼真再现客观对象的技术形式。诚如罗兰·巴特所说:摄影的真谛在于“这个存在过(此曾在)”,[1]“照片和拍摄对象是共生的”。[2]鲁·阿恩海姆在讨论摄影的性质时谈到:“即使是最富于想象力的摄影师,除了亲临那个可以实现他的设想的场所之外,也找不到别的替代方式。”[3]这些观点都道出了摄影与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本质的区别,摄影是引导人们进入现实的工具,是关于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记忆,这使得摄影成为最民主、运用最广泛的大众媒体。而数字影像技术颠覆了我们已有的关于摄影——特别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真实性价值,数字影像技术天衣无缝的编辑和改变影像的方式将使“照相机永不说谎”、“摄影作为证据”的观念打上句号。早在1988年,美国《时代》周刊出于和平的意愿,曾利用电脑合成制作了里根和阿拉法特、沙米尔握手和谈的照片,而以严谨著称的《国家地理》杂志为了使画面更加完美,曾使用电脑处理使金字塔间的距离缩短了。在数字技术背景下,文本可轻易被篡改,使得作者的本意发生了细微而有效的变化,新闻摄影的伦理学正面临着威胁。2004年3月11日,《EI PAIS》报摄影记者帕布鲁(Pablo Torres Guerrero)拍摄了一幅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的照片,在照片左下角处于前景的突出位置可以清晰地见到一块尸体的残片,而英国的《每日电信报》、《太阳报》,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的图片编辑在“道德和品位”的名义下对此图片前景中的尸块做了相应的处理,[4]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照片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另一个曾经广为争议的事件是:《洛杉基时报》派驻伊拉克前线的摄影记者布莱恩沃斯基在一幅伊拉克战争的照片中,为了改进构图、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用电脑合成了照片。[5]这件事情在国内外的媒体和广大读者中引起震动,也引发了对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争论,特别是数字影像所引发的新闻伦理道德问题被摆上了议程。近年来,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摄影比赛中,不断有获奖作品被指出通过PS改动或合成图片造假,如,首届“华赛”①自然及环保新闻类的金奖作品《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②、第二届“华赛”经济与科技新闻类单幅的金奖作品《中国农村城市化改革第一爆》③、中央电视台《影响2006》年度新闻图片铜奖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④,就是最具权威性的荷兰新闻摄影比赛(简称荷赛)也未能幸免,2010年的荷赛揭晓不久,荷赛官方网站就公布了一个声明:乌克兰摄影师斯蒂芬·鲁迪克(Stepan Rudik)的体育特写类组照三等奖的奖项被取消,原因是他修改了照片⑤。一些摄影师在名利的驱使下,或导演或修改或合成了新闻图片,引发新闻摄影的诚信危机,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薇姬·戈德堡在《摄影的力量》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发聋振聩:“一旦公众深信照片已不再是交流的可靠手段时,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相信。”[6]
因此,在数字成像技术时代,对图片的篡改变得异常容易时,新闻摄影工作者需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需要具备作为信息记录者与传播者的职业道德、伦理品格,滥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将会毁掉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人们对新闻摄影手段的信任。当摄影的真实性不再被人们所接受时,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
二、摄影艺术本源权威性的瓦解
摄影的瞬间纪实特性是摄影诞生的原动力之一,也是摄影的本质特征。罗兰·巴特在《论摄影的信息》中,把摄影称为“一种完美的、绝对的通过缩减,而不是改变物理对象所获得的类似物。”[7]约翰·伯格认为,“摄影和其他视觉影像不同之处在于,照片不是对主题的一种描写、模仿或诠释,而是它所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种油画或素描,不管它是如何的写实,都无法像照片一样属于它的主题。”[8]这些观点来源于早期的影像多是现实世界的纯粹反映,基于摄影是对对象的忠实复制。而数字影像既可以来自客观现实,也可以运用剪辑合成和电脑绘图的手法进行,强调人的情感存在而非世界的客观存在,这种创作手段直接破坏了影像反映客观世界的权威性,使得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摄影受到严酷的挑战。
传统摄影虽然也可以在暗房里合成照片,H.P.罗宾森、O.G.雷兰德的高艺术摄影和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就是一种绘画性的再创作,但是,他们毕竟是以人的现实经验为基础。而数字影像的记录方式从实体的以光化学为基础的银盐变成了虚拟的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像素,既可以来自客观世界,也可以随意更改照片的内容,还可以不受固有影像的限制,是纯粹的虚拟创造,创造出不存在于人的现实经验界的影像,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影像再创造。数字影像还通过混淆拍摄者、制作者和观者,混淆影像的客观现实性,最终使摄影艺术本源的权威性变成了泡沫。[9]数字摄影颠覆了摄影艺术纪实美、瞬间美的本体特性,彻底瓦解摄影艺术的本源权威性。
在手工制作影像时期的摄影作品与外在世界的物象几乎是重叠的,是建立在对情节的美化上的;而电子影像时代的作品却是建立在运用数学化技术传达着模拟扩展和广泛重造上,摄影作品与外在世界的物象的关系变得不大,也可能没有任何关系。[10]
三、摄影艺术创作从“观察”到“想像”
在摄影艺术创作中,传统摄影受制于特定的技术条件,只能对拍摄对象、拍摄时机等进行选择、提炼,然后应用娴熟的摄影技术技巧,有时再借助极其丰富的暗房经验,才能把自己的创意物化为照片上的视觉形象。而数字技术给艺术摄影带来极大的创造性,开创了影像表现领域的新空间,真正步入了瓦尔特·本雅明所预示的“艺术作为摄影”的时代。借助数字图像处理及电脑绘图软件,摄影的再创作变得无所不能。“有了数位科技与机器人,生化科技工程已经逼近将自然与人工结合的边缘,现在的摄影已经可以进入想像,创造虚构的世界。”[11]它不仅仅是用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弥补在拍摄创作中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完成的许多遗憾。还使摄影“不仅能‘拍’见到的东西,还能‘拍’想到的东西,不仅能‘拍’感到的东西,还能‘拍’悟到的东西”,创作出非现实时间、空间中存在的视觉形象,大大丰富了摄影的表现手法。
摄影创作不断向其他媒体的边缘拓展自己的空间,1970年代以来,一些艺术家们加入到媒体实验的行列,开始尝试将摄影和现代艺术相结合,摄影与美术、装置艺术、身体艺术、行为艺术等日益交融、混合,出现了一股观念摄影创作的热潮。如,杰夫·沃尔(Jeff Wall,1946- )、南·戈尔丁(Nan Goldin,1953-)、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1954- )、埃里克·菲谢尔(Eric Fischl,1948- )、格利高利·克鲁逊(Gregory Crewdson,1962- )等当代艺术家游走于摄影界与艺术界,摄影与绘画等艺术创作相互渗透。19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的普及与资讯的共享,数字媒体艺术在当代艺术中开始大量涌现,洪浩、王庆松、邵逸农、栗宪庭、缪晓春等国内的一批艺术家也开始尝试将数字影像技术应用于艺术创作,对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经济、文化等进行反思,融入世界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数字技术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跨材质、多种媒体的融合,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展现方式。
当今,摄影不再单纯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种客观记录的手段,而是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的创作媒体和表现形式,重在用主观化的处理方式去表达人的自我内心精神、人生观感和审美意识,摄影只是艺术家观念的一种依托物,他们着眼的是自己的观念如何被视觉化,创意、想象力和艺术观念成为创作的灵魂,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更为艺术家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提供了可能性,摄影艺术实现了从“观察”的艺术发展为“想象”的艺术,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得以更完美地表现出来,使摄影创作成为无限的可能,真正实现了摄影艺术创作的自由。
四、影像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
摄影发明以来,无数艺术家致力于提升其艺术品位,使摄影跻身于高雅艺术之林。早期的画意派摄影强调摄影模仿绘画,从作品主题的选择、画面形式的处理、技术的运用都努力使摄影接近绘画效果。而美国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倡导的直接摄影使得摄影从模仿绘画的尴尬身份中突围,把摄影有别于其他媒体的艺术特质发掘出来。斯蒂格利茨的现代摄影理念在保罗·斯特兰德、爱德华·韦斯顿、安塞尔·亚当斯等摄影家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他们用纯净的摄影技术获得了摄影所特具的美感效果——高度的清晰、丰富的影调层次、微妙的光影变化、纯净的黑白影调、细致的纹理表现、精确的形象刻画。特别是安塞尔·亚当斯的“分区曝光法”以“化学实验般的精确精神,以此获得的作品在影调表现上臻至完美境界。”[12]为摄影树立了高标准的品质,把工业时代“科学与美的结合”发挥到极致。以此同时,马丁·慕卡西、安德烈·柯特兹、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等摄影家则致力于视觉构成规范的建立,形成了基于自身技术特性的语言系统,这些探索都是基于贵族式的高雅和精英文化。而在数字成像技术时代,艺术家“对于摄影的技术、材料、过程这一些传统摄影关心的手工部分无所用心。”[13]他们强调影像内容和主观感受,而不是视觉趣味,数字化影像无疑把影像从贵族式的高雅沦为大众的通俗,迎合了以消费主义、娱乐主义为特征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
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摄影者在数字技术的潮流中面临的不仅仅是拍摄工具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从图像制作到图像传播乃至实现其价值的转型问题。随着数字相机的普及、拍照手机的流行,人人都成为影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尤其对于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现场,专业摄影者与业余摄影者的身份已经很模糊。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遭遇恐怖袭击时,地铁内的乘客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并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头版采用。同年,在加拿大温哥华诞生的网站Nowpublic由网民提供原创新闻,在网站注册成为“平民记者”的人数急剧上升,并吸引了一部分传统的国际通讯社的关注。当下流行的微博使得“人人都是记者”,它的即时性、互动性、分众化的特点对传统媒体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在国内,新闻媒体已经大量采用手机拍摄的突发新闻事件,无所不在的“平民记者”拍摄的影像逐渐进入主流传播渠道之中。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摄影还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一种大众化的书写和阅读工具,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记录下身边许许多多的有趣瞬间,留下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形象记忆,拍摄后的照片可自主地在网络上发表、展示,博客和个人空间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自由的渠道、自我展示的平台,摄影正在以这种共享方式丰富着大众生活中的娱乐元素。不论是作为个人休闲娱乐,还是作为现代视觉传播媒体,或者是艺术创作方式,摄影在当今社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与电影、电视、绘画、动漫、广告、设计、游戏、多媒体等互为激荡,塑造着当今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时代。
摄影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数字摄影解构了传统摄影的确证和记录的本质,给新闻图像的真实性带来了信任危机。通过后期再加工合成或电脑绘图制作的影像把摄影从记忆中的现实空间转化为想象中的拟像空间,就如《阿凡达》中展现的时空交错的戏剧性述说,形象失去原来的内容和意义,产生了新的意义系统,催生了数字媒体艺术。陈丹青对此曾作了精辟的论述:“二战迄今,国际摄影可谓创意纷繁,已经超越‘目击’、‘确证’的传统摄影观,采用虚拟、挪用、并置、投影、录像、电影等多媒体科技,在宏观与微观的每一方面,塑造着当今时代的视觉文化。今日摄影不再试图与“艺术”分庭抗礼,而如虚拟现实主义摄影家杰夫·沃尔所言:数码摄影与电脑技术,能使我们接续戈雅时代绘画艺术的未竟之业——‘艺术作为摄影’,在本雅明身后半世纪,在我们的时代,已然蔚为大观。”[14]
数字技术使影像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方式产生剧烈变革。19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传统摄影即将消亡这一担忧,这与19世纪中期摄影诞生之初写实主义画家的担忧相类似。但是,摄影术诞生170多年来,摄影技术发展史上曾经采用的工艺、方法从未消亡,有些摄影家把它们作为更加纯粹、具有独特美学意味的艺术活动,所以,传统的摄影方法将作为一种历史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沿用,“就像摄影时代的绘画,电视、视频时代的电影和照相机,网络时代的电话一样,旧的形式仍在延续,但却根据新形式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位置。”[15]
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多元选择,一些艺术家从中找到一种全新的表达自己思想和观念的创作媒体。还有些摄影家依然坚守摄影媒体的本体特性,以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记录现实,观照内心,留存历史,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思考。但是,不管是哪一类摄影创作,都应该关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主题,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参与现实生活,回应现实,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持久的震撼人心的魅力。
注释:
①“华赛”是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的简称,这是由中国举办的国际性新闻摄影比赛。
②画面上有两只鸽子成像几乎完全一致。
③画面上几栋楼瞬间倒下的瞬间采用接片合成。
④作品中的藏羚羊是后期合成。
⑤荷赛评委通过调取RAW格式的原图,发现作者移除了原始照片中的某个元素,违反了比赛“不可修改图像内容。只允许进行符合当前行业标准的润饰”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