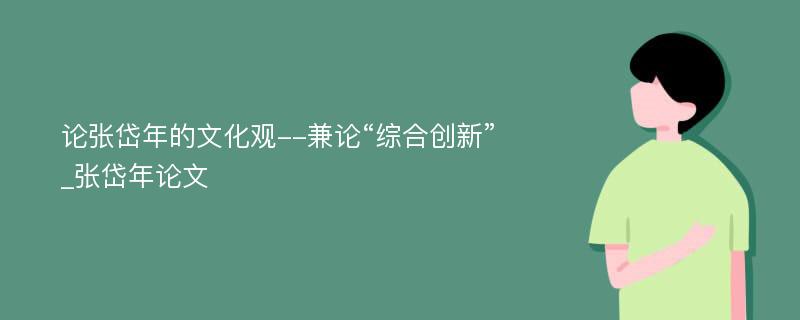
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人类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文化的“综合创新”时代。
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说的“综合”。亦即博采各学派或学说之所长,而“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这种方式可称之为文化的内部“综合”。(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综合”。亦即立足本民族国家,吸取外来文化之所长,以补本民族、国家文化之不足,而“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这种方式可称为与外部文化的“综合”。以上两种方式,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说,在一定时期内侧重于第一种方式,而在另一时期内则侧重于第二种方式。两者交替进行,不断“综合”,不断“创新”,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100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后半个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文化上促使人类认真思考,探索并掌握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之前,人类的文化虽然是按照“综合”“创新”而发展的,但是人类并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它具体地表现在:(一)地域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化“综合”仅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或几个民族、国家之间。它还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二)领域的局限。在这一时期,文化的“综合”仅是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的一个或几个领域之内,它还不能称之为全方位的。由此可见,在20世纪之前,人类尚未进入文化“综合创新”的新时代。
20世纪末人类已进入文化“综合创新”的时代
人类能够比较自觉地对已有的文化进行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综合”,以“创新”人类的文化,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重大突破,对人类的文化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现在已是20世纪末,人类已进入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新时代,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渐进的艰苦的历程。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兴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他们站立在全人类的高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批判,激励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凋敝,造成人类空前灾难。但战火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以铁的事实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深重矛盾已暴露无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得到迅速传播。一批中国有识之士,梁启超写有《欧游心影录》,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对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为了和缓社会矛盾,避免中国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医治战争的创伤,复兴经济。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完善”资本主义的措施,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国家资本成分,以便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减轻生产的盲目性。(二)实施累进税制,对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课以累进的重税,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三)建立“福利社会”,政府从高税的收入中,提取一部份用于贫困者的衣食住行、生养病死,以至教育的资助,以提高人民福利,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盘剥第三世界。因此他们提出的所谓“完善”资本主义的措施,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在战后50余年中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基本稳定起了一定作用。如果认真地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从体系上说社会主义和“完善”后的资本主义是两个相异思想体系,但是西方“完善”资本主义的一些措施与社会主义又有相近之处。由此,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对资本主义的“完善”得益于社会主义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铁幕”使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在世界之外。在西方国家“完善”资本主义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批有识的经济学者,为了“搞活社会主义经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提出了“开放改革”的思想。虽然,在社会主义诸国之中,于时间上有先有后,于程度上有深有浅。而在思想上则基本一致: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有了商品生产就必需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必需加强经济管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世界范围内,两种不同政治体系之间,虽然尚处于壁垒森严的时期,但在文化上却进行了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标志着人类已迈入“综合创新”的时代。
从本世纪60年代起,人类的高科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由于讯息工程和交通的发展提高,世界变小了,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讯息。这必将加速人类在世界范围内,从全方位上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进程。在本世纪末、90年代初,东欧诸国和原苏联相继解体,世界的政治形势已产生重大转变。以两个阵营为对垒的冷战已结束。人类意识形态的分歧相对削弱,以及世界政治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为人类文化“综合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观
人类已进入“综合创新”的文化新时代,与之相适应,也欲呼唤出新的文化观。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包括海外华人社会)再一次掀起了讨论中国文化的“文化热”。从近百年中国历史来看,关于文化的讨论,“高潮”迭起,延绵不绝。在人类文化史上诚属罕见。推其原委,不可忽视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薰陶之下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关注。就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争论与本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何把握时代精神,以区分历史上的文化争论与80年代“文化热”的本质不同。
(一)把握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张岱年先生为研究、整理、发掘中国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倾住了他的全副精力。早在二三十年代,尚在求学时期的张岱年先生就接受了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他当时的话来说,对这种新的哲学为之“心折”。同时,又对西方哲学家怀德海、博岩德等的逻辑分析法大加赞赏,并吸取其科学内容。张岱年先生撷取西方哲学之“精华”,与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整理、发掘融为一体。因之,在对中国哲学的主要范畴、概念的厘定上,在对中国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的整理上,在对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发掘和提练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
张岱年先生在治学上求“新”(创新)、求“诚”(真理);在为人上刚毅木纳,宽厚待人,体现出中国学者的高尚风范。而且他又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并不满足于平静的“书斋”生活。当时已年近8旬的张岱年先生以全副热情投入这场文化之争。他以敏锐的目光,指出“在近几年的文化问题讨论中,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很‘新’,实际上却没有把握时代的精神。”[1]今日的时代精神与二三十年代有无不同?应如何把握今日的时代精神?对此,他作了深刻的分析:
“在二三十年代,当时讨论的是:中国走向何处?中国文化走向何处?中国到底应如何办?这是那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国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二三十年代面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目标和方向已经确定了。现在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我国当今的社会状况与二三十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大不相同,而且是大大的进步了。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建设上,今天我们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2]
以上这些精湛之言,是针对80年代“文化热”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否定论”而说的。张岱年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可是在80年代的中国人中,有人却偏偏看不起自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说中国国民性中有‘奴性’的一面,那末这些人看不起中国的思想,正是‘奴性’‘劣根性’的表现。我们有责任来纠正这种思潮。”[3]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张岱年先生就投身于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争论中。1935年5月,他写出《西化与创造》一文,他指出:
“现在的中国文化问题,已不是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将来的中国,无所逃于此二者。……事实所昭示,现在中国处在世界公共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国主义重重束缚之中,想建立一个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企图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平等的地位,那是绝不可能的,……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准备工作。[4]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先生就预料中国的前途绝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当时的中国文化工作,必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准备。联系80年代《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可见他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执着追求是始终如一的。
(二)从“综合创造”到“综合创新”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萨孟武等10位当时文化名流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又称“一十宣言”)。该文的发表,引起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次文化争论高潮。张岱年先生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场争论,在此前后,写出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西化与创造》(1935年5月)等三篇文章(均收入《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张先生对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的基本文化观作了简明的归纳:
“主张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
张岱年先生提出[5]文化必须“综合”,而且强调这种“综合”是“创新”的“综合”,甚至提出了“文化的创造主义”:
“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更显明的说,其实可以说是‘文化创造主义’。不因袭,不抄袭,而要从新创造。对于过去及现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态度;对于将来,要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只有创造力永远不灭而是值得我们执着的。
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预文化之再生,然后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出路。”[6]
在这一时期,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既强调“综合”,更强调“创造”。因此,有的学者将张先生在30年代的文化观,归纳为“综合创造”这是可取的。
由于张岱年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沿用了“中国本位文化”这个词,而且也说过,他的文化观“大体上是与‘一十宣言’所说相同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张先生在30年代的文化观是赞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这一认识,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在以上引文中,张先生的确沿用过“中国本位文化”一词,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词之前,一般都冠以“所谓”和“创造新的”等限定词。第二,张先生说,他的文化观与“一十宣言”大体相同。“大体”相同,并不等于“全部”赞同。事实上,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多处对“一十宣言”提出了批评:“也许因为是一个简单的宣言,所说似还不免笼统”。“欲使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意义成清楚的,还须考察:过去的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特色在哪里?世界文化之大流趋于何方?中国所缺乏、即所需要者是些什么?不然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7]既然,张岱年先生对“一十宣言”提出了“似还不免笼统”,“观念还是模糊不清”等批评,就不可能得出他完全赞同的结论。
1995年11月10日,我带着以上问题请教了张岱年先生。我问:“岱老,您在30年AI写作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对‘一十宣言’是否持批判的态度?”岱老回答:“是”。又问:“您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一十宣言’‘观念模糊不清’,又提出您的‘文化创造主义’强调文化的“综合”与‘创造’。是否因为‘一十宣言’虽谈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它强调的是‘中国本位文化’,因此,它没有彻底摆脱近百年来‘体用’之说的束缚,从而,您对‘一十宣言’持批判态度?”岱老肯定地回答:“是!”通过此次访谈,我更加深了对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理解:在主编《张岱年文集》过程中,我曾考虑过,为什么岱老在《张岱年文集》的6大卷、近400万字的著作中,论及“中学”和“西学”谁是“体”,谁是“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8]。经过访谈,恍然大悟,因为岱老所追求的文化观,是超越于传统的“体用”之说,彻底摆脱“体用”之说束缚的文化观。这也就是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新意”之所在。
从1984至1989年,在神州大地上又掀起了本世纪末“文化热”的最高潮。年届80的张岱年先生仍抖擞精神,笔耕不辍,在短短的5年中写出了近20篇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其中,明确地提出他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并加以系统阐明的,首推《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成稿于1987年,收入《张岱年文集》第6卷,第1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89页)。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是在1987年,这年的秋季在北京组织了两次座谈会,参加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会上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反复进行论证。是年冬季,在山东济宁市召开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由张岱年先生作主题发言,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什么是综合?什么是创新?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9]
30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造”,而80年代提出“综合创新”,对比两者,在思想和思路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综合创新”是“综合创造”的延伸和发展。而从文学上看,以“综合创新”取代“综合创造”仅一字之差,那末,“综合创新”中的这个“新”字应如何理解,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了。
“文化综合创新论”其中“新”字的含义
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其中这个“新”字的蕴含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有三个重要方面:
(一)揭示出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以中国三千年文化为例,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先秦至两汉时期: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异说,百家争鸣,史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黄金时代”。至战国中后期,《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庄子》有《天下》篇,对诸子百家之说作出初步评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综合”的开始。秦吕不韦兼采诸子百家,著《吕氏春秋》。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旧说多认为是对诸子百家学说的“折衷”。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文化的发展看,《吕氏春秋》应是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综合”的尝试。西汉初,刘安著《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以道家为主体,兼采诸子百家。与此同时,西汉初又出现了相类似的“黄老之术”,对西汉初恢复经济、充实国力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成功的文化“综合”。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旧说对董仲舒的主张多有贬词,其实,董仲舒既没有“罢黜百家”,也没有“独尊儒术”,而是建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兼采道、墨、法、农、阴阳、五行之说的新文化体系。这次文化的“综合”,为中国后世的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综合时期。
第二,隋唐至宋明时期:外来文化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至隋唐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外来佛教与老庄、儒家学派逐渐结合,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派别,促使佛教在中国广泛流行。但是佛教的中国化,仅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已,它仍属于佛教,还不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宋代朱熹、程颐大胆地吸收了佛教文化中“一多相容”说,称之为“理一分殊”,并以此为架构,建立了一个以儒学为主,兼采道家、魏晋玄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学”体系。从哲学而言,这个体系博大缜密,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丰富了中国文化。后世称程朱创立的“理学”体系为“新儒学”,从南宋至明清,在这600年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
谈到朱熹的“理学”,必然要想到韩愈。韩愈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文起八代之衰”之美称。他又是中国“道统”说的首创者,认为中国从尧、舜、周公、孔子到孟子存在一个道的传统(“道统”),他自认是孟子之后“道统”的当然传人,决心为封建鼎盛时期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按韩愈的才华和决心,他是有条件完成的,但是,事与愿违,这个使命直到封建的中后期,由程朱完成。其原因何在?从文化方面来考察,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佛教产自古印度,传入中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韩愈与朱熹受到佛学的薰陶,同时又反佛,这是相同的,而在反佛的内容上却是不同的。佛教既是宗教,又是蕴涵丰富的佛学文化。韩愈说,如果将夷狄之教(指佛教,包含宗教和文化)加之于先王之教(指儒学)之上,“岂不悉为夷也”。为了防止中国“夷”化,对外来佛教(包括外来文化--佛学)采取简单排斥的办法。但朱熹则不同,他反佛,仅限于宗教,而对外来文化--佛学则大胆地吸取。由此可见,韩愈的反佛是简单地“排佛”,而朱熹的反佛则是有分析地“融佛”。这也就是韩愈之所以失败,朱熹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历史留给后世以深刻的启示:其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至为重要,只有大胆吸取,“综合”人之所长,才能“创新”中国固有文化。其二,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必须“中国化”才能植根于中国。但是中国化了的外来文化,仍属外来文化,只有经过逐渐的“融合”,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份,成为真正的中国文化。
从隋唐至明清是中外文化第一次交流时期,亦即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综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不仅丰富了中国固有文化,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三,明末清初至今后时期:从明末开始,“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传入中国,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至清朝后期,帝国主义以武力入侵中国,中西文化之冲突更趋激化,引发出文化争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争论达到高潮,不少人提出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关于引进“赛先生”,从清朝后期起直至五四时期的文化争论都未有阻力,争论的关键在于该不该引进西方“德先生”。由于在五四时期,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普及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当时中国的文化争论的焦点转为:是以西方为师,或是“以俄为师”,亦即“中国应往何处去”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应往何处去”已成定局,而文化的争论余波未熄,迄今尚未终止。
从明末清初至今后时期,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流,亦即中西文化的“综合”时期。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综合”,现存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是中外文化的“综合体”。足见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不断“综合”,不断“创新”的过程,“综合创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欧洲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大体相同,亦有一个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今日的欧洲文化继承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古代,古希腊罗马吸取了古埃及文化,这是第一次“综合”;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和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建立,将古中国和古印度文化传入欧洲,这是又一次的“综合”;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近代欧洲文化,虽然它标榜着回到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而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当时海运大开,为欧洲文化博采人类文化之众长提供了条件。
由上足以证明,“综合创新”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又符合欧洲文化的发展,它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亦即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其中“新”字的首层涵义。
(二)超越于近百年以来中国的旧文化观“体用”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于新的时代,必须更新。而传统文化的更新,首先要求文化观的更新。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观以“体用说”为主体:一为“中体西用”说,即“国粹派”;一为“西体中用”说,即“西化派”。历史已证明,以上两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既要保持中国封建专制这个“体”,就不可能发展西方科学技术之“用”;同样,既以完全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体”,则中国文化成为“奴才”文化,中国文化之“用”无从依附。这已是历史的结论。
这两种文化观在历史上虽长年争论不休,而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都有错误,并且是同一个错误:即将某一种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另一种文化则视为绝对的坏,因此,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扬彼抑此。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其实,中西文化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都受到历史时代的束缚。不存在谁优谁劣、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中西文化都讲“对立”与“统一”,西方文化强调一个事物的“统一”体中两个“对立”面的“对立”“斗争”,强调量变的积累必然引起质变的飞跃,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谐”,强调量变的积累以适“度”(即最佳状态)为限,以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发展。从中西的“对立”与“统一”观中,可见两者都反映出一定的客观真理,两者都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偏。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综合中西,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中西互补,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
形而上学的“体用说”已被历史淘汰,唯有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新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才能适应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的要求。这亦即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中“新”字的第二层涵义。
(三)顺乎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前文已作详细论述,自世界二次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迁,加之通讯和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讯息量增多,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当前人类已进入了新的时代--“文化综合创新”的时代。今天,人类文化的“综合”已突破了历史上“地域”的局限,不仅是国与国之间,而是世界范围的“综合”,同时也突破了历史上“领域”的局限,不仅是文化的某个领域之内,而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综合”。这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为适应这一人类文化新潮流而提出的。这是其一。同时,在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已提到议事日程,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正是为这一宏伟目标而服务的。此为其二。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亦即“文化综合创新论”中,其“新”字的第三层涵义。
“文化综合创新论”自1987年提出之后,在中国已获得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在海外华人中亦获得广泛的共鸣。1989年张岱年先生又发表了《超越传统,理解传统》一文(收入《张岱年文集》第6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阐明了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研究、理解传统文化,目的是要超越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而要超越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又必须研究、理解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传统文化。这一任务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将出现在神州大地之上。
注释:
[1]《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收入《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以下简称1995年版)第489页。
[2]《张岱年文集》第1卷,1995年版,第489页。
[3]《张岱年文集》第1卷,1995年版,第491页。
[4]《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以下简称1989年版),第281页。
[5]《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以下简称1989年版),第256页。
[6]《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以下简称1989年版),第263页。
[7]《张岱年文集》第1卷,1989年版,第256、258页。
[8]1986年2月张岱年先生写过一篇《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收入《张岱年文集》第6卷,第1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文中对传统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作了有力的批判。文末提出:“是否可以讲‘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呢?”按张岱年先生的解释“今中为体”即指以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
[9]《张岱年文集》第6卷,第490-491页。
标签:张岱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新文化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