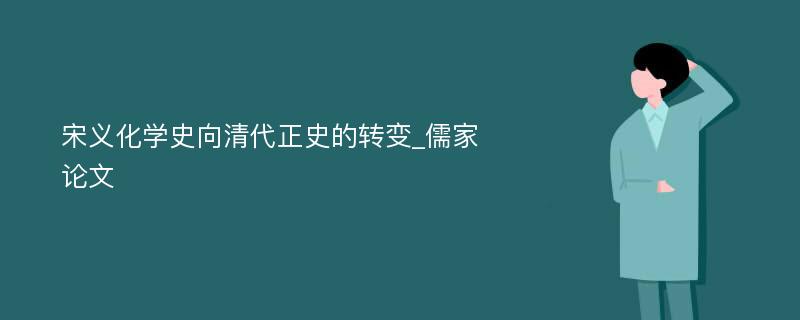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理论文,史学论文,实证论文,宋代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2-0005-10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先后产生过各种史学思潮,而每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 其治史宗旨对中国史学重新加以诠释,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探讨各种史学思潮的内 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将会有助于揭示历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 统史学呈现出由繁荣与深化走向总结与嬗变的特征[1](p432,670),产生出两大主要史 学思潮,即宋元明时期的义理化史学思潮和清代的实证性史学思潮。这两种史学思潮在 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并且直接影响到 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本文即以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内容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揭 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 展中某些内在规律。这不仅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 代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
两宋社会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因而宣扬“大一统”和“尊王攘夷”观念的《春秋》学 在宋代史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春秋》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它不但 保存了先秦史官纪事的书法,而且融入了孔子的政治观念和史学思想,强调为史之义。 孟子说过这样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 ,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离娄下》)这里所说的“义”,是对于历史的评价褒 贬之义,亦即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然而后代学者却夸大《春秋》寓含的政治思想,片 面强调《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这一观念发展到宋代,又因理学的兴盛而极端强 化,特别是元明以来,理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影响。
宋代史学中有一派史家宣称史学的性质在于明道,欲借《春秋》儒家义理思想褒贬世 道风俗,借以抬高经学的地位。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后圣明理以为经,纪 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3](《序》)。朱熹说得 更明确:“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 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 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 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 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便汲汲焉以看 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4](《读书法下》) 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 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原则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 ;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 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诫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 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 志!元明两代史家又断章取义,借口理学家说过“读史令人心粗,玩物丧志”的话,束 书不观,空谈义理,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褒贬的治史学风。“自明中 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 无根之徒耳!”[5](《甬上证人书院记》)史家注重义理思想而轻视历史事实,导致了元 明两代史学研究极端空疏的弊病:“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史,拘 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加子云以新莽,削郑众于寺人,一义偶抒 ,自为予圣。究之而大者,如汉景历年,不知日食;北齐建国,终昧方隅。其源出于宋 之赵师渊,至其后如明之贺祥、张大龄,或并以为圣人不足法矣。一则词人之读史,求 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 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逞其抑扬之致,忘其质直之方。此则读《史记》数首而 廿史可删,得马迁一隅而余子无论。其源出于宋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后如明张 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艺之法行之矣。”[6](《杭堇浦先生三国志补注序》)在这种 治史学风影响下,宋元明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褒 贬性质,过分强调史学劝惩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中国 传统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趋势,史学面临沦为经学附庸的境况。
义理化史学思潮对儒家义理思想讲求缜密,史家撰史强立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修 史义例。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以薨、诛、 杀、死相互区别,以示褒善贬恶之旨。然而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书“死”者固然 属于奸慝,罪有应得;而书“薨”者却不都是功臣。予夺之际,出现混乱。朱熹撰《资 治通鉴纲目》,更是处处效法《春秋》。他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岁周于上而 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7]( 《序》)《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 例如记载武则天以周代唐的历史,不用武则天的年号纪年,而是模仿《春秋》“公在乾 侯”的书法,纪唐中宗之年,而书帝在某地。然而设例愈繁,愈无定论。欧阳修和朱熹 的做法对当时和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宋元明史家为了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 务,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南宋尹起莘撰《纲目发明》,元代陈桱撰《通鉴续编》,明 代商辂撰《通鉴纲目续编》等,都极为重视书法义例,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 宋元明时期,还出现多家用义理史观修撰魏、蜀、吴三国和辽、宋、金三代历史的书籍 ,如萧常《续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郝经《续后汉书》、张枢《续后汉书》 、赵居信《蜀汉本末》等,均以蜀汉为正统,魏、吴为闰位;而王洙《宋史质》、王惟 俭《宋史记》、柯维骐《宋史新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旂《宋元 资治通鉴》等,则以赵宋为正统,辽、金为僭伪。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 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把史学纳入政治的范畴,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 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没有价值,充分表明义理化史学不仅对史学发展无益 ,而且造成混乱和危害。
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灾难,导致了史学榛莽荒芜的 局面。清代史家钱大昕举例说:“即一部《晋书》论之,纪传之文无有与志相应者,以 矛刺盾,当不待鸣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来曾无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学之不讲也。 ”[8](《十驾斋养新余录》)宋元明义理化史学产生的不良影响,说明这种史学思潮已 经走到穷途末路,失去了学术活力。穷则必变,任何事物发展都遵循这种规律。义理化 史学思潮的积弊,为自身的衰落建造了坟墓,同时也为新史学思潮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末清初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开始扭转义理化史 学思潮。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 大力提倡考据,出现了历史考证学。历史考证学派史家强调记载历史事实不应受史家主 观因素干扰,更加重视考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清代史家根据这种认识对中国古代的历 史著述重新审视,作了全面考证,着重阐明史学贵在征实,而不在褒贬,形成了以求实 考信为宗旨的实证性史学思潮。王鸣盛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尊重历史的真实,史家记 载历史应当直书其事,不能把史学作为褒贬世道的工具和目的。他说:“大抵史家所记 ,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 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 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 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 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 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 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9](《序》)在 今天看来,王鸣盛把历史评价中的“议论褒贬”一概斥为“虚文”,未免矫枉过正。值 得肯定的是,在他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 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真实地记载历史事 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认为,据事直书是中国史 学的正宗。他指出:“《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 无所隐而已。……纪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8]( 《潜研堂文集》)后人离事而空谈褒贬,显然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宗旨。钱大昕主张:“ 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 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十驾斋养新录》)阐明了史学的本质在于求得历史的 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赵翼认为:“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 审核传闻。”[10](《梁陈二书》)他在考史实践中,能够坚持求真求实态度,尊重历史 的本来面目。针对宋元明史学中出现的以稗官野史妄訾正史的不良学风,赵翼强调树立 严谨的考证学风。他申明自己的治史宗旨是:“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 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 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11](《小引》)他反对以野史驳 正史,在考史的实践中自觉坚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对于树立实证治史学风起了重要 作用。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提倡求实考信、据事直书,目的是要以考证和记载历代典制与事 迹之实为己任,为后人提供真实可靠的信史。这表明乾嘉时期的史家对史学性质的认识 更加明确,承认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褒贬构建。这种史学观念的 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这就为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变 提供了条件。
二
无论任何时代的史学,事实和褒贬都是历史编纂学的两项最根本要素,记载事实和评 价历史是任何史学著作都不可或缺的内容。记载事实是为求得历史的真相,正确认识历 史;而评价历史则是对史实作出价值判断,给世人提供经验教训。前者反映出史学的求 真特征,而后者则反映出史学的致用特征,表现为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对立和统一。在 宋代以前,历代史家虽然在修史实践中对二者内容各有侧重,但在价值观念上却没有轩 轾之分。据事直书和议论褒贬两种修史义例,历来并行而不悖。实际上,事实和褒贬作 为历史记载的要素,根本不可能泾渭分明地截然分离开来。即使再标榜客观公正记载历 史的史家,修史时也不可能丝毫不融进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念,作到纯粹客观。而 史家对历史所作的议论褒贬,也是基于对客观历史的评价,倘若完全脱离历史事实而主 观褒贬,那就不成其为历史评价。
随着宋元明义理化史学思潮的形成,驰骋议论之风大盛,不少史家逐渐脱离历史事实 而主观褒贬,出现“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12](《考信录 提要》)的不良风气。义理化史学一派史家以儒家义理思想为历史评价标准,不顾客观 历史发展的时代,也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一味作出道德评价。宋代史 家撰史,大多标榜要效法《春秋》“笔削”之义,以褒贬历史为己任。“宋人略通文义 ,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 此风益盛。”[9](《唐史论断》)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周世宗攻打北 汉时,“其击旻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 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詈之为“无耻之尤”!于是《冯道传》中便有周 世宗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山陵使的记载。然而历史事实终究不能掩盖,冯 道作为后周首相,按照朝廷礼仪制度应当出任周太祖山陵使,不关周世宗好恶之事。又 考《新五代史·世宗本纪》,冯道任山陵使在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而世宗亲征北 汉乃在三月乙酉,所以不存在因冯道进谏被任命为山陵使的问题。欧阳修从义理思想出 发,对历史人物仅作道德评判,而不顾及客观历史存在,导致历史记载舛误。苏轼评价 战国时期燕将乐毅伐齐之事,不同意前人所谓燕惠王临阵易将,以致功败垂成的结论。 他指出名将乐毅欲以仁义感化齐人,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数年不攻,“以百万之师,攻 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即使燕昭王不死,庸将骑 劫不代替乐毅统兵,“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1 3](《乐毅论》),同样难逃失败的结局。至明代方孝孺,又不同意苏轼关于乐毅欲以王 道服齐致败的结论,认为乐毅乃因贪利失去民心而失败。他说:“彼乐毅之师,岂出于 救民行义乎哉?特报仇图利之举耳。下齐之国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齐父子兄弟之心 ,而迁其重器宝货于燕。齐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余城,畏其兵威力强而 服之耳,非心愿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与即墨。毅之心以为在吾腹中, 可一指顾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气已怠,士卒之锐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坚,齐民之心 方奋。用坚奋之人御怠肆已挫之仇,毅虽百万之师,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 俟其自服也,亦非爱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诚使毅有爱民之心,据千里之地而行仁政, 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尔之二城哉!汤武以一国征诸国,则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国 征二小邑,且犹叛之,谓毅为行王道可乎?汤武以义,而毅以利,成败之效所以异也。 ”[14](《乐毅》)乍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然而他们的共同错误在于立论没有事实依 据。考《史记·乐毅传》可知,历史的真相是乐毅连续苦战数年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 ,尚未来得及攻下莒和即墨两城,就被燕惠王临阵易将,齐将田单乘机反攻,燕国大败 。苏轼把乐毅连续数年征战攻下七十余城说成破七十余城后相持数年而不决,方孝孺则 把乐毅连续数年征战攻下七十余城说成破七十余城后将骄师惰而不克,显然违背历史事 实,因而所做出的评论也就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但没有学术价值,反而湮没了历史真相 。台湾史家杜维运认为这类议论褒贬的性质根本不属于历史评价:“史论是否属于历史 解释,是一极富争论性之问题。正史上之论赞,往往能高瞻远瞩,以剖析历史;苏轼、 吕祖谦等则又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此实为纵横捭阖之论,全无历史意味。 凡苏氏之史论,皆此之类,虽文字铿锵有声,史实屡被称引,而文字流于虚浮,史实全 无地位,以此类史论,视之为历史解释,自极不可。”[15](p16—18)这话很有道理。 因为如果离开历史事实而主观臆度发表评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纵横驰骋, 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当然不属于历史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钱曾《读书敏求记 》说:“宋以来论史家汗牛充栋,率多庞杂可议,以其不讨论之过也。”[16](《十七 史纂古今通要提要》)这话击中了义理化史学驰骋议论而不检讨论据的致命要害。宋元 明时期的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治史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或故为高论,势所难行; 或主观臆度,褒贬失当。宋代胡寅撰《读史管见》,“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 、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 而不近人情,不揆时势,卒至于滞碍难行。”[16](《读史管见提要》)元代杨维桢撰《 史义拾遗》,“杂举史事,自为论断,上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补辞者,如《子思 荐苟变书》、《齐威王宝言》是也;有作拟辞者,如《孙膑祭庞涓文》、《梁惠王送卫 鞅还秦文》是也;有作设辞者,如《毛遂上平原君书》、《唐太宗责长孙无忌》是也。 大都借题游戏,无关事实。”[16](《史义拾遗提要》)明代胡粹中撰《元史续编》,“ 其中书法,如文宗之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于明宗元年转削而不记,仍书文宗 所改之天历二年,进退未免无据。又英宗南坡之变,书及其丞相云云。盖欲仿《春秋》 之文,而忘其当为内辞,亦刘知几所谓貌同心异者。其他议论,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 ,未免优孟衣冠,过于刻画。”[16](《元史续编提要》)这种论史风气对史学的危害相 当严重,不但给历史评价带来极大混乱,而且导致了史学的空疏无用。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针对宋元明以来史学中出现的抛开历史事实而腾虚褒贬的驰骋议 论流弊,力图扭转史论空疏无用的学风。他们把考察历史的真相作为史家的根本任务, 目的在于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善恶垂鉴将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历史考证学派 的史家大力提倡考据,反对史家离开具体历史事实对历史作主观褒贬,不主张轻易评价 历史,形成了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治史学风。
第一,在清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是主张通过据事直书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 ,认为义理化史学那种没有事实基础的议论褒贬无法考察清楚历史事实的真相。王鸣盛 认为史学的重要性就在于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凡所贵乎史者,但欲使善恶事迹炳著于 天下后世而已,他奚恤焉!”[9](《昭哀二纪独详》)只要把历史上的善恶事迹记载和考 证清楚,后人自然可以明辨是非,从历史中借鉴前人的成败得失。他极不赞成对历史任 意褒贬的做法,主张“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与夺;读史者宜详考其实,不 必凭意见发议论”[9](《唐史论断》)。王鸣盛抨击治史空疏学风给学术和社会造成的 危害,阐明了史学求真的历史认识价值。钱大昕批评那些以褒贬历史为己任的史家,而 强调:“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 奚庸别为褒贬之词!”[8](《潜研堂文集》)指出史家只要搞清历史事实,善恶直书,后 世自会有公论,无须另外画蛇添足,主观褒贬。赵翼不赞成把历史褒贬作为治史的重点 ,大力扭转驰骋议论的论史学风。他说:“记事详赡,使后世有所考,究属史裁之正, 固不必以文笔驰骋见长也。”[11](《元史列传详记月日》)因为议论褒贬如果不切合实 际,或者是没有事实作基础,一切议论褒贬都没有意义,不仅无益于史学,而且有害于 社会。史家只有客观全面地记载下历史的真实情况,才能给后人认识历史提供借鉴,史 学才能表现出自身的价值。这种慎重对待历史评价的态度,无疑是从前人的教训中总结 出来的,非常值得重视。
第二,清代史家不赞成人为地确立各类标准褒贬历史。王鸣盛指出,史家纪事书法前 后应当一致,凡例越多越容易造成名不副实。他说:“大凡一时官制,宜据实详书之, 使后世可考。《宋》、《齐》、《梁》、《陈》皆依《晋书》书法,不料李延寿出一人 私见,创为两种书法,失实而不明妥,皆非是。”[9](《都督刺史》)对李延寿《南史 》纪事书法歧互而褒贬失当提出了批评。钱大昕也指出:“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 名目既多,则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8](《潜研堂文集》)史家确立的主观分类 标准越多,在划定事实归属上越容易出现紊乱,进退无据,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实。这种 条分类别记载和褒贬历史的做法,必然给后世考史者带来无穷的麻烦,“即以其例求之 ,则与夺之际殊未得其平,而适以启后人之争端”[8](《潜研堂文集》)。这样就会给 后人留下臆度纷争的余地,把史学变为揣测书法义例的渊薮:“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 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8](《廿二史考异》)史学到了这种 地步,人们也就不去关心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历史评价必然会失去学术价值。邵晋涵 指出擅自立目褒贬史实的危害,认为范晔《后汉书》创立《独行》、《党锢》、《逸民 》三传,实为后世史家多分门类的滥觞:“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 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 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 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 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17](《南江文抄》)指 出设类例褒贬,不如直书其事褒贬更有价值。他批评《新唐书》说:“使[欧阳]修、[ 宋]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抉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 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 始哉!”[17](《南江文抄》)史家把主观立类标准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并据此对历史 作出议论褒贬,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史家在注重历史记载 的真实,反对空言褒贬的立场上具有共识,表现出尊重历史事实与客观公允评价的有机 结合,其实质就是强调道德评价与事实评价相互统一,以便最大限度地认识真实的历史 。
第三,清代史家对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谈义理的历史评价学风给予尖锐批评,提出义 理观念必须结合客观时势的历史评价原则。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强调客观时势在历史评 价中的重要性,反对空洞抽象的史论。他们指出义理化史学的治史宗旨背离了儒家学说 经世的精神:“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 ,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 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16](《凡例》)阐明了 历史评价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结合客观时势,才能够做到既不苛求前人,又符合历史实 际。四库馆臣特别指出历史评价对于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 贬。”[16](《御制评鉴阐要提要》)但是如果没有事实作依据,褒贬就无的放矢。因为 尽管“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16](《凡例》)事 实才是褒贬的对象,倘若事实不明,则无从褒贬:“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 》,不知所以褒贬。”[16](《史部总叙》)这是从历史认识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事实与 褒贬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出据事直书与公允褒贬相互统一的原则。崔述主张通过考察 客观时势评价历史,不应存在先入为主之见。他认为:“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 后论其世,然后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 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12](《丰镐考信录》)突出了历史认识中义理 思想结合客观时势评价原则的重要性,理论认识非常明确。钱大昕批评“后儒好为大言 ,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8](《十驾斋养新录》)的迂腐之论,强调 考察客观时势的必要性。他在宋金议和问题上通过考证南宋张浚北伐,兵败符离;韩侂胄北伐,函首金人;联蒙灭金之役,反为垂亡之金朝所败的历史事实,得出不同于传 统看法的见解:“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 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盖由道学诸儒耻 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 。”[8](《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对结合客观时势评价历史认识更加深刻,指出宋儒以 义理思想为标准评价宋金关系,是因为他们置身政治局势以外,不考虑双方国力对比悬 殊,极力反对宋与金议和,空发议论。胡铨上书倡灭金复仇之说:“天下之谈义理者, 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 。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 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 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11](《和议》)他还比较了南宋与 金、明与后金的关系,指出宋、明朝廷未尝不愿议和,皆因书生纸上谈兵,议论纷纭, 导致不敢主和,以致亡国。赵翼最后总结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 家国者。”[11](《明末书生误国》)指出了仅仅注重义理原则而不考察客观历史的危害 。赵翼强调历史评价必须结合客观时势,例如宋代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去,中原沦为金 朝版图,从儒家义理观念来看,当然应该出兵收复失地,迎还二帝。然而刚刚立足江南 的赵构政权根本无力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偏安江南,这是客观时势造成的。所以“义理 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 真义理也”[11](《和议》)。事实证明,南宋国势积弱不振,无力收复失地。然而宋儒 不能正视现实,一味从义理观念出发,反对议和。元代史家修《宋史》仅仅从崇尚理学 的角度立论,推波助澜,过分贬抑使金通和之人,极力丑诋王伦,甚至把赵良嗣等人列 入《奸臣传》,造成历史评价不实。清代史家赵翼则认为:“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 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 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 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11](《王 伦》)同样,北宋“銮舆北狩,神州陆沉,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谋国不臧,于[赵] 良嗣无与也。乃事后追论祸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 与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论也”[11](《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对王伦、赵良嗣二 人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说明历史评价中道德评价原则和事 实评价原则往往会发生矛盾,怎样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学应当研究的重要问 题。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宋代理学家强调义理原则,纷纷指责南宋朝廷议和苟安; 而乾嘉史家则强调客观时势,不片面夸大道德评价的作用。这固然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 决定的,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后者无疑比前者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客观。清代史家比宋元 明时期史家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反对完全以义理思想为历史评价标准,批评离开具体事 物而空谈义理标准,明确提出要结合客观时势来评价历史,理性意识更加突出。他们以 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时势为标准,以此衡量义理评价是否恰当,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这 样可以准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揭明历史发展的真相。尽管他们的历史观念中还残 存着浓厚的义理思想,但他们与宋元明史家相比,更突出了以客观时势作为历史评价的 标准。从他们的历史认识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理论 总结与嬗变的趋势。
三
宋元明时期的一些史家,根据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儒家的义理思想视为永恒的真 理,以为可以适应于任何历史时代。他们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研究历史,只是笼统而抽象 地评论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而对各个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和具体问题则很少关注。宋 代程颢和程颐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有善 有恶,善则理当善,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章显之;恶则理当恶,彼自绝于理,故五刑 五用曷尝容心喜怒于其间哉!舜举十六相,尧岂不知?只以它善未著,故不自举;舜诛四 凶,尧岂不察?只为它恶未著,那诛得它?举与诛,曷尝有毫发厕于其间哉!只有一个义 理。”[18](《二先生语二上》)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由永恒的天理决定的,而贯穿其中 的就是儒家义理思想。朱熹继承程颢和程颐的思想,进一步阐明历史演变存在天理。他 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 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4](《大学五》)他认 为经学为史学之本:“《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 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4](《读书法下》)朱熹主张治史应当揭示义 理思想,否则没有价值。他提出的治史方法是:“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 之变,以验得失之机,而必反之身以见其实者,学之正也。”[19](《己酉拟上封事》) 这种治史方法注重整体与感悟,而不注重分析和实证,不可避免地流于浮泛空疏,得出 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切合历史的实际。正如吴怀祺所说:“朱熹说读史穷理,不过是以历 史验证先验的义理。本着这样的认识,历史的研究很难得出新鲜的结论,史学不过说明 天理、纲常、名分等级礼制的永恒性。”[20](p169)然而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各种 史学成果无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要正确考察前人的史学成就,必须认清它们赖以 产生的历史条件。这就要求史家运用分析的和实证的史学方法,而不能笼统地抽象地研 究和评价历史。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针对宋元明数百年来愈演愈烈的空疏治史方法,展开了全面的清 算。史家对历史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义理观 念。他们反对不察时代而抽象地研究历史的做法,强调考证清楚一人、一书、一事而求 得事实之真,在此基础之上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们认为,只有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才能认清历史演变之道,反对脱离历史实际而空谈义理原则以求道的方法,从理性的 角度对历史演变规律作了新的阐述。
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认为“道”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真理。他指出:“《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矣。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 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 ,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21](《原道上》)只有在天地产生以后,自然界阴阳交替 才形成“道”,而不存在宋儒所谓先天地而生的“道”。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 背后的原因和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本身。所谓明道,也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不 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事物发展变化背后深层次的内涵,揭示其发展 动因及法则。章学诚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说明“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 生而产生的,没有先天存在的“道”。他说:“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 ,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 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21](《原道上》)人类产生以前,根本不存在所谓人 伦之道,而夫妇、男女、长幼、尊卑以及仁义忠孝之道,只有随着人类的社会活动才能 产生。人类社会在发展,“道”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后世出现的封建、井田、郡县以及 各种礼乐制度,都是各个时代“道”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客观事物,也就谈 不上关于这些事物的“道”。他认为既然“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 当然,那就只能在研究具体的事物中才能认识“道”。章学诚说:“天下岂有离器言道 ,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21](《原道中》)章学诚反对宋明理学舍“器”求“道”的空谈方法,提出“即器以 明道”的主张。他认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 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 。”[21](《浙东学术》)宋明理学家由于把义理思想过分理想化,以致学者只关心达到 目的,而忽视了达到目的的途径,逐渐舍弃读书明道的正确方法,抽象谈论道德性命, 结果把历史事实架空,使义理思想变成虚渺之物。章学诚对此批评说:“宋儒之学,自 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 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 ,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2](《家书五》)宋代以来的道学家离事而言理,不但不重 视探讨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关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轻视考证具体的历史事实 ,脱离历史的发展而空谈人类社会的天理,对历史的认识极其肤浅,极大地阻碍了宋元 明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章学诚认为研治经史,如果轻视典章制度的考订和研究,必然 导致离事而言理,内容空洞无物。他说:“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 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22](《家书五》)只有把义理思想建筑在客观历史事实 之上,才能够真正揭示历史演变之道。即使孔子删定的《六经》,也只不过是三代先王 的政典,仍然是“器”而不是“道”。他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 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21](《原道中》)后人之所以尊崇《六 经》,只是由于“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21](《原道下》)。因为《六经》是存道 载体,舍此无以求道。从章学诚对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承认客观 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是具有物质性的“器”;而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动力 和法则,才是寓于该事物之中的“道”,是学者应该努力探究的真理。章学诚“即器以 明道”的认识和主张,有助于启发世人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因,揭示社会运动的法则,阐 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历史考证学派史家批评宋明理学徒执义理原则以求明道的方法,强调以文字训诂和重 人事而明道,揭橥了由训诂文字而阐发义理思想,由阐发义理思想而揭示事物发展之道 的方法。钱大昕说:“夫性命之学有出于义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谓 之命,自人言之谓之性,而性即理也。穷理斯可以观物,区物理与义理而二之,而谓物 理之学转高出于义理之上,有是理乎?……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曰 :道不远人。凡离乎人而言物,离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谓道也。”[8](《潜研堂文 集》)他的意思是说:道合于物,而义理之学见;道合于人,而性命之说出。二者相即 ,而不可相离,舍事物而求义理之说,舍人事而求性命之说,就流于空谈性命与义理之 弊,“道”也就变得空洞无物。他主张以文字训诂明道:“夫《六经》皆以明道,未有 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8](《潜研堂文集》)因为不通训诂,就不明《六经》之旨, 不懂儒学之道。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8](《潜 研堂文集》)。他论音韵训诂与义理之道的关系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 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8](《潜研堂文集 》)强调把义理思想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揭明历史发展之道,找到社会历史进程的法 则。王鸣盛主张研治经史的目的首先在于搞清事实真相,然后才能找到寓于事物之中的 “道”。他说:“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 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 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 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9](《序》)治史需要作具体细致的考证,才能得到正确 的历史认识。他通过对《春秋》的考察,得出新认识:“《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 以揣测。学者但当缺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况乃欲拟其笔削,不已僭乎!究 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9 ](《李昭德来俊臣书法》)在今天看来,王呜盛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史家对历 史的研究如果不用征实考信的方法,仅仅注重书法褒贬而不注重考证历史事实,不但无 法探究历史演变的法则,反而会把历史事实搞乱,使后人无法看到历史的真相。王鸣盛 特别强调史学考据征实的价值,主要意图在于说明史家治史应当根据确实,着重记载于 后世有益的史实。他针对《新唐书·兵志》关于“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 ,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的记载 ,评论说:“愚谓征防守卫,事之大者,后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谓其不可悉 记而略去之,何也?既略去制度不详,而记废置治乱何益!”[9](《总论新书兵志》)历 史上的治乱兴衰,正是通过特定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事迹表现出来的,离开这些内容 而泛论治乱兴衰,后人将不知何谓,无法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不能发挥垂鉴后世的 作用。戴震认识到:“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 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 而行事乖。”[23](《戴东原集》)批评了宋元明义理化史学对历史抽象考察的不实学风 ,指出这样做只能导致掩盖历史真相,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特别指出了这种治学 方法的危害:“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则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 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 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 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23] (《戴东原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指出训诂可以发明古人的义理思想,而通过领会古人 的义理思想可以达到对事物真理的认识。这就把训诂明道的意义揭示得更加清楚,其研 究历史的方法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纪昀在治学过程中认识到舍“器”言“道”的危害 ,认为只有从人事之中寻求义理思想,才能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他说:“《易》之 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其书至繁至赜,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于事。既切于 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24](《黎君易注序》)说明义理思想只能从社会的人事之中 表现出来,否则就看不清历史演变之道。他还指出:“周公手定周礼,圣人非不讲事功 ;孔子问礼问官,圣人非不讲考证。不通天下之事势而坐谈性命,不究前代之成败而臆 断是非,恐于道亦未有合。”[24](《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强调了“道”与“器” 相互结合对于考察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性。纪昀关于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中的人 事以明道的方法,比主张训诂文字而明道的认识更能够揭明历史演变之道,达到对历史 进程的正确认识,具有比较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四
中国传统史学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发展到清代实证性史学,对宋元明史学空疏的治史学 风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树立起客观研究历史的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第一,端正了对史学固有性质的认识,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从 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发展到宋元明的义理之学,标志着学术研究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 到理论层次的研究,是学术发展的进步。但是,义理之学必须以实证之学为基础,否则 会流于空泛不实。宋元明时期的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义理思想为治史原则, 把经史关系解释为主从关系,宣称治史的目的在于阐扬儒家义理之道,史学的作用只不 过是用事实为经学作注脚,史学的性质被扭曲。清代史家提倡“六经皆史”,主张经史 地位平等。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 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易教上》)他认为《六经》记录的是古人政教典章,是 当时制法行政的历史记录,并没有垂后世以作则的微言大义。《六经》不是载道之书, 更不是“道”本身,而只不过是历史记载。由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经》又是先王 的政教典章,属于史书,所以由史可以明道。钱大昕对经史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因而对 经史关系也有深刻认识。他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 》、《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 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 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 ,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11](《序》)他考察了历史上的经史关系,认为经史之学不 分轩轾,肯定了史学的重要作用。钱大昕抨击前人治经而不重史,导致学术无益于实用 ,这种认识在乾嘉经学独尊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崔述以理性目光审视上古历史, 更明确地认识到:“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后世学者不 知圣人之道体用同源,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记载,博 采旁搜,而不折中于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于章句之末务,殚精于心性之空谈, 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12](《考信录提要》)他认识到后人治学经史分途的危害, 治经则空谈性理而不重征实,治史则鹜趋博古而不知体要,导致学术空疏而不能实用, 贻患后世。洪亮吉也强调重视史学:“古今之大文曰经曰史,经道乎理之常,史则极乎 事之变,史学固与经学并重也。”[25](《序》)认为学者只有经史并重,相互参会,治 学才能明体用而达变通,促进学术健康发展。清代史家把史学摆正到与经学同等重要的 位置,史学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可以与经学并驾齐驱的程度。
第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保证了史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中国传统史学 如果按照义理化史学道路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政治化 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清代史家在批评前人治史虚妄不实的同时,以求真求 实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开创出“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钱大昕强调学者 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脱离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他反对治史“驰骋笔墨, 夸耀凡庸”和“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 时势”的做法,强调“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8](《廿二史 考异》)。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26](《与巡抚毕侍郎 书》)公开阐明“实事求是”的史学宗旨,明确主张治史不应存在门户之见,墨守陈说 。王呜盛对轻易褒贬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做法极其反感,批评这类史家论史“动辄妄 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 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9](《马融从昭受汉书》)。谆谆告诫后学引以为 戒,避免误入歧途。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真相,意欲剥去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古人真实面 目。他说:“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 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纠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 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12](《考信录 提要》)只有对上古历史不讳不增,才可以真正达到护惜古人的目的;而要对古人之史 求实考信,就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他指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 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 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12 ](《考信录提要》)这种既不盲目信奉前人成说,又不故意贬抑晚出见解的治史态度, 正是乾嘉史家治史求实考信的理性精神。这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清代 史家的头脑里,影响着他们的治史活动。在这种理性精神的驱使下,清代史家本着求实 考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历史,一扫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不实学风,强调史学自身 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从而奠定了历史 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理论基础。
收稿日期:2002-09-01
标签:儒家论文; 读书论文; 潜研堂文集论文; 十驾斋养新录论文; 文化论文; 春秋论文; 宋朝论文; 宋元明论文; 续后汉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