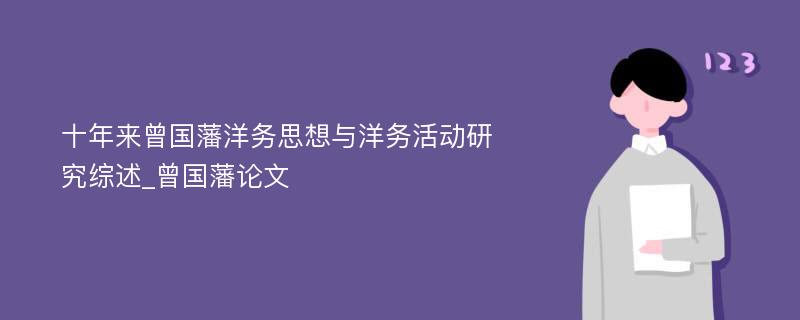
近十年来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曾国藩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他在初期洋务运动中对设厂制造、培养人才、创建水师、对外交涉等许多方面提出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纲领,为后来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基本方针、路线和政策。然而,与对整个洋务运动研究的争论有关,学术界有关曾国藩洋务理论及其实践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就显得异常活跃。回顾一下十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对于推进曾国藩研究领域的深入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和形成原因的争议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天朝至高、至上,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观念在他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他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初倡导洋务自强新政,敢于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呢?因此,探讨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原因,是学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王少普在《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一文中指出,曾国藩从封建理学家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思想转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由于他比理学中主敬派实际一些,从而具备了“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内在因素”。第二个阶段是在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尖锐激烈,促使曾国藩兼采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开始注意西方情况,重视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这就“为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个阶段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在伦理政治观念上由原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同时,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喻盘庚在《试析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观因素》一文中,提出了与“王文”有所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本人的主观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因素主要包括:“治学上的开放宽容态度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而后者是构成曾国藩洋务观产生的直接的主观因素。作者针对“王文”提出的曾国藩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用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论证对外妥协的合法性”的观点,以曾国藩对阿思本舰队的基本态度为例,说明他的民族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这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举办洋务的重要主观因素之一(《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成晓军在《试析曾国藩洋务观的产生和形成》一文中,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比加以分析考察,认为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进而在这种基础上又产生了避害反映,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技艺”和“术数”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作者提出了与“王文”不同的观点,即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举办洋务自强新政,并非对外妥协的结果,相反是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而用以“靖内患,勤远略”的出发点(《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
关于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和性质的争议
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尤其是直接目的何在呢?以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的。近十年来,这种观点有所变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为了“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腐朽封建统治。
李金奎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来是以镇民为目的”,都是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内患”之实。作者认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绝大多数洋务派人物都是持着这样一个目的来兴办洋务的(《求索》1984年第4期)。戴学稷、徐如在《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实践的。”(《福建论坛》1984年第2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观点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既有“靖内患”即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又有“御外侮”即对外抵抗列强侵略两个直接的目的。
殷绍基在《曾国藩与洋务运动》一文中指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既有封闭狭隘的一面,也有开放变通的一面。”他倡导选派文童出国,也只是学“艺”而已;但他又强调经世致用,提倡重视社会,了解社会,这是他的开通之处。曾国藩办理洋务的目的,“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这与他生平注意“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有关(《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综观近十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持此观点的人是相当普遍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其“御外侮”的目的是主要的。徐泰来在《也评洋务运动》一文中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作者在《试论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曾国藩虽也认为购买和制造外国船炮,‘可以剿发逆’,但同时他也强调‘可以勤远略’”,“办洋务的御侮目的是无可否认的。”(《求索》1984年第4期)喻盘庚在《曾国藩办洋务初探》一文中也认为,“如果讲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对人民的反抗没有一点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那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动机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求索》1986年第6期)总之,有关曾国藩举办的洋务军事工业的目的问题的评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讨论仍在继续进行下去。
关于曾国藩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的性质的评价,一直是学术界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曾国藩等人举办洋务运动究竟对中国近代社会起了促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倡发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起了一种阻碍的和反动的作用。其理由是:领导这一运动的人是一些大官僚,他们把持了洋务企业,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服务的。因为他们举办洋务的动因就是借西方科技来制造军火船舰镇压人民起义。近十年来,仍有较多的人持这种观点。姜铎、黄逸峰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中认为,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三大恶果”,即使清政府腐败统治延长了五十年之久;为外国资本主义奠定和维持了一个半殖民地秩序;初步形成了一个早期官僚资本和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从而,这些恶果都是“直接间接使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祁龙威在《坚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文中认为,在近代中国只有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才能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曾国藩等洋务派即使学习西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是“阻碍历史前进”。这是因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一样,都是社会的衰朽势力”(《红旗》1982年第2期)。这种观点不是从经济入手来考察洋务运动,而是用政治的评判来否定其进步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曾国藩倡导的洋务事业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并且在它的后期积极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李时岳、胡滨在《论洋务运动》一文中认为,“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在《也评洋务运动》一文中,肯定了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具有开创和兴办了军民用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逐步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陈旧状况、开了新的社会风气、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和造就、培养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通过洋务实践活动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开始改变一些传统的观点、对中外往来和了解外国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等七大进步性。作者认为,这些“足以说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喻盘庚在《曾国藩办洋务初探》一文中也赞同这种观点:“曾国藩办洋务事业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求索》1986年第6期)这种开拓性具体表现在:一是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二是促进了我国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三是促进了我国军事的近代化。殷绍基在《曾国藩与洋务运动》一文中认为,曾国藩办洋务“限制和延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彭靖在《曾国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曾国藩倡导的洋务事业,其意义在于: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军械所和机器制造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他是最初的倡导者。这是不能抹煞的。”(《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朱东安的《评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一文中指出:曾国藩是当之无愧的洋务派首领,他所倡办的洋务军事工业,如“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史都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求索》1988年第1期)尽管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评价,其轻重主次不尽一致,但人们大都认定曾国藩办洋务军事工业有其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
关于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的态度问题评价的争议
这个问题,是近十年来曾国藩研究中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较多的人仍然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曾国藩“一味崇洋媚外,卖身投靠,是可耻的卖国贼。”(何玉畴、杜经国:《试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甘肃日报》1979年1月11日)王少普在《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一文中指出,尽管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曾国藩与资本主义列强也可以发生一些矛盾和对抗,“但这种矛盾和对抗从来没有上升至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总是很快趋向妥协。”(《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戴学稷、徐如在《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一文中指出,曾国藩的所谓“保民之道”和“立国之本”,说到底就是“一心曲全邻好”,“善全和局”。虽然他也同时举办了“自强”新政,“但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准备用以抵御外敌的。”(《福建论坛》1984年第2期)姜铎在《曾国藩其人》一文中认为,曾国藩的妥协外交路线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结合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成为晚清政府始终奉行的外交主要方针,导致晚清政府最后不得不堕落为‘洋人政府’;而且,旧中国后起的反动统治者,同样也奉行着这条路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朱东安在《论曾国藩与曾国藩研究》一文中也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方针,“归根到底还是‘委曲求和’四字。”他“既要妥协退让,又要讲究战略;既要练兵造船,又绝不抵抗外国的武装侵略。这就是曾国藩对付西方列强的所谓‘隐图自强’之策。”(《人民日报》1989年1月29日)
一部分人则通过对曾国藩对外交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考察,认为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也有矛盾抗争的一面。邓亦兵的《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一文中指出,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是以勾结、妥协为主要方面,同时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并不盲目崇洋媚外,卖身投靠外国。”(《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成晓军在《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一文中,通过对曾国藩对外交涉全过程的分析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华洋会剿”等问题的个案分析,着重探讨了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抗争的一面。作者又明确指出:“对外妥协的一面,在曾国藩整个对外交涉过程中,最终占有着主导的地位。”(《求索》1986年第4期)林建曾、成晓军在《试论曾国藩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态度》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作者认为,曾国藩以承认和维护因不平等条约而稳定下来的中外“和局”,“其中还存在着策略上的考虑。”曾国藩从消极接受到开始利用不平等条约“徐图自强”的变化中,“深刻反映出他对外抵抗和妥协退让双重矛盾的官僚士大夫心理状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以往,人们之所以认定曾国藩投降卖国,对外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理由,就是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处理的基本态度问题。因此,近十年来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观点差距较大。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总体评价曾国藩对外交涉的态度问题。冬青在《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指出,曾国藩奉命到达天津以后,“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所以曾国藩“屈从洋人”,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唾骂(《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该文的观点虽可代表一家之言,但在一些史实上弄错了。董蔡时在《略论曾国藩》一文中认定曾国藩“处处顺着法国侵略者的意志办事,乱杀爱国人民,再次暴露了他媚外卖国的奴才本相。”(《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成晓军在《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一文中指出,“曾国藩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准备向洋人妥协投降,相反他还打算据理力争,可是掌掘清政府外交实权的慈禧等人,不准曾国藩再拖延时日,决意妥协迁就,不伤洋人和气。“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曾国藩最终以捕杀爱国群众,充军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赔款、修造教堂的惨痛代价来换取侵略者的谅解。”(《求索》1986年第4期)许山河在《论曾国藩与天津教案》一文中,为曾国藩因这一事件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作了辨析。作者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虽有妥协退让的地方,但也作了抗争。经过他的反复争取,天津府县才免作刀下之鬼,与当时一些著名教案相比较,“清政府在天津教案中遭受的屈辱,较其它教案为小。”曾国藩“毕竟与崇厚不同,实际上他是作了清朝廷的替罪羊。”(《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有关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的评价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议。争议之所以这样激烈,分歧之所以这般多样,是与这一研究课题复杂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是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开始萌发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产生和开展起来的。曾国藩既然作为地主阶级政治派别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必然要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可是,镇压了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却无意识地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掘墓人,这就是说,他所倡导进行的洋务运动从总体上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并未给满清王朝这一腐败的机体中注入什么旧质的新鲜血液。从而,由曾国藩所引发的洋务运动不能不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就曾国藩的基本对外方针来说,体现了他对西方列强的“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这是当时复杂的主客观诸种因素所决定了的。曾国藩本人无法超脱,也不可能超脱。他在晚年说过一段颇为后人玩味的话语:“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全集》卷二十九,传忠书局版,第60页)曾国藩在这里明确指出,“言势者”看到了西方列强造成的变局;“言理者”宣泄了因民族矛盾而激发的义愤。但前者因“势”而走向消弭苟安;后者因“理”而依连于盲目暗昧。他们各自从一端片面地触及到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内容,却又无法彼此联结,从整体上考虑对外政策。曾国藩比言势者更深地攀结于传统,又比言理者更多地见到过西方事物。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的观点,并着意告诫当道和后人,必须谨守此法,才能解救满清王朝于困境。这“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二语,既包含了明显的“制夷”意识,又包含了明显的“和戎”意识。“制夷”与“和戎”的并存,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西方列强抵抗以伸张其“理”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对“理”的伸张为“势”所压抑之苦。如果我们从固定的政治观念出发,或者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曾国藩思想和言行中反映出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那末任何有关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的研究也就很难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我们只有在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进行整体的分析考察,才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渐符合历史的实际。
标签:曾国藩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华文史论丛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求索论文;
